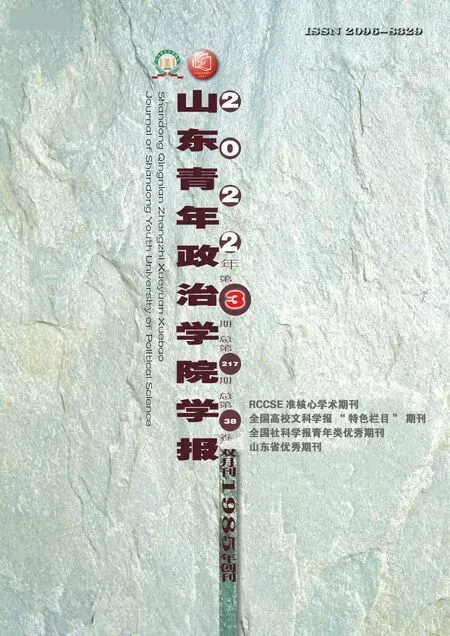新加坡國家認同構建的三級階梯
韓雨筱
(上海師范大學 哲學與法政學院,上海 200233)
國家認同是一種心理活動,指向一國公民整體對本國的歸屬認知和情感依附,它指一國公民對本國統治權威和政治權力的自覺認可、服從和效忠,體示著公民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關系。這種互動關系一方面由公民指向國家,表現為公民對國家承擔義務,奉獻忠誠;另一方面由國家指向公民,表現為國家通過制定法律,頒布政策等保護公民權利。既然國家認同生產公民自覺認可的情感基礎,而這種情感態度又是現代國家統治的合法性來源,那么國家認同便是國家合法性的基礎,是一國之生命。[1]需要注意的是,國家認同的形成并非自發,而是一個自覺的構建,是現代國家構建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相對于國家疆域、結構、制度、法律體系等客觀實在層面,國家認同作為一種態度和信仰,主要涉及主觀精神層面,并以精神基底的角色為實在性的國家制度體系構建提供合法性來源。
目前,新加坡已經較為成功地構建起了國家認同。作為一個移民國家,新加坡從一開始就面對著國家認同基礎薄弱的困境,因此取得獨立地位后,國家認同構建成為了人民行動黨的重要關注。回溯新加坡的國家認同構建歷史,大致可以將其構建邏輯以三級階梯式的遞進層級展開:第一級階梯是基于經濟發展績效而產生的國家認同情感,這種類型的認同情感能夠隨著利益識別而在短時間內迅速產生,但是弊端在于難以長期維系,需要繼續發掘更深層次的認同動力支撐;第二級階梯的工作重點在于促進新加坡國內多民族的交流與融合,淡化阻礙國家認同情感產生的狹隘民族認同①,為接下來塑造一個包容各族群的國族掃清民族心理“障礙”;第三級階梯著力發掘各民族共同傳統文化底蘊,在此基礎上打造新加坡國族,以國族身份標識凝聚各民族共識,將民族認同上升到國家層面,完成國家認同的內生性深層次構建。這三級階梯并非按照時間順序劃分,而是按照國家認同構建動力的深淺層次劃分,前一級階梯往往是后一級階梯的基礎。在第一級階梯當中,國家認同產生于人們的利益識別,這種認同構建動力純粹來自于外部力量;在第二級階梯中,政府將矛頭對準阻礙國家認同產生的民族矛盾問題,此時的認同構建動力已經在各民族交流融合的過程當中開始由純粹的外部推動轉移到內力自生,但是此階段各民族融合的根本動力大多還是源于政府強制力量的推動;在第三級階梯中,政府越來越減少對強制力量的依賴,通過追尋深層文化因素激發各民族自覺融合的意愿,培育全民族共識,國家認同構建逐漸轉向了以內力自生為主的模式。
一、生存政策和危機意識:基于經濟發展績效的利益認同
新加坡國民的同質性低,缺乏構建國家認同的內部動力,想要在短時間內構建起國家認同,需求助于外部動力。新加坡政府已經認識到:“認同是皈依的,因為它們呈現的正是人們想要的”[2],政府通過政策制定實現當下人們最想要的,這就是新加坡國家認同構建的最初外部動力。那么,什么是當下人們最想要的呢?生存。
新加坡國土面積狹小,自然資源匱乏,缺乏發展工業的自然物質基礎;農業用地緊張,農產品基本依賴國外進口;從殖民地時期就形成的單一轉口貿易經濟,加劇了新加坡對外國資本的依賴;獨立前長達百余年的殖民統治和遭受侵略的歷史記憶以及國際緊張局勢,使得生存危機意識成為新加坡民眾的共同心理特征。正是抓住了人們的這一心理特征,新加坡政府開始在關乎每個人的生存處境中尋求最基礎的利益共同點,以此凝聚共識,進而構建國家認同。基于此,新加坡政府強調“生存是第一位的”,并將發展與生存聯系起來,提出沒有發展就沒有生存,發展停滯意味著危機。在此基礎上,人民行動黨制定了一套“生存政策”,把國家和人民的關注重點引到經濟建設和工業化上,形成了一套“生存意識形態”:國家生存是根本目標,沒有國家利益就沒有個人利益,其他目標都處于從屬地位。這就將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息息相關的意識擴散到了全國人民群眾的信念當中。在生存政策和危機意識的召喚下,新加坡人民開始為了謀求國家的生存和發展,當然本質是為了實現個人利益而不分民族地投入到國家建設和公共事務當中,并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出了不同民族之間的團結合作。這種生存意識形態將公民對”自我“利益的識別與對國家利益的識別聯系起來,不同民族的關注焦點被高度統一在國家建設層面,“不管我們屬于什么種族,信仰什么宗教,我們之所以有權取得我們的東西,是由于我們參加了生產,而不是由于我們的種族或宗教”[3]。
生存政策的作用不僅僅在于加強各民族之間以及個人與國家之間的聯系,更重要的是在這一意識形態動員下,新加坡在經濟領域實現了起飛,成為東南亞經濟發展的龍頭國家,躋身于“亞洲四小龍”行列,創造了震驚世界的“新加坡奇跡”。新加坡這一時期的經濟成就在國內具體體現為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長以及失業率的顯著降低,在人民行動黨執政的第一個十年結束之時,新加坡共和國就幾乎實現了完全就業。在新加坡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可以說,每一個新加坡公民都實實在在地分享到了經濟騰飛所帶來的利益蛋糕。這種利益的識別極大地鞏固了人民行動黨的統治合法性,顯示出了新加坡制度的優越性,從而構建起了以經濟績效識別為基礎的國家認同。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是國家認同的物質基礎,也是將不同種族、文化、語言的人們凝聚在一起的繩索,因此,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并不僅僅局限于經濟上的進步,更在于為政權提供合法性,為國家認同提供外部動力。[4]就像馬克思曾指出的:“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只有那些被他們視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或至少是有用的東西,才能將他們緊密團結”。[5]新加坡作為一個從無到有的現代國家,利用經濟手段鞏固政權合法性,是其構建國家認同的成功捷徑。[6]
但是,建立在經濟績效基礎上的合法性認同并不能滿足長時期的認同感生產需要,分析新加坡的政治實踐,其弊端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威權體制合法性的固有困境。在威權主義體制下,經濟增長速率成為生產認同感的重要來源,但是,將認同感和合法性與經濟增長速率聯系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種短暫的繁榮幻覺,一旦經濟增長放緩,或者人民對經濟發展提出更高的,超過政府能力的要求,隨之而來的就一定是合法性和國家認同的崩潰。縱觀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歷史,經過了某一階段的經濟起飛之后,增速放緩是必然趨勢,加之新加坡的外向型經濟性質決定了其經濟發展對于世界經濟和外資的依賴性極強,一旦世界經濟形勢波動,新加坡將極易面臨巨大的危機。其次,在現代化理論中,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是一對矛盾體。[7]一般來說,經濟發展速度越快,人民貧富差距就越大。相對剝奪理論認為,社會動蕩的根源不在于絕對的貧困,而在于相對的被剝奪感,所以,在經濟發展速度越快的社會中,人們希求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就越大,被剝奪感就越強烈,就更易產生對國家和政權的負面情緒,這也是亨廷頓提出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速度成反比的原因之一。②再次,在經濟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推動下,“全面對外開放”政策促進了西方文化的全方位傳入,新加坡社會不斷涌現出新的問題,例如“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等等。原本的“西化發展”逐漸衰變成了“西化墮落”。在這些問題的共同驅動下,人民行動黨在構建國家認同的進程中勢必不能依賴于單一的經濟發展路徑,而是要發掘認同貧瘠的根源,尋求一種具有深層動員力量的構建路徑。
二、民族融合政策:淡化狹隘的民族認同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張力,狹隘的民族認同會阻斷其上升為國家認同的通道,不僅會對國家認同構建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會造成民族沖突和國家分裂。在當今世界民族國家體系下,多民族共同生存于同一國家領土疆域范圍內已成為常態,因此,正確處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化解二者之間的張力,就成為一國繁榮穩定的前提條件。在新加坡國內,民族問題更加嚴重且深刻,這不僅是因為新加坡的民族構成復雜,更是因為其移民社會的性質以及長期實行民族隔離政策,導致新加坡各民族之間敵視猜忌,國家認同貧瘠而民族認同狂熱且狹隘。雖然建國之初,新加坡政府通過發展經濟構建起了初步的國家認同,但是多民族的社會構成以及各民族之間離心離德始終是新加坡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正因如此,加強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促進多元民族融合,以淡化狹隘的民族認同情感,將構建國家認同的動力從外部轉化到內部,將構建動力從基于利益識別深化為基于民族融合,是新加坡政府構建國家認同的基礎前提。
(一)“英語加母語”的語言政策
語言是多民族國家的重要黏合劑。在對新加坡政治現實的分析中不難發現,多元復雜的語言環境是新加坡國內民族矛盾產生的重要原因,其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首先,復雜的語言環境和統一語言的缺失使各民族之間喪失有效交流和溝通的可能,不僅各個民族之間所使用的語言不同,甚至每個民族內部也存在混亂復雜的語言構成,這就更增大了各民族之間交流的難度。其次,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凝聚了使用者對文化的認同,隨之產生的,是以語言為界線的對“我”與“他”的區分,通過這種語言紐帶被聯系起來的居民,由此獲得了一種民族性身份,文化認同是國家認同的重要內容,因此,統一的語言是國家認同構建的必備要素。然而,在國家層面,新加坡缺乏一種共同語言凝聚認同,在民族層面,多元語言又強化了各民族對自我的認同,使民族認同更為狹隘和狂熱。因此,加強民族間交流,構建共同國家認同亟需制定一套統一的語言體系。
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采取的是推行“英語加母語”的雙語政策。首先,人民行動黨有意提高英語在國內生活中的作用,例如在校使用英語授課,并將英語定為官方語言等。這樣做的目的在于構建起一套超越民族局限上升到國家層面的語言體系,使各民族能夠克服語言不通的隔閡從而進行有效的交流和溝通,同時在語言文化紐帶作用下凝聚各民族共識,塑造國家認同。其次,人民行動黨從執政一開始就意識到任何政策的頒布和施行都必須建立在新加坡“多元民族社會”的基礎上,這就要求所有政策都必須基于各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則,語言作為民族文化的代表性體系,必須以不偏不倚的公正態度待之。因此新加坡政府在重視英語學習的同時也沒有放棄各族群的民族語言,鼓勵人們在私人場合使用民族語言。[8]
人民行動黨選擇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也是有其特殊考量的,一方面新加坡有著長達一百四十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歷史,獨立前英語實際上已經長期作為行政和公共機關通用語言而存在;另一方面,若選擇國內某一族群的民族語言為官方用語,會違背民族平等原則,勢必會招致其他民族的不滿,因此,英語無疑是最好的選擇。[9]
德國哲學家費希特有言:“國家首要的、最初的、并且是真正自然的邊界毫無疑問就是他們的內在邊界。那些講相同語言的人們天生就有無形的巨大吸引力,他們相互聚集起來……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體。”[10]在新加坡政府語言政策的推行下,各民族之間固有的隔閡逐漸淡化,統一的語言體系凝聚起了新加坡人民的文化認同,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愈發弱化。
(二)組屋政策
組屋政策是新加坡政府打破民族隔閡,塑造國家認同的又一重要舉措。面對新加坡嚴峻的“屋荒”問題以及民族間深刻的隔閡和矛盾,人民行動黨于1960年成立了建屋發展局,圍繞組屋出臺了“居者有其屋”政策和混合組屋政策,以解決新加坡實際面臨的社會困境,凝聚各族群的國家認同。
“居者有其屋”政策主要聚焦的是二戰以來新加坡國內的”屋荒“困境,新加坡政府于1968年修訂了《住房所有權規劃》并出臺了新規定,允許購房者使用個人中央公積金支付住房首付款,這就有效緩解了大多數人住房和購房的經濟壓力,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屋荒”問題。房屋不僅是一個居住之所,更是公民個人安家立命之本,是家庭穩固之基,通過使“居者有其屋”,人們被安頓和容納在新加坡社會秩序之中。更重要的是,隨著“家”的安定,人們不僅基于利益識別而產生了對政府的合法性認同,更由于擁有了私人財產而切實感受到了個人與國家之間緊密的聯系——只有國家穩定,個人才能安定,因此,公民便會將忠誠自覺奉獻給國家,并把捍衛國家視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而這種對國家的效忠感,正是國家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11]
混合組屋政策則將視線對準各民族之間存在的鴻溝和隔閡。殖民地時期形成的各民族分割居住狀態是導致民族鴻溝的重要原因,因此,要促進多元民族的融合,就必須打破各民族原有的居住格局,為此,人民行動黨出臺了混合組屋政策。混合組屋制度規定,建屋局在銷售和分配組屋時,同一組屋和鄰區必須由不同比例的民族構成,且各民族的居住位置不能憑各自意愿任意改變,這就迫使各民族人民不得不生活在同一個空間之內,為各民族提供了一個無法回避的交流平臺。[12]混合組屋政策的強力推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招致了人們的不滿,但整體上對于打破世代以來在宗族、血緣、宗教和地域基礎上形成的傳統社區有著顯著效果。在共同的生活中,各民族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交流愈加頻繁,原有的狹隘民族認同和排他情緒也逐漸黯淡。
統一的文化心理是凝聚人們共識的內在力量,各民族內部認同之所以強烈而牢固,正是這種文化認同發揮了作用,然而,當多民族共同聚集到同一片領土中時,各民族內部在長久共同居住的歷史和血緣地緣中產生的文化認同無法自發地形成于各民族之間,“當文化的差異和地理位置的差異重合時,可能就會出現暴力、自治或分離運動”[13],這時,就需要政府通過政策措施對這些差異進行有效整合,以此緩解族際關系的緊張,促進各民族融洽融合。通常而言,這些政策會多集中于確立統一的語言,打造共同居住環境,創造共同記憶等能夠促進族際之間交流溝通,團結親密的方面,試圖通過打造族際交流平臺來整合文化、思想和精神情感方面的差異,從而平衡族際關系,消解民族矛盾,構建國家認同,新加坡政府針對多民族現狀制定的語言政策和居住政策正是試圖通過文化整合實現民族融合的政策體現。[14]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雖存在張力,但通過使用政策手段,促進多民族融合團結,在此基礎之上塑造國族身份,可以實現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和諧同一。因此,在第二級階梯中,新加坡政府通過打破各民族之間的心理屏障,淡化了狹隘的民族認同情緒,接下來第三階段,便是構建一種包容多元民族文化的國族身份,將狹隘的民族認同上升到國家層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這第二階段中,新加坡政府依然借助了強制的政策和制度力量推動民族融合,也就是說,促進民族融合的根本動力不是來自于民眾心底,因此接下來便需要政府繼續發掘國家認同的深層次內在文化動力,以實現各民族的自覺融合,塑造國族身份,凝聚國家共識。
三、公民身份和國家意識:構建包容多元民族的國族認同
國家認同是人們將原本局限于民族范圍內的接納、承認和效忠情感轉移至國家層面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民族確立自己的國族身份,將自己的民族自覺歸屬于國家的進程。弗朗西斯·福山認為,構建國家認同的關鍵在于構建民族,這里的民族并不是指族際隔閡狀態下的民族,而是具有共享的記憶、歷史、符號和習俗傳統的民族,[15]在現代民族國家當中,這種民族就是國族。在單一民族國家中,基于先天血緣關系形成的民族與國家相重合,因此民族即國族,國家認同也就能夠自發構建。然而問題在于,單一的民族國家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并不存在,多元民族共存于一個政治共同體中才是現實常態,因此,就必須塑造一個能夠容納多元民族的國族,以實現“民族”認同向國家認同的轉化。塑造起來的國族,將各民族聯系起來,使人們的自我意識不再被基于血緣、宗教、語言而形成的初級認同所束縛,這就是在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的公民群體,即是說,公民群體的形成,標志著多元民族向國族轉換的完成。[16]實際上,國族就是人為構建的“民族”,是使民族認同上升為國家認同的工具性群體身份。
既然國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人為構建的“民族”,那么民族認同的某些要素也可以被納入國族認同構建的邏輯當中,例如共同的歷史記憶,統一的語言體系等,而由于國族具有多元民族屬性,因此國族認同的構建又要以調整民族間以及民族與國家間的關系為基礎。在新加坡國家認同構建的第一級階梯中,人民行動黨通過培育危機意識,頒布生存政策,制定發展計劃實現了新加坡的經濟騰飛,激發了人們的驕傲感和自豪感,從此新加坡各民族人民關于國家的記憶書上不再是空白一片,他們擁有了新加坡人特有的共同歷史記憶。在第二級階梯中,新加坡政府調整了國內的多元民族關系。一般來說,調整民族間以及民族與國家的關系大致有兩種路徑,第一種路徑秉持“沖突論”論調,認為各民族認同會阻礙國家認同的形成,因此主張通過強制同化政策消除具有差異性的各民族認同以實現同質性的國家認同構建;第二種路徑則堅持多元主義價值觀,主張在尊重各民族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培植國族認同。[17]新加坡政府無疑是在第二種路徑模式的基礎上調整關系的。“多元民族主義”是新加坡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礎性原則,當然,在尊重各民族認同的前提下,人民行動黨同時也注意淡化狹隘的、排他的、不利于國家認同構建的民族認同情感,這表現在新加坡政府一面通過鼓勵各族母語在私人場所的使用,營造各民族平等環境,一面通過大力推廣英語以統一語言體系及混合組屋政策來促進民族交流與融合,弱化民族邊界,努力清除各民族心理“隔離區”。
接下來在第三級階梯中,新加坡政府著力打造一個包容各民族的國族群體,完成民族認同向國家認同的轉化。認同實質上就是對自我身份的認知,人民行動黨意識到這一點,提出了“我是新加坡人”的口號,大力強化人們“新加坡人身份”意識。關于什么是“新加坡人”,李光耀這樣回答:“新加坡人是一個出身、成長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維持現在這樣一個多元種族的、寬宏大量、樂于助人、向前看的社會,并時刻準備為之獻出生命”。其實,“新加坡人”就是政府主動構建的一種國族身份,是專屬于新加坡公民群體的身份名詞,這個身份名詞給予了所有新加坡公民以確定的身份邊界,將“自我”與“他者”明確劃分開,將個人與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在這種身份認知的推動下,人們開始認為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不是華人、印度人或馬來人,這就表明人們的認同情感已經開始自覺地超越狹隘的民族局限而上升凝聚到了國家層面。
雖然國族的構建是一個主觀能動過程,但是也需要借助民族認同中的某些原始初級因素,這些初級因素可以發揮強大的紐帶作用,淡化各民族之間的心理防線,[18]這些初級因素一般來說以文化性的居多。新加坡本身就屬于亞洲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是新加坡國內各民族共同的傳統文化價值,因此,借助儒家文化可以有效凝聚各民族共識。“西化發展”轉向“西化墮落”,更為人民行動黨復興東方文化和儒家文化提供了必要性理由。20世紀后半期,新加坡政府開始主動傳播和應用儒家文化,在全社會范圍內展開了“禮貌月運動”“敬老周運動”和“推廣華語運動”等一系列活動,以復興儒家文化,凝聚國民意識。當然,新加坡政府并非全盤復興儒學文化,而是著力宣傳其中有關人際關系以及個人與國家關系的內容,例如把國家、社會和民族的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提倡和諧的人際關系等等。這樣,政府通過對各民族共同傳統文化底蘊的發掘和利用,儒學文化成為凝聚全民共識和認同的重要紐帶力量,各民族在文化共識中開始自覺融合。
為進一步凝聚全民國家意識,強化國家共識,以儒家文化和東方文化核心價值為基礎,新加坡政府又提出了新加坡“共同價值觀”,其內容為: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文化為本;關懷扶持,尊重個人;協商共識,避免沖突:種族和諧,宗教寬容。[19]這種共同價值觀成為新加坡政府為民眾制定的國家意識。由于其根植于東方傳統文化,極易被民眾接受,很快就得到了全社會人民的接納認可,國家高于民族,國家認同序級高于民族認同的觀念也潛移默化地刻印在了每個新加坡人的心中。新加坡國家認同構建的第三級階梯,發掘并利用了各民族的共同傳統文化,激發了各民族自覺融合的意愿,并在傳統文化核心價值的基礎上制定國家精神和國家意識,打通了民族認同向國家認同上升的通道。同時主動塑造國族群體,以”新加坡人“這樣一個富有標識性的身份概念刺激著新加坡公民強烈的以國家為界限的”自我”意識,在國族認同的基礎上構建國家認同,這是一個聚焦于啟動公民內心自發認同動力的過程。
四、結語
國家認同構建作為國家構建進程中重要的一環,承擔著為國家政權輸送源源不斷合法性的任務,它是國家繁榮穩定的精神力量,失去了認同的國家體系,宛如失去基底的危樓,隨時面臨著轟然倒塌的危機。因此,構建國家認同是每個政權都會予以高度重視的工作,這一點在新加坡的國家構建進程當中尤為明顯。新加坡政府沿著遞進式的三級邏輯階梯展開國家認同構建工作,不斷挖掘和激發更深層次的國家認同構建動力,終于取得了重大進展。如今,“新加坡人”意識也已經深刻烙印在了每個新加坡公民的心中,成為國家認同構建的內在動力源泉。
當然,國家認同的構建并不是一項一勞永逸的工作,而是一個無止境的持續性進程,且現階段新加坡的國家認同也并非完美無缺,未來隨著其發展模式的轉變,現代化層次的深入等,新加坡政府都需要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根據現實的政治實踐需要調整國家認同構建模式和動力,才能保證政權合法性生產源泉永不枯竭。
注釋:
①本文中的民族認同指的是基于原有的血緣關系形成的民族認同以及基于原有的文化關系形成的民族認同,這種民族認同在性質上是較為狹隘的,會使民族成員的認同視野局限在本民族內部從而不利于構建起一種超越民族的國家認同。
②亨廷頓在《變化中的社會秩序》一書中認為,一個社會的動蕩程度與其現代化速度成正比。一舨來說,現代化速度越快,一方面會激發人們更多的希求,從而導致指望與渴望之間的差距;另一方面會增大貧富差距,導致人們在與他人的比較中產生負面情緒,兩個方面的綜合作用導致動亂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