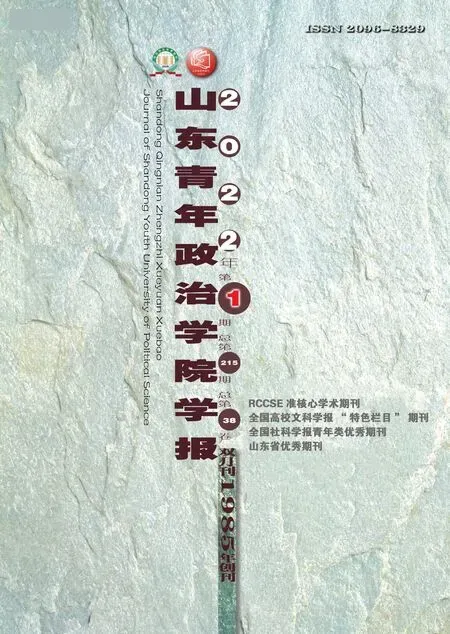復仇精神與革命文化的“落幕”之時:《鑄劍》與《左鐮》對讀
李旭斌
(中國海洋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青島 266100)
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家,長期以來,學界更多關注《狂人日記》《阿Q正傳》和《祝福》等文本的啟蒙精神和“國民性”批判對當代作家產生的影響,或是《傷逝》《在酒樓上》和《孤獨者》“反抗絕望”的精神救贖。然而,新時期作家卻對《鑄劍》的復仇情節和復仇精神情有獨鐘;不獨莫言,殘雪也十分鐘愛《鑄劍》,她讀出了小說內含的兩種復仇,一種是“表面結構的復仇”,也就是親情道德內的為父報仇;另一種則是“深不可測的、本質的復仇”,是指向自身的復仇。[1]或許是出于對自己“無傳統”反叛姿態的憂慮,余華的《鮮血梅花》就是對《鑄劍》這一前文本的“改寫”,是新時期語境下對復仇敘事的“故事新編”,最終指向的是“自我投射”的“虛無”。[2]然而,始終對復仇精神和“打鐵”情節念茲在茲的還是莫言,他先后多次談到閱讀《鑄劍》的感受,并認為《鑄劍》是“魯迅最好的小說,也是中國最好的小說”[3]。他每次重讀《鑄劍》都有新意,從“感到渾身發冷,心里滿是驚悚”[4]到“看透了的英雄”[5],再到讀出“超越了憤怒,極度的絕望”[6]的“黑色”精神。《鑄劍》如同一條河流的源頭,沿著文學的脈絡發展,流淌到莫言的作品里,莫言早期充滿野性的《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家族》《食草家族》《酒國》,后期“大踏步撤退”的《檀香刑》以及“消除”仇恨的《生死疲勞》,都能見出莫言對《鑄劍》的接受和改寫。2017年,獲獎后已經“沉寂”了五年的莫言攜帶著書寫故鄉土地和童年回憶的系列小說《故鄉人事》①“重返”文壇,在《左鐮》中,作者“不由自主地又寫了鐵匠”。[7]“打鐵”情節背后是莫言從魯迅那里承繼的復仇精神,那么,《左鐮》又是如何完成“復仇”敘事的?正在探索“晚期風格”②的莫言,或者說身處革命文化“落幕”的時代中,他在復仇敘事中是否表現了對革命、歷史、人性的新態度?同時,《左鐮》與《鑄劍》在何種意義上產生了對話關系……這些都是本文嘗試探討的問題。
一、復仇精神的原初隱喻:滌蕩“舊我”,走向“新我”
莫言對魯迅的復仇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和闡釋,《左鐮》就是對魯迅復仇精神的延續,二者之間呈現出一種“對話”關系。然而,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人們更熱衷于談論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以及他對馬爾克斯和福克納的接受,但是,莫言很早就指出,他讀福克納的小說“頂多10萬字”[8],甚至一度“忘記”自己曾在《世界文學》雜志上閱讀過馬爾克斯。更多的時候,莫言談論的是中國民間傳統和魯迅對他創作的影響,在談到《鑄劍》時,他認為:“《鑄劍》里的黑衣人給我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我將其與魯迅聯系在一起,覺得那就是魯迅精神的寫照,他超越了憤怒,極度的絕望。他厭惡敵人,更厭惡自己……這篇小說太豐富了,它所包含的東西,超越了那個時代的所有小說。”[9]可見,莫言是從《鑄劍》中的人物入手,來理解魯迅的復仇精神。與魯迅之前的小說相似,《鑄劍》的人物并不多但個個典型,眉間尺和黑衣人性格迥異,一個顧慮重重,一個堅毅果斷,似乎是人性中相反的兩極。1960年代,《鑄劍》被編入語文課本,莫言最早從中讀到了“冷如鋼鐵的黑衣人形象”[10],令莫言難以忘懷的是“黑須黑眼睛,瘦得如鐵”[11]的外貌和如同“兩點磷火”[12]般的眼光,黑衣人就像是為拯救存在性格缺陷的眉間尺而橫空出世的“俠”,這黑色形象的描述讓人不由得聯想到與黑衣人復仇精神相通的魯迅,或者說就是魯迅的理想甚至是化身,這也是黑衣人給莫言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黑衣人“宴之敖者”③也是魯迅曾經使用的筆名,1924年,魯迅編《俟堂磚文雜集》時就署名“宴之敖者”,這自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在丸尾常喜看來,黑衣人的身份可以追溯到魯迅作品中其他黑色人物系列,比如《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以及《過客》中的“過客”等。如果說眉間尺是子報父仇,那么,黑衣人為什么要復仇呢?為什么莫言認為黑衣人身上體現出了魯迅的復仇精神?“宴之敖者”這樣解釋自己復仇的動機:
“我一向認識你的父親,也如一向認識你一樣。但我要報仇,卻并不為此。聰明的孩子,告訴你罷。你還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報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靈魂上是有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傷,我已經憎惡了我自己!”[13]
當黑衣人話音剛落,眉間尺緊接著自斷其首,二者的生命和使命實現銜接,我們可以將黑衣人和眉間尺看成是個體生命不同階段的呈現,黑衣人是復仇的實際執行者,他的內心壓抑著深廣的憂憤,但他并不是報殺父之仇或血緣之仇,而是向“憎惡了我自己”的“我”復仇。即使這種復仇未必有手刃仇敵的快感,甚至要與仇人同歸于盡,但只有通過復仇,才能滌蕩令人“憎惡”的“舊我”,實現自我的拯救,也就是走向“新我”。我們認為,魯迅的復仇精神并不是以牙還牙的生死對抗,而是一種深植于內心的憂憤和焦慮,由此產生了“人我所加的傷”的“復仇”,要完成這樣的復仇,必得經過自我的蛻變。這類從“舊我”走向“新我”的復仇者形象,在莫言創作伊始就得到了繼承。《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與《鑄劍》的人物形象極為相似。黑孩有著“一顆天真爛漫而又騷動不安的童心,一副憂郁甚至變態的眼光”“寡言而又敏感多情,自卑而又孤僻冷傲,內向而又耽于幻想”。[14]黑孩就像是眉間尺和黑衣人的結合體,性格矛盾而又復雜。《鑄劍》中的眉間尺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少年,莫言也讓黑孩以兒童的視角來觀察世界。兒童“只能用一種窺探著的眼光去打量遠遠超出他們理解能力而他們又必須適應的成人社會的游戲規則。透過這樣的兒童眼光,自然就有可能避免覆蓋在現實生活上的謊言和虛偽。”[15]繼而,不論是眉間尺還是黑孩,都會在認清“成人”世界后完成“復仇”的使命;當然,這種復仇不僅是外向的,更多的時候是內在的,也就是從“舊我”走向“新我”的過程。《透明的紅蘿卜》中的黑孩盡管遭遇饑餓與孤獨的苦難考驗,而菊子姑娘的情愫無疑喚醒了他內在的生命欲望和美好的生活感受,紅蘿卜在他的眼里“晶瑩透亮,玲瓏剔透”“包孕著活潑的銀色液體”[16],這個帶有性愛暗示的心理意象隱喻了黑孩被激活的生命力,即使未來仍會遇到挫折,但生命主體將會追求超越的存在姿態以反抗絕望。如果說在表現復仇者形象時,魯迅依托的是一個荒誕化的“理性”世界,那么莫言追求的是充分感覺化的主觀世界。黑孩能聽到頭發落地的聲音,嗅到幾年前的氣味,看到“晶瑩剔透”、流淌著“銀色液體”的紅蘿卜。黑孩的感覺世界占了《透明的紅蘿卜》中“故事”的大部分,他對苦難遲鈍的忍耐力與他對色彩、聲音、氣味的感受力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常感受能力的黑孩兒,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17],在這之后,充分感覺化的復仇者形象貫穿莫言的創作過程,像是《紅高粱家族》為中華民族復仇的余占鰲、羅漢大叔,以及《我們的荊軻》中的刺客荊軻。
而《左鐮》中的田奎,同樣可以納入從“舊我”走向“新我”的復仇者譜系,這也是小說中復仇精神的原初表現。與《鑄劍》相同的是,在《左鐮》中,莫言也沒有將敘事的重心放在情節的推進和性格的轉變上,而是用冷靜和節制的態度描述了幾個關鍵性的場景,像是“打鐵”的場面、惡作劇的場面、田奎割草的場面。至于“故事”中的一些因果線索則被隱去,留給讀者想象的空間。這樣的敘事策略是為了更好的凸顯創作者的主體精神,也就是復仇精神。“左鐮”在小說中是給田奎“私人定制”的鐮刀,因為田奎的右手被父親砍掉,他只能用左手拿著“左鐮”割草。其實,田奎失去右手是因為“我”和“我哥哥”情急之下的嫁禍,也是革命文化盛行之時不容辯說的結果。幾個心智尚未成熟的孩童的惡作劇,卻就此斷送了田奎的一生。他不僅變成了殘疾,也失去了讀書的機會,只能終日在幽森的墓地中收割野草。究竟是誰先喊出的那一聲“打啊,挖泥打傻瓜啊”[18]已經無從知曉也無需知曉,因為失去右手的田奎已經默默承擔了仇恨的苦果和歷史的責任。田奎身體的殘缺,本身也成為一種“無言”的訴說和歷史的反諷,就像是“十年動亂給人留下精神和肉體創傷的原始見證”[19]。從某種程度上說,“左鐮”就是田奎的象征,三個鐵匠鍛打“左鐮”的過程呼應了田奎經歷磨難的“復仇”過程。失去右手的田奎或許可以選擇強力的反抗,就像《紅高粱》中的余占鰲和戴鳳蓮那種不顧一切的反叛;也可以就此頹廢,變得更加沉淪,進而以自身的荒誕來對抗現實的荒誕;然而,莫言并沒有安排田奎選擇這兩條復仇之路,田奎完成的“復仇”是從“舊我”到“新我”的轉變,這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漫長而殘酷的考驗。田奎沒有在失去右手后也失去對生活的信心,他信仰的似乎是民間的生存哲學——打鐵還需自身硬,將仇恨和磨難看成是成長成熟前對自我的“鍛造”,只有這樣,才能讓自身成為“最柔軟的和最堅硬的,最冷的和最熱的,最殘酷的和最溫柔的”[20]利器。而“最冷的和最熱的”利器不就象征著莫言所說的“冷得發燙、或熱得象寒冰一樣的”[21]魯迅一貫的復仇精神嗎?就像三個鐵匠“打鐵”一樣,復仇者從“舊我”到“新我”的轉變勢必要伴隨烈火的烘烤和承受巨錘的敲打,只有經受住這一切才能得到成長,田奎也在鍛打中完成了指向自我的復仇,就像小說中的“我”好奇田奎是否懼怕墳墓和毒蛇時,他說:“自從我爹剁掉了我的手,我就什么都不怕了”[22]。
二、復仇精神的深度拓展:一出“清爽”的悲劇
《鑄劍》凝聚著濃厚的俠義精神,嚴家炎先生甚至將《鑄劍》看成是一部“武俠小說”,在他看來,“主人公黑色人就是一位代人向暴君復仇的俠士”[23]。黑衣人的復仇,并非為了消解自身的恨意,他本身并不像眉間尺一樣負有道德義務或現實仇恨,他追求的是復仇的本質或本質的復仇。莫言同樣認為,眉間尺決然地自刎,并將自己的頭顱交給黑衣人,“這種一言既諾,即以頭顱相托和以頭顱相許的古俠士風貌,讀來令人神往”[24]。在莫言對《鑄劍》的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反復從黑衣人出發來理解魯迅的復仇精神,在他看來,如果說《鑄劍》是對“原俠”精神的集中展示,而其中的黑衣人就是魯迅的化身,黑衣人是魯迅內在人格凝聚而成的俠士,魯迅可以通過這個人物來實現指向自身的“復仇”。應該說,莫言對《鑄劍》的解讀抓住了這個精神實質,他看到了“真正的復仇者應該是魯迅”[25]。
《左鐮》中的田奎也經歷了人與鐵的鍛打之道,在“火”的淬煉中成長起來,然而,我們不應忽視的是小說的敘事者“我”在文中起到的作用。《左鐮》的創作主體莫言又是如何拓展魯迅的復仇精神的?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小說的敘事者“我”或者敘事者“莫言”與現實中的作家莫言等同起來,但我們認為,作家莫言對魯迅復仇精神的拓展正是通過敘事者“莫言”完成的,這是對《鑄劍》“合于一”的復仇敘事的“改寫”,同樣也是對莫言此前復仇文本的“新寫”。這是因為,在《月光斬》和《生死疲勞》中,復仇主體往往是單一而明確的,敘事者“我”有時不免陷入“操縱”復仇者的漩渦之中。但到了《左鐮》中,看似“分散”的復仇主體分別承擔不同的復仇要義,但最終都是指向自身的復仇,比如田奎的復仇是之前論述的滌蕩“舊我”、走向“新我”的“鍛造”;敘事者“我”的復仇是一種自審的懺悔意識;而作家莫言的“復仇”則是“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把自己當罪人寫”[26]的主體意識,特別是通過田奎和敘事者“我”,莫言傳達的是他既同情“弱者”又同情“強者”的悲憫,他認為強與弱之間沒有“定于一”的永恒而是不斷辯證的轉換。在這一點上,我們能夠看到《鑄劍》與《左鐮》的“對話”關系。《左鐮》中的多個復仇主體指向的是同一的復仇精神,即指向自我的復仇,因此,作家莫言就以一種“輕盈”的方式書寫著原本“沉重”的復仇主題,讓《左鐮》成為一出“清爽”的悲劇。
此外,《左鐮》中反復出現的“打鐵”情節已經不僅是敘事的情境,還成為展現人物命運的載體,甚至是作家揮之不去的生命情結——“打鐵”是敘事者“我”和作家莫言的復仇敘事展開的契機,“打鐵”情節負載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鑄劍”。魯迅最早是在1927年4月3日的日記中記錄了這篇小說:“星期。雨。下午浴。作《眉間赤》迄。”[27]小說首發在這一年的《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的第八、第九期上,題目為《眉間尺》;只不過魯迅在1932年將其收入《自選集》時才改為了《鑄劍》。魯迅對書寫“鑄劍”的過程似乎沒有太大的興趣,只用了幾筆匆匆帶過,在魯迅的其他小說中,也未見“鑄劍”的描寫,但魯迅還是給寶劍賦予了象征的意義,“寶劍在作為俠客文化的代名詞之外也是武的象征”[28],這與《鑄劍》和黑衣人的俠義精神有關。但到了《左鐮》中,“打鐵”的場面鋪排都是通過敘事者“我”的回憶引出的,“許多年過去了,我還是經常夢到在村頭的大柳樹下看打鐵的情景”[29];更為重要的是,“我”在回憶“打鐵”時,倒敘穿插了“我”當年參與的那次惡作劇,“我經常回憶起那個炎熱的下午,那時候田奎還是一個雙手健全的少年”[30];田奎也就是在這次惡作劇之后失去了右手,只能在墓地里用“左鐮”割草。其實,莫言使用的是明、暗兩條敘事線索,這兩條線索的交匯點就是“左鐮”,它一方面是“打鐵(鐮)”的原因——田奎因為“我”和“我哥哥”為躲避父親的懲罰而嫁禍于他,從而失去了右手,需要定制特殊的“左鐮”;另一方面,它又是“打鐵”的結果——田奎在磨礪中得到了成長,同時也成為“我”生命中揮之不去的陰影,因而,每當“我”回憶起“打鐵”的場景時,就會聯想到是“我”造成了田奎的殘疾。那烈日火光下一錘一錘的敲打,不僅造成了田奎的痛苦,也代表了“我”的自責。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解釋《左鐮》反復出現“打鐵”情景的原因,“打鐵”成為了我內心深處對田奎的不安和愧疚得以展現的過程,是“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也是“我”完成復仇敘事的契機,耳邊回想起的“打鐵”聲是自我反思的流露,這當然是一種指向自身的“復仇”。莫言曾經說過,“知惡方能向善”[31],“我”對自己內心之“惡”的解剖隨著一次次“打鐵”情節的展開而逐漸深入,到最后甚至發展成為一種對田奎的敬畏。如果說當年“我”在父親和劉老三的“凝視”之下迫不得已將田奎作為替罪羊,彼時的“我”暫時擺脫了懲罰,似乎是惡作劇的“勝利者”,田奎作為地主家的孩子,自然沒有辯駁的機會,失去右手的他是一個“失敗者”。但“打鐵”傳來的鏗鏗鏘鏘的聲音,卻是一曲“勝利者”的悲歌,也就是莫言書寫的一出“清爽”的悲劇。“我”早已不是什么“勝利者”而是贖罪者,觀看“打鐵”就是“我”懺悔贖罪的過程。法國思想家福柯在他的《性史》中曾經指出:“懺悔是一種在權力關系之中展開的、特殊的話語方式,即‘話語儀式’。”[32]也就是說,贖罪者的懺悔話語本身蘊含著一種權力關系或者結構,這種結構建立在懺悔主體與懺悔客體不平等的關系上,懺悔話語的背后明顯有意識形態色彩。在革命文化“落幕”的時代,“我”即使家庭出身再好,也不能高高在上,像當年一樣用“話語”權力給田奎造成傷害;相反,“我”和田奎的權力關系此時發生了顛倒,田奎的無辜讓我無法逃脫歷史和良心的罪責,所以,書寫“打鐵”情節成為我不斷進行懺悔的“話語儀式”。
《左鐮》中敘事者“我”的存在,是莫言“把自己當罪人寫”的一次實踐。莫言安排了“我”自責內心的“惡”,這是作者莫言在復仇精神上對魯迅的拓展,魯迅對生命的熱愛是與對毀滅生命的“惡”的憎恨相聯系的,正如他所說的,“人在天性上不能沒有憎,而這憎,又或根植于更廣的愛”[33]。魯迅對他者和自我生命的珍愛,讓他敢于直面“惡”的人生和人性,《鑄劍》以一種狂歡化的形式——三頭共葬、民眾送葬作為復仇的結束,“魯迅里面有一些調皮的東西和因素,跟狂歡差不多的”[34],魯迅在《鑄劍》中的筆法充滿歡樂和游戲的快感,但他傳達的現實卻是荒誕的。戲謔的輕快是魯迅對沉重的現實長期清醒的認知,也是對自我的審思和批判,是對人的生命和靈魂的自覺關注,是“向內轉”用血凝聚而成的復仇精神。因此,黑衣人不惜犧牲自己來達到復仇的目的,這是毫無保留的自我懺悔,更是對自己毫不留情的批判。莫言所做的是“對魯迅的氣質和個性的呼應”[35],他將自己放置在歷史回憶與現實社會中進行靈魂的拷問,與《左鐮》一同發表的《地主的眼神》,同樣也是因為“我”的無意之舉——一篇三年級小學生的作文,卻成了“炮打”地主孫敬賢的“大字報”。年少的我,對“懲治老地主感到幾分快意”[36],可多年之后,當“我”反思自己對孫敬賢造成的傷害時,也難掩自責和懊悔,“我至今也認為孫敬賢不是個心地良善的人,但我那篇以他為原型的作文確實也寫得過分,尤其是因為我那篇作文,讓他受了很多苦,這是我至今內疚的”[37]。莫言復仇精神中的主體意識在魯迅的基礎上既有延續也有變異,在《晚熟的人》中,最出色的部分已不是他先前小說中對生命意識的歌頌,而是對主體意識的哲理思考以及對人性“隱秘”的探索,同時,在“同情弱者而又同情強者”這一點上也有對魯迅的致敬。在莫言看來,弱勢群體值得同情的背后也存在著精神上的缺陷,而僅因為處境的弱勢而占據精神的高地是他不想看到的,他一方面意識到弱者的可憐,也意識到強者的不易。他超越善惡的道德評判,有著同魯迅一樣對人性的悲憫,記得魯迅在翻譯《窮人》時,曾在小引中談到:“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38]
三、復仇精神的主體反思:“虛妄”的救贖與“融合”的默契
王富仁先生認為“劍”的意象涉及到魯迅的“革命觀”與反抗精神,同時也隱括了“立人”思想與革命文學的論證。而我們認為,《鑄劍》中鮮明的意象其實帶有豐富的文化隱喻——“劍”是權力的隱喻,干將莫邪鍛造寶劍并不是為了自己使用的,而是要獻給“王”;眉間尺和黑衣人的復仇行為象征著革命,死亡意味著革命的“勝利”,但勝利的代價是革命與專制權力的同時滅亡,在魯迅看來,“同歸于盡”未必就是復仇(革命)的勝利。這里隱含著魯迅對復仇精神的主體反思,或者說,是他對革命文化的某種憂慮。《鑄劍》充滿了復仇的因素,卻在仇恨中夾雜著絕望與希望的矛盾,正如顧慮重重的眉間尺一樣,面對紅頭老鼠對家具的咬嚙和對睡眠的影響,眉間尺恨,當面對弱小的生命時,眉間尺憐憫;面對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眉間尺恨,當審視手無縛雞之力的自己時,眉間尺懷疑……這些猶豫與焦慮都一步步地激化眉間尺心中的“惡”,他除了復仇別無選擇,而這注定又是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也就是魯迅所說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39]。然而,橫沖直撞的刀劍相逼在現實的條件下無法實現復仇的計劃,他只好迂回地達到復仇的目的,也就是以犧牲自己的肉體為代價,讓黑衣人代替自己復仇,畢竟肉體的消亡在一個只剩仇恨的人眼中不值一提。那么,為何認同“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40]的魯迅讓眉間尺和黑衣人選擇了用迂回的方式來完成復仇呢?聯系當時的社會背景,《鑄劍》寫于“女師大學潮”和“三一八慘案”后,創作時間從“1926年10月”[41]到1927年4月,魯迅在1927年4月3日的日記中提到的《眉間赤》應該是小說發表前的定稿。可見,《鑄劍》并非是魯迅對“清黨”的復仇,但魯迅對復仇精神或革命文化的反思卻早已產生。從魯迅的思想史來看,1926—1927年的魯迅正處于思想的低潮期,《野草》也是寫于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從《野草》來窺見他此時的思想傾向。懷疑的悲觀主義貫穿于魯迅的創作歷程中,而在《野草》時期更為顯著,他對革命文化產生了懷疑,魯迅此時的心境變得“分外地寂寞”,甚至是空虛,其實,魯迅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焰和毒,恢復和報仇”;在經歷過一連串的“自欺的希望”和“空虛中的暗夜”之后,此時的他認為,大刀闊斧的“復仇”也許是暢快淋漓的,但是往往只會兩敗俱傷,并不會解決實際問題。[42]《鑄劍》的底色是一種對革命“虛妄”救贖的悲涼,因此,小說中的眉間尺最后用犧牲生命的代價換來復仇的勝利,以看客圍觀的方式作為結尾更具諷刺意味。同樣,《頹敗線的顫動》中的老婦人,為了養活子女而飽受苦難,甚至做出違背道德的事,但這些付出非但沒有得到子女的認可與同情,反而招致了冷笑與謾罵;但她不再指望“虛妄”的救贖,而是獨自走向荒野,“赤身露體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43],她用這種“無言”的形式傾訴心中的怨恨與詛咒,以完成“復仇”的目的。
《鑄劍》其實是對歷史的另一種解讀,魯迅將鑄劍的過程虛化,隱去干將莫邪的名字,只以眉間尺母親的口吻回顧往事。可以說整個故事是模糊的,并未指向具體的歷史,由此,魯迅的歷史觀也得到彰顯,這是一種同歸于盡、不分你我的虛無的終極歷史觀。《鑄劍》所體現出來的獻身犧牲的復仇者譜系以及超越個人恩怨的復仇觀都和魯迅的歷史觀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歷史觀隱含著對復仇觀、創作觀乃至人生觀的思考,莫言認為魯迅作品中的復仇并不是以牙還牙的對抗,而是一種根植于內心的憤恨與憎惡,是對“人我所加的傷”的報仇。“我已經憎惡了我自己”,魯迅把自己同樣放在復仇的對立面,對自己的批判毫不憐惜,由此產生的“內省”和“懺悔”是對黑暗現實深刻的復仇體現,這是革命文化“落幕”之時經魯迅改造的現代的復仇觀。“復仇”絕非為了追名逐利,而是對自身的省思,同樣,莫言針對新時期現實生活中追逐名利的現象,或反諷或批判,重新編寫荊軻刺秦的復仇故事,完成了《我們的荊軻》這部以復仇為主題的話劇。在這部具有現代意義的復仇話劇中,沒有了血緣的纏繞,復仇指向了其本質,即“向自身的復仇”。然而,與魯迅對復仇精神的反思不同,在受到仁慈母親的耳濡目染與民間文化的沁潤影響之下,莫言變得溫和,形成了“仇必和而解”的復仇觀。在莫言看來,采取“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方式,并不能斬斷仇恨與恩怨,身負仇恨的人永遠不會逃脫自我折磨的陰影,反而容易成為仇恨的傀儡。《生死疲勞》中的西門鬧“六道輪回”而不能轉世投胎就是因為無法擺脫報復的輪回與仇恨的記憶,因此,只有告別過往,與仇恨和解才能解開生活的死結。
與《鑄劍》具有相關性的《左鐮》也體現了莫言對復仇精神和革命文化的反思,小說雖然沒有明確時代背景,但通過人物的對話,我們卻可以推測田奎對貧下中農孩子的“人身攻擊”,很有可能會在極“左”政治的年代上綱上線為對革命的反動。當階級斗爭成為社會的風向標時,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系處在人為制造的敵意與仇恨的緊張氛圍中,似乎每日都在上演“革命”對“反革命”的“復仇”悲喜劇。在《左鐮》這篇小說中,身處政治邊緣地位的地主階層,田千畝不想給家族和個人再招惹是非;面對氣勢洶洶,前來“復仇”的貧下中農,他無法承受想象不到的壓力,又不敢將這種壓力轉向“出身好”的劉老三,因此,他只能把自己的恐懼、憤怒和暴力發泄在無辜的田奎身上。田奎那只缺失的右手,隱喻的是一個階層的“失語”,是占統治地位的所謂“革命”階層對“反革命”階層的規訓和懲罰。其實,福柯就認為政治權力話語對人的作用最終要在肉體上表現,“在任何一個社會里,人體都受到極其嚴厲的權力的控制。那些權力強加給它各種壓力、限制和義務”[44]。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明明學習比“我”二哥還優秀的田奎,為何只能早早輟學在家,用“左鐮”從事無休止的體力勞動,“割草”似乎是對田奎身心自由的限制和約束。在形而上的層面中,“左鐮”是莫言對革命文化的反思,現代性的“革命”激發了人性的邪惡,而人性的邪惡卻葬送了革命的“現代性”。在革命文化“落幕”的時代,田奎本來可以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對曾經傷害過他的人“復仇”,但他默默承擔了革命文化加之于他的傷害,以和解的態度對待仇恨的記憶,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可以發掘出莫言執迷于“打鐵”情節的深層原因。他相信“打鐵”不僅象征了田奎從“舊我”到“新我”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仇恨的消弭,“這就是勞動,這就是創造,這就是生活。少年就這樣成長,夢就這樣成為現實,愛恨情仇都在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鍛打中得到了呈現與消解”[45]。在小說的結尾,田奎竟然接納了“仇人”的女兒歡子,這是命運的糾纏和救贖。最后的一個“敢”字,說明仇恨早已消失遠去,留下的是溫情和感動。
莫言在革命文化“落幕”的時代對復仇精神的反思,也與他的歷史觀聯系在一起。從創作伊始,他書寫的便不是史詩性的英雄歷史,而是以平民或底層的視角審視歷史,用民間化的語言區別于“十七年”文學二元對立的歷史“控訴”。他曾經說過:“我認為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應該超越黨派、超越階級、超越政治、超越國界的。”[46]《月光斬》正文的結尾又變回了書信寄語,整部小說沒有涉及復仇、反動、殺戮的過程,只有無奈和無聊的現實,人物只能繼續被控制,“月光斬”不再含有敵意仇恨,而是消失于歷史長河之中,只剩下沒有意義的惡作劇。在《左鐮》中,莫言對待歷史中的仇恨記憶更加寬容,更具有“與歷史和解的意味”[47]。由此可見,魯迅和莫言盡管都對傳統的歷史觀進行消解,但他們所理解的“傳統”并不一致,這也讓二人對復仇精神的反思呈現出差異:一種是虛妄的,一種是融合的。雖然他們的歷史觀有些不同,但“虛妄”與“融合”最后指向的都是仇恨的消弭,只不過方式不同,魯迅是通過肉體的消亡,而莫言則是一笑泯恩仇,不再執著于復仇行為本身。
莫言曾談到《鑄劍》“跟我的生命經歷有某種契合”[48],作為黑衣人的化身,魯迅自然也和莫言有著關聯,而黑衣人“黑得發亮,冷得發燙”[49]的精神也流淌在莫言的文字中,成為莫言創作的一部分。通過《鑄劍》與《左鐮》的對讀,我們可以看到在革命文化“落幕”的時代,魯迅和莫言對復仇精神的認知、應用和反思。莫言將魯迅的“黑色”精神轉變為自身的“和解”態度,從“復仇”起始到仇恨消弭,他們對復仇精神的書寫,既有相通的一面,也有符合個性的創造。這兩部作品的“對話”,不僅可以彰顯魯迅與莫言的精神通聯或是莫言對前人的“變”與“不變”,還從一個側面展現了“五四”新文學精神在今天的延異。
注釋:
①《故鄉人事》系列首發在2017年5月《收獲》創刊60周年的紀念刊上,包括《左鐮》《地主的眼神》和《斗士》三個短篇小說。這三篇作品后收錄在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莫言小說集《晚熟的人》中。
②這是王德威對莫言的新近評價,他借用的是薩義德在《論晚期風格:反本質的音樂與文學》中的理論,但在論述過程中前后矛盾,并混淆了“晚期風格”和“晚熟”狀態這兩個并不同一的概念;但他認為《晚熟的人》不僅是莫言對前期創作的延續,同時也是新的探索,這一點可以深究。參見王德威.晚期風格的開始——莫言《晚熟的人》[J].南方文壇,2021(02).
③對“宴之敖者”的解釋有很多,其中一種是“宴之敖者”生活在“汶汶鄉”,“汶汶”指昏黑,昏暗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