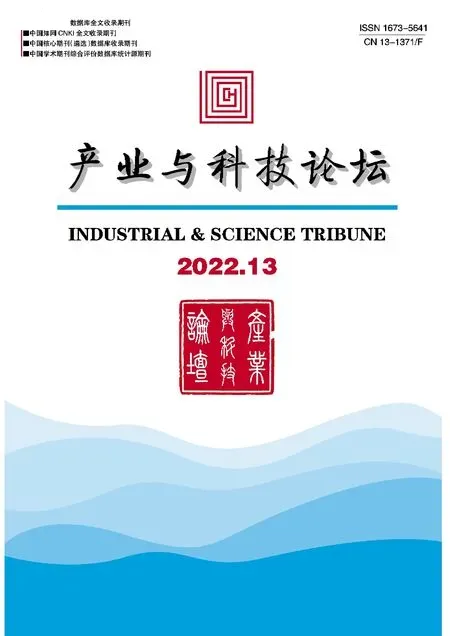校園網絡詐騙犯罪的困境反思與司法應對
□洪樹湘
一、問題的提出
迄今為止,網絡社會已歷經三代更迭而步入“Web3.0”[1]時代,在改變民眾生活和行為模式的同時也成為新型網絡犯罪滋生的溫床,其中以網絡詐騙犯罪為禍尤烈。一直以來,在“零容忍”刑事政策的導向下,我國對網絡詐騙犯罪采取嚴厲打擊的態勢:在立法層面上通過《刑法修正案(九)》和《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等規范性文件嚴密網絡詐騙犯罪法網;在司法層面上開展云劍行動、長城2號等一系列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專項行動。在我國刑事立法和司法雙層面的集中打擊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已經取得階段性進展、高發類案也得到有效遏制[2]。
但是,山東大學生被騙猝死案[3]、廣東大學生被騙跳海自殺案[4]、清華教授被騙千萬案[5]等校園網絡詐騙極端案件頻頻見于報端,凸顯當前網絡詐騙犯罪規制的重災區:校園網絡詐騙犯罪。2021年,武漢法學博士生被騙十余萬案[6]再次將校園網絡詐騙犯罪拉入公眾視野。吊詭的是,明明我國在立法和司法層面上都不斷加強對網絡詐騙犯罪的打擊,但不僅網絡詐騙犯罪屢禁不止,而且針對校園群體的校園網絡詐騙犯罪更是層出不窮。這一現象不得不引起國家和社會的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校園日益成為網絡詐騙犯罪的重災區?校園網絡詐騙犯罪有何特殊性?當前刑事司法應當從哪些維度應對校園網絡詐騙犯罪?有鑒于此,本文擬在厘清校園網絡詐騙犯罪發生機制的基礎上,對當前我國規制校園網絡犯罪機制失靈的原因進行反思,并嘗試提出司法的應對路徑,以期能為刑事司法實務提供有益參考。
二、校園網絡詐騙犯罪“屢禁不止”的困境反思
(一)應接不暇:司法資源有限與罪案數量繁多的齟齬。
1.犯罪場域擴張與網絡技術裂變使網絡詐騙犯罪數量爆發式增長。詐騙犯罪作為財產犯罪的典型形式之一,在傳統社會背景下只能以“線下”的方式進行。這種模式決定了其往往以“一對一”的形式出現,且數量有限。及至網絡社會的到來,詐騙犯罪的發生場域也從“線下”擴張到“線上”,呈現線下詐騙犯罪與網絡詐騙犯罪并存的樣態。與此同時,網絡技術一方面提高信息交換效率和擴大受眾范圍,另一方面也使違法犯罪信息的傳播、犯罪行為的實施“愈加高效”。在傳統社會背景下,詐騙犯罪只能以“接觸式”的方式緩慢推進,受害者范圍難以無限擴大。但在網絡社會背景下,無論是虛擬電話呼叫、虛假信息群發、虛假鏈接發布等方式都具有“廣撒網”式的特點,幾乎能使所有的網絡用戶都成為潛在的受害者。
2.活動場域與行為模式特定化的校園群體更易淪為“精準打擊”對象。校園群體(包括學生、教職工等)不僅在生活場域上具有相同性,而且在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上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這些特點使校園群體獨立于社會一般公眾,也為詐騙犯罪分子進行“精準打擊”提供可乘之機。首先,就收入而言,校園群體多為大學生,由于缺乏獨立經濟來源,可支配資金往往不多,從山東大學生被騙1996元、廣東大學生被騙1萬元等案例便可窺見一斑;其次,校園群體基于科研、網購、外賣等原因幾乎時刻都在與網絡社會打交道,無形中也增加了曝光于網絡詐騙分子的概率;再次,許多學校往往統一為入學大學生制發銀行卡、手機號碼卡等,這些卡證的賬號名和密碼往往具有相似性,容易被批量泄露;最后,在校大學生出于求職、兼職等原因往往在網絡上大量投放簡歷,網絡詐騙分子利用這些記載著個人身份、工作和學習經歷等詳細信息的簡歷能輕易獲得相關大學生及其親友的信任。所謂精準打擊式詐騙,指犯罪分子通過不法渠道獲得大量個人信息,從中篩選出受害人職業、愛好、現狀等基本信息后“量身定做”詐騙方案[7]。根據研究表示“有別于廣撒網、隨機式的詐騙方式,精準詐騙更具有針對性和指向性,因此其欺騙性、迷惑性進一步增強,成功率也更高”。[8]事實上,根據部分高校實證數據顯示,高校網絡詐騙類型恰恰是“以虛假購物和虛假兼職類為主”。[9]
3.有限的司法資源難以覆蓋龐大的潛在受害群體和爆發式的罪案。任何國家的司法資源都是有限的,在傳統社會中尚且如此,更遑論在潛在受害群體和詐騙犯罪具有無限擴大可能的網絡社會。網絡犯罪場域的擴張與網絡技術的裂變使潛在的受害主體無限擴張,而校園群體(包括學生、教職工等)也概莫能外。據教育部發布的《2020年全國教育事業統計主要結果》[10]可知,我國大陸地區在校生人數達2.89億人、專任教師人數達1,792萬人,其中,高等教育在學規模達4,183萬人、專任教師人數達183萬人。這么龐大的潛在受害者群體一方面成為網絡詐騙分子眼中的“香饃饃”,另一方面也加劇有限司法資源和爆發式罪案數量之間的緊張。
(二)規制乏力:傳統司法手段與網絡詐騙犯罪的抵牾。傳統司法手段深受古典主義刑法的影響,對于犯罪的規制著眼于實害結果的產生,換言之,刑法必須等到實害結果發生之后才能介入。但是,校園網絡詐騙犯罪的危險并非在“詐騙行為實施”的瞬間才產生,而是在具有辨識性、特定性的個人信息泄露之時便已產生“詐騙的抽象危險”和“個人信息泄露的實害結果”。如上所示,清華教授被騙千萬案恰恰是因為網絡詐騙分子準確知道“已賣房籌款、購房合同編號”等足以使受害人信以為真的個人信息;再如徐玉玉被騙學費恰恰是因為“該年度山東省五萬余條高考考生信息”泄露。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意味著在等待詐騙行為實施、乃至詐騙結果發生之后再予以介入的傳統司法手段已經不能適應規制網絡詐騙犯罪的現實需要。此外,隨著風險社會的到來,各個體制、機制、措施自身可能存在的風險以及可能受到外在風險的影響逐漸普遍化,這也要求刑法必須進行前置化、預防化、積極化的管轄和打擊。按照常理,詐騙團伙“一般選擇有經濟實力的人作為重點目標”,[11]因此,本身缺乏獨立經濟收入來源大學生由于資金有限本不應當成為網絡詐騙分子的重點目標。但是,“校園貸”現象不僅意味著互聯網金融平臺將校園群體作為“精準營銷”對象,也反向激勵了網絡詐騙分子將目標投向校園群體、以校園貸款為切入點實施校園網絡詐騙犯罪。以武漢法學博士被騙十余萬案為例,涉案款項正是由于受害博士研究生“通過京東白條、支付寶借唄等貸款平臺借貸”[12]所得。究其緣由,校園網絡詐騙犯罪的誘因之一恰恰在于校園網絡貸款的寬泛化與無序化,但傳統司法手段對此卻幾乎無能為力。
(三)力有未逮:法網交織致使司法適用出現競合難題。傳統社會背景下,詐騙犯罪主要局限在直接詐騙、偽造印章等行為,傳統司法規制也遵循“財產犯罪—轉化犯罪”短鏈條的單一邏輯進路。但網絡社會“操控式、非接觸性”[13]的特性使網絡詐騙鏈條得以延長、牽涉的犯案主體范圍泛化,由之帶來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詐騙罪—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長鏈條式邏輯進路給司法實踐帶來犯罪構成、共同犯罪、牽連犯等適用難題。以校園網絡詐騙犯罪中的“協助發送詐騙信息、提供結算通道”等行為為例,可以同時為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所涵攝,而各地法院對該行為的定罪量刑也不盡相同、有違反司法適用統一性的嫌疑。由于大學生通過網購、外賣、簡歷等方式廣泛且深度地參與網絡社會,校園網絡詐騙犯罪的危險端口也前移至特定化的個人信息泄露之時。但司法實務中往往難以認定泄露者“明知”買受者具有詐騙故意,進而無法認定泄露者構成詐騙罪的共犯,而只能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論處。然而,校園群體信息的泄露對校園網絡詐騙的成功實施存在關鍵影響,對泄露者僅論以侵犯個人信息罪可能存在罪責刑不相適應的問題,尤其是在出現被害人死亡等嚴重后果的情況下。在部分情況下,司法實務中甚至會出現信息泄露者逍遙法網、得不到應有懲罰的情況,如央視“315晚會”所曝光的“智聯、58等平臺個人簡歷信息泄露”事件的當事人并未被追究相應的刑事責任,這恰恰體現當前司法在應對校園網絡詐騙犯罪上的力有未逮。
三、以積極化刑事司法應對校園網絡詐騙犯罪
(一)以技術反制技術,切斷網絡詐騙鏈條。網絡詐騙犯罪分子往往采用虛擬號碼呼叫、虛假鏈接群發的方式對潛在的受害人實施誘騙行為。在此情況下,如果能確保來電號碼、鏈接、信息的真實性及各自的歸屬信息,顯然能有效切斷網絡詐騙鏈條,阻止網絡詐騙行為的實施。以美國為例,谷歌和蘋果、AT&T等通信業巨頭成立“反自動呼叫電話打擊行動組”,通過“主叫號碼ID識別技術”屏蔽虛假號碼撥出的詐騙電話,力圖通過“技術反制技術”的方式規制網絡詐騙犯罪。事實上,我國搜狗、騰訊等企業所開發的軟件也具有號碼識別、分類和標識功能,能有效鑒別號碼所屬的行業、并通過用戶標識區分是否存在過往詐騙行為或存在詐騙嫌疑。在校園群體被騙的案件中,基本上都是由于受害人“輕信”或“不得不信”網絡詐騙分子的謊言是“真實的”。我國目前“針對新型網絡犯罪所涉及的信息流、通訊流、資金流、人員流等數據的偵防技術研發、適用還不到位”。[14]在網絡社會的背景下,從個人信息的非法獲取,電話、短信、鏈接等渠道的接觸與誘騙,涉案資金的提取和轉移等整個鏈條都與互聯網通訊技術密切相關。對此,應正視網絡犯罪行為“時空分立”[15]的特性,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構建“電信網絡詐騙信息平臺”。[16]如上所述,校園群體在人群團體、活動場域和行為模式上具有特定化和相對穩定性的特征,可以考慮將校園群體的聯系方式納入統一數據庫、設定“助學金、網貸、求職”等校園詐騙高發類型關鍵詞進行重點防控,切斷校園網絡詐騙鏈條。
(二)預防化前置化應對網絡詐騙衍生犯罪。校園貸看似只關涉高利貸、暴力催收、貸款詐騙等犯罪,實則從側面反向激勵了校園網絡詐騙犯罪的興起。與之類似,信息技術所導致的個人信息泄露風險增加,以及信息的精準化、特定化也為詐騙分子實施“精準化、個性化”的詐騙行為提供更大可能。以在校大學生多發的簡歷泄露為例,記載著個人生活和學習經歷、聯系方式、乃至家庭背景等信息的簡歷看似與校園網絡詐騙風馬牛不相及,實則無形中使潛在的校園網絡詐騙犯罪現實化。《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將“詐騙在校學生”作為“酌情從重處罰情節”、《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將出售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列入‘情節嚴重’情形”,刑事司法層面更應予以積極回應,以前置化、積極化、預防化的態度打擊泄露大學生個人信息、非法發放校園貸款等校園網絡犯罪的衍生犯罪行為。
(三)構建常態化、全方位的校園反詐機制。與社會公眾相比,在校大學生在生活閱歷等方面往往存在經驗不足的情況,這也導致在校大學生容易因輕信、誤信而陷入校園網絡詐騙的圈套之中。事實上,盡管我國設置了96110電話、國家反詐中心APP等方式規制校園網絡詐騙犯罪,但許多在校大學生對此并不知情、甚至許多大學教師對此也聞所未聞。盡管部分地區公安部門組織“反詐宣傳進校入室”活動赴各大中小學校進行反詐宣傳,但如何通過恰當的途徑宣傳校園網絡詐騙犯罪的類型與危害、反詐技能和反詐機制,是擺在校園內部各個主體、乃至整個社會面前的重大課題。由此可見,靠公檢法機關一己之力顯然難以構建常態化的、行之有效的校園反詐機制。因此,可以通過“公檢法機關階段性、專項反詐宣講、提供7*24小時”和“學校相關部門將反詐教育融入日常教學宣傳”,即校園外部和校園內部兩個支點構建常態化、全方位的校園反詐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