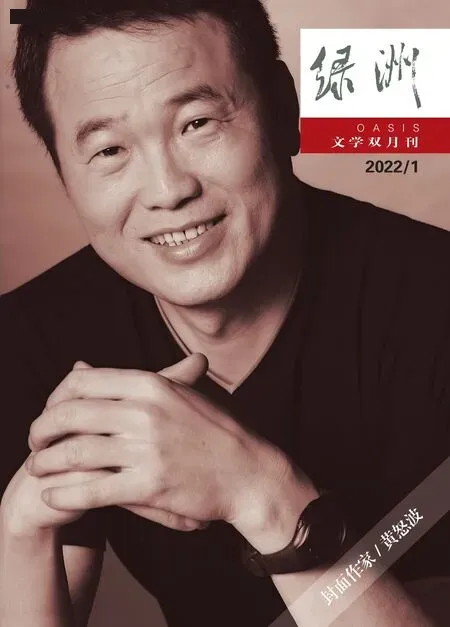梅花開了
胡竹峰
梅花開了
路過梅林,花似開不開,藏在干枝里,似乎在等著一場春雪。
果然,飄起了春雪。喜歡春雪。春雪如春色,春雪易逝,春色易逝。
雪后訪梅者說梅花開了。
雪中梅更熨帖,應了金農明月前身之論,梅林里又疏影橫斜,一時如畫,是梅花冊頁。
白梅是畫在紙上的好。王冕一生畫了不少梅花,多是老梅,或一枝或繁枝,梅影參差,密蕊交疊,以淡墨圈花法勾勒花瓣,好看幽古。臺靜農先生亦好作梅,圈圈點點,有骨格有風致,又自負又寂寞,不染俗塵,有一種高貴的落魄不羈。
白梅白得不一般,我想可以稱“梅花白”吧。黃梅之黃是“梅花黃”,紅梅的紅也自然是“梅花紅”。我喜歡的白有梨花白、杏花白、梅花白,白出一片冰心。一片冰心未必非要在玉壺,在枝頭也頗好。
紅梅是生在地上的好。
近日課業,教五歲小女背《梅花》詩:
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王安石宦海沉浮,不失書生心性,不失詩人心性。
少年時,我家庭院栽有幾株梅樹,曾祖手植。當真是老梅愈老愈精神,尤其是大雪天,開得精神抖擻,梅香馥郁。二十多年前的雪天了。
一九九〇年代的某個隆冬,我家舊庭院的紅梅開了一樹花,清秀可喜,又吉祥又好看。祖父高興,帶我們在梅邊賞玩。寒梅清幽探雪,祖父清癯臨風,風動圍巾。快三十年了,我忘不了。《紅樓夢》上薛寶琴披著鳧靨裘站在山坡上遙等,身后一個丫鬟抱著一瓶紅梅。快二十年了,我也忘不了。丁酉初春,我與友人在老家小城訪梅不遇……
梅花落滿了記憶,大雪落滿了記憶。
雪后園地仿佛一卷宣紙,踏雪尋梅更是踏雪尋春。紅梅落在雪地里,密有密的風韻,疏有疏的神采,如胭脂點染,疏朗清雅,入眼靡瑰,春意比杏花枝頭足。
臘月手記
打豆腐,擰漿,看黃色的汁水從麻布縫隙里流下來,木盆接住,海海一汪漿水。
炸生腐,豆腐條放入油鍋,膨脹松軟金黃。用線串起來,累累墜墜。
臘肉咸魚掛在樓閣上,晃悠悠的,陽光正好,肉和魚冒著油光。老人攏起手,雙腳放在火爐上,歪在屋檐下打盹,竹杖歪在一旁,竹煙筒歪在一旁,花貓歪在一旁,黃狗歪在一旁。
夜里炒干果,鐵砂與瓜子花生交織的氣味洶涌如濤,滾滾而來在池塘上方,滾滾而來在小路上。
梅花上落滿雪,白梅更白,紅梅如胭脂如雞血石,黃梅如琥珀。小兒穿著紅色的棉襖在樹底下玩冰柱。
清早,牽牛出欄飲水。陽光未及處,霜色朦朧,牛蹄踩出腳印。牛飲水時,一只鳥站在牛角上東張西望,一小童在牛后站著。
幾個人廊下打紙牌。一男孩跪坐椅子上一張張收攏打出的紙牌。
山是枯的、白的、灰的、青的、綠的、黃的,一切都黯淡著。
陽光大好,掛面上架,像瀑布,一架又一架。
回鄉的車遠遠地過來,一點點大起來。
行李包裹由家人扛著,回家的人空著手,跟在后面,一路向村子里走去。
整日冒著煙氣的煙囪,灶上做糖、蒸米粑、打年糕、鹵肉……灶下柴火熊熊,堆在屋檐下的柴矮了半截又矮了半截。鋸好的樅樹段一堆堆,樹輪對外,一圈圈一圈圈。穿短襟襖子的莊稼漢劈柴,手起斧落,一劈為二。劈好的柴碼在墻角,長了半截又長了半截。
大胖豬泡在桶里,黑毛豬。毛一點點褪盡,豬肉白,像璞玉一樣。須臾,豬肉倒掛在梯子上,豬頭割下來,在案板上耷拉著大耳,笑瞇瞇的。午飯后,吃殺豬飯的人三三兩兩地散去,農婦在豬肉上撒一把粗鹽,壓上石頭,腌進大缸里。
白色的米粑攤放在竹籮里,擠在一起,一團團富貴。
石臼里搗碾芝麻,咯吱有聲,一縷幽香飄向屋頂。
上墳,踩在荒草上,穿過田埂,穿過山坳,鞭炮聲里有一種寂寥。靜靜地看紙燃起來,漸漸成灰,有一種失落,也有一種生息。冬陽照耀,近映山際,山雞飛過,一只、兩只、三只,平添傷感,又增野趣。背一布袋的少年扛著鋤頭挖冬筍。
祭祖,新婦挈新兒,新兒著新衣。紅燭高照,一家子跪在牌位前,鞭炮如雷。
山林
順著老屋后邊石子路慢慢走,到了山中。這條路我已經走過無數遍,小時候經常去玉米地里放煙盆熏野獸。每天夜里,點一束葵稈火把照明,橘黃色火焰一下子切開了夜的黑,葵桿燃燒出一種特殊的香味飄浮在山野間,淡淡的,美極了,像輕紗一樣若有若無。不時有螢火蟲擦身而過,給夜行增添了很多詩意。
已是初春,路邊有些樹木冒出了嫩芽。很久沒有感受到時令的變化了。
我喜歡山中。這是回家后的第一天早晨,正是城里人剛剛打出睡醒后第一個呵欠的時候,我悄悄起床了,慢慢地走在去往山林深處的小路上。
草深處微微動著,是睡醒的兔子還是捕食的野鳥,我不知道。萬物各歸其處,相互羈絆,不相往來,這應該是很好的境地吧。兩個飛蟲停在我的肩頭,停了就停了吧。在山中,我是可以讓蜻蜓立上頭的小荷尖角。不忍心把這兩只飛蟲掃開,它們膽子很大,從我的肩膀順著袖子慢慢往下爬。
我極喜歡那些體形微小的生物。小時候去學校的路上有一塊沙地,沙地上經常有螞蟻盤踞,每次總會逗留片刻,看螞蟻搬物、散步、打架……我看見一只螞蟻在搬運一個比它的身體大三倍的蟲子;我看見一只螞蟻繞著一塊小石頭轉圈;我看見一只螞蟻匆匆如急事在身;我看見一只螞蟻緩緩似信步徜徉;偶爾也會抽一根草芯,逗弄螞蟻,讓兩只螞蟻把頭抵在一起較力。
山中有個廢棄的水井,是當年村民灌溉用的,這幾年退耕還林,水井已廢棄不用了,井四周雜草叢生,水浮動著很多水黽。說浮動,因為它們太小,仿佛是漂在水面的一抹浮萍。
一個個水黽在水面滑動,姿勢優美而從容,觸角過處,水波不興,輕盈得如風吹落葉。我停下來盯著它們看,水黽有三對長有油光光絨毛的腳,一對短,兩對長,靠近頭部的短足用來捕食,身體中部和尾部的兩對長腳用來滑行。足的附節上,生長著一排排不沾水的毛,所以,與足接觸的那部分水面會下凹,但不會沖破表面張力。
一切微渺的生動,即便小若蜉蝣、微如細菌,造物主也賦予了它們一定的智慧和生存的技能。水黽在水上滑翔,不是與水嬉戲,而是為了捕食水中的小蟲子或者死魚蝦,獵物一旦到手,就用管狀的嘴吸食它們的體液。水黽忽動忽靜,靜如處子,動若脫兔,它們這樣的節律使人變得松弛、慵懶。井里的一方天地,對水黽而言,也是一個大千世界。
天色徹底大亮,山風推動著樹枝,陽光射下來,山腰上昨夜的白霧悄悄在散,舒緩的松濤聲輕和著樹林深處婉轉的鳥鳴。“仁者樂山,知者樂水”,說什么仁者喜愛山,智者喜愛水,我覺得應該是仁者像沉靜的山一樣恒久,智者像流動的水一樣快樂,畢竟仁者也可以喜愛水,智者也可以喜愛山的。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沒有酒,以清風代之,飲下無邊原野與漫漫山嵐。
常聽人說,山要青,水要秀。南方的山以樹多草滿而青,南方的水也因澄澈透明而秀。沒有樹木的山,即便是春夏之際,也顯得蒼茫雄渾。
有一年,我去太行山邊看山,北方的山與南方截然不同,山體的走勢,土石的顏色風格迥異。下午時,太陽西斜,我站在平原上看巍巍大山,懸崖峭壁,怪石嶙峋,山與山之間巨大的投影壓迫得人喘不過氣來。這樣的山,毫無秀美可言,但自有一份厚重。
鄉村的黎明幾乎是被鳥兒喚醒的。一只八哥在樹林里唱胡編亂湊的歌,一只喜鵲在覓食的間隙,跑到電線桿上嘰嘰喳喳叫上幾嗓子。山雞揮舞著長長的尾羽躍過山場,還不忘沙啞悠長地說話。翠鳥在山谷對水而鳴,錦雞在土坡仰天長歌,麻雀在杉樹林蹦來蹦去,發出細碎的聲響。
在這種鳥的音樂會中,有一種聲音特別的突出。你不知道它在哪里響起,山林的東邊,山林的西邊,山林的南邊,山林的北邊,拖長的聲音,有五個音節,懶洋洋的,音色卻出奇地亮。
頭頂發出群鳥撲棱著翅膀的聲音,回頭看,一群白鳥離窩了,那流線型的纖長身體,姿態輕盈,雪白的羽毛,鋼色的長喙,那雙青色的腳像一件精心打磨的青玉長桿。潔白的身子襯著大樹的蒼翠,四周靜悄悄的。
我儼然一腳從滾滾紅塵踏進了山河歲月。
太陽慢慢爬過山尖,金色的陽光照著樹木。白鷺四散著展開雙翅,飛快地劃過樹杪,輕盈地落在對山的電線桿上,也有幾只飛得更遠,直接奔向泥田,或在田埂上漫步,或繞著水田來回盤旋,在初春清晨陽光的映照下,它們潔白的身子如粉雕玉砌。
山邊麥地的邊上有一株樹,一株樟樹。樟樹是江南四大名木之一,人們常把它看成是景觀樹、風水樹,說能避邪。當年祖父對此深信不疑,他說屋基旁植樹會讓一個家庭有更多的生機與活力。
最多愁善感的年紀,早上起床后總要在院中樟樹下靜坐片刻,鼻息間淡淡的藥氣,讓人靈府一醒。樟樹之香斯文安靜地飄浮在清晨的空氣中,沒有桂花濃烈,沒有槐花清淡,沒有蘭花素雅。
眼前的這棵樟樹已經很老了,老得連村子里最老的老人也不知道它的來歷。空中飄來的種子,偶然落在這里生根發芽,也就隨遇而安了。樟樹皮頗粗糙,質地卻很均勻,沒有楊樹的斑駁,更不像桃樹長滿無數的疤瘤。它的樹干筆直且長,一分二、二分四地豎在那里,球形的樹冠像一把巨傘,在天空中撐出優美的一團,圓潤中有連綿,規矩中透著俊秀飄逸的神韻。
那些年,常常站在山邊,默默地望著這棵樹,它會不會孤單,會不會和其他樹種閑聊呢。此時,這株樟樹在早春微涼的風中搖曳著,我看見幾個鳥窩,不知道是空巢,還是有鳥在其間棲身?放在十年前,我會爬上去看看的。
樹猶人。世間萬物皆有性情,山中的樟樹比屋前屋后的樟樹多了幾分從容。當年莊子多么愿意做深山中的一株樹啊。“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栗乎廟堂之上。”大山嵁巖之下,有一份沉默與天真,還有甘于卑下的淡然。山中光水充足,土壤肥沃,樹長得自由舒展,鳥雀翔集,在漫漫山林中享盡天年。
一個人倘若能秉山而居,他做人可能會崇高厚重一些,有嶙峋的風骨、氣格。我常常在深山的村子里發現不同尋常氣息的人們。
大千世界雖有大千,大千終究是有限的,大千世界到底是樊籠。陶淵明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走進山中,忘掉肉身,甚至忘掉心靈,一切都松弛下來,如樹,如草,如山泉青鳥。陶淵明又說:“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山林即在樊籠之外,山林頓成隱逸。
露
韋應物的詩《詠露》中,“秋荷一滴露”一句極好。最好看的露,是在荷葉表面上的。夏天去湖邊玩,大清早,一池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不沾一絲風塵。
古詩里有太多關于露的句子——
“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花蕊里含著一滴露,在風中搖曳。庭院里的果實熟了,落在臺階上,清脆的聲音擊破空氣。寫實,但充滿了禪意。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夜深露重,一下子讓露的意味也凝重了起來。也非怪此前陶淵明說:“露凝無游氛,天高肅景澈。”
溫庭筠《荷葉杯》前半闋說“一點露凝冷,波影滿池塘,”足以讓人低回。
自然界中的美,需要屏除世俗的喧囂,心靈在極度的寧靜中才能發現。譬如露。這么多年,我都忘了露的模樣,差不多只存于記憶了。小時候在鄉下生活,安靜的晚上,總喜歡一個人站在月光下感覺露意。
露有藥用,鄉下有人患眼疾,每日清晨取竹葉上的露擦洗。《紅樓夢》中薛寶釵平時吃的冷香丸,配方里即有露。
露于我而言,是美。多么美好的早晨啊:露閃爍,蘑菇遍地,小鳥兒在歌唱……普里什文散文集中的句子,讀到有十年了,仿佛今晨的露水一般明晰。我不怎么讀中國文章之外的文章,普里什文那本《林中水滴》卻一翻再翻。普里什文的文章,像露打濕的村莊。
天地間靜寂無聲,一顆又一顆露,停在瓦片、青藤、樹葉上,最好看的是各種瓜果蔬菜上的露,茄子上的露發紫,南瓜上的露翠綠,豆娘翅膀上的露剔透晶瑩如水晶,顆顆點點,無邊無際又無休無止。
露在草葉上聽了一夜草葉的心事,聽了一夜松針的心事,聽了一夜瓜果的心事。心事裝得太多,露的世界很小,一觸即碎。它才是真正的“可遠觀而不可褻玩”吧。
面對原野一片露的時候,心里總有空茫感。譬如朝露呵。
故鄉的野菜
立春前后,疇壟開始耕作了。水牛拖著沉甸甸的犁具,垂頭掙扎向前。農人尾隨其后,手執牛鞭。所謂鞭子,不過是細長的竹枝,并不舍得直直抽打下去。鐵鏵一圈圈掀開沉睡經冬的水田,草腥氣和著泥土味撲面而來。這時田埂上常有幾個孩童在挖薺菜,與犁田的農人一體,成為民俗畫。
薺菜是皖西人暮冬至春時的節令野菜。走在鄉野,不時看到幾個垂髫的女孩拿一把挑鏟或者小鋤頭,挎個筐籮,蹲在地上挑薺菜。薺菜有大小多種,故地所生者甚小,一叢叢扁平的薺菜緊釘在地上,只能從土中將它們連根挑起,又稱“地釘菜”。
在地頭田尾挑薺菜,是最詩意的勞動,因為有的玩,事后還有的吃。薺菜色如翡翠,葉帶鋸齒,吃在嘴里有點澀,輕嚼幾下卻口齒生香。其做法很多,可炒食,能入餡,做餛飩甚宜,故鄉人多用作燙菜。將薺菜放入平菇的香湯里,挖半匙豬油,鮮氣一下子就上來了。碧綠的薺菜在鍋底蕩漾,淡褐的平菇幾番沉浮,入口淡苦,微有清香,能品出苦盡甘來。
薺菜與豆腐可做羹,入嘴濃淡相宜。與臘肉同炒也好,臘肉表里一致,煮熟切成片,透明發亮,色澤鮮艷,黃里透紅,肥不膩口。金黃的臘肉有厚實的富貴,薺菜碧綠,帶著清涼的苦味。一時甘苦自知。
薺菜慢慢老了,開出花。這時節,馬蘭頭來了。
馬蘭頭是故鄉春時常吃的野菜。正月天暖和起來,阡陌間馬蘭頭悄悄冒出新芽。過些時日,新綠瘋躥,即可摘來吃了。明人寫詩贊馬蘭頭滋味之美,讓人忘卻酒肉。
馬蘭頭剁碎后拌豆干、芝麻油,春風拂面,婉約如小令。食后得清涼味,足以抵消酒肉的肥膩。馬蘭頭是常見的野菜,故鄉的路旁、田野、山坡常見,夏秋之交開花,或紫或白的小花。
紹興童謠,“薺菜馬蘭頭,姐姐嫁在后門頭”,讓人浮想聯翩。小時候希望自己有個姐姐。還有紹興人念:“薺菜馬蘭頭,姐姐嫁到瓦窯頭。”說當年瓦窯頭一帶人以制磚瓦、缸甏為業,窮工春時糧荒,野菜度日。聊備一說。故鄉也有童謠:“一二三四五六七,馬蘭開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一串極長的數字,并無寓意,朗朗上口而已。
天氣暖了,河里春水碧綠,與岸上麥苗互映。竹筍冒尖,蠶豆、豌豆開始拔高抽莖,蘆葦爆出新芽。馬蘭頭老了,樹蔭濕地上,紫紅色的襄荷生出花苞,紅彤彤像筍尖。襄荷滾刀切,用青椒爆炒,一時怡紅快綠,艷而不俗。還可以和豇豆、辣椒、生姜一起泡入菜壇子腌食,脆生生可做下飯小菜。
襄荷模樣粗壯,腰身渾圓,它的名字卻風雅,像舊時大戶人家深鎖樓閣的閨秀,云鬢玉顏,柳眉鳳眼,一襲綠蘿裙,撐印花布傘,裊裊婷婷走過,如朵蓮迤邐池水。
襄荷不僅能入饌,也能入藥,馬齒莧更是如此。小時候,背部生癰,紅腫脹痛,不得著衣。照仿醫書,以馬齒莧搗爛敷在患處,竟得痊愈。只是患處留下了一個疤痕,那是故鄉野菜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跡,時間揮之不去。
我喜歡涼拌馬齒莧。取嫩莖夾葉,用開水燙軟,切細放醋,淋上芝麻油,炒吃或涼拌皆可。這道菜做了幾次,馬齒莧入嘴滑嫩清脆,酸酸甜甜,伴著淡淡的清香。后來吃過一次馬齒莧扣肉,肉味豐腴,搶去野菜風致,不如涼拌見本色。野菜之佳美,正在本色。
故鄉的野菜,郎菜名頭最大。
關于郎菜有一故事。說某戶人家兒媳被人強占,逼得新郎逃進深山,饑不擇食,只好以野菜果腹。后來那兒媳逃出家來,見郎君餐風飲露,依然俊朗如初,尋思那野菜有救命養生之功效,故稱它為“郎菜”。故事不可當真。或者故事都當不得真,所以故事開篇都說很久以前,讓后人無法追究。小時候很喜歡聽故事,現在也喜歡,但沒人說了。
郎菜是一種通體微綠泛白、淡紅帶絨的野菜,幽居空谷,隱在深山中,如絕代佳人。放香油小蔥配臘肉清蒸,為風味獨特、溢香爽口的郎菜扣肉。將郎菜曬干泡水飲用,味香爽口。
故鄉的野菜,以野水芹居首。水芹葉子細小,根莖一節一節空心,生在溪水小河邊。小時候去河邊玩,手一扭,順手帶一把水芹回來放辣椒清炒,倘或摻一小塊臘肉,我能多吃一碗飯。野水芹有奇香,入嘴天馬行空,又孤峭桀驁。早春的水芹輕嫩一些,清明后香氣始濃郁,隔水就能聞到蓬勃的野氣。
除了野水芹,故鄉水邊濕地多蔓生有魚腥草,葉肥如蕎麥,莖紫赤色,食來腥氣洶涌,我從來不敢染指分毫。
先秦山坡上有蕨菜和薇菜,我的故鄉亦如是。蕨菜向陽,易采摘,而薇菜喜陰,多長在河溝山谷間,采擇殊為不易。薇菜模樣好看,剛長出來時,頂部曲卷如耳,毛茸茸的。將其棉絮狀絨毛去掉,摘去芽株上的嫩葉,用開水焯透曬干揉搓即可持久柔嫩。
知堂《故鄉的野菜》一文提到的鼠曲草,我鄉也有。做法與紹興人家差不多,春天采嫩葉,搗爛去汁,和粉做糕。
鼠曲草鄉俗稱茅香,驚蟄后,雜草現綠時,從田頭地角、山溝荒地上冒出來,毛茸茸一小撮。茅香莖細長、淡黃色、稈直,葉片扁而質厚,上生微毛,有香氣,捏在手里頗軟。茅香清明時開花,圓錐花序,淡黃褐色,有光澤,花頂成坨。
茅香含香豆素,可制香可入藥,故鄉人只用它做茅香粑。茅香洗凈后搗成凝膏,淡綠如芥末。將浸泡好的糯米磨成粉,添水與茅香膏揉成團,軟硬適中,而后做成粑,以臘肉、竹筍、粉皮之類做餡蒸熟。口味不同,餡可自選。熟后的茅香粑顏色墨綠,香、糍、軟。每年三四月,故鄉人家總要蒸幾籠,飯前飯后貼鍋邊或在灶爐內烤而食之。貪食者,還備有茅香干末,口感不如新鮮茅香。在杭州吃過茅香粑,當地稱為草餅,味道不正,大概是做不得法,選料不精之故。
故鄉的野菜,大抵他鄉也有,那是中國野菜。有種豆腐,如果也能算野菜的話,別處似乎不容易吃到。這種豆腐并非豆制品,食材為樹葉,山民俗稱神仙槎,學名叫作二翅六道木。
神仙槎葉有奇香,放涼開水中揉搓,滲出汁,以柴灰點鹵成豆腐,凝如綠脂,顏色碧翠。即做即食,隔夜即化為一汪碧水,遁去無痕。
神仙豆腐切成薄片,撒上白糖,綠波之上點點冰心,或者加入紅醬,萬綠叢中一朵紅,美味之外,入眼還有絕好顏色。也可以將其切塊,溫水煮開,加鹽、蔥花、芝麻油。以勺舀食,讓人惘然,覺得濁氣去盡,心頭如明月清風拂過。
那日郊游,偶遇野蒜,兜頭有舊事感,三十年前吃過很多野蒜。老家后山都是菜地,春夏之際地角生有野蒜,祖父與我拔回家煎雞蛋。野蒜切成碎末,摻入雞蛋拌勻,以香油煎至兩面金黃。金黃透著碧綠,是金玉滿堂,也是金玉富貴。少年時不喜歡那味道,覺得沖,三十年后再吃,唯有清香在喉。
故鄉是有很多野菜的。童年口感,覺得野菜滋味有詭異的地方。今日吃野菜,大抵閑逸,閑情與逸氣。
故鄉人采食的野菜還有蔞蒿、苦菜。蔞蒿加蒜泥爆炒,有冰雪消融風味。鄉農取鮮嫩的苦菜去根,洗凈過水焯,揉去汁,柔軟如同泡后的茶葉,微微香澀,加小蔥拌炒,清苦里有一些鮮艷,配米粉做成苦菜粑粑,頗讓人回味。
《本草綱目》記載:“南人采苦菜嫩者,暴蒸作菜食,味微苦而有陳醬氣。”南人口腹之欲廣袤,大有神農風范。我怕苦,早年吃苦太多。人生多苦,口味多些清香多些甘甜多些芳美,肉身受用。
野菜的好,依時令而來,順應天時。這里有歲月時序,有鄉土節氣。
故鄉遍地野菜,隨生隨滅,再平常不過,因為長在荒野草澤,有一股淋漓元氣,荒年可溫貧度日。明人朱橚作《救荒本草》,錄四百多種野菜,或葉可食或根可食或果可食,濟世之心拳拳,讀來心熱。豐年里,野菜被好食者采來,入菜入藥入酒入茶,化成唇齒的縷縷滋味,是另一種福澤綿長。人生之富貴不過一飯一蔬自適愉悅。
下雪了
冬天下點雪才有意思,小雪怡情,大雪壯懷。有時雪太大了,出門幾十米竟也白了頭。
人在城里,玩雪是奢侈事,比不得過去在鄉下,可以玩山丘雪樹林雪竹枝雪茶園雪草地雪庭院雪。
玩山丘雪如看古畫,況味如明清山水手卷,底色是蒼莽的。
雪天的山林,青白相間,浮漾濕濕的白光,青而蒼綠,白而微明。清晨起來,站在屋檐下遠望,看見那發白的山頂,大片的是綠的松,馬尾松,密密匝匝。那些馬尾松是亂長的,大小高低不一,一棵一棵挨著,依山勢上下起伏。
竹枝雪是水墨小品。一枝雪,淡淡冷氣裊在三五片竹葉上,況味如宋人宮廷畫,盡顯幽清之態。茶園里的雪一壟壟潔白,沒有風,雪色下平靜安謐。草地雪仿佛一張大宣,不忍落墨不敢落墨,不忍落腳不敢落腳。庭院雪最有趣,像個大饅頭。在山東初見枕頭饃,枕頭那么大,嚇人一跳。
下大雪,庭院的荷葉缸中落滿了雪,盆栽里落滿了雪,老梅枯枝上的積雪一寸厚。
北國雪如豪俠,江南雪是文士。江南的雪是嬌羞的,輕輕然,又像是舊時未出閣的少女,羞澀地飄舞著,落個半天,才放開膽子,肆意地撕棉扯絮簇簇而下。頃刻間,田野皚然。
雪片飛舞,伸手去接,直落掌心,一片又一片,濕漉漉的清涼。
江南的雪下滿湖堤,下滿板橋,下滿勾欄瓦肆,下在農人的黑布衣上,下在文人的油紙傘上,下在烏篷船的斗篷上,也下在田間地頭,下白了山尖,下白了塔頂,下肥了峽谷,下厚了屋檐。在白的世界,時間似已靜止,只剩晝夜。
于一個南方人而言,沒有什么比冬天里下一場雪更動人心。一年后的再次重逢,雪色依舊,人事全非,頗有一番思量。獨臨雪于屋檐下,泡杯熱茶,默默打理著往日歲月遺留在體內的燥熱、喧囂與不安,聆聽雪落大地的聲響。
午后,流連于水鄉弄堂。窄長的石板路,灰褐色的老墻,墻角邊有菊花盆。菊花殘了,枝干兀自立在雪白里。空氣里沒有什么聲音,巷子停滯在舊時雪色的意興闌珊和波瀾不驚中。
空曠的大路邊,天空泛出灰藍色。
記憶里昏黃亮白,暮色由遠及近,田園一點一點隱沒。天漸漸暗下去,萬物像失了魂魄,雞鳴犬吠,牛羊在欄里吃草,貓窩在屋檐下,各種聲音悄然隱在積雪中。依依炊煙自囪口濃濃涌向天上,先是洶涌沉沉的一團團,漸漸變淡,慢慢消散融入虛空。溪流自顧自在山溝里,水滴卻凝在石縫成了冰晶。
黃昏時,鄰人自集市買得酒菜踏步而歸。雪地淡淡足跡,如白紙墨痕。庭院斗大的燈罩亮起,似燃火炬,雪白里有燈光,燈光里有雪白,雪色與燈光輝映。紅塵世俗之樂有真意,當浮一白也。
少年鄉居時,最喜歡下雪。午后朔風卷地,傍晚開始下雪籽,一顆顆在地上滾動,終于飄起雪花。任雪下了一夜,閉門讀書作文,天下可置之度外。清晨起床,窗臺一簇簇雪,屋檐與樹上低垂著冰凌。庭院一夜之間白了頭,田間地頭都白了,夏日十分葳蕤的枸骨樹也白了,泛著蒼青。雪落滿蒼綠的香樟葉,落在肥碩的梧桐樹上,棕櫚一掌掌白,臘梅淡黃的花蕊結數點素心。瓦屋頂上更有厚厚的雪,幾天不見消融。伴雪而居,原野皚皚,人茫然不知時序。每天夜里與祖父圍爐而坐,鄉野傳奇一章章仿佛古老的舊畫。這是有意思的。花月流水的獨語,煙波浩渺的長歌,總不及雪夜清寒令人低回。湛然虛明,天地間一白,憂樂由我。
有雪的夜晚,有月亮更好看。雪光與月光一起,雪光清涼,月光也清涼。輕盈的雪映著昏黃的月亮,滿目清白。沒有月亮的時候,天際滿目星斗,是另外的況味。星光下彌漫著晴朗冰冷的氣息,遠處農家院子人影晃動,隱居著無數壇壇罐罐,家長里短。徹骨的寒氣透過紙窗,冷得人心一緊,紅彤彤的火爐熏了半天,方才滿室春意。
天晴的日子,瓦檐融雪如覆水,像古老的更漏,晝夜滴答。偶爾積雪自屋頂轟瀉下來,如奔馬騰空而至,又像玉堆傾倒,那是時間滾滾的見證。日子一天天淡淡來去,該走的走,要來的來。
記得一年深冬,夜風已經透涼,突然飄起細雪。凜冽的夜,像幽深的古井,片片雪花如寒星點點沉落。雪花透過樹枝零落地上,一片片在燈下晶亮,又清素安靜。庭前石頭清涼,雪片靜靜揚下來,石頭一半清幽,一半明媚,真是動人心腸。想告訴別人雪夜有多美,卻遍尋不到。留在少年記憶的心緒又寂寞又曠遠。
于一泓清冷里看雪,靜中開花,開的是心花。雪里莊嚴,心中怡悅端然。雪下了一夜,山林閑寂,有冰霜氣骨玉精神。冰霜氣骨玉精神是好文章的質地,古人說柳宗元文章如玉佩瓊琚。黃山谷論文,尤重從容中玉佩之音。過去的高人逸士,作山水自娛,常寫雪景。尋常見慣的巒姿,積雪覆白,驀地添出層疊來,寄托歲寒明潔的意思。
今年的雪一直未下,心里念叨了許久。前些天,好不容易有了寒風,聽到泠泠意思,到底沒有下雪,路邊青霜簌簌,倒是厚了些許。每天翻唐人傳奇,總舍不得看完,簡素,古艷,奇崛,應該留幾篇在雪夜里看。如此沉迷,畢竟趣味。
故鄉的雪多年未見了,他鄉的雪也是好的,天下處處有好雪。雪讓天地靜默,遠處山脊鑲玉,樓臺檐角染白,萬木失翠,宛然新生,平旦之氣充盈。茫茫白雪,林木疏落有致,像水墨畫,又有文章的風致。
文章有風有露有花有月皆可喜,但不及霜雪落在紙頁間沉穩。那是天地的雪,村野的雪,草木的雪,也是白茫茫一片往昔的雪,通往明月前身,通往舊日韶華,通往安靜故園。
責任編輯惠靖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