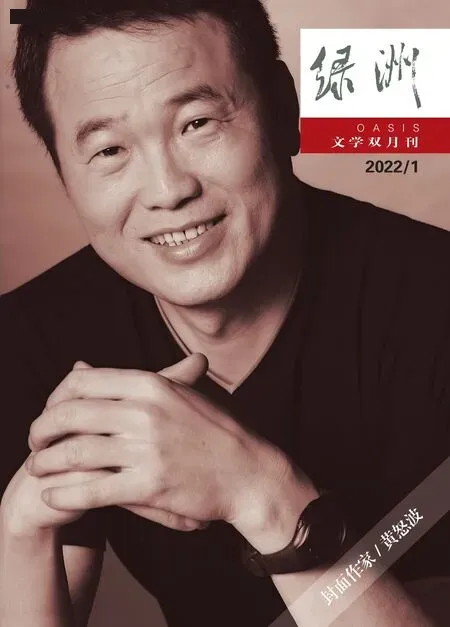鄉野之歌
田鑫
蛤蟆
甘渭河兩岸的人們,一直把青蛙和蛤蟆都叫蛤蟆,為了描述起來有所區別,又把生活在水里的青蛙叫水蛤蟆,把生活在土里的蛤蟆叫癩蛤蟆,它們長相不同,各有樂趣。
在鄉下,癩蛤蟆坐在荷葉上,像個禪定中的智者盤腿坐在蒲團之中。它一動不動,陷入深思。有時候目空一切,所有從它身邊經過的事物,都影響不了它;有時候雙眼有神,目視前方,好像要洞穿一切。
其實,鄉下會發呆的事物很多,比如牛,比如松鼠,可你會發現只有蛤蟆發呆時你才覺得是真的在發呆。持久,有定力。它是在思考生命的來處和去處?還是考慮今天吃啥的問題?也可能都不是,僅僅只是發個呆。
沉默的智者,也有聒噪的時候。在把情欲和愛情作為羞恥的鄉下,只有青蛙才把發泄和繁衍公布于眾。在野外,它們疊羅漢一樣,粘連在一起,然后發出肆無忌憚的鳴叫。有時候,整個村莊都被這種聲音包圍,此起彼伏。后來才知道,這“呱呱呱呱”的叫聲里,包含很多種信息,有辨別、有吸引、有曖昧、有宣泄……在鄉下,情欲從來都沒有如此被釋放過,只有蛤蟆做到了。
叫聲消失,新生命就會出現。小溪邊、澇壩里,到處都是一串串的黑色小果凍一樣的卵,伯母知道,這是最好的雞食,從一小點開始到孕育出蝌蚪,這個過程持續一個月,雞也能吃一個月。黑壓壓的蝌蚪,在小溪和澇壩游走,生命的第一個歷程就這么大張旗鼓然后悄無聲息地完成。
我第一次明白孕育的過程,就是通過觀察一只蛤蟆獲取的,它們無形之中,也豐富了我的童年。多年以后,當我想用鄉下的蛤蟆豐富在城市里長大的女兒們的想象時,過程卻并不是那么順暢。
是一個暑假,孩子們跟我回鄉下,第一夜就被蛤蟆的叫聲嚇到了。入夜,鄉下的黑,比城市里的黑更徹底,除了星光和三三兩兩的微弱燈光外,大地一片漆黑死寂。我們在屋子里看電視,女兒突然一怔,然后做出噤聲的表情,示意我們仔細聆聽。關掉電視的聲音,這聲音準確地落地,是一只青蛙在叫,應該是在院子里。這久不住人的院落,突然有了光亮,蛤蟆就被吸引,從四合院出水的水洞眼里進來,大搖大擺,一點都不顧及別人。我好多年沒見過蛤蟆了,孩子們更是從一出生就沒見過蛤蟆,于是循著聲音用手電筒打了一柱光到它身上。
它像站在舞臺中央的演員,原地不動,女兒先是趴在窗戶上看,距離太遠,就到院子里觀察。剛一走近,她就被它瘆人的樣子咋哭了,半夜才哄好。隔了有一年的樣子,一天,女兒讀維克多·雨果的代表作《巴黎圣母院》,丑陋的卡西莫多出場,她突然就聯想起了那只鄉下的癩蛤蟆。看來,童年那一幕,給她留下了小小的陰影。
在鄉下,大人們抓小蝌蚪喂雞,我們抓小蛤蟆做實驗,或者捉弄女孩子。我們把蘆葦稈折斷,然后戳進水蛤蟆的屁股,朝它的肚子里吹氣,一只干癟的水蛤蟆就立馬豐滿起來,再把它扔到地上或者河里,它就變得笨拙,無法爬行,也不能游動,一只青蛙以生命為代價,給了我們快感,而我們從未就此事內疚過。當然,我們會因為用癩蛤蟆嚇唬女孩子而內疚,那時候,覺得哪個女孩子可愛,就想辦法和她靠近,于是有人抓只癩蛤蟆,放進女孩子的書包就躲在一邊看熱鬧。往往是女孩子“哇”一聲,一只青蛙就在教室里蹦跶起來了,班主任很快就會找出“兇手”,一頓教訓過后,總能老實幾天,而多年以后,再想起曾經被捉弄過的女孩子,就暗暗后悔,后悔她最后成了別人的新娘。
蛤蟆除了可以用來捉弄人,也經常被我們拿來給別人起綽號。樣貌丑或者個子矮一點的人,往往會獲得這一綽號,于是,他的本名就慢慢消失了,綽號取而代之。叫得時間長了,被叫作蛤蟆的人,就有了蛤蟆的特征,比如發呆,比如說話語速很快聲音很大,比如會生很多孩子。有一個長得清秀又高大的小伙,也被我們叫作蛤蟆,他就很不配合我們,總是反過來說你們全家都是蛤蟆。他更愿意讓我們叫他老三,因為他在家里排行老三,前面有兩個姐姐。我們不管他愿不愿意,一直叫他蛤蟆,都忘了他排行老三,也忘了他的本名。
蛤蟆怕火,我們曾經用火烤炙過一只水蛤蟆,后來證實,味道超乎我們的想象。這里想起一個笑話,那些年吃水,要去溝底挑泉水,經常有水蛤蟆浮于水中,人們不但不嫌棄,還覺得有蛤蟆的水才是干凈的水。有視力不佳者去挑水,一馬勺下去,剛好把一只來不及跳走的蛤蟆舀進水桶,中午做飯的時候,這只蛤蟆就成了佐料。飯是白面加土豆,可一家人吃出了肉的味道,最后才發現,鍋里的蛤蟆已經被燉爛。這個笑話,讓大家對蛤蟆肉有了興趣,經常看到有人用繩子穿一串蛤蟆回來。也有人靠吃蛤蟆肉治療一些疑難雜癥,只不過效果微乎其微。
被我們叫作蛤蟆的老三也怕火,可他一生的前三十年,以及以后的余生,卻都跟火脫不了干系。上小學那會兒,校園離家不遠,但要過一道溝,冬天,這溝里陰風嘶吼,穿著單薄的我們,每過一次都要經歷一次冷戰,于是大家就人手一個小火爐,鐵絲做坯泥做外衣,火爐里放一塊炙熱的炭,既能照明也可以取暖,從家走到學校,一塊炭就這樣溫暖了我們。老三的火爐比較獨特,鐵制,還有手柄,擎在手里,像極了古裝電視上的取暖器。它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老三的爹是我們村的電工,他不光掌握著一個村莊的照明,家里還儲存大量鐵制品。于是,老三就有了一個鐵火爐,它總出現在人群的最開頭,鐵引領著泥,走在去學校的路上。
夏天的時候,溝里到處是蛤蟆,我們經常要像跳泥坑一樣躲著它們,老三卻不管,一雙大腳一抬,一會踩到一個,一會踩到一個。他不怕蛤蟆,他憎恨蛤蟆,這可能跟我們叫他蛤蟆有關系。
老三家是在我們上了初中以后衰落的,他的父親死于肝硬化,此前毫無征兆,只說喝了一場酒,吐了一地血,就沒救過來。老三父親沒來得及安排后事,當然也來不及給老三安排好人生。死了爹,兩個姐姐也很快就嫁人了,剩下老三不知所措,書也讀不進去。有一年鎮上征兵,他報了名,去東北當了消防兵。當兵三年,我和老三沒有任何聯系,唯一的關聯是,在村里見到他媽會打聽下他的消息,也是語焉不詳,好像這人從世界上消失了一樣。那段時間,村里的蛤蟆也聽不見聲了,興許是澇壩干涸的緣故吧。
再見老三的時候,他已經復員回鄉了。還是清秀,還是高個,只是身材明顯魁梧,眼神更有光了。聽說他曾被大興安嶺的大火圍困,也曾被在建工地的火舌舔舐,但他完好無損,我們聽他說救火過程,就當聽小說。他講得波瀾不驚,我聽得膽戰心驚,因為有這段經歷,我們之間似乎有了鴻溝,他在那邊,我在這邊。
這個經歷過大火的人,回來的幾年,跟著鄉里的人去城里務過工,開過貨運,賺了一些錢。一次由于醉酒后吸煙,煙頭點著了屋子,他被燒得不輕,搭上了一條腿。你是沒見過,被火燒過的胳膊和臉,像極了蛤蟆的背。雖然他不背著我們,自打那以后,我們說話行事開始有了規矩,再不叫他蛤蟆了。可他的行為越來越像蛤蟆,受傷的腿走路時一蹦一跳,還老是坐在人群里發呆,那時候,我們都不敢去打擾他,總怕有一天,他一張嘴,發出“呱呱呱呱”的叫聲。
磚瓦
磚瓦是鄉下土生土長的兄弟倆。一個敦實憨厚,靠得住,就讓它做地基,做墻,遮風;另一個圓滑、輕浮,好高騖遠,就讓它站在高處,替房子充門面,擋雨。
磚頭出生前,泥土一直統治著村莊里的所有建筑,它們還把自己變成人的樣子,在山神廟里接受跪拜。日子久了,泥土不思進取,看不見自己的短處,也沒意識到會有一天被代替。
而代替它的,是它的遠房親戚——黏土。這些質地細膩的黏土,經過篩揀,加水而和成陶泥,放在坯斗里做成方正的樣子,晾干,碼放在磚瓦窯里,秣秸干柴高溫燒制一天一夜,黏土的軟弱性格就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棱角分明的瓦的氣質。
瓦窯像個煉丹爐,把黏土當孫悟空一樣煉的時候,泥土還在逍遙地曬著太陽,一點也沒有預感到泥土王國即將土崩瓦解。青色的磚破窯而出,鄉下就變了天,灰蒙蒙的泥土,被鐵鍬和镢頭推倒,磚頭順勢把根扎進了大地。
泥土沒來得及總結經驗,就變成歷史書上干巴巴的文字,磚開啟了屬于自己的王朝。磚和瓦來勢洶洶,它們替代了泥土和草簾子,也代替貧窮和可憐的光景。
那時候,整個鄉下都灰土土的。冬天的時候,一場雪降下來,鄉下就消失了,雪的顏色就是萬物的顏色。夏天的時候,樹木蔥郁,綠色高高在上,泥巴小屋,面帶土色,像個被生活壓得抬不起頭直不起腰人,死氣沉沉。磚頭讓鄉下挺直了腰板兒,磚瓦匠讓它們站得筆直筆直,遠遠看上去,就很有底氣。瓦讓鄉下的審美格調提升了一個檔次,一個人從遠處來,看著村子瓦藍瓦藍的,就知道這個地方富庶,安逸,如果看到的還是灰白單調的色彩,他的失望略大于冬天吹過村莊的風。
突然就想起杜甫來,如果那時候他有磚瓦的話,就不怕“八月秋高風怒號”,也不擔心“卷我屋上三重茅”。可惜,他能揮毫潑墨指點文字江山,奈何沒有只磚片瓦,落了個“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的下場。不過沒有磚瓦也罷,有了磚瓦便沒有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是更大的損失。
我們的日子,何嘗不是杜甫筆下所寫的樣子呢?泥土為家的時候,房頂的草簾子和泥巴,經常被雨水侵蝕,滴滴答答的雨,落在屋子里,看著不大的屋子里大盆小盆接著水,土炕上蜷縮著一家子,可憐,但是眼睛里都有光。
這樣的日子大家都一樣,所以沒有人看誰的笑話。磚瓦也不看人的笑話,它們替人保守秘密。白日里人們去田里,磚瓦和木頭一起,替人們保管并不富裕的家底,無非是面柜里幾升新磨的面,衣柜里幾身舊年臘月扯的布,雞圈里幾只等著過年的公雞。那時候,每個院子里的光陰都差不多,也沒人惦記別人家的東西,磚瓦和木頭卻很在意這些,再小的東西,再不值錢,也不能在它們眼皮子底下丟失。
在眼皮子底下的,還有隱秘的夜晚。猴急的男人,等不到娃娃們睡熟,手就溜進女人的被窩,女人將不安分的手打將回去,起身關了燈,夜就徹底黑了,暗夜里的摸索、迎合、喘息和壓抑,怎么能躲得過磚瓦呢?整個夜晚,最讓人臉紅的悸動,在磚瓦的眼皮子底下進行著,它們秘而不宣,替人們保守秘密。
磚瓦變成兇器,還是后來的事。鄉下人心里不擱事,遇到吃虧的情形,就破口大罵,整個村子都就知道誰又占了誰的便宜。有脾氣好的,躲在家里生悶氣,脾氣暴躁的見罵著沒動靜,就把磚瓦摔在地上,撿起磚塊和瓦礫當武器,朝對方的院子里扔。我們也經常兵分兩路,埋伏在各自的營地,沖著對方扔磚頭,也經常把瓦分成幾份,對著水面打漂。被扔得久了,這磚瓦也開始帶上人的戾氣,經常讓人頭破血流。
磚瓦鼎盛的時期,我們剛從教科書上知道,鄉下之外還有城鎮,城鎮之外還有城市,城市之外,是此起彼伏源源不斷的城鎮和城市。磚瓦給鄉下的人鋪了一條通往城鎮和城市的路。我的父輩們,背起鋪蓋,順著磚瓦的指引,到城市里去務工。干的還是磚瓦的事,只不過,城里的磚腰桿更硬,它們有鋼筋水泥撐腰,不光硬,還高,高得站在頂部就能看到鄉下一樣。
城里的磚瓦,就沒有鄉下那么光鮮,它們甚至都沒有自己的樣子,被一層層光亮的外衣包裹著,沒有人知道磚在哪里,又長成什么樣子,瓦也一樣可憐,屋頂已經看不到它的影子,每個單元門口象征性地裝幾片瓦,讓房子有個屋檐的樣子。這樣的房子,在鄉下人眼里,帶著濃郁的魔幻現實主義。魔幻是這看不到磚見不到瓦的房子究竟是房子嗎?而現實則是,不管它是不是房子,只要能在這積木一般的地方有立錐之地,就已經很知足了。
很多人在這里迷失了,他們憑借著從鄉下帶來的手藝,用磚瓦把城市抬高、填滿,然后把自己也安置在這擁擠的地方。他們開始喜歡這看不到磚也見不到瓦的魔幻現實主義生活,把鄉下變成了故鄉。他們穿梭于樓宇之間,幾乎忘記了鄉下的磚瓦四合院和房子。被遺忘的物件,失落、迷茫,很快就淪陷在時光中。摧枯拉朽式的遺忘,讓腰桿挺直的磚腐朽,輕浮的瓦片上,蜘蛛布下陷阱,等飛蟲落網,沒有飛蟲,網就只能被風調戲。磚和瓦再也聽不到暗夜的摸索、喘息、呻吟,只聽見來自房屋內部的炸裂、松動,連落腳的鳥雀,也都只是留下糞便,不說任何話。
終有一天,它們將承受不住這生命之重,轟然倒塌。這時候,磚和瓦這一對身處一室卻久未謀面的兄弟,一定會面面相覷,而又無言以對。
罐子
鄉下的器皿,無非是鍋、碗、瓢、盆、勺、桶、缸、甕、壇、罐、盅、壺這幾類。壇子和罐子因為長得太像,不拘小節的鄉下人,經常忽略它們之間的體征區分,把壇子叫成罐子,又把罐子叫成壇子,有時候,索性將兩者歸為一類。這些肚量大小不一名稱混淆的玩意,盛放過水酒米面油,現在,它們塵封在鄉下,盛放著我的童年記憶。
這么多器皿,最喜歡的還是罐,它們有符合鄉下人品味的身型,有守口如瓶的高貴品質,它們既能內封珍饈束之高閣深藏不露,又能敞開口子置于田野。這和我鄉下的親人們具有一樣的特質,真讓我癡迷。
在鄉下,最小的罐子,是架在火上用來煮茶的,我們把茶葉和水在罐子里交織煎熬的過程,叫熬罐罐茶。鄉下的人,生活的哲學并不是寫在紙上,而是身體力行。在他們這里,生活本身就是哲學。拿熬罐罐茶來說,一個熬字,就把一切說透了。鄉下的水硬,煮熟喝著覺得咸,加了茶葉,慢火一熬,就有了味道,趁燙喝下去,整個人都通透了。放大了說,生活再怎么艱難,只要熬就有希望。
我嘗過燙嘴的罐罐茶,這深淵一樣的罐罐,把清淡的艱澀的日子倒進去,翻騰、蒸發,倒出來的釅茶,比原味的水更苦,可鄉下的人卻喝出了喜悅的味道。我的祖父喝了一輩子罐罐茶,熬了一輩子日子,最后熬出了個啥,我不知道,只知道他用過的那個已經變了形的茶罐罐,后來被我的父親帶到了城里,他繼承了祖父的倔強和執著,也繼承了祖父熬日子的竅門,換個地方接著熬,好像這小小的罐子遲早能熬出什么一樣。
想起童年時光,腦海里經常有這樣的一個場景:清晨,祖父和父親趕著牛去田里,祖母在遠去的牛蹄聲中,將水桶里的水用瓢舀出倒進鍋里,從甕里拿出幾顆雞蛋,打碎盛在碗里,和上白面,然后燒水,水燒到七分,開始翻滾,把雞蛋倒進去,攪勻,加上蔥花,再滴出幾滴油,一鍋滾燙濃香的雞蛋面糊糊就做好了。她用勺子一勺一勺將雞蛋面糊糊舀進罐子里,封好,然后喊我把罐子送到山上去。一個罐子,兩個青花敞口大碗,三個饅頭(有一個是給我的),在我的籃子里,跟著我穿過巷子,到山上去。
這是一只圓形的壇子,釉質粗糙,摸上去有大地的質感,這個出自于本土瓦窯的劣質瓦罐,此刻就放在田壟,滾燙的雞蛋面糊糊,在穿過鄉間小路的時候,已經降到最適合送進肚子的溫度。我掀開蓋子,香氣就從罐子的口中彌散開來,祖父和父親喊停耕牛,向我靠近。歇下來的耕牛,時不時朝它看一眼,整個田野里,罐子自帶光芒和熱氣,顯得耀眼。
我能察覺出來,荒野確實向罐子涌起有看不到卻能感知的氣息。多少年以后,再回想這一幕,才能理解一個圓圓的罐子置在地上,有君臨四界的氣勢。這只灰色無釉的罐子,正如美國詩人史蒂文斯所說,它不曾產生鳥雀或樹叢,與別的事物都不一樣,但是那一刻它卻用自己圓潤的身體和小小的光芒,在我心里撒下了種子。
罐子里裝過水,清澈的水、渾濁的水、燒開的水、變涼的水、隔夜的水……罐子原本就是為了水而生的,就像鄉下的人為大地而生。它粗糙的外表之下,是趨于圓潤但又扎手的堅硬,內心卻異常柔軟。它面帶土色,也夾雜著顆粒,這雀斑一樣的物質,更讓它與人之間有了某種相近。在鄉下,罐子是另一些無法行走的人,而人,是行走著的罐子。后來,人們發現,罐子和人之間是可以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如同茶和水。
人們把生活藏在罐子里,有時候也把對生活的氣撒在罐子上。鄉下的男人性子大,遇上麻煩事,除了打老婆,就是砸東西,碗和碟子是最常見被砸物件,罐子有時候也會被連帶。我們家最漂亮的一個罐子,是祖父分家的時候悄悄分給我們家的,母親用它來裝胡麻油,一家人的油水在它的肚子里,有一回父親醉酒,砸碗的時候,勁用得大了,摔到罐子上,罐子瞬間就破了,油像父親的壞脾氣,蔓延開來,母親急得一把抱住了罐子,而我則伸出舌頭,朝流了一桌子的油舔去。隨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家的飯菜寡淡無味,直到母親叫人把罐子補好。這個帶著傷疤的罐子,后來去了哪里我已經搞不清楚,只知道那罐子胡麻油,流出來的時候,一家人的心和罐子一起碎了。
罐子里裝過甜蜜,也裝過酸楚。甜蜜的東西很多,我最中意的是胡麻油和土蜂蜜。酸楚的范圍很大,寒酸的生活也可以裝在罐子里,一是可以防止它丟失,還能讓光溜溜的罐子保守清貧的秘密。我要說的酸楚,來自一種叫醋的液體。每年夏天,祖母總要把廚房騰出來,做一個鄉下女人該做的事情——窩醋。窩字,在這里完全脫離了它的基本釋義,引申為釀的意思。至于它的詞性,就有些不好歸類,你說它是動詞,那口被祖母安置在廚房的大缸卻紋絲不動,大熱天的,還用被子裹得嚴嚴實實,像坐月子的女人;你說它不是動詞,大缸里的小麥、麩皮、玉米、豆子,在輔料的作用下,暗自洶涌,這些物件裹得久了,就發出酸腐的氣味,奶奶一點都不知道,還嫌不夠酸。到了神秘時刻,祖母就把我們趕出屋子,她一個人守在土炕上,拿一個圓形的大罐子,在大缸底部的小孔里插上竹子,憋了許久的液體泉水一樣涌出,整個四合院就酥了。
我一直癡迷于發掘人與罐子的關系,有一段時間,我一直被一張油畫所吸引:深色的背景下,一個裸體的少女,扛著一個水罐,水泉一樣傾斜而出。少女柔嫩的腳下,質感堅硬的青灰色巖石,即刻濕潤,周圍零星的幾朵嬌小野花,綻放了,有安靜、純潔之美。少女以同樣柔美的曲線,站在畫中間,用兩手扶持著左肩上的水罐,那清澈的流水正流過玉雕一般的軀體,沒有表情的臉上,是純潔、無邪的神態,美麗的大眼充滿童稚,如泉水般寧靜、清亮。說實話,一開始,我被這年輕的裸體所吸引,很快目光就轉移到了她手里的陶罐,水緩緩地流出來,少女微屈的雙膝,和舉起陶罐所表現出的肌肉曲線,讓我知道了什么叫典雅,什么是純潔的脫俗之美。很長時間,我都在想這幅畫,想裸體的女孩子為何抱著一個罐子。這個問題沒有答案,我也說不清楚去哪里尋找答案,就像你永遠不知道鄉下的罐子會被用來裝什么一樣。
在大地上過完一生的鄉下人,信奉土地,一輩子也離不開土地,死了埋到土里,才覺得踏實。他們用棺材安置一個人,但城里人用的是罐子。這事是我后來才知道的,我的一個在渭河一帶有些名聲的遠房親戚,一直在外地生活,他的根留在了城市,但是臨終的時候,他囑咐孩子一定要把他送回鄉下安葬,城市里的人去一趟火葬場就交代了一生,這個遠房親戚也沒能免俗,家人把他帶回鄉下的時候,用一個精致的罐子盛放了他的骨灰,村里的人把罐子當棺材埋進祖墳。這事之后,罐子在村里的地位有了變化,人們才知道,它們也能當棺材收留人。人用了一輩子罐子,最后卻被罐子帶走了,這看上去多像一個輪回。
名字
一個人一旦擁有了名字,名字就替這個人活在世上,即便這個人死了,看不見了,名字還活著,不管是在墓碑上,還是在別人的嘴里,名字繼續代替這個死去的人,領受贊譽和詆毀。
我的祖父是把名字留在大地上的人,他去世多年以后,還有人在看到我的時候就想起他,并試探性地打聽,我是不是誰誰誰的孫子。當他們從我的面孔、身形上看到我祖父的影子時,祖父的名字就再一次被提起,他們帶著惋惜和贊揚的語氣,讓我從陌生人那里聽到了對祖父的肯定,我覺得,他這一生沒有白活,他也沒有浪費那個名字。
因為有了這個經歷,我就不自覺地想讓自己也做一個好人,這樣的話,我的名字就能繼承祖父的優良品質,我這三十多年就沒有讓名字辱沒,我就對得起這個名字,也只有這樣,這個名字才會給我帶來好運氣和好名聲。
名字能帶給一個人好運,也能讓一個人倒霉,好運氣的名字,能叫一輩子,下輩子也有人叫,倒霉的名字叫不了幾年就突然消失了。村里每隔幾年就有一個名字叫著叫著便沒了,很不幸,我們家兩代人里就有三個早夭,一個在盛年的時候歿了。這兩個早夭的,有一個是我的大伯,饑餓年代出生,很不幸死于一場持久的痢疾,他死后,原本排行老二的二叔,代替了他的位置,成為大伯。他和他的名字一起消失。雙胞胎來自三嬸家,兩個一模一樣的男孩子,剛把驚喜送到我們家,緊接著劇情就變成了悲傷得讓人無法接受的內容,早產的孩子,連名字都沒來得及起,就告別了人世,而沒有名字這事,讓雙胞胎的早夭,變得更為沉重。那個在盛年歿了的,是我的母親,她本來活得好好的,每個認識她的人都覺得,她是個難得的好人,可是好人偏偏命不長,她的名字里有一個“梅”字,這個帶著芬芳的名字,最后把霉運帶給了我們家,她的名字叫著叫著人就沒了。多少年后,再提起早夭的和歿了的親人,祖母表情平淡,我知道,那些年她的眼淚已經流光了,對于這些夭亡了的名字,還有沒來得及起名字的親人,她再也哭不出來。那些人的名字,那些人的模樣,悄悄在她心里烙上了烙印。我相信,在我們家,只有大字不識一個的祖母,在心里給亡故的人和名字立著碑。
在鄉下,名字還有叫魂和詛咒的作用。鄉下人總能把常見的疾病和鬼魂掛上鉤,一個人突然暈厥,就說他的魂丟了,暈厥的人確實像丟了魂似的,軟塌塌躺著,還沒等赤腳醫生來,上了年紀的人就開始給他叫魂。我的魂就丟過,所以我清楚地記得叫魂得整個流程:一個敞口青白色的碗里裝滿水,一把筷子立在碗中,上了年紀的人開始繞著丟魂的人燒紙錢,朝遠處扔掰碎的饅頭。叫魂的詞我已經記不清了,只知道,我的名字被反復地呼喊著,后面加一句:回來回來,回來回來……我的魂就這么被叫回來了,赤腳醫生來的時候,我已經活蹦亂跳了。我一直癡迷這個解釋不清的過程,可是它的法力似乎是有限的,因為我的母親在彌留之際,這個辦法并沒有奏效。
沒有奏效的還有詛咒,那時候討厭一個人,罵不過他,又打不過他,心里的怨恨無處發泄,就把討厭的人的名字寫在墻上,然后朝著它扔泥巴,好像那些厭惡就能被泥巴蓋住一樣。解完氣后才發現,這根本就不頂用,被我們詛咒的人,照樣好好地活在村莊里,只不過那些被我們扔了泥巴的墻,看上去像被唾棄的人一樣,斑駁、失落。后來我們也把名字寫到樹上過,多少年以后,樹長到很粗很高,那個名字也變高變大,叫這個名字的那個人,還活得好好的。看來我們的詛咒,這些名字從來沒有認領過。
被名字認領的,是命運。一個人和他的名字一起,不知要經歷多少事,人的命和名字的命一模一樣,每個人都活在各自的命,命鑲嵌在每個名字里。那些五花八門的名字,就是各種各樣的命運。誰誰家的,是我們村對女人的稱謂,也是我們村女人的命。那時候看電視上的宮斗劇,有所謂的母憑子貴,就覺得,在母憑子貴這事上,我們村竟然和歷史掛著鉤,可不是,創造我們村歷史的女人們,沒有自己的名字,只能跟著男人或者兒女叫,可不就是母憑子貴?兒女的名字起得好,女人的名字就叫得響亮,兒女的名字起得不好,女人們也就背一輩子。同樣,兒女的命不好,女人的命也好不到哪里去。誰誰家的女人,就像木偶一樣,被別人的名字提著,在村莊里活著,她們活完一輩子,臨終該有自己的名字了吧,可是誰誰家的時間叫久了,人們就連她本來的姓名都忘記了,按照鄉下的習俗,最后在墓碑上寫下某某氏。這方面來說,女人在村莊里活一輩子,還不如花花草草。在鄉下,花有花的名字,草有草的名字,有時候花也叫草的名字,草也叫花的名字,但是它們是獨立的,不依附于別的花花草草。
女人在名字上沒有選擇權,但是少年們有,并且他們的覺醒,或者說和村莊的戰斗,往往從改名字開始,就像一個朝代要代替另一個朝代,先改了國號再說,至于隨后的革命如何,另當別論。
轉運,一出生他爹就這么叫他,按理說,這個名字很不符合村里起名的規律,既沒有用村里的物件,也沒有按照族譜里的排序,從字面一看,能看出大人們寄托在他身上的愿望。上一輩子人,在土地上折騰了一生,最后被土一口吃了,只留下一抔黃土,代替他們活著。這一輩子人,不想再重蹈覆轍,可是輪到自己走了,這路怎么走才能和上一輩有區別,大人們一點辦法也沒有,于是就在孩子身上下注。先給他們起個好名字,看能不能靠這個名字轉運。
十幾歲的時候,本應該上學的轉運,告別了父輩們的生活方式,背著行囊去了內蒙古。他走的那天,我們去看熱鬧,所以對當時的情景記憶深刻:他爹給他放了一掛鞭炮,在鞭炮的炸裂聲中,在煙霧和塵土中,在我們的注視中,轉運頭也不回地走了,他走的姿勢,跟電視劇里的一模一樣,那時候,我覺得這是村里最帥的姿勢。
后來,他真的就轉運了,說是在內蒙古攢下了家業,買了樓房,還把他爹他娘接了過去;再后來,說是他把有病了的媳婦送到丈人家,又娶了更年輕的女人過日子。總之,關于他的故事,基本上能作為我們村的教科書了,很多人鼓勵孩子,就讓孩子向轉運學習,至于學習什么,家長們不知道,孩子們就更不知道了。
很多人都說,他是村里靠名字轉了運的人。我對此很好奇,就在微信上問他。可我發現,轉運已經不叫轉運了,在微信里,他叫田飛。私下里琢磨,他應該是覺得轉運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人生進入新的征程,所以要向更高的天空飛,因此直接叫田飛。而在村里的微信群里,我看到好幾個叫田飛的,他們以前叫前程、彥龍、旺盛……現在他們收起小名,混在人群里,說著普通話,他們輕盈地飛翔,鄉下的血脈不斷地給他們輸送著營養,讓他們飛得更高更遠。
從這個意義上說,村莊并不是狹隘的、小氣的,相反,它用寬廣的胸懷,讓改了名字的人滑行、爬升,然后默默注視著我們遠行。這樣,飛得再遠,都不會覺得孤單,因為不管哪一天,不管已經叫什么名字,村莊一直給我們留著降落的跑道和機場。
在村莊里,每個名字代表著一個人,每個人的名字只要在村莊里,這個人就還在村莊里,但是改了名字的人,或者名字突然消失的人,越來越多,村莊開始變得輕盈起來。坦白說,我也是改過名字的那個,但是名字這個套在我頭上的魔咒,并沒有讓我因為改名而變得和別人不一樣,相反,我不管怎么改名,到了春節、清明、端午、中秋,到了吃玉米吃土豆的日子,總覺得有人在家鄉的位置呼喊我,內心的河流就不自主地朝家鄉的位置匯合。這么多年,我背著一個改過來的名字,行走在村莊以外的地方,以為這樣就能逃離過往,但是當有人叫出我的小名時,我又被打回原形。而當我跪拜在祖父的墳前的時候,看著墓碑上刻著的一大家子人的名字,才發現,不管我們以什么樣的名義各奔東西,我們的名字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從來就沒有分開過。
照片
有一張照片我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了,它是我和母親唯一的一張合影,一寸大小,邊緣齒輪狀,照片里母親站在院子里的土墻下,我和妹妹在她身邊追逐,攝影師摁下快門的瞬間,我的手拍在屁股上,俏皮地給妹妹一個鬼臉,而母親則直視鏡頭,對這一切一無所知。
這張黑白的一寸照片,頗有一些現代性,因為畫面中母親并不是像傳統的拍照姿勢一樣懷抱孩子,也不端坐于椅子之上,我們也沒有為了照相而刻意收拾,其實,收拾也無非是撣去身上的土,母親把包裹頭發的頭巾扎緊一些而已,還不如隨意。
照片上,沒有看上去還像點樣子的廂房或者別的地方為背景,可能我們原本不是為了拍一張像樣子的全家福,而是我們一家三口隨意的狀態,被攝影師以生活的瞬間準確地抓取。
這張照片拍出來沒多久,母親就從生活中徹底消失,且永遠定格在照片里。此后的很多年里,這張照片都不在我的視野里,我是后來在一本母親用來夾鞋樣的舊書里找到它的,不知道為什么,它并沒有出現在相框里,也沒被玻璃板壓在桌子上,可能母親也是隨手把它夾進舊書里的。
我發現它的時候,有一種苦苦找了很多年的母親被找到的興奮感。我珍重地把它夾在嶄新的相冊里,想母親的時候就翻出來看看,可是它后來卻不見了,沒有任何征兆,就像當年母親消失一樣。
有那么一段時間,我把它的消失放在腦后了,可又有那么一段時間,我特別著急想找到它,我怕再找不到,母親留在我腦海里的樣子會愈來愈淡,可是,越想找到它就越找不到。我把家里能翻開的東西都翻了一遍,我找到了舊時的糧票、借據、畢業證書以及兒時的接種證明,偏偏就是找不到它。
我懷疑,這張照片用自己的齒輪劃出了一條路,然后偷偷溜走,它不想幫我留住那個遙遠的瞬間,不想在我懷念母親的時候給我提供影像。一旦物要刻意和人保持距離,你永遠也沒辦法找到它。于是,我放棄尋找它,就像當年放棄尋找母親一樣。
那些年被我們放棄的東西還少嗎?每次回鄉下,我都會去鄉下的小學看看,這里留著我對童年最美好的記憶:菊花開著的時候,我們在樹蔭下蕩秋千、打籃球,上課鈴總是在最精彩的那一刻響起,我們一哄而散,空留秋千在風中搖曳,旁邊是逐漸停下來的籃球。
走在荒蕪的校園里,我使勁回憶過去,卻發現除了剛才列舉的一些畫面之外,其他細節根本想不起來,譬如,那些陪伴過我的同學們都叫什么名字、長什么樣,老師們在什么情況下才會打我們,那些被傳來傳去的字條最后都去了哪里?等等。
很多事很多人都想不起來了,只想起我們用童年的大半時光,把偌大的校園填滿,然后又一哄而散。每一年,散一批,再來一批。一批又一批,能留下的記憶不多,唯有畢業合影。
我一直不喜歡合影。18歲之前,有過三次合影。第一次是小學畢業,我們幾個稚嫩的還不理解畢業意味著什么的娃娃,把語文老師和數學老師圍在中間,拍下人生第一張合影,攝影師說了一句“看這兒”,我們就被定格在一張彩色的紙上。
去領中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一張畢業證里夾著的這張照片,宣告我們在村里的讀書時光結束。我拿著錄取通知書到鎮上報到,遇到的全是陌生的面孔,我們從不同的村里來,被分配到不同的班級里。我以為中學和小學沒啥區別,無非是換個地方念書而已,可很快就發現,初中和小學是兩個概念,小學我們熟悉到知道每家午飯吃的啥,而初中想熟悉彼此,需要經過害羞,經過試探,經過字條的指引。
在鎮上的三年,比鄉下的五年快多了,我都沒做好準備,就要拍第二張合影了,相處時間雖短,但是和第一次不同,這一次合影,心里竟然生出了不舍。我以為,所有人站在一起,被拍進照片里,這些人就再也不分開了,可是,誰也沒想到,坐在一起拍照竟然成了這群人最后一次在一起。現在,照片里的每個人都看著,我有些慌亂,第一次對應接不暇這個成語有了切身體會。他們看著我的神情,還是二十年前的神情,此刻我應該感動,但是并沒有,內心泛起的卻是陌生的漣漪,忐忑不安的漣漪。他們對于二十年后的我,竟然沒有絲毫的陌生感,或者說,我本身就是陌生的,他們只不過是用本能的目光在打量一個陌生人。我說不清楚。
鄉下的孩子畢業,沒什么貴重物品可以作為紀念,攢錢拍的個人照片就成了唯一能拿出手的禮物。在照片后面寫上:某某留念,就等于我的人生中,你到此一游過,潛臺詞是勿忘我。可是,照片哪有記憶穩妥,存放在腦海里,隨時可調動,可照片不行,被夾在什么東西中間,什么東西丟了,照片也就丟了;放置在相框里,相框被歲月磨去光澤,照片也漸次變白,最后只剩下一張模糊的紙。
在時光面前,沒有人是贏家,即便是被記錄進歷史的人,他們最終也只留下一張張照片,沒有人能活得比一張未曾遭受意外的照片壽命長久。人知道這個道理,所以從未試圖和一張照片比生命的長度,他們懂得利用照片,記錄和封存人一生最重要的時刻。
我丟掉了母親和母親的照片,四合院丟掉了我們,我們一大家子,在同一個四合院生活過,可沒有出現在同一張照片上。現在,我們的全家福以城市為背景,等于一條河流生出來支流。而祖父祖母,以照片的形式,母親因為根本沒想過要準備照片而缺失一張遺照,只能以紙牌位的形式坐在桌子上,他們三個人替我們守著這個家,他們沉默不語,他們不用惦記。
責任編輯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