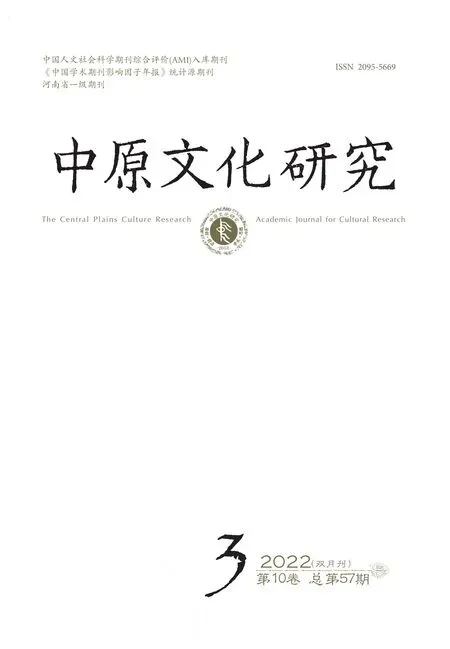朱熹論“性”與“命”*
史少博
在朱熹的理論中,“理”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天地萬物的形成都是“理”賦予其中,加以“稟氣”而成“形”。世間萬物根據“理”稟氣而生之后,萬物的“性”便隨之具有了,即:“先有個天理了,卻有氣。氣積為質,而性具焉。”[1]2依“理”氣聚而化生人,“性”具焉、“命”具焉。萬物皆有“理”與“氣”,“氣之聚,則理亦在焉。”[1]3“理”與“氣”不相離,“理”是本,“氣”之聚集處,“理”便在其中,“氣”如果不凝聚,則“理”也無所依附。“氣”能造作、能凝聚,然而“理”只是精潔空闊的世界,既“無造作”[1]3,也“無計度”[1]3。世間萬物皆有“理”、世間萬物皆有“氣”、世間萬物皆有“性”、世間萬物皆有“命”。關于朱熹論“命”與“性”,分析如下:
一、“性”與“天命”及“性”與“人命”
(一)“性”“天命”“人命”之內涵
關于“性”的涵義有多種,并且關于“性”的解讀也是中國古代哲學家經常探討的話題。早在《易傳》中就有“成之者性也”“各正性命”的說法。在朱熹的理論系統中,“性”即“理”,具有本體的意義。朱熹認為天下萬物都有“性”,沒有無“性”之物,也沒有無物之“性”,有物必有“性”。人與物皆有“性”,但“人”與“物”的“性”不同,“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論偏塞。
古代哲學論“命”的視野也有不同,“天命”“人命”中都有“命”字,但是意義不同、指向不同,并且“人命”和“天命”中“命”的內涵也不同。“人命”指向具體的個體人之命,“人命”具有形而下的意蘊;“天命”指“天”的命令,這里的“天”不是自然之天,在朱熹理論中,這里的“天”等同于“理”,“天命”具有形而上的意蘊。
(二)“性”與“天命”
關于“性”與“天命”之關系,《中庸》中就有涉及,《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就把“天命”與“性”聯系在了一起。這里“天命之謂性”,就是說按照“天”的命令將具有固有本質的“性”賦予人,人受“命”于“天”而成“性”。正如朱熹所言:“命猶誥敕,性猶職事,……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1]82
“天命”即“天”的命令。正如朱熹指出:“‘天命之謂性’,亦是理。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職於君。”[1]63朱熹認為“天命”之“性”,沒有偏全,因為人皆稟了天地之理,并無差異;人的品質因人而異,是因為稟天地之氣的厚薄明暗造成的。朱熹認為“天命”就像“君”的命令,我們可以想象,“君”之“命令”的形式有可能是一樣的,但“君”之“命令”的內容不可能是一樣的,故而“天命”形式相同,而“天命”內容各異;“受職”于“君”的形式相同,“受職”于“君”的內容亦會不同,故而朱熹認為“天命”之“性”沒有偏全,也只能是就受“命”之“理”而言。朱熹進一步解釋道:“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1]58朱熹又曰:“問:‘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札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1]64“告札”是古代授官之符,按照朱熹的闡釋,“命”就像授官之“符”,“性”就像“合當”做的“職事”。
(三)“性”與“人命”
“性畢竟無形影,只是心中所有底道理是也。”[1]63從此角度,朱熹認為“性”與“理”相同。朱熹所說的“性”相同,也只是“天地之性”相同,而“氣質之性”則不同。
朱熹理論中所論及的“理之命”“氣之命”,也基于“人命”而言。朱熹認為人既有“理之命”,同時也具有“氣之命”;“理之命”“氣之命”是“人命”所具有的二重性。值得注意的是:“天命”“理之命”雖然具有形而上的意蘊,但是都離不開“人”,如果離開人也就無所謂“天命”“理之命”,因為“天命”是“天”對“人”的“命令”,“理之命”是依據“理”借助“氣”賦予“人”之“命”。“天命”是“人”無法操控的,是人力無法改變的。“理之命”是“天”依據“理”賦予人的“仁義禮智信”,“人之初”就具備了“理之命”,也就是說個體的人在“人之初”先天稟賦“仁義禮智信”之“理”是相同的,雖然“人之初”稟賦給每一個人的“仁義禮智信”之“理”同,但是每個人受“稟氣”影響,“人之初”的善性之顯發受到阻礙,由此,朱熹認為在“仁義禮智信”方面人“后天”是可以修養的,根據人的努力,人的“仁義禮智信”方面的修養是可以改變的,由此,可以說“理之命”是人“后天”能改變的。朱熹所說的“氣之命”卻是不能后天改變的,朱熹所說的“氣之命”是“理”與“氣”的混合物,不僅僅是“氣”的產物,而且是人依“理”而稟氣的產物,朱熹認為“氣之命”決定人或富貴、或貧賤,或長壽、或夭折等,是人自身所無法操控的。朱熹的“理之命”“氣之命”中之“命”,都必須借助“氣”才能形成。
朱熹認為人“命”雖有不同,但“性”本同。“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1]58人“性”本同,只因為“氣”稟異,氣質則異。朱熹又曰:“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1]89朱熹認為“性”即“理”,如日光本是相同的,只是每個人接受的日光多少有所不同。由此,朱熹認為每個人的“天地之性”相同,而“氣質之性”各異。那么“天地之性”與“理之命”都是以“理”而言,相對于個體的人來說,“天地之性”與“理之命”都是相同的;“氣質之性”“氣之命”都是兼氣而言,相對于個體的人來說,“氣質之性”“氣之命”都是不同的。
二、“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
(一)“性分”是以“理”言之
朱熹并沒有像董仲舒和韓愈那樣把“性”分為三品,而是把“性”分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朱熹認為人之“性”是“理”“散在處”,“性只是理”[1]85。從另一個角度看,人依據“理”而生,也就是“生之理謂性”[1]82。“性分”必須依據“理”而分之,故而,生之為人都賦有“天地之性”。“先有個天理了,卻有氣。氣積為質,而性具焉。”[1]2朱熹這里所說的有“氣”有“質”而具有的“性”是指“氣質之性”,故而,生之為人也都被賦予“氣質之性”。而“氣質之性”之前,就有“天理”了,由此,無論“天地之性”,還是“氣質之性”都不能離開“理”,“理”始終是本體,兩者都依“理”而言。
朱熹認為人在沒出生之前,“理”就存在那里,當人出生后,通過“理一分殊”,“理”就被賦予了人而形成了“性”,在這層意義上“性”就是“理”,是“理一分殊”了的“理”。天在人化生之際賦予其“理”,猶如命令。在人出生時,根據各得其所賦之“理”,被賦予五常(仁、義、禮、智、信)之德,就是所謂的“性”。按照朱熹的理論,所賦予人的(仁、義、禮、智、信)純善之性即“天地之性”,從“性即理”的命題來看,本善的性,從圣人到凡民,無一例外地稟受著同樣的“天理”,只不過在形成人格形而上資質的氣域,每個人不僅稟賦“天地之性”,而且同時稟受“氣質之性”。“朱熹闡述人的普遍性(作為本然性的成分天賦的界限),更進一步說明‘性分’形而上展開的職別(作為人類社會的構成成員個別分配的職能性資質的分界)構成。‘性分’有男女、賢愚等個別差異,在與前人論述有關的部分,是人格的核心,相當于宇宙生成中的‘理一’(普遍的根源的原理),職分得到了男女、賢愚的個體差異和對事物的適不適合等具體的資質的差異在成為生物學存在(形而上的存在)之后,對應于根據個別的存在性而設定的‘分殊’(在普遍原理的各論展開中導出的個別理論),理一和分殊不是兩項對立的概念,‘理一’在生物學存在之前形成人格的核,在生物學存在后,以‘理一’為核心的表層形成‘分殊’。也就是說,以人為中心,在表層形成了個別存在的個別原因(個性)。”①朱熹把“性”分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依據“理一分殊”闡釋人與人之間“天地之性”的共同性,并且采用“稟氣”說闡釋了人與人之間“氣質之性”的差異。
(二)“命分”是“兼氣”言之
“關于‘命’,自古以來有形形色色的分類。孟子《盡心·上》有正命、非正命之分,莊子《列御寇》有大命、小命之分,《孝經援神契》有受命、遭命、隨命之分,王充《論衡》有國命、人命、壽命、祿命之分,……朱子將‘命’分為兩大類:理之命、氣之命。”②朱熹認為:“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令之謂命也。然命有兩般: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稟不同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之性。”[1]1463朱熹認為“命”是“天”賦予人的,然而“命”有兩種:一種是以“氣”而言,人生之初因人而異所稟清濁厚薄不同之氣;另一種是以“理”而言的“理”之“命”,人生之初所稟賦“仁義禮智”之“命”。
朱熹雖然把“命”分為“理之命”和“氣之命”,但是卻認為每個人被賦予的“仁義禮智”之“理之命”是相同的。朱熹所說的“命分”是“兼氣”而言,是指“氣之命”之別。“氣之命”之差異,主要是每個人“稟氣”的差異造成的,因為“天命”不能分,“理之命”也不能分。朱熹認為“命”之分是由稟氣而定,他指出:“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1]81朱熹認為“人”之“命”是“生時”所稟“五行”之“氣”所定,“五行”又各有其性,人所稟“五行”“陰陽”之“氣”又各有厚薄、明暗。朱熹說:“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1]9因此,人的“命”與“稟氣”有關,稟得“氣”厚其“命”就會福厚,稟得“氣”薄其“命”就會福薄。
無論是“理之命”,還是“氣之命”,都離不開“氣”,因為“天”通過“氣”而“命”于人,人通過“氣”接受“命”,即:“蓋天非氣,無以命于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理”是天地萬物的根據,“氣”是天地萬物化生必不可缺的要素。由此,無論是“理之命”和“氣之命”之分,還是“氣之命”的不同等級之分,都既是以“理”為本質、本體的,又是“兼氣”而言的。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認為“命分”是“兼氣”言之,“兼”字體現了“命分”不能脫離“理”而言,而應看到“理”和“氣”兩者之間的關系。
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與“理之命”“氣之命”之關聯
探究“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理之命”“氣之命”之關聯,首先要分析“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理之命”“氣之命”的內涵以及朱熹對其的闡釋。
宋明理學家們常常把“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對應起來。張載從氣本體的角度闡釋了“天地之性”及“氣質之性”,他認為“天地之性”是人稟“太虛之氣”而形成的“人之初”之性,“氣質之性”是稟受陰陽之氣而形成之性。朱熹從理本論的角度闡釋了“天地之性”及“氣質之性”,他對“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有不同的理解。朱熹從“理”“氣”維度論述兩者,認為“天地之性”是專指“理”而言,而“氣質之性”是指“理”與“氣”雜而言。正如朱熹所說:“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1]67朱熹認為“氣質之性”是“理”墜入“人”之后與“氣”結合的產物,在此過程中“理”被“氣”部分遮蔽。“氣積為質,而性具焉。”[1]2“天地之性”雖然相對“理”而言,但是“天地之性”的“性”不能簡單地被認為等同于“理”,只是“理”被賦予人而成之“性”,在此意義上“理”是指“性”的本體,但是“性”也是“理”,“性”也具有本體論的意義,即朱熹所說的“性即理”,由此可以說“性”是人得以生之“理”,“性”使得“理”實體化而被賦予人,也就是說人沒出生之前,作為本體之“理”不能稱其為“性”,只有人出生之后“理”有存放處才可以稱之為“性”,故而對于現實的人而言,其“性”只能是本體之“理”的體現。人之形成是“理”與“氣”的結合,人之形成過程中“理”借助于“氣”而形成“天地之性”,“理”與“氣”雜形成了“氣質之性”。總而言之,在朱熹那里形成了“性”二元論,“性”有兩個來源,即“理”來源和“氣”來源,從而把“性”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朱熹認為“天地之性”是“純善”之“本然之性”,無不善,是與生俱來的“人之初”就存在的,而人之“氣質之性”有善也有惡。朱熹認為“天地之性”是“理”在人身上的表征。“天地之性”是“本然”“本體”意義上的“性”,還是“理”在人身上的呈現。日本近藤正則對此也有相應的論述:“‘氣質之性’也是生來就有的個別資質,相對于‘性即理’的‘本然之性’,從可能成為感知對象的形而上的資質這一點來看,根據自覺的意識性的功夫和存養留有改良可能性的余地。”①
“理之命”“氣之命”是朱熹的創造性闡釋。朱熹將“命”分為“專以理言”的“理之命”和“專以氣言”的“氣之命”,并且朱熹認為無論是“天命”還是“人命”都與“氣”有關系,沒有“氣”,“命”無法被授予。正如朱熹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1]66故而,“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與“理之命”“氣之命”四者是由“理”“氣”把它們交織在一起,無法分割的。
關于“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與“理之命”“氣之命”之關聯,朱熹并沒有詳細闡釋,但是據其理論,我們可以作如下分析:朱熹的“天地之性”“理之命”二者都是“以理言者”;“氣質之性”“氣之命”二者都是“以氣言者”。值得注意的是:“天地之性”“理之命”雖然是“以理言者”,但是也不能離“氣”,因為離開“氣”,“性”“命”都無從所授;“氣質之性”“氣之命”二者雖然是“以氣言者”,但二者也不離“理”,因為二者都以“理”為本體、為本質。由此可見,朱熹認為“理”“氣”是聯結“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與“理之命”“氣之命”的紐帶。
總之,朱熹論“性”和“命”是從不同的角度闡釋其“理”。朱熹認為:“理、性、命,只是一物,故知則皆知,盡則皆盡,不可以次序言。但知與盡,卻有次第耳。”[1]1969“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理之命”“氣之命”四者的本體都是“理”,“理”貫穿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理之命”“氣之命”。只不過“天地之性”“理之命”是“專”以“理”言,而“氣質之性”“氣之命”是以“理”為本體“兼”“氣”而言。無論是“命”,還是“性”都是從不同的側面體現了“理”,可以說,“理”借助于“氣”把“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理之命”“氣之命”交織在了一起。
四、對朱熹“性”和“命”理論的評析
(一)朱熹論“性”和“命”的理論貢獻
1.朱熹通過“理一分殊”論“性”“命”
朱熹認為萬物本源于“理”,“理”不離于“氣”,日本遠藤隆吉分析朱熹的“理”“氣”關系時說:“‘理’作為形而上的存在具有力學性的意味,‘氣’作為形而下的質料具有必然性的意味。朱子又把‘理’等同于周子的‘太極’作為一切萬物普遍性的東西。……一切萬物,都是“理”“氣”的結合。”③在朱熹的理論中,“性即理”,故而也是論“性”必論“氣”,并且人依“理”稟“氣”而各有“命”。
“性”“命”都是人特有的,而“理”是人產生之前就有的存在,不管人是否存在,“理”始終是存在的。可見,朱熹把“性”“命”都統一于“理”。朱熹認為“氣”在聚集、凝結的過程中,不是雜亂無序地聚集、凝結,而是在“氣”聚集、凝結的過程中,“理”“性”“命”都起了作用。由于萬事萬物“稟氣”各異,從而形成了人、物之間“性”的相異,也形成了人與人之間愚賢、短命長壽等等“命”的差別。人之稟氣差異是“理”在起作用,“氣”的聚集、凝結、厚薄、混濁或清明都是“理”決定著,“理”始終是本體、是依據。正是由于“理”對“氣”的這種主宰和先在性的作用,才能形成形形色色的個人,由此通過“理一分殊”完成每人各一“性”“命”的過程。雖然朱熹認為“性”即“理”,但是在現實層面,現實人的“性”不能簡單地被認為等同于“理”,只不過現實人的“性”“命”通過“理一分殊”體現了“理”,也體現了現實人的“性”“命”之本體為“理”。朱熹認為“命”“性”由“天”(理)以及理兼氣而定,“理”是“命”“性”之本體、本質。在朱熹理論中,“性”“命”既分離又統一:一方面,“性”與“命”有著不同的內涵;另一方面,“性”與“命”都統一于“理”。朱熹認為宇宙之內天地萬物只有一個“理”,而天地萬物又各有各的“理”,這就是朱熹所說的“理一分殊”。朱熹通過“理一分殊”之理論,論述了“性”“命”的統一性。
朱熹論“性”“命”都與人有關系,雖然朱熹論“性”也涉及到了物性,但更多地論及人“性”。朱熹認為人共有其“性”,也各有其氣質之“性”,他利用“理一分殊”的理論闡釋“性”,并且通過“性即理”把“性”與“理”統一起來。朱熹論“命”,無論是“天命”還是“人命”,都離不開人,即使“天命”是“天”對“人”的命令,離開人“天”也無從下達命令,“天”依據“理”給予人命令,使人受與“天”之“令”而成“性”。由此可見,朱熹論“命”“天命”“性”都與人有關系,朱熹論“天命”“人命”“天地之性”“氣質之性”是以人為參照而論。朱熹無論闡釋“天命”“人命”,還是闡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都離不開主宰性的本體“理”。正如二程分析:“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于身為心,其實一也。”[2]204也就是說,“天命”“性”都是一樣的東西,“天”之“命”、人之“性”都是“理”的體現。朱熹認為:“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1]82朱熹這里是說“命”是“理”之所用,“性”是人所承受的“理”,即“性是許多理散在處為性”[1]83。
2.朱熹論“性”和“命”貫通了“人性論”“宇宙論”“本體論”
朱熹繼承了前人思想,尤其繼承了張載及二程的思想。張載通過以“氣”為本體,把“本體論”與“宇宙論”融合在了一起,在“人性論”方面提出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程顥認為“性”是“理氣”一體的,主張“善惡”皆“天理”,因為“性”中的“天地之性”來自“天理”的“純善”,“性”中的“氣質之性”來自于“善惡混雜”的氣稟。正如日本武內義雄分析:“宋以前的儒者有的只是拘泥于訓詁之學而不能貫通宇宙與人世,有的只是流于佛老空理而不顧及實踐,北宋的先儒周張二程開創了貫通宇宙與人世的究理哲學,朱子繼承之而集大成。”④
從朱熹以“理”為本原,通過“二氣五行交感”化生萬物的宇宙論,到“理”為本體、本質的本體論,再到“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的人性論,都始終以“理”為根據。此外,在朱熹的理論體系中,無論是作為宇宙論本原的“理”,還是作為本體論本質的“理”,亦或是人性論中作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依據的“理”,都離不開“氣”的參與,所以日本許多哲學家認為朱熹的理論是“理”“氣”二元論,即“朱子的哲學是‘理’‘氣’二元論,闡釋了‘理’‘氣’不可分”⑤。他們認為正是朱熹“理”“氣”為本原的宇宙論、“理”“氣”為本的二元本體論,導致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的二元人性論。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在理論界大多數學者認為,雖然朱熹論“理”不離“氣”,但是據《朱子語類》“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后”[1]3,說明朱熹仍是理本一元論。如此,在本原上朱熹主張了“理先氣后”的宇宙論,在本體上還是主張了“理是本”[1]2的本體論,在人性論上也是把“理”作為了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的本體,“理”亦是“理之命”“氣之命”之本體,故而朱熹無論是論“性”、還是論“命”,都把“理”作為依據。朱熹以“理”貫通了其“人性論”“宇宙論”和“本體論”。
3.朱熹通過對“性”“命”的闡釋,說明了人道德修養的重要性
朱熹認為“理”通過“氣”賦予人本善的“天地之性”,如仁義禮智信,從而使人具有“理之命”。日本學者近藤正則分析朱熹論“性”時指出:“生來,人的本性是善的,心都具有仁、義、禮、智、信的德性(道德資質),然而通過私情、物欲會使本善之性迷失,就會顯現與禽獸同類的姿態,因此,以五常五倫為人本性,無論如何都要注意恢復本性之善的修養,在恢復本性(恢復本性之善)上下功夫是不可缺少的。實現復性,去除私欲的手段,沒有比學問修養和日常功夫更大的了。”①稟性(在成為人類存在之際稟受的陰陽五行之氣的個人差異)的拘泥之處,成為人欲的隱藏之處,則會黃昏(失去本性的清明)。然而,其本體之明(本善之性根源性的清明),則有尚未嘗過之人。因此,學習者應根據自己所發之所(從稟性和人欲的間隙中漏出的明德的光明),最終將其弄清楚,以復其初。
根據朱熹分析,在天地陰陽之氣交融產生萬物之時,得到木、火、土、金、水五行之氣的純粹優秀之物而產生人類。“在朱子學中,‘理’把自然和道德聯系起來,而且‘理’作為‘本然的性’存在于人,因此能保證人與規范一致。當然,實際上很多人都達不到規范,那是因為‘人欲’成了障礙,只要去掉‘人欲’,任何人都可以達到規范。”⑥于是在道德修養方面,朱熹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當然朱熹不是想滅掉人所有的欲望,朱熹所說的“滅人欲”只是想滅人的貪欲、不正當的欲望。朱熹極力推崇修養,從而號召人們努力恢復“人本善”的本性。朱熹認為“人之初”的先天素質不盡相同,有的人天生就比較忠厚,有人的天生就比較奸詐,故而,社會、學校對人的道德教育要因人而異,根據個體的秉性特點對其進行道德教育,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道德發展。
(二)朱熹論“性”和“命”的理論局限性
1.對“性”的闡發只是限定在了孔孟“性本善”的路線
朱熹論“性”,是按照孔孟“性本善”的路線,利用“天地之性”“天命之性”論證人的本性是善的。朱熹認為:“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1]67就本質而言,“性”與“理”是相同的,這里朱熹所說的“性”即“天地之性”“天命之性”。朱熹又認為人性的本然狀態為“善”。陳來教授分析:“嚴格地講,對具體現實的人來說,不能簡單地說性即理,只能說性之本體是理。”[3]205“理”是人“未生”之前之稱謂,“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人“已生”后對“理”之稱謂,在這里可以說“理”是“性”之本體。“理”在人出生之前、在人出生之后一直存在,即人“未生”“已生”“理”都一直存在,而“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都是相對于現實的“人”而言。朱熹分析:“但因‘氣質之廩,各有清濁’,故人有善、有不善。”在朱熹的理論體系中,“人之初”不僅有“天地之性”,而且也有“氣質之性”,這樣的話,那也只可以說成:“人之初”“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本相同,而“人之初”由于稟氣不同,故而人的“氣質之性”因人而異。所以朱熹又說:“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卻只是此日。”[1]58也就是說,“性”最難說明白,說“性”相同也適合,說“性”相異也適合。就像縫隙中的“太陽”,縫隙的大小及長短自然不同,然而卻是同一個“太陽”,這里朱熹所說的“太陽”就是“理”。先秦以來,古代哲學家們對“性”進行過各種各樣的思考,有主張“性本善”者,有主張“性本惡”者,有主張“性本有善有惡”者,有主張“性本無善無惡”者。朱熹論“性”只是按照孔孟“性本善”的路線,對人“性”的善、惡進行了闡述,并且把人的“惡”歸結為“氣”對“本性”的遮蔽,這勢必會遭到主張“性本有善有惡”、“性本無善無惡”“性本惡”流派的異議。
2.未闡釋“天命之性”“天地之性”的細微差別
朱熹論“性”,有時論及“天命之性”,有時又論及“天地之性”。朱熹既把“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相對應,也把“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相對應,但是朱熹并沒有闡釋“天命之性”與“天地之性”的差別。
朱熹論述的“天命之性”與“天地之性”有共同之處:其一,“天命之性”與“天地之性”都以“理”為坐標,并且都與人有關。無論是“天命之性”,還是“天地之性”,都是“專”以“理”言,例如朱熹曰:“‘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1]63朱熹又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1]67并且“天命之性”與“天地之性”都是“理”就著于“人”之“性”,人稟“天命之性”而生,人稟“天地之性”而生。其二,“天命之性”與“天地之性”都與“氣質之性”相對應。例如朱熹曰:“有氣質之性,無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無氣質之性,亦做人不得。”[1]64就是說,任何人不僅只有“天命之性”,而且還有“氣質之性”,二者缺一不可。朱熹“天命之性”“天地之性”都與“氣質之性”相對應,都以“理”言,實質上朱熹所說“天命之性”“天地之性”所指是一樣的,但也有細微差別。也許只是語境不同,使用異名而指向相同,朱熹對此并沒有闡釋。
在朱熹理論中,“天命之性”與“天地之性”可能只是名稱不同,實際上指的是同一個東西,正如日本山鹿素行指出:“‘天命’這個詞本身來自于‘中庸’,自古以來就存在。但是,《中庸》中的那個并不是與‘氣質’對立的。直到宋代,張橫渠才設置了‘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分。此后,朱子也采用了這個區分,張橫渠將‘天地’這個稱呼按照《中庸》換成了‘天命’,固定下來。”⑥由此,可能朱熹認為“天命之性”與“天地之性”異名而同義,但是朱熹對此卻沒有闡釋。
注釋
①參見近藤正則:《松平定信〈難波江〉の主題と朱子學的ジェンダー論の構造——“性分”と“職分”をめぐって》,岐阜女子大學紀要(第30 號),2001年第3 期。②參見服部富三:《東洋道德原論》,內外株式會社大正十三年版,第335-336 頁。③參見遠藤隆吉:《東洋倫理》,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大正十七年版,第126 頁。④參見武內義雄《朱子·陽明》,巖波書店昭和十一年版,第35-36頁。⑤參見下澤瑞世:《東洋哲學思潮大觀》,東京刊行社大正十三年版,第129 頁。⑥參見山鹿素行:《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巖波書店1941年版,第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