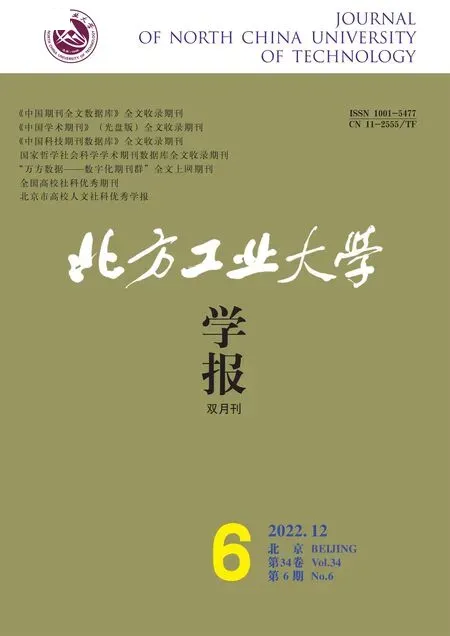21世紀非洲法語文學特征探微*
田妮娜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語言文化學院,100089,北京)
相較于非洲古老悠久的文化文學傳統,誕生于近代的非洲法語文學(la littérature africaine francophone)可謂是一種年輕的文學形式。19世紀殖民時期出現的記錄非洲風土人情的法語作品大多由傳教士、民俗學者、探險者所撰寫,以描摹異域風貌為主旨。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在撒哈拉以北的馬格里布地區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相繼出現了由非洲本地作家用法語撰寫的文學作品,其中阿爾及利亞軍官默罕默德·本謝里夫(Mohamed Bencherif)1920年出版的《士兵艾哈邁德·本·穆斯塔法》(AhmedBenMostapha,goumier)被視為阿爾及利亞首部法語小說,而生于馬提尼克的黑人作家赫勒·馬郎②(René Maran)1921年出版的小說《霸都亞納》(Batouala)獲得了當年法國的“龔古爾文學獎”,赫勒·馬郎也因此被視為黑人法語文學的先驅。此后,非洲法語文學蓬勃發展,迅速成長為世界文學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20世紀,馬格里布和撒哈拉以南兩個非洲地區的法語文學有著相似的經歷,它們關切大眾民生,反映了20世紀非洲大陸所經歷的世界大戰、殖民主義制度瓦解、民族獨立運動、后殖民時期的探索、1980—1990年代的政局動蕩與種族沖突等時代巨變,以及這些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和人的精神狀態。
非洲法語文學在邁入21世紀的同時,也站在了自身發展歷史的交匯點上。這一時期的非洲法語文壇既活躍著1960—1970年代涉足文壇的阿瑪杜·庫魯瑪(Ahmadou Kourouma)、阿西婭·杰巴爾(Assia Djebar)、亨利·洛佩斯(Henri Lopes)、伊夫-伊曼紐爾·多格貝(Yves-Emmanuel Dogbé)、阿米娜達·索烏·法勒(Aminata Sow Fall)、塔哈爾·本·杰倫(Tahar Ben Jelloun)等經典作家的身影,又涌現出一大批年輕化、多元化的新生代作家。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出生或成長于后殖民時期,沒有親歷過歐洲殖民統治,但見證了國家民族獨立后的種種曲折,他們的創作與前輩相比有了新的訴求和主張。此外,非洲文學向來擅長反映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間的沖突與融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洲法語文學不僅需要突出民族文化特性,更需要應對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認同的困境、思想觀念的沖擊、文化斷層等等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危機。
1 “文史交融”特色的傳承
非洲法語文學誕生于殖民主義和去殖民化的歷史洪流之中,本身就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文化產物,同時也在民族國家的近代歷史進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天然地具有關注歷史、見證歷史、反思歷史的傳統。新世紀的的文學作品盡管在題材和體裁上都更加趨于多元,但“以文見史”“文史交融”作為非洲法語文學的主要要藝術特色之一,得到了傳承和發揚。歷史何以至此?今人又當如何理解這種錯位?書寫歷史無疑是書寫自我、解讀自我、接納自身矛盾、彌合自身傷痕的方式。
非洲大陸近代以來所經歷的苦難是新世紀文學作品中的重要母題。非洲國家從西方殖民體系下獨立以后,并沒有像人們所期待的那樣迎來和平與繁榮,國家內戰曠日持久,種族沖突持續存在,政局動蕩不安。1994年的“盧旺達大屠殺”是種族仇恨以及殖民制度遺留問題的集中爆發。這一駭人聽聞的血腥事件在在新世紀初的文學作品中被反復書寫。事實上,從20世紀末起,乍得詩人諾基·杰達努姆(Nocky Djedanoum)就多次集結非洲藝術家為這場發生在非洲大陸上的慘劇發聲,1998年,多位非洲作家前往盧旺達參加杰達努姆發起的“盧旺達:為記憶的責任而寫作”項目,以盧旺達大屠殺為題材進行文學創作,這些作品在新世紀初相繼出版。2000年出版的塞內加爾作家布巴卡爾·鮑里斯·迪奧普(Boubacar Boris Diop)的小說 《穆蘭比,白骨之書》(Murambi,lelivredesossements)就記錄了1994年4月21日發生在穆蘭比村一所技術學校內的慘案。作者不僅以殘酷、露骨的方式敘述了暴行的經過,更詰問了這場殺戮背后的深刻的歷史、社會、文化根源 ,同時質疑了當時西方國際社會冷漠、縱容的態度。書寫的目的是“不要背叛他們的痛苦”。[1]該書2000年在法國一經出版就引起巨大反響,獲得當年的“黑非洲文學大獎”。同樣該年出版的、出自該項目的作品還有幾內亞裔作家蒂埃諾·莫內南波(Tierno Monénembo)③的小說《孤兒兄長》(L’Anédesorphelins),講述了喪親兒童的流浪生活;諾基·杰達努姆本人的詩集《尼亞米朗博!》(Nyamirambo!)也在同年出版,這部冠以盧旺達首都基加利市中心城區之名的詩集將該地區熱鬧的街景,宜人的風光與1994年發生于此的恐怖暴行融為一體,對比強烈,令人觸目驚心。2004年,盧旺達女作家埃斯特·穆賈瓦約(Esther Mujawayo )的小說《女幸存者:盧旺達,大屠殺的十年后》(SurVivantes:Rwanda,dixansaprèslegénocide)出版,摘得了首屆“阿瑪杜- 庫魯瑪文學獎”。作為大屠殺的親歷者,作者從個人經歷出發講述了事件的經過,呼吁社會關注幸存者、尤其是幸存女性所遭受的精神創傷。而穆賈瓦約兩年后出版的作品《斯蒂芬妮的花》(LafleurdeStéphanie)以“和解與拒絕之間的盧旺達”為副標題,探討了今天仍生活、勞作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幸存者與劊子手之間達成諒解的可能與困難。2014年,喀麥隆作家歐仁·艾波代(Eugène ébodé)以大屠殺女幸存者蘇維埃拉·馬尼菲克的經歷創作的對話體小說《蘇維埃拉·馬尼菲克》(SouveraineMagnifique)獲得了當年的“黑非洲文學大獎”。該書展現了大屠殺20年后種族間依然存在的緊張態勢,更探討了大屠殺后司法與正義重建所面臨的挑戰。
盧旺達大屠殺是個異常沉重的話題,不僅因為這場災難奪去了百萬人的生命,帶來了幾代人都無法愈合的傷痕,更是因為它發生在距今僅僅20余年的20世紀末,發生在所謂的“文明時代”,這無疑是現代文明的恥辱。是什么觸發了“沉睡在基因里的種族仇恨”?[2]這場發生在非洲人之間的殺戮該如何被敘述、理解和回憶?從殖民遺患到種族隔閡,從仇恨驅動下的集體癲狂到傷痛壓抑下的集體失語,從對人性泯滅的痛心到對人性回歸的渴望,非洲法語文學對其進行了持久、多維的再現和探討。從更廣泛的角度說,剖析種族沖突根源,銘記歷史教訓,撫慰心靈創傷構成了21世紀初非洲法語文學創作的重要動力。
在告別了殖民制度40年后的今天,對殖民歷史的書寫仍未過時。2013年,加蓬作家奧古斯丁·埃馬內(Augustin Emane)的人物傳記《阿爾貝特·施韋澤,非洲圣像》(AlbertSchweitzer,uneicneafricaine)獲得了“黑非洲文學大獎”,該書記錄了德國人阿爾貝特·施韋澤自1913年起傾注畢生精力在加蓬開展的醫療援助行動。作者在敘說這位來自歐洲的神學家、哲學家在非洲的經歷時,力求擺脫殖民者—被殖民者、壓迫者—受害者的二元對立窠臼,從人道主義和文化融合的視角記錄并評述了施韋澤的旅非生涯。同年,喀麥隆哲學家、史學家阿奇里·姆貝姆貝(Achille Mbembe)的哲學著作《黑人理性批判》(Critiquedelaraisonnègre)一書出版,書名與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遙相呼應。作者從黑奴貿易說起,闡述了黑人近代歷史是如何被西方定義、構建的,也詮釋了黑人文化傳承在當今世界的意義。2015年,喀麥隆女作家艾茉莉·布姆(Hemley Boum)的小說《游擊隊員》(LesMaquisards)同樣以殖民時期以來的歷史為藍本,講述了喀麥隆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而進行的不懈抗爭。本書選取了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和標志性事件,敘事時空跨度宏大,可謂一部喀麥隆建國史,獲得了2015年“黑非洲文學大獎”。四年之后,這一非洲法語文壇最重要的獎項再次垂青于一部以殖民歷史為題材的小說,即科特迪瓦作家高茲(Gauz)④的小說《爸爸同志》(CamaradePapa)。這部作品的敘事視角橫跨一個世紀,既回顧了19世紀末法國年輕人前往殖民地科特迪瓦開拓商業的經歷,也講述了20世紀末非裔少年重回故土的尋根之旅,作品文本力圖打破時空阻隔,在當下與往昔間建立對話。
回顧百年來的進程便不難發現,非洲法語文學對殖民歷史的書寫由來已久。在民族獨立運動如火如荼的20世紀中期,文學曾是揭露殖民制度掠奪本質、喚醒民族自豪感與反抗精神的利器;獨立后,文學反思社會發展的種種困境,同時揭示了殖民時代遺留的痼疾在后殖民時期的持續影響;進入新世紀,殖民歷史這一話題依然具有現實意義。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對立、仇恨以及弱勢受害者的視角被逐漸淡化,代之以更開放、更辨證的解讀方式,書寫的目的也從強調非洲文化的“特異性”“獨立性”拓展到探索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共生關系。
當然,非洲法語文學的歷史情結還體現在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對殖民前民族發展史的重新審視。2004年,阿爾及利亞作家薩利姆·巴希(Salim Bachi)就借柏柏爾民族歷史上的女王、女先知卡希娜之名創作了小說《老屋卡希娜》(LaKahéna)。這位曾率領柏柏爾人成功抵御阿拉伯軍隊入侵的女英雄后來成為柏柏爾人勇敢堅毅、敢于反抗強者的民族精神象征。巴希筆下的“卡希娜”是一幢見證了三代阿爾及利亞人愛恨情仇的老屋,同時也是阿近代殖民史與獨立史的經歷者和講述者,老屋還是民族英雄的化身,她歷經風雨而屹立不倒,為阿爾及利亞人提供庇護。從1970年代至今筆耕不輟的塞內加爾作家阿米娜達·索烏·法勒也是一位重視傳統文化價值的女性。2005年,她的小說《憂傷宴會》(Festinsdeladétresse)講述的是當代黑人家庭兩代人的遭遇,卻深刻地探討了黑人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現實和前景,指出在價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傳統文化依然具有為現代道德教育和社會治理提供借鑒的可能。同樣在2005年,科特迪瓦女作家薇羅尼克爾·塔迪奧 (Véronique Tadjo)的歷史題材小說《波庫王后》(ReinePokou)斬獲“黑非洲文學大獎”。這又是一部取材于民族女英雄傳奇故事的作品。18世紀,西非歷史上著名的波庫王后為躲避王室成員間的互相殘殺而帶領巴烏萊人從加納出逃,跨過科莫埃河,抵達今天的科特迪瓦并建立王國。 為了讓族人平安渡河,波庫王后不惜獻祭出獨生子的生命。波庫王后作為女性力量的象征,不論在傳統口頭文學還是近代書面文學中都是反復出現的人物形象。⑤塔迪奧的作品中既有對傳奇故事本身的呈現,也包含作者接觸、理解、改寫故事的過程,刻畫歷史傳奇女性的同時書寫了當代不同年齡普通女性對波庫王后的認知。出生于科特迪瓦的人類學家安熱爾·格諾索亞(Angèle Gnonsoa)2007年出版的學術性文學作品《衛族社會中的面具》(Lemasqueauc?urdelasociétéwè)獲得了當年的“科特迪瓦文學大獎”。在這部民俗學作品中,作者通過收集口頭傳說和實地調研,闡述了面具在科特迪瓦西部衛族人社會中的作用。面具作為人與神靈、后代與祖先之間的溝通媒介,是傳統文化的載體,也象征著部族文化的傳承。有意思的是,這種將學術撰寫與文學創作融為一體的“跨界作品”在非洲文學中并不鮮見。非洲法語文學早期就有類似作品出現,如展示了伊斯蘭教的禮儀、規范以及朝圣之旅意義的游記《在伊斯蘭圣城》(Auxvillessaintesdel’Islam, 1919),⑥細致描繪了摩洛哥北部扎亞納人的部落風俗的《柏柏爾的山》(LaMontagneberbère, 1929),⑦以上作品既是文學作品,又具有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參考意義。正如格諾索亞在其作品中談到的那樣,舶來的文化和宗教“將持續地削弱衛族社會的根基”,[3]而今天年輕人更應該具備民族文化傳承的意識,因為“對自己文化都含混不清的人注定屈從于他人的文化”。[4]
對歷史的關照是非洲法語文學的特色,是文化傳統在當代文學中的體現,也是當代文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需要。在非洲地區廣泛存在的口述文學將“回顧往事”的文化、文學傳統保留至今,敘述“歷史”(l’Histoire)和講“故事” (l’histoire)本就有著內在的統一性。此外,對于非洲作家而言,用他者的語言講自己的故事本就有與生俱來的矛盾性,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成為文學創作的天然素材,因為它本身就意味著復雜曲折的過往和深刻的矛盾。正如幾內亞法語作家卡馬拉·拉耶(Camara Laye)指出的那樣:“想要在光復非洲思想的道路上做得更好,并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必然要從我們特定文明的歷史真相和非洲的現實中汲取力量。”[5]
2 對社會現實的介入與批判
在追問歷史的同時,21世紀非洲法語文學也表現出直面當下社會現實和尖銳矛盾的勇氣,這種擔當賦予了文學作品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源源不斷的生命力。作家們在時代的脈動中形成對社會面貌、民族身份的新感悟、新認知,又在時代的漩渦中與自我相認,重構自我身份,而時代的變遷也激發作家們洞察新問題,反思新現象、開拓新的想象空間。新世紀非洲法語文學對現實的關照使它充分體現出時代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非洲法語文學對社會現實一直抱有積極介入的態度,能反映社會重大問題的宏觀視角在文學創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08年,多哥作家科西·埃弗伊(Kossi Efoui)的小說《返鄉者的獨奏》(Solod’unrevenant)摘得“阿瑪杜- 庫魯瑪文學獎”。作品虛構了一個剛剛經歷了十年內戰的國家,主人公為躲避戰爭而流落他鄉,戰后回鄉后卻發現,生活已經難回正軌。戰爭留下滿目瘡痍,政府弄虛作假,法律公平不在。雖是虛構國家,但埃弗伊的文字依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是20世紀末陸續陷入內亂的非洲國家的縮影。剛果作家因·科力·讓·博法納(In Koli Jean Bofane)2008年出版了處女作《剛果數學》(Mathématiquescongolaises),次年獲得“黑非洲文學大獎”。在這部諷刺小說中,作者將剛果(金)首都金沙薩描述成一座貧富差距巨大、政治腐敗橫行的城市。主人公誤打誤撞成了政府公務員,親眼目睹了現代信息和媒體技術如何輕而易舉地操控社會輿論,為金錢和權利服務。來自剛果的另一位作家伊曼紐爾·唐加拉(Emmanuel Dongala)2010年的小說《河邊的集體照》(Photodegroupeauborddufleuve)中,也將故事背景設定在一個官商勾結的虛構國度,當權者利欲熏心,反抗者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科特迪瓦作家安德烈·西爾弗·科南(André Silver Konan)2013年的小說《國家利益》(Raisond’état)也是一部針砭時弊之作,獲得2013年“阿瑪杜- 庫魯瑪文學獎”及第三屆“科特迪瓦文學大獎”。作品指出了當下困擾非洲社會運轉的種種痼疾,如金錢政治、法律不公、暴力執法、秩序缺失等等。2015年,阿爾及利亞作家布阿萊姆·桑薩爾(Boualem Sansal)的小說《2084,世界末日》(2084,lafindumonde)摘得“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該小說也同樣虛構了一個叫“阿比斯坦”的帝國,在那里人的思想被束縛,語言被僵化,行為被監控,理想被抹殺。作者通過這個被恐怖氛圍籠罩的國度影射了阿爾及利亞政壇,尖銳地批評了阿爾及利亞的政治、社會、經濟狀況,揭露了政府內部的行賄、誹謗、造謠等腐敗行徑。這一類作品不僅表達了作者的某些政治主張,更體現了作家對現實的關切,對社會發展現狀的憂慮以及對公平自由社會的向往,體現了非洲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
此外,以講述個人經歷、家庭關系為主的微觀視角和日常敘事在新時代的文學作品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這其中又以反映女性權益、女性地位、女性經驗的作品最為突出。阿爾及利亞當代女作家阿西婭·杰巴爾的中短篇小說集《房間里的阿爾及爾女人》(Femmesd’Algerdansleurappartement, 1980, 2002)在1980年版本的基礎上增補后重新出版。這部作品呈現的是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前后普通女性的生活境況,她們身份各異,有母親、新婚妻子、浴室女工、大家閨秀、職業女性等,她們被置于宗教戒律、社會地位、家庭關系的牢籠中,如果說整個阿爾及利亞社會正在承受時代巨變帶來的沖擊和壓力,那么阿爾及利亞的女性則是帶著多重腳鐐艱難地適應著社會生活和價值觀念的變化。2010年,喀麥隆女作家艾茉莉·布姆(Hemley Boum)出版了處女作《女性部落》(LeClandesfemmes),講述了一位出生于20世紀初的非洲女性的人生經歷。這位名叫“薩哈”的女性9歲成婚,16歲生子,丈夫去世時又被當做財產分配給丈夫的兒子,傳統觀念中女性身份伴隨著她的成長,然而來自西方的男女平等、女性獨立等女性主義觀點又讓她看到了改變命運的希望。同年,同樣來自喀麥隆的女作家德賈伊莉·阿瑪杜·阿瑪勒(Dja?li Amadou Amal )在小說《瓦朗德,共享丈夫的藝術》(Walaande,l’artdepartagerunmari, 2010)中,通過批判非洲傳統社會中廣泛存在的“一夫多妻”制,指出在“一夫多妻”家庭中,婦女們竭力的“和諧關系”恰恰是造成女性家庭地位、社會地位乃至文化地位低下的罪魁禍首。作品標題中的“瓦朗德”在非洲中、西部的頗爾語中意為“結為伴侶”或“婚姻”,阿瑪勒筆下的“瓦朗德”構成了限制女性的第一道枷鎖。以女性家庭生活為題的作品還有突尼斯作家法茲婭·祖阿莉(Fawzia Zouari)《我母親的身體》(LeCorpsdemamère, 2016)。在這部以作者母親為原型的作品中,突尼斯傳統母親的形象躍然紙上,她子女眾多,安分守己,少言寡語。這樣一位母親在邁入老年時竟然愛上了樓下的看門人,為追求愛情,迫于世俗的她只能佯裝患上了老年癡呆癥。她對女兒說:“我們可以無所不談,我的女兒,烹飪、戰爭、政治、財富,但就是不能談家庭秘密,因為那就相當于將秘密兩次暴露于視線中。安拉建議將秘密遮起來,頭一個秘密就是女人。”[6]該小說剖析了父權社會制度下,當代家庭婦女的精神狀態,獲得第六屆“法語國家及地區五大洲文學獎”。應該說,女性在當代的非洲法語文學中是具有時代性的話題,不僅因為女性作家數量或女性主題作品數量的增加,更是由于女性的家庭角色、社會地位、文化話語權等問題集中體現了全球化背景下非洲女性的時代身份。然而,不同于倚重“個人體驗”的法國本土女性文學,非洲法語文學更加注重從日常經驗出發書寫具有代表性的“集體經驗”,通過普通女性的境遇以及家長里短的生活瑣事反映女性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狀態,作品所塑造的藝術形象也通常代表了特定環境中的一類女性,聚焦于她們所共同面臨的沖擊和困惑。
進入21世紀,由于不同民族在價值認同和言論自由上的分歧有著復雜的歷史根源,移民問題在西方社會日益凸顯。以法國為例,近年來不斷發生的惡性事件揭示了法國社會日益凸現的文化撕裂加劇、移民融入困難、極端思想蔓延等重重危機。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旅居歐美的非洲移民作家作為一個具有文化特征的創作群體,在法語文壇扮演著越來越突出的角色,而非裔移民文學也漸漸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多哥法語作家、社會學家薩米·恰克(Sami Tchak)2001年出版的《節日廣場》(Placedesfêtes)講述的便是一個住在巴黎郊區的非裔法籍家庭的故事。書中的一家人生活并不如意,父親一心希望回到非洲,兒子卻對父親遙遠的故鄉沒有感情,他堅持認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法國人,在實際生活中卻又總是不被他人認同。恰克筆下非裔移民的“底層性”以及對于非洲文化的矛盾視角是極具代表性的,他們大都是西方社會中的邊緣人,帶著對母國文化既親近又疏遠的矛盾心態。從創作手法上說,《節日廣場》集中體現了當代非裔移民文學的特色,例如以探索自我身份,完成自我認同為主旨,以歐洲大城市市郊為主要環境,以作者本人經歷為素材以及非洲景象與歐洲畫面的交替、書面語與街頭俚語的交織等等。2005年,塞內加爾女作家法圖·迪奧姆(Fatou Diome)出版了代表作《大西洋的肚子》(LeVentredel’Atlantique)。這也是一部反映移民身份困惑的自傳式小說。作者以一對姐弟間的電話交流將法國城市斯特拉斯堡與塞內加爾一個小島聯系起來,一端是在法國為生計奔波的姐姐,另一端是對法國生活充滿憧憬的弟弟。女主人公牽掛遠方的弟弟,卻絕不愿回到那個傳統、閉塞的小島。故鄉意味著童年與親情,同時也是她主動拒絕踏足的往昔。同樣以城市郊區移民青年為主要人物的作品還有剛果作家威爾弗里德·恩松德(Wilfried N’Sondé)的小說《豹孩之心》(LeC?urdesenfantsleopards, 2007)。作品敘述了一個自幼移居歐洲的非裔年輕人在爭取社會地位的過程中所遭遇的暴力,呈現了移民在經濟生活、人際交往、個人情感等方面所面臨的困難,尤其是與警察的緊張關系。該小說同時獲得了“桑戈爾文學獎”和“法語國家及地區五大洲文學獎”。科特迪瓦作家高茲的成名作《保安》(Debout-payé, 2014)也生動地反映了巴黎非洲少數族裔的生活狀態。主人公在科特迪瓦本是一名大學教師,移民法國后卻以保安為職業,居住在巴黎郊區,社會地位出現了巨大落差。他一面以自嘲的口吻講述自己的身份變化,一面以學者的眼光審視著法國“保安”這一被外來移民占據的行業。作品語言幽默犀利,獲得了“科特迪瓦文學大獎”。
談及對移民生存狀況的書寫,不得不提及來自喀麥隆的女作家萊奧諾拉·米亞諾(LéonoraMiano)。這位18歲就赴法國求學、定居的非裔作家從2005年在法國發表處女作《夜深處》(L’Intérieurdelanuit)以來,至今已經出版超過20部小說,獲得了包括“黑非洲文學大獎”⑧和“費米娜文學獎”⑨在內的多個文學獎項,在法國和非洲都擁有較高知名度。2014年,米亞諾榮獲法國文化部頒發的文學藝術騎士勛章。在喀麥隆度過的童年和少年時光使米亞諾對非洲一直懷有深厚情感,她的大部分作品都以講述“非洲故事”為主旨。作為非裔移民,米亞諾對法國社會的移民問題深有感觸,在其作品中多次探討移民身份認同的話題。在小說《如同熄滅的恒星》(Telsdesastreséteints, 2008)中,作者講述了三位黑人移民在歐洲的生活,盡管家庭出身、旅法經歷、精神信仰各不相同,卻因為膚色問題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移民融入的困境和身份困惑;2010年的《獻給愛麗絲的藍調》(BluespourElise)作為一部現代都市小說,展示了法國的非洲裔女性的日常生活;而2012年的短篇小說集《為說而寫》(écritspourlaparole)則以幽默諷刺的語言探討了種族問題與法國社會價值觀的沖突,指出法國社會關于“少數族裔”“弱勢群體”的話語體系是落后而虛偽的,這套說辭聽起來開放、包容,卻只會進一步激化矛盾。
應該看到,在多重語言環境、多重社會形態、多重生活場景的共同作用下,移民作家的寫作方式具有跨文化、多視角的特征。他們既是帶著異鄉氣息的外來者,又是時刻體驗著當下的本地人;既期待被西方社會接納,又希望保持自己的獨特性;既關心自己個體際遇,也關注非裔移民作為西方社會少數群體的疾苦。他們的作品中融合了內部與外部視角以及微觀與宏觀維度,內容主旨上體現了融合與疏離的矛盾。此外,盡管他們來自非洲的不同角落,語言、宗教、家庭、職業都各不相同,在西方社會卻很難被仔細地區別開來,于是,如何敘述自己“身在異鄉”的故事成為考查自我身份的新角度。與20世紀以面向西方人展示非洲“文化身份建構”為主旨的作品不同,新一代非洲移民作家在探尋自我的過程中,更注重“文化身份認同”,更關心個人或群體的自我評價和自我接納,體現出一種更具自問性、自省性、內向性的寫作方式。
3 文學對非洲未來的構想
在西方描述非洲文化的話語中,“未來”處于長期缺席的狀態。1993年,美國作家、社會文化評論家馬克·德里(Mark Dery)提出了“非洲未來主義”(afrofuturisme)[7]的概念,將非洲傳統的部落文化、神秘主義與科技文化融為一體,催生了一系列電影、繪畫、雕塑、造型甚至服裝設計作品。然而事實上,在國家獨立后不久的1970年代,非洲知識界就已經開始思考民族的前途未來。1976年,多哥哲學家、社會學家、作家伊夫-伊曼紐爾·多格貝撰寫了《黑人文明與非洲的未來》(Civilisationnoireetdevenirdel’Afrique)一文,提出非洲文化的未來不應被政治綁架,政治應為知識界創造更寬松有利的環境。1979年,幾內亞作家蒂埃諾·莫內南波就在其首部小說《叢林蛤蟆》(LesCrapauds-brousse)中,將接受了西方高等教育的非洲知識分子諷刺為“神情空洞,低眉順眼,舉止唯唯諾諾,像是整個人都要化掉”[8]的可憐蟲,探討了知識分子在非洲未來的建構中應承擔的責任。這種關注非洲社會未來發展趨勢,將非洲作為未來的主體,將非洲文化置于世界未來文化體系中的視角同樣體現在新世紀的法語文學作品中。
法語文學創作首先體現了面對未來的憂慮,非洲大陸持久的地區沖突不僅帶來了當下的社會動蕩,也讓未來被蒙上陰影。2000年,科特迪瓦作家阿瑪杜·庫魯瑪在其小說《人間的事,安拉也會出錯》(Allahn’estpasobligé)中就講述了一名10歲的孤兒在部落沖突中的遭遇,通過小主人公的自述,探討了非洲戰亂地區的“兒童兵”現象。“當你沒有父母,沒有手足,沒有叔嬸,當你一無所有的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去當兒童兵。”[9]在庫魯瑪看來,武裝沖突最殘酷、最令人痛心的一面并非沖突本身造成的破壞,而是這些流離失所的未成年人充當了各武裝派別的廉價兵源,輕易地被訓練成殺人機器。這些武裝斗爭在剝奪少年兒童正常成長環境的同時,也正葬送著國家和社會的未來。該小說一經出版便迅速引起了熱烈反響,于2000年同時獲得了法國“雷諾多文學獎”和“高中生評選的龔古爾獎”。庫魯瑪透過少年兒童的生存狀況而對非洲未來產生的憂慮并非孤例,剛果(布)小說家伊曼紐爾·唐加拉在其2002年的小說《瘋狗強尼》(Johnnychienméchant)中也同樣關注了非洲的“兒童兵”現象。作者筆下的兩名少年對于身邊連年的戰火早已是熟視無睹,殺戮、掠奪是他們司空見慣的場景,其中一名是燒殺搶掠樣樣在行的兒童兵,他必須表現得足夠狠毒,才能獲得“上級”的信任,甚至得到提拔;另一名少年則是個女孩,武裝沖突襲來時她不得不與家人背井離鄉。一個是施暴者,一個是受害者,兩個主人公都過早地卷入了暴力,喪失了童年和未來,無疑都是社會混亂現狀的受害者。作者唐加拉通過小說不斷詰問的是,今天的殘局由誰來收拾?在混亂中成長起來的下一代如何能結束混亂?講述少年經歷的作品還有2016年多哥劇作家康尼·阿勒姆(Kangni Alem)的戲劇《著陸》(Atterrissage)。這部根據真實新聞改編的劇作講述了一起慘劇。兩名幾內亞少年懷揣著到歐洲發財致富的夢想,藏進了一架國際航班的起落架艙內,希望能用這種方式偷渡到理想中的自由國度。飛機著陸后,人們發現兩名少年早已死去。阿勒姆的劇作將非洲年輕人的困境描繪得淋漓盡致,他們未來渺茫,要么留在非洲,死于饑餓或戰亂;要么冒險出發,卻又死于偶然降臨的不幸,該作品既是現實社會的寫照,又是關于非洲未來的隱喻:地中海對岸的歐洲是否應該成為理想中的幸福彼岸?不滿于現狀的非洲人又是否能在歐洲的模式下找到屬于自己的未來家園?在當代非洲法語文學中,將青少年作為主要人物,把年輕個體的發展與社會總體發展聯系起來的敘述方式體現了非洲知識分子的未來視角和憂患意識。如果年輕一代看不到明天在何方,那么一個社會的明天則無從談起,青少年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影射了非洲的前途未來。
非洲法語文學思考未來的另一個維度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傳承。以闡述傳統對未來的啟示,重新發掘古老文化的價值為主題的文學作品正試圖構建一個立足于非洲本土文化的未來觀。剛果(布)作家阿蘭·馬邦庫(Alain Mabanckou)在2006年發表的小說《豪豬回憶錄》(Mémoiresdeporc-épic)中,就依托人與“靈獸”的傳說,以一只豪豬的口吻講述了發生在村莊里的一樁樁離奇命案。該書與其說是一部小說,不如說是一則以現實中的西非村落環境為背景的長篇寓言故事,具有鮮明的口語語言特色,夾雜了諺語、警句,體現了非洲古老文化的口頭傳承。書中呈現的村落文化具有“尚古”的價值取向,強調“延續”和“積累”的力量,希望從傳統、傳說、祖先遺訓中獲得生存之道,同樣,這也是以口傳的方式實現的,正如貝寧當代詩人貝爾納貝·拉耶(Bernabé Laye)所言:“在非洲,生命中所有的儀式,從生到死,從猴面包樹下的集會到篝火旁的不眠之夜,一卻都被置于言語的權威之下。”[10]該小說獲得了法國著名的“雷諾多文學獎”。作者馬邦庫曾旅居歐洲和美國,一直致力于讓非洲文學融入世界文學的探索,其作品傳達出非洲文化自覺的強烈訴求。2008年,加蓬作家讓·迪瓦沙·恩亞馬(Jean Divassa Nyama)的小說《崇高的使命》(LaVocationdeDignité)獲得了“黑非洲文學大獎”。⑩作品女主人公“崇高”自幼在普努人傳統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間長大,后為了追隨心中“崇高使命”的召喚,成為一名基督教修女。小說記述了女孩的心路歷程,事實上也是加蓬本地的普努人文化與來自歐洲的基督教文化的一次無沖突、無偏見的對話,既涉及了傳統的繼承問題,也探討了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作者通過小說完成了一次不同文化共存共榮的設想。
以文學的方式對未來進行思考是非洲法語文學體系日趨成熟的標志。在書寫未來的過程中,未來與個體自身的關聯愈發緊密。換言之,在作家們筆下,未來并非一種形而上的展望,而非洲的未來決定于自身。它寓于每一個鮮活的個體之中,不論是憂慮、憧憬,或是構想,都來源于特定的個體經歷,體現了面向未來的現實主義視角。
在今天看來,非洲法語文學這一年輕的文學形式在經歷了百年發展后正在從一種文學現象演變為歷史主體。它通過回望歷史,剖析當下,詰問未來,逐漸塑造出文學自身的發展史和傳承史,體現了非洲法語作家擺脫西方話語、構建自身敘事體系的訴求。總的來說,今天非洲法語作家筆下的被殖民者與殖民者、非洲與歐洲、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關系,不像在民族獨立運動的那一代作家筆下那樣對峙和緊張,他們的創作也不以凸現民族特性為主旨。從主題上看,這一時期的作品具有更大的普世性,更注重反映普通人的生命體驗。然而對于個體經驗的重視并非要摒除共同經驗和共同記憶,而是要透過個人視角,呈現與歷史共在的經驗,思考個人如何從當下社會出發,把握自己的命運。從書寫方式上看,新時期的作品更強調通過具有個人特色、地方特色、時代特色的文字呈現民族文化,以更加平和的方式使非洲文化擺脫邊緣化的地位,重新回到世界文化體系。
注釋:
① 如法國-塞內加爾混血沙漠探險家列奧波爾德·帕內(Léopold Panet)于1850年發表于《殖民雜志》(LaRevuecoloniale)的游記;又如法國-塞內加爾混血神父大衛·博瓦拉(l’abbé David Boilat)撰寫的民族學著作《塞內加爾圖略》(Esquissessénégalaises, 1853)。
② 本文中,該作家的姓名,作品名以及書中人物名采用1928年李劼人中譯本中的譯法。
③ 作者原名蒂埃諾·賽義杜·迪亞洛(Thierno Sa?dou Diallo)。
④ 作者原名阿曼德·帕特里克·巴卡布里德(Armand Patrick Gbaka-Brédé)。
⑤ 法國作家馬克西米連·格諾-波西-貝里(Maximilien Quenum-Possy-Berry)1946年出版了童書《非洲三傳奇:科特迪瓦、蘇丹、達荷美》(Troislégendesafricaines:Cted’Ivoire,Soudan,Dahomey),其中一則傳奇題為《巴烏萊人傳奇》(LalégendedesBaoulé),講的正是波庫王后的故事,而“巴烏萊”的意思正是“孩子已亡”。科特迪瓦作家貝爾納·達迪耶(Bernard Dadié)也曾在其整理編撰的《非洲傳說》(Légendesafricaines, 1966)中敘述了波庫王后的故事。
⑥ 由阿爾及利亞軍官默罕默德·本謝里夫(Mohamed Bencherif)所著。
⑦ 由阿爾及利亞作家薩伊德·蓋努恩(Sa?d Guennoun)所著。
⑧ 2011年,萊奧諾拉·米亞諾以全部作品獲得該獎。
⑨ 2013年,萊奧諾拉·米亞諾以小說《影子的季節》(LaSaisondel’ombre)獲得該獎。
⑩ 該小說1998年首版, 2007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