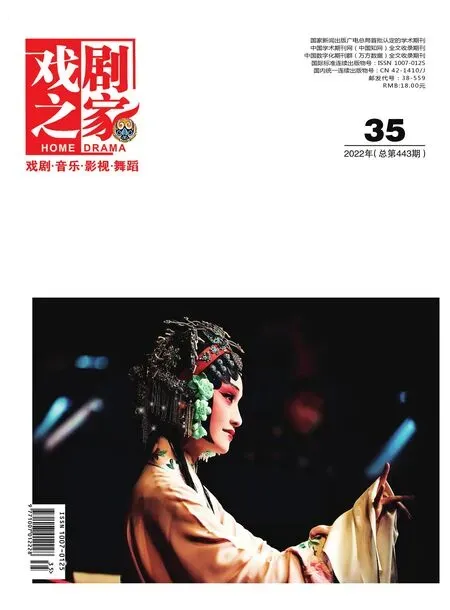民族舞劇《絲路花雨》的審美與特色分析
楊繼紅
(黑龍江省藝術研究院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
1979 年,由甘肅省歌舞劇院創作并上演的民族舞劇《絲路花雨》堪稱我國民族舞劇發展史中的里程碑,其所創造的價值,遠遠超出舞劇的藝術價值與審美價值。該劇蘊含的深厚內涵、獨特的美學思想以及民族性的舞劇題材,使得“敦煌藝術”重新回歸到人們的視野,隨之而來的是沉寂多年的中華民族古典舞的復蘇。《絲路花雨》走出國門,沖向世界,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包容、接納、天下大同的思想觀念,彰顯出中華民族熠熠生輝、別具一格的藝術特色。研究民族舞劇《絲路花雨》的審美與特色,將對我國民族舞劇的現代化創作及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一、民族舞劇《絲路花雨》的審美意蘊
民族舞劇《絲路花雨》是形式美、內容美、立意美與音樂美的高度統一,不僅可以為人們帶來極佳的視聽覺享受,還給人們帶來社會、環境、時代的深刻啟示,堪稱我國民族舞劇歷史上的里程碑,是我國舞劇藝術中的一朵奇葩。
(一)跨越藝術門類的形式之美
民族舞劇《絲路花雨》以匯百藝之長為美學向度,該舞劇集中國古典舞、印度舞、黑巾舞、波斯馬鈴舞、波斯酒舞、土耳其舞、盤上舞、新疆舞等多種舞蹈藝術形式于一身,展現出極高的舞蹈藝術造詣,且舞劇表演形式千變萬化、富有光彩。若說其中最具有創意的審美體現,便是對靜態敦煌壁畫的動態化演繹。舞劇編導們從2000 余尊彩塑、4 萬余平方米的敦煌壁畫中汲取靈感,以高度的藝術素養及審美追求判斷其或騰空、或落地的舞姿,開創了“敦煌舞”這一獨特的舞蹈語匯。例如,舞劇中英娘手抱琵琶,雙臂反別在背后,時而輕捻慢攏,時而如驟雨般傾瀉而下,再加上旋轉、跳躍、蹲起等輕盈靈動舞姿的配合,使敦煌壁畫內反彈琵琶的畫面動態化、直觀化與形象化,展現出獨特的中國神韻;再如英娘使用的長度超過2.4米的長綢,被演員揮舞得柔中帶剛,表現出飛天浮游的俊逸灑脫,但不失小女子的溫柔淡雅,每一個婀娜的舞姿都動人心弦,每一種舞姿的變化都打動人心,如此飽滿、奔放與優美的舞姿造就了民族舞劇《絲路花雨》那跨越藝術門類的形式之美[1]。
(二)深蘊歷史價值的立意之美
民族舞劇《絲路花雨》之所以在我國乃至世界藝術舞臺上久演不衰,除了其形式之美再現與還原敦煌文化博大精深與獨特風韻之外,其深蘊歷史價值的立意之美也是開創新高、成就經典的重要原因。此部民族舞劇以我國唐代的“開元盛世”為背景,以絲綢之路及敦煌壁畫為藝術元素,歌頌了老畫工神筆張、歌伎英娘父女二人對藝術的貢獻,也表現出他們與波斯商人的生死之交,體現出我國自古以來包容、接納的文化觀,再現了唐朝極盛時百國來朝、文化交流、對外貿易的盛況,也將舞劇的思想與精神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僅如此,民族舞劇《絲路花雨》塑造的鮮活生動、有血有肉的形象感動了千千萬萬人,無論是神筆張、英娘,還是波斯商人伊努斯等,都是漫漫絲路上無數人命運與故事的縮影,這部舞劇為人們創造了虛實交織的審美空間,讓人們回到唐朝、回到敦煌文化的鼎盛時期,以貫通古今的視野實現了一場超越時空的對話。民族舞劇《絲路花雨》的誕生,并不僅僅是一種新的舞劇語匯的創造,而承載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積淀,以及在輝煌歷程中所形成的獨特美學思想、價值觀念、思想精神與民族氣節,因而造就了此部舞劇深蘊歷史價值的立意之美。
(三)富有時代氣息的視覺之美
民族舞劇《絲路花雨》有著傳統意蘊,也帶著時代的氣息。在舞劇開場階段,繚繞的青煙以及朦朧的霞光營造出似真似幻、曠達高遠的意境,背后為溫和而莊嚴的佛像,前面則是身姿婀娜的飛天舞女,只見演員手捧絲竹樂器,在裊娜的青煙與縹緲的燈光之下顧盼生姿,將一幅敦煌畫以舞姿的形式展現在人們的面前。隨后,燈光驟亮,音樂響起,五光十色充斥著舞臺,襯托著六臂如意輪觀音的剪影,營造出古色古香的意境,也將人們的思緒帶到唐朝的極盛時期,給人以穿越古今、身臨其境般的藝術享受。在舞臺樣式上,民族舞劇《絲路花雨》極富時代氣息,現代藝術手法的應用以及舞臺裝備的融合,都使得舞臺燈光、舞臺調度、舞臺設計達成高度統一與和諧的美感,使得整個舞臺面貌、場景布局真實可信,再加上不同場景表演者服飾與燈光的交相輝映,場景變化下情節的發展與舞段的遷移,都將這場視覺盛宴推向高潮,也讓該部舞劇體現出一種傳統與創新交織的視覺之美[2]。
(四)隱含中西合璧的曲調之美
音樂是舞劇的靈魂所在,也是舞劇表演的基礎藝術要素。民族舞劇《絲路花雨》的曲調特色鮮明,吸收了《春江花月夜》等中華民族古典音樂調式調性、節奏型與旋律進行方式,整部舞劇內的音樂仿佛一首大型敘事詩,不同音樂要素與人物形象交織融合,以音樂語匯為人物形象的塑造增色,為配合各個舞蹈場面與舞劇的情節,全劇中還出現了相對完整、富有特色的音樂段落,如《霓裳羽衣舞》《飛天仙子》等。不僅如此,該部民族舞劇內的音樂還包含著交響樂、弦樂等,尤其是民族器樂的巧妙運用使得全劇韻味十足。如舞劇中英娘淪為歌伎時,以陜北嗩吶為主奏樂器,以嗩吶特有的音色體現出英娘命運的悲慘與凄涼,更添蕭瑟氣息,也為舞劇營造了一種悲傷的氛圍,由此可見,民族舞劇《絲路花雨》隱含著中西合璧的曲調之美。
二、民族舞劇《絲路花雨》的特色分析
民族舞劇《絲路花雨》首演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但其蘊含的思想與鮮明的特色依然具有時代意義。尤其是該部民族舞劇的民族性、藝術性與文化性特色,使其葆有強大的生命力,在舞劇舞臺上久演不衰并對后世的創作與創新提供參考。
(一)古典意蘊的特色體現
葉寧同志曾言,舞劇《絲路花雨》不僅開創了我國舞劇藝術的新高度,而且在舞蹈繼承與創新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貢獻。舞劇編導們對古典意蘊的追尋是該部舞劇成就經典、經久不衰的源泉,編導們從我國戲曲舞蹈中汲取精髓,但意識到戲曲藝術嚴謹的程式性難以體現出我國舞蹈藝術的博大精深與瑰麗多彩,因此,這部舞劇以我國傳統戲曲舞蹈為基礎,提煉我國古典戲曲藝術內的美學觀念,再與敦煌文化交織融合,創造出別具一格的“敦煌舞”藝術語匯。不僅如此,舞劇編導們借鑒了我國戲曲藝術的身法韻律,配合著音樂節奏的快慢、音樂力度的強弱,塑造出有血有肉的英娘形象,詮釋出人物內心的起伏變化與情感的迸發。除了經典的“反彈琵琶”舞段之外,全劇內不乏盤上舞、波斯舞等華彩片段,這些都是舞劇編導們從古典藝術中吸取精髓,對古典藝術予以當代觀照,并以創新意識為驅動,對我國傳統藝術的再造與再現,在傳承與創新的辯證統一中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古典舞風格流派,將中華民族舞劇提升至思想意識高度,展現出我國舞劇藝術無窮無盡的魅力[3]。
(二)倫理價值的特色彰顯
中國古典美學強調美與善的統一,注重藝術的倫理價值。民族舞劇《絲路花雨》是對古典的繼承,但絕不拘泥于此,以一種全新的語境審視藝術中的倫理與判斷善惡的評價尺度。在這部舞劇中,無論是流動、輕盈、變化莫測的舞姿,還是精巧的舞蹈構圖、舞劇的時空關系,都體現出一種平衡與陰陽調和的古典神韻與價值特色,含蓄內斂的情感抒發與情緒表達也契合中華民族歷來的審美價值追求,帶有氣韻生動、形神兼備的藝術特色。與此同時,該部舞劇在善與惡的對比上,從宏觀架構下選擇了一個小的切口,展現人物在時代下的命運,體現出人物命運與社會時代間密不可分的關系,由故事到精神,由具象到抽象,這部舞劇大膽地應用了寫意性的藝術表現方式,使得立意深遠、情感真摯、情節真實、故事豐滿、人物突出,但對內在與內涵的追求,并沒有弱化此部舞劇對歷史、對現實的關照,而是以更加深刻的筆觸、更加打動人心的藝術方式賦予人們更為開闊的情感空間,讓人們可以與劇中的角色進行心靈上的交互,從中提煉出判斷善惡之標準,激發潛藏在人們內心的對真善美的追求[4]。
(三)民族文化符號的樹立
民族舞劇《絲路花雨》是以民族文化符號講述中華民族故事的典范。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正值我國社會百廢待興的歷史時期,此時對待西方文化還以照搬照抄、一味模仿為主,西方文化思潮的侵入以及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對我國古典舞劇藝術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民族舞劇《絲路花雨》正是頂著重重壓力,大膽突破而誕生的富有民族性特色的舞劇藝術作品,其在國內外多次巡演,一方面讓高揚中華文化精神的舞劇乃至其他藝術形式重回舞臺,讓千千萬萬的藝術家看到我國古典文化與傳統精神的頑強生命力,也讓人們的民族意識逐漸復蘇,開始追求最為原始、最為樸素的具有中華神韻的藝術;另一方面,此部舞劇走向世界的同時,也向世界宣誓,中華民族必然有復興之日,讓我國舞劇藝術在世界舞臺上擁有話語權。
三、結束語
民族舞劇《絲路花雨》創作并首演于1979年,該劇以我國唐代的“開元盛世”為背景,融匯多種藝術形式,有著跨越藝術門類的形式之美、深蘊歷史價值的立意之美、富有時代氣息的視覺之美、隱含中西合璧的曲調之美。《絲路花雨》不僅是一種全新的古典舞流派,而且承載著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積淀,是古典意蘊的特色體現,倫理價值的特色彰顯與民族文化符號的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