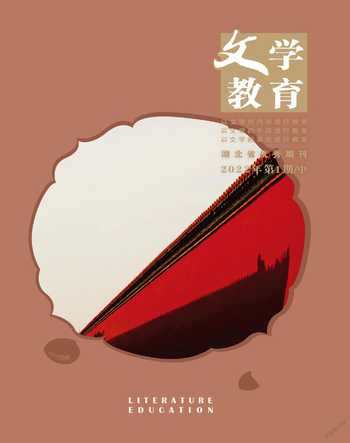論《南方與北方》中的疾病敘事
駱沁玥 吳慶宏
內(nèi)容摘要:《南方與北方》是英國維多利亞時(shí)期女作家蓋斯凱爾夫人的工業(yè)題材代表作之一。小說以英國北部工業(yè)城市米爾頓為背景,從南方淑女瑪格麗特的視角對(duì)英國工業(yè)革命期間復(fù)雜的勞資關(guān)系和社會(huì)現(xiàn)狀進(jìn)行了細(xì)致入微的描繪。大機(jī)器生產(chǎn)在給北方帶來經(jīng)濟(jì)繁榮的同時(shí)也引發(fā)了環(huán)境污染和疾病盛行,文中黑爾太太和貝西·希金斯從患病直至死亡的過程便集中體現(xiàn)了疾病在工業(yè)文明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眾多隱喻。本文以《南方與北方》為例,旨在探討工業(yè)文明影響下的疾病敘事以及背后的社會(huì)問題。
關(guān)鍵詞:《南方與北方》 工業(yè)革命 疾病敘事
十九世紀(jì)無論對(duì)世界,抑或大英帝國而言都可謂歷史的關(guān)鍵轉(zhuǎn)折點(diǎn)。以英格蘭中部地區(qū)為發(fā)源地的工業(yè)革命將“機(jī)器時(shí)代”的文明之風(fēng)吹遍了歐洲大陸乃至北美,一系列技術(shù)革命引起了從手工勞動(dòng)向動(dòng)力機(jī)器生產(chǎn)轉(zhuǎn)變的重大飛躍;生產(chǎn)力的巨大進(jìn)步促進(jìn)了英國資本主義的蓬勃發(fā)展,生產(chǎn)方式的改變使得新興的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jí)和工人階級(jí)登上了歷史舞臺(tái)。與此同時(shí),英國迎來了經(jīng)濟(jì)文化最強(qiáng)盛的“日不落帝國”時(shí)期,即維多利亞時(shí)代。
然而,工業(yè)革命更像伊甸園內(nèi)高高懸掛的誘人蘋果,在給人類帶來智慧結(jié)晶的同時(shí)也種下了欲望與災(zāi)禍。整個(gè)維多利亞時(shí)期,英國雖然享受著工業(yè)文明帶來的花團(tuán)錦簇般的繁榮,人們卻愈發(fā)無法忽視其滋生的越來越多的社會(huì)問題:隨著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jí)掌握了社會(huì)上的大量財(cái)富,他們的目光也從單一的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轉(zhuǎn)移到了能夠提高政治地位的議會(huì)席位上,故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jí)與既得利益集團(tuán)內(nèi)部的舊貴族、舊地主階級(jí)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沖突;貧富差距因大機(jī)器生產(chǎn)的推廣而日益擴(kuò)大,辛勞工作卻只能獲得微薄薪資的工人階級(jí)逐漸發(fā)現(xiàn)資本主義社會(huì)分配的不公,認(rèn)識(shí)到靠個(gè)人的努力無法在大工業(yè)制度下爭得應(yīng)有的物質(zhì)改善和社會(huì)地位,由此爆發(fā)的憲章運(yùn)動(dòng)表明無產(chǎn)階級(jí)也正式登上歷史舞臺(tái);過度的工業(yè)化生產(chǎn)導(dǎo)致環(huán)境污染等諸多生態(tài)問題層出不窮,隨著人口數(shù)量的激增,民眾健康問題成為十九世紀(jì)困擾英國的重要社會(huì)問題。(齊驥,滕海鍵 2012)
生活在這一特定歷史時(shí)期的英國女作家伊麗莎白·蓋斯凱爾極擅長觀察與捕捉并描寫在不同社會(huì)處境中的人們的言行舉止,加之其擁有作為牧師妻子經(jīng)常從事慈善事業(yè)的女性經(jīng)驗(yàn)、對(duì)社會(huì)問題的洞察、對(duì)勞動(dòng)大眾的同情,以及她致力于促進(jìn)社會(huì)不同階層相互理解與包容的意愿,她所創(chuàng)作工業(yè)小說《瑪麗·巴頓》與《南方與北方》中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描寫不僅揭露了維多利亞時(shí)期工業(yè)文明繁榮背后的荒蕪,而且時(shí)時(shí)流露出對(duì)下層貧苦人民的人道主義同情。正如馬克思所言,伊麗莎白作為“現(xiàn)代英國的一批杰出的小說家,在自己卓越的、描寫生動(dòng)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huì)真理,比一切職業(yè)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
長久以來,由于其作品帶有鮮明的女性視角和階級(jí)融合觀念的特點(diǎn),學(xué)術(shù)界多數(shù)從“性別”與“階級(jí)”兩個(gè)主要方面作為宏觀切入點(diǎn)研究蓋斯凱爾夫人的小說。但無論是作為推動(dòng)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的要素,還是充當(dāng)工業(yè)文明背景下富有深意的隱喻,有關(guān)疾病的敘事廣泛存在于蓋斯凱爾夫人的作品之中,是極具研究價(jià)值的主題。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2018)一書中寫到:“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gè)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則屬于疾病王國。盡管我們都只樂于使用健康王國的護(hù)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huì)有那么一段時(shí)間,我們每個(gè)人都被迫承認(rèn)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工業(yè)時(shí)代的人們?cè)谙硎芪镔|(zhì)帶來的極大滿足的同時(shí)不可避免要面對(duì)諸多健康問題,疾病成為物質(zhì)繁榮的陰面,其中最具工業(yè)文明代表性的疾病便是由空氣污染導(dǎo)致的肺病和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壓力引起的神經(jīng)衰弱。在蓋斯凱爾夫人的工業(yè)題材代表作《南方與北方》中,女主人公瑪格麗特的母親黑爾太太和朋友貝西·希金斯,雖享有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社會(huì)地位,卻都是“工業(yè)化”的受害者。(Starr, Elizabeth 2002)她們從患病到死亡的歷程所反映的不僅僅是疾病的外在屬性,更是借由疾病傳遞出了這個(gè)時(shí)代內(nèi)部的病變過程。
一.貝西·希金斯:首當(dāng)其沖的工人階級(jí)犧牲品
工業(yè)革命時(shí)期的英國階級(jí)矛盾嚴(yán)峻,而疾病的風(fēng)險(xiǎn)也是社會(huì)所醞釀的深刻危機(jī)之一。蓋斯凱爾夫人筆下的貝西·希金斯所罹患的結(jié)核病便是具體的、擁有明確致病因素的“時(shí)代病”。肺結(jié)核是一種很古老的疾病,它在十七世紀(jì)就已經(jīng)成為了流行病,但是到了十九世紀(jì)患肺結(jié)核的人數(shù)卻顯著增多。它通常被想象成一種“貧困的、匱乏的病”,與簡陋的衣衫,消瘦的身體,冰冷的房間,惡劣的衛(wèi)生條件以及糟糕的飲食相聯(lián)系起來;恩格斯(1845)還曾在《英國工人階級(jí)現(xiàn)狀》中這么說到:“倫敦特別是倫敦工人區(qū)的壞空氣,最能助長肺結(jié)核的發(fā)展。”這些都是構(gòu)成英國下層人士患上結(jié)核病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注重效率與經(jīng)濟(jì)效益的工業(yè)時(shí)代令絕大多數(shù)追求更高利潤的工廠主盡可能地壓榨工人的生存條件,只有些許具有同情心和道德感的工廠主會(huì)試著改善工作環(huán)境,這便導(dǎo)致工人們拿著微薄的薪資卻做著繁重的工作,需要在擁擠、骯臟且黑暗的工坊內(nèi)忙碌一整天。以貝西·希金斯所工作的梳棉車間為例,當(dāng)女工們梳棉時(shí),“棉花上會(huì)飄起很多一小團(tuán)一小團(tuán)的飛絮。這些棉絮在空中到處飛舞,就像是一片白色的灰塵”(蓋斯凱爾 1994:92)“一直在工作,直到耳朵里總是充滿噪音,嗓子里全是棉絮”,導(dǎo)致貝西像車間里的很多工人那樣時(shí)常咳嗽和吐血。
貝西是千千萬萬因惡劣工作條件而損害健康的女工的縮影,而資本主義為工人提供非人的生活條件正是造成她們患病乃至死亡的根本原因。(劉文青 2019)根據(jù)桑塔格的說法,疾病隱喻經(jīng)常被引入政治領(lǐng)域,成為最順手的修辭學(xué)工具。它“使對(duì)社會(huì)腐敗或不公正的指控顯得活靈活現(xiàn)”(桑塔格 2018)。維多利亞時(shí)代的英國空氣污染嚴(yán)重,受污染地區(qū)居民的平均壽命甚至要明顯低于其他地區(qū);呼吸道疾病成為維多利亞人的一大困擾,肺結(jié)核在抗生素發(fā)明前奪走了無數(shù)人的生命。在工業(yè)文明轟鳴而過的車輪碾壓下,像貝西·希金斯這樣出身于英國底層家庭的女性首當(dāng)其沖,成為了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的第一批犧牲品。工業(yè)革命帶給了女工巨大的災(zāi)難、困苦的境遇、非人的折磨與摧殘,由于所在的行業(yè)并未受到嚴(yán)格監(jiān)管,女工的工作時(shí)間可能會(huì)隨著貿(mào)易量或季節(jié)的變換而產(chǎn)生波動(dòng),這導(dǎo)致女工們?yōu)榱松畈坏貌灰誀奚眢w健康為代價(jià)進(jìn)行工作;她們看似迎來了靠自己的雙手謀生的機(jī)會(huì),實(shí)際上在工廠的日子嚴(yán)重?fù)p害了她們的身心健康,也極易引起墮落。(蔣燕 2013)過度勞累削弱了她們的免疫力,使得她們面對(duì)疾病時(shí)毫無抵抗之力。“從隱喻的角度來說,肺病是一種靈魂病”(桑塔格 2018),此處作為隱喻的結(jié)核病不僅是貝西一人身體缺陷的外在表征,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以貝西為代表的所有女工的生存困境的內(nèi)在隱喻。貝西是被工業(yè)文明所淘汰的人,即“一個(gè)不適應(yīng)社會(huì)的人”,而當(dāng)她所患的結(jié)核病被擴(kuò)散到整個(gè)工人階級(jí)成為了普遍現(xiàn)象時(shí),便是整個(gè)階層都患上了“時(shí)代病”:這是一種工人階級(jí)表達(dá)憤怒的方式,也被用來表達(dá)對(duì)社會(huì)的不滿和焦慮,于是象征著工業(yè)文明的“城市”也被看作致病的環(huán)境——一個(gè)病態(tài)的,充斥著欲望的地方,以此來指責(zé)工業(yè)革命造成的社會(huì)壓抑。
蓋斯凱爾筆下的疾病隱喻充斥著對(duì)工業(yè)文明終究會(huì)波及每一個(gè)個(gè)體的擔(dān)憂以及極大可能引起公共災(zāi)難的不滿。瑪格麗特曾向貝西描述故鄉(xiāng)赫爾斯通的寧靜與美好,那是“關(guān)于鄉(xiāng)間和樹林里發(fā)生的故事”(蓋斯凱爾 1994:90),貝西也時(shí)常流露出對(duì)自然與鄉(xiāng)村的憧憬和向往,可她知曉自己注定終生被困在這個(gè)嘈雜工業(yè)城,這便是她最終的結(jié)局:“天生就該在這個(gè)糟糕的地方染上疾病,像這樣把生命和情感一點(diǎn)點(diǎn)消耗殆盡”(蓋斯凱爾 1994:91)。等待疾病的結(jié)果通常只有兩種:一種是被治愈,另一種則是死亡;而在工業(yè)文明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維多利亞時(shí)代,如貝西這樣被拋在歷史車輪之后的下層工人階級(jí)無從適應(yīng)、更無法改變社會(huì)大環(huán)境。工業(yè)化與城市化已然成為不可逆轉(zhuǎn)的社會(huì)趨勢,“遠(yuǎn)離城市”的夢想注定破滅。因此,治愈疾病的方式只剩下了死亡。
二.黑爾太太:式微南方舊貴族的心疾
除卻在政治領(lǐng)域充當(dāng)修辭學(xué)工具以外,疾病敘事還在美學(xué)或者是道德范疇內(nèi)有所建樹。如果說貝西·希金斯所患的是具體的“時(shí)代病”,那么黑爾太太所患的便是抽象的、具有“貴族病”特點(diǎn)的心疾。女主人公瑪格麗特的母親黑爾太太出身于上流社會(huì)的舊貴族世家,遵循自由戀愛原則嫁給一名清貧的牧師。可美好的愛情并沒有抹去黑爾太太對(duì)婚后生活日益增加的不滿,階級(jí)差異導(dǎo)致夫妻二人在生活習(xí)性上有諸多不合,勤儉拮據(jù)的生活也讓曾經(jīng)養(yǎng)尊處優(yōu)的貴族小姐百般不適,而這種長久的不如意,讓整個(gè)家庭都不和諧。(何申英,樊華 2014)瑪格麗特發(fā)現(xiàn)她那一向十分疼愛她的母親似乎總是對(duì)家里的生活表示不滿,認(rèn)為黑爾先生理應(yīng)擔(dān)任薪水更高的牧師職位,還總說“是家附近茂密的樹林讓她的健康受到了影響”(蓋斯凱爾 1994:14);到了天氣忽冷忽熱的夏末秋初,她又開始覺得“這里的氣候會(huì)讓健康受損了”。
德國學(xué)者維拉·伯蘭特(1986)說: “在文學(xué)介體即語言藝術(shù)作品中,疾病現(xiàn)象包含著其它意義,比它在人們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的意義豐富得多。”黑爾太太從患病至死亡都沒有被醫(yī)生明確地定性過究竟罹患的是何種疾病,仿佛疾病也具有了階級(jí)性和不同的美學(xué)等級(jí),縈繞在黑爾太太周圍的疾病富有一種模棱兩可的神秘性,她所展現(xiàn)的憂郁氣質(zhì)以及敏感羸弱的特性恰好與浪漫派所推崇的疾病之美相吻合——悲傷使人變得“有趣”,而優(yōu)雅和敏感的標(biāo)志正是悲傷。黑爾太太的病更像是一種偏執(zhí),是無法適應(yīng)脫離貴族階級(jí)與生活的意志失敗(Elliott, Williams D 1994),也是源自過于強(qiáng)烈的對(duì)兒子思念的情感。她無比懷念年輕時(shí)和妹妹一起在貝雷斯福德街長大的日子,每天在飯桌上說的英國保皇黨常用祝酒詞:“國教和國王萬歲!打倒殘余議會(huì)!”她也無時(shí)無刻不在思念自己因被陷害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愛子,總是因此而失眠并患上了容易驚醒的病;而當(dāng)她得知連自己素來虔誠的丈夫也背棄了信仰要舉家搬遷到到處都是煙囪和灰塵的工業(yè)城市北米爾頓時(shí),黑爾太太立刻難以承受地病倒了。就連她的貼身女傭狄克遜也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緣由:“似乎太太的問題不是身體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蓋斯凱爾 1994:42)
在資本主義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十九世紀(jì),神經(jīng)的能量被認(rèn)為是有限的,而社會(huì)對(duì)能量的需求則是無限的。罹患精神疾病的人群十分廣泛,無論是窮人抑或是富人都難逃工業(yè)文明快節(jié)奏下的高壓,以及惡劣環(huán)境對(duì)身心健康的影響。(毛曉鈺 2018)處在傳統(tǒng)社會(huì)與工業(yè)社會(huì)的變遷時(shí)期,神經(jīng)衰弱成為了一個(gè)新的醫(yī)學(xué)標(biāo)簽。盡管精神衰弱有遺傳的影響,但是經(jīng)濟(jì)困難和壓力,諸如喪親、家庭困難、憂慮、打擊都是主要的致病因素。小說中瑪格麗特和父親離米爾頓還有幾英里的時(shí)候就發(fā)現(xiàn)米爾頓方向的上空飄著“一層呈現(xiàn)出鐵灰色的云”(蓋斯凱爾 1994:51);新居的環(huán)境也不容樂觀,“濃霧一直彌漫到了窗前,演變成一團(tuán)團(tuán)白色的霧氣,從敞開的門窗里沖了進(jìn)來”(蓋斯凱爾 1994:57),“它們讓人喘不過氣,毫無疑問十分有害健康”;黑爾太太在赫爾斯通居住時(shí)出入都能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但米爾頓的空氣卻沒有一點(diǎn)能夠讓精神振奮的味道;再加上經(jīng)濟(jì)愈發(fā)拮據(jù)后家里總有很多令人心煩的事情,因此家中所有的女性都感到非常不痛快;再者,從婚前的貴族身份到婚后的牧師妻子身份,黑爾太太經(jīng)歷了一個(gè)從上層階級(jí)到中層階級(jí)的心理降級(jí):英國上層階級(jí)的貴族婦女通常享有較高的社會(huì)地位,與此同時(shí)社交的機(jī)遇甚多;下層階級(jí)的婦女則必須通過外出打工養(yǎng)家糊口,因此她們也具備較為獨(dú)立的人格。唯獨(dú)中等階級(jí)的婦女成為維多利亞時(shí)代的典型受害者,她們既不具有社會(huì)性,也缺乏獨(dú)立性。因此當(dāng)黑爾太太得知丈夫要離開教會(huì)去和工廠主打交道時(shí)十分氣憤,她意識(shí)到將來可能再也不會(huì)有上流人士與之交往,而這對(duì)于她而言是莫大的恥辱。正是在這些復(fù)雜要素的綜合作用下,黑爾太太的健康每況愈下。
與人情淡薄的工業(yè)城市形成鮮明對(duì)比的是,蓋斯凱爾夫人筆下的赫爾斯通是一個(gè)帶有強(qiáng)烈情感色彩以及被回憶“濾鏡”渲染過的和諧鄉(xiāng)村社會(huì),在這個(gè)社會(huì)里,黑爾家作為教區(qū)牧師時(shí)常給教區(qū)里需要幫助的人家送去慰問品、用薪水補(bǔ)貼貧窮的老年人,人們相親相愛,互幫互助。蓋斯凱爾以尚未被資本主義勢力蠶食的鄉(xiāng)村小鎮(zhèn)之美反襯出由資產(chǎn)階級(jí)主導(dǎo)的工業(yè)都市的丑陋,同時(shí)也折射出南方封建貴族的遺風(fēng)遭受現(xiàn)代化進(jìn)程沖擊后的逐漸沒落。在全速向工業(yè)文明邁進(jìn)的維多利亞時(shí)代里,像黑爾太太這樣“舊時(shí)代”的遺民不得不面臨著隨生產(chǎn)關(guān)系發(fā)生改變的階級(jí)變動(dòng)。(Jennifer Mary Curtis 1993)再觀蘇珊·桑塔格所言:“疾病本身一直被當(dāng)作死亡、人類軟弱和脆弱的一個(gè)隱喻”,降臨在黑爾太太身上的疾病一方面隱喻著個(gè)體精神上的孤獨(dú),另一方面展露了舊貴族在工業(yè)社會(huì)壓力下的精神病變;“疾病是一種懲罰,病人自己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病,他就是該疾病的病因。”(桑塔格 2018)米歇爾·福柯曾說,“任何一個(gè)威脅固有中心權(quán)力的人都會(huì)被邊緣化”,黑爾太太所遭遇的困境境使她進(jìn)入到一種更加脆弱的生活狀態(tài)之中:不盡如人意的婚姻、社會(huì)地位的突變、財(cái)富的喪失共同構(gòu)造出了一個(gè)夾裹在歷史洪流中無法抽身,飽受工業(yè)文明折磨,并逐漸演變成醫(yī)生口中罹患無名“不治之癥”的絕望舊貴族女性形象。
疾病早已不只是純粹的醫(yī)學(xué)問題,而是廣泛牽涉政治、歷史等文化的多個(gè)面向,經(jīng)過文學(xué)作品加工后被賦予隱喻意義,帶有意識(shí)形態(tài)屬性的主題。現(xiàn)代小說文本里的疾病意象身處數(shù)種不同意識(shí)形態(tài)緊緊包圍的語境之內(nèi),正如《南方與北方》中的疾病,一方面在小說的敘事中承擔(dān)了推動(dòng)情節(jié)發(fā)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憑借其獨(dú)特的隱喻反應(yīng)了維多利亞時(shí)期工業(yè)化背景下的時(shí)代特征和社會(huì)各階層現(xiàn)狀。
蓋斯凱爾夫人根據(jù)疾病造成的兩類不同影響進(jìn)行細(xì)致描述,其一是貝西·希金斯因有形外界因素誘發(fā)出的病變和生理上的痛苦,其二是黑爾太太因無形內(nèi)在因素引發(fā)出的衰弱和精神上的創(chuàng)傷,卻殊途同歸,共同指向了工人階級(jí)和舊貴族階級(jí)在十九世紀(jì)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的沖擊下失敗的求生之路。約翰·鄧恩曾提到:“生病是最痛苦的,而生病的最大痛苦來自孤獨(dú)”,但疾病卻將黑爾太太和貝西這兩個(gè)階級(jí)出身截然不同的人聯(lián)系在一起,如黑爾太太所言那般:“好像大家全都得病了”。傳統(tǒng)的生活已經(jīng)逝去,無法適應(yīng)工業(yè)化進(jìn)程的人終將被時(shí)代潮流所淹沒。
參考文獻(xiàn)
[1]齊驥,滕海鍵.英國工業(yè)革命時(shí)期的城市環(huán)境問題[J].綠葉,2012(08):14-21.
[2]Starr, Elizabeth. 'A GREAT ENGINE FOR GOOD': THE INDUSTRY OF FICTION IN ELIZABETH GASKELL'S MARY BARTON AND NORTH AND SOUTH.[J]. Studies in the Novel, 2002.
[3]伊麗莎白·蓋斯凱爾.主萬,譯.南方與北方[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4.
[4]蔣燕.19世紀(jì)英國婦女就業(yè)的困境及其原因[D].四川師范大學(xué),2013.
[5][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M].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6]劉文青.探尋社會(huì)問題的解決路徑[D].南京師范大學(xué),2019.
[7]何申英,樊華.《南方與北方》中工業(yè)革命時(shí)代背景下的愛情觀[J].名作欣賞,2014(35):155-156+167.
[8]維拉.伯蘭特.文學(xué)與疾病——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一個(gè)方面[J].文藝研究, 1986.
[9]Elliott, Williams D . The female visitor and the marriage of classes in Gaskell’s North and South.[J].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1994.
[10]毛曉鈺.19世紀(jì)英國工業(yè)革命帶來的健康問題[J].科學(xué)文化評(píng)論,2018,(02):29-39.
[11]Jennifer Mary Curtis. Illn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emininity in the English Novel,1840-1870[D].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1993.
(作者單位:江蘇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