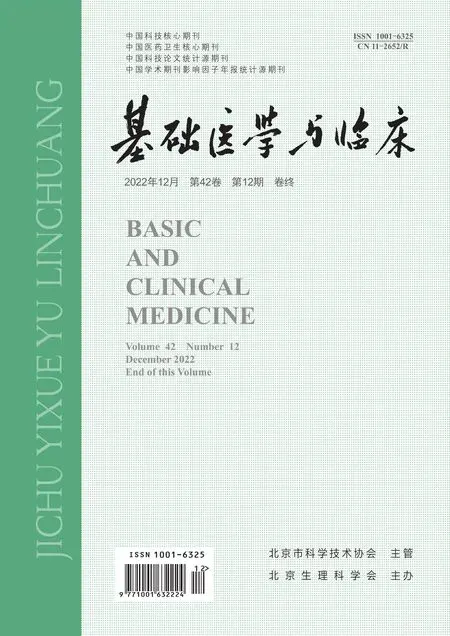Blau綜合征的研究進展
寇玉輝,葉菜英,邢成鋒*
(1.廣州銀珠生物醫藥技術有限公司,廣東 廣州 510700; 2.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 藥理系,北京 100005)
Blau綜合征(Blau syndrome,BS)是兒童肉芽腫性自身炎性疾病的家族性和散發性形式,屬于單基因自身炎性綜合征,由核苷酸結合寡聚化結構域蛋白2(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2,NOD2)基因突變引起。1895年兒科醫生Edward Blau 首次描述該疾病為一種遺傳性慢性炎性綜合征,一般4歲之前發病,發病時的表現通常以關節和皮膚癥狀為代表,隨后是眼部表現。不典型的BS病例涉及心血管、神經、腎臟、腸道和其他器官。BS還沒有專門的治療方法,主要采用經驗治療。國內近年來報道的患病人數逐年增多,基因檢測手段也普遍用于疾病的診斷。本文就BS的病因、發病機制和模型研究、治療進展做一綜述。
1 Blau綜合征的病因
BS屬于自身炎性疾病(autoinflammatory diseases,AIDs),最早被認識的AIDs是一組符合孟德爾遺傳規律的周期性發熱,稱為遺傳性周期性發熱綜合征,其特征是不定期或周期性發作性發熱伴局部炎性,包括家族性地中海熱(familial Mediterranean fever,FMF)、或冷炎素相關周期性綜合征(cryopyrin-associated periodic syndrome,CAPS)、Blau綜合征等。
NOD2蛋白是調節先天免疫的關鍵分子之一,由NOD2基因編碼,主要在抗原遞呈細胞中表達。先天免疫中的錯誤識別造成AIDs的發生,這是一系列T細胞和B細胞很少或沒有參與的異常炎性疾病。遺傳性AIDs往往以兒童發病為先兆,表現為典型的炎性癥狀和發熱,而未確定病因的AIDs則源于遺傳因素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一些退行性和代謝性疾病,以及由核轉錄因子(NF-κB)和干擾素介導的疾病也被定義為AIDs。
BS是由NOD2突變引起,NOD2突變導致其編碼蛋白NOD2受體發生活化,激活NF-κB通路,產生大量炎性因子,導致炎性反應持續過度,表現出一系列的病理生理變化及臨床表現。
2 Blau綜合征的發病機制
2.1 CARD15/NOD2
BS遺傳位點的首次報道與克羅恩病(Crohn disease, CD)相關,該基因位于常染色體16q12.1-13上[1], BS是由于胱冬蛋白酶激活與募集區(caspase activation and recruitment domain 15, CARD15/ NOD2) 基因突變所致。CARD15/NOD2編碼含1040個氨基酸的核苷酸結合寡聚蛋白2(NOD2),NOD2含有3個不同的功能結構域,C端富含亮氨酸的重復序列(leucine-rich repeats,LRRs),N端包含了2個caspase募集結構域(CARDSs),中央區為核苷酸結合寡聚化結構域(NACHT)。LRRs與配體結合可誘導NACHT發生寡聚化,通過其CARD分子與受體相互作用蛋白RICK(RIP2-like kinase)相互作用,最終導致核轉錄因子(NF-κB)活化及前炎性細胞因子轉錄合成[2]。
近年來,對不同人群的BS發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至今為止未有明確的BS發病率。已在不同人群的BS患者中發現不同的CARD15/NOD2突變,最常見的突變是影響高度進化保守精氨酸的錯義替換位置334處的殘留物(R334W或R334Q)突變。這些突變的等位基因密碼子334成為突變的遺傳熱點。中國BS患者以R334W、R334Q和C495R發生頻率最高[3]。
NOD2主要在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中表達。除了產生炎性細胞因子,NOD2也可以通過NF-κB和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通路上調趨化因子的產生,以募集對根除細菌病原體至關重要的免疫細胞。NOD2促進腸中Ly6C單核細胞的CC趨化因子配體2(C-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2, CCL2)依賴性募集。
2.2 炎性因子
BS被歸類為典型的自身炎性反應疾病。BS的發病機制可能不僅僅是由骨髓細胞控制的炎性微生物信號驅動的,還可能包括失調的T細胞反應。這是基于明顯缺乏高滴度的自身抗體如:類風濕因子(rheumatoid factor,RF)抗體、抗核抗體(anti-nuclear immune body,ANA)、抗中性粒細胞胞質抗體(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ANCA)和與其他核苷酸寡聚化結構域(NOD)樣受體(nucleotide-binding domain and leucine-rich repeat,NLR)介導的自身炎性疾病表型相似性,推測這是由于先天性髓系細胞過度產生IL-1β等炎性因子。
對轉染NOD2或變異的Blau NOD2的HEK細胞系研究顯示,在基線水平上NF-κB活性過高,并對免疫反應肽(muramyl dipeptide,MDP)有反應,提示在BS中NOD2信號軸過度激活。然而,最近來自BS患者的外周血單核細胞(peripheral blood monouclear cells,PBMCs)或單核細胞的體外研究顯示,在MDP的作用下NF-κB活化和IL-1β等細胞因子降低,提示髓系細胞功能喪失或“耗盡表型”。來自BS患者的巨噬細胞中MDP信號通路和NF-κB活化受損,功能失調的NOD2引起的高致病性Th17細胞可能與BS發病有關。來自BS患者的T細胞在T細胞受體(T cell receptor,TCR)傳遞時產生過量的IL-17和過度表達的CCR7。雖然這種特別罕見的疾病患者樣本數量很少,但這些患者眼睛和皮膚肉芽腫中的效應/記憶CD4+ T細胞增加,這也與IL-17和IL-23R免疫反應性增加相吻合[4]。
2.3 環境因素與Blau綜合征的誘發
雖然不經刺激不會改變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但表達NOD2的突變型THP-1細胞在乙酸肉豆蔻酸鹽刺激后持續附著在培養板上。與這一現象相關的是表面細胞間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ICAM-1)的持續表達,但沒有發現ICAM-1 mRNA和受損的解聚素-金屬蛋白酶17(ADAM17)mRNA持續表達。然而刺激后的THP-1衍生物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B(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B,PDGF-B)mRNA瞬時誘導表達。在一例BS肉芽腫性皮損中,表達NOD2的巨噬細胞免疫染色顯示ICAM-1和PDGF-B陽性。這些表明攜帶突變NOD2的新分化巨噬細胞持續表達表面ICAM-1和短暫產生PDGF-B可能在BS肉芽腫形成中起作用[5]。
近年來臨床研究結果表明外部環境刺激因素可誘發BS。NACHT 分子突變可能是一種功能獲得性突變,由于 NACHT 寡聚化與 NF-κB 活化有關,推測其基因突變可造成NACHT分子持續寡聚化,從而降低NF-κB活化閾值,輕微刺激或無刺激即可致NF-κB活化及前炎性細胞因子釋放。干擾素γ同樣也可以誘發BS,接種卡介苗、某些細菌、毒素等因素啟動了NF-κB或者干擾素γ的活化同樣也可誘發BS[6]。
IFN-γ刺激是驅動BS相關巨噬細胞異常炎性反應的關鍵信號之一,IFN-γ通過上調NOD2發揮啟動信號的作用。然而,即使在IFN-γ刺激的情況下,抗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藥物的長期治療也能改善這種異常。因此,在巨噬細胞發育過程中,預先暴露于TNF或功能類似的細胞因子誘導NF-κB驅動的促炎信號是IFN-γ刺激BS中加速炎性反應的先決條件[7]。
2.4 Blau綜合征的藥理模型研究
BS存在多種臨床表現,根據發病機制和臨床表現,多種藥理模型在藥物研發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2.4.1 基于誘導多能性干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s)的疾病模型:iPSCs模型已經有效地用于各種小兒疑難疾病的診斷、病理分析和治療開發,成為疾病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其特點是可以從遺傳性疾病患者的血細胞或皮膚成纖維細胞中建立,具有與患者相同的基因表型,可以制備顯示疾病表型的細胞類型,如中性粒細胞、單核細胞和巨噬細胞。因此,iPSCs模型有望促進對自身炎性疾病,特別是單基因突變引起的自身炎性疾病的認識和治療。自身炎性疾病研究中經常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病例數少。當只有一兩種情況下可以建立iPSCs時,通常很難獲得統計上可靠的數量表型。在這些情況下,通過基因組編輯技術生成等基因對等體,能夠更可靠地評估突變的表型影響[8]。
但在某些情況和疾病中,使用iPSCs在體外復制表型細胞的準確性尚未被確定。在這些情況下,需要仔細選擇所需的細胞類型和優化分化,選擇適當的刺激來獲得與自身炎性相關的表型也很重要。
2.4.2 計算機模型:隨著計算機系統在藥物研發以及臨床研究中的應用普及,其在疾病模型中具有廣闊的應用發展前景。研究報道利用計算機模型從UniProt、ClinVar和HGMD等數據庫中檢索了144個錯義突變,其中17個突變是最具致病性的突變,通過分子對接分析,了解ADP與NOD2蛋白相互作用的變化。可以從分子動力學模擬中了解NOD2蛋白和基因突變的聯系,該模型研究有助于理解ADP和ATP之間的突變和切換在ADP與NOD2蛋白結合中所起的作用,從而了解BS的發病機制,有望為開發BS靶向藥物治療提供平臺[9]。
3 Blau綜合征的臨床治療
目前BS的治療方法較多,然而這種基因突變的變異與治療反應之間的關系尚不清楚,目前還沒有特異的治療方法。以往治療多采用逐級遞增治療方案,優先使用皮類固醇糖皮質激素,然后在藥效不滿意的情況下,使用免疫抑制劑進行額外治療。
3.1 類固醇糖皮質激素
低劑量糖皮質激素被認為有助于控制BS葡萄膜炎及關節癥狀,在急性期大劑量糖皮質激素有助于控制癥狀。但是糖皮質激素的不良反應包括高血壓、生長遲緩、庫欣綜合征以及眼壓升高等,在BS的治療尤其是在兒童患者治療中限制了其臨床應用[10]。
3.2 免疫抑制劑
傳統的免疫抑制劑在BS治療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甲氨蝶呤(methotrexate,MTX)對關節癥狀的改善,沙利度胺對皮膚癥狀的改善,以及抗腫瘤壞死因子(TNF-α)抑制劑對癥狀的改善。但是用甲氨蝶呤、抗腫瘤壞死因子(TNF-α)抑制劑和皮質類固醇治療后,臨床癥狀和炎性指標可能得不到有效控制,還會出現多種不良反應。沙利度胺治療的病例數有限,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評估沙利度胺長期療效和不良反應。
酪氨酸激酶(Janus kinases,JAK)抑制劑托法替尼對BS有顯著的療效。托法替尼可以有效抑制肉芽腫組織中的磷酸化和信號傳導及轉錄激活因子1(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1,STAT1)。托法替尼治療后BS患者的臨床癥狀和血液指標均有顯著改善,可顯著降低非JAK-STAT通路直接介導的TNF-α以及依賴于JAK-STAT通路的干擾素-γ(interferon-γ,IFN-γ)水平,同時可抑制TNF-α和IL-6以及其他炎性細胞因子的產生[11]。
3.3 生物制劑
近年來,抗腫瘤壞死因子α制劑等生物制劑在BS治療中的應用逐年增多,但由于其安全性較低且繼發性失應答率較高等,臨床應用受限。隨著新型生物制劑不斷涌現,BS的治療進入生物制劑時代,新型生物制劑有可能成為BS藥物治療的主體。
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1,IL-1)抑制劑治療BS有顯著效果,但最新的結果表明一些患者體內IL-1β并沒有顯著升高,在這些患者的血清中或在MDP刺激的MNC培養中無法檢測到IL-1β,IL-1β抑制劑對這些患者的治療也無反應。
托珠單抗用于類風濕關節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對一種或多種抗風濕藥物(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DMARDs)反應不佳的成人中度至重度活動性類風濕關節炎有顯著療效。托珠單抗易產生耐藥性,在治療過程中可能產生抗托珠單抗IgE抗體而影響其療效。
英夫利昔單對關節癥狀有效,還能預防眼部重癥癥狀的發生。阿達木單抗用于非感染性葡萄膜炎的治療,并對眼部癥狀、關節癥狀和全身癥狀起緩解作用。依那西普在兒童BS患者中的應用已有報道[12]。
4 問題與展望
目前針對BS仍無理想的治療手段,主要采用經驗治療。然而早期診斷可以預測未來可能出現的癥狀,及時治療可以預防或延遲嚴重癥狀(關節攣縮和失明)的出現。隨著對BS發病分子機制的深入研究,從分子水平遏制BS的發生和發展已成為未來BS藥物治療的主要方向。生物制劑在BS臨床治療仍處于探索階段,但仍給患者帶來新的希望和曙光。在疾病的早期應用TNF-α抑制劑藥物以及生物制劑藥物對預防疾病的進展起重要的作用。新型小分子藥物在近幾年發展迅速,新靶點的發現也為高效特異性藥物的開發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