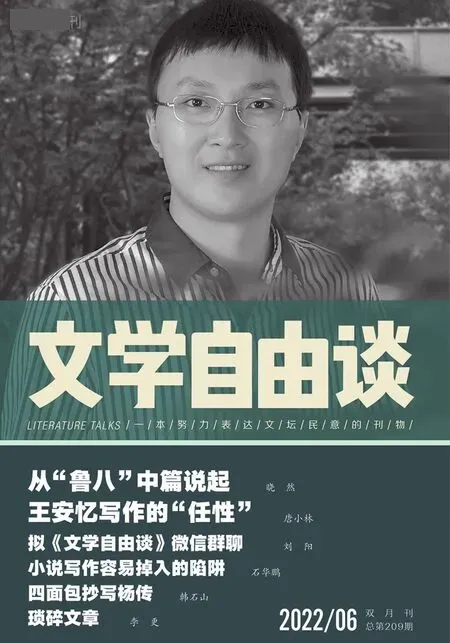從“魯八”中篇說起
□曉 然
《讀“魯八”短篇想到的》(見《文學自由談》2022年第5期)一文發表后,有讀者即在該刊公眾號留言:“‘魯八’中篇存在的問題,或許更值得談談。”更有讀者去信編輯部,稱:“《文學自由談》這一期發表談‘魯八’短篇小說的文章,朋友們都說寫得很好。大家還建議作者談談‘魯八’中篇小說,請編輯部斟酌,可否把讀者意見轉給該評論家?”輾轉得知,這是湖南的一些老作家,點名讓我這名不見經傳的“評論家”繼續談談“魯八”中篇。
其實,此前早有幾個與我私交甚厚的小說家,在讀到“自由談”文章并向我求證后,也在微信里不斷鼓動我:“再談談唄!”我當然知道他們看熱鬧不嫌事大的心理,而且,我還知道,他們自己的魯獎參評作品最終沒能上榜,現在一看有人出來對獲獎作品“扯閑篇”,正捂著嘴樂見其成呢。我會上他們的“當”么?
會。
被讀者“牽引”、被朋友“拱火”而走進“魯八”中篇閱讀現場,最多算個外因,主要原因卻是:我算個文學職場的“專業讀者”,而且已經做了大半輩子。我這“專業讀者”,并非自封,有證明這份職業的薪水、頭銜及其他旁證擺在那里;至于到底怎么個“職業”法,不在本文論述范圍,不說也罷。
就體量而言,“魯八”五部中篇,遠大于短篇,要一氣讀完這些沉甸甸的篇目并寫下“札記”,我還是有點兒犯怵的。但是我必須擺開架勢認真閱讀。為了閱讀札記的“可靠”,我特意做了個小試驗:邀請幾位朋友,在不同的地方,與我一起共讀。他們分別是:作家(以小說為主)、教授(包括副的)、文學博士(在讀)以及某位時間和財富相對自由者(曾經的文學女青年)。當我用微信把“請求”分別向他們提出時,出于多年的“文學友誼”(部分還有早年的師生之誼),他們沒有直接拒絕,但都告訴我:沒讀過(僅有寫小說的一人表示,曾讀過其中少數篇什,但已經印象全無)。這個好辦。我給他們分別郵購了新鮮出爐的某刊“魯八”專號,并約定了反饋“心得”的“交卷”時間——十月七天長假結束之后。于是,天南地北的我們,開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魯八”中篇閱讀。
以下,為陸續收到的閱讀反饋(摘要)——
甲:幸好有老師布置的這道額外作業,要不喜歡長假湊熱鬧的我,很可能現在還連人帶車困在“靜默”的某地呢。
先選出我比較喜歡的兩部吧:《過往》和《荒野步槍手》。《過往》好在善于講故事,《荒野步槍手》好在善于寫人。講故事和寫人其實關乎小說存在的合法性,完全離開這兩個要素而存在的小說是難以想象的。《過往》開篇即先聲奪人,以咖啡館預謀殺人現場啟幕,勾起閱讀的懸疑期待,但這不過是一個噱頭。真實的過往,既是天下熙熙攘攘的過往,也是人生愛恨情仇的過往。小說在不斷翻轉中,將有故事的一家兩代的命運描繪得跌宕起伏,讓人讀來欲罷不能。《荒野步槍手》寫人,貴在一個“準”字,精準的語言如同狙擊步槍手每槍都精準上靶,且在十環,語言簡潔明快,情節層層遞進,人物性格鮮明,呼之欲出,讀來過癮。
乙:多數都讀不進去啊!比如那個《飛發》,雖說普通話是全篇基調,但夾雜太多粵味港味包括吳儂軟語的方言串燒,這種所謂的地域性,太燒腦又容易出畫分神,不是讀小說的節奏吧?而且,你看我從小說中隨手抄下的這一段:“二十世紀整個六十年代,是香港工業騰飛時期。由1962年至1973年,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GDP撇除通脹后,每年以9.4%復式增長。1962年的本地生產總值為86億港元,上升至1973年的410億港元。一九六〇年代,香港工業成就舉世知名,是全球最大的紡織制衣、鐘表、玩具、假發、塑料花等的出口王國;旅游業亦享有盛名,有‘購物天堂’之稱。就業情況良好,失業率幾乎接近零……”
這樣的段落可不是只此一處哦。我也知道這是作家借助統計數據用以表達香港巨變的“快進”之筆,但這能算與讀者早已達成過默契的小說語體嗎?寫者或許自以為是語言創新,但評委沒覺得這樣的語體別扭丑陋嗎?
讀不進去還有一個原因:大多數獲獎小說離我們真實的現實生活距離較遠。我當然知道文學不是新聞,不能奢求獲獎小說一定要關注到時下社會熱點和現實普遍困惑,但也不能大多是變著法兒的贊美詩或表揚稿吧?瀏覽了所有篇目之后,我有隱隱的失望和不滿。
丙:假!那個寫核工業題材的,寫了個“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真正的男一號。他最早出場時,還是一名剛剛熱戀的大學畢業生,卻猝不及防地遇到一道大考:要面前活色生香的戀人,還是要遠方看不見的事業和理想?“潘大興的態度很明確……他確實很愛她,但如果讓他在顧芳和去那邊工作二者之間選擇,他只能選擇后者。”他是如何做到斬釘截鐵毫不猶豫的?沒有必要的鋪墊嘛。難道只有我對那個年代單純圣潔的英雄不能理解嗎?還是因為作家認為在這些細枝末節上不必拖泥帶水而一筆略過?
丁:讀這些小說要考驗耐心、細心和一點文學素養。至少《荒野步槍手》《紅駱駝》是這樣子。兩部作品都采取了“彎彎繞”的寫法,即以瑣屑寫宏大,以庸常寫崇高。讀者需要耐著性子,讀到最后才能感知作家的“良苦用心”,才會被淹沒在塵封歲月或滾滾沙場的英雄所打動。《過往》倒是容易進去,但后半盤有點像散沙。《荒原上》也有同感。以前常說某些好的小說存有“半部小說”的遺憾,意思是前半部分比較好,緊湊,精致,藝術邏輯合理,而后半部分“拉胯”,丟三落四,后語不搭前言,“抖包袱”變成多余的包袱皮兒,就像長篇連續劇導演少了跟班的“場記”一樣,顯出作家在后半盤思維和體力的明顯跟不上。這種現象通常說的是長篇,但現在中篇也出現這個問題了。
戊:為什么是這么五部?我來猜猜答案:一是主題和題材。核工業,現代強軍,脫貧和鄉村振興,回歸前后的香港,當然也有傳統戲曲和都市紅塵相交織的。重大吧?正能量吧?二是地域和作者。內地都市和香港城市各一,其余故事的發生地,都在西部——核工業一篇寫西北戈壁沙漠深處的礦區,沙場秋點兵是內蒙戈壁荒漠,雪域高原滅鼠的故事發生在青海大山,都是人跡罕至的艱苦地區。這是一種明示也是一種鼓勵:作家應該到艱苦的地方去,寫底層光榮的奮斗者。至于作者的年齡段,一個偏資深,相對中年和青年各二,沒有特別老的也沒特別小的,且兼顧了軍隊作家、少數民族作家、香港地區作家等不同作者身份。稍微沒照顧到的是性別,中篇這里全部是男的(當然在短篇以及詩歌特別是散文中基本扯平)。那些特別老的“大前輩”作家,好像通常出現在茅獎中,王蒙、徐懷中……都上過那個份量更重的榜單吧?
己:我在海邊。出發前忘帶雜志了。
最后這個朋友,發來一連串“拱手抱拳”的表情包,告訴我:她溜去了泰國。然后發來一組芭堤雅海灘寫真,以示“此言不虛”。
現在該收攏思緒,談談我的閱讀心得了。
上述“讀者”觸碰到的問題,有相當部分,其實也是我在閱讀“魯八”中篇時感知并想深入討論的話題。如果把話題談得集中一些,我覺得,首先需要重點關注兩點:一是這些獲獎作品到底成色如何?二是為什么這些作品可以獲獎?
一般說來,看取一部中篇小說的藝術成色,憑借常識范疇的審美經驗即可做出判斷。“魯八”五部獲獎中篇,都以寫實的現實主義文學為其表征。因此考量其藝術成色,自然應該以現實主義文學作為參照,看看這些作品在汗牛充棟的現實主義文學之林中,又有哪些長足的進步或嶄新的異質。
平心而論,還是可以看到一些閃光之處的。
比如增添了一些比較新鮮別致生動典型的人物形象。《荒野步槍手》開篇就“先聲奪人”,這聲音來自一個不知道什么時候從“車底下”鉆出的“白瘦的中士”:
“領導,您有意見我們虛心接受,做得不對您盡管批評。”中士停了幾秒鐘,“不過說話最好不要帶臟字,畢竟這種話大家都會說,您覺得呢?”
中士的這段發聲有個前置場景:一輛軍用大卡車開往演習沙場,車廂里坐了前去采訪新聞的少校記者“呂”、體驗生活的作家“他”。途中,因為憋尿和解開卡車篷布遇到的麻煩,少校記者與中士發生了齟齬,并順口說出臟話——這在軍隊曾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白瘦的中士”卻不卑不亢地說出這一段軟中帶硬的話,一個有個性有見識且有分寸的現代軍人形象呼之欲出,由此勾起敘述者“他”帶著讀者一起,開始了對這個“白瘦的中士”即“荒野步槍手”的琢磨關注。
《荒野步槍手》里的中士身上有一種非常特殊的軍人氣質,簡言之可以稱為是“現代性”。這種現代性既是傳統軍人固有精神基因的有效延展,又有著屬于他的時代的鮮明烙印。兩代軍人對比中的無痕敘事,顯示出寫作者觀察入微又駕輕就熟的藝術功力。《荒野步槍手》的中士形象讓我一下子想起徐懷中《西線軼事》里的“劉毛妹”——那個從一開始“玩世不恭”到最后慷慨赴死的底層軍人,是那個時代“假大空”文學英雄形象的終結者。《荒野步槍手》的中士形象,是不是也具有軍人典型畫廊相似的里程碑意義呢?
而且不止于這位中士形象新鮮別致,那個著墨不多的少校記者“呂”,也寫得特別鮮活,特別具有“鏡子”一樣的反射和映照價值。可以看出,《荒野步槍手》的作者王凱是當代軍旅文學以徐懷中、李存葆為代表的這一脈的優秀后來者,不見硝煙寫硝煙,跳出戰場寫軍旅,對傳統意義的軍旅題材實現了某種程度的超越,從而獲得了難能可貴的心靈自由——這對于軍旅文學創作而言,有著非同一般的價值和意義。如果要追溯到其理論源頭,則可以回到恩格斯關于現實主義文學的那個著名論述:“除了細節的真實,還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也可以用來回答前述問題:什么是《荒野步槍手》的藝術成色,為什么它可以獲獎。
相似的成績也體現在《過往》《紅駱駝》等篇什上。《過往》提供了一個罕見的“青衣”母親形象。這個女性似乎只為戲曲而生,為戲曲中的角色而生。作家艾偉試圖通過小說完成他對人性的勘探——人性中的黑暗與光明、毀滅與重生、寬恕與警醒,糾纏在瘋狂的青衣和她的家庭以及三個孩子之間。艾偉以其洞幽察微的敘事,有力量地詮釋著他對人性之美德和丑惡的真切理解。《紅駱駝》講究的是虛實關系的處理。近景的實和遠景的虛,生活現場的一地雞毛與遠方的風景和詩,寫得克制而別致,通篇有著引而不發的彈性和張力,有“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意境和想象,有理想主義的光芒和召喚。
相形之下,雪域荒原上冬季滅鼠的故事卻講得不盡如人意。與《荒野步槍手》和《紅駱駝》相似,這也是一個西部故事,也有鮮為人知的故事和場景,而且作者還有過與故事人物相同的浸淫其中的人生經歷和深度體驗。作家力圖用疙里疙瘩的語言還原人物的獨特習俗以及生活場景,應該說一開始也帶來了某種程度的閱讀驚喜。但隨著故事情節的演繹發展,人物的性格和命運越來越多地出現了設計安排的痕跡,說到底是一種筆力不逮之使然。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飛發》中,據說作者為觀察和感受港式理發,甚至有過多次深入實地的調研和體驗;但最終的講述和呈現,猶如拼貼的碎片,拉雜松散,讀過即忘。
本文無意于全面展開研究評析這些獲獎中篇的優長或得失。給我總的印象是,“魯八”的幾個中篇,放在整個中篇小說序列中,是無足輕重的,沒有特別讓人驚訝或驚喜的。當然這可能與當下中篇整體呈下降趨勢有關。
“魯八”中篇評委之一謝有順說:“總體而言,報送的兩百多部作品,質量并不理想,比之以前,中篇整體質量是下滑的。我沒有讀到那種令人眼前一亮、錯過了就會覺得有重大遺憾的作品。”我們簡單回顧一下。中篇小說的發端之作,是1921年魯迅在《申報》連載的《阿Q正傳》,誕生至今剛好百年。但中篇小說的“好日子”,也就是最近四十來年——可以說,中篇是改革開放的時代產物,在差不多四十年的時間段里,中篇獨領文壇“風騷”,曾是勢頭最猛、發展最好、水準最高的一個小說門類。這與它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所有好處有著直接關系。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各地各種大型文學刊物風起云涌,它們好像就是中篇小說的催生婆或產床一樣,就等著好的中篇小說呱呱墜地,茁壯成長。一些刊物因為發表了一兩部優秀中篇而洛陽紙貴,一些小說家因為創作了一部或幾部好的中篇而青史留名。比如蔣子龍、張賢亮、諶容、陸文夫、從維熙……跟他們的名字連在一起的,一定是《喬廠長上任記》《綠化樹》《人到中年》《美食家》《大墻下的紅玉蘭》這些作品。盡管他們此前此后也曾寫過無數短篇和相當數量的長篇,但對他們而言,被讀者和文學史記住的,一定主要是他們的中篇。
反觀眼前這些中篇,我武斷地研判,會被讀者記住的可能會較少,會經受住時間淘洗成為經典的則更少或者沒有。我這樣說,首先是以我自身的閱讀體驗為依據——不到半個月時間,我和我們(那個特邀的閱讀團隊)已經不能清楚記得這些剛被認真仔細閱讀過的作品,人物都長什么模樣,故事是如何發展的,精彩細節或對話都有哪些……被人記住并且準確復述,對于小說而言,以此作為評判好壞的重要標準,這或許會被認為是一種苛求。就像有人喜歡拿現代詩歌和舊體詩詞相比較——隨便一首唐詩宋詞,就可以讓人出口成誦,張嘴就來,而再好的新詩,有幾首能夠被人記住甚至背誦的?但這其實是個偽命題,沒有可比性的。還是拿幾十年間的小說來說事,比如:你讀了《西線軼事》,你會忘記劉毛妹桀驁不馴的樣子以及電話班那群可愛的女兵嗎?讀了《高山下的花環》,你會忘記貼在烈士胸口的那張欠賬單以及那份專為高干子女臨陣逃脫曲線調動的調令嗎?有人也許會說,這兩部與戰爭有關的小說是因為過于血腥濃烈而讓人過目不忘,好吧,來點清淡的,比如遲子建的《清水洗塵》,多年后我還是記得那個叫“天灶”的一大家子人,在每年臘月二十七,全家燒水洗去塵垢的場景。因為小說里的東北人一年到頭就像樣兒地洗那么一回澡,這場面就格外有故事、有儀式感,也格外有“說道”;潘向黎的《白水青菜》更讓我記憶猶新,兩個女人一個男人和一罐“白水青菜”的故事,多年以后我甚至還聞得到其中深藏不露的誘人氣味兒——而這些,也不過是十年二十年間獲得過魯獎的小說。它們怎么就那么“能”釘在記憶的柱子上櫛風沐雨呢?
時間無法穿越,在這里討論十年二十年以后是否還有人記得住今天這些小說,這本身就是個無意義的話題。那么我們來討論一個或許比較現實也比較有意思的話題:為什么是這五部獲獎?
有人會說,因為魯獎評獎規則設定了每個種類有五個獲獎名額,所以總會有五部中篇高中上榜,“名垂”魯獎,意思是,獲獎作品在必然中帶有一定或然性。這話聽起來說得不錯。謝有順說:“評獎,常常融匯有平衡、妥協和遺憾。”本屆評中篇的另一位評委饒翔說了他的“遺珠之憾”:有一些個人風格突出的作品,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未能最終獲獎,但它們也是我的“心頭好”,如孫頻的《騎白馬者》,才華橫溢,氣象萬千;海勒根那的《巴桑的大海》,空間遼闊,感染人心;馬小淘的《骨肉》以“酷”寫“情”,倍顯真摯。饒翔還開出“支票”,表示“相信這些年輕作家憑借自身才華,會在未來給我們帶來驚喜”。這位評委提到的年輕女作家孫頻,確實是近年在中篇領域“才華橫溢、氣象萬千”的佼佼者。我讀過她的大多數中篇,原以為此次應該是上榜概率很高的作家,因為國內所有重大的主流文學評獎,既是評某部單篇作品,也是對某位作家一時甚至一世的綜合評價。對孫頻,當然還遠到不了“一世”的定評,但以她正勁的風頭,且有中篇總體萎靡相襯托,從她得到推薦的數部作品中挑選一部上榜,本來不是難事。為什么卻沒有呢?
這恐怕就要說到評審團拿捏的當下評審標準了。看官也許會說,標準不就是“評獎條例”,一直擺在那里嗎?是,也不全是。條例是死的,不同時空之下掌握、執行條例的人卻是活的,評委以及最終的把關者會根據條例自由裁量并予解釋,所謂與時俱進,此之謂也。
那么時下又會如何自由裁量呢?我不是評委,當然不得而知,也不妄加推測。但評審團中擔任小說評委副主任的潘凱雄專門撰文告訴了我們答案:
任何一項評獎都會有自己的標準,理直氣壯地張揚自己的主張十分正常。作為國家級最高文學獎項之一的魯迅文學獎,以國家意志、家國情懷、藝術精湛作為自己的選擇標準本是題中應有之義,也完全符合厚重內容與藝術個性完美融合的藝術規律。
這個表述,比較清楚地說明了為什么是這五部而暫時還不能包括孫頻那樣的作品獲獎的主要原因。我以獲獎作品中題旨趣味相對靠近的艾偉《過往》,來與孫頻做個比較——兩者都在努力以小說勘探人性,但艾偉對人性的把握要謹慎穩重一些;孫頻則更加自由狂放地深挖貧窮和野蠻導致的人性之惡——我記得她的中篇《柳僧》,就寫到瘆人的程度。小說寫一對開車回山西鄉下老家的母女,原本是送骨灰入土為安的,卻“嘚瑟”了一段“衣錦榮歸”的插曲,最后引來無比凄慘恐怖的結局:母親在探視了早年心儀的男人之后,被窮困潦倒的獨眼老男人率領倆兒子攔路于荒道,“三人在沒有麥子可收的季節各持一柄鋒利的鐮刀”,手起刀落就讓還沒反應過來的母女成了葬身柳林下的冤死鬼。《過往》的母親也是一個人性撕裂的形象,她雖然以羸弱之軀在最后也手刃了企圖謀害兒子的刺客,但艾偉文字的描述是節制的,其表達的重心與孫頻相比也絕對是兩種——這或許就是閱歷、職業、性別、年齡和審美意趣的差異使然,落實到文本上,兌現為作家個性或風格也說得通。
時下有個熱詞叫“行穩致遠”。文學評獎的行穩致遠是什么?從“魯八”中篇結果來看,我見到的關鍵詞是“穩重”——主題和題材乃至文風,都趨于穩重。面對小說的多義性和豐富性,穩重甚至保守的評獎考量似乎可以規避某些風險。這是前所未有的。有分析認為,本屆魯獎中篇小說獎獲獎作品有亮點,有新意,但偏于穩重。這位分析者還說:這次評獎,我感覺,大家明顯更傾向有時代感、有大局觀的作品,對文字細節也更加注意了。可見,作家如果要參評這些主流獎項,不能只琢磨自己的藝術趣味,還要傾聽現實的聲音,對時代性的命題也要有回應。小情調、小趣味的寫作很難再感動評委了,大家還是希望在獲獎作品中碰到一些有重量的話題、有使命感的思索。當然,如果純屬個人寫作,不參評獎項,作家大可自由書寫、自由發揮。
這實際上揭橥了一個秘而不宣又人所共知的“秘密”:主題寫作正在日益受到重視強化,特別在重大文學評獎等重要文學活動中明顯增加了權重。以前,配合節點、節日或重大主題的創作也受到關注重視,但在最高文學殿堂主導的文學評獎中,其位置還不是特別突出。今非昔比,主題創作已成大勢,而且一定還會不斷增加其優先和權重。這對于重視評獎的寫作者尤其是值得關注的。事實上,爭取獲獎特別是獲得重要的文學獎項,這是大多數寫作者的光榮與夢想。在我看來,寫作從來就有多種價值取向:依靠作品自身實力去爭取獲獎特別是獲重要大獎,這是名利雙收的快車道,也是無可厚非的一種取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不必在意獎項,超越功利的寫作,肯定是值得鼓勵、卻也很難以堅持的一種取向;即便如某些寫作者所聲稱的自己就是單純寫著玩,這也不失為一種取向——眼下暫時是寫著玩,寫了就放抽屜,存硬盤,沒準兒是藏之名山傳之后世的一種取向呢。我就見過一個著名的前輩學者,他賣房后取得一筆不菲資金,然后“豪橫”——與老伴兒搬進了舒適的養老會所并開始潛心寫作。他說,從此以后的著書立說,絕不為換取一分錢稿費,也不追求任何轟動效應,“這種與現世功利無涉的寫作,或許才是我畢生所求呢”。
主題寫作正在成為“顯學”,其利弊得失也值得探討。如果僅從重大評獎來看,有關方面對主題文學的倡導和鼓勵,主要還停靠在“泛主題”文學層面。比如時下特別強調,創作導向須以人民為中心,文學作品須予人以精神力量。如果寬泛一點解讀,正可以看著是“泛主題”文學的一種變通表達。傳統文學理論強調“文學是人學”,“泛主題”文學強調以人民為中心,予人以精神力量,從“人”到“人民”,只要不做過度的意識形態化解讀,我認為二者是相通的,也可以說后者是前者的時代化表達,是對傳統文學觀的延展和豐富。“泛主題”文學可以泛化或寬化,也可以深化或窄化——比如將主題創作進一步界定為主旋律創作,就是窄化的一種表現。
我們對時下影視文藝的主旋律化已然耳熟能詳,事實上主旋律正在覆蓋包括文學在內的所有文藝領域。但我還是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種文藝樣式和類型——哪怕它確實顯得非常重要甚至主要。作為文學的主旋律或主旋律的文學,其關注生活內容或藝術表達方式,依然有較大的探索或深化空間。傳統主旋律文學較多采取非黑即白、非愛即恨的表達,抹去了客觀存在的生活灰度或中間地帶,只是簡單地迎合,這大約是主旋律文學的幼稚期;現代的或時代化的主旋律文學,則注重委婉含蓄、柔性騰挪——就好比圍棋行棋,柔軟的充盈彈性和張力的著棋調子,才彰顯棋手的內力和修為。所以主旋律創作也依然可以在“泛主題”文學層面推進。回到“魯八”中篇評獎結果來看,可以見到評審團在強調主題創作的前提下,在力推“有時代感、有大局觀”作品的同時,還是特別注意到了對作品文字和細節的選擇,對藝術感染力的重視,即在服務時代需求的大前提下,盡可能鼓勵、提倡作家和作品貼近生活真實、符合藝術規律,接近讀者高級一些的審美趣味。
當然,如果我們把視線放到更寬范圍,不難發現,在一些地方,一些文學門類,主題創作中的刻意迎逢的現象,主題或主旋律不斷窄化的現象,狹隘理解導致的簡單化創作趨勢……還是比較普遍的存在,令人擔憂。
主題創作中“報喜不報憂”的“花刺子模信使問題”也值得警惕。花刺子模是中亞一個古國,這個國家的君王特別喜歡聽好消息。他派出的信使,據實稟報壞消息的,會立即被投去喂老虎;而花言巧語報告好消息、哪怕是假消息的,就會得到賞賜和提升。久而久之,君王聽到的就都是好消息了——前方將士捷報頻傳,領土面積日益擴大,國家實力不斷增強……直到有一天敵人打到跟前,真相才終于大白。
此外,還要防止主題文學直奔主題、過于急功近利的趨勢。這種主題文學,往往淪為我稱之為的“撫摸文學”。由此形成順應主流導向易、做出獨立前瞻判斷難,表達與主流價值觀不完全相同(哪怕是“小罵大幫忙”)的聲音更是難上加難的“主題文學”膚淺化現象。當然我知道,不是書寫者不懂得這些規律和這樣淺顯的道理,而是外部語境或許還有某些欠缺,一些作家也還缺乏足夠的準備,這既包括思想修養、藝術修為和知識結構的準備,也包括生活閱歷、人生智慧和文學技術的準備,當然也有缺乏“修辭立其誠”的責任情懷和擔當勇氣,有的還可能受投機取巧、見利忘義等因素影響。
回到評獎話題。魯獎開獎以來歷經八屆,基本實現了評獎的“程序正義”,但最終結果還是不盡如人意。僅以“魯八”中篇及此前我評價過的短篇來看,目前魯獎只是達到了評獎的底線,即:不讓差的、不好的作品得獎;而與評獎的上線——評出標桿性旗幟性的最好作品并使其效益最大化——還有較遠差距。評獎導向和讀者期待之間存在著較大矛盾,即:提升了口味的讀者對優秀小說的向往和評獎結果暫時還不能完全滿足這種需求的矛盾。
究其原因,我認為魯獎在頂層設計上依然有值得改進的空間。比如——
減少獎項種類。魯獎按文學門類評選,分為短篇、中篇、詩歌、散文雜文、報告文學、理論評論和文學翻譯等七個門類。在我看來,種類太多,且不對等,應該減少種類。比如文學翻譯獎,不要因為魯迅翻譯有成就,就設計出這個種類。魯迅文學獎其他獎項既是對作家的,也是對大眾讀者的,唯文學翻譯獎主要是對翻譯者的,相對專業而且小眾,擺在這里面,既不能參照比較,也無法引起更廣大受眾的關注。連續八屆的評獎,最安靜的就是翻譯獎,從來沒有在公眾中引起熱議或反響,說明這是一個誤設在這里的獎項,某種程度上說,還加重了文學自娛自樂的小圈子化趨勢。建議取消。
減少獲獎數量。如前所述,魯獎現有七大門類,每類五名獲獎者,每屆共三十五個獲獎者,數量太多。有作家擔憂:再過若干年,這數量會很大啊!顯而易見的是,獲獎者數量越多,質量必然越低,這個獎的效果也就越差。以公信力較高的諾貝爾文學獎和郁達夫文學獎為參照:前者每年一屆,每屆頒予一人,而且是世界范圍;后者兩年一屆,立足國內,面向全球華語文學,評選中短篇首獎各一名,中短篇正獎各三名。設想一下,如果魯獎也改為每個門類只設大獎一名,作家競爭和社會爭論都必將更加激烈,評獎和講評的“雙效”一定會實現,獲獎作品的美譽度或經典性也必將大大提升。何樂而不為?
減少評獎評委。還是以諾貝爾文學獎和郁達夫文學獎為參照,前者以瑞典文學院為評選常設機構,評委實行終身制,刻有評委名字的十八只咖啡杯永遠安放在那里,除非故去或其他重大原因,評委不變,而且人數也不增不減。這為評獎標準的恒定性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后者設立主任副主任各一,評委八名,在兩個月時間里各自挑選作品并寫下推薦評語,最后面商投票。現在包括魯獎在內的重大文學評獎基本都采取了實名制,實名制的最大好處除了接受社會監督,其實更主要的是讓作品和評委捆綁在一起,說得好聽一點是與有榮焉,說得難聽一點是一丑俱丑。但魯獎評委人數太多,變量太大,且評委來源有太多的兼顧性,這為評獎過程中的平衡和妥協留下了足夠空間,而且標準尺度也必然因人而異不易掌握。
我認為可以適當借鑒諾獎經驗,在最高文學殿堂建立常設評獎機構,而不是現在這樣每屆臨時組建團隊。在現有框架下適當調整,只需為每個固定獎項設立專職秘書,聯系一批固定的實名的高水準專業評委(保密還是公開根據利弊再議),常年閱讀、分析與之相關的文體作品并提交報告,在評獎年提前集結,自主廣泛交流研究,按程序設計完成評獎結果并在規定時間公布,全過程接受輿論監督,最終結果對社會負責。
曾經當面聽一個文學評獎“專家”(更適合的頭銜應該是評獎“專業戶”,因為他當過茅獎、魯獎和“郁獎”等多獎評委,而且是終評委,其他小獎評委則無以計數)“退役”后說,任何評獎都有標準,也有平衡、妥協、兼顧;至于暗箱操作和潛規則,現在應該是難以藏身了吧?但大的語境存在某些客觀困難,要想絕對的純粹是不可能的,特別是文學這個具體對象,本身就充滿無法量化的各種不確定性,所以,公平、公開、公正,是一個大的公約數,關鍵是上上下下如何掌控這個度,以保證最終結果經受得住社會和時間的雙重檢驗。
一個寫作者如何成為自己,這肯定比成為獲獎所需的某種尺寸規定要好。獲得文學大獎其實也是面臨一次新的大考,就像中了彩票大獎一樣,有人會無限度地揮霍人生,也有人會重新理性地規劃人生。謝有順說:“獲不獲獎并不是評價一個作家的唯一標準,大家不必太在意獎項。以往的許多魯獎得獎作家,今天都不寫了,也沒什么人再記得他們了,而很多沒有獲獎的作家卻越寫越好,可見,真正決定作家地位的仍然是作品本身。好的作家不僅要寫得好,還要寫得久。”他說出了一個接近真理的常識,說得很好。我愿意在此重復一遍,讓身邊所有熱愛寫作而暫時未獲得大獎的朋友都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