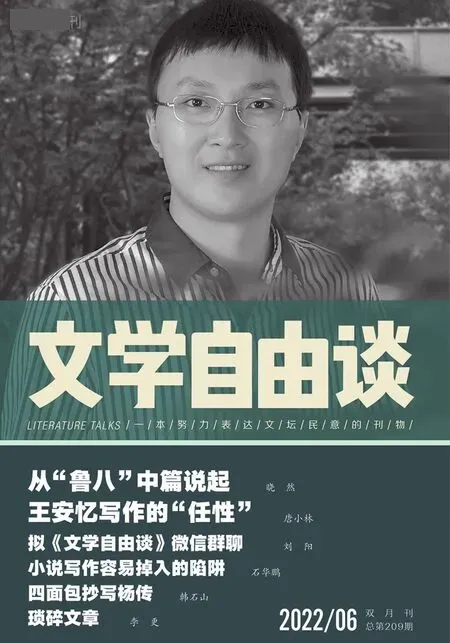當代小說經典化的一種路徑考察
□徐福偉
《小說月報·大字版》有個“經典再讀”專欄,每期選載一篇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經典小說。這些小說我以前零散讀過,為了做好這個欄目,這次是系統閱讀,時隔多年,有的甚至二十多年。在我經歷了職業小說閱讀工作的錘煉之后,對小說的審美要求明顯提高了,并且對大量題材同質化、情感平淡化的作品深惡痛絕,有時甚至閱讀得有點反胃;但當我重新閱讀這些經典小說時,仍然會帶給我強烈的情感沖擊力,仍然會不自覺地被帶入小說的敘事時空中,仍然會被人物的命運所感動,仍然會被溫暖的細節所觸動,雖然我反復告誡自己:注意,不要被帶入進去,這是圈套,要保持理性的閱讀。但是在這些經典小說面前,我對自己的告誡往往是徒勞的,我所依持的職業素養也是無效的。這些經典小說中就有劉醒龍的《鳳凰琴》。
《鳳凰琴》首發于《青年文學》1992年第5期,《小說月報》1992年第8期選載并榮獲第五屆《小說月報》“百花獎”,2010年被《小說月報》編選入《小說月報三十年》這一小說經典選本,時隔三十年后,《小說月報·大字版》又將其選入“經典再讀”欄目。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小說月報》參與并見證了《鳳凰琴》不斷被經典化的過程,不能不說《小說月報》與劉醒龍,與《鳳凰琴》有著極深的緣分。《小說月報》最先選載劉醒龍的小說是1989年第3期的《十八嬸》,1993年第4期選載了《秋風醉了》,1996年第3期選載了《分享艱難》,等等。可以說,除了長篇小說,劉醒龍的中短篇小說代表作都曾被《小說月報》選載過。
這促使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經典小說為何能夠永流傳,我們一代又一代的讀者義無反顧地投入進去,享受閱讀所帶來的有效情感慰藉。這是因為故事情節嗎?是因為人物形象嗎?是因為哲思內涵嗎?是因為細節嗎?似乎這些原因都有,但又似乎不全是,我一直在苦苦尋找著那個最為重要的著力點,無論是情節、人物、細節還是哲思都是從創作主體及文本本身出發的,但經典小說能夠經典永流傳與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有很大的關系,從讀者接受美學的角度而言應該是情感共鳴,也就是共情,這是閱讀主體與創作主體在小說文本所構建的時空中的交流與碰撞,從而產生共同的情緒情感的深刻體驗,這絕不是物理反應,而是有效的化學反應。因此我認為,情感是小說創作的靈魂所在,也是經典小說永留傳的不二法門。我特別認同作家劉慶邦的那句話,“從本質上說,小說是情感之物。小說創作的原始動力來自情感,情感之美是小說之美的核心。我們衡量一篇小說是否動人,完美,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看這篇小說所包含的情感是否真摯、深厚、飽滿。倘若一篇小說的情感是虛假的、膚淺的、蒼白的,就很難引起讀者的共鳴。這就要求我們寫小說一定要有感而發,以情動人,把情感作為小說的根本支撐。我們寫小說的過程,就是挖掘、醞釀、調動、整理、表達感情的過程。”劉慶邦提出了“小說是情感之物”的論點,“緣情而作”的創作路徑,他的創作實踐也踐行著這一標準。這與歷史上劉勰之論“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李卓吾之論“《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形成了遙相呼應的關系與印證。
誠然,考察當代小說經典化的路徑不難發現,除了與讀者共情之外,還依賴于文本本身所具有干預現實生活的能力路徑,具有中國特色的選刊、選本的“文選”促成路徑,不斷獲獎的加深路徑,影視化改編的“普羅大眾”路徑,等等。但這些路徑的開發歸根結底還是依賴于文本本身的情感因素,是否能夠與最廣大的讀者“共情”。
小說是關注人的內心情感世界的,尤其是帶有普遍意義與價值的情感更是其所關注的重中之重。這是中國小說的典型傳統與文脈,尤其是明清時更為注重“情理”。明代李漁說:“凡說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清代西湖釣叟則說:“小說始于唐宋,廣于元,其體不一。田夫野老能與經史并傳,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生則文附焉,不論其藻與理也。”現代周作人說:“我們寫文章是想將我們的思想,感情表達出來的。能夠將思想和感情多寫一分,文章的藝術分子即加增一分,寫出得愈多便愈好。”當代錢谷融也曾說:“文學作品本來主要就是表現人的悲歡離合的感情,表現人對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對于不幸的遭遇的悲嘆、不平的。”經典小說《鳳凰琴》繼承中國古典小說的“情理”傳統,將豐富的人生閱歷內化為情感體驗,更具有“沉郁頓挫”的特點。其并不是單純著眼于小說的藝術審美價值追求,而是更加注重對小說情感空間的開拓,執著于對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情物理”和“世道人心”的深入開掘,強調情感的日常化、倫理化、傳統化。這種對情感空間的深入開拓極易與讀者產生共情的化學反應。《鳳凰琴》就像是一個大的情感吸納器,吸納著一個人的情感,一群民辦教師的情感,甚至一個時代的情感。從這個角度而言,劉醒龍是一位典型的人道主義作家,與現實社會始終保持著“痛癢相關、甘苦與共的親密關系”。劉醒龍說過這樣一句話,“對于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必須以筆為家,面對著遍地流浪的世界,用自己的良知良心去營造那筆尖大小的精神家園,為那一個個無家可歸的靈魂開拓出一片棲息地,提供一雙安撫的手。”此語道出了作家所堅守的“為人生”的五四文學傳統以及關注“普遍人性”的價值立場。
《鳳凰琴》的共情能力根源于“有意義”的小說品質。小說作為一種虛構性的敘事文體,尤其是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首先應該是能夠講述一個生動的故事,其次還應該“讓讀者能夠一掬感動之淚、產生心靈的共鳴,而且還是最精確的社會-道德的地震儀,甚至能對未來的暴風雨、民族、社會心理乃至人類的苦難做出預報”,這是對哲思層面的要求,也就是所謂的“有意義”。
韋斯坦因說,“‘意義’指文學作品中和問題或思想有關的方面,要言之,即作品的‘哲學-思想的主旨,道德的基礎’方面”。小說是寫給讀者大眾看的,總會不自覺地探求“意義”。布魯克斯說,“我們不應該忘記,每個人或早或晚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即:生活的意義何在?要是一篇小說不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關心這個問題,我們就會失望之至”。米蘭·昆德拉說,“小說的存在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護我們不至于墜入‘對存在的遺忘’”。由上述人的言論不難發現,小說一定要“有意義”,其指涉小說的思想、主旨,隸屬于哲思層面,代表著作者對這個世界、社會、人生、歷史、文化的一系列的看法和見解,此外,還關涉小說閱讀者的代償心理的需要。
《鳳凰琴》以平實的筆調,書寫兩代鄉村民辦教師的悲欣命運故事,提煉出鄉村民辦教師身份轉正這一有“意義”的社會話題并予以藝術呈現,從而讓隱蔽在中國鄉村角落里的四百萬人之眾的民辦教師進入讀者的閱讀視野中,引發了整個社會的持續關注。
《鳳凰琴》中充斥著濃郁的情感因子,在界嶺小學所形成的時空中悠揚飛翔。坐落在大山深處的界嶺小學只有五位民辦老師,其中一位是因為急于參加轉正考試而蹚冷水過河患病的明愛芬老師,還有一位是托舅舅萬站長的關系想以此為跳板轉正公辦的剛畢業的青年學生張英才,其余三位是界嶺小學的教學主力團隊,分別是余校長、副校長鄧有梅、教導主任孫四海。正是這幾位力量有限的民辦教師保留住了鄉村孩子們受教育的種子,并且在他們的細心呵護下發芽生根,甚至茁壯成長。教學環境和生存境況的惡劣,也是通過張英才這個外來者的敘事視角來呈現的,雖然在這種惡劣環境中,民辦老師們依然在努力地維護著教育的尊嚴,兢兢業業地培養著學生們,希望他們能夠有朝一日飛出大山。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民辦教師的這種質樸的堅守與守護之愛溫暖著大山里孩子們的心。如吹笛子升國旗的嚴肅場景,護送學生回家的場景,余校長家成為學生食堂兼宿舍的場景,等等,這些由溫馨細節構成的場景無疑在強化著民辦教師們身上善良質樸品格的堅守,這種堅守正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有教無類”的傳統優秀文化因子在當代社會的傳承與弘揚,正是“師者所以傳道授惑解也”的當代表達,在他們的身上閃爍著東方人倫情感的魅力。正是這種最為普通的司空見慣的情感感動了無數的讀者,打動了人心,深化了人倫情感的認知。
誠然,界嶺小學民辦教師們的身上也各有缺點,并非傳統意義上完美的師者形象,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其中最為重要的訴求就是期待轉正名額,由民辦教師轉為帶編制的公辦教師。這種身份轉換的訴求是他們為之奮斗的重大目標,其迫切性、重要性可能是我們這些沒有類似生活體驗的人所無法體會的,但是這種身份轉變的情感確是共通的,或許我們每一代人都有可能在生活中遇到這種困境。這種身份的轉正一方面是他們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更是一種心理情感上的社會身份認可的需要。他們雖然名義上是教師,但前面還有兩個刺耳的字——“民辦”,這種情感的困境并不是界嶺小學的幾位民辦老師,而是千千萬萬民辦教師所遭遇的普遍性困境。這種困境由此導致了很多極端事件的發生,如明愛芬老師就是因為這種迫切的追求而葬送了自己后半生的幸福。張英才、余校長、鄧有梅、孫四海也都在暗中較勁,張英才甚至因看不慣他們的作風與行為而故意惡作劇捉弄他們,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差點引發出大事件,鄧有梅為此去偷樹差點犯罪,孫四海無心送孩子回家差點導致孩子被狼群吃掉。是張英才這個關系戶的到來打破了這種平衡,同時也帶來了新的變革的因子。作為外來的闖入者,張英才一方面擔負著呈現他們的日常工作、生活的重任,另一方面也經歷了激烈的思想斗爭,由對他們的隔膜,甚至厭惡,再到認同,甚至最終主動讓出轉正名額,決定在此扎根鄉村教育事業,這種轉變暗示著一種難能可貴的和解。正如劉醒龍所說,“我相信善能包容惡,并改造惡,這才是終極的大善境界。”
這里就涉及小說創作中關于情感的一種有效的處理方式了。《鳳凰琴》一方面寫出了鄉村代課教師共通的故事、共痛的情感、共思的哲理,能夠獲得讀者的普遍性共情,另一方面若對情感的處理極端化則會誤入歧途。考察經典小說,我們不難發現其對情感的處理幾乎都是在克制中走向和解的。這對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來說,無疑是極其重要的能力和品質。在我們的現實世界中,黑暗與光明、善良與邪惡、救贖與沉淪往往是并存的,作家們往往對人性之惡揭露得很順手,而對人性之良善的書寫則缺乏足夠的信心。小說中的和解無疑關涉小說中的情感空間。就我觀察而言,我覺得當下青年寫作普遍存在拒絕和解的情感價值傾向,以為只有寫的決絕、寫得極端才能體現深刻,其實寫好和解同樣可以深刻。《鳳凰琴》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值得青年作家們關注并學習。舅舅萬站長因為走婚姻的捷徑而由民辦老師轉正成功但卻陷于良心的譴責與婚姻泥沼中難以自拔,雖然買了鳳凰琴送給明愛芬老師想以此贖罪,但最終事與愿違,成為了刺激明愛芬老師的導火索,最終在轉正的問題上尊重了張英才和余校長們的意愿,將轉正名額給了明愛芬老師,明愛芬老師才得以瞑目。舅舅和明愛芬都走向了情感的和解,雖然這代價是巨大的。余校長、鄧有梅、孫四海,尤其是張英才,更是如此。張英才從進入界嶺小學的第一天就夢想著轉正,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經歷了那么多刻骨銘心的事件之后,張英才與環境、張英才與余校長他們、張英才與自身也達成了情感的和解。
《鳳凰琴》創作至今已三十年了,還在被不斷地經典化的過程之中。我每讀一次感動一次,也許這就是經典永留傳的不二法門:情感是小說創作的靈魂所在,而當下的許多小說恰恰丟失了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