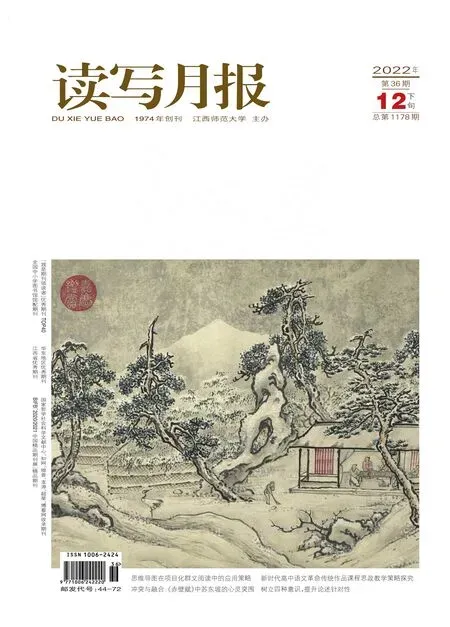小說閱讀教學如何面向未來?
——聽王瑛老師講《百合花》
鐘培旭
課,常聽;好課,并不多見。
有一些課標榜最新理念,經過精心打磨,聽起來耳目一新、無比精巧,但余味寥寥,有隔靴搔癢的遺憾。而有一些課未必緊扣什么教學理念,還沒經過多少次精心打磨,但聽起來自然而然,有不落窠臼、推陳出新的感覺,印象深刻。在2022年廣東省李烜名師工作室學員跟崗研修活動期間,松山湖未來學校語文科組長王瑛老師9月26日在東莞高級中學上了一節以《百合花》為探討對象的小說課,主題為“探尋小說閱讀的新密鑰”,設點新但不突兀,課堂熱但不喧鬧,得到不少好評。
課后幾天,筆者還常想起該課,既琢磨該課的妙處,也反思自己的小說教學。因此,筆者試圖以拙思談好課,述評該課的妙處,并一探小說閱讀教學該如何面向未來。
“今天,我們怎樣教小說?”想想自己的設計,看看身邊的課堂,我們有了大概的答案。就教學內容而言,我們教小說仍然鐘情“四大件”(人物、情節、環境和主題)。20年前,課程論專家鐘啟泉教授分析道:“在中小學語文教學中,小說,除了被擰干的‘人物、情節、環境’這三個概念,事實上已沒有多少知識可教了。”[1]20年過去了,我們仍未走出“泥淖”。就教學形式而言,我們總是按部就班地講授課文、布置作業、組織考試。我們希望突破“灌輸式”教學的藩籬,但似乎也還行而未遠。
“未來,我們應該怎樣教小說?”這個問題里應該熔鑄師生共同的期待,非三言兩語可以回答好。但是,我們知道用舊的方式不行。于是,這個問題就有了這樣的方向:課辟新“徑”,讓學生有探索的可能;內容突破,讓學生有未知的發現;開放包容,讓學生有分享的快樂……
一、取道:從“教課文”到“做任務”
時下,“三新”(新課標新教材新高考)常提,教改卻難行。“三新”成了多數教師放在案邊的擺設。或許,難就難在“三新”面向未來的取向。其中,《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設置了18個“學習任務群”,素養導向,實踐引領,主體轉變,從形式到內容都滿賦新意,有未來味兒。
題至此處,“學習任務”的設計與實施,作為語文教學“履新”關鍵一步已很明確。
王瑛老師是個有心人,她依循“新課標”指引設計任務,轉化現實生活擬制學習情境。她在課前與學生互動,和學生聊起全市最為引人關注的新學校——松山湖未來學校,勾起話題;也夸獎莞邑名校東莞高級中學的學生都“高級”,期盼配合。上課伊始,她輕松地講起松山湖未來學校正在開展的首屆讀書節,引入本節課的學習任務:
東莞松山湖未來學校首屆讀書節恰逢“十一”,學生導演組為在案頭山水間深化師生的家國認知,擬在匯演時安排一個課本劇表演。經調查分析,大家決定對《百合花》進行劇本改編,但是……改寫過程中,編劇組對“我”的去留看法不一。
編劇一:小說的主角是通訊員與新媳婦,“我”只是講述者,沒有太大作用,可以刪除。
編劇二:小說是“我”的所見所感,刪去后就丟失了那種感覺。
編劇三:《哦,香雪》里面沒有“我”也寫得很好,那么《百合花》去掉“我”也沒關系,要不選《哦,香雪》進行表演,更簡單。
請大家談談對“我”的認識,為松湖莞未的編劇組提供解決方案。
此任務一出,旋即引起學生的興趣。學生已經熱鬧地討論起來了。為了指引學生討論方向,王瑛老師在后面又為該任務做了分解引導。統觀整節課,學生全程跟著這個任務走,很放松,也很活躍。回望過往的課堂,課堂氛圍熱烈有可能來自于老師的個人魅力,也可能來自于課堂的教學設計。不否定王瑛老師的課堂掌控能力,但我傾向于認為這節課之所以有激活點燃之功,更重在任務設計的準且趣。這節課的成功,首推從“教課文”到“做任務”的變化。
其一,任務真實,讓學生有體驗感。
王瑛老師的這個任務的情境設計看似閑庭信步,無甚高招,實則深藏機心,有些玄機。例如為什么不直接把“讀書節”以授課學校“東莞高級中學”為背景,而以自己單位為切入。一方面,據介紹該校真的在舉辦首屆讀書節,還原現場;另一方面,松山湖未來學校創校首年,在中考宣傳時宣傳“炸裂”,高一的學生們(還有老師們)對這所起點很高的新校充滿好奇。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對情境設計有這樣的指引:“真實、富有意義的語文實踐活動情境是學生語文學科核心素養形成、發展和表現的載體。語文實踐活動情境主要包括個人體驗情境、社會生活情境和學科認知情境。”[2]就王瑛老師的任務情境來看,既導向《百合花》的深入閱讀,契合個人體驗情境;也借著學校首屆讀書節的背景,蘊含社會生活情境;談談對“我”的認識指導學生認識敘述視角,包孕學科認知情境。學生依境完成學習任務,實現真實情境下的學習。
其二,任務有趣,讓學生有探索欲。
好的任務設計,除了要為學生校準學習內容,還應該讓學生有探索欲,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體會到學習的樂趣,獲得更多的啟發和生長。
王瑛老師為加深學生對“我”這一敘述視角的認識,還進一步讓學生換成其他敘述視角來講述故事,如新媳婦兒。王瑛讓學生們推薦本班“戲精”(最大膽、最愛演的學生)來表演這兩個片段,班里最外向最自在的兩個學生接下這個任務,拿捏表情,敘述生動,逗得全班哈哈大笑。此種氛圍下,后續探討自然從容而有序。
其三,任務有物,讓學生有提升感。
任務設計的好壞,難以有統一的衡量指標,但有一項必須明晰,那就是指向學生語文核心素養的培養。
論者曾提醒道:“《百合花》《荷花淀》等小說,教師們多會選擇電影場景拍攝和話劇排演的任務,但完成這些任務資源應該是劇本,缺乏從小說到劇本的轉換環節,任務就違背了自身的邏輯。”[3]而王瑛老師的設計明顯注意到這個問題,以課本劇表演為終極目標,任務卻是落在小說改編為劇本,尤其是“我”的去留上。也就是說,這個設計符合教學邏輯。從“我”的去留,走向敘述視角的探討,這是解讀《百合花》的一條路徑,也是小說閱讀的“密鑰”。學生觀“我”,能留能去,學生讀書,又得秘技,這自然是師者的期待,何嘗不是好的設計的成果?
二、聚焦:從“寫什么”到“怎么寫”
小說“三要素”重要嗎?當然重要,必須重視。但節節如此、篇篇如是,那就不能怪學生望而生厭了。
《百合花》這篇小說,如果按“三要素”來解讀,主軸就是小通訊員送“我”(文工團的女兵)到前沿包扎所,隨后一起向老百姓借被子,在“我”的幫助下,跟剛過門三天的新媳婦借到她那床“棗紅底上面撒滿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當晚,小通訊員為解救戰友,勇撲手榴彈而犧牲。新媳婦將新被子作為了小通訊員的陪葬。故事感人,無甚難解。
“如果讀小說僅僅滿足于讀懂故事,就沒有必要讀小說了。”[4]王瑛老師的課視角奇崛,改編劇本探討“我”的去留過程中,借一些新的視角來講述這個故事,讓學生體會“我”的敘述魅力。如前文所述,學生的表演極富張力,提升了課堂的熱度,但這并不是重點。王老師借由這兩個同學的表演,把問題落到——“我”的敘述到底起什么作用:
(1)“我”的敘述讓情節的松弛有度;
(2)“我”的敘述讓小通訊員不落入“高大全”的窠臼,有天真的一面,也有偉大的一面;
(3)“我”的敘述讓主旨更加深沉多面。
……
對學生的回答加以提示和總結,很容易就轉向本節課想要關切的重心——“敘事視角”。王老師在不徐不緩間,已將這把小說閱讀的新密鑰交到學生手中,課中簡單板書如下:

小說閱讀的新密鑰最終亮相的時候,這節課的重心也就明確了——王老師已經帶領高一的學生們,實現從小說“寫什么”到“怎么寫”的轉向。“我們知道,小說,通俗地講,就是‘講故事’。無論‘情節’‘人物’還是‘環境’,都屬于‘講了什么故事’的范疇;而敘述,無非就是‘講故事’的‘講’。”[5]這是兩個不同維度,將啟發學生發展文學鑒賞思維。整節課力避繁難,讓學生邊讀邊思、邊演邊論,有的放矢卻視角開拓。
這一節課的框架正是從“敘事視角”去深度理解小說家對情節、人物、環境和主旨的精心建設。當這一框架最終揭曉時,這節課存在的些許遺憾也暴露出來。那就是王瑛老師帶著學生往這個方向前行,卻或多或少遺漏了沿途風光。例如,為什么用“文工團女兵”這一視角?其實首要原因應該是茹志鵑自身的文工團女兵經歷,茹志鵑在創作《百合花》時家庭正面臨種種壓力,不由得懷念起戰時的人事。“戰爭使人不能有長談的機會,但是戰爭卻能使人深交。有時僅幾十分鐘,幾分鐘,甚至只來得及瞥一眼,便一閃而過,然而人與人之間,就在這個一剎那里,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6]再如,女性視角到底有什么作用?王瑛老師在帶著學生分析過程中困于課時,基本沒涉及到“我”眼中所看到的細節:莊稼的“青翠水綠,珠爍晶瑩”,小伙兒“那副厚實實的肩膀”,以及小伙兒步槍筒里用“稀疏地插了幾根樹枝”作為點綴。這些細微和瑣碎,這些畫面與詩意,蘊藉著小說的詩化風格。受設計框架束縛,這節課從文本領會詩意的開拓略微薄弱。
三、形態:從“問答式”到“共生式”
把這節課拎出來甩干水分,內容確實并不多,但遠比形式繁多的課顯得扎實,遠比內容豐富的課顯得有收獲。這里值得一提的便是,王瑛老師在教學設計的匠心之外,是對學生的始終關注。
首先在設計時,王老師從敘事視角(“我”的去留)著手探究小說,不從常規落筆,但最終還是倒向經典的“四大件”。這樣的設計,與直接告訴學生敘述視角有什么作用一樣嗎?當然不一樣!敘述視角作用的講授,看似精簡高效,其實低質無痕,學生聽進去了,也沒有深度理解。而學生通過完成任務探尋答案的過程,是曲徑通幽,是步步為營,這樣的基礎上再接受點撥,有心的孩子定然是恍然大悟,靈性的學生或許將進一步探尋。
其次是互動時,王瑛老師仿佛有魔力,讓學生牢牢吸附在課堂里。細節一是王老師宣稱自己“耳不聰,目不明”,以此為由鼓勵學生大膽發言、大聲發言。細節二是她在提問完一個學生之后,喜歡讓下一個學生概括前一位同學講了什么。這簡直是個教學小妙招,學生除了要準備好自己的發言,也要細心聽同伴的發言。這種分享較多的課堂,一大弊病就是參與的學生收獲大,不參與的學生完全放空。王老師這樣做,這一定程度上擴大參與度,也吸引學生認真聽取同伴發言。細節三是她對上臺發言的學生充滿鼓勵和積極反饋,一些比較內向的學生開始不敢發言,登臺發言后含笑離開講臺,可見王老師鼓舞到位,對學生勉勵有效。
從“滿堂灌”到“問答式”,語文教學已經算是取得了一定進步,但一問一答,往往充滿預設,難有旁逸。從“問答式”到“任務驅動”,我們又向前邁了一小步,看起來差異不大,但學生在完成任務時,思維少點束縛,語言多點靈動,我們看到的是課堂的更多共生。
再次是課后,任務學習不是到下課鈴響為止。王瑛老師這節課集中講的是《百合花》的“我”,但她也指引學生留心《哦,香雪》的敘述視角。她希望學生們課后進一步:“《百合花》可不可以采用全知視角來敘述?《哦,香雪》可不可以采用有限視角來敘述,比如鳳嬌?”這些任務是課堂的延伸,也是深入閱讀小說的“步履不停”。
干國祥老師在《理想課堂的三重境界》中提出:“理想課堂第一重境界,落實有效教學框架;第二重境界,發掘知識的內在魅力;第三重境界,知識、生活與生命的共鳴。”[7]王瑛老師這節面向未來的小說課,有巧思,有價值,有生命,自然也有了境界,契合理想。
注釋:
[1]鐘啟泉:《語文教育展望》,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99頁。
[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2020年修訂)》,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48頁。
[3]李欣榮:《任務驅動式學習課堂的評價原則——以袁晗毅〈裝在套子里的人〉的教學為例》,《中學語文》,2022年第13期,第70頁。
[4]王榮生:《小說教學教什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頁。
[5]孫健:《今天,我們該怎樣教小說?——從爭議獲獎課例〈裝在套子里的人〉談起》,《語文教學通訊·高中》,2014年第3期,第35頁。
[6]茹志娟:《我寫〈百合花〉的經過》,《青春》,1980年第11期,第50頁。
[7]干國祥:《理想課堂的三重境界》,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年,第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