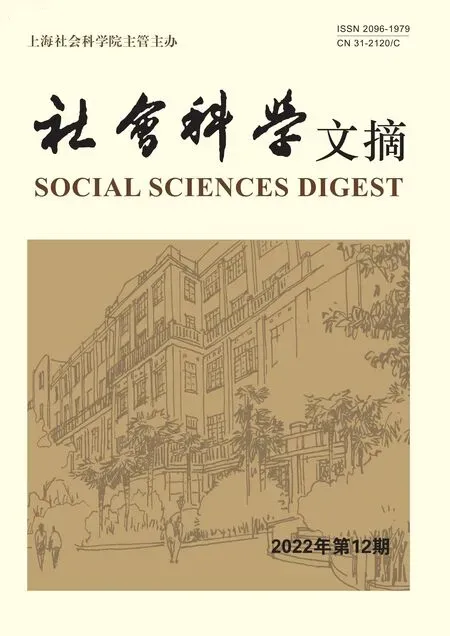“非個體”與個體觀念的松動
文/殷杰 張冀峰
重啟個體之問
“個體”“個體主義”無疑是這個時代極為重要的觀念構型,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著現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如戴維斯(John B.Davis)所言,個體概念是當代社會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它甚至可能是我們所有概念中最基本的概念,個體性是當代人類社會的基本關注點。社會世界是由“人”組成的意義世界,但問題是社會世界是由什么樣的人組成?是“經濟人”“理性人”“個體人”,還是其他什么樣的人?人是活生生的人,人對自己的理解和塑造是隨時間而改變的,很多研究已經令人信服地指出今天流行的“個體”觀念其實是基督教的產物,是西方的產物,是近代的產物,去語境地將人與個體等同起來是非常粗礪的描述。
我們承認社會世界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構成的,這個本體基礎雖然不容置疑,但從不容置疑的本體并不必然導出不容置疑的本體論,科學哲學中著名的“非充分決定性”論題也同樣存在于社會科學和社會科學哲學中,社會本體論不是完全由經驗證據支撐的,同樣的經驗證據可以服務于不同的本體論承諾。不同的本體論承諾如果不想淪為自說自話就必須保持有效的對話,而如果想保持有效的對話就必須尋求共同的對話基礎,于是當代社會本體論研究最終要轉向形而上學,轉向對本體之“范疇”基礎的探究,澄清具有范疇意義的“個體”概念就成了社會本體論研究的基礎性課題。
從哲學史的角度看,社會本體論研究主要是圍繞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之爭這條線索展開的,而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最初的理論形態是社會唯名論與社會實在論,即將唯名論與實在論的觀點應用于社會世界,故其爭論焦點是“殊相”與“共相”,討論的是何者是根本性范疇或具有相對優先性的基本范疇。因此,在當下澄清具有范疇意義的“個體”概念是一次向起點的回歸,故筆者將這項任務稱之為“重啟個體之問”。從社會科學哲學的角度把握社會本體論,需要有對科學哲學的整體理解,需要在溝通科學與形而上學的整體意識下,以“立足科學而跨越學科”的方式重啟個體之問。不同科學學科內討論的“個體”雖然具有很大差異,但從本體論的角度,“個體”作為一個基本形而上學范疇,有可能并且也應該達成一個統一的概念圖式。社會科學有必要關注自然科學對個體觀念的沖擊。
概而言之,現代自然科學對常識個體觀念的沖擊主要有三大領域,即量子力學、生物學和分形學。量子力學為我們貢獻了非個體(nonindividual),生物學為我們貢獻了非典范個體(nonparadigmatic individual)和超個體(superindividual或superorganism),分形學為我們貢獻了自相似個體(self-similar individual)和非理想個體(nonideal individual)。這些自然科學的新觀念給我們的常識個體觀念帶來了極大的困惑和挑戰,也為我們重新理解個體提供了有利契機。考慮到量子力學對世界和世界觀的巨大影響,也考慮到量子非個體問題已經討論了近一個世紀,其基本觀點和處理方法已然明朗,故本文暫且只討論量子力學的非個體觀念。
量子力學對“個體”觀念的沖擊:非個體
量子統計帶來的一大奇特之處是粒子的置換不變性,即兩個相同類型的粒子互換位置并不算作新的狀態,置換前與置換后的狀態被認為是毫無差異、毫無影響、不可分辨的,這顯然違背了萊布尼茨的“不可分辨物的同一性”原則。于是,量子力學一開始就提出了“非個體”(non-individual)和“非個體性”(non-individuality)的觀念。量子力學的公認觀點是,從量子粒子統計行為來看,量子對象是沒有同一性也沒有個體性的奇特對象。然而,傳統的個體觀念并非沒有辯護的余地,為量子個體性作出辯護的路徑主要有二:一是先驗辯護,即訴諸屬性之外且超越屬性的東西來保證量子對象的個體性。先驗辯護帶有“特設性”色彩,其特設的提供個體性的東西是那些“無情的”“無法言說”的東西,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拒絕了對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因而很少真正被有科學頭腦的哲學家采用。二是屬性辯護,即指出量子對象仍有某種屬性能保證其個體性,例如訴諸隱變量、時空位置、弱可分辨性、基數性等屬性。屬性辯護有更大的討論空間和啟發價值,其中弱可分辨性辯護和基數性辯護具有很強的哲學性,也具有很強的迷惑性,在此值得重點討論。
弱可分辨性的主張立足于非自反性,以馬克斯·布萊克(Max Black)的宇宙為例,假設該宇宙只由兩個本質上在所有方面都完全相似的球組成,在這個宇宙中,沒有什么能將這兩個球區分開,但它們是二而非一,這顯然違反了萊布尼茨的“不可分辨物的同一性”原理。然而弱分辨性的辯護者主張兩個球并非不可分辨,其實二者之間存在弱可分辨性,即存在一種對稱但非自反的關系。例如它們每一個球都有與另一個球相距一英里遠的關系,但與自身卻沒有這種關系。然而,所謂的“弱可分辨性”其實沒有為賦予每個實體確定性的同一性提供任何依據,它僅僅表明實體確實在數量上是二,而沒有告訴我們同一性。“與自身相距一英里遠”是有歧義的屬性,既可以理解為純粹的“質性”屬性,也可以理解為非純粹的“質性”屬性,這種歧義可以借助λ抽象標記法澄清。如E.J.勞所言,所謂的“弱可分辨性”是一個產生于關于謂述和屬性歸屬的邏輯與語義的混淆的“虛假概念”,一個非常有欺騙性的概念。
一些學者主張從計數和基數性來為個體性作辯護的策略。所謂基數性,就是在每一個包含多個粒子的情況下,它們都有一個明確的數目,這意味著那些被計數的粒子必須彼此不同,因此他們認為在非相對論量子力學中,基數性為原始個體性提供了積極的證據。然而“個體性、同一性和基數性之間的聯系并不像乍一看那樣強烈,我們可以放棄‘對象是自我同一的’這個想法,即使如此,它們也可以形成具有明確基數性的集合。這種觀點是可維系的,于是個體性與基數性的鏈接被打破了,非個體性可能與明確的基數性并存。既然這個事實是量子力學圖景所需要的,那么非個體性似乎是量子力學本體論最簡單的假設”。在不預設同一性的情況下能得到基數性嗎?克勞斯指出,“沒有同一性的對象(即非個體)也能被計數”,克勞斯設計了一種做減法的計數程序,借此程序將對象集合的元素一步一步地消除至空集,基數就來自應用程序的步驟數,這就將“對對象進行計數”轉換成了“對操作進行計數”,從而繞過了在計數中需要對對象做標記并預設對象之同一性的問題。因此,可以在不假定它是個體的情況下完成消除過程。
個體與非個體的形而上學都可以與量子力學兼容,量子力學本身并不足以完全決定形而上學。要對形而上學作出選擇,就必須訴諸其他理論美德或偏好,如簡單性、經濟性、美感等。如果從這些角度綜合來考慮的話,量子的非個體本體論要比個體本體論更簡約。因此,筆者認為,非個體本體論要優于個體本體論。當然,這也是目前大多理論者所堅持的觀點。
科學與社會文化的互動:保衛“個體”?
從科學社會學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物理學理論本身不是純粹屬于科學的,對理論的闡釋常常滲透或摻雜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文化因素。圍繞量子力學的詮釋問題,這種“內行”的爭論被更普遍地注入了一股“外行”的文化意義上的“個體性”意涵,在理論之外,對于一些物理學家來說,“保衛個體”是更高的信念,量子力學的闡釋不能威脅到普遍意義上的“個體”觀念,保衛形而上學領域的“個體性”就是保衛社會歷史領域的“個體性”;在社會歷史領域,“個體性”觀念是神圣不容侵犯的,個體身份恰恰是物理學家在現實生活中的真實境遇和價值訴求。
保羅·福曼(Paul Forman)在《文化價值是如何規定屬于量子力學的特征和教訓的》一文中表明,德國魏瑪文化對量子力學理論表征產生了重要影響,一些物理學家出于文化價值的考慮而有意識地回避量子力學可能帶來的“個體的消解”,或者逆量子力學而行,明確為個體性作辯護。“量子力學及其所包含的統計學的一個無可爭辯的‘教訓’是原子世界中不存在個體性。這種明顯的蘊含,與德國和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如此大相徑庭,以至于物理學家在事實面前,或壓制它或無視它以維持截然相反的主張。”“量子力學與在它上面的哲學建構之間,或者與從中得出的世界觀蘊含之間,幾乎沒有什么聯系。物理學家們允許他們自己,也允許其他人,讓這個理論成為他們想要的樣子——很大程度上,無論他們的文化環境迫使他們想要它成為什么,他們就會想要它成為什么。”福曼的觀點只能解釋適應文化環境的情況,不能解釋反叛文化環境的情況。福曼論題雖有失嚴謹,但無疑是十分有價值的,他讓我們看到了社會文化對量子力學的影響。
反過來看,量子力學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則更明顯、更巨大,在此我們僅聚焦于量子理論對社會科學的影響。伴隨著“統一科學”“自然主義”“科學主義”等宏大愿景,將量子力學的思想應用于社會科學,日益成為非常有誘惑力的嘗試。例如,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在《量子心靈與社會科學:統一物理本體論和社會本體論》中提出了一個量子社會科學的強綱領,即必須用量子力學的術語來理解所有的社會生活。溫特主張清除古典世界觀的所有痕跡,代之以量子力學和心靈哲學的新綜合。他將人類視為“行走的波函數”(walking wave functions),量子心靈產生意識,而非人類的量子系統共享主觀性。他認為,這一觀點對于社會科學的實踐具有多重含義,消除了純粹唯物主義本體論的某些成問題的特征,生成了一個新的、統一的、更好地處理主體—結構(agent — structure)問題的物理主義本體論。量子理論對社會科學的影響有擴張之趨勢,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提供了重要發展契機,也對社會科學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傳統的社會本體論研究被放置到了一個視域更宏大、思維更開放、學科更融貫的綜合性語境中,對于很多傳統觀念需要新的哲學反思,“個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觀念之一。
由此再來審視玻爾對個體性的辯護,看來玻爾并非杞人憂天,在某種意義上玻爾是一位先知,他最早預料到了量子世界觀可能帶來的文化后果并提前對之作出了反應。身處21世紀的我們,今天面對著怎樣的文化環境?是否仍存在“保衛個體”的文化要求?其實,今天的社會文化環境十分復雜,我們所需要的已遠非“保衛個體”或“消解個體”那么簡單。
個體觀念的松動
在當代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圍繞個體問題存在著一種“撕裂”或“吊詭”。一方面,“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似乎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個體”和“個體性”又并非如現代人想象得那么堅固、那么基礎,一些學者指出,它們只是文化歷史的建構物。根據貝克的“個體化”理論,現代化的發展使以前鎖住每個人人生的家庭和職業這兩個軸支離破碎,人被現代性塑造成作為個體的人。現代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也是一個個體化社會。個體化被認為是一種命運,而不是一種選擇。在“個體化”的時代大潮下,“無意義感”“非真實感”“被植入感”成了現代“個體”的人之重要生命體驗和人生困境。人們不禁追問:成為“個體”究竟意味著什么?“個體化”是“社會化”的反題嗎?“個體化”意味著“社會原子化”或“社會沙化嗎”?如何理解個體的個體性?如何理解個體與社會、個體與整體的關系?保衛個體還是消解個體?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個體?一系列對“個體”觀念的反思或否思,表明“個體”不能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了。
阿穆德納·赫爾南多(Almudena Hernando)在《個體性的幻想:現代主體的社會歷史建構》中批判道:“直到17世紀,人(person)的概念才變得等同于個體(individual)的概念。”拉里·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在《發明個體:西方自由主義的起源》中指出:自從16世紀和民族國家出現以來,西方人逐漸將“社會”(society)理解為一種由個體(individuals)組成的團體,這是非常可疑的。“個體”起源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在某種意義上,保羅的基督觀念創造了個體”,“基督教的上帝觀念為個體提供了一種本體論的基礎”,成為個體意味著成為獨自面對上帝的個體,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個體,因此在基督教的觀念里,個體主義的另一面就是普世主義。路易·迪蒙(Louis Dumont)在《論個體主義:人類學視野中的現代意識形態》中指出:現代意識形態的構型是個體主義的,這種個體主義的起源可以在基督教中找到,最初成為個體就是成為出世的個體,即與上帝相關的個體,個體是拋棄社會的“絕棄者”,隨著宗教的改革,個體經歷了從出世個體向入世個體的轉變。
就目前的嘗試來看,我們暫時還無法具體評估量子力學的“非個體”如何能跨越層次而直接影響社會世界的個體觀念,以及這種跨越是否合法。但從兩者的互動來看,它們共同指向了一個問題意識——常識“個體”觀念是可疑的,它缺少一種本體論的前提批判。從作為概念圖式的形而上學角度來講,個體性不再被視為存在之必要條件或必然特征。伴隨著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反智主義、懷疑主義、虛無主義、神秘主義、非理性主義等種種思潮,“個體”或許是一種幻想?一種建構?傳統的“個體”觀念開始松動了,圍繞“個體”之形而上學的一系列問題(如個體與整體、個體與集體、個體與機制、個體與社會等的關系)需要重新加以審視。形象地講,構建整個社會科學大廈的磚塊不再被視為一個絕對堅實的磚塊,于是,重鑄最小的單元,就是重構最大的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