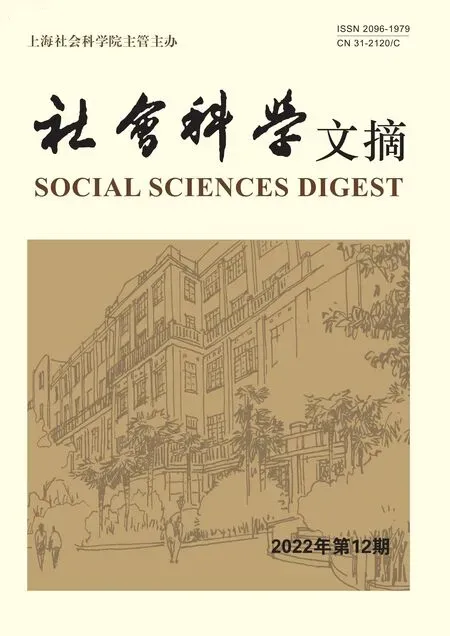文學的城市:空間區隔與文化區隔
文/南帆
一
“空間”話題引起廣泛的興趣,顯然與一種認識密切相關:空間始終與文化觀念存在互動。空間并非均質的、恒定的、事先設置的,不同的歷史主體可能生產出不同的空間。現今的空間內部填滿了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關系。從福柯、哈維到雷蒙·威廉斯、弗·詹姆遜、愛德華·薩義德,眾多思想家不僅圍繞這種認識展開工作,而且帶動這種認識迅速擴散到文學研究領域。從殖民與后殖民研究、性別研究、經典、身體、監視到文化地理、公共空間、民族與地方性體驗、全球化、多點透視,諸如此類的考察陸續匯聚于所謂“空間轉向”的概括之下。羅伯特·塔利提到了文學寫作與空間繪圖的比擬關系:“就像地圖繪制者那樣,作家必須勘察版圖,決定就某塊土地而言,應該繪制哪些特點,強調什么,弱化什么;比如,某些陰影或許應該比其他陰影顏色更深,某些線條應該更明顯,諸如此類。”
城市是文學持續關注的一種特殊空間。對于社會學來說,城市空間的表征策略往往是,鄉村空間被預設為無形的“他者”。兩種空間的不同性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兩套迥異的社會關系演繹的。從鄉土中國的歷史背景、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略到鄉村振興的理念,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流露出對于鄉村的特殊眷顧。相對來說,城市扮演了一個不無尷尬的角色,猶如罹患某種文化隱疾。
“城”的早期形象是與城墻聯系在一起的。古代社會的城墻具有特殊的防御功能。帝王、貴族或者官員的聚集不僅深刻地影響了這個空間的社會組織,同時帶來某種身份的優越感。“城里人”與“鄉下人”之間的鴻溝至今猶存。“市”的主要涵義是市場。眾多人口聚居伴隨的大規模商品交易不得不訴諸市場形式。
作為“現代性”的一個突出表征是,世界范圍的大城市正在提供愈來愈相似的城市經驗。另一方面,鄉村與城市的矛盾進入縱深,并且多向地展開。城市始終顯現出強大的吸引力,吸引大量人口持續涌入城市,重新設計生活方式。由于活躍的市場,城市經濟的繁榮程度遠遠超過鄉村;依附于城市的龐大行政體系提供了眾多就業崗位,大部分職業不必由汗流浹背的重體力勞動完成。學院、研究機構、文學藝術人才通常集聚于城市,知識的廣泛流通塑造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對于城市各種負面現象的批判并未削弱多數人對于城市的向往。
耐人尋味的是,社會學給予城市的樂觀評價并未獲得文學的同等響應。許多文學作品毫不吝惜地貶損城市。大部分作家躋身城市,然而,他們熱衷于對于城市空間的各種人情世故冷嘲熱諷,懷念鄉村甚至成為一種文化時髦。農業文明訓練的美學趣味業已根深蒂固。
二
無論是踞守城市、維護城市還是尖銳地批判城市,鄉村往往成為一個參照坐標。農業的歷史遠遠超過工業與商業,城市時常被視為可憎的暴發戶。另一些思想家更為痛心的是文化遭受的破壞:鄉村生活之中某些依附于自然和土地的習俗傳統正在被徹底斷送。例如,西美爾的《大都會與精神生活》明顯流露出“人心不古”的感嘆。
20世紀之后的中國文學愈來愈強烈地意識到“鄉土中國”與城市、工業、現代社會之間的復雜糾纏。相對于城市的嘈雜、市儈習氣乃至爾虞我詐的算計,古典文學反復出現的田園意象令人心曠神怡。然而,愈是悠然自得地吟詠唐詩宋詞的名篇佳句,一個持久不變的歷史事實愈是刺眼:古往今來,為什么效仿陶淵明返鄉事農的人寥寥無幾?城市的持續膨脹表明,多數人的選擇恰恰相反。當古典文學的鄉村景象作為“他者”的時候,城市暴露了諸多負面因素;一旦恢復鄉村的真正面貌,恢復鄉村的貧瘠以及繁重的田間勞作,城市再度迅速地贏得競爭。很大程度上,鄉村的山光水色毋寧是城市居住者的“象征之風景”(landscape of symbols)。許多時候,文學乃至繪畫的鄉村景象恰恰是城市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些“土地修辭學”包含了一系列隱蔽的詮釋和建構,“遮蔽掉的東西可能如其顯示的東西一樣多”。
不同版本的鄉村神話隱含了某種相似的觀念:鄉村的氣氛安寧、遲緩、祥和,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沉悶、閉塞乃至蒙昧。然而,這些觀念低估了鄉村的革命能量。中國的現代歷史很快打破了鄉村形象,“農村包圍城市”與土地革命翻開了新的一頁。這時,文學的城市與鄉村開始按照另一種劇本重新書寫。
三
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的文學史顯明,鄉村贏得的文學成就遠遠超出了城市。相對于鄉村、土地,以及阿Q、朱老忠、梁生寶以來幾代農民形象,圍繞城市的文學敘述乏善可陳。20世紀上半葉,“無產階級”概念的引入并未轉換為深刻的文學形象。葉圣陶《倪煥之》的主人公僅僅停留在革命的大門之前,茅盾的《蝕》三部曲是失意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如何在革命失敗之后進退失據,老舍《駱駝祥子》的祥子最終還是沉沒在城市的污泥濁水。城市革命、工人與無產階級歷史命運的扛鼎之作始終闕如。20世紀下半葉,城市進入無產階級政權的管轄范圍,這個轉型不僅負有振興社會主義工業的使命,同時負責多方面清除資產階級消費意識形態和頹廢墜落的生活方式。然而,文學對于城市和工業十分陌生,許多作品拘謹僵硬。人們既無法體驗灼熱的、富有活力的城市,也無法看到獨特而復雜的人物性格。一種觀念對于文學的束縛可能超出了預想:城市是不潔的、狡詐的,充滿風塵氣息乃至邪惡的誘惑,城市的享樂主義與不勞而獲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溫床,如同茅盾的《子夜》或者曹禺的《日出》所表現的那樣。許多圍繞鄉村展開的文學敘述之中,城市通常扮演一個帶有貶義的空間坐標。那些試圖進入城市謀生的農民往往事先與虛榮浮夸、貪圖享受、忘恩負義、好逸惡勞這些道德瑕疵聯系在一起。
作為“海派”與“京派”之爭的主角,上海時常被視為更為典型的現代都市代表。文學考察表明,上海帶動的文學敘述可以引申出多個迥異的方向。20世紀20年代以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葉靈鳳為首的“新感覺派”對于上海現代景觀的魅惑抱有夸耀式的贊賞。然而,茅盾的《子夜》已經自覺地將夸耀式的贊賞替換為批判。茅盾的雄心是在《子夜》之中解剖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經濟結構,再現民族工業如何在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和壓迫之下可悲地破產。20世紀80年代之前,城市的文學敘述遠遠低于預期。各種“想象”資源并未成功地被轉換為作家的文學構思,并且賦予特定的美學價值。相當長的時期,城市的文學敘述沉悶乏味,線條粗糙。張愛玲與錢鍾書的重見天日——張愛玲的小市民刻畫或者錢鐘書的《圍城》之所以引人入勝——恰恰反襯出城市的文學敘述停滯不前。
四
城市的眾多人口和龐大的消費需求時常引起經濟學的關注。城市之所以贏得文學的注視,城市意象的歷史文化縱深與美學光芒往往是更為重要的原因。城市的時尚和商品并非僅僅表示虛榮和浮淺。當時尚與商品獲得另一種歷史文化注釋的時候,當樓房、橋梁、金屬架構被視為另一種現代美學風格的時候,城市不再是背景而開始充當獨立的角色。對于李歐梵的《上海摩登》說來,20世紀上半葉充斥上海市面的雜志、畫報、商品廣告、月份牌這些日常物品開始顯現出歷史的光澤,甚至可以充當懷舊的對象。外灘的銀行大樓、飯店、教堂、俱樂部、電影院、咖啡館、餐館、豪華公寓、跑馬場,這些建筑不僅標志了西方的霸權,同時還表明現代性的降臨。現代性名義下的描述開始暴露上海內部遭受遮蔽的另一些文化空間。
對于城市的文學敘事,王安憶的《長恨歌》是一部不可忽略的作品。《長恨歌》的眼光落到城市的底部,一本正經地開始考察弄堂、閨閣這些處所。農耕文化造就的美學趣味將風花雪月、青峰、扁舟、小橋、黃葉組成“詩意”圖景的基本元素,現在是城市的獨異風貌邁進美學門檻的時刻。現今的一些作家正在推出另一個片面的上海——只不過“階級”的概念被替換為商品與消費。批評家曾經從郭敬明的《小時代》之中整理出一份時尚生活指南。這種敘事的一個潛在預設是,無論是浪漫、憂傷,還是怨恨、憤怒,商品與消費是表白一切的語言。
金宇澄的《繁花》轉到了日常生活的洪流背后,察覺的是五花八門又千篇一律的基本架構。小弄堂、小包間、小庭院等眾多切割出來的小空間,小風月、小情欲、小試探印染而成的流水一般日子。《繁花》不厭其煩地將諸如此類匯合起來,構成一個規模可觀的格局。這是另一種歷史文化的縱深。
五
追溯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二元對立,正視兩種空間的經濟、社會鴻溝是不可忽略的前提。20世紀80年代初期,高曉聲的《陳煥生上城》名動一時,以至于延伸出一個“陳煥生”系列故事。然而,喜劇的笑聲毋寧說來自城市視角。置身于鄉村文化,主人公的更多感受是被鄙視、排斥和屈辱。相對于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文學開始坦率承認一個事實:鄉村文化并未成功地提供一套抵制乃至反抗城市的價值體系;相反,鄉村文化翹首期盼城市的發達與繁榮,并且對于鄉村的封閉和保守流露出愧疚之意。從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到賈平凹的《廢都》《秦腔》,鄉村出身的主人公始終遭受城市文化的折磨。骨子里的自卑迫使他們迅速站到城市文化這一邊,以模仿的方式扮演一個合格乃至標準的“城里人”。
城市對于鄉村的戶籍限制已經結束,相當一部分農民進城務工,他們的收入足以維持日常開銷。盡管如此,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隔閡遠未消除。從膚色、言辭、表情、服裝到室內裝飾、消費傾向、職業選擇、藝術評價,“城里人”與“鄉下人”無不存在明顯或微妙的區別。年輕一代的鄉村子弟的品位仍然無法企及“高雅”的城市文化,例如“殺馬特”,他們無法掌握城市文化時尚的微妙、得體,無法掌握刻意修辭與風輕云淡之間的平衡,種種奇裝異服透露出不可祛除的鄉土氣質。鄉村文化拒絕這種風格,城市文化嘲笑這種風格。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一個重大差異是,前者仍然按照生存的基本需要衡量物質的價值,后者根據多重標準評判物質的功能——物質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符號。以飽暖為首要乃至唯一主題的鄉村文化對于這一套懸浮的符號魅惑茫然無知,茫然無知的表征首先顯現為“土氣”。
從大眾傳媒到各種文化機構,城市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大規模的符號生產。由于復雜的專業知識訓練,符號生產往往甩開“鄉下人”而被城市文化壟斷。這些符號充當了城市拒絕“鄉下人”的文化城墻。一個耐人尋味的比較是:借用符號改造“鄉下人”的身份顯然比具備足夠的物質經濟條件容易得多。如果說,鱗次櫛比的大樓、繁華的街道與開闊的田野、偏僻的山區是城市與鄉村的首要區別,那么,互聯網設立的虛擬空間之中,這種區別遭到輕松的解構。只要簡單地配備光纖和信號發射塔,荒山野嶺可以立即享用大都市所擁有的符號產品。人們的文化身份、社會關系、經濟來源以及消費方式將在數字社區經歷深刻的震蕩與調整;而且,虛擬空間與傳統的城市、鄉村之間的復雜互動甚至開始動搖一系列人們耳熟能詳的社會學范疇。
林那北對于虛擬空間帶來的日常生活改變保持特殊的興趣——她的《雙十一》幾乎聚集了這些改變的各種元素。“雙十一”即是虛擬空間人造的消費狂歡節。利用手機和互聯網促銷,這是數碼時代成功的商業策劃。傳統商業遠遠無法企及手機與互聯網制造的消費規模。人們可以使用各種虛擬的文化身份登陸虛擬空間,“城里人”或者“鄉下人”的區別不再是一目了然的表象。擺脫“鄉下人”的身份烙印,利用虛擬空間的特征謀利,這恰恰是《雙十一》主人公的人生設計。一對來自鄉村的年輕夫妻居住在城市的破敗出租房里,熟知互聯網生態的丈夫將妻子的照片貼到征婚網站,慫恿妻子以未婚的身份與諸多征婚對象約會,從而謀取若干不義之財。《雙十一》的情節展開的另一個空間顯現出種種前所未有的可能,甚至發現某些重構生活形態的節點,例如社會身份。虛擬空間可能重置現實空間的各種傳統區隔——眾多社會地帶的重新劃分包含了改善自身待遇乃至反抗不公的可能。由于虛擬空間提供的新型誘惑,蟄伏于人物內心的各種欲望突然擺脫了冬眠狀態,開始蠢蠢欲動。
互聯網虛擬空間的誕生動搖了傳統空間生產的各種原則,譬如城市與鄉村的區隔、商業與文化的區隔。很大程度上,上層與下層、邊緣與中心,國界、語種、專業知識的門檻、地理距離等界限的效力正在被削弱。互聯網開放了空間生產的權限,以至于許多人興致勃勃地參與虛擬空間的生產。《雙十一》的主人公試圖為自己再造一種新型的社會身份。
當然,傳統的空間并未消失,種族、階級、性別,以及職業、職務等傳統的身份標志并未過時,但是,數碼身份的誕生觸動各種既定身份標志的再度排列與組合。從反抗、革命、冒險、犯罪到組織動員、發現商機、社會監管、制造新的工作崗位,一批迥異的情節呼之欲出。眾多跡象表明,新的空間繪圖正在醞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