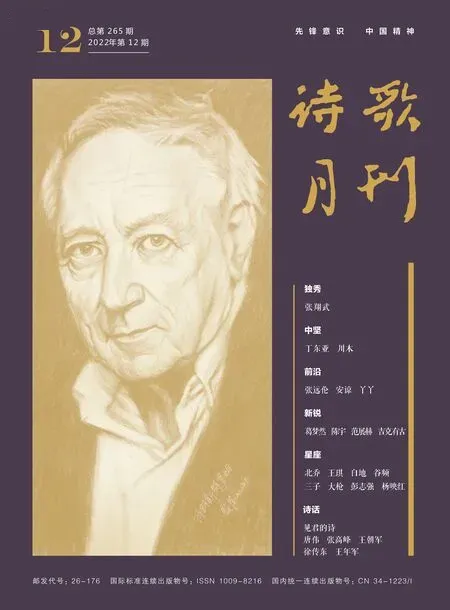訪談:從日常中淬煉出智慧
丁東亞 川木
1.緣何寫詩?
丁東亞:我絲毫不避諱,一開始寫詩是為喜歡的女孩而寫,那種有感而發、由心而生的分行,此時看來算不得是真正的詩,卻足夠真誠。但真正開始愛上寫詩,卻是高一下學期在山西的《作文報》上發表第一首詩之后。
川木:剛開始寫詩時沒有別的考慮,完全是因為傾訴的需要。詩歌是最適合傾訴的文體,每次寫完后,都有一種如釋重負、大病初愈的感覺,甚至有一種浸潤全身的幸福感。慢慢地,我從詩歌的傾訴中發現了語言的魔力、邂逅心儀之詞的驚奇。再后來,我就自覺地通過詩歌寫作,重建我與世界、我與他者、我與自己的關系。
2.你的詩觀是什么?
丁東亞:不管詩是對回憶或所見之物的所感及記述,還是對心境的寫照、世相的諷喻,無疑都是為了提升詩歌中源自現實的高尚層次,以及讓日常事件與客觀事物在進入文本時轉化為形而上和倫理的思維。也只有如此,個人經歷才有普遍性社會意義,并飽含文學性。
川木:與其他文體相比,詩歌最終指向那不可言說的言說。在一首詩里,詞語與詞語之間既可經由呼喚、呼應、呼號而相互慰藉,也可經由拆解、悖謬、反諷而反目成仇。衡量一首詩,不能僅僅解讀詞語的意義,而要借助于結構的安排、詞語的組合、氣韻的流動,感受其內在節律、復合意旨、隱喻關系等等。
3.故鄉和童年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丁東亞:故鄉必將是我一生寫作的起點與根。在外生活多年,豫東平原始終是令我魂牽夢縈之地。詩歌作為一種時間性的體驗,其細節的獨特性就是詩的肌質,而且這種肌質不會消失,會長久地留在詩人的記憶,甚至會確定詩歌結構的形態。
川木:童年和故鄉不僅僅是一個時間和空間概念,也可能是一種味覺、聽覺或者視覺概念。比如,對于一個常年漂泊的海外游子來說,童年和故鄉已經融入其味蕾中;而對于一個有著文本自覺的詩人來說,童年和故鄉已經融化在其語言里。
4.詩歌和時代有著什么樣的內在聯系與對應關系?
丁東亞:我相信任何一個詩人都無法回避時代性。每一代詩人的作品都飽含特定時代的因子。盡管一些時候我們擁有借助想象與生活意識將人們引向另一種生活的能力,通過自我挖掘或敞開,完成深入生活寫作的可能,但自身與生活中的事物依然存在著某種界限或隔閡,并在竭力趨近生活本真的過程中被限制。
川木:時代對詩人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時代是發問者,詩人是回答者。有的詩人熱忱擁抱和回答時代的提問,有的詩人則要經過反省、咀嚼和發酵才能理解時代,進而矯正自己在時代中所處的位置。因此,詩歌與時代的關系既有線性對應關系,也有非線性折射關系。
5.對于當下的詩歌創作,你的困惑是什么?
丁東亞:意義和價值的缺失。作為詩人,應真誠地面對自我和真實世界,用哪怕微弱的聲音去吶喊,抑或敦厚地記錄,也從不失去本我的思考與觀點。這也正是詩歌的“意義”所在。畢竟詩能直接通過賦予平凡生活的事件與事物以意義,從而使它們免于毀滅在某種糟糕的處境。
川木:創造力衰退是我對當下詩歌最大的困惑,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更多地是在重復前人的詩歌,重復他人的寫作,重復自己的表達。橫向上看,詩歌的同質化比較嚴重,缺少視角、題材、詞語、想象力等方面的開拓;縱向上看,影響的焦慮依然彌漫在個體的寫作中,文本和風格的固化猶如堅冰。
6.經驗和想象,哪一個更重要?
丁東亞:后者。詩人必須有著精確而生動的想象力。本雅明在談及詩歌的想象力時,則將之與意志聯系起來,認為“沒有精確生動的想象力就沒有完好無損的意志”,畢竟生活之意象只是作為詩人寫作的強化和輔助。
川木:經驗和想象是詩歌的雙翼,二者缺一則無法達到寫作的自由狀態。只有通過寫作經驗的積累,詩人才能找到適合自己的觀照視野、創作題材、表達方式、文本風格,才能在一首詩歌里處理好起承轉合、節奏演進、詞語組合。而想象,則以其感同身受的方式為我們提供日常生活中難以享有的體驗,這也是對貧乏世界的補充、對麻木不仁的補償。
7.詩歌不能承受之輕,還是詩歌不能承受之重?
丁東亞:不能承受之重。更多時候,詩歌寫作猶似一種精神的慰藉與寄托,是一個人與這個時代集體心靈的對話,為其發聲,是為了像一個真正的人那樣活著,在辯證性的精神生活世界,表達出那“既讓人害怕又感到愉悅的無解、未決的抗爭”。
川木:關于詩歌的輕與重需要辯證分析,不可籠統言之。有的詩人處理的題材是輕盈或歡快的,有的則承載著沉重或悲壯的話題;有的情緒和節奏是自由奔放的,有的則是壅滯凝重的。總體看來,當下詩壇上“輕”的詩歌偏多,“重”的詩歌偏少,像昌耀那樣用生命寫作、以寫作為生命的詩歌更是十分難得。
8.你心中好詩的標準是什么?
丁東亞:《壇經》“坐禪第五”篇,六祖惠能為眾人講授“坐禪”時云:“善知識,何名坐禪? 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于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詩歌寫作是否如坐禪,我淺薄地認定它們可以一并而言,那種“本性元自清凈”之作,大概就是我認定的好詩歌。譬如雷平陽的《伐竹》,又如胡弦的《尺八》……
川木:詩無達詁,我們無法用量化標準來衡量一首詩的好與壞,但是好詩依然是可以辨認的。好詩的詞語會令人驚異,好詩的節奏會契合默讀或朗誦時的脈動,好詩的情緒會浸潤讀者的身心,激發身體的戰栗和靈魂的共鳴。一句話,好詩是那種一見鐘情、百讀不厭的詩,是那種可以陪伴我們人生之旅的詩。
9.從哪里可以找到嶄新的漢語?
丁東亞:我個人時常會從民間文學中汲取養分,那些流傳數百年的民歌、民謠,以及童話,都是有益于詩歌創作的。特別是少數民族的。土家族是湖北少數民族人數最多的一個,主要分布在恩施和宜昌,他們的民歌、舞蹈和哭嫁習俗等,都影響了我。
川木:要想找到嶄新的漢語,一方面,我們要回溯漢語詩歌的源頭,恢復其在《詩經》《楚辭》及其以前的原初生命樣態;另一方面,我們要借鑒非漢語寫作的成功經驗,為漢語詩歌寫作注入新鮮血液,擴大其可能的創造邊界。
10.詩歌的功效是什么?
丁東亞:對我個人而言,詩歌的功效是盡可能真誠地表達自己的愛與憎;當然,我并非總是沉湎這種小我的情感,因為沉湎自己的私人情感時,可能會徹底背對這個世界。只是一些時候,當我們想要用詩歌書寫當下的困境所在時,我們又是何其無力與渺小。贊歌亦然。
川木:詩歌在不同層次上、對不同的閱讀對象具有不同的功效。就宏觀而言,詩歌是時代的見證,是對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守護,是文學語言的開拓創新;對讀者個體來說,詩歌給我們提供一種緩慢前進的勇氣和信心,為那些無可慰藉之人提供心靈的慰藉。
11.你認為當下哪一類詩歌需要警惕或反對?
丁東亞:我想要稍稍更改一下問題作答,就是要警惕那些對著鏡子說“你看,他多完美啊”的人,因為他的自戀一如他們的作品,實在太過自戀和矯情。
川木:詩歌寫作是值得我們終身托付的事業,需要“一個一個生命地書寫/一個一個死亡地書寫/一個一個詞語地書寫”(埃德蒙·雅貝斯)。對那些缺乏真誠、沒有耐心、不愿付出的寫作,我們都要加以反對。在當下,尤其要警惕那些以詩歌之名行討巧之實的假詩、偽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