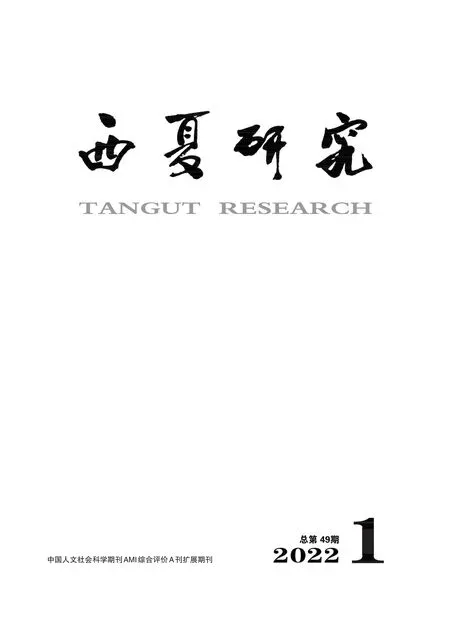敦煌莫高窟第3窟壁畫“新特征”
□景利軍
莫高窟第3 窟,作為敦煌莫高窟晚期石窟的典型代表之一,因其新穎的繪畫風格、精湛的繪畫技法、獨特的布局形式和高超的線描技藝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但長期以來,莫高窟第3 窟的時代問題學界一直爭論不休,一說認為是元代晚期營建,一說則認為是西夏時代營建。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最早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1]中將莫高窟第3窟劃分為元代窟,隨后《敦煌石窟內容總錄》[2]、《敦煌石窟藝術》[3]、《敦煌石窟鑒賞叢書》[4]、季羨林主編的《敦煌學大辭典》[5]、趙聲良的《敦煌石窟藝術簡史》[6]以及《敦煌石窟全集》[7]等文獻、圖錄資料,相繼遵循第3窟為元代窟,并進行了簡要釋解,為研究敦煌石窟藝術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20 世紀90 年代,敦煌研究院成立50 周年之際,霍熙亮在《莫高窟回鶻和西夏的新劃分》一文中指出:“第3 窟壁畫精湛出群、線描獨領風騷。但很難找出它的來龍去脈,據以往調查的印象,與安西東千佛洞第7窟西夏壁畫藝術十分接近。若出自元末畫工之手,如何出現復古的線描?改為西夏較為合適。”[8]54隨后,關友惠的《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畫裝飾風格及其相關的問題》專門就第3窟壁畫時代,從崖面位置、壁畫內容、題記、裝飾圖案等作了初步分析,認為主要的壁畫是西夏所繪:“可能始鑿于北宋曹氏時期,佛龕頂部裝飾是曹氏末期樣式,四壁菩薩又是西夏風貌,推測龕頂與藻井裝飾可能始繪于曹氏末期,繪工未完因故而終止,或是西夏占領瓜、沙之后,由本地畫工繪了龕頂與藻井部分,不久又請中原內地來的名師高手繪了四壁菩薩人物。應是西夏諸窟中較早的一窟。”[9]謝繼勝在《莫高窟第465 窟壁畫繪于西夏考》中提到南區的第3窟作為元代石窟值得懷疑,提出很可能是元代修補的西夏窟[10]。與此同時,沙武田、李國的《敦煌莫高窟第3 窟為西夏洞窟考》從西夏在敦煌石窟營建背景、佛教藝術及河西的觀音信仰、供養人畫像、裝飾圖案的時代特征等多方面分析了莫高窟第3窟為西夏時期所營建的洞窟[11]。
蘭州大學于宗仁《敦煌石窟元代壁畫制作材料及工藝分析研究》通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對敦煌元代9 個窟和榆林窟保存元代壁畫的6 個窟的制作材料和工藝進行了研究,提取第3 窟壁畫的顏料成分,深入解讀了壁畫所用顏料的成分及由來,充實有加[12]。中國美術學院陳氏河玲的《敦煌第3 窟與越南筆塔寺的千手觀音造型研究》主要以觀音的造型異同為主,探究兩國觀音造像的時代、地域、民族、文化、本土信仰和宗教思想等諸多的差異[13]。
著手觀音經典造像及源流考的有:王惠民《敦煌千手千眼觀音像》[14],謝生保、謝靜《敦煌藝術中的千手觀音》[15],彭金章《千眼照見 千手護持——敦煌密教經變研究之三》[16],馮漢鏞《千手千眼觀音圣像源流考》[17],其中有介紹第3窟壁畫造像的內容及千手千眼觀音的由來。李月伯《從莫高窟第3窟壁畫看中國畫線描的藝術成就》一文中,對線描表現技法、壁畫的制作方法等作了進一步的研究,從美術學的角度閱覽了第3 窟別樣的藝術特色[18]。莫高窟第3 窟壁畫損害嚴重,藻井大部分已破損。針對壁畫的制作材料和顏料分析,探討壁畫病害成因的研究有:段修業等《莫高窟第3窟泡疹狀病害的研究——溫濕度觀測和制作材料的分析》[19]、趙林毅等《莫高窟第3 窟壁畫制作材料與工藝的無損檢測分析》[20]。
經研究發現,第3窟壁畫人物形象出現了新的造型樣式,即同一種形象有不同的造型特征,如“世俗化”的人物形象、從“神格”到“人格”的毗那夜迦神像、異樣的飛天造型。本文欲在學界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就這三個方面的新特征來凸顯具有時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特點的“佛教中國化”的重要體現和元代工匠敢于突破傳統、大膽創新的精神,“新特征”的發現亦是證明此窟為元窟一說的有力依據。
一、人物形象的“世俗化”
吉祥天女,最初傳入中國是以女性形象公之于眾的。據考古實物可知,我國現存最早的吉祥天女形象在新疆和田(古代于闐)丹丹烏里克遺址,其形象出現在一座廢寺的殘壁上(可見《文史知識》1994年第8期封面),這身天女身姿優美,呈S 形曲線,以鐵線描勾勒后略施淡彩暈染而成。該壁畫時代約為公元8 世紀,內容取材古代于闐建國傳說“地乳育嬰”的情節,形象塑造上明顯運用了古印度常用女體“三屈法”繪制,同時更令人想到于闐著名畫家尉遲乙僧的繪畫風格[21]。吉祥天女的造型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在古人當時的審美觀下,根據理想女性的形象原型升華而成。
唐至元代的敦煌壁畫中,吉祥天女有時出現在大型經變畫、維摩詰經變畫、藏經洞絹本佛畫中,以及在龍王或天王的形象中一起出現,描繪之處只多不少,數量可達十數以上甚多[22]。第3 窟北壁西側的這身吉祥天女(圖1),被描繪的有點像唐代宮廷里的宮女,整體展現給我們的是一位體態豐滿、風采迷人的女性形象,這種以體滿豐韻、大袖襦裙為主旋律的漢族傳統服飾繪制的作品在唐以后就屬元代最為盛行。相比莫高窟壁畫中元代仕女或供養人,體態豐腴且輕盈,體現的是元代以健康為主的審美意趣。這種飽滿的造型與明清時期骨瘦溜肩的仕女形象有著很明顯的區分,同樣都是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升華出不同的具有世俗化的佛教藝術形象。這與山西芮城永樂宮壁畫中的仕女形象倒十分相像。從人物形象分析,頭冠相對簡化,沒有元代永樂宮壁畫中捧香爐仕女(圖2)繁復,但人物的面部塑造基本一致,都是雙眼注視前方,嘴唇微抿,眼眉間的線描向后拋出,交領長袍于腰間束帶,形象氣質十分相似,但前者更加形神兼備。天女和仕女的襦裙擺動幅度大,線條的勾勒采用鐵線描和折蘆描的結合,瀟灑自如、酣暢淋漓。在圖像的布局形式上,二者都是作為畫幅中主像的眷屬出現在其左右,這種近乎相似的組合樣式肯定是出自某種特定的模式或在默認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同屬元代的產物是值得肯定的。
世人常言“北敦煌,南大足”,然而遠在千里之外的重慶大足石窟,其北山的千手觀音圖像中功德天和婆藪仙的布局依然如此,呈對應分布,這就說明即使不在《千手觀音造次第法儀軌》記載之列的神靈,在佛教造像和壁畫繪制時,同樣把這類眷屬巧妙地安排在觀音左右。其實儀軌中不被記載而經常出現的神靈還有很多,如世人皆知的文殊、普賢、地藏菩薩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在其他典籍中記載的他們的形象,時常被應用于造像或繪壁。因此,研究圖像本身對于分析佛教石窟壁畫藝術、文化特點及宗教藝術就顯得尤為重要。吉祥天女作為千手觀音眷屬,由最初裸露的印度風,逐漸在中原本土文化的影響下,更加具有生活氣息,接近世俗性,體現了當時古人對于優雅智慧女性的一種認知,從而體現在佛教壁畫藝術作品之中。

圖1:莫高窟3窟北壁·吉祥天女

圖2:《永樂宮三清殿壁畫朝元圖(原版)》西王母右側·捧香爐仕女
二、從“神格”到“人格”的毗那夜迦神像
毗那夜迦早在唐以前均以神王立像出現,基本特征是獸頭人身,位于造像的最底層,其作用主要是守護佛法,多為護法神。唐宋元時期的毗那夜迦一般屬于惡神,受到佛或佛教諸神的降服,這與早期守護佛法的性格完全相反[23]44。這些惡神的出現無疑不在展現著觀音的威力。松本榮一將象頭神定為毗那夜迦,又將豬頭神定為金剛面天[24]656。敦煌繪畫品中有千手千眼觀音變70 多鋪,其中毗那夜迦有14鋪(見下表),一般為兩身,位于下方兩角明王前面[14]。法國藏MG.17659 千手千眼觀音變繪于981 年,在下方兩角各有一明王,明王的前面分別有豬頭神、象頭神,榜題分別是“毗那鬼父”“夜迦鬼母”(圖3)[23]46-55。關于象頭神(圖4)的起源,饒宗頤先生把它譯為“讠我尼沙”,意思謂:歸命讠我尼沙神,是一切障礙的克服者,好像中國人念南無(namo)觀世音菩薩一般。敦煌石窟后期,元代亦有讠我尼沙像,蒙古銅制佛像也有不少象頭人身像[25]483。這也就證實了第3 窟就是元代時期的壁畫一說。
因此,即使是惡鬼的毗那夜迦在該鋪經變畫中,也如吉祥天和婆藪仙那樣呈對應的形式布局繪制而成,雖然從圖像上、獸冠上無法判別其男女之別,但依據法藏MG.17659千手千眼觀音變中的榜題基本可以確定豬頭的代表男性、象頭的代表女性,這剛好與東西兩側的男性婆藪仙和女性吉祥天對應。因為在藏密中的毗那夜迦大多數以男女相抱之形出現。唐代的佛經中也規定毗那夜迦應為男女相抱之形。關于相抱之形的毗那夜迦在莫高窟其實也有出現,莫高窟第465窟是藏傳佛教薩迦派藝術的典型代表,窟里就繪有男女相抱的毗那夜迦像,是一個很好的對照。這里把不可分割的毗那夜迦拆分后,采用對稱式的構圖方式繪制在僅次于菩薩眷屬、侍從的位置,不僅是畫師巧妙經營的高藝,更是中國本土毗那夜迦的形象產生的結果。

敦煌繪畫中千手千眼觀音變中的毗那夜迦統計表

圖3:法藏MG.17695中的毗那夜迦

圖4:印度的象頭人身Ganesha塑像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第3窟北壁底層東、西兩側的二身毗那夜迦像,此時的毗那夜迦早已幻化成人的模樣,更像是戴著豬頭形、象頭形的帽子,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象冠人面人身”和“豬冠人面人身”的毗那夜迦形象,即“象冠毗那夜迦”(圖5)、“豬冠毗那夜迦”(圖6)。這兩身毗那夜迦的形象,沒有像以往一樣雙手合十做求饒狀,而是神嫻自若,各自胡跪。“象冠毗那夜迦”和“豬冠毗那夜迦”的頜下,都系著象爪和豬爪的束帶,有點像戲劇中假面具的意味,很有可能也是受到宋元時期發達的戲劇影響。從“獸面人身”到“獸冠人面人身”的變化,我們可以明確的意識到,畫師賦予了這些神像更多的人性化特征,這就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重要體現,是進一步結合了時代文化和地域文化之后,演變產生的“人首人身”毗那夜迦像。

圖5:莫高窟3窟北壁·象冠毗那夜迦(局部)

圖6:莫高窟3窟北壁·豬冠毗那夜迦(局部)
除此之外,豬冠的毗那夜迦所戴的帽子,和蒙古人鈸笠帽的造型特征十分相近,側面造型可視為一個“平面三角形”的帽子,造型完全吻合。從榆林窟第3窟甬道的蒙古男裝中可以明確看到二者是有共性的,在這里將豬的嘴部和耳朵加大加長向外延展開,與元代地位較低的人所戴鈸笠帽幾乎一模一樣。同時,榆林窟第3窟甬道有明顯的題記“維大元至正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嘉議大夫沙洲路總管……”與莫高窟第3窟的題記“至正十四年”,時間相差11年,二者同屬元代晚期石窟藝術的風格特征,這種造型和蒙古人彪悍的民風有著極大的關系,敢于打破常規創造出新的事物,在藝術上更是大膽的嘗試,不束縛于傳統壁畫造型的模式中,在承襲中推陳出新。
三、南壁異樣的飛天造型
飛天傳入中國后,最早的雛形是以飄動的披帶來代替可以飛起來的翅膀,因此早期壁畫中多見系帶飄舞的飛天,造型大多呈“V”字形,如莫高窟257 窟北壁,北涼時期的飛天群就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飛天的形象歷代以來不斷變化,到了隋唐時期呈現出新的面貌。唐朝以胖為美,這一時期的飛天亦是如此,身體多趨于肥胖,大氣、雍容。
第3 窟南、北壁上方所繪四身飛天,神態輕盈,自由回旋飛舞而來,同踩欄墻上金黃色祥云,這種造型極其少見,因為敦煌壁畫中的飛天大多以伎樂為主出現,而這種類似夫妻形式出現的飛天在敦煌莫高窟中實屬罕見。北壁所繪兩鋪飛天應為同一粉本正反面進行復制而成,只是在人物面部塑造上有著明顯的區分:西側飛天(圖7)面相圓潤,白發束紅巾,柳葉彎眉,眼睛微睜,抿嘴賦紅唇,像極了女性羞怯之色,很明顯為女相;東側(圖8)則面相方正,粗眉大眼凝視對方,未設唇彩,黑鬈發扎紅帶,顯然是男相。因此,北壁上方兩側的飛天在構圖形式上滿足了對稱,造型特征上也異形不多,姿態和服飾上也基本相似,只是在局部配飾、著彩設色和面相特征上做了區分。這種圖像形式背后所蘊含的意味與道家天人合一、陰陽兩行的思想主導不謀而合,兩身飛天的神貌儀態已經不像佛教的飛天造型,更像是道教的仙童形象乘云而下,從發髻和面相特征來看,明顯有性別區分,這種巧妙的男女搭配、陰陽的左右平衡,與元代所崇尚的道家思想極為相似,更加證實了此窟為元窟一說。

圖7:北壁西側·飛天

圖8:北壁東側·飛天
觀音畫像在唐宋時期就已經女性化了,如莫高窟第57窟南壁觀音就是一鋪體態婀娜、美麗動人的女性觀音畫像。又如榆林窟第2 窟,窟門左右兩側的水月觀音壁畫,用蝌蚪式的胡須來區分男女。而到了這里將飛天同屬于觀音形象體制中進行創作,不再使用胡須來區分男女,而是以胭脂涂紅唇來區分男女之別,本身就是一種大膽的嘗試,這樣的巧妙運用在敦煌莫高窟中為首例,又是敦煌飛天創作中的一大突破。南壁異樣的飛天,下著裙帶,雙膝跪于金黃色云端呈禮拜狀,像極了一位遠道而來的男供養或信奉者手托貢品雙膝跪地,身體豐滿,面相龐大,黑發設色束金飾。每一個云頭中心涂上厚厚的白色,增加了云層間的體積感,又是一個小小的創新,使其既有創新又不拘泥于傳統,將飛天形象提升了一個境界,使得畫面恢宏有氣勢且不缺少細節。同時,體現了這一時期的飛天,不但具有世俗化的形象特征還出現了區分男女的新藝術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第3窟的四身飛天中,北壁兩身(圖7、8)和南壁東側(圖9)三飛天身后云紋一模一樣,沿上檐繪制的云尾都添加了云團,身姿也是呈飛來欲下之勢,唯有南壁西側上方這一身飛天(圖10)別出心裁。首先是如飄帶般順滑的云尾,沒有繪制小云團來增添變化,而是用順暢的線條直接繪制云尾,像極了人物的衣帶,更加趨近世俗化、人性化。其次,相較于其他三身欲勢而下在乘于云端的飛天,這身飛天則是虔誠地跪敬。因此,筆者推測可能是畫工在繪制時,這一身飛天為四飛天中最后完成的,也許是偷工減料所為。另一種可能就是呈禮拜狀的飛天應是供養人的體現,飛天雙手托供品,跪于云端,就是信仰者在世俗生活中的體現。遺憾的是,經仔細查驗并未在此處尋覓出絲毫關于供養人題記的線索。雙膝跪在云端的飛天于元代壁畫中倒是第一次出現,在其他壁畫中筆者也未曾見到,再一次體現了元代畫工的匠心獨運。

圖9:南壁東側·飛天

圖10:南壁西側·飛天
同時,在技法上也表現出濃郁的中原畫風,飛天的構圖飽滿、疏密得當,線描技法嫻熟細膩、線條酣暢淋漓。元代的“朵云紋”在保持朵狀體積感的同時,往往呈現較強的組合感[26]21。南北兩壁這四身飛天所乘的祥云紋,無論是組合形式、繪畫技法還是顏色都如出一轍,這四朵祥云紋就是“朵云紋”的造型模式。主要造型特征是以“卷云紋”為基礎,四周環繞多個雙勾卷云紋。雙勾卷云紋皆對稱排列,既有內斂式的,也有發散式的(指“云頭”向內旋轉或向外旋轉),云頭的方向也各不相同,有的朝上、有的朝下、有的朝外、有的朝內,其組合模式多樣,彼此間聯系也十分緊密,然后再加上一條“云尾”,一個完整的朵云紋繪制成功。四個朵云紋全部以黃色染成,其云尾都只有一個,全部蜿蜒細長如飄帶,翻折自如地回旋在飛天上方,形成一種強烈的動感。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
第一,元代在思想文化和藝術方面的政策十分寬松,在藝術領域極大地提高了畫家在繪畫藝術過程中的自主性,使元代的文人畫家及畫匠都有著便利的創作自由空間,能夠隨意地表達自己的創作思想和繪畫情感。他們融匯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努力找尋二者間的平衡和在藝術上的體現,構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繁華景象。因此,第3窟的藝術價值已經遠超它自身的宗教意義。
第二,元代畫工在追溯唐人遺風的同時,兼容并蓄地吸收了西夏在敦煌壁畫中以線造型的白描技法,并在其基礎上結合佛教儀軌,重新創作題材、豐富內容、經營位置,于傳承中求創新。第3窟壁畫藝術具有獨特性、代表性和不可替代性,在這一時期出現這種新的造型樣式,如“世俗化”的人物形象、從“神格”到“人格”的毗那夜迦神像、異樣的飛天造型等藝術風格都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體現,這種“中國化”突出了時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點,更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