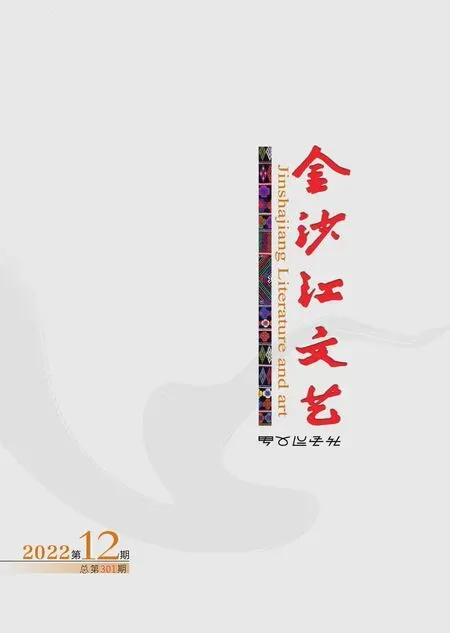潮州巴黎
◎邢若琳(山東)
(一)
高三那會兒,安況睡我下鋪。我那時候點燈熬油學到半夜,上進啊,跟現(xiàn)在不一樣。有天夜里起來上廁所,見他光著上身,瘦得皮包骨,趴在窗臺上,翻看什么紙張。細長的指間煙霧升騰,汩汩融進夜色里。那時我覺得抽煙是只有況子這樣的“二流子”才干的事,瞎拽,有屁意義。如今的我,沒有煙一天都活不下去。我愣了半天,頭一回覺著,他抽煙的樣子挺好看。那也是他頭一回跟我講,他叔叔的故事。
他說他有個叔叔,叫安勇。72年生,比他爸小兩歲。他從沒見過這個叔叔,只能從街坊四鄰的只言片語中,拼湊出一個人的一生。若不是偶然發(fā)現(xiàn)安勇親筆寫的日記,他都不相信,真有這么個傳奇般的人物。神經(jīng)兮兮,聽起來都笑人。
“高考完,我就去找他。我真很想知道,他最后,最后到底找到安妮沒有。”況子吐出一口纏綿的煙圈,將手中一沓泛黃的紙遞給我。
(二)
仔細想來,那個十八歲的夜晚,離現(xiàn)在已有十年。都說這十年是最好的時候,年輕人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我舉著T大的錄取通知書,騎著單車沖出東坪縣城,我還沒明白孔老夫子這一套純屬扯淡。后來我恍然發(fā)覺,那時候堅信不疑的事,與現(xiàn)在全都驚人地相反。我從沒以為我會一直記得況子,沒以為他給我的那幾張破紙還留著,就像沒以為自己會回到這個當初拼了命也想離開的地方,結婚生子。十年,我忘了高中時追過的姑娘到底是長發(fā)還是短發(fā),忘了父親喝醉時甩在我臉上的巴掌是怎樣刻骨銘心的疼痛,忘了當初離開東坪時信口說著的那些豪情萬丈的鬼話。但是我記得況子給我講的、他叔叔“安勇”的故事。奇怪吧,我這么個從小到大按部就班的好學生,怎么會對這么古怪又離奇的故事感興趣,著魔似的,魂牽夢繞這么多年。
“他有個表妹,叫安妮。他倆從小就好,但近親結婚違法,你造吧。”況子吐字不清,口頭禪“你知道吧”聽起來像“你造吧”。我心里發(fā)笑,他這個人就是這樣,拽一點生澀的臺灣腔,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只是東坪縣城一個最不起眼的小混混。我接過他手里七零八落的紙張,目光所至,滿是潑潑灑灑的鋼筆字,隨意寫就,但蒼勁有力。夜涼如水,況子額上留得很長的頭發(fā)被風刮到腦后,剩下這張記憶中永不褪色的面孔。香煙嗆進鼻腔,濃烈而清冽。
“這都是你叔叔寫的?”
“嗯。”
(三)
2000.3.30
小安病了。兩歲的孩子,燒得臉通紅,手一摸都燙人。開始還哭,后來連哭的力氣也沒有,蜷縮在被子里睡著了。我給她吃了退燒藥,在臺燈下看著她很長很長的眼睫毛。有那么一會兒,我覺得安妮就在旁邊,小安要是我和安妮的孩子,就好了。
退燒藥起作用了,小安額頭上起了大滴汗珠,背上更多,被褥洇濕了一大片。我終于松了口氣,出了汗就降溫了,她能舒服一些,我想。我去壁櫥里拿新被褥,秀珠正酣睡,她都不知道小安身體不舒服。她跟她那個賣金銀首飾的老爹一樣,除了打算盤什么都不會。潮州是個好地方,但是人心冷漠。
半個月前,那個東北來的家伙把五百條皮褲的錢付清了,還是北方人講義氣,說什么是什么。其實錢不是問題,兩年以前我就已經(jīng)準備好去巴黎的路費,還想著雇個翻譯,到處打聽打聽。巴黎一共能有多少中國留學生?安妮不難找,肯定不難。
但是現(xiàn)在都沒用了,因為有了小安。秀珠本來不想這么快要孩子,潮州人沒有北方那樣“多子多福”的觀念。我更不想,我準備動身去巴黎。那時候我覺得已經(jīng)很接近了,就像安妮就在國際機場等我一樣。但是一下子沒用了,小安來了。
秀珠在店里忙,連跟了她爹一輩子的那個管家都不放心。她說不行就打掉,我說別,是條命啊。
我不后悔生了小安,可我覺得命運在捉弄我。從十八歲到二十八歲,這十年就像是一個個應接不暇的錯誤。千璽年,說什么世紀之交、時來運轉,這不扯淡嗎?今天和明天之間,沒有任何區(qū)別。
有時候我想,人也不能活得太悲觀了。就算有了小安,也不要緊。不過就是再晚個三五年,我還可以帶著小安一起去巴黎。安妮會喜歡她的,我們可以一起坐下來,好好聊一聊,關于未來啊、教育啊,什么的。就算三五年還是去不了,那再等十年可以了吧?十年,如果你一直想做一件事,怎么會做不到呢?巴黎又不是火星,還能一輩子到不了不成?等到小安長成了大姑娘,再去也不遲。
我一開始就不該來潮州的。
去巴黎吧,一切就都會好起來。
(四)
“他本來跟安妮好,但是安妮去巴黎了。他去了潮州,批發(fā)褲子。娶了個叫秀珠的女人,生了小安。是這意思吧?”我翻過一頁,饒有趣味地抬頭看況子。他把細長的身子探出窗外,吐出一口煙,不耐煩似的:“往下看行。”
“別吸了,進去說。陽臺這么黑,字兒又小,眼都瞎了。”我拍拍況子的后背,這小子真他媽瘦啊,肩胛骨突著,咯得我手疼。
“不想看算了,耽誤你考清華。”況子瞇縫著眼,舌頭抵著上膛,發(fā)出“嘎嘎”的怪聲。我笑,我倆就是這樣,一個奮發(fā)向上,一個吊兒郎當。外人看來,從頭到腳沒一點相似之處,卻擱一塊兒廝混了三年。
況子這人了解了以后其實挺有意思的,他知道很多別人打死也不知道的事,比方說他這個什么安勇叔叔。我沒跟他說過,我從來沒像別人說的那樣“看不起”他,打心眼里沒有。是他自己,心情不好就發(fā)飆,拍個圖片一排喝空了的酒瓶子。電話里罵,說什么沒人管他,哪個妹妹又對不住他了。當年他說這些我覺著很笑人,他分明很享受這種狀態(tài),港臺片里的古惑仔不是潮流就是偶像。如今十年過去,我不知為何開始覺得,當他說自己很難過的時候,也可能是真的不好過。
“別鬧,還真挺有意思。你講講。”我踮腳進屋,把床上的臺燈提進來。
(五)
1998.5.28
1992年夏天吧,大概是,最后一回見安妮。當時我已經(jīng)在部隊待了一年,管吃管住還發(fā)工資,回家都是大包小包地帶。安妮比我小一歲,剛高考完,在家等成績。我衷心地盼著她考好,別來當女兵,訓練苦啊。我還記著當時坐的綠皮火車是T字打頭的,說是條件好,死貴。上車以后才知道被坑了,悶罐一樣的車廂里人擠人,前面一大隊赤膊的農(nóng)民工大聲嚷嚷著什么。沒有風,汗珠子從臉上一串串地淌,紙都擦不跌。我忍不住高聲問乘務員:“這破車咋這么貴啊?”那女的瞥我一眼:“空調(diào)車。”“那咋這么熱啊?”“還沒安呢。”
我剛想罵,忽然被剛上來的一對母女擋住了視線。那女孩兒也就十七八歲,一手提一個大包袱,臉上掛著汗珠,白嫩水靈。我不由得笑起來,她長得挺俊俏,但跟安妮比,還差得遠。安妮現(xiàn)在干啥哩?她知道我回來,燒飯沒有?那些年我爹在海上當漁民,不著家。娘開門市部,忙得自己都吃不上一頓熱乎飯。我天天往三姨家跑,就是她蒸的那些饃酥肉香的花卷子把我喂大的。三姨很稀罕男孩,但是懷不上,年過四十只有安妮一個姑娘。我娘常開玩笑說,把小勇送給你家當兒子,安妮換給俺。三姨光笑,說你可別反悔。后來懂事了我才知道,三姨那時對我有多好。上初中的半大小子,頓頓來家吃,任誰不煩?三姨卻像是比我娘還疼我,可勁兒往我碗里盛肉,還給我洗衣裳,干凈、軟乎。
那時候小啊,有的是勁,三姨家的體力活都是我干的。三姨說:“安妮沒個兄弟姊妹,孤單得很。你就把她當親妹妹,照應著點。”
是啊,她是我妹妹啊。我陪她玩布娃娃,給她擦眼淚,在三姨發(fā)火的時候拉著她往我家跑。替她背鍋,逗她笑,一起趴在老李家后院偷葡萄被逮住的時候說是我的主意。我陪她上學放學,給她講題,逮住那個給她遞情書的小子,一拳揍得他鼻子冒血。從小到大,我無數(shù)次提醒自己,要好好保護安妮,因為她是我妹妹啊。
她也只是我妹妹啊。
(六)
2003.1.06
部隊四年,潮州八年。十多年下來,彷徨無措有時,左右逢源有時,但我從未在任何場合、對任何人提起過安妮。侃大山的時候沒有,醉得不省人事的時候沒有,跟秀珠剛開始還能聊到一塊的時候也沒有。潮州人會做生意,就在于明白這個理兒。嘴上說的和心里想的,不一定是一回事。
安妮走后,我再沒回過家鄉(xiāng)。回去干啥呢?難受。我跟我爹說,娘反正沒了,來潮州跟我住唄,好吃好喝伺候您。我爹腰雖然弓了,口氣硬得很,說打死不跟那個南蠻子媳婦一塊兒過,瞧不上。在海上打了一輩子魚,老了反倒戀家。也不知道當初是誰雄才大略,可勁兒勸我下廣東。
“時代變了,勇。當兵有啥好?早不時興了。你五叔家那一對小子,沒上幾天學,跟著兩個南方來拉貨的到處跑,不知倒騰啥,沒兩年就發(fā)了。”我剛退伍那會兒,恰逢禁漁期。我爹一到晚上搬個馬扎坐在院子里,嗓子眼兒咳咳咔咔,張三李四咋著咋著。我心想,人高馬大的小伙子,又不憨不傻,咋就干不了?去。
我娘當時就不愿意,拼死拼活地反對。我離家的前一晚,我娘攥著我的手,哭得眼都腫了。說我爹凈看見人家發(fā)財,不曉得人家受罪。就算掙幾個錢就活得舒坦了?賠了咋辦。還有,千萬別跟那些南蠻子走得太近,尖嘴猴腮、鬼精鬼精的,坑得你找不著北。
我當時心里還笑,我娘一直也算是個識大體的人,怎么會對我南下潮州這件事這么抵觸。如今再回想她那晚說過的話,竟句句應驗。又想她年輕時操勞過度,體弱多病,離世前一刻還在牽掛著這個遠在潮州的兒子,不由心如刀絞。
我真不該來潮州的。
去巴黎吧,安妮在等我。
(七)
“不是,瘋了吧這人。安妮就算還在巴黎,也早就結婚生子了,怎么可能在等他?”我翻看著這些泛黃發(fā)皺的紙張,想要再尋出點蛛絲馬跡。“這日記殘缺不全,中間甚至隔了有七年。而且這只寫了潮州,后來呢?巴黎才是重頭戲。你還有沒有?”
況子抽一口煙,定睛看我,語氣半死不活:“沒了。就這些。說了這事兒很邪乎,當真啊?”我笑了,拍拍他陡峭的肩峰,說話慢下來:“不是那意思。就是單純好奇,這個人最后怎么樣了。很明顯,他腦子有病,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找不利索。”
況子扭過頭,將煙頭在窗臺上捻滅。“咋著有病?”
“二三十的人,天天想著上法國找個女的,魂不守舍想了十年。這不是有病是什么?”
他垂下腦袋,很久沒再說話。
“睡吧,明天還得上課。”我熄滅了臺燈,剛想回屋,卻聽見他撕紙的聲音。
“干嗎!你不要我要。”我猛地拽住安況的手臂,搶過已被他撕裂一半的紙張。
“不是說腦子有病么?”他沒好氣地吼。
“那也不能撕啊!不管怎么說,這是你叔叔很珍貴的東西。”我使勁將揉皺的紙張展平,拎回床上,在枕頭底下壓好。“先放我這兒,畢業(yè)的時候還你,省得你哪天喝醉了又給撕了。”我在燈下早已看得眼疼,倒頭便睡。況子依然站在陽臺,月光將他清瘦的背影斜斜拉伸。我不知道他又站了多久,只聽到一聲輕微的“謝謝”。
(八)
2003.5.30
吵架,天天吵架。祖宗八輩兒的罵,然后就是摔東西。秀珠跟她老爹一個模子刻出來,平時慢聲細氣、眼珠子溜兒轉,雞毛撣子的小事實際都給你攢著,惹惱了就罵不絕口。也怨我,一點就著。都不敢想,那時候在部隊,戰(zhàn)友們都愿意和我拉呱,山東人就是厚道,他們說。可是來了潮州,一切就都變了。做生意的,厚道掙誰的錢?
散了吧!汕頭裁縫、大連批發(fā)商,從南到北沒一個好人。上個月我瞅準的那個卡其色,在隔壁店里賣成了“紅門”,看著都眼饞。當時差點就拿下來了,干這行許多年,眼光總還有。結果秀珠嫌貴,怕虧本兒。現(xiàn)在好,悔斷了腸子,錢還是進人家腰包。
能不怨她嗎?就會瞎叫喚,沒一個大心眼兒。但我不當家,她老爹是大拿。東南沿海這一片,但凡做服裝的,沒一個不認識老明。我剛從家鄉(xiāng)出來的時候,血氣方剛一身闖勁,碰釘子、吃虧。跟秀珠結婚以后,這些破事兒都沒了。在家坐著、數(shù)錢。
潮州擁有一切,又什么都沒有。
(九)
我從沒想過自己會回東坪。
本科畢業(yè),讀研,進了家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拼死拼活。凌晨兩點,特濃咖啡喝到反胃。有天我媽來電話,說今天老糊涂了,以為我還在家,包了我愛吃的花邊餃子。我擠在人潮洶涌的地鐵中,如鯁在喉。
當初騎著單車沖出東坪縣城的小男孩,不知何時起,再沒搖旗吶喊的熱情。
決定回家鄉(xiāng)考公務員的那天晚上,我在狹窄老舊的出租屋內(nèi)收拾行李。逼仄的空間本就擁堵,又堆滿凌亂不堪的雜物,心煩意亂。掀起堆在角落的舊被單,一時間灰塵嗆鼻,我才發(fā)覺這個屋里除了那個常在手邊咖啡杯,沒有任何一樣東西得到過清潔。從我搬進來的第一天,它們就靜靜地待在那里。靜默、蒙塵、生根、發(fā)芽。無人記起、無人挪動。
這屋子是時候有個女人了,我想。
被單底下有幾本小說,舊得起了毛邊兒,同樣一層灰。藍色封皮的一本,王小波的,里頭有張照片,露出一半的人像。大紅T恤、牛仔褲、黝黑的皮膚。手插在兜里,笑得燦然。
那是最年輕的況子。
那是我們的黃金時代。
(十)
2010.4.17
三姨葬禮,大人小孩站一屋,臉孔陌生。除了當年做鄰居的友慶叔,沒一個人和我搭腔。
“回來了,勇?”
“替我爹娘,來賠個不是。”我看著靈堂上被花圈擁簇的黑白相片,想到那些年吃過的饃酥肉香的花卷子,眼淚止不住地冒。我去潮州沒兩年,我娘和三姨因為分房子鬧惱了,兩家再不來往。忘了是哪年過年,我?guī)阒榛丶遥胫粔K兒看看三姨。我娘擋在門口,說我要敢去,她就敢死。
我問友慶叔,安妮去了法國以后,回來過沒。他說沒見,就是你三姨兩口子,去看過兩趟。
“那丫頭從小就跟你三姨不親,看不出來?她是抱來的,性子怯,就跟你能玩到一塊兒。這么些年,我一直不明白,你為啥上廣東了,沒和她一起去那什么法國。”
我問我爹,知道這事兒不?他說知道啊,街坊四鄰哪有不知道的。以后別再提他們家,堵得慌。
原來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我不知道。
(十一)
高考放榜,我考上T大,一下成了縣里的紅人。我爸擺了二十大桌,喝得眉開眼笑,說兒子比老子強,這回可算是光宗耀祖。我心情大好,哼著小曲兒去況子家找他,心想今兒個得徹底跟他去酒吧浪一回。結果他家大門鎖著,有只野貓趴在草窩里,發(fā)出咕嚕咕嚕的聲音。第二天再去,他母親開的門,朱唇粉面,有幾分姿色。屋子里煙霧繚繞,赤膊的男人圍桌而坐,彌漫著打麻將的吆喝聲。女人說,況子沒考上大學,去南方打工了。
我猛然發(fā)現(xiàn),高中時勾肩搭背玩兒了三年的人,竟連個電話號碼都沒留下。
從此以后況子消失了。沒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沒人關心。
可是他那晚給我的幾頁日記,依然壓在我的枕頭底下。平平整整,沒有一絲皺褶。
(十二)
2010.6.01
這些年掙下的錢,我單獨存在一張卡里,七位數(shù)。姓劉的翻譯今天到了,一起吃了飯。這小伙子很機靈,巴黎留學回來的,法語說得溜。
潮州的最后一夜,悶熱欲雨。
巴黎很遠,也很近。
(十三)
再看到?jīng)r子叔叔的日記,我已在縣交通局工作了兩年。娶了條件相似的明慧為妻,有一個可愛的女兒。大年初一,帶著妻女回父母家。來了許多親戚,一屋子吵吵嚷嚷,熱鬧得很。母親照例包了花邊餃子,小時候的味道,一點沒變。父親喝得滿臉通紅,興致勃勃地總結往事,說咱們家?guī)讉€后生都長大了,成家立業(yè)。你瞧老五家剛子,別看上學不中用,如今日子過得最紅火。我們家阿亮,當個公家人,雖說不算有大出息,也還湊合。
一個遠房的堂兄起身給我敬酒,神情激動:“你就是阿亮啊?早就聽說二叔家出了個高才生。你咋回東坪了呢?也不再闖闖。咱這地方小,真是屈才。”
我尷尬地笑笑,碰杯喝酒,突然想到前幾天在書柜里找到的,安勇的日記。那些隨意寫就的鋼筆字,我一氣讀完,好似回到那個浸透香煙的夜里,做一場十年一覺的美夢。況子的臉、況子的脊背、況子點煙的神態(tài),還有他那不可名狀的憤怒和沉默,就全都想起來。
況子說他就是個廢人,我說別呀,人要有點兒追求。比方說你那個安勇叔叔,哪怕天天想著去巴黎,也算有個盼頭不是。
安勇說他不喜歡潮州,打死都不喜歡。至于批了幾條皮褲、掙多少錢,其實都無所謂的。潮州的空氣令人絕望,絕望到窒息。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去巴黎找安妮,又有什么不好的呢?這些無聊的看客,憑什么說人家不對?我當時真傻啊,說安勇“腦子有病”。十年下來,發(fā)現(xiàn)是自己無知。
我不也不喜歡東坪。
(十四)
我再拿著日記去安況家的時候,還是他母親開的門。她老了,眼角綻開皺紋,蠟黃的臉上溝壑縱橫,再無年輕時的姿容。我說我是安況的高中同學,這是他叔叔的日記,當時放在我這兒,忘了給他。
女人很震驚,連忙請我進屋。看完幾頁,她面色凝重,說我肯定是搞錯了。這些東西要么是哪本書上的,要么是安況寫的小說,反正不是真的。她說安況沒出息,念書念不好,凈整些沒用的。十八歲離家以后,再也沒來信,要么出事兒了,要么是不想見她。
“我這樣的人,哪能培養(yǎng)出你一樣的好學生。不怨況子。”女人說。
我鼻子一酸,把我的電話寫在紙上,告訴她以后有什么需要幫忙的,可以聯(lián)系我。
臨走之前,女人盯著我看了一會兒,說感覺面熟,是不是在哪里見過。
“是啊,阿姨。我以前來過的,高考完那會兒,來找況子。”我聲音哽咽,匆忙下樓。我怕她看見我臉上的淚,也會回頭難過好久。
我們已然各自過了十年。
(十五)
后來我想,況子母親說的,也不一定對。
她都沒提到?jīng)r子的父親,又怎么證明,他有沒有叔叔呢?還是說,其實她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不愿對我這個外人講。不論怎樣,有關安勇叔叔的故事,到這兒就算是沒了下文。我的日子一切照常,今天和明天之間,沒有任何差別。只是我開始喜歡上安勇的日記,一遍遍看,越看越有味兒。
如果這是十八歲的況子寫出來的,他還真算是個人物。不過不像啊,他當年就燙個頭發(fā)泡個妞,哪還能搞得了文學。有天夜里,我站在陽臺上抽煙,看那濃白的煙霧一汩汩融進黑夜,被瞬間吞噬,突然覺著,安勇的故事,我也能繼續(xù)往下寫。
那個姓劉的翻譯,是個騙子,卷了他所有的錢,跑了。他就一個人晃悠在巴黎的大街上,逮個人就問,見著安妮了沒?見著安妮了沒?人家罵他一句,他不理會,繼續(xù)問下一個。他想啊,巴黎一共能有多少中國留學生?安妮不難找,肯定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