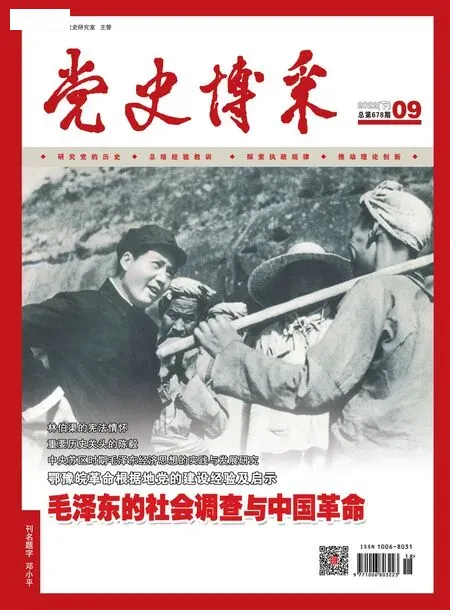抗戰時期延安日本工農學校考察研究
羅 亞
中國共產黨從井岡山時期就把優待俘虜作為戰爭的基本準則之一,并進一步指出,給予戰俘物質上的優待、人格上的平等和對靈魂的醫治。①抗戰時期,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為著更好地推進優待俘虜這一政策的實施,1941 年5 月15 日,以教育改造日本戰俘為目的的新型學校——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正式成立。
一、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成立
抗戰時期,黨的軍隊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是瓦解敵軍,然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如何對待越來越多的日本戰俘。使其接受教育改造進而正確認識到戰爭的本質,這將為實現瓦解敵軍發揮巨大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優待俘虜的政策,誕生于井岡山時期。1928年2 月18 日,工農革命軍攻克寧岡縣縣城——新城,俘敵200 余人。在押送俘虜的路上,毛澤東發現了打罵俘虜的現象,當天晚上,毛澤東就召集其他領導人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對待俘虜的問題。2 月19 日,工農革命軍集合在攀龍書院門口的坪地里,召開軍人大會。毛澤東宣布,“今后,我們對俘虜的政策是:第一,不打罵俘虜,不搜腰包;第二,受傷者給予治療;第三,愿留者留,愿走的發給路費。”②共產黨在井岡山時期就有優待俘虜的思想覺悟,這為日后宣傳自身、擴充軍隊、瓦解敵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隨著戰局的擴大和戰線延長的消耗,日軍戰斗力逐漸減退,與此同時,被俘的日軍也越來越多。1940 年3 月,在中國共產黨的盛情邀請下,日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野坂參三(岡野進)秘密抵達延安,參與到中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中來。野坂參三觀察到被送往延安的日本戰俘大都有強烈的反抗情緒,同年10 月,他便提出在延安創辦一所特殊學校——以改造日軍戰俘,使其能夠客觀公正地看待中日兩國人民以及這場侵略戰爭,這一提議得到中共中央的有力支持。不久后,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校址選在延安寶塔山下的原東北地區培訓干部學校處,由八路軍總政治部和“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共同籌備學校的開學等事宜。③
1941 年5 月15 日,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在延安文化溝的八路軍大禮堂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為大會題詞:“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的帝國主義和中國的民族敗類。”④深刻啟示了在場的日軍戰俘,使其認識到日本人民是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其野蠻侵略所操縱的棋子。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校長是日本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野坂參三,為了保密,對外宣稱校長是王學文,副校長是趙安博。學校的辦學目的是“對日本士兵進行政治教育”;辦學宗旨是為宣揚中國共產黨俘虜政策之精神;具體任務是培養協助八路軍做日本軍隊的政治工作的人才;校訓是“和平、正義、友愛、勞動、實踐”。
二、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改造戰俘的方式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對學員的教育上。因為教育對象的特殊性,教育已經不是指傳統意義上的課堂教育,而是指在政治中、生活中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對戰俘的改造和爭取。⑤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運轉模式充分體現了共產黨教育改造戰俘政策的正確性。
學校的辦學進程分為三階段。剛到延安為第一階段,用約一個月的時間審查學員是否具有入學資格;之后開啟以預科生為教育對象的課程,時間為兩個月;最后進行本科生教育,時間為10 個月。入學原則為學員自覺自愿,并無半點強迫。⑥在課程設置方面,按文化程度和學歷的不同將學員分為A、B、C三個年級,如此便于對不同學員進行有針對性的授課。A 年級由剛被俘虜的官兵組成,他們中多數“除了知道自己是俘虜外,關于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不但什么都不知道,而且還抱有偏見和憎惡的心理”⑦,甚至還有些日本士兵有自殺的行為。究其原因,可歸結為以下三點:第一,認為如果投降做俘虜會給家庭和國家帶來恥辱;第二,對中國共產黨的俘虜政策不了解,以為即便投降做俘虜也難逃被殺的命運;第三,即便日后能回到日軍處,仍舊會因其俘虜身份而被無情處死。針對以上種種,把改造其思想作為當務之急。首先讓其學習《政治常識》《社會發展史》等課程,講授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與實踐、中日戰爭爆發的真實原因以及在國際上對這場戰爭的認知,使其逐漸轉變心中固有觀念,改過自新,有人再次返回前線時,已由戰爭分子轉變為反法西斯戰士。B 年級學習《政治學》《經濟學》等課程,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王學文講授,王學文曾在日本帝都大學留學,對日本的國情和民生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能夠更好地實現因材施教。C 年級的學員有著較高的學術理論水平和政治覺悟,由共產國際代表兼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校長野坂參三講授蘇聯共產黨史。⑧《日本問題》《時事政治》是三個年級學員的公共課程。通過學習,使日本戰俘“懂得全世界無產階級是兄弟、中日兩國人民是兄弟,懂得什么叫國際主義精神,也才真正懂得應該怎樣去做人……”⑨政治覺悟高的學員鼓勵帶動政治覺悟低的學員,“語言與心理的相通,確保了新入校的戰俘在短時間內思想上就發生明顯轉變,區分出正義與邪惡,找到前進的航向”。⑩這些戰俘表示:“努力學好革命理論,畢業后竭盡全力為日本帝國主義早日停止侵略戰爭、為了日本的和平以及日本建立民主主義的人民政府而奮斗,我們也一定和八路軍官兵一起去同我們共同的敵人戰斗到底!”?實踐證明,大多數學員在戰爭后期以及戰后中日關系的發展中履行了承諾。
對于一些無論用何種方法都無法消除其心中根深蒂固的軍國主義思想的學員,首先采取說服教育的方法,如若無效,則召開全員大會,對錯誤行為進行批判,從而引導學員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通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得大多數學員漸漸認識到自己在思想、學習、生活和工作中的問題,從而洗心革面、改過自新。學校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手段,還粉碎了一系列特務行動。日軍為了打探情報以及暗殺共產黨領導人,派出一批訓練有素的日本特務以假投誠的方式潛入到學校內部。共產黨發現了敵人這一陰謀,便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中開展“坦白運動”檢舉揭發可疑分子,共產黨對這些特務并沒有一網打盡,反而是采取了寬大政策,“當他們受到學校的思想教育,特別是整風運動的影響,能重新回到勞動人民的立場,承認自己是特務,就既往不咎,并且作為同伴歡迎他們”。?對于那些軍國主義思想極其頑固的特務分子,則將他們隔離到工農學校二部,防止他們影響到其他學員,直到他們改過自新,再轉到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據統計,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辦學期間,有一半的特務已經完全擺脫了軍國主義思想的禁錮,進而轉向了共產主義。
隨著各地日軍戰俘的不斷增多,延安日本工農學校開始在其他抗日根據地設立分校。1943 年7 月7 日,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晉西北分校成立;1944 年11 月2 日,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山東分校成立。分校與總校有著相同的任務,都致力于將日本戰俘改造成為反戰勇士。?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不僅在教學方面因材施教,對學員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也給予了充分的優待。當時物資供應相當緊張,但學員的食宿標準均按照八路軍連級干部的標準發放,且全部免費提供。?1941 年,因日軍對陜甘寧邊區的“掃蕩”、國民黨反動派的經濟封鎖和黨員隊伍的不斷壯大,邊區一度面臨著相當嚴重的經濟、物資短缺狀況,在如此艱難的境遇下,邊區政府仍然盡可能地滿足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一切物資需求。為了克服困難,邊區軍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也紛紛自覺加入到大生產運動中來,學員的主要生產勞動包括開墾荒地、種植糧食、建造校舍等。?在全體軍民的共同努力下,邊區生活狀況逐漸好轉。為了豐富學員的業余生活,學校每月還會舉行一次娛樂晚會,節目包括合唱、日本舞蹈、戲劇和朗誦等。1944 年中秋節晚會上,學員們表演了一系列反戰戲劇,政治上具有進步性,內容上突出新穎性。?
在政治參與中,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一項基本政治權利。1941 年陜甘寧邊區舉行第二次普選,要求從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敵軍工作干部學校等學校推選出三名候選人,并從中選取一人作為邊區參議會參議員。位列第二名的是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森健,按照邊區“三三制”原則,最后決定推選森健為邊區參議員。
這些活動不僅激發了學員們對勞動的熱情和興趣,而且豐富了他們的精神生活,推進了其思想改造工作。特別是大生產運動,既緩解了生活物資短缺的問題,又重塑了他們對共產黨軍隊的觀念,也增進了他們同八路軍的感情。
三、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意義
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教育改造下,學員們的思想得到轉化,畢業后紛紛投入到反戰宣傳和瓦解日軍的工作中。這對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來說,既培養了一批重要的反戰力量,又擴大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進而也為戰后日本本民族的解放事業培養了一批有用之才。
(一)為國際上處理戰俘問題提供了經驗
1944 年,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時,約翰·艾默生對研究當時中國的兩大黨派——共產黨和國民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分別在延安和重慶考察了數月,重點參觀了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和重慶的日本俘虜收容所,對比之下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艾默生感慨道:收容所的戰俘們拖著腳鐐,情緒低落,精神麻木,這與延安日本工農學校那些快快活活的學員,“真是鮮明的對照”。?
當時正在與日本交戰的美國因不知如何安置日本戰俘而傷透了腦筋,美國觀察組從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對待戰俘的問題上學習到的經驗為其處理戰俘問題提供了一定的借鑒。
(二)為抗戰培養了反戰力量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是人類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學校,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創舉和光輝實踐,它所教育培養出的日本學員有的留校從事學校的教育和管理工作;有的直接參加了八路軍,奔赴華北、華中前線;有的忙于反戰的籌建、組織和領導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延安日報》報道了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對戰俘的教育改造情況,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大部分學員經過生產勞動和思想改造后,逐漸認識到了這場戰爭的本質和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所犯下的罪行,并希望在戰后能夠回到日本幫助日本人民重建一個民主、和諧的國家。毋庸置疑,八路軍對日軍戰俘的改造很成功。?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 月初,野坂參三攜延安日本工農學校200多名學生從延安啟程回到日本,參與到戰后日本的民主建設和為早日恢復中日友好關系的努力中。
結語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從1941 年5 月正式開學到1945 年8月日本投降后停辦,4 年多的時間共教育改造了900 多名日軍士兵和下級軍官。該學校既教育改造了被俘的日本士兵,孤立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和好戰分子,溝通了中日兩國人民的感情,又在世界戰爭史上樹立起了和平、友愛的旗幟,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注釋]
①張可榮.延安日本工農學校述略[J].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01):91-93.
②劉 曉農.我軍優待俘虜政策的誕生[J].黨史文匯,2004(07):24-25.
③韓偉.抗戰時期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創建及其歷史貢獻[J].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05):15-19.
④王向立.延安日本工農學校[J].八路軍軍政雜志,1941,第3 卷(06):81.
⑤⑧杜維澤,張小兵.和諧之音:抗戰時期的延安日本工農學校[J].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09(02):86.
⑥王仕琪.日軍戰俘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改造[J].檔案天地,2011(02):33.
⑦野坂參三選集·戰時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08.
⑨?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內日本兵[M].趙安傅,吳從勇 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34-47.
⑩李治國.精誠所至 金石為開——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對戰俘的教育改造[J].政工學刊,2005(12):19.
?野坂參三.亡命十六年[M].北京:中國建設印務股份有限公司,1949:45.
?開展全體盟員的防奸斗爭 粉碎日本軍部的特務政策[N].解放日報,1944-2-18.
?謝慧君,耿妍.抗戰時期的日本工農學校[J].蘭臺世界,2010(21):32.
?趙安博.從戰俘到反侵略戰士——憶延安日本工農學校[J].科技文萃,1995(10):58.
?曲利杰.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日軍戰俘的思想改造——基于日本工農學校的考察[J].黨的文獻,2021(03):107.
?小林清.在華日人反戰組織史話[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57.
?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軍內日本兵[M].趙安傅,吳從勇 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84.
?共產黨在這里把“鬼子”感化成“八路”——探訪抗戰時期獨一無二的延安日本工農學校[N].延安日報,2021-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