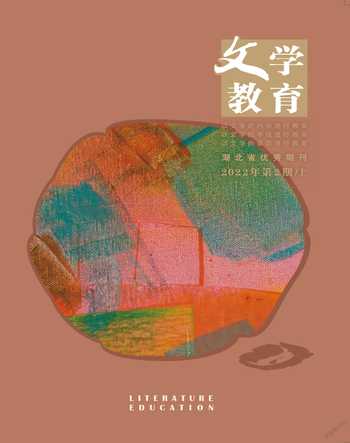“我自信有一首詩一直在我身旁”
謝湘南是70后代表詩人之一。因其獨特的詩歌書寫,在詩壇備受關注。謝湘南的詩歌屬于“民間的立場”,因為他來自民間,并且時刻在關注著“民間”,以其詩集《零點搬運工》《過敏史》《謝湘南詩選》為標志,這種由自身而及于對民間的關注,非常值得敬佩。
自“第三代詩”以來,在詩歌中反省自我與詩歌的關系、傳達個人獨特經驗成為寫詩的一大潮流。從當代詩的發展歷史看,這是詩歌寫作的一種內化趨勢。強調主體的個人化經驗,其實即是強調詩歌從“觀”與“群”的功能向“興”與“怨”的功能轉換,突出一種微觀的寫作理路,強化了個體私密經驗在詩歌生成中的重要作用。為此,面對這樣的理路變化,思考個人與詩歌的關系乃成為一種必須。謝湘南早年曾有幾首詩體現出他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如其《自嘲詩》《需要或不需要湘南的N個理由》《請多一些謝湘南這樣的詩人》等。它們都是詩人從責任感的角度出發,試圖呼喚出底層中那些有責任感的人,以為身處民間的底層人代言。《讓一首詩參與我的生活,坐在黑皮沙發上,看我憔悴》一首,首先談論到詩與詩人生活的關系,很難得的是詩人在詩中表現出這樣的自信:“我自信有一首詩/一直在我身旁/多少年來,它不說一句話,不離我/半步。它就這樣望我”。然后詩人指出,是這種自信祛除了生活中的苦難,并且自信最終會“釋放出——自個的牢籠”。
謝湘南很早來到城市打工,對于城市的態度,他是矛盾的。一方面對于繁華的現代文明帶有認可、崇拜和欽羨之情,另一方面也對城市中的各種現代病癥進行著有力的批判和揭橥。在詩歌中,謝湘南主要是從后者著手的。首先,對于這些城市的現代病癥,他有著深切的體驗,比如從對于“灰塵”(《與灰塵作戰》)、居室內甲醛(《甲醛》)和對于“酸菜小筍肉末”(《酸菜小筍肉末》)的戲劇化描述、從家中的一次“裝修”(《撕開》)入手,為我們揭示出城市生活中最基礎的住和食的重大問題;同時,他從自身的工作經歷出發,批判了現代工業文明中城市對自然形成的沖擊,以及機器對人的異化和人對人的壓迫(《前沿軼事》);從對日常生活的體驗中,他還細膩而真切地傳達出不能融入城市的隔膜以及那種異鄉飄零的孤獨感,如《我喜歡夜晚恰如其分的黑》《這世上有許多我們猜不出的謎》以及《坐在九州大道邊上吃一個快餐》中所表達的。即使《流水默念著箴言》這樣有點搗虛的詩歌,也蘊藏著一些這樣的意識。
當然,詩人的視野不會只關注個體自我,他時時都在打量著現代城市的世俗百態和文明癥結。2010年他曾寫下《再現》一詩,不厭其煩地羅列出城市中那些小人物的生存狀態,表現出對他們的關注。在詩歌中,謝湘南關注“收廢品的人”(《地盤》),關注“葬在深圳的姑娘”(《葬在深圳的姑娘》),關注“開診所的人”的荒誕生存現狀(《德德診所》),關注在市委門前“散步 游戲 請愿 挑釁 示威 抗議”的人們(《在路上》),關注從“樣板房”里所呈現出的人生百態,并聯想到了“樣板房”與“墓穴”的內在邏輯關系(《樣板房》)。這是一種由此及彼、愛屋及烏的能力。謝湘南有他觀察世界的獨特視角,也有觀照世界、觀照小人物的良苦用心。很顯然,城市的現代文明具有雙重性、兩面性,然而就詩人的天職言,發掘、反省和批判是應有的責任。在《天坑》中詩人就理性地分析了城市中高樓與天坑的關系,“讓我們看到天堂與地獄的間距/多么小,多么微不足道”;當然,詩人有時候也會發出看似深刻而又深感無奈的生存性體悟,比如:“我看到的無非是孔子看到的/那些不動的事物每天都會變一點/那些流動的事物以不變的面目/在眼前流動”(《在16樓衛生間看廣深高速公路上的流逝》)。
謝湘南是一個有心的詩人。這從他由己及人對“民間”的關注即可以見出。盡管以詩歌書寫個人經驗是一個大勢所趨,是寫作的一個普遍潮流,然而由個體經驗進入對社會的思考卻是一個詩人成熟的標志。謝湘南是一個具有思考力的人。他1993年進入深圳打工并寫詩。個人的身份與社會地位,使得他在寫詩的過程中不得不思考一系列與人生有關的重大問題。生存的處境對于個體人生畢竟具有決定性的一面。2000年,謝湘南寫了一首名曰《琢磨這件事》的詩,透露出他喜歡琢磨那些捉摸不透的事,這是他善于思考的“證據”。也許是出于個體身份自覺的緣故,他經常對一些社會性的問題給予關注,并進行深入的思考。這也是外界關注他的直接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趙目珍,青年詩人,批評家。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教育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