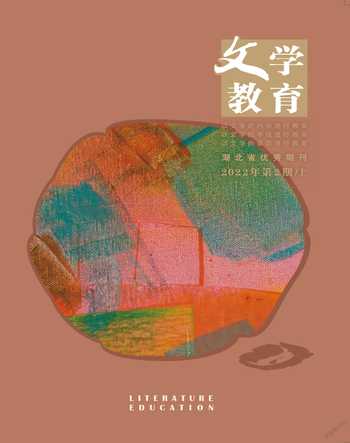認知暴力視角下《所羅門之歌》中的派拉特形象
林羽璇
內容摘要:托妮·莫里森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非裔女作家,其黑人女性作家的身份賦予她獨具匠心的寫作視角,她的作品也揭示出黑人女性真實的生存困境。自1997年出版以來,《所羅門之歌》就受到了眾多讀者的關注與好評。國內外學者對于《所羅門之歌》的文學研究主要集中于對主人公奶娃的解讀,而小說中的女性小人物,如奶娃的姑姑派拉特,則有待挖掘。本文基于后殖民主義理論,嘗試以斯皮瓦克的“認知暴力”概念分析派拉特的邊緣困境及其在困境中所患的“失語癥”,并在此基礎上解讀派拉特在困境中的反抗與其對文化身份的探尋。
關鍵詞:《所羅門之歌》 派拉特 認知暴力 邊緣困境 失語癥
《所羅門之歌》以黑人飛行的神話為基礎,講述了黑人的尋鄉之旅,展現了美國北方與南方的沖突,并批判了其背后的種族對立,是莫里森的代表作之一。后殖民理論對于《所羅門之歌》的解讀有著重要作用,而斯皮瓦克的“認知暴力”這一概念,對于小說人物的研究有著重要參考價值。斯皮瓦克曾在其著作《屬下能說話嗎》中將認知暴力定義為“把殖民者主體構成他者的計劃”(100)。由此,被殖民者被孤立于社會及政治權力之外,淪為了“屬下”。伴隨著權力的喪失,被殖民者的話語權被瓦解,屬下便不能“說話”了。
小說中對于派拉特的著筆不算多,但筆者認為她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富有魅力的,對自由與平等充滿激情與向往的女性角色。值得一提的是,派拉特的名字與英文單詞“飛行員”相似,且派拉特雖然一窮二白,但無論去哪兒都攜帶地理書,因此部分學者認為派拉特一生都在追尋自由的旅途中,是“黑人文明的代言人”(王守仁 84),同時也是主人公奶娃的尋鄉之旅中的“引路人”(Peach 68)。然而隨著對文本的深入探索,不難發現派拉特這一人物的悲劇性,其追求自由平等與保護黑人文化遺產的旅途與風雨兼程:她實質上被孤立于白人社會,黑人社區,甚至是戴德家族之外,因而是斯皮瓦克眼中游走在社會邊緣的“失語的屬下”。
本文擬借助后殖民主義理論中認知暴力這一概念,分析派拉特的邊緣處境,揭示派拉特在邊緣化的過程中出現的“失語癥”,并進一步解讀派拉特如何在被殖民主義,消費主義與男權中心主義所滲透的社會中,重塑自己的黑人文化身份,并重獲自主話語權。
一.孤立于中心之外——邊緣的飛行者
“斯皮瓦克的使用中,‘認知暴力’指帝國主義以科學、普遍真理和宗教救贖這樣的話語形式對殖民地文化進行排斥和重新塑造的行為”(李應志 60)。毫無疑問,這種形式的“軟暴力”(61)會導致被殖民者文化主體性的逐漸淪喪,進而造成被殖民者被排擠至文化中心之外的邊緣化處境。在《所羅門之歌》中,派拉特作為一名黑人女性,正反映了當時其所處階級的真實境況:在父權制與帝國主義“兩座大山”的排擠下夾縫生存,茍延殘喘。
小說中,派拉特是一位被賦予了神秘能力的傳奇人物。在派拉特落地前,她的母親已難產而死,然而,她掙脫了母親的襁褓,帶著她沒有肚臍的“光滑肚皮”由一個深淵爬向了另一個深淵。她神秘又恐怖的出生,預示了她與其他黑人的隔閡。在某種意義上肚臍象征著“重復性”(龔莉嵐 44),意味著一代代女性困于依附男性和繁衍生命這一循環的枷鎖之中,進而暗示了女性應當安守本分地生活在這的禁錮之下,服務于以男性為中心的家族與社會里。派拉特一出生就沒有臍帶,這樣神秘而明了的出場設定從一開始便寄寓了莫里森對她的厚望,希望她以反叛的血肉之軀去挑戰男權中心主義所制定的規則。事實證明,派拉特確實沒有讓她的締造者失望。不同于常人,派拉特的童年經歷了家破人亡,手足失散,這個本能在愛與關懷中無憂無慮成長的女孩一夜之間被迫淪為孤兒。然而,這個苦命的人并沒有向命運屈服,而是踏上了尋找家園與自我的航程。這一路顛沛流離,曲折離奇,派拉特使勁渾身解數,干了數不盡的臟活累活,只為了尋找自己的容身之處。但現實往往事與愿違,派拉特的勤勞,真誠,與熱情換來的是本族裔男人的側目與女人的碎語閑言:“那些男人叫她美人魚,女人們把她的腳印打掃干凈并且在她的門口懸上鏡子”(莫里森 153);她獨特的肚皮所象征的勇敢獨立與反叛反而使她和她可憐的女兒與外孫女被孤立于黑人族裔之外。
派拉特不僅擁有非同尋常的出生與人格,還踐行著自己獨具一格的生活方式。小說伊始,莫里森就對奶娃的父親麥肯·戴德的殘暴形象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畫。在莫里森筆下,麥肯是那個時代一名典型的戴著“白面具”的黑皮膚商人。他視金錢為一切行動的信條,而視自己同胞的性命如草菅;消費主義金錢至上的冷漠價值觀對麥肯精神的蠶食,使得他的良心與憐憫蕩然無存。麥肯儼然已將黑人文化中友愛互助的價值觀拋諸腦后,且對自己族裔所承受的痛苦視而不見。然而派拉特作為麥肯的親姐姐卻與其所秉持的冷血價值觀大相徑庭:她對西方文明以財富衡量成功的倡導嗤之以鼻;她與自己的女兒與外孫女在城市貧民窟里僅僅依靠自制酒水的生意與新鮮水果的采食維生;她所有行囊僅包括一袋尸骨,一本地理書,幾顆石頭,以及一個裝有自己名字的耳飾。這種至簡的生活方式背后,既體現了派拉特對于過往的密切聯絡,也是其對于塑造其人格的黑人文明之敬畏(Ahmad 66)。因此,盡管派拉特落戶于一個現代化白人至上的城市,但仍然拒絕由白人倡導的消費主義觀,拒絕購買工業化現代社會所謂的“必需品”(如燃氣,自來水),并引領著一種純粹又原始的,與現世格格不入的生活。
顯然,派拉特從骨子里就帶著的反叛及其獨具一格的生存方式注定使這名女勇士遭受世人的隔絕,且被迫承受黑人文化與白人文化的雙重排擠,在邊緣奄奄一息地飛行。
二.陷入在沉默之中——失語的飛行者
在被邊緣化并逐漸淪為“屬下”的過程中,被殖民者的語言系統也同時被摧毀。“在父權制與島國主義之間……婦女的形象消失了”,女性進而也陷入了失語的境地(斯皮瓦克 126)。這里所言的失語癥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失去了發音能力”的病理癥狀,“而是指他們不能用自己的方式進行思考和文化表達”,進而“喪失了自己的文化主體性……從而被迫處于依附狀態”(李應志 61)。小說中的女性人物亦是如此,她們難以從女性視角出發敘述自己的獨特經歷,更喪失了作為黑人族裔的文化主體性。
派拉特的童年恬靜而美好,她的父親老戴德用自己的真情實感緊緊維系著這個貧窮但有愛的三口之家,并經營著自己用汗水換來的富饒的“林肯天堂”。然而白人殖民者的貪婪覬覦終止了這個三口之家的豐收與天倫之樂,他們在“林肯天堂”這篇富饒的土地上暗殺了老戴德,讓小派拉特一夜之間從天堂墜入地獄,迫使這個年僅幾歲的孩子流離失所,開啟了尋找自己的漂泊之旅。然而,派拉特一生也沒能歌頌真實的自我:她錯聽了父親對她母親“興”(Sing)的呼喚,誤以為父親在鼓勵她歌唱,因而失去了母親的名字;她沒能理解“所羅門”(Soloman)的真正含義,誤將“所羅門”歌唱為“售糖人”(Sugarman),從而失去了家族的名字。“售糖人飛走了,售糖人走啦,售糖人掠過天空,售糖人回家嘍”(莫里森 50)。——她的歌聲清脆響亮,愉悅了他人,卻沒能歌頌最真實的自我與靈魂。殖民者不僅掠奪了派拉特一家的錢財,也剝奪了她作為一名女性真實敘述自身經歷的可能性。
在白人主導的主流話語中,“東方人是……被加以審視的”,因而“東方就與西方社會中的某些特殊因素(罪犯,瘋子,女人,窮人)聯系在一起”(薩義德263-264)。大多數黑人在失去話語權的社會中都難以反抗,甚至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自身被強加的惡人形象。從白人的視角與話語規則出發,派拉特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瘋女人”。童年恐怖的遭遇給予了派拉特異乎尋常的成熟,她繼承了“本該”屬于男性的自力更生的奮斗精神,依靠自己的勤懇勞作筑造了一個簡陋但幸福的家:“威士忌……成為派拉特穩定的謀生手段。這種技能給她時復一時、日復一日的自由”(莫里森 153);她用自己黑人女性獨特的愛與智慧哺育了女兒與外孫女;她貧窮但樂觀,盡管深陷帝國主義的囹圄,經歷了一世的苦難,但臨終前仍堅持黑人族裔所弘揚的博愛團結的價值觀:“我會愛他們大家的。要是我認識的人再多些,我也就可以愛得更多了”(莫里森 346);她以自己的身體力行揭開了女性獨有的“后人道主義”本色,“體現了令人難忘的本質和人性中的閃光點”(任冰 50),也打破了男權社會強行拷在女性身上的枷鎖。不幸的是,派拉特所擁有的勇敢、獨立的特性,冒犯了男權主義的規則,因而被自己的同胞宣判了女性不該犯的“原罪”。固執而勇敢的抗爭換來的是黑人族裔眾叛親離,派拉特在這樣的孤立無援的處境中失去了言說對黑人族裔之愛的能力。
無論是出于白人殖民者的迫害,還是由于黑人族裔的排擠,派拉特作為那個時代為數不多的獨立女性注定無法融入被帝國主義和男權主義教條滲透的社會。她無法言說,只能在時代的旋渦里陷入沉默,淪落成失語的飛行者。
三.風雨兼程——無畏的飛行者
事實上,沉默與失語作為小說中黑人女性的癥狀,并不意味著妥協或放棄,因為“屬下(在沉默中)能夠通過反抗主流話語的方式,實現自身的某種程度上的發展,從而構建屬于反帝者的光明前景”(Lawson 150)。莫里森筆下堅毅且樂觀的派拉特就是一位沉默的勇士。為了沖破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的雙重枷鎖,重獲話語權,派拉特終其一生都在追求獨立的人格,保護她的家人,并盡其所能繼承黑人文化中的仁義與大愛。
小說中,盡管派拉特失去了家園、自我身份、甚至是發聲的權利,但在尋找家園的旅途中,派拉特逐漸重塑了自身的話語體系,構建了其獨特且獨立的女性身份,是小說中邊緣女性人物的模范。值得一提的是,這位女勇士用于反抗不公的有力武器之一是其口中的歌謠。派拉特的歌聲清脆動人,像磁鐵般吸引著麥肯,讓其“感到白天的煩躁從身上消失了”(莫里森 29),并暫時抽離了現代物質世界的冷酷與疲憊;她的歌聲婉轉悠揚,使奶娃流連忘返,沉溺于她簡陋而充滿愛意的溫柔鄉;她的歌聲娓娓道來,在音符之間向麗巴和哈格爾傳遞著在窮苦中仍要努力勞作的價值觀。派拉特的歌聲激勵著自己與家人,婉轉地向族人訴說著自己重構女性話語體系的勇氣與決心。
此外,不同于狡詐且殘忍的兄弟麥肯,派拉特以女性特有的勇氣與愛為保護罩,在種種壓迫下不僅堅毅地守護著家人的安全,還捍衛著周圍女性發聲與抵抗強權的權利。在得知奶娃的母親露絲被厭棄時,派拉特借助藥物幫助露絲懷孕,并以此抵抗麥肯的欺凌。很多時候,迷藥都是男性用以迫害女性的毒藥,而派拉特以男性迫害女性的利器反撲男性,在女性深處弱勢地位的社會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彰顯了女性智慧,捍衛了女性權力。在麗巴被男友威脅時,作為母親的派拉特不顧力量的懸殊奮起反抗,擊退了施暴者,并奪回了麗巴作為女性的尊嚴與話語權。侵犯者胸前留下的血與傷是派拉特反抗男權的勛章,再現了派拉特在那個男女地位極度不公的年代,“以暴制暴”的壯舉。當哈格爾因奶娃的拋棄喪失理智與意志時,作為外祖母的派拉特想盡一切辦法幫助這位墜入深淵的女孩重拾對生活的希望與信心;而后哈格爾過世,派拉特又對奶娃暴力相向,大快人心。派拉特對于哈格爾的維護與安慰與對奶娃的咒罵與報復從某種程度上表現了派拉特對弱勢女性的同情與痛心,和對強者欺凌的不屑與憎惡,凸顯了派拉特捍衛女性主體地位的堅韌與無畏。
與此同時,堅毅獨立的派拉特拒絕淪為白人文明的囚徒,對捆綁了麥肯與奶娃的所謂“先進”的霸權式價值觀視如敝屣。麥肯與奶娃作為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在有形與無形之中都將自己的財富與地位建立在黑人同胞的痛苦之上,他們與本族裔的割離,最終也導致了自我的迷失。極具戲劇性的是,作為二者親眷的派拉特盡管活在社會底層,即使飽經滄桑與不公,仍將黑人文化中仁義、善良、與勇敢的價值觀視為自己的行事原則,將自己對于黑人文明的記憶、黑人族裔的歸屬、以及黑人身份的認同作為人生準則——派拉特在苦中作樂,與風雨作伴,用歌聲重塑了女性的話語,用智慧與勇氣維護了女性的尊嚴,用愛與善良守護了女性獨立的人格,是莫里森筆下無畏且偉大的飛行者。
本文基于后殖民主義視角,對《所羅門之歌》中派拉特的邊緣地位進行了分析。筆者認為奉行“金錢至上”的帝國主義文明與宣揚“女性依附于男性”父權主義價值觀是導致派拉特邊緣困境的罪魁禍首;困境里的派拉特無法真正謳歌自己的根與靈魂,也無法表達自己對黑人族裔的熱愛與歸屬,進而淪為了一個失語者;然而派拉特不甘于在邊緣無聲地飛行,并在其顛沛流離的人生之旅中以自己的歌聲為利器,以智慧為武器,以愛為力量反抗壓迫,重塑了女性話語,保護了女性尊嚴與人格,重構了獨立的黑人女性身份。正如小說中所言,作為祖先的所羅門飛越了山川與河流,而作為后裔的派拉特則帶著女性獨有的勇敢與智慧飛向了平等與自由。
參考文獻
1.Ahmad, Soophia. “Women Who Make a Man: Female Protagonists in Toni Morrison’s Song of Solomon”. 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 28.2 (2008): 59-73.
2.Lawson, Victoria. Making Development Geography.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2007.
3.Peach, Linden. Toni Morris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5.
4.龔莉嵐:“《所羅門之歌》中‘肚臍’的象征意義”,《散文百家》04(2017):43-44。
5.李應志:“認知暴力”,《國外理論動態》09(2006):60-61。
6.莫里森·托妮:《所羅門之歌》。譯:胡允桓。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13。
7.任冰:“論《所羅門之歌》的后人道主義思想”,《當代外國文學》33.04(2012):46-53。
8.薩義德·愛德華·W:《東方學》。譯:王宇根.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9.斯皮瓦克·佳亞特里:《從結構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讀本》。編:陳永國,賴立里,郭英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10.王守仁, 吳新云:《性別·種族·文化—托妮·莫里森與美國二十世紀黑人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作者單位: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