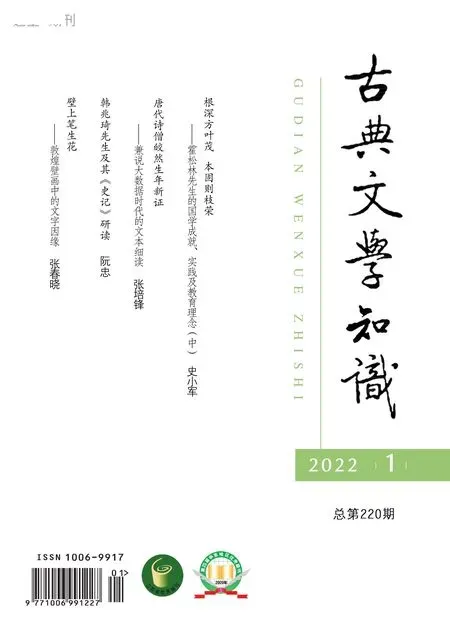張溥收撫沈承遺孤始末
陸巖軍
張溥(1602-1641),字天如,號西銘,私謚仁孝,南直隸蘇州太倉人,復社領袖,著名學者及文學家,在晚明影響極大。社會活動方面,張溥創建中國古代第一大文社——復社,并以主盟身份培養、團結、獎掖一大批優秀士人,在古代社團史上具有重要影響。政治活動方面,張溥與閹黨奸佞勢不兩立,彰顯出士人高度之正義感與擔當;又成功運作周延儒復任首輔,于晚明政治走向頗有影響。學術方面,張溥尊經重史,興復古學,所倡導之經世致用的實學風氣對清代樸學產生較大影響,其史論亦對后世影響頗大。文學方面,通過文學交游、創作及全面整理漢魏六朝百三家文集,對晚明文學產生重要影響。張溥之所以獲得如此大的成就與影響,與其為人、品行、社會活動能力、學術造詣、文學創作息息相關。通過四百年前張溥為諸生時毅然收撫友人沈承遺孤的一樁義舉,亦可以對其為人與擔當略窺一斑。
沈承,字君烈,號即山,太倉人。萬歷、天啟間諸生,有才名。其一生清貧坎坷,科考頗不利,曾先后七次參加鄉試,均以落榜告終,所謂“七戰金陵氣不降”(薄少君《悼亡詩》其二十七)。年未四十,含恨而逝,赍志沒地。然其才華高逸奇崛,質性閑澹清高,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雖科考不利,卻多獲有司及友朋賞識揄揚;雖英年早逝,卻幸得有司及友朋之助而使遺集刊刻,身立祠廟,名揚后世,受人敬仰。可謂死而不亡、夭而實壽。其泉下有知,亦可欣慰。
關于沈承之史料寥寥,本文通過爬梳其遺集《即山集》及張溥、張采等人著作來對其行實稍作勾勒,藉以還原四百年前張溥與沈承之交往及收撫遺孤之始末。
據嘉慶《直隸太倉州志》卷六十五《沈承傳》所載“未四十卒”及其卒年推算,沈承大概出生于萬歷十四年(1586)。沈承“少負異才,喜讀奇書”,攻詩賦,為古文,弱冠即受知于有司及學使者,諸生試每多高等。沈承性格清高孤傲(沈承《顧幼陶稿敘》云:“大要立身無傲骨者,其下筆必無飛才;其胸中無素心者,其舌底必無警語。”),“至性耿介,不與俗伍。單衣葛巾,飄若神仙中人”(周鍾《沈君烈遺集序》),才氣豐沛淋漓,文章嬉笑怒罵、生新尖刻,自云“善為迂語、誕語”(《李范合選序》),因此注定在程式化極強、代圣人立言的科考中屢遭失敗。科考的失敗和性格的孤傲又進一步強化了他詩文中的孤憤,也注定了他一生的坎不平。其詩作《婁門阻風》云“向日東出門,西風觸船首。今日西歸來,東風復噎口”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幾類阮籍窮途慟哭。
萬歷三十七年(1609),沈承再次鄉試失利。這既在意料之中,亦在情理之中。從沈承《即山集》來看,沈承為文多戲謔游戲之作,意在炫才呈博,其為詩多生新尖刻,意在求新求異。這種才子文學化的創作與科舉程式化的書寫自然不合拍,雖曾獲得惜才者的賞識,卻也易遭考官之拋棄。鑒于此,毛一鷺曾云:“君烈文不宜科第,而有英靈之氣。”(《對山書屋墨余錄》)太倉訓導張三光亦對沈承時文予以指正,而沈承對此似不以為然:“君烈才故空群,而氣橫思奇,瑕處間或未除。余輒乙其字句,庶幾他山之石。君烈弗是也。異日君烈試輒冠軍,然其瑕處,當事者亦往往乙之。”(張三光《沈君烈軼事》)萬歷四十年(1612),沈承第三次鄉試失利,郁悶萬端,作《慘賦》以散郁抑。其序云:“自謂英雄之苦備嘗,軋茁之魔銷盡,而猶然朱衣不點,白臘空歸。馬飛棄漢,慚無國士之追;囊竭游秦,羞乏下機之怨。……憶自昔年垂翅,吳歈自憐;及今再困公車,楚騷堪續。憔悴傷神,聊擬辭成《漁父》;支離獨嘯,何時賦獻《甘泉》?”以韓信、蘇秦不得志時自況,又以屈原流放之際作《漁父》自喻,渴盼異日能像揚雄一般奏賦朝廷。雖不得志,然自視亦甚高。毛一鷺評曰:“十分悲憤帶得十分簡傲。”可謂解人。
萬歷四十一年(1613),沈承娶薄少君為妻。薄少君,字西真,太倉人。二人琴瑟和諧,詩書唱和,“評詩詞之工拙,究內典之精微”(周鍾《沈君烈遺集序》),共同生活十二年,育有二女一子,惜均夭折。次年,薄少君生長女。因此年為丙辰,故起名阿震。求子心切的沈承起初頗為失望,“汝生之初,我實不喜。三十許人,不男而女”。但長女的可愛又使沈承倍加憐愛,“迨汝未期,汝即可憐。以頷招汝,汝笑盈盈”(《祭震女文》)。萬歷四十六年(1618),沈承四赴南京參加鄉試,又戰敗。落寞歸家后,長女可愛,“歸來牽袖,索物而戲。有汝在側,愁亦快意”(同上),稍散郁悶。次年冬,四歲長女阿震、二歲次女阿巽俱因天花不幸先后夭折。沈承痛苦萬分,在長女去世三七之際,作《祭震女文》,筆下字字如血:“嗚呼,痛可忍言哉!論世俗情,女死何哭?論我平生,壯志窮獨。汝又頗慧,雖女亦足。誰知鬼神,虐我太酷。先汝十日,汝妹阿巽。少汝二歲,與汝同病。同三日亡,汝所狎認。今汝無伴,當與妹并。汝稍能行,妹立未定。往來攜手,相好無競。”生離死別,誠為人生之至慟!林語堂先生亦感嘆此文乃“不可多覯的作品,是天地間之至文”(《介紹沈承〈祭震女文〉》)。
周鍾為沈承和張溥共同的朋友。萬歷四十六年(1618)鄉試期間,沈承與周鍾定交,頗為相得。周鍾對沈承了解頗深,云沈承“大約其為人也,介然負難群之志,故時有不可一世之慨,而間托之嘯歌諧謔,以與世浮沉。意之所是,雖以劍客、酒人、山僧、樵叟與之徘徊流連,竟日而不能去;若意所不可,即以王公貴人與當世之所號為名流碩彥,欲交歡之,掉頭而不顧也。故于世常落落寡合,而獨以其牢騷孤憤之氣寓之賞花賦詩、吟風嘲月之間”,“懶似嵇叔夜,放若阮嗣宗,嗜酒則劉伶之對壘,善笑則陸云之后身”。據周鍾《沈君烈遺集序》“余托在社末”及末署“金沙社盟弟周鍾書于吳門舟次”,可知沈承亦曾與周鍾一道參加文社。王家禎《研堂見聞雜錄》云:“吾婁前故有沈君烈者,名承,亦才士,試輒高等,三居第一,聲價蔚起,四方高才皆與結社。”亦可為其參加文社之一證。沈承曾為周鍾《名山業》作序,極盡戲謔嬉戲之能事,末署“婁湄風魔招討沈承咄咄書”(《名山紀事》)。又為周鍾《名山小論》作序,其文以三寸鬼戰八腳小鬼,比喻當時文風,末以周鍾《名山小論》戰勝三寸鬼與八腳小鬼來揄揚其作(《名山小論敘》)。毛一鷺評曰:“姑妄言之,何妨說鬼一番,部勒正使文場生色。”
沈承與張溥之交往,從有限之文獻記載可稍窺一斑。沈承集中有《壽張太仆夫人孫七十敘》云:“不佞余兄子之子是依泰頂之峰,故稔婦道,而益以驗夫人之母儀云。”張太仆即張溥大伯張輔之,據是,則沈承兄之孫娶張輔之女。故沈承與張溥可謂遠親。萬歷四十五年(1617),張溥父張翼之去世。沈承代他人作《祭張虛宇公文》,贊張溥父云“世宙聰明男子、意氣丈夫,如公者固少”。沈承亦曾兩度為張溥所選刻時文集作序,其《匡社敘》開首云:“匡社主人張天如嘗謂余曰:文章顧為雄霸,無為雌王。”又云:“挾匡社一編,坐臥其下,夜以手捫而讀之。”《王丘合刻敘》云:“張天如兄弟有概焉,重起而合刻之。而其友君烈沈子有概焉,亦起而敘之。”由這兩條記載可知,張溥在建立應社、復社前已加入匡社,且與沈承結交,多有文事往來。張溥“文章顧為雄霸,無為雌王”的文章觀,與沈承狂放恣肆、怪誕新奇的文風,亦有相通之處,亦可看出二者的相互欣賞與惺惺相惜。
天啟四年(1624)八月,沈承七赴南京參加鄉試。因途中耽誤,到南京時差點錯過鄉試日期。沈承與張溥相約,一起會晤周鍾。傍晚時,沈承致書張溥,中有“幾作防風”之語。大概是說赴試來遲,險遭懲處。用《國語·魯語下》“丘聞之,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之典。張溥當時即覺此言不祥,孰料后竟一語成讖(張溥《即山集序》)。
因旅途勞累,加之飲食粗陋,沈承此時身染痢疾,“病而瀕危”,但仍“匍匐終場”,堅持考完鄉試(《沈君烈軼事》)。結果自然可想而知。經此一役,沈承身心俱疲,復經病痢與報罷雙重打擊,歸家月余,即撒手人寰。
沈承病逝時,薄少君已懷胎數月。忽遭此打擊,晝夜悲傷,“甘心灰沒”(《即山集序》),悲慟難抑,血淚交加,化而為《悼亡詩》百首,長歌當哭,字字如血,“愁怨悲栗,痛逾柳下之誄”(《即山集序》),“天下傳而傷之”(張采《張殤童壙銘》)。《悼亡詩》今存八十一首(《對山書屋墨余錄》云:“少君詩凡百首而佚其三,天如又刪十六,實存八十一。”),附于《毛孺初先生評選即山集》后。托名鍾惺《名媛詩歸》卷三四亦錄薄少君《悼亡詩》,亦僅八十一首。其一云:“海內風流一瞬傾,彼蒼難問古今爭。哭君莫作秋閨怨,《薤露》須歌鐵板聲。”在刻骨的悲慟中,又有著曠達與堅韌。《名媛詩歸》評曰:“器識便非他人所及。”《玉鏡陽秋》評曰:“少君以奇情奇筆,暢寫奇痛,時作達語,時作謔語,《莊》《騷》之外,別辟異境。”可謂的評。
次年(1625)五月,薄少君產下一遺腹子。孤兒寡母,其生活之艱辛可想而知。鄉人唐文治先生曾記其少年時從其母胡太夫人處所得聽聞:“文治幼年聞先妣胡太夫人述少君當先生歿后,每挽一絕,哭暈一次,無所得食,取書嚼之。”(《書沈即山先生詩文鈔后》)
薄少君因“雅知書,能詩工棋。君烈文成,嘗為之脫稿”(張三光《沈君烈軼事》),亦有才名。太倉訓導張三光憐沈承家貧,于是請求督學助其喪。又多方周濟,令薄少君代領沈承尚未領取的食餼。薄少君所作代領文“文妥字莊”,張三光讀后,“不勝惻然者久之”(《沈君烈軼事》)。
沈承逝后,張溥幫助料理后事。周鍾得其死訊后,亦急赴太倉吊祭,“余聞之慟焉,急驅車往吊其廬,則談扇猶新,玉樹已萎,遺書在案,哭聲在帷”(《沈君烈遺集序》)。張溥悲慟之余,感慨沈承“獨遘奇剝,負疴不蠲,撤瑟之余,遂退托山椒,變越恒數,愊抑莫陳”,憂其“風流墜息,孰為依據”(《即山集序》)。于是與周鍾商議整理沈承遺集,“以為君烈千秋計”。復與訓導張三光商議刊刻事宜,“謀以事上白,公其文于人間”。張三光對沈承夙所賞識,亦極力玉成此事。
此時恰值毛一鷺任大中丞駐吳中,憐惜沈承早逝,“惻然痛之”。天啟元年(1621)毛一鷺督學三吳時,就對沈承青睞有加,云其“磊落負奇,兀傲自喜,不可一世,每操觚角技雄踞作者之壇”(毛一鷺《序沈生君烈即山遺稿》),常拔沈承為諸生冠軍。經張三光之請,毛一鷺遂為沈承遺稿作序并逐一評點,“以一日之契,遂不忘國士之愛,為點次其集而行之”(《沈君烈遺集序》),又慷慨捐資以助剞劂。張三光又“為之左右董政,不闕月已報功”(《即山集序》)。
天啟五年(1625)十月,沈承去世周年祭日。面對亡夫靈位,薄少君痛不欲生,哭罷即絕。張溥《即山集序》云:“(薄少君)侵染成疾,殞其身躬,計去君烈之亡,裁余一年有一日耳。病證相然,月時不異。”沈承、薄少君夫妻相繼而逝,留下尚在襁褓中之遺孤,“遺孤僅生五月,斷乳且斃”(張采《庶常天如張公行狀》),“平時稱慕悅者,不得一人顧”(《張殤童壙銘》)。見此情景,張溥“獨心惻惻”,請示母金太夫人后,毅然收養亡友遺孤。王家禎《研堂見聞雜錄》云:“未幾,妻薄氏死,一子襁褓,天如張公時為諸生,憐而育之。”周鍾對此深為感動,贊揚張溥義舉:“此固今日友道中所謂旦盟而夕寒者。君烈曾無一言之約,天如乃為金石矢之而不辭。則天之所以報君烈者其深且厚,又何如也。”(《沈君烈遺集序》)張三光亦大為贊嘆:“君烈為畸人,少君為畸配,天如為畸友,撫公為畸遇。”(《沈君烈軼事》)盛此公亦感嘆道:“嗟乎!天生天如以為君烈哉!”(《薄少君詩小序》)
張溥為遺孤起名張忱,“忱示不沒沈”,寓紀念沈承、為之傳嗣之意。其高情厚誼、俠肝義膽,四百年后仍令人感動。張采更感于張溥之義舉,次年將所生之第四女許配于張忱,與張溥結為姻家(《張殤童壙銘》)。婁東二張,不負其名,“不愧友于”(張采《祭天如兄文》)。
天啟六年(1626),毛一鷺刻《毛孺初先生評選即山集》六卷附《悼亡詩》一卷出版。毛一鷺、周鍾、州守劉彥、張溥、陳組綬、訓導張三光等作序跋。張溥以“鄉人”兼“明友”而作序,并在序末表達嗣后欲為沈承作傳及墓志銘的愿心。
崇禎元年(1628),張采攜家赴任臨川。次年四月,所許配張忱之女方四歲,不幸以痘瘍夭折于臨川。張采“哭幾絕,非哭女,哭我許兄家一意爾”,張采母亦痛哭,慟慨“何以慰天如家”(《祭天如兄文》)。五年(1632)春,張溥時在翰林院,張忱隨在京,亦因痘瘍不幸夭折,年僅八歲。夏五月喪歸,張采為之經理喪事,并作《張殤童壙銘》以志慟:“天酷沈,舉家墜。嗟兩生,翳急義。女不育,兒空字。徒盡傷,負初志。”沈承“舉家墜”之殘酷命運,令人神傷;張溥收撫遺孤、張采義結姻家之義舉,扶危濟困,同道相助,足以彪炳史冊,令人欽敬。
崇禎七年(1634)春,在張忱夭折三周年之際,張溥作《哀薄少君兼感忱兒賦痛》詩以抒哀傷亡友與亡兒之悲慟:“百律鵑紅燭已灰,貞心夜夜變風雷。靈歸何處看兒死,詩到于今似古哀。此日碧鏤知斷絕,十年繡褓幸招來。橫悲只逐東流水,梁孟墳邊思子臺。”
因毛一鷺、張三光等作為官方的表彰,因張溥、周鍾、張采等友人整理遺集予以揄揚,又因沈承、薄少君的美才懿行,鄉人為沈承建立祠堂,以表紀念敬仰。值得一提的是,太倉名賢、上海交大老校長唐文治先生以表彰前賢、整理鄉邦文獻為己任,對前賢沈承亦多致敬。1924年5月,唐文治先生“與諸同志集貲刻同鄉沈即山先生文集”,并作《書沈即山先生詩文鈔后》,贊云“今讀其詩文,悄悄乎其憂也,惓惓乎其忠也,浩浩乎,凜凜乎,壯懷之激烈而光明也”,“薄少君衡門偕隱,冰霜之操,松柏之姿”。1943年秋,颶風暴作,沈承祠宇坍圮,邑紳錢詩棣募捐巨貲,重加修葺,唐文治先生感而作《重修沈即山先生祠記》,更贊云:“吾婁沈即山先生,近世之夷齊也。……志節之清,莫與比也。”1944年冬,朱屺瞻繪《太倉十二古跡圖》,沈即山先生祠即為太倉十二古跡之一,唐文治先生為其作題記《太倉十二古跡圖記》,殷殷希望“后之閱是圖者,學諸先賢之學,行諸先賢之行”。唐文治先生于沈承三致意焉,既出于鄉黨之至情,更出于弘揚先賢、敦風厚俗、激勵士氣、感召人心之深意。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南朝詩人劉峻曾有感于任昉逝后諸子流離,而舊交莫恤,作《廣絕交論》以刺世。世態炎涼,令人慨嘆。然亦不乏高風亮節、“可以托六尺之孤”之“君子人”(《論語·泰伯》),令人景仰。如前有春秋亂世程嬰等義救趙氏孤兒,義薄云天,可歌可泣;后有晚明季世張溥義撫沈氏遺孤,情深義厚,可敬可贊。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張溥年譜長編”(21BZW1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