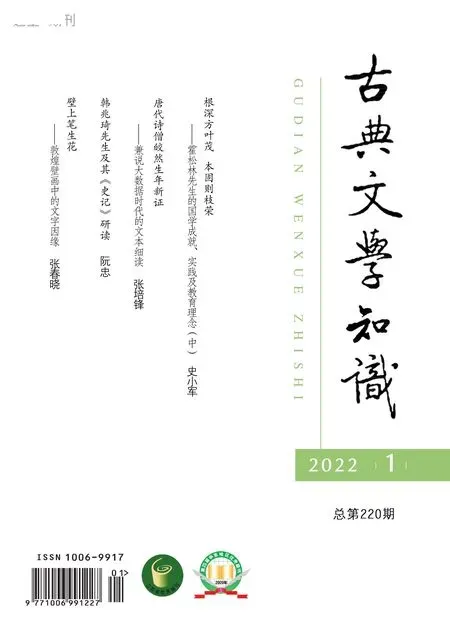哀婉的風雅:花冢與詩冢
李鵬
冢,《說文解字》說是“高墳也”,即封土高高隆起的墳墓。《紅樓夢》第六十三回里邢岫煙說妙玉認為從漢晉五代至唐宋皆無好詩,只有“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這兩句好。這兩句詩出自范成大《石湖詩集》卷二十八《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是他在給自己營建墓地時有感而發,原詩“鐵門檻”作“鐵門限”。范詩詩題里的“壽藏之地”和詩句中的“土饅頭”,指的都是冢,只不過前者典雅,后者則直白而形象。此前王梵志早就寫過兩首白話詩,其一為“世無百年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其二為“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里。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范成大巧妙地將這兩首詩綰合在一起,熔鑄成工整精粹的一聯,更顯得警醒,也更有沖擊力,因此受到《紅樓夢》作者的激賞。小說中除了借妙玉之口特意予以標舉外,還設置了“鐵檻寺”“饅頭庵”這樣的地名,并在第十五回回目“王鳳姐弄權鐵檻寺,秦鯨卿得趣饅頭庵”中加以對舉,該回說“因他廟里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諢號”,不過是小說家的障眼法。情種秦鐘這一回里還在饅頭庵和智能幽會尋歡,下一回便夭逝黃泉成了土饅頭里的餡兒。饅頭庵里的饅頭,表面上帶給讀者的是肉感的香艷,隱藏在背后的卻是凄冷的驚心,真給人一種忙著生、忙著死的無常感。不過,《紅樓夢》里這種幾乎揮之不去的生命無常感,在黛玉葬花的“花冢”前尤顯得哀感頑艷。
《紅樓夢》第二十三回,寶玉讀《西廂記》至“落紅成陣”,正巧風把樹上的桃花吹落在他身上、書上,寶玉不忍花瓣被踐踏,便兜至水邊抖落,讓其隨流水飄蕩而去,倒也應了《西廂記》里“花落水流紅”這句唱詞。此時恰逢黛玉擔著花鋤、拿著花帚過來,卻說:“撂在水里不好。你看這里的水干凈,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臟的臭的混倒,仍舊把花糟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冢。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干凈。”黛玉這里提到的花冢,第二十七回回目作“埋香冢”。在這一回里,黛玉一邊葬花,一邊感花傷己,隨口吟唱:“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未若錦囊收艷骨,一堆凈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于污淖陷溝渠。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一旁寶玉聽了,“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一念及此,可謂空落落無所歸依。其實,有人沒人,花照開照落,花冢里葬的不是花,而是有情人傷春自憐的意緒。
黛玉葬花,因為《紅樓夢》影響巨大,花冢為人所熟知;而清代顧光旭葬詩,雖為一時佳話,但知道詩冢的人并不多。
顧光旭(1731-1797),字華陽,一字晴沙,號響泉,江蘇無錫人,清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官至署四川按察使司,著有《響泉集》三十卷等。生平詳見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四《甘肅涼莊道署四川按察使司顧君墓志銘》。據王昶所撰墓志銘,顧光旭歸隱林下后,“以無錫東南文藪而賢人淑士湮沒未盡彰,網羅詩什,人各系以傳,成《梁溪詩鈔》四十八卷”(《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5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顧光旭編選的《梁溪詩鈔》是一部郡邑類詩歌總集,選錄了古稱“梁溪”的無錫一地自東漢至清乾隆間一千一百余位詩人兩萬余首詩,全書并非王昶所謂四十八卷,而是五十八卷。有意思的是,選完詩之后,在同鄉賈崧的建議下,顧光旭將選詩時所用各家集子原本埋在錫山南麓,建一亭子,上立石碑,號曰“詩冢”。除了在葬詩時邀請眾多士人會葬外,顧光旭還專門派出賈崧向詩壇名流廣泛征題索詩,一時之間轟動不小。
翻閱《清代詩文集匯編》(以下簡稱“匯編”)及其他清集,我檢得題詠此事詩歌如下:
袁枚《詩冢歌》、
趙翼《顧晴沙選梁溪詩成,瘞其舊稿于惠山之麓,立碑亭其上,名曰詩冢,為賦七古一首》、
翁方綱《詩冢歌》、余集《戲題賈素齋詩冢詩》、戴殿泗《梁溪詩冢(有序)》、張云璈《詩冢歌并序》、
法式善《顧晴沙光旭觀察選〈梁溪詩鈔〉,賈素齋綜其遺稿為冢,紀以詩》、吳文照《詩冢歌》、曾燠《梁溪詩冢》、劉嗣綰《梁溪詩冢歌為賈文學崧作,兼哭響泉先生》、郭堃《梁溪詩冢》、宋鳴琦《無錫顧晴沙觀察選其鄉自漢魏以來詩,都為一集。既竣事,賈上舍崧匯各遺稿,葬于錫山之麓,名曰詩冢。索詩》、潘世恩《詩冢歌》等。
與葬花一樣,葬詩也是癡,正如余集題詩其二所謂“能詩本是癡人事,想到埋詩事更癡”。不過,賈崧與顧光旭并非詩冢的首創者,郭堃題詩中的“自今名始創,于古事希聞”其實并不準確。明初宋濂《文憲集》卷十五有《詩冢銘(有序)》,序中提到有個叫魯修的詩人,“懼其詩失傳,埏埴為甓刻,瘞芝山中”,即將詩燒制在土磚上埋于地下,企圖借此讓自己的詩躲過戰亂傳到后世。顯然,從時間上看,魯修的詩冢創立在前。
而比顧光旭稍早一些的陶元藻(1717-?)在編訂自家詩集時,也將刊落之詩放入一石函中,埋入地下,題曰“詩冢”。陶元藻《泊鷗山房集》卷三十四中有《詩冢》兩首,詩中雖然認為這些被葬的詩只是“雞肋”“瓦礫”,之所以割愛埋掉是為了“免使人間論短長”,但一句“惆悵敲門月下僧”(見《匯編》第341冊),也能看出對作者來說,要親手埋葬這些當年曾費盡心血仔細推敲寫出來的作品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詩寫完之后,陶元藻還特地寫信邀請一眾好友唱和,梁同書《頻羅庵遺集》卷三有《蕭山陶篁村元藻自訂詩集竟,不入選者置石函埋之,題其阡曰詩冢,撰二律索和,因簡寄五首》,而吳騫《拜經樓詩集》卷十也有《山陰陶叟篁村詩集刊成,復匯其不入梓者,作石函而瘞之,號曰詩冢,自為之記,遍征友人題詠,山舟太史邀予同賦》。
上述詩冢間略有不同的是,魯、陶所建詩冢,雖然一個是為了傳世,一個是為了藏拙,但所埋均為自己的詩;而顧光旭修的詩冢,埋的卻是他人的詩。
顧光旭同年錢載《梁溪詩鈔序》說該總集“取例于元遺山《中州集》、朱竹垞《明詩綜》,上遵御定《國朝別裁》之義,大要以詩傳人,而亦以人傳詩”,話里所揭示的編纂宗旨,實際就是顧光旭自己在該書跋文中所謂“志在獻不在文”,即之所以抄錄詩篇,為的是讓這些詩人的名字流傳下去。對于詩人而言,寫下的詩作實際上是其生命的另一種形式的存在,他們渴盼的是文字能夠穿越時空成為永恒。可是,文人仰屋著書,詩人嘔出心肝,真正能流播人口的又有多少?最后只落得個詩冢同歸,一抔黃土掩風流,到底令人心酸不已。曾幫助顧光旭選詩的劉嗣綰題詩所謂“詩魂古今同一丘”,顧光旭建一詩冢將眾多詩魂匯聚在一處,一瞬間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紅樓夢》中所謂“千紅一窟”“萬艷同悲”。只不過,一為女兒,一為詩人。
在張云璈題詩中,他對詩人傳世的渴望表達了極大的同情,所謂“從古名心不肯死,姓氏長教堆故紙。骨雖已朽力可爭,所志區區只在此”。因此,他很贊許顧光旭選詩“隱然以詩為性命”。不過,他認為葬詩之舉并不妥,因為“文字潛幽氣不滅,漿酒寒澆心尚熱。請看一字二字間,猶是千痕萬痕血”。他覺得,最好學前人將詩集藏于古寺的做法,將這些集子都安置在錫山龍光塔上,以便后人續選詩鈔,“來補先生所不足,不教滄海有遺珠”。
除了張云璈,顧光旭的老鄉秦瀛也特地寫信對此舉表示明確反對。秦瀛《小峴山人文集》卷二有《與顧丈響泉書》,中云:
吾邑自漢以來迄近今之詩,先生以前無有裒而錄之者。先生殫數年之苦心,搜羅采擇,發潛闡幽,人系以傳,登之梨棗,甚盛舉也。然諸家之詩之原本,或鋟刻,或鈔寫,或專集流傳,或錯見別本,或藏之于其子孫之家,或不必子孫而他人藏之。先生之鈔梁溪詩,多者不過一人鈔數十首至百首,少且一二首至十數首耳,豈能盡其人之詩而鈔之?即謂所鈔之詩,其人之真精神已在于是;而此外未鈔之詩,其人一生心血所在,亦應聽其自存自亡于天地之間,不應舉而棄之土壤也。瀛意先生方采詩時,邑中之人各以詩送鈔,先生必且逐一標識;俟鈔既成,一一還之。夫古人往矣,其骨已朽,幸其詩僅存,不至與形骸俱敝,為狐貉啖盡。今先生欲不朽之,而又欲速朽之,何歟?(《匯編》第407冊)
秦瀛信的后半提到唐代劉蛻建文冢。劉蛻《文泉子集》卷三有《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并序》,文章開門見山:“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可見他埋的只是自己文章的草稿而已。由于劉蛻該文極有名,顧光旭等人建詩冢很可能受其啟發。唐人劉蛻外,秦瀛還提到當時有一個叫朱櫚香的同鄉也曾想建詩冢埋他朋友的詩作,但并未實行。在信的最后,秦瀛直言:“先生道高德重,不宜聽后生小子無知之言而有是舉。”
而在趙翼題詩里,他認為建詩冢的先例除了文冢外,可能也包括筆冢,即所謂“文冢筆冢可援例”。關于筆冢的傳說,唐代李綽《尚書故實》說是王羲之孫子智永“積年學書,禿筆頭十甕,每甕皆數石”,后來埋了,號為“退筆冢”。巧的是,李綽還提到因為來找智永題字的人太多,把門檻踩壞了,于是用鐵葉把門檻給包上,稱作“鐵門限”。另外,唐代李肇《國史補》卷中“得草圣三昧”條則說:“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圣三昧。棄筆堆積,埋于山下,號曰筆冢。”看來,與埋詩作冢一樣,埋禿筆成冢的書法家也不止一個。
在顧光旭之后,清咸豐六年(1856),黃琮輯完《滇詩嗣音集》之后,也將遺稿埋葬在太華山,并作銘文。據由云龍《滇故瑣錄》卷三“黃文潔詩冢銘”條記載,冢上也立了一碑,“約高五尺,闊一尺五寸,上書‘詩冢’二大字,下為銘”。這真可謂流風遺韻,嗣響不絕,令人嘆惋。
倘若說花無知,人有情,花冢里葬的落花寄托的是傷春女兒的愁緒,那么詩本身就是生命的結晶,詩冢里掩埋的,絕不僅僅是文字,而是詩人們的魂靈。其實,無論是花冢,還是詩冢,風雅的背后,都是對短暫而真實存在過的生命的溫情關注。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