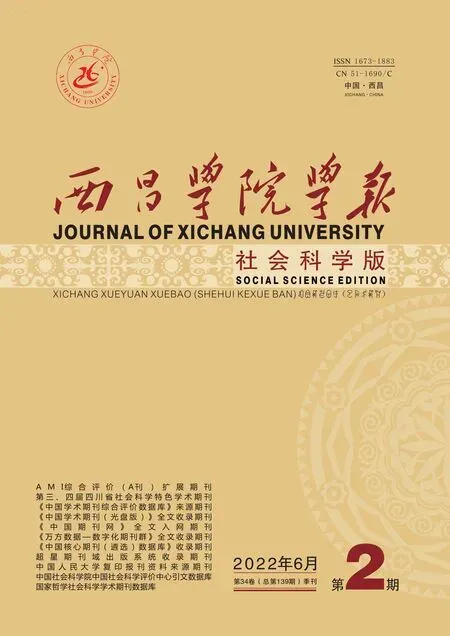生的自由與死的光亮
——《額爾古納河右岸》生命詩學探析
達則果果
(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四川 成都 610041)
《額爾古納河右岸》是一部蘊含著歷史的哀婉、現實的動蕩無奈與文化的變遷等豐富意蘊的作品。作者以抒情的口吻追溯了一個族群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繁衍、興盛到衰落的復雜歷程。 “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與鄂溫克族人的坦誠對話,在對話中她表達了對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堅持信仰、愛憎分明等等被現代性所遮蔽的人類理想精神的彰揚”[1]。 小說具有文化相對主義的思想與立場,遲子建以民族志工作者的姿態對鄂溫克族的文化結構、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和生存哲學進行了探索,用細膩柔情的筆調呈現了鄂溫克民族在生產生活里表現出來的生死意識,試圖展現一個古老族群生命圖景的深層況味,張揚了其熱衷繁衍和渴望生存的原始生命力,以及在現代文明的誘惑前把守孤獨、堅守家園的寶貴品性。
一、孤獨與自由:生命底色的堅守
弗洛姆認為,人在不經意的時間和地點無來由地被拋到世上,于千千萬物種中人是最絕望的一種。 可見人之孤獨與生俱來,但現代人的孤獨承受力是很有限的,他們總是試圖通過群體的熱鬧去緩解或逃避孤獨。 同時,他們又渴望自由,不愿活在他人的監視之下,卻渾然不知“孤獨是自由的必經階段,真正的自由是對孤獨的超越和揚棄”[2]。 而超越喧囂的孤獨亦是真正的自由。 馴鹿民族從熟人小圈子匯入現代社會的那一天起,就注定要沾染上現代人的孤獨,追求自由即是奢侈。 《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鄂溫克民族在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下歷經了從凝聚到分散、群居到個體、熱鬧到冷清的生存變遷。 在百年大變動中,這個族群從山上搬往山下試圖融入城市文明,沒過多久,他們中的部分人又重新回歸到大自然,有的則始終堅守家園從未離開,呈現了一種不為世俗的喧鬧所迷惑,堅守孤獨與自由的生命底色的執著。
鄂溫克人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然家園,他們每一次搬遷前都把垃圾埋掉以防止散發臭味,他們從不會砍伐活樹木,為防止燒毀樹林而發明了不用點火的口煙。 吊死在樹上的人要連同那棵樹一起燒掉,金得為保護樹木選擇一棵沒有生命力的樹木吊死。 然而,滾滾而來的現代文明帶來科學技術與豐富物質的同時,也對安寧祥和的自然家園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大興安嶺的被迫開發使得鄂溫克人的搬遷更為頻繁。 現代家園的開發切斷了鄂溫克人與大自然緊密相連的紐帶,他們被拋入孤立無援,無家可歸的迷茫境地。 無奈之下,烏力楞的人紛紛遷往山下,但他們離開時的眼神是無助迷茫的。“文明有時候是個隱形殺手。 當我們結束了茹毛飲血的時代而戰戰兢兢地與文明接近時,人適應大自然的能力也在不同程度地下降”[3]9。 許多生來就與大自然相依為命的鄂溫克人,一旦貪戀“山下”世界的便利后就不會再回歸大自然,但象征族群原始精神的“我”對文明這個“殺手”一開始就保持距離與警惕,“我”怕聽不到鹿鈴聲耳朵會聾,看不到星星眼睛會瞎,“我”認為讓馴鹿下山無異于將他們關進監獄,“我”覺得汽車放出的尾氣是“臭屁”。 “雖然營地只有我和安草兒了,可我一點也不覺得孤單。只要我活在山里,哪怕是最后一個人了,也不會覺得孤單的”[4]3。 比起虛無的熱鬧與狂歡,散發著神性光芒的大自然比人更加豐富,也更加誠實。“我”、伊萬、安草兒等人始終是屬于大自然的,留在山上的人極少,卻不覺得孤獨,沒有要與他人接觸、交往的心理需求,覺得不孤獨是因為在大自然里找到了精神與靈魂的寄托。 這種看似孤獨的不孤獨實際上是對心理學意義上孤獨的超越,因為這種“孤獨”是個體生命體驗與獨立人格的彰顯,從而讓人更加接近內心的真實與自由。 盡管拒絕了山下的熱鬧,但那不是孤僻的、封閉的、消極避世地逃避變化,而是對“生命獨立與自由的追求”[5]。 此外,作為鄂溫克族群最后一位族長的遺孀,“我”的堅守從某種程度上代表了這個族群最后的自然神性與精神光輝。
“我”等人的堅守是一種超越孤獨的精神自由,依蓮娜的孤獨回歸則是對現代性的反叛。 遲子建說:“二十一世紀能真正給予我們一些什么? 更高更新的科學技術? 如秋水一般波瀾不興的和平?只有教堂而沒有監獄的空間? 人人都成了彬彬有禮、深有教養的文明人? 倘若人類果真發展到這種境界,世界還稱其為世界嗎?”[3]10現代文明帶來了理性、技術、教育的普及等一系列積極變化,然而許多富有生命力與獨特個性的文明正在遭遇擠壓甚至消逝,人的精神家園在全球化進程中日益受損。依蓮娜是鄂溫克民族的第一個大學生,她從小在山下的烏啟羅夫讀書,畢業后當了一名美術編輯,嫁給了一名工人。 相較于祖輩們物質貧乏的狩獵生活,依蓮娜的人生應是充滿幸福與安全感的,但她的靈魂卻生長在傳統與現代的斷裂處,集體記憶將她往馴鹿、流水、星空與月亮處拉扯,現代生活的喧囂與便利又將她喚回山下,這使她的心理發生了某種分裂。 在山上才住上一段時間她便感到寂寞,沒過多久就回歸城市,卻又覺得“城市里到處是人流,到處是房屋,到處是車輛,到處是灰塵,實在無聊”[4]242-243。 在城里,她喪失了弗洛姆所說的伊甸樂園,失去了與自然的相依和靈魂的自由,成了永恒的孤獨流浪者。 她想回歸自然同祖輩一樣生活亦不再可能,因為她已從原始狀態走出,時間的不可逆性決定了她不可能再完完全全回到過去。 在城市的束縛與山里的自由間她痛苦掙扎,二者之間她終究厭倦了城市,辭職回到山里畫完氏族的最后一場薩滿儀式后,帶著畫筆伴著貝爾茨河水走向另一個世界。 與“我”不同,她的孤獨是一種漂泊無依,找不到精神歸屬的存在的荒誕感。 于她而言,死亡是對孤獨的最好擺脫和自由的最后去處。 作者將依蓮娜的死亡描繪得詩情畫意,出于反叛現代發展觀蘊含的毀壞人類家園的力量,遲子建對為捍衛心靈自由而死的伊蓮娜是充分同情與贊揚的。
“我”與伊蓮娜、安草兒等人或以生命捍衛自由,或以孤獨捍衛自我。 他們的堅守是對原始信仰,精神自由、自然家園和原始生命狀態的堅守,是對淳樸、簡單、真實的向往。 他們的靈魂是寧靜而孤獨的,這種“孤獨并非消極地無所依傍,而是指人徹底的自由——沒有什么決定論”[6]。 他們保持人格獨立,不求功名利祿,不與世俗同流合污,這種孤獨是達觀自由,高標己見的,同時也反映了狩獵民族對現代城市與時代變遷的不適。
二、性與食:原始生命力的表征
性與食是日常的,生活的,充滿人間煙火味的。但在遲子建充滿靈性的筆調下卻變得富有生機與詩意,同日月星辰,山河大海互融互生。 郁達夫說:“種種情欲之中,最強有力,直接動搖我們內部生命的,是愛欲之情。 諸本能之中,對我們的生命最危險而同時又最重要的,是性本能。”[7]遲子建筆下的性描寫不追求露骨大膽的性特征或動作,而是一種充滿隱喻色彩的詩意抒發,用藝術的審美筆觸對性愛的過程進行朦朧地描繪,呈現出水中賞月的含蓄委婉之美。
《額爾古納河右岸》里寫道:“希楞柱里也有風聲,風中夾雜著父親的喘息和母親的呢喃,這種特別的風聲是母親達瑪拉和父親林克制造的。”[4]7“風聲”來自大自然的空曠悠然,作者將它隱喻為性愛過程中發出的喘息聲是充滿深刻含義的,即達瑪拉與尼克的交融是人與大自然交融的隱喻,釋放激情與血液的時刻人與自然是同一的。 新生命的誕生正是在大自然的風聲與人造的風聲中得以延續,繁衍。 鄂溫克民族生活在邊地,廣博的天地自然賦予他們充沛自然,豐富細膩的情感底色,敢愛敢恨的性格彰顯了其生命的真實性和豐富性。 達瑪拉在林克死后不因畏懼世俗的眼光,絲毫不掩飾對愛的渴望與需求,嫁給了另一個部族的酋長瓦羅加,婚后他們在希楞柱的夜空制造“風聲”:“我和瓦羅加詩那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就像水與魚的結合,花朵與雨露的結合,清風與鳥語的結合,月亮與銀河的結合”[4]167。 靈與肉完美融合,這是力與美的抒發,在性愛的張力中人回到了生命最真的原初狀態。 描寫魯尼與妮浩、維克特與柳莎、達西與杰芙琳娜結合時的筆調也同樣深情流露,詩意盎然。 如老倫斯所言,在男女關系中,純粹的精神或者純粹的肉體的結合都是病態的,有缺陷的,只有將兩者結合才會帶來生機與希望。 遲子建對性的描寫并非為迎合世俗心理有意為之,她的出發點不在于尋求肉欲挑撥或者感官刺激,而是在探尋人的自然天性。 “藝術無性則干枯”,貫穿《額爾古納河右岸》的“風聲”使得小說色調飽滿豐盈,每一次的“風聲”都是人之靈魂在往自然和生命之道回歸。
遲子建筆下的北國風土靈動溫暖,人情純真美好。 不過她也寫生的凋敝,破敗與人性的丑陋,如懶惰,貪婪,冷漠。 也正因為如此,其筆下的文學世界才更加豐富,完整。 性愛在達瑪拉等人身上皆是愛,但在依芙琳與坤德那里則變成了恨。 依芙琳是《額爾古納河右岸》中最復雜也最鮮明的女性形象,她有著剛烈的反叛性格,得知坤德與她結婚前曾喜歡過一個蒙古族姑娘后,一直不愿與他同床,她反感兒子金得與父親一樣萎靡不振,不顧金得反對為他娶了歪嘴姑娘,金得為此自殺。 從此,夜晚的希楞柱里常常傳來依芙琳的叫聲:“坤德沒有講話,但我聽見了他沉重而急促的喘息和一種鞭撻人的風聲,他就好像在對伊芙琳‘噠噠噠’地發射著子彈。”[4]129坤德和伊芙琳之間的性關系源于責備、恨、報復與懲罰。 一股濃厚的仇恨氣息將他們籠罩,帶著仇恨情緒的性愛于讀者接受而言是殘忍的,性的生機在他們身上不再給人以審美的愉悅,但卻是深刻的,因為“性描寫既然是文學作品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它就必須服從于藝術整體的辯證法和諧地交織在故事的敘述、情節的發展之中為人性的開掘、心理的刻畫、性格的塑造和主體表現服務”[8]。作者創造伊芙琳這個角色正是服從于藝術整體的辯證法,充實人物形象及其心理,揭露人性的不同面和人物心靈深處的波濤洶涌。 伊芙琳從拒絕“性”到被迫接受之間呈現了生命的悲、喜、愛、恨等不同的維度,從而演繹因強烈的情感滲透而生成的生命意識和審美意義。
食物是生命存在的最基本需求。 《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鄂溫克民族在同惡劣環境的搏斗中獲取食物的行為表露了人對食物的深切熱愛,但遲子建刻畫鄂溫克人的食物欲望并非僅僅表達一種世俗化的物質性生活觀念,她以神秘的筆調再現了鄂溫克民族在長期的狩獵生活中形成的莊嚴神圣的狩獵文化,且“食”的背后蘊含著他們艱難困苦的生存狀態與生命境遇。 “我”的父親林克是氏族打獵好手,在捕獲堪達罕的時候林克像個功臣似的春風得意,而氏族的其他人則興致勃勃地集體去馱運獵物,曬肉條。 食物的來之不易令他們格外喜悅和珍惜,用獵物維持生活但不為戰勝它們而感到優越,出于萬物有靈的生命觀念,他們對獵物的犧牲充滿敬畏與感激,因而在“吃”的隆重中賦予獵物充分的儀式與祭奠。 饑餓貧窮,生存環境惡劣的條件下人對生命的認識和體驗會更加深刻,人之本性亦最易暴露。對待食物的態度映射了鄂溫克人勤勞、踏實,善良的生命品性。 老達西求孫子不得而養了一只老鷹將其作為情感的依托。 那時正值馴鹿遭上黃塵雪一只只死去,氏族人心惶惶,食物尤顯可貴。 達西的善良與對動物的尊重即在此時躍然紙上,為了讓老鷹吃飽,達西拒絕食物,把自己省下的都給了老鷹。 老鷹也懂得達西的犧牲,叼回一只山雞送到達西面前。 那晚,吃著山雞的達西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在這里,食物不僅僅停留在生存與溫飽的物質層面,它更多的是心理和情感的,是人與動物之間情感互通,共生共存的和諧,一種犧牲自我成全他人與生命皆可貴的思想呈現,流露出善良,淳樸的生命色彩。
三、誕生與死亡:互滲互照的生命張力
生與死互滲互照,生向著死,死來于生。 《額爾古納河右岸》呈現了“生死互滲”的生命張力,“死”并非作為生的對立面存在,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可作為另一種新生。 鄂溫克人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求生,于神性世界中豁達看待死亡,他們渴望孕育生命,并具備旺盛的生殖力,把“誕生”看作生存與血脈的延續,但生的每一天也都在朝死亡邁進。 遲子建以溫情憐憫的口吻書寫了作為生命兩端的生與死,透露出別樣的人性美與生命美。
貫穿《額爾古納河右岸》始終的是一層濃濃的死亡氣息,人們借死亡體悟生的意義和價值。 遲子建善于刻畫充滿神性色彩的死亡事件,其背后暗含著博愛、濟世,關懷萬物的深層意蘊。 鄂溫克人的死亡意識首先表現為“以死換生”,鄂溫克人可為保護馴鹿而不惜生命,老達西從狼口中救下了馴鹿而犧牲了自己的腿。 列娜在病危之際能夠被救活,是因為有一只馴鹿崽代替了她死去。 人與馴鹿生死相依,互敬互愛。 在人性與神性交相輝映的世界里,淡然、樂觀、平靜,充滿希望的死亡觀念指引鄂溫克薩滿義無反顧犧牲自己的骨肉去救贖他人。妮浩作為薩滿擁有神秘莫測的力量,她每一次跳神救活別人都是以犧牲自己的孩子為代價,第一個孩子果格力代替何寶林的孩子死去,第二個孩子交庫拖坎代替馬糞包死去,第三個孩子耶爾尼斯涅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尼浩。 救人之前明知自己的孩子會死去,卻不忍見死不救,這種舍生忘死的“英雄”色彩代替了死亡的悲痛,讓死亡具有一股詩意的浪漫色彩,蘊含溫暖的審美意義和道德意義。 這樣的生死替換觀淡化了人對死亡的恐懼以及死亡本身的悲劇性。 盡管“我”以滄桑的口吻訴說死亡的陰霾,但作者筆尖流露的對生死的悲憫情懷使得死亡氛圍染上一層救贖眾生,萬物有靈的盎然詩意。
除“以死換生”外,《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還通過眾多的意外死亡情節來反映和關照生命,闡釋一個族群的生存困境。 林克死于雷電,達西死于狼口,列娜死于寒冷、就連槍法極好瓦羅加也死于熊掌之下。 死亡的陰影始終伴隨著鄂溫克人,“因為每個人都會死。 每個人的出生是大同小異的,死亡卻是各有各的走法”[4]222。 鄂溫克人對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充滿敬畏,但在生命的有限性與脆弱性面前,他們難免遭受大自然無情的傷害與剝奪。 不過,他們并不因此悲觀絕望。 烏力楞族長去世的那一天本該將維克特的婚禮推遲,“但我想生命就是這樣,有出生就有死亡,有憂愁就有喜悅,有婚禮也有葬禮,不該有那么多的忌諱”[4]174。 因此在酋長葬禮當天依然舉行了維克特和柳莎的婚禮。 對死亡的理智認識讓鄂溫克民族在苦難中追求快樂,在無情的大自然面前勇敢生存,強大的生存意志激勵他們走出死亡的悲傷,苦難的現實生存條件導致的死亡早已成為常態,死亡意識已成為一種原始的直接經驗,從而經驗教人“充分意識到生命的脆弱性和有死性,面對不可避免的死亡,積極籌劃并從容度過人生”[9]。
生兒育女是種族延續的必然途徑。 生命的誕生,是個體生命體驗和香火延續的基本條件。 遲子建的筆下誕生同死亡一樣頻繁,《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魯尼與妮浩在孩子們一個個死去后擦拭悲傷,繼而努力孕育新生命,拉吉米撿回被遺棄在馬圈里的孩子并對之百般呵護,馬伊堪在決定結束生命前為養父孕育了新的生命等,整個烏力楞都永不停止孕育繁殖是鄂溫克民族熱愛生命,渴望生存和壯大人丁的心理映現。 瑪利亞與杰芙琳娜為得子去拜瑪魯神,祈求神賜子則將本為自然現象的生育神化,展露出一個原始民族的生殖崇拜現象,人們迫切希望得到神的保佑以綿延子嗣。 繁衍是生命生生不息的延續,孕育新生在某種層面上亦是對死去的生命的彌補,老達西死后不久瑪利亞竟有了懷孕跡象,“他們恰恰覺得是達西的靈魂保佑他們有了孩子”[4]52。 施韋澤認為“每一個生命都有一個秘密,每個生命都有價值”[10]。 小說中作者除描繪人的生命外,也刻畫馴鹿的孕育,誕生和成長。 鄂溫克人為找馴鹿的優良配種不惜跋山涉水,為鹿仔的誕生欣喜不已。 在他們看來一切生命平等,充分肯定生命存在的價值與權利。 他們對待生死的態度彰顯了舍身忘我、救贖眾生、豁達樂觀,萬物平等和詩意棲居的人性之美,也展露了作者獨特的生命價值判斷。
四、結語
綜上,《額爾古納河右岸》中,孤獨與自由是遲子建生命書寫的底色,在現代化進程的推動下,鄂溫克民族的生產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過程中“我”與伊蓮娜等人對自然家園的堅守與回歸具有一定的反現代性色彩,他們的孤獨是一種保持獨立人格,捍衛自由與真實的生命品質。 其次,生命書寫表現為性與食的原始生命力的表征,鄂溫克民對動物的捕獵是不得已的生存需求,對捕獲的動物要舉行儀式示以歉意,展現出尊重和珍愛生命的善良品格。 另外,他們敢愛敢恨,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張揚性力,散發出蓬勃的原始生命力量。 最后,鄂溫克民族用“以死換生”的自我犧牲來拯救他人的生命,于艱難的生存環境中繁衍孕育,以博愛情懷和別樣的生死觀念淡化了死亡悲劇,彰顯出積極樂觀的生命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