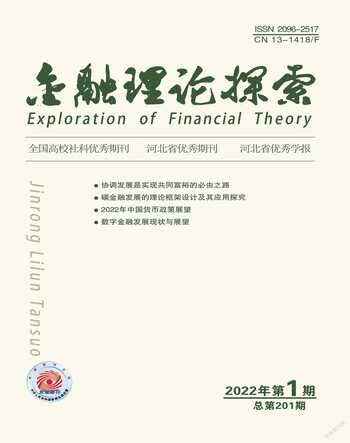2022年中國貨幣政策展望









摘? ?要:2021年12月以來,我國貨幣政策穩中趨松越發明朗。本文主要分四個層次對2022年我國貨幣政策的空間進行展望:一是貨幣政策寬松的必要性之來源;二是貨幣政策寬松的工具如何使用,并對降準、降息的空間進行定量評估;三是貨幣政策寬松的空間如何打開;四是貨幣政策寬松基調之下,人民幣匯率將如何助力調節貨幣政策的內外平衡。結論是:2022年我國貨幣政策兼具寬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存款準備金率仍有1~1.5個百分點的下調空間,通過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降準,即可帶動實體經濟付息壓力下降;而若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需以類似2016年的更大力度支持實體經濟,則還需降息10~15個基點。因此,貨幣政策需要“多措并舉”支持實體經濟,并避免我國宏觀杠桿率再度過快攀升。
關? 鍵? 詞:貨幣政策;通貨膨脹;存款準備金率
中圖分類號:F832?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2096-2517(2022)01-0019-11
DOI:10.16620/j.cnki.jrjy.2022.01.003
2021年12月以來,我國貨幣政策穩中趨松越發明朗。12月6日央行宣布全面降準0.5個百分點,12月7日央行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0.25個百分點,12月10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貨幣政策采用了“靈活適度”的積極表述,12月20日LPR利率如期下調5個基點。
展望2022年, 我國貨幣政策有無進一步放松的必要性?貨幣政策的工具將如何使用?掣肘貨幣政策寬松的因素將如何演變?在國內貨幣政策寬松而外部美聯儲政策收緊的環境下,人民幣匯率又將如何演繹?
對此, 本文主要分四個層次對2022年我國貨幣政策的空間進行展望。第一部分,從政策定調、就業壓力、經濟增長和實體經濟的結構性不均衡問題入手,闡述2022年我國貨幣政策寬松的必要性。第二部分,按照寬松程度由小到大的順序介紹2022年央行貨幣政策寬松的工具如何使用,并對降準、降息的空間進行定量評估。第三部分,從外部因素、通脹因素和監管因素出發,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掣肘因素趨弱,2022年我國貨幣政策寬松的空間將會打開。第四部分,將人民幣匯率與貨幣政策結合起來, 認為2022年人民幣匯率將會成為調節中美貨幣政策“松緊差”的平衡器。
本文認為,2022年我國貨幣政策兼具寬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存款準備金率仍有1~1.5個百分點的下調空間, 通過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降準,即可帶動實體經濟付息壓力下降;而若經濟下行壓力較大, 需以類似2016年的更大力度支持實體經濟,則還需降息10~15個基點。本文認為,貨幣政策需要“多措并舉”支持實體經濟(尤其是其中的薄弱環節),并避免我國宏觀杠桿率再度過快攀升。
一、貨幣政策寬松必要性之來源
2022年我國經濟總量走弱與結構不均衡的壓力并存,貨幣政策寬松的必要性主要有四個來源。
一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22年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奠定了貨幣政策寬松的政策基調。 近年來,“靈活適度”的表述出現在對2016年、2020年的貨幣政策部署中,都對應著寬貨幣、寬信用的年份。而2019年是“松緊適度”,2017年、2018年都提到了“貨幣總閘門”,2022年貨幣政策偏向寬松的趨向不言自明。此前,央行在《2021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①中,也去掉了延續多時的“管好貨幣總閘門”的說法。
二是就業壓力逐步顯現,凸顯出貨幣政策托底的必要性。 我國滾動12個月的城鎮新增就業人數已從2021年8月的1343萬人顯著下滑至2021年11月的1294萬人, 遠低于疫情前的1350萬人的中樞水平(見圖1)。回顧歷史,與當前就業壓力較為相似的是2015年至2016年、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末、2020年上半年三個時間段,貨幣政策在這些時間都以寬松托底為主。
三是2022年若無進一步的逆周期宏觀政策,我國GDP可能仍運行在潛在增速之下,給完成“十四五”規劃與2035年的遠景目標帶來挑戰。一方面,根據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課題組在《“十四五”期間我國潛在產出和增長動力的測算研究》② 中的測算,2021—2025年我國潛在產出增速分別為5.7%、5.5%、5.5%、5.3%、5.1%。而2021年三季度我國GDP兩年復合增速已回落至4.9%低位,2022年GDP增速也較難達到5.5%。另一方面,雖然“十四五”規劃沒有明確制定GDP增速目標,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有希望、有潛力保持長期平穩發展,到‘十四五’末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③ 這蘊含著未來15年中國經濟需實現年均4.73%的增速水平。考慮到2025—2030年我國潛在增速水平還可能進一步下移,若“十四五”疫情正常化后開局GDP增長僅在5%甚至以下, 則對后續完成遠景目標會帶來更多挑戰。
四是 實體經濟結構不均衡問題仍然突出,重點行業和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仍有降低的必要性。2021年以來,原材料價格持續高漲,導致利潤不斷向上游采礦和中游原材料行業集中,擠壓了中游裝備制造、 下游消費制造及公用事業領域的毛利率。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經營數據看,私營企業的負債與財務費用在近兩年快速上行,是我國經濟運行中的薄弱環節。 以可比口徑的上市公司數據計算,由于上游工業品價格上行幅度較大,集中于制造業中下游的民營企業ROIC三季度已降至4.9%的低位,與三季度的銀行一般貸款加權平均利率5.3%出現“倒掛”。預計2022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后,需求端或將進一步承壓,相關行業和民營企業的投資和盈利情況不容樂觀,貨幣政策有必要對癥下藥,進一步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
二、貨幣政策寬松的工具如何使用
2022年貨幣政策的工具選擇按照寬松程度從低到高,依次為再貸款、降準、降息。接下來分別評估其作用與空間。
(一)再貸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重要一極
2020年以來,再貸款、再貼現開始在我國基礎貨幣投放中發揮突出作用。2020年,央行通過三批再貸款、再貼現政策和兩項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工具,投放基礎貨幣達到1.0845萬億元, 而2020年基礎貨幣凈增加量僅為6253億元。2021年前三季度,再貸款、再貼現余額略有下降,但四季度以來政策再加碼, 尤其碳減排支持工具采用再貸款形式,勢將成為2022年基礎貨幣投放的重要一極。
這也意味著,央行從基礎貨幣投放開始就具有了較強的定向特征,將在引導資金流向上發揮更大作用。 根據銀保監會在新聞發布會上的介紹,2020年6月末, 小微企業不良貸款率為2.99%, 比各項貸款不良率高出0.88個百分點①。 由于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貸款的不良率較高、 單筆金額低, 銀行從自身屬性來講對這些領域的放款積極性不高。央行創設專項再貸款工具之后,銀行如若在這些領域放款,可以享受更低的資金成本,一定程度上能夠彌補其“風險溢價”和“管理成本”的提升,形成市場化的激勵,有助于促進貸款結構的調整。需要注意的是,再貸款、再貼現工具并不能直接作用于銀行貸款利率中樞的下移,而是通過“開正門,堵偏門”,為原本難以從銀行體系貸款的小微企業提供低成本的融資渠道。否則,部分小微企業只能從小額貸款公司、 民間融資等渠道以超過10%的利率借款(見圖2)。
(二)降準凸顯彌補基礎貨幣缺口的中性含義
2018年以來, 我國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逐步轉向“價格型”工具,而降準作為“數量型”工具將愈發突出其中性意味。2018年3月份,周小川在出席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期間表示,“中國將推動貨幣政策調控從數量型工具向價格型工具轉變”。同時,央行貨幣政策的目標也不再是此前固定的M2、信貸和社融增速,而開始改為“與名義GDP相匹配”。在此框架下,降準作為一種數量型工具的中性意味越來越強。2018年以來,我國大型和中小型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17%和15%分別下降至11.5%和8.5%, 除2020年1月疫情期間外,每次降準均伴隨著MLF存量規模的下降。
從基礎貨幣缺口的角度來看,2015年以來伴隨外匯占款規模的下降,我國貨幣創造對貨幣乘數提升的依賴明顯提高。截至2021年11月,我國M2供應量同比增長的8.5%中,貨幣乘數的貢獻達到7.3%。而降準就是作用于貨幣乘數的提升。2018—2021年,降準幅度分別是2.5%、1.5%、1.5%(中小型)、1%。2022年1月、8—12月的MLF到期規模均超過了5000億元, 相關時點的MLF續作情況值得關注。2022年,如果央行不希望進一步擴大公開市場操作規模,考慮到碳減排支持工具的規模擴張(從而投放基礎貨幣)需要一個過程,且隨著貿易順差可能高位回落,外匯占款有回落壓力,那么要保持大致平穩的M2增長,通過圖3可以看出,2022年還需通過提升貨幣乘數穩定貨幣供應,存款準備金率仍有1~1.5個百分點的下調空間。
不過,我國存款準備金率的調降空間可能已經收窄,并非“一降了事”那么干脆簡單。2018年4月至2021年12月, 我國存款準備金率累計下調了5.5個百分點,當前8.5%的存款準備金率的平均水平已經處于2006年8月以來的絕對低位。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 我國存款準備金率也并不算高。易綱行長在2019年3月(當時我國中小型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約11.5%)的人大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曾表示,“從國際比較而言,我們的存款準備金率在國際比較中是中等的,不算特別高也不算特別低”。孫國峰司長2021年1月15日(當時我國中小型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約9.5%) 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不論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是與我國歷史上的準備金率相比,目前的存款準備金率水平都不高。”
考慮我國的經濟發展階段、最優資源配置和金融機構自身穩健經營問題,5%的存款準備金率在中長期內或將成為我國存款準備金率的隱形下限。一方面,易綱行長在2019年3月的記者會上提到,發展中國家有個發展階段的問題, 在這個階段,一定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還是合適的,必要的。所以,我們通過準備金率下調, 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應該說還有一定的空間,但是這個空間比起前幾年已經小多了。 另一方面,2020年5月15日的降準落地后,部分符合“三檔兩優”標準的縣域法人金融機構就享受到了5%的存款準備金率,2021年的兩次降準中都排除了這部分金融機構。 央行于2021年7月宣布降準后的答記者問中提及,“不下調部分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的主要原因是,5%的存款準備金率是目前金融機構中最低的,保持在這一低水平有利于金融機構兼顧支持實體經濟和自身穩健經營。①”因此,可以大致認為,5%的存款準備金率是考慮“金融機構兼顧支持實體經濟和自身穩健經營” 后的我國存款準備金率的隱形下限。當然,在通往5%的存款準備金率的道路上,央行仍會權衡評估我國經濟金融周期的變化, 有前瞻、有針對性地做出調整。
(三)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存在三條路徑
從銀行的角度出發可以將貸款利率拆分為風險溢價與LPR報價。 其中,LPR報價受銀行息差和銀行負債成本的影響,而銀行負債成本又可以進一步拆解為存款利率、高成本負債占比、金融市場利率三個方面②。
基于以上拆分,2022年我國貨幣政策可通過以下三個渠道引導貸款利率下行。
1.第一個渠道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改革
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改革, 進一步釋放LPR改革紅利,有望推動貸款利率進一步下行7~8個基點(對應于貸款利率與LPR之間利差的收窄)。
2019年LPR改革以來,一般貸款利率自2019年6月的5.94%下降至2021年12月的5.30%,累計降低了64個基點,在此期間,一年期的LPR利率共調降了35個基點,其中29個基點的軋差主要來自于LPR改革的紅利和銀行凈利差的壓降。 目前,LPR改革在打破貸款利率0.9倍隱形下限、壓降銀行貸款點差方面已卓有成效,銀行貸款利率中LPR減點等于LPR利率的占比自2019年8月至2021年9月累計提升了16個百分點。不過,疫情后執行LPR減點的貸款占比先降后停,側面體現出銀行讓利實體經濟的壓力較重,后續銀行凈息差的壓降空間可能比較有限,未來改革的重點或是推進存款的利率市場化改革, 通過降低銀行負債成本推動貸款利率下降。 央行2021年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及,“持續釋放LPR改革潛力, 充分發揮LPR改革在優化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督促落實優化存款利率監管措施,保持銀行負債成本基本穩定,繼續推動金融系統向實體經濟讓利。”具體措施或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強化銀行存款自律機制,打擊高息攬儲行為;另一方面,完善貨幣基金、現金理財等資管產品的管理制度, 打破隱形剛兌預期,大力發展同業存單指數基金,以居民資產配置的優化為銀行拓寬低成本資金來源。
2.第二個渠道降低存款準備金率
降低存款準備金率1~1.5個百分點, 或可間接推動貸款利率下行7-8個基點(對應于LPR與MLF之間利差的收窄)。
目前,降準除了彌補基礎貨幣缺口的中性意義以外,其寬松意義主要體現在:增加銀行可用的低成本資金, 替換高成本的MLF,以降低商業銀行負債成本,進而間接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由于傳導路徑較長, 降準帶動貸款利率下行的效果相對有限。具體測算如下:
從商業銀行成本節約的角度出發,央行每調降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約可引導商業銀行LPR報價下行5個基點。一是直接影響方面,假設降準用來置換MLF,降準釋放1萬億元資金(降準0.5個百分點約釋放8000~12 000億元資金)可為銀行體系直接帶來10 000×(2.95%-1.65%)=130億元的成本節約,占2021年11月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191.6萬億元的比例約0.68個基點,即為降準對負債成本的直接影響。二是廣義影響方面,考慮到存款準備金率每降低1個百分點可以提升貨幣乘數0.335倍(2010年至今回歸結果),而基礎貨幣自2017年底至今穩定在30~33萬億元,降準0.5個百分點預計可為銀行體系帶來約5.28萬億元的派生存款。截至2021年中報,上市銀行計息負債成本率約2.2%,用此來替換成本相對較高的同業負債(假設1年期同業負債成本為3.0%,略高于目前MLF的利率),廣義上可為銀行體系帶來5.28萬億元×(3.0%-2.2%)=422.4億成本節約,占2021年11月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191.6萬億元的比例約為2.20個基點,即為降準對負債成本的間接影響。
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增刊《有序推進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改革》①中,降準對于LPR報價的影響也大致如此。其中提到,“LPR改革后中國人民銀行分別于2019年9月和2020年1月兩次降低法定準備金率各0.5個百分點,對報價行資金成本等加點因素有明顯影響,降準當月均有部分報價行根據自身情況下調了報價,并帶動報價的算術平均值下行了0.02~0.03個百分點,但因為變動小于LPR的最小調整步長,向0.05%就近取整后,兩次降準當月只有一次觸發了LPR變化。”
3.第三個渠道降低公開市場操作的政策利率
降低公開市場操作的政策利率,可最直接、有效地降低融資成本。
在“健全中央銀行操作目標體系”的過程中,央行已經打造并正在健全“以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貸便利利率為中期政策利率的政策利率體系”,“健全從政策利率到LPR再到實際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利率形成和傳導機制”。在這一框架下,降息的全局性意味(牽一發而動全身)最強,意味著從貨幣市場上的7天逆回購利率,到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再到實際貸款利率的整體性下調。
從減輕實體經濟利息償付壓力的角度出發,上述前兩類政策工具紅利釋放之后,實體經濟付息規模的同比增速有望下降至7%左右,增速水平橫向對比不算高。如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需以類似2016年的更大力度支持實體經濟,則政策利率還需下調10~15個基點。考慮到目前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基調與支持實體經濟的訴求,假設2022年信貸規模以11%~12%的速度增長,將2021年12月20日1年期LPR調降的5個基點納入考慮后,本文測算(見表2):(1) 如需將2022年實體經濟付息增速控制在5%左右(與2016年、2020年相當,弱于2015年的刺激力度),貸款利率的中樞較當前水平還需進一步降低24~28個基點。在扣除前兩類政策工具降低貸款利率共約15個基點后,還需調降政策利率10~15個基點。(2)如僅將實體經濟付息增速控制在7%左右(與2019年相當),貸款利率的中樞較當前水平需降低14~19個基點,依靠前兩類政策工具即可基本滿足。本文認為,第一種情形可能性更高,即貨幣政策需要“多措并舉”支持實體經濟(尤其是其中的薄弱環節), 并避免我國宏觀杠桿率再度過快攀升。
三、貨幣政策寬松的空間如何打開
2022年我國貨幣政策寬松面臨的掣肘整體減弱,貨幣政策寬松的空間已然打開。
從外部因素看,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掣肘有限。 金融危機后的美聯儲三輪QE間隙和加息周期中,我國貨幣政策保持著“以我為主”的獨立性。尤其是在經濟增長下行壓力突出的2012年、2015年和2018年, 面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邊際趨緊,我國央行堅持以我為主,以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穩定就業形勢。
從通脹因素看,2022年溫和上行的CPI與下行較快的PPI組合對貨幣政策不構成緊約束。本文預測,2022年的CPI整體溫和上行,但核心CPI受制于需求端的疲弱趨于回落;PPI則受制于2021年的高基數及黑色、原油系商品價格中樞的相對下行,全年趨于回落。復盤2010年以來我國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降準降息的操作往往伴隨著PPI的下行及核心CPI的相對低位,2022年的通脹組合難以對貨幣政策的寬松構成緊約束。
從監管因素來看, 在防范化解風險的過程中,為緩解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避免“因處置風險帶來的風險”, 在關鍵時點還有必要配合性地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就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問題,馬駿等(2019)梳理國際文獻的初步結論表明,為了同時實現價格穩定和金融穩定目標,大部分情況下需要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反向操作(由于政策的替代性),具體的最優政策組合取決于宏觀沖擊的類別和風險的來源[1]。本文認為,2022年在防范化解風險的過程中, 為緩解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避免“因處置風險帶來的風險”,在關鍵時點還有必要配合性地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2022年促進房地產行業“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成為穩增長的核心內容,而歷史上當穩定房地產投資訴求增強時,往往伴隨降準、降息的推出(見圖5)。當前,在“房住不炒”的中長期基調下,配合房地產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框架的形成,貨幣政策寬松的空間也已打開。
四、貨幣政策寬松下的人民幣匯率
(一)人民幣匯率或為調節內外貨幣政策“松緊差”的平衡器
2022年人民幣匯率可能成為中美貨幣政策“松緊差”的平衡器,為釋放國內貨幣政策空間,可能允許人民幣匯率在貶值方向釋放更大彈性。截至2021年12月31日, 聯邦基金期貨已經隱含了美聯儲2022年加息3次測預期。 而中國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靈活適度”的定調、就業壓力的凸顯、經濟低于潛在增速運行的壓力、民營企業和部分中下游行業盈利增長承壓來看,中國貨幣政策將加大寬松力度。 本文預計,2022年可能有1~1.5個百分點的降準空間, 在經濟壓力加大情況下還有10~15個基點的降息(政策利率)空間;美聯儲加息期間,中美利差收窄一定程度上對我國貨幣政策操作形成掣肘, 從而中美利差將向80個基點的警戒水平運行,給人民幣匯率帶來貶值壓力(見圖6)。而在人民幣貶值與貨幣政策“以我為主”之間,政策選擇從2021年12月央行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的含義中已然明朗。
(二)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的政策信號
2021年12月9日央行發布公告稱,將于2021年12月15日起將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由現行的7%提高到9%。 這是年內央行第二次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上一次是5月31日宣布從6月15日起將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由5%提高到7%,也是央行時隔14年再次啟用這一工具。而在此之前,主要運用“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在0%與20%之間切換。在2020年10月22日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下調為0%之后, 人民幣匯率仍然持續升值, 因而到2021年5月31日人民幣升值預期過于集中時, 央行啟用了“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工具。二者的差別在于,外匯風險準備金率下調, 是降低了企業遠期購匯的成本,有利于增加外匯市場美元需求,從而抑制人民幣過快升值;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上調,是強制增加銀行的外匯存款留存, 減少外匯市場美元供給,從而抑制人民幣過快升值。
2021年央行兩次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的背景是, 外匯存款相比于外匯貸款需求增長過快。銀行外匯貸存比由2020年10月的1.05進一步下降至2021年11月的0.93,說明有較多的外匯流動性淤積在境內商業銀行體系內,形成了寬松的美元流動性,為人民幣匯率帶來了升值壓力。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可多鎖定一部分美元流動性。 不過,兩次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時,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預期集中度并不相同。本文以扣除中美利差影響的一年期USDCNY NDF衡量遠期匯率隱含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可見,2021年6月是在人民幣升值預期顯著上升的背景下采取調控政策;而2021年12月人民幣升值過程中并未伴隨升值預期的上升(相反升值預期還較前期有所下降)。
這意味著,2021年12月央行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人民幣匯率所達到的點位觸及了政策的心理關口,從而也意味著如果人民幣匯率進一步上升,后續不排除更多政策工具的使用。央行兩次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時,美元兌人民幣匯率都位于6.35附近(2021年5月31日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為6.3682,12月9日為6.3498)。2021年11月舉行的全國外匯市場自律機制第八次工作會議指出,人民幣匯率未來“雙向波動是常態,合理均衡是目標, 偏離程度與糾偏力量成正比”。2021年12月“糾偏力量”的出現,說明人民幣匯率與基本面的偏離程度或已超出“合理均衡”的范圍(見圖7)。而人民幣匯率過度升值會對外向型企業造成不利影響, 在2022年我國出口面臨增速下行時,這種不利影響可能凸顯出來。
(三)貨幣政策寬松基調下的人民幣匯率展望
2022年人民幣匯率強勢的基礎并不會快速消退,人民幣匯率可能成為調節中美貨幣政策“松緊差”的平衡器,在貶值方向釋放出更大彈性。
1. 2022年國際收支對人民幣匯率的支撐趨弱
2021年人民幣匯率強勢主要體現市場供求因素的影響,而市場供求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國際收支狀況優化,包括:貨物貿易順差的擴大、服務貿易逆差的縮窄、直接投資的大幅增長以及證券投資的持續流入。2022年, 海外疫情演變方向仍不明朗,傳播能力更強的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可能延緩海外開放經濟的步伐。而且,考慮到當前全球疫苗接種仍高度不平衡,病毒在疫苗普及不足的低收入國家仍可能進一步變異,給后續全球疫情防控政策帶來不確定性。在此情況下,預計2022年我國服務貿易逆差很難大幅地重新擴大,貨物貿易順差回落的過程將是漸進的,從而經常賬戶順差在高位仍可受到一定支撐。直接投資的高額順差可能隨著中國經濟的常態化放緩而趨于回落,證券投資差額在中美利差收窄的情況下也有一定下行壓力,但二者仍然受到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政策支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22年要“落實好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吸引更多跨國公司投資,推動重大外資項目加快落地”。本文認為,總體上,2022年國際收支層面對人民幣匯率的支持面臨減弱,但在疫情不確定性的影響下、在中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支持下,人民幣匯率強勢的基礎并不會快速消退。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2022年中資美元債的大量到期也會對國際收支差額產生影響。根據中資美元債發行流程,海外發債募集資金主要通過兩個渠道回到國內: 一是自身經營范圍內的經常項下支出,二是資本項下的債權投資和股權投資,二者均會影響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2022年我國中資美元債到期量達到1731億美元, 占中資美元債存量(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18.4%,而2021年以來中資美元債在海外募資愈發困難(2021年全年中資美元債共募集資金1292億美元,較2020年下降24.8%)。在此情形下,2022年中資美元債的凈融資金額可能繼續下降, 進而帶來資金的凈流出。并且,如果2022年人民幣匯率出現階段性貶值,則國內企業以美元計價的中資美元債的實際融資成本將上升,而中資美元債的融資主體又以處境艱難的房企居多,這可能成為壓倒部分房企的“最后一根稻草”,進而帶來海外融資進一步惡化的負循環。
2. 2022年美元指數仍有偏強基礎
國際收支對人民幣匯率的支持減弱,將使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指數的相關性重新增強, 而2022年美元指數仍受到美國經濟復蘇和美聯儲加息的支持,從而給人民幣匯率帶來一定壓力。2021年人民幣升值主要受外匯市場供求因素驅動,而“保持一籃子貨幣匯率穩定”(使得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指數相關性增強)主要起到反向平抑作用,其結果就是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指數的“脫鉤”。2022年隨著市場供求對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驅動減弱,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指數之間可能重新趨于“掛鉤”。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 美元指數已反彈回到95.97,而2015年“8·11”匯改以來,當美元指數處于這一位置時,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均處于6.65到7區間內。因此,若后續國際收支的支持弱化,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有可能向此區間回歸。
2021年12月31日, 外匯交易中心發布新版CFETS貨幣籃子和權重。 相比于2017、2020、2021年的權重調整幅度,2022年屬于微調。美元權重小幅上調了1.09個百分點至19.88%,為CFETS指數推出以來首次上調美元權重;加上港元、阿聯酋迪拉姆、阿拉伯里亞爾這三個釘住美元貨幣的權重之后,美元的實際權重僅上調0.5個百分點至27.29%;而歐元的權重繼續穩步上升至18.45%, 日元權重繼續溫和下降至10.76%。在CFETS人民幣指數中美元權重下調/上調的意義, 不在于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力是上升還是下降[2],因為美元作為全球霸權貨幣,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力仍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影響更多體現在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彈性的影響:當美元的權重下調時,意味著人民幣相對美元的升貶幅度,要更多地向其他貨幣相對美元的升貶幅度看齊, 從而人民幣對美元的波動彈性將加大。因此,與此前權重下調相反,2022年美元權重小幅回升,意味著將會稍微抑制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彈性,但這主要體現的是疫情影響下中美貿易占比的提升,而不應視為對“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訴求的某種倒退。
2022年美國經濟相對全球仍可能保持“一枝獨秀”,加之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進入加速階段,意味著美元指數仍有偏強基礎。美元指數作為美元對全球六種主要貨幣的相對指數,其走勢很大程度上與美國相對全球的經濟增長差異有關。 歷史上,當美國經濟相對全球表現更好時,美元指數往往處于回升階段。根據IMF 2021年10月發布的預測,2022年美國的實際GDP增速有望達到5.2%,高于IMF對2022年全球4.9%的實際GDP增速預測。且按照目前聯邦基金期貨的預期,2022年美聯儲加息3次,而歐央行可能到2023年才會首次加息,這亦會給美元指數帶來支持。
3.中美關系的變數仍是人民幣匯率最大的風險
2021年9月開始中美關系不斷釋放積極信號,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到期后,由于美國通脹問題(“脹”)已成為經濟走向“滯”的催化劑,而本文梳理后發現, 受對中國加征關稅影響較大的商品,所遭遇的供應鏈瓶頸問題也更嚴重,成為加重美國通脹壓力的因素之一。因此,2022年美國可能通過放松關稅豁免規則,下調部分關鍵產品稅率,從而帶動中美經貿關系進一步邊際改善。這一預期也在當前人民幣匯率中得到了體現。不過,近期美國宣布新增制裁中國多家企業等,意味著中美博弈形勢依然膠著。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將至,盡管民主黨目前仍然掌管兩院,但與共和黨之間割裂嚴重且難以彌合,以參議院議員曼欽為代表的黨內溫和派使得拜登新政的推行困難重重,拜登的民意支持率也一路走低,目前已接近特朗普時期的支持率。在此背景下, 美國內部政治僵局的演化還有不確定性,屆時人民幣匯率可能再度受到風險偏好上的沖擊。
參考文獻:
[1]馬駿,何曉貝.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J].金融研究,2019,474(12):58-69.
[2]張璐,鐘正生.人民幣升值三問:原因、空間、影響[J].國際金融,2021(3):24-30.
Prospect of China’s Monetary Policy in 2022
(Chief Macroeconomics Experts Team, Ping An Securities, Beijing 100032, China)
Abstract: Since December 2021, i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lear that China’s monetary policy has been steadily driving stabler and easier.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China’s monetary policy in 2022 from four levels: First, the source of the necessity of easy monetary policy. Second, how to use the tools of easy monetary policy, and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space for cutting the requirements reserve ratio and interest rates. Third, how to open the space of easy monetary policy. Fourth, under the loose tone, how will the RMB exchange rate adjust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 of monetary policy behave. We believe that China’s easy monetary policy in 2022 will be necessary and feasible.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a 1~1.5 percentage point reduction in the requirements reserve ratio. By promoting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interest rates and cutting the requirements reserve ratio, the pressure on the real economy of paying interest can be reduced. However, if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is very great and the real economy needs to be supported with greater efforts similar to that in 2016, the interest rate needs to be reduced by 10~15 base point. We tend to believe that multiple measures of monetary policy are needed to be taken to support the real economy and avoid the rapid rise of China’s macro leverage ratio again.
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 inflation; reserve requirement ratio
(責任編輯:盧艷茹;校對:龍會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