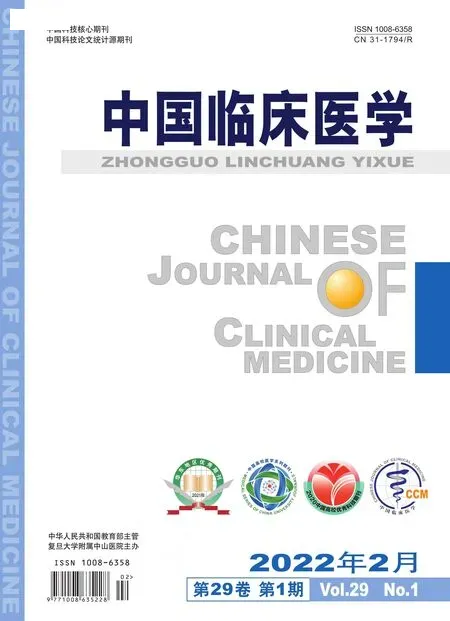肝動脈門靜脈瘺相關肺動脈高壓1例報告
胡昕嬰,王穎穎,張 雯,潘文志,錢菊英*
1.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內科,上海 200032
2.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放射科,上海 200032
3.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介入科,上海 200032
1 病例資料
1.1 病 史患者女性,67歲,1年前無明顯誘因出現登樓后心悸、氣短,無明顯胸悶、胸痛,無咳嗽、咯痰,無頭暈、黑矇等不適。患者于2019年4月15日來院就診,心超示:左房增大,余腔室形態、功能未見明顯異常,肺動脈收縮壓31 mmHg (1 mmHg=0.133 kPa)。2019年5月14日查胸部CT平掃,示:兩肺散在炎癥,左肺上葉結節;肺功能:中度混合性通氣功能障礙,彌散功能降低,支氣管舒張試驗陰性;血D-二聚體0.66 mg/L,心肌肌鈣蛋白T(cTnT) 0.015 ng/mL。2020年患者胸悶、氣短癥狀明顯加重,平地走10余步即有癥狀。患者于2020年8月12日至本院就診,心電圖示:竇性心律,Ⅰ度房室傳導阻滯;心超示:重度肺動脈高壓(肺動脈收縮壓75 mmHg),左房增大,左室射血分數64%。患者為進一步診治入住本院。患病以來,患者精神可,胃納佳,夜間無陣發性呼吸困難,下肢無浮腫,二便正常,體質量無明顯變化。
1.2 既往史患者生長于原籍,否認煙酒史,否認家族遺傳疾病史,父母子女均健康。患者于2003年行乳腺癌切除術。
患者2006年因上消化道出血診斷為肝硬化、門靜脈高壓,否認病毒性肝炎及自身免疫性肝病史,肝硬化病因不明。患者于2008年5月行經頸靜脈肝內門腔靜脈分流術(TIPS)+經皮門靜脈栓塞術+肝動脈-門靜脈瘺栓塞術。患者2008年7月再次出現上消化道出血,于2008年7月至2009年4月先后行肝動脈-門靜脈瘺栓塞術、經TIPS聯合食管下段胃底靜脈曲張栓塞+經皮肝穿刺門靜脈造影術、肝門靜脈支架再通術、胃冠狀靜脈栓塞等手術。
1.3 體格檢查患者神志清晰,精神可,呼吸平穩,血壓141/83 mmHg;全身皮膚無黃染,無紫紺,肝掌(-),蜘蛛痣(-),無貧血貌。患者頸軟,頸靜脈充盈,甲狀腺未及腫大;胸廓無畸形,雙肺叩診為清音,聽診呼吸音清;心前區無隆起,未捫及震顫,心界無明顯擴大,心率78 次/min,律齊,肺動脈瓣第二心音亢進,肺動脈瓣區可聞及Ⅲ級收縮期雜音;腹部平軟,肝脾肋下未觸及,肝腎區無叩擊痛,腸鳴音5次/min;雙下肢無浮腫,神經系統檢查(-)。
1.4 實驗室檢查血常規示三系略低,肝腎功能、凝血功能、甲狀腺功能無明顯異常,cTnT正常,N端腦鈉肽前體(NT-proBNP)603 pg/mL,乙肝表面抗原陰性、丙肝抗體陰性,補體略低,抗核抗體為1∶100(顆粒型),血清淀粉樣蛋白 12.5 mg/L,余自身抗體及風濕免疫相關指標未見明顯異常。動脈血氣分析(未吸氧):pH7.42,二氧化碳分壓33.0 mmHg,氧分壓97.0 mmHg,實際碳酸氫鹽21.4 mmol/L,二氧化碳總量22.4 mmol/L,標準堿剩余(細胞外液)-3.1 mmol/L,標準碳酸氫鹽 23.1 mmol/L,動脈血氧飽和度98.0%。
1.5 影像等輔助檢查2020年7月10日門診腹部增強CT檢查示:肝硬化門脈高壓介入術后,肝動脈-門靜脈瘺,肝臟多發囊腫,脾大。2020年8月12日心電圖檢查示:竇性心率,Ⅰ度房室傳導阻滯。2020年8月29日胸部X線檢查示:兩肺慢性炎癥,心影增大,兩肺門血管影增寬。2020年8月31日心超檢查示:重度肺動脈高壓,肺動脈收縮壓 86 mmHg,左房增大伴輕度二尖瓣反流。2020年9月2日肺動脈CTA檢查示:未見明顯栓子,肺動脈主干及左右分支增寬,肺動脈高壓。
患者入院后行右心漂浮導管檢查(2020年9月2日):患者平臥位,常規消毒鋪巾,1%利多卡因局部麻醉,穿刺左鎖骨下靜脈,置入9F血管鞘,于9F鞘中置入漂浮導管,無創血壓120/75/91 mmHg,氧飽和度94%(未吸氧)。檢查測得上腔靜脈壓10/0/4 mmHg、靜脈血氧飽和度(SvO2)59%,右房上壓12/0/6 mmHg、SvO267%,右房中壓12/3/6 mmHg、SvO278%,右房下壓12/3/7 mmHg、SvO273%,下腔靜脈壓13/8/10 mmHg、SvO272%,右室壓59/2/25 mmHg、SvO272%,肺動脈壓62/17/35 mmHg、SvO271%,肺動脈毛細血管楔壓(PCWP)18/0/9 mmHg、SvO280%。心輸出量(CO)為6.7 L/min,肺血管阻力(PVR)為3.9 wood。漂浮導管放至TIPS分流通道出口時,SvO2為85%。
1.6 本次手術經過患者于2020年9月4日行經皮肝動脈-門靜脈瘺栓塞術。患者仰臥位,常規消毒鋪巾,1%利多卡因局部麻醉,穿刺右側頸靜脈,置入4F豬尾導管,進入肺動脈主干后,測肺動脈壓為59/19/34 mmHg,外周血壓為126/74 mmHg。穿刺左側橈動脈成功后,以4F MPA導管插管至腹腔動脈進行造影,示肝左葉明顯肝動脈-門靜脈瘺,血流由門靜脈經分流道回流至右心房(圖1A)。再插管至腸系膜上動脈進行造影,示肝右動脈起自腸系膜上動脈,肝右葉亦可見少許肝動脈-門靜脈瘺,程度較肝左葉輕。微導管超選擇插管至肝左動脈靶血管支,造影明確導管位置后,考慮患者肝動脈-門靜脈瘺血流較快,選擇以彈簧圈(NESTER)栓塞。引導微導管至靶血管,經導管注入0.018 14 cm×4 mm彈簧圈7枚,0.018 14 cm×6 mm彈簧圈2枚。術后造影示肝左葉肝動脈-門靜脈瘺血流流速較前明顯減慢(圖1B),中心靜脈壓(CVP)為12 cmH2O。

圖1 栓塞前后腹腔動脈造影
1.7 隨 訪患者于術后6周來院回訪,自述活動耐量較術前改善,心率、血壓較前無明顯變化;心超示:中度肺動脈高壓,肺動脈收縮壓62 mmHg,左心房內徑40 mm,余指標與前相似。
2 討 論
2015年歐洲心臟病學會(ESC)肺動脈高壓診療指南[1]將肺動脈高壓的病因分為5類:(1)肺動脈血管壓力升高;(2)左心疾病;(3)肺部疾病和(或)低氧血癥;(4)慢性血栓栓塞性以及其他原因引起的肺動脈阻塞;(5)不明原因和(或)多重因素。其中,肺動脈血管壓力升高的原因較為復雜,除了特異性、遺傳性、藥物或毒物誘導等因素外,結締組織病、HIV感染、門脈高壓、先天性心臟病、血吸蟲病等也會引起肺動脈血管壓力升高。
門脈性肺動脈高壓(PPHTN)在慢性肝病患者中的發生率為2%~5%,在準備接受移植的終末期肝病患者中發生率為5%~10%,而在接受原位肝移植手術的患者中發生率可達16%;PPHTN一般出現于門脈高壓發生后4~7年[2-3]。門脈高壓癥的持續時間越長,PPHTN的發生風險越大[4]。門脈高壓狀態下,內臟血容量超負荷、腸壁充血,易導致內毒素和細胞因子釋放入內臟循環,導致內臟高血流動力狀態[2]。肺血流的增加導致肺血管壁的切應力增加,進而損傷肺血管內皮細胞,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缺氧誘導因子1α(HIF-1α)、HIF-1β等促進血管生成的細胞因子過度表達,同時可出現前列環素/血栓素、一氧化氮/內皮素、促凝物質/纖溶物質等系統失衡,進而引起肺血管重塑,使肺血管阻力增加,導致肺動脈高壓[5-6]。
本例患者經詳細的病史詢問、回顧既往檢查及治療記錄,完善相關血液及影像學檢查,除外左心疾病、肺血管血栓栓塞性疾病、結締組織病等病因,推測其肺動脈高壓與肝硬化門脈高壓史、肝動脈-門靜脈瘺及TIPS術史相關。肝動脈-門靜脈瘺是一種少見的血管畸形,多起源于肝動脈瘤破裂或穿刺損傷,患者常無癥狀,也可引起消化道出血、腹水、高排量性心衰、腹瀉、門脈高壓及肝硬化[7]。患者有相關肝病及介入手術史,且本次入院后右心導管檢查結果雖然顯示其肺動脈壓升高,但肺血管阻力無明顯升高,且導管在TIPS分流通道出口處測得SvO2為85%,明顯高于右心血氧飽和度,提示此處為動靜脈混合血。據此,推測該患者的肺動脈高壓主要由肝動脈-門靜脈瘺血液經TIPS分流通道大量回流至右心所致,尚可逆,說明肝動脈-門靜脈瘺可以作為治療靶點。
患者后續轉至介入科,行左右肝動脈造影,發現多處肝動脈-門靜脈瘺,局部血管扭曲成團狀,其中左肝動脈-門靜脈瘺血流分流量很大、血流速度快,大量肝動脈的血液快速通過瘺道及TIPS分流通道回流至右心房,導致容量性肺動脈高壓發生,故將左側肝動脈-門靜脈瘺作為干預靶點。明膠海綿或彈簧圈栓塞是治療肝動脈-門靜脈瘺的一種安全及有效的方法[8]。本例患者局部血管經彈簧圈栓塞后,肝動脈造影示經門靜脈至下腔靜脈回流至右心房的血流減慢、流量減少,表明手術干預成功。因患者在栓塞術中出現一過性肺動脈痙攣,導致一過性氧飽和度下降,為避免肺動脈再次痙攣,栓塞后未復測術后即刻肺動脈壓力。但患者術后勞力性呼吸困難明顯改善、活動耐量增加。術后6周,患者回訪時訴癥狀持續改善,心超示肺動脈收縮壓62 mmHg,較術前下降約20 mmHg。
由于患者肝動脈-門靜脈瘺為多發,且本身存在不可逆轉的肝硬化及門脈高壓疾病基礎,后續仍可能進展為阻力性肺動脈高壓,故給予患者安立生坦(5 mg/次,1次/d)口服治療,以控制肺血管重構,延緩肺阻力升高,并對患者進行長期密切隨訪,擇期復查心超、肝血管CT及右心導管檢查,觀察肝動脈-門靜脈瘺分流量對肺動脈壓力的動態影響,以期改善患者的生存質量。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