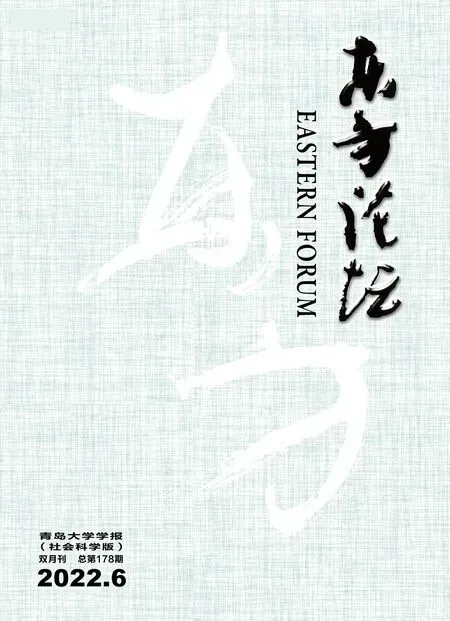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構建
——評馮光廉先生的學術貢獻
李 春 林
遼寧社會科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1
馮光廉是蜚聲學界的學者,在魯迅學、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他的研究既有鮮明的理論建樹,又有細膩的文本分析,可謂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出色結合;同時他又能將自己的學術研究自覺地置于關于民族和人民命運的思考基礎之上,有著濃烈的使命意識與擔當意識,閃現著他所崇敬的魯迅遺風。
一、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理論建樹
馮光廉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所做的貢獻,首先應予提及的是他對這一學科的規劃與命名。
馮光廉于2012年明確提出應以中國現代文學作為學科名稱,廢除現有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名稱。“其目的在于實現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名稱的規范化和協調性。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名稱具有三個最為顯著的功能,能夠解決學科名稱所面臨的困難問題。但對它必須重新進行解釋,賦予它以新的內涵功能。”①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青島:青島出版社,2015年,第631頁。第一,全面涵容功能。從民族上看,它能包括中國各個民族的文學;從地域上看,它包括大陸和臺港澳文學;它包括海外華人文學;包括各階級、階層、黨派的文學。這樣,就有力地糾正了只研究漢民族的、大陸的、以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為主的文學的偏狹。第二,整體貫通功能。“現代”二字可以具有更為廣泛、豐富、深刻的內涵,凡是具有與中國固有傳統不同的新因素,均可稱之“現代性”或者“現代化”的新因素。這樣從縱向上可以向上與十九世紀中期以后具有新質因素的古代(近代)文學相貫通。從橫向上看,又可實現與中國現代文學領域內多種類別樣式相貫通,如中國現代作家寫的古體詩詞、古體散文(以前它們多被排除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視域之外)。而21世紀中國文學也在承續著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文學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仍可涵容在中國現代文學之內。這是縱向上的向下貫通。第三,協調融合功能。通行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名稱是一種并列混合,不能真正實現中國近百年文學的一體化,而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名稱可有效地解決這一難題。事實上,馮光廉的一系列貢獻,均與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正確命名相關。馮光廉和他帶領的青島大學學術團隊,經過初創期十余年(1986—1999年)的拼搏,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這一學科上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三大步:第一步,對近百年中國文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進行系統考察,寫出了三部系列性專著:《中國近代文學研究概論》《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概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概論》;第二步,對中國近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進行再認識,寫出了三部系列性專著:《中國文學現代化的先導——近代文學發展史綱》《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中國當代文學史綱》;第三步,對近百年中國文學的體式流變進行梳理,寫出了五種系列性著作:《中國近百年小說體式流變史》《中國近百年詩歌體式流變史》《中國近百年散文體式流變史》《中國近百年戲劇體式流變史》《中國近百年文學批評體式流變史》。
馮光廉是這一系列著作的總策劃人、總設計師,并且親力親為,直接撰寫了諸多篇章,尤其是許多書的序言與跋,深刻而清晰地闡釋了諸多系列研究的要旨和意義。他為《中國新文學發展史》所寫的《導論》即為典型篇章。《導論》從文學價值觀念、作家關注的主要對象、文學表現形態等幾個角度比較了新文學與舊文學(古代文學)的不同,還從審美角度考察了兩者的相異。認為“中和之美”是我國封建社會最高的審美理想和審美規范,而中國新文學則建立了以崇高美為主要特征的現代審美觀念。多樣悲劇形態的確立,徹底打破了傳統文學的“大團圓”結局,有力地激發人們從“瞞和騙”的大澤中解脫和覺醒。中國傳統文學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喜劇意識,止于滑稽,傷于溢惡;新文學則從社會歷史發展和人的解放的高度對假惡丑進行理性批判,達到對美的肯定。從審美角度考察了新舊文學之不同,應該說具有學術創新意義。更重要的創新是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撰寫提出了一個全新的體例:“以文學主題現象為線索,實行多維角度錯綜交叉,建構新的文學史框架。”①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606頁。馮光廉認為,文學史的發展是由多種內容、多重層面組成的有機統一體,但“創作主題現象占有最為重要、最為突出的地位。因為它是構成文學史的主體和核心的東西,其他則相對地處在從屬的位置”。因之,他要求以此為中軸,“建立全景式的立體化的文學史體系”②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606頁。(這一體例最初是由譚桂林提出的,有很強的創新性意義)。同時,“為了較好地建立以創作現象為中心、多維錯綜的文學史框架”,他還提出了如下幾個基本原則:整體性原則、錯綜性原則、開放性原則。這些原則在全書的撰寫中得到了較好的貫徹。全書的論述每每采用中外古今的比較研究方法,尤令人稱道。在他看來,中國新文學不是一個封閉的自足體,它不僅是中國古代和近代文學的歷史發展,而且它同我國傳統的哲學、政治、社會、倫理、文化、藝術、審美等各種思想觀念存在著無法分割的復雜聯系,因此,它有著對內的縱的開放性;中國新文學又是外國文學催生的結果,它同諸種形態的外國文化文學也有著各種各樣的關聯,因此,它又有著對外的橫的開放性;而中國新文學的許多重要線索和素質,又被中國當代文學所承接,因而新文學又呈現出通向未來的開放性。基于此,該書在論述中國新文學的創作現象叢時,注意闡釋它同中國古代文化和文學、外國文化和文學以及中國當代文學的關系,從而更加清晰地展現出中國新文學全方位(古今中外)開放性網絡系統。如晚明文學革新對“五四”新文學的作用,在以往的文學史著作中提及較少,該書卻給以較為厚重的筆墨,對這一文學革新雖然在明末清初業已中斷卻仍能對“五四”文學革命的先驅者們發生作用,則用晚明文學革新諸種質素“已滲透為民族精神的基因”加以解釋。這表明他關于文學與民族精神之關系的辯證認識,將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視為一體的重要觀點在具體撰寫時得到了較好的體現。對于中國現代文學與外國文化和文學的關系的闡釋,該書也多有自己的開拓。如《野草》所受外國作家的影響,該書在已有的比較研究成果之外,又提出了望·靄覃和愛羅先珂對其的影響,體現出馮光廉所大力主張的學術創新精神。而對于中國新文學各種主題與中國當代文學的關聯的論析,則體現著他的要以歷史研究為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服務的明確意識。
基于馮光廉關于歷史從來不是單一的軌跡或線性連綴的理念,該書極為重視各種文學現象的聯系與互補,中國新文學各個主題群落的通聯與碰撞、互滲與融合。從而使得這部文學史真正成為色彩斑斕而又主調鮮明的立體塑像。全書對中國新文學的理解與把握,思索與評判,昭示出不同凡響的史識與史才。如果說認為啟蒙與救亡兩大主題的對立與統一決定著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走向的解釋有一定新意,那么關于文學為民族復興與強大付出了歷史代價的論述,以階級政治的傾向性和現實主義內在規律二者關系認識的不同作為分野,將毛澤東文藝理論體系與胡風的文藝理論體系置于對峙的格局予以評析,就不獨是史家的見地,而且是史家的膽魄。這部《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乃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這一學術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收獲,其成就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同類著作。學界有人稱之為系繼王瑤本和唐弢本之后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第三個里程碑,可謂實至名歸。
馮光廉為《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寫的總序是又一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理論文獻。該文指出,近百年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雖然取得了諸多積極性成果,但對文學體式的生成演進的歷史過程和經驗規律,尚缺乏系統完整的專門性觀照,研究相當粗疏,所以有必要撰寫專門的文學體式流變史。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的創造性轉化,體裁模式的生成機制,審美特征的全面建構,文體實現現代化、民族化、個性化的途徑和方法,能給文學理論批評學和文體學提供生動的材料和豐富的經驗。馮光廉考慮問題總是出于“經世致用”這一根本目的。至于如何研究,他提出要“開拓視野,打破近代、現代、當代的機械切割,以文學的現代化為中心,實現中國近百年文學研究的一體化”①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625頁。,而這正是他觀照近百年中國文學發展史的基本出發點,與他的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乃是同一步調。顯而易見,所謂“近百年文學”的理念要比已有的試圖打破原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閾限的“20世紀文學”“19—20世紀文學”等提法要更科學、更嚴密一些,具有更廣的視域和更高的視點,于是有了更大的研究格局,更深的理論開辟。他提出的該書的編撰目標是:從大量的創作文本中梳理近百年五種文體(在通識的四種文體之外另加文學批評——這又是一種創新)的流變軌跡,描畫出文體發展的總體性線索和階段性脈絡,從縱向上展現其發展格局;從同中外文學、社會歷史、思想文化的多重關聯中分析近百年五種文體發展的動因、流變的規律和逐漸形成的文體規范,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自覺地站在當代的高度,在反思歷史的基礎上,提出前瞻性的看法,預示文體發展趨勢;以歷史—美學方法為主導,廣泛吸取中外各種研究方法的優長,“力求使研究對象同研究方法達到基本的契合和協調”①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626頁。。事實上,此處是提出了方法論和目的論的同一性問題,同樣有某種理論創新的意義。馮光廉這些理論構建和研究路徑、目的、方法等規定,在書中也都得到了較好的實現。
要之,《中國近百年文學體式流變史》是一重要的學術貢獻。我覺得,馮光廉所主持的三個系列著作儼然形成了一處值得關注的學術景觀,成為治文學史者應去的學術之地。
馮光廉的另一成就則是屬于魯迅學方面。
而今魯迅學早已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就對這一學科的命名與建設而言,其貢獻首先是彭定安關于建立魯迅學的首倡與論證,其次也許就應是張夢陽2002年出版的《中國魯迅學通史》,復次也許就應是馮光廉和劉增人、譚桂林2002年主編出版的百萬字《多維視野中的魯迅》了。馮光廉為此書寫的《導論》(以及其他相關著述)為魯迅學的建設和發展設計和構筑了一個龐大、復雜而又堅實、精妙的理論大廈。
馮光廉首先對魯迅的“革命家”的稱謂進行了辨析。他認為魯迅從整體上說不是從事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的革命家,而是從事文學——文化革命活動的革命家。魯迅的基本特質是“文化巨人”,因而必須從文化的角度來把握和闡釋魯迅。他為這部巨著規定了這樣幾個學術追求:首先是多維視野。魯迅是百科全書式的偉人,他在文化的諸多領域如文化學、哲學、人格學、倫理學、思維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文學創作學、編輯學、批評學、美學、藝術學、語言學、翻譯學、學術史、文化史、歷史學、教育學等理論和實踐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建樹,因之我們的研究也必須“潛心于魯迅在文化領域內的多向開拓,力圖比較全面地闡釋他的多方面的成就”②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70頁。。其次是求異創新。他認為求異創新是學術研究的根本要求和生命所在。基于此,他提出撰稿人必須積極吸收融合有關人文學科的理論成果,對魯迅進行新的闡釋,賦予魯迅研究以新的理論深度和思辨色彩;要借鑒有關人文學科研究方法,開掘過去研究未及之內涵,有所突破和超越,賦予魯迅研究以新鮮感和創造活力;以史的眼光和尺度重新探究魯迅在哪些方面比他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賦予魯迅研究以清晰的歷史感和扎實的可信性,體現史家風范。最后是歷史反思。他重在把握魯迅研究的總體態勢和重要傾向及所存在的主要問題,以此作為我們研究的借鑒和創新的參照。表層上看,這只不過是對該書撰稿人提出的寫作要求,實質上卻是為魯迅學進一步深化所指出的途徑,兼有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意義。尤其是后面對于人文學科理論的吸收與融合,人文研究方法的借鑒與更新,人文學科歷史的審視與定位,人文學科理論、方法、歷史的內在關聯,等等,都昭示出作者廣博的知識,縝密的邏輯,深厚的理論修養,進一步豐富了魯迅學的內涵與外延,為魯迅學豎立了一塊路碑。由于各位撰稿人能夠按照馮光廉提出的要求和設想精心撰寫各自所承擔的部分,可以說全書達到了預定目的。現在,該書業已成為任何一位試圖從事魯迅學研究的學人所不能繞開的峰巒,不認真細讀此書,容易陷于迷茫乃至盲目;不認真體會此書,就難以在魯迅學路上前行。據了解,現在許多開設魯迅研究課的院校多列此書為參考書目,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就魯迅學本身的學科建設而言,彭定安首次提出了魯迅學這一名稱,并寫出了《魯迅學導論》這一專著,可謂魯迅學的第一塊路碑;而馮光廉主持的《多維視野中的魯迅》尤其是他撰寫的導論,以及后來所寫的《改革創新:魯迅精神的靈魂和價值核心——重釋魯迅的總體視角論綱》《魯迅傳寫作應實行三重視角的有機融合》(仰視、平視、俯視)等文,事實上對魯迅學學科的本質、內涵、研究方法與規范、研究成就及前景等項,在彭定安研究的基礎之上又有新的發展和深化,可謂是魯迅學在學科建設方面的又一重要貢獻。
這諸多學術著作的問世,不僅成就了馮光廉本人的學術地位,而且帶出了一批學術骨干、學術新人。這是馮光廉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魯迅學的別一方面的貢獻:培養和壯大了合格的研究主體。
二、探求作家作品真諦,細微處挖掘大精神
馮光廉的大家風姿不獨表現在他能夠構建氣勢恢弘的理論大廈,登高望遠,并且能夠鉆研具體文本,在細微處挖掘大精神,昭示出他對作家乃至讀者的尊重,體現出他治學的堅實嚴謹。
馮光廉是著名的魯迅學學者,他魯迅研究的成績不單體現在他作為學術帶頭人(他先是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組主任,后來系青島大學現代文學學科的創始人和奠基人。他一貫積極提倡學科群體崛起,共生共榮的方略,而不是只埋頭于個人著述),有很強的組織領導能力,曾帶領學術團隊編撰出版了多種著作,而且也表現在他個人的單兵作戰方面。他的專著《魯迅小說研究》是魯迅研究的重要收獲。關于此書,我寫有《魯迅小說研究的開拓與論辯》①李春林:《魯迅小說研究的開拓與論辯》,《社會科學輯刊》1990年第3期。此處不綴。這里重點談談他對魯迅諸多單篇作品的精細研究。
首先談談馮光廉對《阿Q正傳》的研究。《阿Q正傳》是魯迅最重要的作品,由于塑造了阿Q這一具有世界性意義的典型人物而蜚聲于海內外。因之研究《阿Q正傳》的學術成果可謂業已汗牛充棟,有人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魯迅學的分支——阿Q學。馮光廉撰寫的《〈阿Q正傳〉研究之研究》是對阿Q這一形象的核心問題——精神勝利法的實質和成因及超時空性的研究。文章分析了以往各種觀點的得失利弊,認為“把精神勝利法作為一種恒久性的普遍性的社會生命現象來認識,帶有極大的包容性,既包容了過去和現在,也包容了未來;既包容了中國,也包容了外國”①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470頁。。關于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成因,他認為,把精神勝利法視為外在的強大壓力禁錮和摧殘的產物,同從社會的階級和民族壓迫、中華民族的屈辱史,勞動人民反抗斗爭的失敗史,同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影響的觀點,同小生產者生活方式的弱點和局限的觀點,同中國釋老的遁世主義和道家的混世主義的毒害的觀點,都有一致性。前者包容了后者,后者從不同側面補充和豐富了前者。顯而易見,馮光廉對阿Q精神勝利法產生原因的評判語言精煉,內涵豐富,涵容了各家學說②我曾在《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中將精神勝利法的成因歸于“人在主觀上要求能動作用充分發揮的無限性和在實際上實現的有限性的矛盾” (參見李春林:《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5年,第86—87頁),看來亦可包容于馮光廉的觀點中。。他還強調,把精神勝利法當作一種超時空的精神狀態、思想特點、思維方法來看待,并不是忽視各階級、階層、集團、個人之間的差異性,而是包容了這諸多差異。但不能因這種差異性的存在,而否定或忽視精神勝利法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因為這將模糊對人類這一社會生命現象的分析,將會影響對阿Q這一藝術典型的深廣久遠意義的認識,將會妨礙對魯迅創造阿Q這一世界典型的杰出成就的評估,并且容易在方法論上陷入機械論和形而上學的泥淖。”③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471頁。筆者對此深以為是。對世界性的典型的分析,也需世界性的眼光。
關于阿Q的革命問題,學界亦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馮光廉在考察和評析了各家觀點后尤其是作品的具體描寫和魯迅本人對此的說明后,指出了阿Q革命的基本動機及其危害性,盡管他有著參加革命的必然性,但如果“讓阿Q式的革命黨主宰中國的命運,必然造成中國社會的腐敗和黑暗,人民更加遭殃”。魯迅寫阿Q革命的目的乃是為了暴露國民的弱點,而絕非肯定和贊美阿Q的革命。
此外,馮光廉對阿Q思想性格的流變性和統一性的分析,對假洋鬼子形象的階級歸屬既非買辦亦非資產階級,而是地主階級利益的代表和多重意義(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歷史的面影;強化了對辛亥革命妥協性的批判;充實了阿Q的典型環境;深化了阿Q性格的悲劇意義;強化了小說的諷刺意味)的剔挖,對所謂兩種“不準革命”(阿Q不準小D革命和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的辨析,等等,都充滿了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精神,令人讀后很有熱天吃了冰淇淋之感。
馮光廉對中國新文學的奠基作《狂人日記》的研究亦堪稱精湛。《狂人日記》的研究學界歧異很多,但焦點是狂人到底是個什么形象。馮光廉研究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充分注意到魯迅所自言的寫作《狂人日記》之前的準備工作之一是有醫學的知識,于是反復閱讀了不少精神病學著作,以自己學到的醫學知識去考察魯迅依憑醫學知識(以及外國的百來篇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可謂是找對了解剖這一人物形象的武器與途徑。再加上多次親自訪問精神病醫生,獲得了更多的一線相關知識。所以,馮光廉對狂人形象的分析與論斷就有著令人不得不服的征服力。他在用醫學知識對狂人形象進行充分考察和審視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由于魯迅懂得精神病患者的特點,由于他把握了塑造狂人形象的藝術手法(既吸取了果戈理和迦爾洵等的藝術經驗,也有他自己的創造),因而能巧妙地解決病狂的表象和戰士的本質的矛盾,達到了科學和藝術的高度統一,病狂人的特殊言行及心理狀態同戰士的思想特點的有機結合。這結合和統一的奧秘,簡言之,即在于:狂人不是一般的普通的狂人,而原先就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基礎;病狂固然危害了他的精神,但并未從根本上毀掉他的記憶、思維和言語能力;他憑著這些能力,對吃人的問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剖析,對吃人的舊勢力、舊制度、舊傳統進行了更加深刻的揭露和斗爭”①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350頁。。從創作主體的條件和準備,探尋和挖掘創作客體(人物形象)的本質特征,在當時可謂是一種學術創新。而研究者力圖使自己接近創作者的知識儲備,甚至進行帶有田野調查風的相關訪問,亦是一種學術研究在技術層面的創造。
學界曾有多人認為《狂人日記》是魯迅小說創作的總綱(筆者亦如是),甚至幾乎成為公論;馮光廉對此也給予了反駁,他引用了布封的名言,“一個大作家絕不能有一顆印章,在不同作品上都蓋有同一印章,這就暴露出天才的貧乏”②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353頁。。同時指出“總綱論”無助于說明魯迅的偉大,說明他的小說創作的豐富性和獨創性,論者本意在肯定魯迅,贊揚他的小說成就,結果卻事與愿違。
《狂人日記》有三處提到“真的人”。究竟如何理解這“真的人”的涵義,馮光廉也做出了自己的獨到的解說。他首先指出,作品中不同處所提及的“真的人”,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共同之處是不同地方所提及的“真的人”,都是吃人的人和野蠻的人的對立物;不同之處在于,首次出現的“真的人”是一般意義上的“真的人”,后面所說的“真的人”則超越了這類不吃人的普通人,而是具有更高的思想品格和人格特質。“他們思想健美,人格超凡,意志力強,具有遠大的理想,崇高的目標;具有創造美好未來的偉力,是將來理想社會的創造者和主宰者。”“這種超群出眾的‘真的人’是那種不吃人的人的‘真的人’的進一步發展和進化,是臻于至美至善的理想人物。”③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361頁。若是說我們將魯迅所建構的“真的人”視為海上冰山,那么文本表層上“真的人”可能不足冰山的七分之一;而馮光廉則潛入水中,為我們探察出了水中的七分之六甚至更多的美妙與奧秘。讀到他的此種分析,不得不為他的發掘細微的功夫擊節。
此外,在對于狂人的時代的考察,對于“勸轉”描寫的多重意蘊的探究,對于“大哥”的研究,對于小說的現實主義和象征主義的融合的創作方法的論說,對于文白兼用的寓意的剔挖,等等,都頗精湛,許多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該文發表于1976年《山東師院學報 》第1期),具有超前的意義。
在馮光廉的魯迅作品細讀中,總是針對著前此研究中的偏頗與不足,提出自己的新見(他曾說,他的治學方法主要是研究之研究,著重在研究學術界的分歧點,薄弱點,困難點,立一家之言,正體現出他研究的創新性要求,他的大部分論文都充滿論辯性,通過論辯指出以往研究的偏頗和薄弱所在,提出自己的新見。這些論辯性論著,往往充滿學術的激情和自信,具有較強的可讀性和啟發性)。如在《〈自嘲〉研究之研究》中,他針對有人認為該詩“名曰自嘲,實則嘲人”的觀點,經過對作品文本的精細分析,認為詩作其實乃是“自嘲與嘲敵”的巧妙融合。在關于《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的研究中,針對諸多研究者主張將魯迅雜文中的形象與小說戲劇中的典型形象嚴格區別開來,提出要用“‘社會相類型形象’”代替典型形象的情況,馮光廉一方面認為其有一定道理,但又擔心如是說容易損傷魯迅雜文的生動性、動態性、完整性、審美性和象征性的特質(諸“性”都是基于他本人研究《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對其中的“狗”的形象的研究結論),會低估其巨大的文學意義和審美價值。他認為在考察魯迅雜文形象特質的時候,不僅要注意與小說戲劇等敘事性作品所塑造的典型人物的差別,還要注意與概念化的缺少審美價值和社會意義的類型人物的不同。所以他主張在“類型”二字后面加一個“性”字,改稱為“‘社會相’類型性形象”①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430頁。。只增一字,看起來似乎是微觀研究,其實捍衛了魯迅雜文的文學本質,所著意的乃是具有宏觀意義的整體性觀照。馮光廉對《孔乙己》審美風格的論說(“含淚的微笑”),對《吶喊·自序》的悲涼基調的把握,對《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的寫作動機的判定——“絕非是那種起因于心境老化的單純懷舊,亦非是僅僅為了解除生活和創作的勞累,而是他深陷孤寂,卻又不甘心居于其中時的寄托,是他汲取來沖刷自己受傷心靈的圣水”②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510—511頁。。都關涉到魯迅作品和魯迅人生的整體性認識,并且“有助于認識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特征”③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494頁。。他對王統照和臧克家某些作品的研究(如對《山雨》的總體構思和結尾的分析以及所謂王統照思想的局限性的論斷),同樣具有此種風貌。馮光廉的微觀研究,是置于宏觀審視的基礎上,又是為宏觀研究服務的。
魯迅所寫多為“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馮光廉認為,我們應當注意到在這些人物中,魯迅對于每一個具體人物的態度并不相同,“對于祥林嫂的慘劇,魯迅是懷著無比深摯的感情進行描述的,內中灌注的是同情和關懷,哀痛和悲憐,而沒有其他相關作品那樣的批評和激憤。在情感的分寸上,魯迅對祥林嫂這個病態社會不幸的人物,不僅區別于華老栓,就是同愛姑、閏土相比,也有明顯的差異”④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380頁。。注意到同類人物形象的差異,對其“同中求異”,不獨可以進一步彰顯魯迅人物畫廊的豐富與復雜,并且有助于理解和體驗創作主體的豐美及多層次的感情世界,提升我們對文化巨人的認識。
在馮光廉的魯迅研究中,還每每提出關于研究方法的論說。他在對學界對祥林嫂的所謂“反抗性”的錯誤分析的評判中強調說:“除了要全面地、準確地把握魯迅的社會歷史觀和創作觀而外,還要端正我們的研究方法,從主觀夸大、隨意生發的思維方法和學風文風中徹底解放出來。”⑤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378頁。這就點中了某些錯誤觀點產生的另一重要根源。此說不單對魯迅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指導意義,對其他學科亦如是。其所關涉的是整個學界的問題了。
三、以學術研究為民族和人民命運服務
馮光廉曾經說過:“將責任感、使命感和興趣、激情、情懷有機融合起來,互滲互透,也許是學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特質。”⑥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3頁。其實他本人正是這樣一位類型的學者。
通讀馮光廉的學術代表作后,會發現,他從來沒有將學術研究視為僅是一種自我的經院之事,而是有著以此報效人民,為民族的命運和將來服務的明晰的自覺意識。他的魯迅研究,他的中國近百年文學史的建構,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為此服務的。當然這一點與他的主要研究對象魯迅相關聯:作為民族魂的魯迅一生所從事的乃是以文學改造中國國民性進而立人、徹底擺脫為奴的時代,打造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第三樣時代的偉業,因而才吸引了一代又一代魯迅學人。馮光廉是比較典型的一位。我在談及彭定安時曾經說過:“彭先生傾心于魯迅研究,其主要誘因是傾心于魯迅人格,他在魯迅的某些方面、某些側影中觀照到了自己。而在他研讀魯迅的過程中,又自覺不自覺地受到魯迅精神的強勁浸漬,從而形成了他自己的與魯迅相呼應、相溝通的價值取向與人格魅力。”①李春林:《魯迅風骨 托翁情懷——彭定安先生印象》,見王建中編:《超越憂患的求索——彭定安先生學術生涯40周年紀念文集》,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3頁。此語也完全適用于馮光廉。馮光廉的此種品格自然地或顯或隱地蘊含于他所寫的那些文字之中,我們在前面的評介中已經有所涉及。此處我們擬重點提及的是他2014年80歲時對魯迅與孔子關系的研究——《魯迅與孔子研究的另一面》②該文原刊載于《魯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8期,后收入《馮光廉學術自選集》。。
一般說來,孔子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部分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是作為否定性人物視之的。他的那些宣傳封建等級觀念、扼殺個性發展的言論則一直處于被批判的地位。歷代皇權統治者往往也都以孔子學說建構自己專制獨裁統治的合法性。所以,作為反封建戰士的魯迅對孔子多有批判乃是題中應有之義。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魯迅對孔子的某些方面亦不乏肯定之處,也就是說兩者有相通連的地方。既然如此,作為魯迅學者對此有意或無意的忽略,恐怕亦不符合魯迅對民族文化遺產的根本態度,亦不符合建設今天的民族新文化的需要。然而,魯學界對此的研究主導傾向一直是以批判為主或不予置喙的。馮光廉認為:“這兩位文化偉人的精神文化遺產及其影響正同時面對著我們,并且和我們當前及今后面臨的形勢與任務,有著直接而又密切的關系,必須做出恰當的判斷和選擇。”③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132頁。出于建構完整的新文化,并以之為民族更好的命運、人民更好的生活服務的目的,他不顧遭到誤解,勇敢地對魯迅與孔子的關系進行了具有開拓性的正面研究。
馮光廉提出魯迅與孔子的思想有通連性:魯迅的人道精神與孔子的仁愛思想相通,魯迅與孔子的積極入世的行為模式相通,魯迅與孔子對人的道德品格的修養重視相通,并給予較為充分的論證。他認為我們應當擺脫在思想文化主流平臺上出現的魯迅與孔子一來一去、一去一來的二元對立思維的束縛,而是兩者我們同時都需要:我們需要穩定和諧有序與發展改革創新的辯證結合;孔子中庸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和魯迅對中庸之道消極影響的批判,都是有用的思想文化資源。馮光廉還指出了魯迅與孔子比較研究的三個難點:(1)在異同研究的基礎上,將兩人的思想文化進行科學的整合,形成新的思想文化系統和具有實踐意義的總體思路,建構中國文化走向未來和世界的新方案。(2)從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重聯系及長時段中,重新評估兩人的精神文化的價值,對其思想文化遺產的未來前景和歷史命運提出富有遠見卓識的預測。(3)將新的學術研究成果運用到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的改革實踐中去,使其真正健康有效地作用于社會,影響于民眾,使中華文明充滿生機,為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發揮更為巨大的作用。其實這里所指出的乃是魯迅與孔子研究的進展方向和最終目的。同時昭示出馮光廉的魯迅與孔子研究乃是為了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當然隨之中國人就成為世界人。這也就解除了魯迅當年所擔憂的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被擠出的危機。所以,他的這一研究,乃是符合魯迅當年的根本愿景的。然而,馮光廉在作魯迅與孔子的比較研究時,始終對孔子的精神遺產有部分重要內容曾被歷代封建專制統治者所利用這一情況保持著高度警覺,在求同研究中從未忘懷兩者之異。例如,在肯定了孔子的中庸思想的積極因素后,又寫了這樣一段話,“它[按:中庸]一方面包含有豐富的智慧內涵,有利于民族包容和諧寬厚團結精神的形成和發展,有利于提升國民的思想修養,而另一方面在復雜激烈的社會矛盾沖突中又容易被保守勢力所利用,成為維護舊文化舊制度、反對革新創造的工具”①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145頁。。在引用了魯迅對中庸之道的批判后,他接著寫道,“魯迅對現實生活里中庸之道的消極影響和危害性的揭露,對國民病態精神的批判,在當今乃至今后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長久的歷史價值,成為優化民族精神性格,重鑄國民靈魂的銳利武器”②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146頁。。我對這段話特別欣賞,它表明馮光廉的魯迅與孔子的比較研究的根本出發點還是為了更好地重鑄國民靈魂,為了達此目標而對孔子持拿來主義的立場,而絕非被孔子所同化。其內心深處是對民族和人民的大愛。馮光廉對魯迅與孔子的通連性研究,引發了學術界對魯迅與孔子的關系問題的關注。2016年中國魯迅研究會和蘇州大學文學院召開了魯迅與孔子的學術會議,紹興魯迅紀念館也舉行了同樣主題的會議,也許可以視為是對馮光廉論述的一種反響。
馮光廉這種在學術研究中含蘊對民族和人民的大愛,含蘊濃烈的對底層人民大眾尤其是弱者和不幸者的深切關懷的人道主義立場和情懷,在對于某些作品文本的分析中,也一再有所體現。
馮光廉在他研究《藤野先生》的論文中這樣寫道:“魯迅因救國而學醫,又因救民而棄醫從文,顯示出崇高的人格精神。”③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444頁。我覺得此處的行文別有一番深意:由學醫而又棄醫從文,這對于魯迅本人來說乃是實現人生價值的一個重要拐點和上升,通常會將兩者的目的統稱為“救國救民”;但他卻將兩者分說,前者是“救國”,后者是救民。我以為這里絕非僅僅是為了避免行文的重復,而是他認識到了“國”與“民”的不同,“民”是高于“國”的。這樣,魯迅由學醫改學文,就不單是實現目的途徑的上升,而且是目的本身的提升。此處不獨是研究主體的善于發掘研究客體的幽深細微,而且昭示出研究主體本身的深厚情懷:對魯迅的,更是對人民的。
在關于《一件小事》的研究中,馮光廉認為作品的重心是寫我,而非車夫,從而對作品的主題得以準確的概括。針對有人認為老女人的形象十分可惡的觀點,他則指出,老女人從其外觀上即可看出,她是一個經濟狀況十分窘迫的窮苦人,大清早頂著寒風出門,心事急迫。對于她是真受傷還是故意訛人,應從具體情況分析判斷。她年老、體衰,饑寒交迫,被車把輕輕刮倒也會受傷。摔壞后并沒有責怪車夫,也沒有訛車夫。車夫主動承擔責任,“毫不躊躇地攙著她的臂膊,去警察分駐所”④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327頁。,也表明她確乎真的摔傷了。馮光廉認為“如何理解老女人的形象,對她持何種態度和感情,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⑤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328頁。,這關涉到作品的主題和思想意義的歸納和理解。筆者覺得,對老女人形象的道德和價值判斷,事實上乃是一個讀者或研究者的人道主義立場和感情的外化。馮光廉之所以給出此種分析,乃是基于他的鮮明和強烈的人道主義思想和感情,使得他無法對一個不幸的弱者進行道德否定。與此相類似的是對《故鄉》中楊二嫂的評判,他認為魯迅對楊二嫂的批評中仍內蘊有某種同情,“把革命戰士的魯迅理解為鐵石心腸,對楊二嫂之類的受侮辱受損害者深惡痛絕,無情嘲諷鞭撻,是不懂魯迅的寬厚胸懷和人道情感的表現”①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416頁。。在這方面,他對作品人物的理解與評判,可以說乃是基于與作者的共情——博大的人道主義感情。
關于《社戲》在選入中學教材但前半部分被刪的問題,馮光廉很不以為然。因為小說的前后兩部分是緊密聯系、互相作用的。通過前一部分的反襯,既突出了人物形象,又深化了主題思想,還強化了感情力度。被刪的主要理由是教材編者認為前半部分難懂,初中學生難以理解。他對此不予茍同,他不但主觀判斷當下的中學生理解力正在不斷提高,而且進行了大量的客觀調查。學生們反映說:“小說的頭一部分內容并不難懂,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實際上我們課外讀的東西比這篇長多了,難多了……”②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395頁。這不獨是對魯迅作品的負責,也是對學生(接受者)的負責,是基于對他們的深愛。馮光廉寫有多篇關于中學課本魯迅作品教學問題的文章,最有代表性的一篇當是《中學語文課本魯迅作品選篇與編排問題之切磋》。這些文章表面上是給編者和教師看的,其實在學理性探討的后面,卻是他對孩子們的眷眷之心,唯恐他們不能很好的理解魯迅,甚至理解得錯誤,從而影響了他們的思想和精神的成長。他還多次深入教學一線同教師和學生共同探討。他的此種舉措,令人想起錢理群的所作所為。他們同樣將幫助學生們正確理解和接受魯迅,作為自己的使命和擔當的一部分。他們是魯迅的“救救孩子”和“立人”偉大工程的賡續者。
對于馮光廉而言,此種使命和擔當還突出地表現在他對研究生的培養方面。1985年,他在時任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崔西璐同志的支持下,排除了多年存在的學術限制,使山東師大現代文學教研組正式獲得了招收研究生的資格。以后,馮光廉便指導譚桂林、魏建等十幾名研究生共同撰寫了《現代作家研究述評》一書,以《山東師大學報(增刊)》名義發行三千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著名學者樊駿先生曾兩次給馮光廉來信,高度評價這一做法,認為這是一個創舉,希望能夠繼續做下去,搞出一整套系統的研究書系,為研究生提供學術研究的入門之作。可惜由于他很快調往當時新成立的青島大學任教任職,未能實現樊駿先生的構想和重托,對此,他深表歉意。
馮光廉為年輕學者寫的幾篇序,他對大學生的學習生活的關心和指導[如《試讓青春多收獲——與文科大學生談學習和研究》,該書河南大學出版社出版時,將書名改為《挑戰自我——與大學生談怎樣學習》。該書由馮光廉講述,叢桂芹(即叢綠)整理。他還主編了《文科研究生治學導論》等],也都體現著他自覺地以自己的工作為民族和人民命運服務的使命意識和擔當意識。有學者稱馮光廉為教育家,我以為也是非常恰當的。他認為把大學生研究生培養好教育好,有助于他們及其家長命運的改善,這同樣體現出他的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
我覺得,馮光廉學術成就的取得,第一,在于他能夠堅定地站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熟練地運用其方法,對豐富復雜的文學現象進行深入分析考察。他的強烈的創新意識,犀利的“求異思維”,都與此相關。而高屋建瓴的恢弘氣勢,也是以此為底氣;發掘細微的力透紙背,也是以此為前導。所以各項成果均能經受住歷史的考驗,不會成為過眼云煙。第二,這歸功于他的生命意識和價值取向。他說:“我以為,體會治學的快樂,是治學的需要,也是人生的需要。因為尋求快樂,通過艱苦的跋涉而得到快樂,應該是人類永恒的精神追求。”①馮光廉:《馮光廉學術自選集》,第740頁。他的生命業已與治學緊密地膠結于一體,所以能夠長期堅持,鍥而不舍。第三,這與他高尚的道德情操亦分不開。他在人際交往中有著根深蒂固的平等意識和寬厚精神。他曾先后帶領著其學術團隊,共同完成多個學術成果。在其中,他既要求每位撰稿人要按照既定的要求寫作,同時又充分尊重每個人的學術個性。這也是一種和而不同吧!所以那些大部頭的碩果,我們讀起來既可以感受到百花般的燦爛,又能夠領略到整體的和諧輝煌。
要之,馮光廉建構的不單單是系列性著作,而且還是一支稟賦正確的科研立場,有明確的科研目的,厚實的科研素質,良好的科研道德的后繼有人的科研隊伍。這同樣是一種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