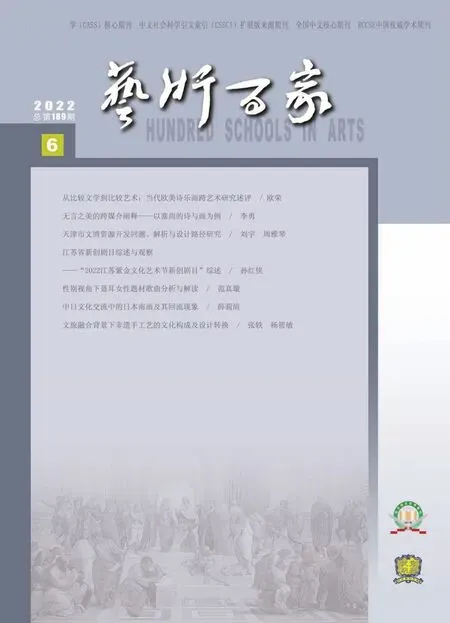從比較文學到比較藝術:當代歐美詩樂畫跨藝術研究述評*
歐 榮
(杭州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浙江 杭州 311121)
詩畫關系研究在歐美素有傳統,其源頭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和萊辛的《拉奧孔》。①文學與音樂關系研究則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興起,成為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進而被音樂學界借鑒,拓展為詩畫樂跨藝術研究,在歐美學界甚為興盛②。
美國學者卡文·布朗(Calvin S.Brown,1909—1989)發表的《音樂與文學比較研究》(MusicandLiterature: ComparisonoftheArts,1948)可謂此領域的系統性開山之作。布朗在探討音樂與文學之間的共性以及二者在聲樂中的合作之后,深入分析現代主義文學對音樂藝術手法的借鑒,也論證了文學對標題音樂和敘事性音樂的影響。其后,布朗又在《語中曲:樂化詩研究》(ToneintoWords:MusicalCompositionsas SubjectsofPoetry,1953)中分類深入分析了詩歌對音樂的諸多借鑒和轉換。在此基礎上,布朗提出:
比較文學承認,一切藝術盡管使用的媒介和手法不同,但卻是相似的活動,它們之間不僅會由于不同時代精神的影響而表現出相似之處,而且常常有直接的相互影響。并非所有這些關系都屬于比較文學學者的領域。例如,巴洛克建筑和巴洛克音樂之間的相似之處就超出了他的研究范疇。但是文學與其他藝術的關系是其領域的一部分,即便只涉及一個國家,我們通常也將其視為比較文學的一部分。[1]75-113
布朗也因此成為美國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先行者。隨著比較文學美國學派的興起,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LA)在跨學科研究分會下設立了“文學與其他藝術”研究小組③,在20世紀下半葉分別出版了《文學研究的關系》(RelationsofLiteraryStudy: Essayson InterdisciplinaryContributions,1967)以及《文學的相互關系》(InterrelationsofLiterature,1982)兩本論文集,兩本論文集都收錄了論及文樂關系的文章。④1970年美國比較文學界的權威期刊《比較文學》(ComparativeLiterature)第2 期推出“文學與音樂研究”專刊,布朗撰文將文樂關系作為新興的研究領域,他甚至將比較文學界定為“至少涉及兩種不同表達媒介的文學研究”⑤。1986年布朗在《音樂與文學比較研究》再版前言中總結了文樂關系的研究成果,梳理了文樂關系研究的學術動態,并預見此研究領域仍方興未艾。新世紀前后,卡文·布朗因其長達半個世紀的開拓之功被烏爾利希·韋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等人尊奉為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精神導師”。[2]ix
自20世紀80年代起,文學與音樂研究的學術研討會相繼召開。1988年美國達特茅斯學院舉辦主題為“音樂與語言藝術:交叉研究”的研討會。1990年奧地利格拉茨大學舉辦“音樂—文學體裁的語義學研究”會議。1995年瑞典隆德大學的“跨藝術研究”國際研討會中設有“音樂與其他藝術對話”的分議題。1997年格拉茨大學召開首屆“語言與音樂研究”國際研討會,探討和確立該領域的研究范疇、研究重心、研究目標、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等;會議期間成立了語言與音樂國際研究學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Word and Music Studies ,簡稱WMA),學會提倡跨越文化邊界,拓展學科范疇,致力于文學/語言文本與音樂互動關系的研究,為音樂學家和文學研究者提供跨媒介研究的交流平臺。學會成立后每兩年舉辦一次學術會議,至2019年在歐美和澳大利亞共舉辦了12 屆雙年會,出版會議集刊18 部,成果豐碩,在歐美影響很大。⑥
概括而言,在歐美學界,史蒂芬·舍爾(Steven Paul Scher)關注“文學中的音樂”,勞倫斯·克萊默(Laurence Kramer)建構“音樂闡釋學”,克盧弗(Claus Clüver)、潘惜蘭(Siglind Bruhn) 和莉迪亞·戈爾(Lydia Goehr )拓展“藝格符換”詩學,奧爾布賴特(Daniel Albright)提倡“泛美學研究”:這些學者的努力都對詩畫樂跨藝術研究起到了開拓和推動作用。
一、文學與音樂
語言與音樂國際研究學會的創立者之一,德國學者史蒂芬·舍爾是文學與音樂研究重要的開拓者。他把音樂和文學的關系劃分為三種類型:“音樂和文學”(music and literature),“音樂中的文學”(literature in music)以及“文學中的音樂”(music in literature)。傳統音樂學主要研究“音樂和文學”(如聲樂)、“音樂中的文學”(如歌劇)以及音樂傳記,而他則關注“文學中的音樂”。⑦
他在《德國文學中的語繪音樂》(VerbalMusicin GermanLiterature,1968)一書中區分了三類“文學中的音樂”:“語繪音樂”(verbal music)、“諧聲音樂”(word music)以及“對音樂結構或表現手法的文學改寫”(如文學作品采用奏鳴曲、賦格、回旋曲形式等)。他對前兩個概念又進行了辨析:
所謂“語繪音樂”,我是指對真實或虛構的音樂作品在詩歌或散文中的文學性再現,即任何有樂曲作為“主旋律”的詩意文本。除了對樂曲的描述,此類文學作品還常暗含著對音樂表演的描繪或人物對音樂的主觀感受。語繪音樂偶爾會營造擬聲的效果,但明顯有別于“諧聲音樂”,后者完全是對聲音的文學性摹仿。[3]8
舍爾尤其關注文學中的“語繪音樂”。在《語繪音樂理論札記》(NotestowardaTheoryofVerbalMusic,1970)一文中,舍爾勾勒了一幅文樂關系圖(圖1),明確語繪音樂的特殊性,其創作意圖“主要為了詩意性地傳達音樂的思想情感內涵或隱含的象征性內容,而非為了肖似樂音或摹仿音樂形式”。他進而區分兩種基本的語繪音樂形式:在第一種形式中,詩人以直接的音樂經歷或加上自己對樂曲的了解為創作來源,描述他能聽出的音樂或推測的音樂,這就是“在語詞中再現音樂”(re-presentation of music in words)。在第二種形式中,詩人雖然受到了音樂的啟發,但其想象是主要的創作來源,這就是“在語詞中直接呈現虛構音樂”(direct presentation of fictitious music in words),詩人創造了“一首語詞之樂”(a verbal piece of music)。[4]151-152

圖1 舍爾的文學與音樂關系圖[4]151
論及語繪音樂的功能,尤其是敘事文學中的音樂插段時,舍爾認為:有效的語繪音樂植根于敘事語境,同時又能激發時空的交融感,因此成功的語繪音樂作家應該能巧妙地融合空間和時間的認知原則,以達到一定程度的共時性,最終創造近似(三維)圖像藝術媒介的效果,同時又超越任何單一藝術形式的審美和認知特性的局限。[4]155以英國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小說《針鋒相對》(PointCounter Point)中的音樂晚會場景為例,舍爾指出,赫胥黎將一次音樂體驗插述為小說敘事序列中一個意義非凡的時刻,作者通過對樂曲的闡釋性描述營造了一個多維時空印象,在之后的情節發展中,這個樂段不斷復現,并與小說人物的精神和情感產生交融,豐富了作品的藝術效果。
德國學者吉爾(Albert Gier)在舍爾的分類基礎上提出文樂關系的第四種類型,即“作為音樂的語言”(language as music),并從語義學的角度分析“文學中的音樂”:在“語繪音樂”中,音樂作為能指;在“諧聲音樂”中,音樂作為符號;在文學性音樂結構與技巧中,音樂作為所指。[5]61-92
舍爾和吉爾從文學本位的立場研究文樂關系,勞倫斯·克萊默則從“新音樂學”(New Musicology)的立場研究文樂關系,倡導文化研究視域下的“音樂闡釋學”(musical hermeneutics)。他在專著《音樂與詩歌:19世紀及之后》(MusicandPoetry: TheNineteenth CenturyandAfter,1984)中對歐美19世紀以降的非戲劇音樂(器樂、歌曲)和抒情詩進行平行比較研究。克萊默首先闡明詩樂關系研究的可行性:“我們盛贊樂中有詩,詩中有樂;作曲家創作音詩(tone poem),詩人寫作序曲和夜曲。尤為重要的是,這兩種藝術很獨特,都有賴于以即時和有形的方式處理時間的流逝。就此而言,二者的結構性基礎是相同的。”[6]4克萊默由此提出:“一首詩和一支樂曲可能會在結構性節奏(structural rhythm)上趨同:一種共同的延展模式可以作為二者顯性維度的闡釋框架。”[6]10以19世紀為分界點,克萊默認為此前的詩樂結尾是一種“話語模式”(discursive models),二者的結構性節奏趨于連貫的“陳述”,使得這兩種藝術個性鮮明,無法相融;而19世紀之后的詩樂結尾是一種“意識模式”(consciousness models),但這種意識模式并沒有取代“話語結構”,而是在其之上疊加了基于意識模式的結構性節奏,作為話語結構的副文本,克萊默稱之為“宣泄節奏”(cathectic rhythm)并提出,19世紀之后以浪漫主義為代表的詩樂作品通過“宣泄節奏”的疏導,趨于融通。[6]17-21以此為主線,克萊默對貝多芬的音樂與華茲華斯的詩歌、肖邦的作品與雪萊的詩作、查爾斯·艾夫斯(Charles Edward Ives)的樂曲與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詩歌以及貝多芬、勃拉姆斯等音樂作品中的歌曲進行了細致的比較分析。
此后,他在《危險的聯系:音樂批評中的文學文本》(DangerousLiaisons: TheLiteraryTextinMusical Criticism,1989)一文中提出了“音樂詩學”(melopoetics)的概念,用來指代音樂/文學批評[7]159,并在文中闡明建構音樂詩學的可能性、音樂詩學研究方法和研究意義。這一概念被舍爾所接受和應用,并在十年之后,對歐美“音樂詩學” 的發展進行了回顧和展望。[8]18-19
在《作為文化實踐的音樂》(MusicasCultural Practice,1990)一書中,克萊默反對純音樂的看法,堅持認為所有的音樂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本音樂”(texted music),音樂也是文本生產的文化活動,與同時代的文化實踐息息相關。因此他提出,“解讀一個寫作文本與解讀一部音樂作品可以說沒有本質的區別”,并總結了進行音樂闡釋的各種條件:
(1)作曲家提供了語言線索;
(2)音樂文本或語言文本(或二者兼有)中包含引用或指涉,以此建構超出樂曲本身的語境;
(3)音樂結構本身以“圖畫”或“象征符號”的方式言說,在特定的歷史框架下或身處特定文化語境的闡釋者中,引發普遍性的共同反應和理解。[9]1-20
克萊默力圖找到文學批評與音樂學的交界面,以便進行更廣泛的文化批評。由此,克萊默將“音樂闡釋學”定位于“與非音樂研究領域互有助益的一項跨學科研究”,他覺得在文化語境中理解音樂創作還不夠,還可以把音樂理解為“一種文化行動”(a cultural agency),即“作為話語和表征實踐的參與者,而非僅僅是其鏡像”。[10]269-270
總之,勞倫斯·克萊默通過音樂與文學關系研究,建構了一套跨藝術批評話語,確立了音樂敘事以及音樂與文化批評的范例。作為詩人兼作曲家的詩樂研究者,克萊默的分析和論證極具專業性和啟發性,在歐美學界產生重大影響。
二、藝格符換:詩畫樂的跨藝術轉換
美國比較文學學者克勞斯·克盧弗把原本用于詩畫關系研究的“藝格符換”(ekphrasis)的概念延伸到詩歌與音樂研究。⑧他在論文《藝格符換再探:非語言文本的語言再現》(EkphrasisReconsidered: OnVerbalRepresentationsofNon-VerbalTexts,1997)中以葡萄牙詩人喬治·德塞納(Jorge de Sena)的兩部詩集為例,批評赫弗南(James Heffernan)對“藝格符換”的界定——“視覺表征之語言再現”(verbal representation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11]3——太過局限,僅涉及從視覺藝術到語言藝術的轉換。
德塞納的詩集《變形集》(Metamorphose,1963)由19 首有關雕塑、繪畫、照片和建筑內觀的詩作組成。第二部詩集《音樂藝術》(ArtedeMúsica,1968)有34 首關于音樂主題的詩作,副標題是“32 首音樂變形和序曲,集錦和作者后記”。根據赫弗南對藝格符換的界定,塞納《變形集》中兩首有關建筑的詩作以及第二部詩集就被排除出藝格符換之列。而克盧弗想做的正是拓展藝格符換的概念。通過文本細讀,克拉夫發現第一部詩集中有關建筑內觀的詩作在語調、技巧、闡釋和思考方式上與其他詩作沒有明顯不同,詩集中還有關于面具和飛行器的詩,雖然描繪對象并非藝術品(赫弗南所謂的“視覺表征”),但“我們把它當作藝格符換來讀”[12]26。第二部詩集的創作宗旨與第一部詩集一脈相承,克盧弗也視之為藝格符換詩。他由此推出自己的界定:“藝格符換是對一個由非語言符號系統構成的真實或虛構文本的語言轉換”(Ekphrasis is the verbal representation of a real or fictious text composed in a non-verbal sigh system.),并補充說明該定義中的“文本”(text)為符號學中所指,“包括建筑、純音樂和非敘事性舞蹈”[12]26。
克盧弗認為這個定義可以把舞蹈和音樂等非視覺文本納入其中,與藝格符換的傳統分離,以此拒絕對“藝術”文本和非藝術文本加以區分。他相信自己的論證將把藝格符換研究從關注表征模式的話語轉變為有關再現、重寫、轉換或曰“變形”的話語。克盧弗對藝格符換的定義加以延伸并把“音樂詩”(musikgedicht)作為一種藝格符換,在此基礎上,潘惜蘭提出了“音樂藝格符換”的概念,并加以深入系統的研究。
德裔美國學者潘惜蘭在跨藝術音樂學領域卓有成就。她參加了1995年在瑞典舉行的“跨藝術研究”國際研討會,受赫弗南和克盧弗的啟發,提出了“音樂藝格符換”(musical ekphrasis)的概念,并以此解讀了法國作曲家拉威爾(Maurice Ravel)的鋼琴獨奏曲《水妖》(Ondine)。這支樂曲是拉威爾的鋼琴獨奏曲《夜之幽靈》(Gasparddelanuit,1908)三首標題樂曲中的第一首,其余兩首分別為《絞刑架》(LeGi-bet)與《幻影》(Scarbo)。這部作品是拉威爾受法國詩人貝特朗(Aloysius Bertrand)的散文詩集《夜之幽靈》中的三首詩觸發而譜就,作曲家也通過樂曲的副標題“仿自阿洛伊修斯·貝特朗的三首鋼琴詩”(Trois poèmes pour piano d'après Aloysius Bertrand)向詩人致敬。鑒于赫弗南把“藝格符換”界定為“視覺表征之語言再現”,潘惜蘭用“音樂藝格符換”指“語言表征之音樂再現”(musical representation of a verbal representation)。[13]48
潘惜蘭在專著《音樂藝格符換》(MusicalEkphrasis:ComposersRespondingtoPoetryandPainting,2000)中對此作出更為系統和全面的研究。她借鑒了瑞典跨藝術研究學者漢斯·倫德的研究范式⑨,把詩畫與音樂的關系分為組合型(poems or paintings and music,如為詩譜曲或創作歌劇)、融合型(poems or paintings in music,如樂譜的視覺排列方式可以暗示所描繪的對象)以及轉換型(poems or paintings into music),并強調音樂藝格符換屬于轉換型作品,即“化為音樂的詩或畫”是她的研究重心。其音樂藝格符換與其關聯領域及支撐性美學理論之間的關系見圖2:

圖2 潘惜蘭的音樂藝格符換、關聯領域及相關美學理論[14]xvii
潘惜蘭分析了藝格符換音樂與標題音樂的異同。二者都是器樂形式,具有明確的指涉、敘事或圖像構思,二者都曾被稱為“說明性”或“再現性”音樂,常被混為一談。但潘惜蘭強調二者有著本質的不同。她借鑒文學批評中對“藝格符換”與“語畫”(word painting)的區分,明確區分的焦點是作品再現的是何人的虛構現實。標題音樂“敘述、描畫、暗示或再現源于作曲家自己頭腦中的場景或故事(事件或人物),這些場景或故事可能真實存在,也可能純粹出于想象”;這個術語的應用非常寬泛,包括“傳記式構思或與自然和宇宙相關的情感表達”,或者對歷史文學人物的塑造,以及用音樂表達對世界的哲學性思考等等。[14]28-29而音樂藝格符換“敘述或描繪的虛構現實是作曲家之外的一個藝術家(一個畫家或詩人)創造的;而且,音樂藝格符換通常不僅與詩意或視覺性虛構現實的內容相關,而且與其內容表達的形式和風格相關”,如勛伯格(Arnold Sch?nberg)基于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劇作《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Pelleas undMelisande)而創作的同名交響詩,再如李斯特取材德國畫家考爾巴赫(Wilhelm von Kaulbach)的壁畫而創作的交響詩《匈奴大戰》 (DieHunnenschlach)等。[14]29
在《繪畫音樂會》(AConcertofPaintings:“MusicalEkphrasis”intheTwentiethCentury,2001)一文中她再次提請學界關注音樂家的跨藝術創作:
詩人可以憑借語言媒介的創造性對視覺藝術品做出反應,把摹本的風格、結構、意義和隱喻從視覺轉換為語言;在本世紀,越來越多的作曲家也致力于探索這種跨藝術模式的轉換。音樂媒介看似抽象,但作曲家就像詩人一樣,能以多種方式對視覺表征作出反應。[15]551
文中,潘惜蘭把“音樂藝格符換”的概念延伸,指“語言表征或視覺表征之音樂再現”(musical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representation or visual representation),即“轉化為音樂的一首詩或一幅畫”(a poem or painting being transformed into music),如勛伯格的《佩利亞斯與梅麗桑德》和意大利作曲家雷斯庇基(Ottorino Respighi)為小樂隊創作的《波提切利的三幅畫》(Tritticobotticelliano)等。[15]566-572
借鑒文學性藝格符換批評的邏輯,潘惜蘭把音樂藝格符換分成五種方式:移位(Transposition)、補充(Supplementation)、聯想(Association)、闡釋(Interpretation)以及游戲(Play)。潘惜蘭以三組基于視覺藝術的交響樂作品為范本,分析了音樂藝格符換的各種手法。這三組音樂作品的藍本分別是意大利畫家波提切利的三幅畫、俄羅斯藝術家馬克·夏加爾(Marc Chagall) 的《耶路撒冷之窗》 (TheJerusalemWindows)⑩以及德國藝術家保羅·克利的畫作《機器啁啾》(TheTwitteringMachine)。如雷斯庇基在對波提切利畫作的音樂詮釋中充分利用了音樂語言所具備的全部描繪手段,如使用擬聲、借用文藝復興時期的舞曲、摘引贊美春天的行吟詩等。
潘惜蘭進一步指出,“真實或假想的音樂摘引(musical quotations)構成作曲家指涉被轉換原作的各種手段”,“所有的音樂參數(音高、音程、和聲、節奏、音步、節奏、音色、質感、結構)都可用來摘引現有音樂材料,或指涉已知的音樂體裁、與音樂有關的情況或音樂中其他意味深長的內容”;就音樂作品與原初藝術品的關系而言,“一個音樂實體并非作為一個符號,而是作為一個信號而存在”;潘惜蘭在此引用蘇珊·朗格(Susan Langer)對“信號”和“符號”的界定:“當一個信號能讓我們注意到它所顯示的對象或情境,它就能被理解了。而一個符號只有當我們能想象它所表征的思想,它才會被理解。”[15]582
在潘惜蘭之后,美國學者莉迪亞·戈爾(Lydia Goehr)遵循音樂哲學的邏輯把藝格符換納入研究視野。她對比分析了兩種藝格符換觀念:古代的藝格符換以描述為主,現代的藝格符換體現為從甲文本到乙文本的轉換,暗含不同藝術之間的競爭。[16]389通常的觀點認為,藝格符換通過語言在受眾心目中產生形象,而音樂既非通過語言也非通過形象進行交流,因而二者之間沒有交集。戈爾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需要對藝格符換的概念進行修訂和拓展。她的論證邏輯如下:
古代和現代的觀點都關注語詞媒介為何能化為圖畫—視覺—形象制造媒介而運作與交流。然后,當我們將藝格符換與新興的藝術相關聯,上述問題就被另一個問題所遮蔽:一件藝術品,其媒介為何,能否把另一件藝術品帶至審美性在場(aesthetic presence)。一開始的問題是:語詞,就像一首史詩或描述性文字,能否把形象,就像我們在畫中所見,呈現在受眾的心目中? 接著,問題就變為:一首詩能否起到一幅畫的作用?最后,問題變為:一件藝術品能否達到另一件藝術品的目的或效果? 隨著關注點轉向互為關聯的藝術品,媒介的特殊性就被弱化。如果一首詩能使一幅畫在場,為什么一幅畫不能使一首詩在場? 或一首音樂作品不能使一幅畫、一首詩或一件雕塑再現呢?[16]398
她認為在以下兩種情形中,音樂和藝格符換聯手:其一,語言對音樂形象或場景的生動描述使之在聽者/讀者的心目中呈現,戈爾稱之為“語言性音樂藝格符換”(verbal musical ekphrasis),這與古代藝格符換概念相關(相當于舍爾所謂的“語繪音樂”);其二,“對一首詩、一幅畫或一件雕塑品的音樂性再現”,這也是“音樂藝格符換”,對應著現代藝格符換的內涵(相當于潘惜蘭理解的“音樂藝格符換”)。[16]389戈爾融匯古今,擴充了“音樂藝格符換”的外延和闡釋力度,以此挑戰兩種看法,一種過于關注媒介和藝術品問題,另一種視音樂獨立于其他藝術;戈爾提出,藝格符換“不僅與音樂相關,而且與所有藝術或者說任何一種藝術相關”。[16]389-390戈爾剖析了音樂藝格符換的心理機制:通過傾聽,聽眾的大腦發生變化,“仿佛達到聯覺—聯知的匯通狀態”(an as if total synaesthetic-syncognitive sense)。[16]395
除了常見的“從作品A 到作品B 的藝格符換”(work-to-work ekphrasis),戈爾還分析了發生在作品內部的“瞬時藝格符換”(momentary ekphrasis),如在許多歌劇中的某一刻,雕像有了生命,或人物從畫框中走出。戈爾認為:
將藝格符換的概念超越從作品A 到作品B 的認識,彰顯了藝術之間的競爭,也讓我們看到不同藝術出于不同的原因如何運用藝格符換策略,有時用來闡明另一件藝術作品,有時則用來創造一個動態的、戲劇性虛擬空間,從而使得言說與展現、隱蔽與揭示之間的所有張力在這個空間內得以上演。[16]409-410
潘惜蘭把本屬于詩畫關系研究的藝格符換概念引入音樂學領域,獨創音樂藝格符換一說,而莉迪亞則把音樂藝格符換又拉回文學研究領域。
三、繆斯之藝:泛美學研究
美國學者奧爾布賴特(Daniel Albright)是現代主義和比較藝術研究領域的杰出學者,他的學術生涯反映了歐美跨藝術、跨學科研究的興起與發展。他在《解開盤蛇》(UntwistingtheSerpent:ModernisminMusic,Literature,andOtherArts,2000)中發掘現代主義的跨藝術實踐,揭示現代主義者許多最重要的藝術實驗都是與其他藝術合作的結果,如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春之祭》(TheRiteofSpring)是芭蕾舞劇,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四圣三幕劇》(Four SaintsinThreeActs)是歌劇,畢加索把立體主義繪畫用于芭蕾舞劇《游行》(Parade)的服裝設計。有學者盛贊他“用現代主義的詞匯極具原創性地重寫了萊辛的《拉奧孔》”。?
在《現代主義與音樂資源選編》(Modernismand Music:An AnthologyofSources,2004)中,奧氏提出,在歐洲早期歷史上,音樂似乎滯后于其他藝術門類的發展,而在現代主義時期,音樂可謂充當了藝術實驗的先鋒。此書選編了這一時期的很多代表性文本,既包括作曲家和樂評人的重要聲明,也有詩人、小說家、哲學家等人有關音樂的評論和隨想,奧氏的相關評注和釋讀深入詳盡地闡釋了現代主義音樂發展的思想和文化語境,為跨藝術音樂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新范式。
奧氏的《繆斯之藝:泛美學研究》(Panesthetics:OntheUnityandDiversityoftheArts,2014,以下簡稱《泛美學》)從哲學的理論高度,結合文學、繪畫、音樂作品的批評實踐考察藝術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是其學術扛鼎之作,有學者高度肯定了這部論著對拓展文學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17]106。他去世后出版的《現代主義薈萃》(PuttingModernismTogether: Literature,Music,andPainting,1872—1927,2017),又一次從跨藝術詩學的視角揭示現代主義文學、音樂和繪畫領域藝術創新的內在關聯與獨立共存,這是他留給學界的寶貴遺產。?
《泛美學》 的中心議題是:藝術是“一” 還是“多”? 即藝術的統一性和多樣性的問題。奧氏的回答是,藝術既是“一”也是“多”。著作導言的標題為“繆斯之藝”(Mousike)。奧氏采用語文學的研究方法,將歐洲多國語言中的“音樂”一詞(如英語music、法語 musique 等) 追溯到希臘詞源“μουσικη,mousike”。希臘詞源并不專指“音樂”,而是與“繆斯”(Muse)一詞相關,指代任何與繆斯女神們相聯系的事物,“不僅包括音樂,還包括舞蹈、啞劇、史詩、抒情詩、歷史、喜劇、悲劇,甚至天文學”。[18]1這反映了古希臘人早期的藝術統一觀。
但從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開始,西方又產生了藝術分離派的傳統,由此奧氏引出了比較藝術學最基本的問題:藝術是“一”,還是“多”? 在奧氏看來,“藝術自身并沒有力量聚合或分離——它們既非一也非多,卻很樂意根據藝術家或思想家的愿望,呈現出整一或多樣的形態”,因此,他“要考察不同藝術媒介之間的相互作用——它們有時親密合作,有時侵入彼此的領地,有時則會發生不和諧的沖突”。[18]3-4
首先,在探討“什么是音樂?”時,奧氏開篇即觸及有關音樂本質的爭議性問題:“音樂是否有表現力?”肯定派以瓦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為代表,否定派尤以愛德華·漢斯立克(Eduard Hanslick)為代表。奧氏對此表現出中庸之道:“不過正如繪畫的本質既非具象也非抽象一般,音樂的本質既不是有表現力的,亦不是無表現力的。有無表現力不是音樂的本質特性,只是音樂發展中的兩個標準矩,但在闡釋一支樂曲時,這些概念便于我們討論音樂的表現節奏——它如何展現自己,接著又如何減弱或是消失的。”[18]148奧氏深入分析了音樂的語言特征以及非語言特征。一方面,“音樂——器樂——具有語言特征,仿佛它能把(真實或想象的)文本轉換成無言的聲音;然而,它同時抵制任何語言特征,甚至把自己說成是不能表達任何事物的反語言”[18]161。另一方面,當音樂試圖逃離語言時,語言則趨向于音樂,“所以我們就陷入了悖論:我們越是想把音樂理解為一種語言,它就越強烈地抵制這種理解;我們越是試圖把音樂理解成語言的對立面,它就越是悅耳、有力、直白地對著我們的耳朵說話。只有當我們不再試圖去聽懂海妖塞壬的歌聲時,我們才能理解它。”[18]173
其次,奧氏探討了音樂的敘事性問題。他指出:“每一門藝術都有自己的敘述學。文學擅長講故事,也擅長解釋它是如何講故事的。音樂也同樣善于講故事,這不僅體現在交響詩中,而且體現在構成主題和變奏的樂章中。”[18]196他堅持認為音樂是一種敘事,“而它所敘述的,嚴格來說并非聽眾的奇思怪想,而是音樂所固有的”,“在某些情況下,‘事件’,敘事的核心,可以像文字描述一樣,通過音樂準確地描述出來”。[18]199
奧爾布賴特還探討了藝術的互動與交織。其中“假晶”是奧氏指代跨媒介轉換的一個核心術語。“假晶”一詞原是地質學術語,指在地質作用過程中,某種后來形成的礦物,其外形保持了原來的他種礦物晶形的現象。“假晶式”(pseudomorphic)一詞由阿多諾(Theodor W.Adorno)引入音樂學,用來描述斯特拉文斯基(Igor F.Stravinsky)如何根據從視覺藝術中竊取的拼貼原則構建音樂。而奧氏用這個詞描述跨藝術轉換——“一件作品由單一的藝術媒介構成,且該媒介被要求模仿或擔當某種異質媒介的功能”;因此,“觀眾面對一個假晶式藝術作品可能會在腦海中構建一個假晶:一個假晶式藝術品應有的形象,即如果它處于其渴望模仿的媒介中,它會是什么樣子”。[18]208
奧氏高度肯定跨媒介轉換的價值,著重指出,“一件藝術品之所以是一件藝術品,不但因為它特別容易被轉換到一種異質媒介中,而且因為這些轉換具有某種迷人的魅力”,“創造性工作通過激發他人的創造性來顯現其創造性。一件沒有故事的作品或沒有其他相似物的作品將不能稱為藝術品……最好的藝術往往有著最錯綜復雜的關系網”[18]211-213。但同時,奧氏也承認藝術中存在不可轉換的特質,在每次轉換發生后得以殘留(residue);然而,沒有任何藝術品只是殘留,全然脫離文化的根基——即使是白色畫布與無聲的音樂。由此,奧氏總結了藝術的兩個悖論:其一,“藝術只有被轉換才能叫藝術;但是這種轉換一直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其二,“只有被改述的東西才有意義;但是所做出的改述總是意味著不同于被改述的東西”。[18]227奧氏把最常見的六種跨藝術轉換界定為假晶藝術:從文學到圖畫(如插圖)、從圖畫到文學(如藝格符換)、從詩歌到音樂、從音樂到詩歌、從繪畫到音樂以及從音樂到繪畫的藝術轉換再創作。但在具體論述中,奧氏常將假晶與藝格符換概念相混淆。筆者認為,奧爾布賴特若放棄“假晶”一詞,用“藝格符換”指代廣泛意義上的跨藝術轉換,論證將會更有邏輯性。
在《泛美學》的結語中,奧氏提出兩個結論:其一,“每一種藝術媒介都是錯誤的媒介”,因為“每一次詮釋、尋找意義的嘗試,都會把藝術作品從其賴以表述自己的媒介推入其他媒介”;藝術的自我解放“只能通過強迫藝術進入一種異質媒介來實現”。[18]271其二,“每一種藝術媒介都是正確的媒介”,因為“聯覺現象表明,媒介的選擇并不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所有媒介彼此都密切相關,……沒有異質媒介:每一件藝術作品都是以一幅畫、一首詩和一支樂曲的形式出現在我們的腦海中,無論其原始呈現的媒介是什么。所有的藝術都銘刻在大腦中,觸動視覺區域的東西也會觸動聽覺和觸覺。的確,在跨越媒體邊界的藝術中,存在一種極其迷人的、溫暖的人性特質”。[18]273-274
歐美學界研究詩畫關系或文學與音樂關系的不乏其人,但像奧氏這樣能在文學、繪畫、音樂間穿梭自如,批評視野如此寬廣的并不多見,他把詩樂畫跨藝術批評從比較文學研究發展到了比較藝術研究,為當代歐美跨藝術研究開辟了廣闊的學術前景,對我國的跨藝術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① 20世紀下半葉歐美學界相繼出版的一些跨藝術詩學著述,如哈格斯特魯姆(Jean H.Hagstrum)的《姊妹藝術》(SisterArts,1958)、倫德(Hans Lund)的《作為圖像的文本》(TextenSom Tavla,1982)、斯坦納(Wendy Steiner)的《圖畫羅曼司》(PicturesofRomance,1988)、米切爾(W.J.T.Mitchell)的《描繪理論》(PictureTheory,1994)、克里格的《藝格符換》(Ekphrasis,1992)、赫弗南(James Heffernan)的《語詞博物館》(Museumof Words,1993)均以詩畫關系研究為重心。
② 本文為了簡練,標題“詩畫樂”中的“詩”泛指文學,“畫”泛指視覺藝術和造型藝術,就如萊辛在《拉奧孔》中對“詩”與“畫”的寬泛界定。參見萊辛《拉奧孔:或稱論畫與詩的界限》,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4 頁。
③ 《文學與其他藝術關系研究成果年鑒》(“BibliographyontheRelationsofLiteratureandtheOtherArts”)1952年開始發布,布朗是創刊人之一,并多年擔任編輯。
④ 前者收錄布朗遜(Bertrand H.Bronson)的文章《論文學與音樂》(“LiteratureandMusic”),后者收錄舍爾(Steven Paul Scher)的同題文章《論文學與音樂》(“Literature and music”)。
⑤ Calvin S.Brown.“TheRelationsbetweenMusicandLiteratureasa FieldofStudy”,ComparativeLiterature,2(1970),102.布朗也是美國比較文學學會(ACLA)早期的重要成員,并曾參與理事會和章程委員會工作。
⑥ 第13 屆WMA年會因疫情影響,推遲到2023年6月舉辦,參見學會網站http:/ /www.wordmusicstudies.net/wma_book_series.html(accessed 2022/12/18)。
⑦ WMA 出版的“語言與音樂研究”叢書第一卷的篇章結構便是基于舍爾的研究類型,分為五部分:理論思考、文與樂、文中樂、樂中文、聲樂之意。參見Walter Bernhart,Steven Paul Scher and Werner Wolf,eds.WordandMusicStudies:DefiningtheField.Amsterdam: Rodopi,1999.
⑧ “藝格符換”,又譯“藝格敷詞”“繪畫詩”“語象敘事”等,筆者對此進行過詳細的梳理和譯名闡釋,提出“藝格符換”之術語翻譯更符合當代跨藝術詩學研究發展的現實和趨勢。詳見歐榮.語詞博物館:當代歐美跨藝術詩學概述[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126-137.
⑨ 倫德1982年以瑞典語出版了《作為圖像的文本:圖像的文學性轉換研究》(TextenSomTavla:studierilitter?rbildtransformation)一書,把文本與圖像關系明晰為三種類型,即組合型(combination)、融合型(integration)以及轉換型(transformation),將跨藝術研究推向跨媒介研究,1992年該著作英譯本出版,對英語學界產生影響。參見Hans Lund,TextasPicture:StudiesintheLiteraryTransformationofPictures.Trans.Kacke Gotrick.Lewiston:Edwin Mellen,1992,6-11.
⑩ 這是馬克·夏加爾為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醫學中心創作的12 幅彩色玻璃畫。
? Adam Parkes,“Putting Modernism Together: Literature,Music and Painting”,1872—1927.http:/ /www.review19.org/view_doc.php?index=401(accessed 2019/7/2)。
? “現代主義薈萃”也是奧氏在哈佛大學開設的比較藝術課程,課程視頻預告片參見“putting modernism together”,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1yA1S6PAYzs (accessed 202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