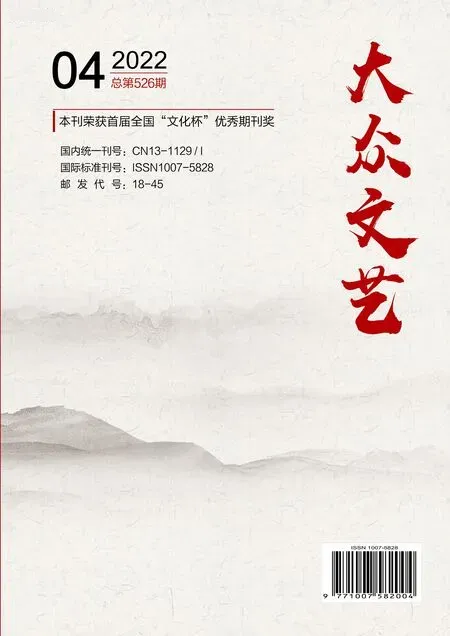女性性別欲望的失序:“泥塑粉”的身份想象
趙 哲
(蘇州大學,江蘇蘇州 215000)
追星群體是當代亞文化群體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群體,大部分追星群體是女性居多,而女性又通過追星來投射自己的欲望身份想象,因此,以追星群體為研究對象,可以集中詳細地探究女性地欲望身份演變。
近年來,一種名為“泥塑”的追星身份逐漸成了一種潮流,“愛他就要泥塑他”“什么都能泥”是這個群體的一種風向。而“泥塑”文化逐漸成為追星文化種不可忽視的存在。“泥塑”群體與普通的追星群體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欲望投射,而我們可以從中探討女性群體的性別欲望的變化。
一、何謂“泥塑”
(一)逆向欲望投射
“泥塑”,原意為“逆蘇”,與“正蘇”相反。“正蘇”另一個更容易理解的名字是“女友粉”,顧名思義,是指的粉絲把偶像當成男友,單方面建立起某種戀愛幻想。這種戀愛幻想并不是指女性粉絲真的把自己當成了偶像的女朋友,而是女性粉絲通過偶像滿足自己的心理上的戀愛欲望,這種幻想并不需要實操,女友粉也沒有極端的占有欲。
而與女友粉相反的就是“男友粉”,即“泥塑粉”,意指把男性偶像當成自己的女朋友,把自己當成男性偶像的男朋友。這一種欲望投射是逆向的,所以被稱為“逆蘇”。
(二)粉絲欲望的大致框架
粉絲欲望大致框架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具有包容和慈愛心態的粉絲心理,以“媽粉”為代表,同理可得姐姐粉等;一種是具有性別欲望投射的粉絲群體,以女友粉和男友粉為代表,這個群體試圖在偶像身上投射戀愛關系。“泥塑粉”的欲望來源也大致可以這樣劃分。
1.“媽粉”
“媽粉”即把偶像當作小孩一樣愛護,套入“泥塑”的思維體系,則是把男性偶像當成女兒來愛護。這一類群體所表使用的詞語通常是“女兒”“囡囡”“妹妹”“寶寶”,通常會強調偶像特質中“女性化”特征。
2.“男友粉”:性別欲望的表現
這里的男友粉就是把男性愛豆當成自己的女朋友,所使用的詞語大部分為“老婆”“女朋友”等象征戀愛關系的詞語。而這一行為是區別“泥塑”粉絲與以往粉絲的最大不同。“泥塑粉”的欲望不再是幻想男友,而是幻想女友,但這個粉群并非真正的女性同性依戀,她們獲得快感的方式還是建立在異性依戀的話語上。只不過,在這個話語體系中,男性偶像變成了女性,自己變成了男性,完成異性依戀。
也有一部分“男友粉”,希望自己能夠使用自己的力量保護男性明星,但傳統話語體系里沒有這樣保護的關系,所以,為了是這種保護更加順理成章,她們就把男性明星“泥塑”成女性,把自己的心理構建成男性,完成保護的想象。
3.“cp粉”
“泥塑粉”中的“cp”,通常是指粉絲幻想一對男性為情侶關系,并且套用傳統異性身份的關系,將其中一名定位成異性關系中的男性身份,另一名定義成異性關系中的女性身份,然后對承擔女性身份的男性偶像進行“泥塑”。在這種粉絲身份中,“泥塑粉”一方面是為了套用傳統異性關系,來構建對這一對男性情侶關系的想象,另一方面是為了切斷男性明星與女性明星產生關系的可能,在心理上對“泥塑”對象產生占有心理。
二、“泥塑粉”的身份想象展演
(一)“泥塑”文化的符號生產
1.打破文字性別界限
“泥塑粉”最開始是通過文字來建構“泥塑”思維的話語。最初區別“泥塑粉”的方式,就是出現一個群體不再對男性偶像使用“兒子”“老公”等投射女性欲望的詞語,而是變成了“女兒”“老婆”等詞語。
在轉移形容女性的詞句到男性偶像的過程中,“泥塑粉”的行為逐漸引起了其他的粉絲的好奇,反對“泥塑”的粉絲對這種行為加以抨擊,而不反感的粉絲則開始學習這種行為,并從中得到跨性別的心理快感。當她們開始“泥塑”偶像之后,偶像某些從未被注意和投射欲望的特質被放大了,而這些特質的放大構建了一個全新的偶像形象,開辟了粉絲的想象范圍,拓寬了粉絲的欲望來源。
2.圖片的具象化
當今信息傳播的形式中,圖片是建立視覺效果最常見形式。所以“泥塑粉”在進行想象展演的時候,也廣泛使用了這種形式。
圖片上最基本的手段就是對“泥塑”對象進行美白、磨皮。男性凝視里,女性被放大的特質就有白嫩、豐腴等適合投射欲望的特質。而“泥塑粉”則用這一套凝視方式來對待“泥塑”對象。
當下修圖的軟件多種多樣,且易于獲得,同時還會有很多模板以供套用。這為“泥塑粉”進行圖片展演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泥塑粉”可以輕松通過軟件完成自己的欲望構想。
同時,這些修圖軟件還可以為男性偶像的圖片加上女性特征,最常見的方式是在圖片上加上長發,通過頭發特征實現跨性別的形象構建。除了加頭發之外,“泥塑”群體也會有意識將人像美白、磨皮,放大女性特征,模糊面容棱角,從而創造出一個更女性化的形象。
4.動態視頻的沉浸式觀看
視頻也承擔“泥塑”創作的一個重要途徑。將視頻放慢速度、放大局部,配上音樂,剪輯手就可以達到想要的氛圍感。“泥塑粉”則運用這種技術,營造柔軟、艷麗等等不同的氛圍感。同時,“泥塑粉”還會使用視頻放大軀體柔軟感,從而更貼近女性氣質,方便凝視主體更好地進行凝視。除了增強氛圍感之外,視頻軟件已經開發出支持AI換臉的技術,“泥塑粉”可以通過軟件進行換臉,把模板中的女性角色的五官換成男性角色,從而在生理上將男性形象完全變成一個女性形象。
視頻的動態屬性,則給視頻增強了一種真實感,削弱了人物被創作的虛空感。勞拉?穆爾維在《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中提到,“攝影機在記錄具有電影性的事件的看,觀眾在觀看最后的產品時的看,以及任務在銀幕幻覺內相互之間的看。敘事電影的成規、否認前兩種,使它們從屬于第三種,其有意識地目的一直是為了消除那闖入地攝影機地在場,并防止觀眾產生距離感。不去掉這兩者(記錄過程的物質存在,觀眾地批判性解讀),虛構地戲劇就不能獲得現實感和真實感”。而在AI換臉的技術下,觀眾甚至不是通過消除記錄主體攝影機,來消除距離感,反而是模擬一種在場記錄的感覺,獲得觀看的真實感。
(二)“逆蘇”文化的情感傳播
陳彧認為,“受到包括新媒體技術、狂熱的粉絲情感、群體驅動等在內的多種因素的影響,粉絲群體呈現出后現代式的創造力,這種創造力在大眾文化社會環境下成了一股自下而上的驅動力量和生機勃勃的文化精神”。
微博,b站,抖音等適合亞文化發酵的平臺,則是“泥塑”群體不斷傳播“泥塑”快感的陣地。而這些平臺中,當“泥塑粉”群體中的創作者傳播上述文字、圖片、視頻時,會源源不斷收到來自他人的反饋,使得她們獲得滿足感。被吸引來的粉絲,也可能會投入“泥塑”文本的創作中。新媒體技術下,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界限被模糊,每一個人既可以是消費者,也可以是生產者,這使得群體形成了一種參與式文化。而“泥塑”群體也獲得源源不斷的生命力,完成情感傳播。
三、女性欲望與文化權力
(一)文化權力的爭奪
“泥塑”群體試圖從“泥塑”的角度女性為凝視主體的可能。在“泥塑”的思維方式里,女性對男性身體進行凝視,投射自己的欲望,完成自己想象,從而牢固自己的主體地位,把握自己的文化權力。
2021年8月,《光明日報》發文痛批“娘炮”審美,表示需要糾正當下的審美觀。這篇文章引起軒然大波,許多網友認為審美應該多元化,不應該被定義,認為即便是官媒也沒有權力定義美應該是什么樣的。這場事件似乎只是一場對于定義審美的爭論。其實批判“娘炮”審美的事件并非此次才發生,在之前,許多人就通過“流量”“偶像”等議題,表達過對這一類審美的不屑。而此前,大部分人都贊同男性應當具有陽剛之氣,而并不想這一次一樣引起許多非議和爭論。反對批判“娘炮”的人認為,美是多樣的,美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沒有人有權力定義美的公式。這樣一種發聲則是與批判一方分庭抗禮,互不相讓。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支持美是不能被定義的群體,大多為女性。在大聲表達觀點的女性群體之中,“泥塑”群體占比不可忽視。這個群體開始抗議自己的凝視傾向被駁斥,抗議自己的審美取向被規定。她們不像之前一樣,在批判的觀點面前謹小慎微,而是敢于表達自己的“泥塑”審美。
反對定義審美的權力,必然是為了使自己的審美合理化。這樣一種合理化的過程,就是在爭奪文化權力的過程。擁有權力的人可以對文化下定義,所以爭奪權力就要從文化的定義開始。發文批判“娘炮”審美的人,是對既有框架里審美失序的矯正,所以他們會認為自己在糾正審美錯誤。而另一方群體已經開始不承認既有的文化秩序,認為可以重建文化秩序。她們的重建就是構建以自己為文化主體的秩序。她們開始不接受女性是僅有的被凝視哲,而是主動把男性納入被凝視的對象。這樣一種文化失序必然會引起男性的恐慌,凝視這個程序本身就是物化個體的過程。被物化的凝視對象想獲得主體地位,便只能學會凝視的程序。這或許就是她們的方法。
(二)隱秘的父權制內化
在父權制的語言系統下,“泥塑”群體在使用男性凝視的框架,套入女性凝視的框架。拉康認為,語言系統本身就賦予了文化權力,他將人的世界分成實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象征界就是語言系統所表達的世界。而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能被語言表達,語言不能描述卻真實存在的就是實在界。“一旦出現了象征符,那么一切事物就都會按照那些象征符和象征界的法則而被規定或結構。”語言系統的構建本身就帶有文化權力,當我們使用這一套語言,就會站在語言系統的權力擁有者立場思考問題。
我們可以站在拉康這一觀點的基礎上,重新思考一下男性凝視的建構。男性凝視的整一套流程都是男性的語言。勞拉穆爾維在《視覺快感和敘事電影》中提到“戀物”的概念。電影中,有一種鏡頭既不能推動情節發展,也不能表達思想主題,這個鏡頭就是對女性美好身體的描摹。這種鏡頭滿足的是男性投射在女性身上的性欲望,通過對女性各個身體部位的放大凸顯,來滿足男性的欲望。而如今,“泥塑”群體也在用這一套框架去建構女性對男性的凝視。女性群體也是使用對男性身體部位的放大和凸顯,來滿足女性的欲望。而更值得細思的是,這一種欲望甚至不是對男性身體的欲望,而是放大男性身體上代表女性化的特征,即“白”“嫩”。另外,上文也提到,有部分“泥塑粉”是基于某種保護的想象,但是傳統話語體系里,女性保護男性的心理快感是不存在的。而女性保護男性的角色最常見的是母親,所以“泥塑粉”中存在“媽粉”。在這種情況下,完成這樣的心理投射,就只能把自己社會心理變成男性,把對方“泥塑”成女性,從而是這種心理快感邏輯通順。
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就不得不思考,這種凝視的建構是否是成功的。表面上,我們完成了對男性的凝視,事實上,是將審美主體從女性心理跨到男性心理,其完成的還是男性凝視的語言系統。這是父權制下審美語言的內化,而“泥塑”群體則更像一種無望的掙扎。
(三)女性氣質的審美重構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泥塑粉”群在父權的話語體系下,重新定義了女性氣質的意義。前文提到,“泥塑粉”放大男性偶像的女性氣質,引起過其他粉絲的不滿。事實上,從“泥塑粉”產生以來,“泥塑粉”和正蘇粉的爭執就從沒有停止過。而“泥塑粉”認為,如果放大女性氣質是對男性偶像的侮辱,這是否意味著女性氣質在我們的文化中是被輕視的。
“泥塑”的含義其實并不限制性別對象。把男性“泥塑”成女性,把女性“泥塑”成男性,都是“泥塑”行為。我們可以看到,當女性被“泥塑”成男性,這個行為并沒有引起爭議。“女漢子”這個詞語,最初是一個褒義詞。通過放大女性身上的社會界定的男性氣質,來夸贊女性。當女性明星被“泥塑”成“漢子”“爺”,也沒有粉絲認為不合適不妥當。而當男性明星被放大女性氣質時,許多人就會認為不合適不妥當,這或許本身就是文化隱形歧視。女性氣質被認為是脆弱的,柔媚的,所以削弱男性氣質,夸大女性氣質,就被認為是弱化偶像。
這樣一種明顯的對比,使我們開始思考社會文化里對女性氣質隱藏的歧視。如果性別是平等的,那么形容女性氣質的詞語就不是貶義詞。如果貶義詞只是針對某種氣質,那么就不應該以女性作為定義前綴。
弗洛伊德把女性的欲望和陽具的缺失聯系到一起,而巴特勒認為,邏各斯中心主義“提出了一種命名來遮蔽女性,竊取其位置。”而“泥塑粉”群沒有解構這種定義話語,而是重新構建了審美標準。在她們的審美標準里,女性氣質是可以放大的,是美好的,是一種夸贊的表示。在這個審美體系里,“端莊”“圣潔”“美艷”“純真”,這些女性氣質都不再是傳統男性審美體系下的定義,而是對女性氣質的贊美,是不依附與他人身份的贊美。
去解構已有的話語體系是一種比較艱難的抗爭,而重新定義審美標準,反而在還無力解構話語體系之前找到了新的抗爭方式。當然,這一切都建立在父權制的話語體系在隱形文化里設定不平等,在表層文化里又試圖呈現平等的漏洞之上。
在追星這個亞文化中,“泥塑粉”的出現,對傳統的性別欲望產生了猛烈的沖擊。她們顛倒了原有的快感秩序,建立了全新的身份體驗,又重構了審美標準。也許大部分“泥塑”愛好者,并沒有將其作為性別議題加以探討,但我們確實可以看到隱藏在其中的性別意識和文化話語權。我們無法預知“泥塑”文化的未來發展,但就現在的觀察來看,“泥塑”文化正興,而也許我們可以通過這個群體,通過性別失序,重新構建新的性別秩序。
注釋:
①克里斯蒂安?麥茨,吉爾?德勒茲著.凝視的快感[M].吳瓊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第16頁.
②陳彧.從文本再生產到文化再生產——新媒體粉絲的后現代創造力[J].學術論壇,2014,37(02):129-132.
③肖恩?霍默著 李新雨譯.拉康導讀[M].重慶大學出版社,第60頁.
④朱迪斯?巴特勒著 宋素鳳譯.性別麻煩[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