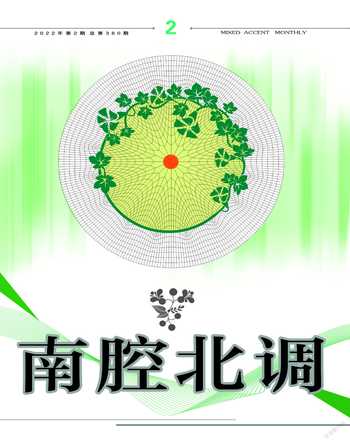雜技敘事的舞臺跨界與劇場探索
董迎春 王露霞

摘要:宜賓市酒都藝術研究院的原創大型雜技劇《東方有竹》,立足四川地區“竹”文化,以寫實愛情和民族情感為基礎講述時代發展的故事。在“劇時代”的背景下,“雜技+劇”的表演模式,將雜技表演以“炫技”為核心轉向以“顯藝”為核心,雜技劇表演更加注重舞臺跨界融合和綜合審美。在此基礎上,雜技敘事的作用更加突出。雜技與敘事兼容,對現實故事進行重構的舞臺演出模式,促進了雜技劇的藝術提升。雜技劇《東方有竹》對雜技敘事性的成功應用,給予當代雜技劇劇場探索以重要啟發。
關鍵詞:《東方有竹》 雜技敘事 跨界 劇場
《東方有竹》是宜賓市酒都藝術研究院原創大型雜技劇,榮膺2019年度國家藝術基金大型劇目資助項目,是目前全國唯一一臺獲國家藝術基金資助的現實題材雜技劇。該劇以雜技本體語言講述常林和孟竹浪漫的愛情故事,體現出傳統雜技和敘事元素的融合創新,展現了雜技強大的兼容性和廣泛的參與性,由此探索出敘事元素在雜技中的應用模式,促使雜技逐漸向劇場性、大眾接受性發展。同時,該劇以雜技與四川“竹”文化相結合,展現出美麗鄉村40多年間“人”和“竹”的變化,弘揚了民族文化,彰顯了中國精神。
一、雜技與敘事的兼容重構
(一)雜技本體藝術的審美價值
雜技歷史悠久,被稱為“百戲之首”。雜技的雛形來自人類對生活的模仿。例如,雜技中的“頂技”是模仿原始先民頭頂載物、背負肩扛的運輸形式而來的;雜技界名為“飛霄霄”的技藝和原始狩獵使用的“飛去來器”動作有很大的關系。隨著社會歷史的演進,雜技逐漸成為怡情娛樂的重要項目,有向大眾化、娛樂化轉變的趨勢。與此同時,雜技的社會作用也逐漸顯現,甚至受到國家重視,在外交場合發揮重要作用。如在封建社會繁榮時期,雜技用來彰顯國威、禮遇外邦。新中國成立之后,雜技表演由于沒有語言上的障礙,深受中外觀眾的喜愛,成為對外交流的重要形式,影響力亦隨之愈加突出。
雜技表演不僅是一種技藝的展現,也是人對身體極限的追求和對自然的挑戰。“雜技演員好像是在完成最高任務,它為自己的工作提出最高的標準并按奇異原則進行創造,假如美是人可以自由駕馭的對象,崇高是人暫且不能自由駕馭的對象,那么,奇異就是對難以掌握的事物進行高超地自由駕馭的天地。”[1]因此,雜技的審美特征,就是在“新、難、奇、美”的技巧表達上,展現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體現人類超脫世俗的精神內涵。
(二)雜技敘事化的審美轉變
當下我國的雜技表演主要呈現出兩種形式:一種是“雜技+情境”的雜技項目串聯表演,也被稱作主題晚會,側重于炫技和簡單的情景體驗;另一種是“雜技+劇”,即雜技劇,側重于雜技敘事化帶來的審美感受。雜技主題晚會表演拙于敘事,但是隨著自媒體時代的到來,人們的審美取向開始發生變化,中國傳統雜技的技巧性、雜耍性以及單一性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市場經濟的刺激和壓力下,中國雜技開始了從雜技造型、造境到雜技主題化及劇目化的現代探索與轉型。”[2]“雜技+劇”的表演模式更符合觀眾審美需求,雜技逐漸成為與歌舞、科技、情節、主題等多種審美元素相結合的藝術作品。如廣州雜技藝術劇院打造的雜技力作《化·蝶》(2021年),全劇共展示了32項雜技項目,包括空竹、軟功、蹬人、蹬傘、球技、綢吊等創新表演,并結合造型設計、舞美、VR科技等一系列操作,講述了梁山伯和祝英臺相遇、相知、相愛而又在封建禮教摧殘下被迫分開,最終破繭成蝶、相依相守的凄美愛情故事。同樣,沈陽雜技團的情景雜技劇《天幻》(2010年),也以其成熟的敘事技巧構建雜技肢體語言,成為一部頗具新意的視聽結合的審美作品。
二、雜技敘事的舞臺跨界
在“劇”時代的背景下,雜技本體在表意上的弱勢逐漸突出,雜技肢體語言很難滿足表達戲劇沖突、情感氛圍、人物特點等方面的需求,雜技劇創作需要找到“技”和“劇”的平衡點。“雜技劇創作者在多年的創作實踐中,逐漸認識到‘雜技+劇’的模式不同于雜技晚會,‘技’不能獨立于劇情之外,必須與‘劇’有機融合,在不斷追求、完善雜技本體語言的同時,達到‘劇’的要求。”[3]雜技敘事將雜技與舞臺藝術相結合,通過敘事強化,增強雜技舞臺的表意性,增加觀眾參與度,使雜技與舞蹈、音樂進行多方面跨界融合。同時,通過舞美、燈光、道具等操作,增強雜技舞臺藝術的表現張力,提升雜技藝術的審美水平。雜技劇《東方有竹》正是通過符合戲劇情感的表現內容和超常的雜技炫技美學,以邂逅、戀曲、情劫、轉折、夙愿、重逢、尾聲七幕故事,呈現出舞臺跨界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一)敘事主題增強雜技表意性
藝術表演要注重文化內涵。因此,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成為許多舞臺藝術創作和表演的指導方向。《東方有竹》共有“邂逅、戀曲、情劫、轉折、夙愿、重逢”六個小的敘事主題,以此串聯起各項雜技本體表演,使雜技技巧的表意性更加明確。例如,第二幕“戀曲”圍繞“戀”的主題,設計了難度遞增的獨輪車組合技巧表演。扮演郵遞員角色的表演者進行獨輪車表演,觀眾結合本場主題,便可聯想到男女主角書信傳情的熱戀場景,有趣生動又不落俗套。在第五幕“夙愿”中,演員們先是表演了街舞、魔術、柔術、綢吊這幾個雜技本體項目,隨后展示了茶藝和川劇,綜合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表演風格,但聯系本場主題“夙愿”便可明白,前面幾個雜技本體展現的是常林考取大學之后苦心鉆研、終成正果的場景,后面的茶藝和川劇展現的是孟竹在海外傳播中華文化的場景。隨著主題的引導,也不難聯想到街舞表演暗喻的是常林鉆研現代科技的過程,魔術表演暗喻的是常林制作藝術品《水晶之戀》的程序。
雜技劇《東方有竹》包含的六個敘事主題,賦予了原本表意不明確的雜技本體以情節和意義。整場表演以陌生化的手法,將雜技的“新、奇、驚、險”與故事的跌宕起伏相結合,用肢體表達的方式,構建出一段飽滿和富于表現力的愛情故事。并且,隨著六個主題的層層升華,雜技表演的難度也逐漸增加。在“重逢”一幕中,利用中國結為道具的高空技巧表演與“重逢”主題完美契合,使全劇達到了高潮,這既是情感的重逢,亦是文化的重逢,更是中華兒女突破自我精神境界的象征。整部劇的感情線也從個人情感上升到工匠精神、民族智慧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守望之情,最終上升到中華優秀兒女對中國夢的追尋和藝術闡釋,產生了極強的感染力。

(二)敘事視角加強雜技與觀眾的聯結
第三人稱的敘事角度,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能夠靈活全面地展示故事的始末,凸顯作品的主題和中心,并且更容易使觀眾產生共鳴。旁白作為一種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在同一時間可以展示不同地點的人物言行,或者使得多個人物的心聲交替出現,達到全方位塑造人物角色的效果。《東方有竹》劇目一開始,便以旁白充當第三者進行敘事,交代了這是一段發生在蜀南竹海綿延了40年的動人的愛情故事,并且簡單介紹了故事主人公以及他們相遇之后發生的事情。這一設計使觀眾的期待視野開始發生作用,觀眾對雜技這一肢體語言如何展現旁白介紹的內容、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產生了疑問,由此積累了足夠的心理能量。同時,開場的旁白也能夠對接下來的技巧表演做一個導入,暗示雜技本體的內涵,進而以雜技語言展開故事的講述。
《東方有竹》還使用流行歌曲充當背景音樂,借以傳遞人物的心聲,展現人物的心理沖突和心理矛盾,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劇中有一段孟竹和父親的對手頂表演,以此來體現兩人內心的掙扎、斗爭。但是單純的對手頂表演并不能很好地展現人物內心細膩的情感和糾結的心理狀態,這時插入一段流行音樂,一方面,觀眾能很快進入音樂所營造的情感氛圍中,另一方面,歌詞的內容恰當地配合著對手頂的表演動作,將人物內心的情緒精妙地傳遞出來。借助背景音樂,觀眾可以準確地把握雜技表演動作中所包含的情感意義,從而與作品產生互動和共鳴。
(三)雜技表演、舞臺呈現緊扣敘事線索
敘事線索是敘事性文藝作品中貫穿始終的發展脈絡,它把作品中的各個事件聯結成一體,其表現形式可以是人物的活動、事件的發展或某一貫穿始終的事物。一部敘事作品通常有一條或者多條線索,但是起主導作用的只有一條。雜技劇《東方有竹》中的核心敘事線索是孟竹和常林的愛情故事以及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雜技動作技巧的設計也緊緊圍繞著這兩條敘事線索展開。首先,第一條敘事線索——愛情,圍繞男女主人公的愛情發展脈絡,每一幕都有雜技技巧對其進行展現。例如,第二幕“戀曲”,以雜技表演“夢幻簸箕”,展現孟竹初戀時的輾轉悱惻;第三幕“情劫”,以對手頂表演,展現孟竹遭受感情的挫折,與父親爆發激烈的沖突;第四幕“轉折”,以頂缸、流星錘表演,展現出兩人分開之后常林混亂的生活和痛苦的心理狀態。本劇運用雜技表演為故事線索服務,使故事線索貫穿于多項雜技表演中,從而呈現出“劇”的起承轉合的效果。其次,對于中國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是全劇的另一條線索,這主要以雜技本體的舞臺呈現形式與道具創新進行展現。劇中的雜技表演形式以傳統雜技技巧(如頂缸、踩高蹺等形式)為載體,輔之以含有“竹、書法、古鎮”等具有中國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舞美元素,體現“傳承”的內涵。另外,該劇在表演道具上又多有創新,如最后的高空表演,演員在一個中國結道具上進行高空技巧展示,并隨著道具組合形式的變化進行動作的改變和調整,最終定格成類似于“圓”的形狀,象征圓滿、融會貫通。可見,無論是雜技技巧還是舞美道具都不僅僅是為了“雜技秀”而存在,而是重視對情節的建構和重組,使雜技本體為敘事結構服務,成為故事內容的象征性符號。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是世界語言,談文藝,其實就是談社會、談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溝通心靈。”[4]《東方有竹》以高超的雜技表演展現了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對自身的超越和對未來的美好期望。同時,該雜技劇通過宏大精彩的敘事,利用服裝、音樂、舞蹈、舞臺等元素展現出常林和孟竹真摯動人的愛情故事和中華優秀文化傳承人的寶貴精神品質。嫻熟的敘事手法的運用,使全劇在時間和空間上表達自如,凸顯出內涵深刻、主題突出、結構清晰的特點,使觀眾更容易感受和理解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優秀傳承人的高風亮節和工匠精神,具有極強的審美性和觀眾參與度。
三、雜技敘事的劇場探索
雜技敘事的發展,使雜技增加了人文關懷,更加注重文化優勢。雜技表演巧借敘事元素,可以表達連貫的故事和深刻的思想情感,給予觀眾更多的啟發。這種形式注重與觀眾的情感互動,有利于培養受眾群體,使雜技真正成為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隨著經濟的發展,雜技可以借助當地文旅優勢和地域文化,與當地的經濟發展相結合,這就為雜技的發展開拓了更廣闊的市場。雜技劇場探索既有了內在的發展動力和發展活力,也有了外在的發展方式,使雜技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擁有了新的發展方向。
(一)雜技劇的融創走向
隨著時代的發展,“雜技+”的發展理念逐漸滲透雜技劇,雜技劇利用“聲、光、電”等現代科技,融合流行音樂、當代舞蹈、魔術表演、傳統戲劇等表演形式,呈現出奇幻的舞臺效應。尤其是音樂和舞蹈帶有很強的抒情性,雜技與之相融合,賦予雜技劇表演以人文情懷,不僅能夠傳達出人物的情感狀態和內心世界,還能調動觀眾的情感情緒,使觀眾參與到劇情的起承轉合之中。如今,更多注重雜技跨界融合創新的優秀雜技劇應運而生,如大型雜技情景劇《英雄虎膽》,以其音樂之震撼最為突出,并且融合了民族舞、跑酷等藝術形式,呈現出戰爭的激烈和英雄的勇敢;雜技劇《追光者》融合現代舞,表達時代青年的內心情感。
(二)雜技劇的地域特色
雜技的創作與發展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征和民族風格,這種“民族風格在世界雜技交流比賽和欣賞活動中受到了高度重視,民族風格越鮮明,在世界上越有代表性,也越有競爭性,這已為多次國際比賽所證實”[5]。“竹文化”在宜賓源遠流長,對宜賓的政治、教育、文化以及人們的深層次心理結構、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前,一些雜技文化基礎雄厚的省份,立足資源優勢,強力推進以雜技為龍頭,集旅游、演藝等文化產業為一體的雜技產業園區的建設,對于發揚光大雜技文化、打造城市雜技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推動地方文化產業的優化升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6]《東方有竹》就是在此基礎上,響應習主席因地制宜發展竹文化的號召,以具有中國特色的雜技藝術結合大量川南地區的民歌、器樂等手法,將民族、地域、雜技、感情等元素深度融合,講述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故事,與現代觀眾的審美心理完美接軌。并且,該雜技劇還應用音樂人類學方法論將象征主義和儀式音樂落實在本劇音樂創作實踐上,以更好地營造民族文化氛圍和推動劇情線索發展,爭取更大范圍的觀眾的接受與喜愛。
(三)雜技劇的文化自信
文藝作品不僅要具有藝術性,也要具有思想性。雜技劇《東方有竹》將中國傳統文化和優秀精神嵌入作品的思想內涵之中,體現了文化自信。如劇中插入精彩生動的川劇表演,展現了中國的戲劇文化。又如,劇情以常林刻苦鉆研、創新發展為載體,體現新一代手工藝人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和工匠精神。再如,孟竹在海外堅持向子孫后代講述中國傳統文化,將中國符號傳承給下一代,體現了珍貴的堅守與傳承精神。更重要的是,整部劇也提出了深刻的時代問題,文藝作品是時代發展的映射和縮影,在現代中國,地域文化應如何走向世界?青年人的時代使命和擔當應該如何體現?這些問題在劇中出現,給予觀眾以思考和啟發。
結 語
雜技劇作為“劇”時代雜技發展的必然產物,“技”與“劇”如何兼容重構成為雜技劇發展最核心的話題。雜技劇《東方有竹》以“雜技+劇”的模式挖掘和演繹文化傳承故事,具有重要的探索意義和啟發價值。劇中對“技”進行了極致演繹和創新,將“劇”融入民族特色和文化價值,這種“技”與“劇”的融合方式,探索出了雜技劇新時代的舞臺表現形式。在文藝事業蓬勃發展的新時期,藝術發展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和傳統精神,展現中華文化的審美特點,雜技劇《東方有竹》的敘事舞臺形式,顯然為藝術融入民族性和文化性做出了積極示范。同時,作為一部雜技劇,《東方有竹》在劇場發展和探索上也有其標新立異之處,它積極將雜技與地方文旅特色相結合,拓寬了雜技的傳播渠道。雜技的發展呼喚創新,雜技劇《東方有竹》在敘事舞臺和劇場探索上的多元創新,豐富了雜技的現代藝術價值,為雜技劇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基金項目:2018年廣西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廣西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研究中心”重點資助項目“廣西少數民族雜技的保護與傳承研究”(項目編號:2018KFZD01);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一般項目“中國當代雜技創作研究”(項目編號:17BE093)。
參考文獻:
[1]邊發吉,周大明.雜技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2.
[2]董迎春,覃才.現代雜技的創作與“雜技劇”轉型——以廣西大型壯族雜技劇《百鳥衣》為例[J].南方文壇,2018(04).
[3]郭云鵬.中國雜技藝術發展報告[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20:44.
[4]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M].北京:學習出版社,2015:9.
[5]薛寶琨,鮑震培.中華文化通志:曲藝雜技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437.
[6]郭云鵬.中國雜技藝術發展報告[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20:67.
作者單位: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
3846500338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