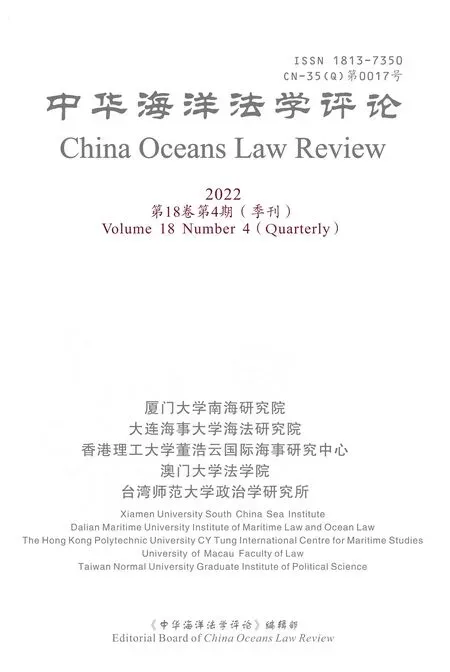國家間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的雙邊或多邊協定:背景、所有權規定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陳銳達
一、引言
沉睡于深海的水下文化遺產,記載著人類航海事業的生動歷史,封存著海洋文明的發展印記,如商業交往、革命戰爭、自然災害、甚至殖民掠奪和奴隸貿易。1The significance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UNESCO (5 Dec 2021),http://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underwater-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protection/significance-of-uch/.在現代海洋法的發展進程中,水下文化遺產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和科學價值,其法律地位也一直備受關注。然而,隨著潛水技術的進步和商業利益的驅使,水下文化遺產不僅成為撈寶者的海底寶庫(treasure junks),亦成為各國競相爭奪的海洋資源之一,其所有權問題因而成為國家間水下文化遺產爭議的焦點問題。
所有權被認為是“一個成熟的法律體系所承認的與物相關的最大利益”,2Sarah Dromgoole,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96.水下文化遺產也不例外。盡管對于考古學家而言,人類的過去不屬于任何人,它代表了當前或未來生活在地球上的任何人的文化遺產,使全人類社會處于平等地位,3Brian Fagan,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rchae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Introduction;Ben Juvelier,“Salvaging” History: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and Commercial Salvage,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32:5,p.1036(2017).然而,文化遺產形成于特定的民族、地域和文化背景,具有天然的民族屬性,只有明確的所有權歸屬和充分的立法保障,才能真正維護全人類共同享有和保護文化遺產的權益。4John Henry Merryman,Cultural Property International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Vol.12:1,p.11-39 (2005).不過,由于所有權概念的復雜性以及相關國家利益難以調和,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的解決面臨諸多困境,現行國際公約未能有效解決,甚至將之明確排除在公約調整范圍外,交由各國民法、其他國內法以及國際私法解決。5The UNESCO 2001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UNESCO (5 Dec 2021),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LT/pdf/FAQ_en.pdf,p.9.
面對當前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國際爭議,各國在外交實踐中形成了諸多有益經驗。6同前注2,Sarah Dromgoole,p.140.針對特定的沉船、其他沉沒物或水下遺跡,相關當事國通過簽訂雙邊或多邊協定,商定締約方對水下文化遺產取得、設立、控制和保護等具體權利義務,成為當前國家間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的有效途徑。有鑒于此,本文將從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解決的角度出發,結合現行有關處理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國際協定文本,探究國家間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的法律背景、所有權條款設計,反思此類雙邊或多邊協定的優勢和局限,冀以為我國通過雙邊或多邊協定的方式解決跨國水下文物所有權爭端提供借鑒。7在國際公約中多稱“水下文化遺產”,中國法語境下多稱“水下文物”,兩者內涵并無實際差異,但在外延上因所適用的法律依據而有所不同,本文根據語境交替使用之。以《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為例,符合該公約第1 條定義的“水下文化遺產”系指至少100 年來,周期性地或連續性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歷史或考古價值的所有人類生存的遺跡,比如:(1)遺址、建筑、房屋、工藝品和人的遺骸,及其有考古價值的環境和自然環境;(2)船只、飛行器、其他運輸工具或上述三類的任何部分,所載貨物或其它物品,及其有考古價值的環境和自然環境;(3)具有史前意義的物品。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第2 條,“水下文物”是指遺存于下列水域的具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人類文化遺產:(1)遺存于中國內水、領海內的一切起源于中國的、起源國不明的和起源于外國的文物;(2)遺存于中國領海以外依照中國法律由中國管轄的其他海域內的起源于中國的和起源國不明的文物;(3)遺存于外國領海以外的其他管轄海域以及公海區域內的起源于中國的文物。前款規定內容不包括1911 年以后的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以及著名人物無關的水下遺存。
在開展研究前,本文需首先厘清以下概念在水下文化遺產語境下的含義:第一,所有權。其首先屬于私法上的概念,包括對物排他性的控制權和支配權,屬于絕對權。而對于文化遺產而言,其既具備財產屬性,又兼具文化價值,因而其支配權能須被限制在一定的界限內,以符合國家對文化遺產進行管理和保護的目的,如禁止非法打撈、出口或非法交易水下文化遺產的行為,因而該權能又具有相對性。換言之,現今所有權的概念,惟于與公益一致之限度內為正當,對社會之一般文化利益,不得不由絕對的而成為相對的。8史尚寬:《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59 頁。是故,本文所討論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兼具絕對性和相對性,這一特征在所有權雙邊或多邊協定的訂立中不僅影響了所有權主體及歸屬的認定方法,還影響了所有權的內容和行使方式。
第二,雙邊或多邊協定。依《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條約是國家間締結而以國際法為準之國際書面協定,不論其載于一項單獨文書或兩項以上相互有關之文書內,亦不論其特定名稱為何。9《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 條第1 款(a)項。與水下文化遺產有關的國際條約,從締約國數量和調整對象來看,既包括調整一般意義上的水下文化遺產的國際或區域性公約;10現行公約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公約草案如《保護水下文化遺產歐洲公約(草案)》《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布宜諾斯艾利斯公約(草案)》等。也包括專門調整特定水下文化遺產,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簽訂的,旨在解決其所有權和管轄權之權利義務關系的雙邊或多邊協定。本文研究僅限后者。在所有權爭議解決中,此類協定同樣受《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規制,作為所有權規范的載體,系協調跨國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糾紛的統一實體法路徑和直接調整方法。其在內容上相當于當事人之間關于財產權歸屬的私法協議,只不過訂約主體是主權國家,具有國際法上的拘束力。11參見[美]艾倫·S·韋納:《國際法》,馮潔菡譯,商務印書館2015 年版,第114 頁。
二、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解決的法律背景
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問題的復雜性和各國立法的差異性,導致了所有權法律沖突的產生,通過訴諸一國司法機關并不能有效解決爭議。現行調整水下文化遺產的國際公約亦對所有權問題采取了沉默的態度,故通過公約機制解決爭端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不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倡導的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協商與合作的原則精神,為各國通過雙邊或多邊協定解決所有權歸屬爭議創造了條件。
(一)所有權的法律沖突
概言之,由于各國立法的價值取向不同,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制度也存在差異,從而導致法律沖突的產生,并主要表現為沿海國與來源國之間的法律沖突。12由于相關國際公約對來源國并沒有清晰的界定,本文從主張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依據將爭議相對國區分為來源國與沿海國。其中,基于一定文化、歷史、民族聯系而對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提出主張的國家為來源國,包括船旗國和國籍國;基于與本國主權或管轄海域相關聯(如沉沒地點位于本國管轄海域內)而主張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國家為沿海國,其與文化遺產在歷史、文化上不存在直接聯系。此外,水下文化遺產分布的偶然性和各國立法管轄權的局限性,也使通過國內立法和司法途徑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存在較大障礙。13特別是對于軍艦和政府船舶等享有國家豁免地位的水下文化遺產而言,內國法院并不愿意主動行使管轄權,即便涉及本國當事人利益。如在西班牙海軍護衛艦“梅賽德斯”號(Mercedes)的打撈案中,美國打撈企業奧德賽公司(Odyssey Marine Exploration,Inc.)向美國法院起訴要求獲得對該沉船打撈物的所有權,法院認為涉案沉船享有國家豁免,且不存在《外國主權豁免法》的管轄權例外,因而拒絕行使管轄權,參見Odyssey Marine Exploration,Inc.v.Unidentified Shipwrecked Vessel and Others,675 F.Supp.2d 1341,1138-44 (M.D.Fla.2010).
首先,對于是否承認原始物主的權利,各國在立法上存在分歧。通常認為,水下文化遺產屬于有主物,船舶的沉沒不會導致所有權的喪失。14同前注2,Sarah Dromgoole,p.106.因此,國內法通常賦予可辨明物主主張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權利,這些物主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權利義務繼受人等。如根據美國1987 年《被棄沉船法》(Abandoned Shipwreck Act),國家宣告位于被淹沒土地上任何被棄沉船的所有權,對于權屬明確且物主未拋棄的沉船則不主張所有權。15淹沒土地指海岸以外三公里的水域,參見Abandoned Shipwreck Act of 1987,Section 6.相比之下,有的國家立法則規定原始物主或繼承人均無權主張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例如,依意大利《文化與景觀遺產法》(Code of the Cultural and Landscape Heritage),無論何人以何種方式在地下或海床發現具有文化價值的古物,且無論為動產還是不動產,均屬于政府財產或其不可轉讓之資產的一部分。16Art.91 of Legislative Decree 22 January 2004,n.42 Code of cultural and landscape heritage,pursuant to article 10 of the law of 6 July 2002,no.137.
其次,在承認原始物主所有權的前提下,若物主無法辨明,則水下文化遺產成為無主物并進入公共領域,不同國家基于不同立場和連結因素主張所有權。一方面,沿海國根據屬地原則,主張國家先占取得本國領海范圍內的水下文化遺產。如英國《1995 年商船法》(Merchant Shipping Act 1995)第241 條規定,在所有權不明的情況下,英國及其水域內發現的無人主張的沉船歸女王及其王室繼承人所有。17Art.241 of Merchant Shipping Act 1995.另一方面,來源國根據水下文化遺產與本國在歷史和文化上的聯系,主張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特別是對沉沒于他國領海的水下文化遺產,與之建立屬物聯系。18在芬蘭與俄羅斯關于“圣母瑪利亞”(Vrouw Maria)號沉船的糾紛中,俄羅斯主張其作為帝國財產權利的繼承人,要求恢復對沉船所載藝術品的所有權,原因在于其與俄羅斯存在特定的文化聯系。同前注2,Sarah Dromgoole,p.109-110;National Board of Antiquities,The Vrouw Maria Underwater project 2009-2012 final report,museovirasto(5 Dec 2021),https://www.museovirasto.fi/uploads/Arkisto-ja-kokoelmapalvelut/Julkaisut/vrouw-maria-final-report.pdf.沿海國與來源國的沖突構成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法律沖突的主要表現形式。
此外,各國水下文化遺產法的管轄范圍有限,表現出法律適用的消極沖突。細言之,各國的主權范圍僅限于內水和領海,而對于領海外的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等海域,各國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只享有對特定事項的管轄權,但并不包含水下文化遺產。此外,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各國在公海上無主權,從而使公海上水下文化遺產的法律地位尚不清晰。19《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89 條規定:“任何國家不得有效地聲稱將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主權之下。”盡管依公約第149 條,“區域”內發現的一切考古和歷史文物的保存和處置應特別顧及來源國、文化上的發源國或歷史和考古上的來源國的優先權利,但是,僅憑此條還難以直接推定“區域”內的水下文化遺產歸屬于上述三類國家。20在有關公約起草的締約國會議期間,締約國代表團對于本條款討論的重點在于“區域”內的文化財產的管理和處置。其中,土耳其和希臘代表團均在提案中提到,“來源國”或“文化上的發源國”有取得這些物品的優先權,而管理局在這些國家未能行使優先權的情況下,有權對此類物品進行處置。由此可見,第149 條所稱來源國至少對“區域”內水下文物的所有權的歸屬和處置擁有一定的決定權。參見[斐濟]薩切雅·南丹主編:《199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評注》,焦永科等譯,海洋出版社2009 年版,第198-199 頁。此外,盡管《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3 條第3 款規定“本條的任何規定不影響可辨認的物主的權利”,但關于該條與第149 條的關系,以及來源國的優先權是否應兼顧可辨認物主的權利等存在諸多爭議,有待進一步討論。參見趙青:《來源國對“區域”內考古和歷史文物的優先權研究》,載《研究生法學》2016 年第2 期。此外,公約也未對何為“來源國”“文化上的發源國”“歷史和考古上的來源國”及各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做進一步闡釋,在實踐中容易引發爭議。
(二)水下文化遺產國際公約的立法空白
當前與水下文化遺產有關的國際公約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及其行動指南(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以下簡稱“《水下公約》”),但兩者都沒有解決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問題。
《水下公約》直接將所有權問題排除在公約的討論范圍之外,將其拋給國內法來解決。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水下文化遺產不僅是“財產”,強調經濟價值;同時也是“遺產”,側重其文化價值。公約的價值取向更接近后者而非前者。21Nicola Ferri,The Right to Recovered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The Neglected Importance of Article 149 of the UN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in Silvia Borelli &Federico Lenzerini eds.,Cultural Heritage,Cultural Rights,Cultural Diversity: New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12,p.253.公約的主要目的在于確保和加強水下文化遺產保護,而非處理沿海國和來源國等主體在私法上的權屬爭議。22同前注2,Sarah Dromgoole,p.96.第二,所有權制度涉及國家和私人所有權以及打撈法等傳統海事規則,對其展開談判將會耗時耗力。23傅崐成、宋玉祥:《水下文化遺產的國際法保護:200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解析》,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213 頁。在各國利益和主張難以調和的情況下,從促進談判效率并使公約被更多國家接受的角度考慮,所有權問題暫時被擱置。因此,《水下公約》只解決了水下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其所有權的法律體系尚未建立,加之水下文化遺產的國內立法本身存在沖突,因此國家間的爭議只能在個案中通過談判和協商來尋求一致的解決方案。24Anastasia Strati,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An Emerging Objective of the Contemporary Law of the Sea,Springer,1995,p.85.
值得一提的是,當前重要的水下考古遺址多為歷史上沉沒的軍艦,其所有權爭議也是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糾紛最為突出的類型之一。25Craig Forrest,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Sunken State Vessels as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Ocea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aw,Vol.34:1,p.43 (2003).作為特殊客體,《水下公約》雖在第2 條第8 款強調公約不改變任何國家對本國船只和飛行器擁有的權利,但并未釋明沉沒之軍艦和政府船舶的法律地位,亦未明確其是否同樣適用主權豁免,這也是主要水下文化遺產大國如英國、美國、荷蘭等尚未加入公約的主要原因之一。26Sean D.Murphy,United States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2: 2002-200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134.對此,各國目前在實踐中形成的基本立場是:無論其在哪個海域沉沒,除非國家明示放棄,軍艦和政府船舶永久屬于國家。27William V.Dunlap,Ownership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Journal of Maritime Law&Commerce,Vol.49:3,p.426 (2018).美國與法國在《水下公約》通過之初并未立即簽署之,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公約沒有承認這一原則。28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在2001 年就美國政府保護沉沒軍艦的政策發表聲明稱,除非按照國會授權或指示的方式放棄或轉讓所有權,否則美國對其沉沒的國家航行器無限期保留所有權。美國承認國際法規則,即只能根據外國船旗國的法律轉讓或放棄外國沉船的所有權。參見William J.Clinton,Statement on United States Policy for the Protection of Sunken Warships,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1 January 2001,Vol.37:3,p.195;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已于2013 年正式批準《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作為重要的海洋大國,法國的加入對于提高公約的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參見France Ratifies the UNESCO 2001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UNESCO (8 Feb 2013),http://www.unesco.org/new/en/culture/themes/underwater-cultural-heritage/dynamic-content-single-view/news/france_ratifies_the_unesco_2001_convention_on_the_protection/.
(三)國際協商與合作的基本原則
盡管目前有關水下文化遺產的國際公約并未解決相關問題,但國際協商與合作是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的趨勢,也為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國際爭端奠定了重要的原則基礎。通過與相關國家協商的方式來確定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是締約國爭議解決的基本原則之一。29江河、於佳:《國際法上的歷史沉船之所有權沖突——以保護水下文化遺產為視角》,載《廈門大學法律評論》2015 年第1 期,第80-96 頁。
作為當前主要的調整水下文化遺產的多邊公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水下公約》均強調國家間合作的重要性。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3 條第1 款,各國有義務保護在海洋發現的考古和歷史性文物,并應為此目的進行合作。30《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3 條第1 款。該義務作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一般規定,顯然應普遍適用于各海域內的水下文化遺產。31趙亞娟:《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法制——論有關水下文化遺產保護的三項多邊條約的關系》,載《武大國際法評論》2007 年第1 期,第93-127 頁。特別是對于“區域”內的水下文化遺產,國際合作既可以避免立法主權的不當延伸,還可對“區域”內的水下文化遺產提供及時有效的保護。此外,公約第303 條第4 款還強調了本條不妨害關于保護考古和歷史性文物的其他國際協定和國際法規則,32《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3 條第4 款。為國家間的合作和雙邊或多邊機制創造靈活適用的空間。
《水下公約》亦鼓勵締約國通過雙邊或多邊機制開展活動。依公約第6 條,公約鼓勵締約國締結保護水下文化遺產的雙邊、地區或其他多邊協定,可提出比公約更好地保護水下文化遺產的規章。33《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第6 條第1 款。從條款的字面意義來看,公約所涉及的合作內容主要為水下文化遺產的合作保護與開發,以及預防破壞和非法打撈活動,并未就所有權問題的解決規定國際協商義務。但從目的解釋來看,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問題的解決更有利于其保護和管理。另一方面,公約對打撈法和打撈物法的排除,雖然規定了例外情況,但其條件很難滿足,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私人打撈者取得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可能性。34同前注23,傅崐成、宋玉祥,第214 頁。以此為指引,國家在雙邊或多邊協議中亦應明確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以回應公約的相關規定。公約第6 條第3 款進一步指出,本公約不得改變締約國在本公約通過之前締結的其他雙邊、地區或多邊協定,尤其是與本公約的宗旨相一致的協定中規定的有關保護沉船的權利和義務。35《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第6 條第3 款。在公約生效前,相關國家已經開展了解決特定水下文化遺產爭議的國際實踐,在其后訂立的協定中商定了與所有權相關的權利和義務,雖不屬于公約的調整范圍,但只要與公約的目的和宗旨相一致,公約就予以尊重和適用。最后,從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角度來看,《水下公約》第25 條將協商作為爭端解決的首選方案,符合當前國際爭端解決的發展趨勢。36郭玉軍主編:《國際法與比較法視野下的文化遺產保護問題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324 頁。
三、雙邊或多邊協定對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規定
目前,各國已通過一系列有關水下文化遺產的雙邊或多邊協議,協調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37代表性的有:1952 年英國與意大利《關于“斯巴達”號沉船撈救換文》、1972 年《澳大利亞與荷蘭關于荷蘭古沉船的協議》、1989 年美國與法國《關于“阿拉巴馬”號沉船的協定》、1989 年英國與南非《關于“伯肯黑德”號沉船救助規范的換文》、1995 年芬蘭、愛沙尼亞與瑞典《關于“愛沙尼亞”號沉船的協議》、1997 年英國與加拿大《關于“幽冥”號與“恐怖”號沉船的諒解備忘錄》、2003 年美國與法國《關于“拉貝爾”號沉船的協定》、2003 年美國、法國、英國與加拿大《關于泰坦尼克號沉船的協議》、2013 年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與英國《關于“富偉”號沉船的諒解備忘錄》,詳見下文。在調整對象上,此類協議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沉沒于一國領海的他國軍艦,爭議焦點在于船旗國所有權與沿海國管轄權之間的矛盾,在尊重船旗國主權豁免的基礎上合作開發水下文化遺產;38同前注2,Sarah Dromgoole,p.338.另一類主要針對商船及其遺址,目的在于協調沿海國與來源國的權利與利益訴求,通過綜合運用屬地管轄原則和來源國實際聯系原則協調相對國之間的關系,妥善分配所有權。這兩類協議的制定均涉及所有權主體、歸屬以及所有權擔保等問題。因此,下文結合協議文本,考察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條款的設計思路。
(一)所有權的主體
除軍艦等身份明確的水下文化遺產可以判定原物主并歸其所有外,在物主無法辨明的情況下,水下文化遺產通常歸國家所有;但在適用打撈物法的國家,私人打撈者亦有可能成為所有權的適格主體。由于條約的效力及于締約國主權管轄范圍內的所有人,締約國可以為本國當事人設定權利義務。在適用于特定遺產的協議中,此類對象主要指可辨明的原始物主及其繼承人或商業打撈公司。此外,出于客體的特殊性和國際影響力,締約國也可能約定放棄任何一方主張排他性所有權的權利,為全人類利益共同開發和保護。因此,當前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雙邊或多邊協定中,所有權的主體主要有三種約定形式:國家所有、私人與國家分別所有或排除特定主體的所有權。
1.國家
在國家間處理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雙邊或多邊協議中,一國政府是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一般主體。國家通過協議劃定爭議財產的所有權歸屬及其權利行使范圍,并為本國公民創設權利或義務。由于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并不因其沉沒而消滅,故對于可辨明物主的水下文化遺產,原則上仍歸其原所有人或繼承人所有。在此背景下,國家作為水下文化遺產之可辨明物主存在以下三種基礎:第一,國家以船旗國或登記國的身份享有對軍艦和政府船舶、航行器的原始所有權,這是由國家的主權權利來決定的。第二,國家以權利義務繼受人的身份繼承原船方所屬企業的財產,進而取得包括沉船在內的該企業沉沒財產的所有權。第三,國家以戰爭保險賠付的方式取得為戰爭運送傷員而沉沒的商船的所有權。此外,在物主不可辨明時,水下文化遺產將成為無主物進入公共領域,國家也可能基于屬地或屬物上的聯系主張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這通常需要一國國內法的明確規定。
國家對沉沒軍艦的所有權在當前的國際實踐中獲得承認。例如,對于1995年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海灣發現的法國“拉貝爾”(La Belle)號海軍輔助船,在獲得美國政府的承認后,法國政府于1997 年正式宣告對該沉船的所有權。39U.S.-France Agreement regarding the Sunken Vessel La Bell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7:3,p.688-689 (2003).雙方于2003 年簽訂《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與法蘭西共和國政府關于“拉貝爾”號沉船的協定》(以下簡稱“《拉貝爾號協定》”),就有關沉船的保管和研究作出安排。40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 recording the Wreck of La Belle,31 March 2003.美國國務院在簽訂該協議時聲明,該協議反映了一項重要的國際法原則,即除非明示放棄,可辨明的政府沉船歸屬于該國家,此項權利不因時效的經過而消滅。41U.S.Department of State Press Release on U.S.-France “LaBelle” Agreement Signed March 31, (5 Dec 2021),https://2001-2009.state.gov/g/oes/ocns/26820.htm.
國家以所有人的名義主張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是以私法意義上的物主而存在的,42徐錦堂:《關于海底沉沒物相關法律問題的幾點思考》,載《中國海洋法學評論》2005年第2 期,第220-232 頁。其取得所有權的方式既包括原始取得,也包括經由繼承、贈與等民事關系繼受取得。在以國家為主體的繼承案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72 年荷蘭政府與澳大利亞政府簽訂的《澳大利亞與荷蘭關于荷蘭古沉船的協議》(以下簡稱“澳荷古船協議”)。43Agreement between the Netherlands and Australia concerning Old Dutch Shipwrecks,6 November 1972.該協議所采取的所有權條款設計,成為后世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的范本。該案涉及一艘在西澳大利亞沿海發現的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古沉船。基于無人繼承遺產歸國家所有的原則,44依照普遍的法律規則,無人繼承財產歸屬于國家或國王或市鎮或其他的公共團體,國家或以最后的繼承人的身份,或因為國王對無主財產享有權利而取得該遺產的所有權。參見[德]馬丁·沃爾夫:《國際私法》(第二版),李浩培、湯宗舜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639 頁。荷蘭政府以東印度公司財產合法繼承人的身份,主張沉船的所有權。澳大利亞則認為由于沉船時間的推移且物主無所作為已被默示拋棄,其基于沿海國主權先占取得所有權。45同前注2,Sarah Dromgoole,p.110.雙方最后通過簽署協議的方式解決爭議,在兩個具有不同連結因素的國家之間就無人繼承的水下文化遺產進行分配。
由國家取得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不僅是為了解決所有權的歸屬問題,更是以文化遺產的有效保護和管理為目的。即使一國政府不直接獲得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歸屬,其也可能行使所有權的其他權能,包括對水下文化遺產的勘探、開發、保護和打撈等權利。如在2013 年,英國政府與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就“富偉”(HMS Fowey)號沉船達成諒解備忘錄。46National Park Service Signs Agreement with Great Britain to Protect 18th-Century Shipwreck,NPS (27 Aug 2013),https://www.nps.gov/bisc/learn/news/fowey-agreement.htm.該沉船于1748 年在邁阿密附近海域觸礁沉沒。該諒解備忘錄承認英國對沉船的所有權以及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根據其政策、2004 年美國《沉沒軍事航行器法》(Sunken Military Craft Act of 2004)和《水下公約》繼續對其實施保護的權利。總而言之,從文化遺產保護的角度來看,賦予國家所有權更有利于文化遺產的妥善保護,預防和打擊非法打撈、販運和破壞文化遺產的活動。
2.私人與國家
在調整特定水下文化遺產的國際協定中,雖然締約主體為國家,但并不排除私人在特定范圍內保有水下文化遺產的權利,即私人與國家共同分享水下文化遺產。在承認原始物主所有權的國家,水下文化遺產原則上應歸屬于原所有人,在物主無法辨明時才歸國家所有。但被認定為文化遺產的水下遺存由于沉沒時間久遠,當事人一般難以提供有效的所有權證明,故原始物主主張所有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47Sarah Dromgoole &Nicholas Gaskell,Interests in Wreck,Art Antiquity and Law,Vol.2,p.103 (1997).
相反,另一類私法上的主體——打撈者則更有可能通過援引打撈法取得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歷史上,在各國尚未就水下文化遺產進行專門立法前,與水下沉船和沉物有關的事項主要適用海事法。如英國《1894 年商船法》(Merchant Shipping Act 1894)一開始并非用于處理被認定為文物的水下文化遺產,而是用于解決海事救助中救助者的求償權。如果水下文化遺產被視為一般海事遺存適用海事法的救助規則,那么其所有權就很有可能根據“發現者即所有者”(Finders,Keepers)的普通法規則,歸屬于打撈者和發現者,或被拍賣用于支付打撈和救助費用。因此,對于早期的水下文化遺產,即使打撈者無法直接獲得打撈物的所有權,也可以主張拍賣打撈物所換取的收益。48根據英國《1894 年商船法》第546 條的規定,由收貨人以外的任何人為英國海岸或附近失事、擱淺或遇險的船舶提供救助的,該船只、貨物或沉船的所有人應向船東支付合理的費用。參見Art.546 of Merchant Shipping Act 1894.
與國內法一脈相承,早期國家簽訂的雙邊協定也體現了對打撈者和發現者利益的維護。例如,在1989 年英國與南非《關于“伯肯黑德”號沉船救助規范的換文》(以下簡稱“《‘伯肯黑德’號換文》”)中,雙方特別約定,除了被認定為私人所有并扣除根據現行救助安排支付給打撈者的部分外,任何打撈的金幣由兩國平均分配。49Exchange of Notes between South Afric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oncerning the Regulation of the Term of Settlement of the Salvaging of the Wreck HMS Birkenhead,22 September 1989.無獨有偶,1997 年英國與加拿大《關于“幽冥”號與 “恐怖”號沉船的諒解備忘錄》(以下簡稱“《“幽冥”號與“恐怖”號諒解備忘錄》”)第4條也作了類似規定:“對于任何在沉船上發現的黃金,在排除私人所有并扣除任何第三人依法享有的部分后,由兩國平均分配所有權。”50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Great Britain and Canada pertaining to the Shipwrecks HMS Erebus and HMS Terror,5,8 August 1997.可見,在不改變船體歸屬的情況下,至少對船貨及黃金等有價物,允許私人取得所有權。
然而,財產與保護的相對立,暗示了商業的掠奪性。51Geoffrey Lewis,Law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by PJ O’Keefe and LV Prot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Vol.1:1,p.257-260 (1992).隨著商業打撈活動對水下文化遺產的毀滅性破壞以及各國水下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的增強,允許私人打撈者取得打撈物的傳統已逐漸被國際社會摒棄,《水下公約》也基本沒有打撈法和打撈物法的適用空間。52《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第4 條規定:“打撈法和打撈物法不適用于開發本公約所指的水下文化遺產的活動,除非它:(a)得到主管當局的批準,同時(b)完全符合本公約的規定,同時又(c)確保任何打撈出來的水下文化遺產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這一嚴格的條件基本無法得到滿足。即使適用打撈法,打撈者也只能取得所獲財產價值一定比例的酬勞,而不會被直接授予全部或部分打撈物甚至沉船的所有權。53Russel G.Murphy,The Abandoned Shipwreck Act of 1987 in the Millennium: Incentives to High Tech Piracy,Ocean and Coastal Law Journal,Vol.8:2,p.167-203 (2003).因此,在水下文化遺產國際協商機制的實踐發展中,允許私人所有權的立法模式也將逐漸被摒棄。
3.排除特定主體的所有權
在現行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中,締約國還可能通過協議共同放棄對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主張,共同行使對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的權利,并排除私人未經許可的打撈活動。這一約定因循了《水下公約》為全人類共同之利益來保護水下文化遺產、鼓勵締約國根據具體情況和各自能力采取單獨或聯合措施的宗旨和主張,54《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第2 條第3 款、第4 款。也符合公約對打撈法的實際適用范圍進行大規模限縮的目的。在此類協議中,所有權的爭議并非懸而未決,而是通過任何國家均不能取得所有權的方式來實現利益的相互制衡。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妥協性安排并不意味著水下文化遺產將成為全人類共同財產,由人類共同享有所有權。人類共同所有權主張文化財產屬于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無論其來源地或所在地如何,均不產生排他性的財產權利或受任何國家管轄。55John Henry Merryman,Two Ways of Thinking About Cultural Propert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0:4,p.831-853 (1986).其理由在于具有重要歷史和考古意義的文化財產應為全人類的利益保護。56同前注27,William V.Dunlap,p.426-427.但是,為全人類之共同利益保護并不能反證人類共同享有所有權。
將水下文化遺產視為人類共同財產既不符合國際實證法的要求,也與各國的國家實踐不相容。在國際層面上,《水下公約》并沒有排除各國通過國內法或國際協議協調水下爭議財產所有權的權利,即承認國家的所有權主張;57《水下文化遺產公約》在序言中提到水下文化遺產是“人類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是各國人民和各民族的“共同遺產”,但并沒有規定各國應該放棄對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事實上反倒是將所有權問題排除到該公約的討論范圍之外,回避對水下文化遺產歸屬的確認,將其交由各國國內法規定,即默認了各國對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主張。《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至少除了國家管轄以外的區域內的資源為人類共同繼承財產,其勘探和開發應為全人類的利益而進行,但僅限于自然資源。58有學者指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49 條并未使用“人類共同繼承遺產”的表述,而是“為全人類利益”的措辭,所以國際海底區域內文化遺產的地位顯然不同于其他自然資源。參見孫雯:《水下文化遺產國際法律問題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64-65 頁。在國內層面上,各國與水下文化遺產有關的政策、主張以及跨國司法實踐,都是以一國對爭議對象享有所有權為前提的。文物國際主義并非要求任何國家都放棄對文物的所有權,而是強調無論文物的歸屬如何,它不僅是所在國的財富,也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強調文物的共同分享和共同保護。59李玉雪:《對“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法律解讀——以文物保護為視角》,載《社會科學研究》2009 年第5 期。
在著名的“泰坦尼克”(RMS Titanic)號沉船案中,“泰坦尼克”號巨型郵輪于1912 年沉沒,其船體于1985 年在加拿大沿海被發現,隨后成為考古學界和打撈者競相考察的對象。為保護船體的完整性和船上遺骸的尊嚴,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四國于2003 年簽訂了《關于“泰坦尼克”號沉船的協議》。60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Shipwrecked Vessel RMS Titanic,6 November 2003.協議并沒有約定所有權歸屬于某國,而是規定任何國家均不得主張所有權。締約國對此主要出于以下現實考慮:對于一艘沉沒時間相對較短且世界知名的沉船,任何觸及所有權的嘗試不僅會導致遇難者后代提出潛在的索賠請求,而且還會引發另一個問題,即如果無法辨明原始所有人或繼承人,那么所有權應歸誰所有?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將會增大締約國在談判過程中的利益摩擦。61Sarah Dromgoole,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Titanic: Problems and Prospects,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Vol.37:1,p.1-31 (2006).是故,出于對所有權復雜性的考慮,協議的締約國最后同意暫時擱置對所有權的討論。然而,約定排除特定主體的所有權并不意味著協議當事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無權對泰坦尼克號進行打撈或主張權利。根據《水下公約》第1 條水下文化遺產應至少沉沒100 年的規定,在協議簽訂時,泰坦尼克號沉船并不屬于公約的保護范圍,無法依據公約禁止對沉船進行商業打撈。因此,《關于“泰坦尼克號”沉船的協議》旨在突破公約有限的覆蓋范圍,既解決所有權的潛在爭議,又為沉船的保護劃定標準。
在1995 年芬蘭、愛沙尼亞與瑞典《關于“愛沙尼亞”號沉船的協議》中,締約方同樣未對所有權提出明確主張,而是將遺骸及其周邊地區作為海難受害者的最后安息地并給予充分尊重。62Art.1 of Finland,Estonia and Sweden Agreement regarding the M/S Estonia,23 February 1995.協議規定各方應通過制定國內法,將破壞沉船及其周邊遺址的行為認定為犯罪,禁止任何由此提出的財產請求。63同上注,Art.4.
因此,在處理水下文化遺產爭議的雙邊或多邊協定中排除特定主體的所有權,其主要目的在于擱置爭議、促進合作、防止私人打撈和破壞,為全人類共同利益而保護之,但并不能由此產生將所有權置于全人類所有權高度上的法律效果。
(二)所有權的歸屬
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歸屬,是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的核心問題。如前所述,由于各國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立法差異,導致所有權歸屬的法律沖突,其中主要為沿海國和來源國之間的沖突。因此,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歸屬爭議的解決,也主要在于調和沿海國與來源國的矛盾。概言之,現行雙邊或多邊協定對所有權歸屬問題的處理主要采取“來源國所有”與“沿海國共享”相結合的折衷方式,遵循水下文化遺產“共同開發”的價值理念。
根據“澳荷古船協議”第1 條,荷蘭作為該公司財產的繼承人,將其位于西澳大利亞州沿海及以外的沉船及其任何物品的一切所有權和利益轉移給澳大利亞。64Art.1 of Agreement between the Netherlands and Australia concerning Old Dutch Shipwrecks,6 November 1972.澳大利亞特別出于歷史或其他文化目的,承認荷蘭繼續享有對該沉船上所獲財產的利益。該條規定對所有權的處理分為兩步:第一,承認荷蘭作為來源國享有對沉船的所有權,且在沉船發現時相較于澳大利亞為原始所有,其法律依據是國家對法人消滅后無人繼承財產自動成為其合法繼承人,進而取得對該財產的所有權;第二,荷蘭政府以所有人的身份對財產進行處分,將其所有權及財產利益轉移給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因而繼受成為財產的實際所有人,有效協調了來源國與沿海國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
折衷方式的優勢在于平衡了沿海國和來源國的權利主張,既尊重了來源國對文物所具有的歷史和文化聯系,又兼顧了沿海國基于國家主權對本國領土范圍內的事務進行管理和控制的權力。同時,協議的規定弱化了水下文化遺產沉沒地點的偶然性所帶來的權利行使的障礙。一方面使來源國的所有權主張得到他國承認和執行,具有域外效力;另一方面又尊重了沿海國的文化遺產保護立法,維護本國的司法主權和管轄權。最后,所有權的歸屬不是絕對的,來源國依然享有對標的物提出主張的權利,并與沿海國合作開展水下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發掘,體現了共同開發和協商合作的基本原則。“澳荷古船協議”雖只調整特定文物,但作為成功范例,影響了其他水下文化遺產國際爭議的解決。
采取類似所有權處理方式的雙邊或多邊協定還有1997 年英、加《“幽冥”號與“恐怖”號諒解備忘錄》和2003 年美、法《“拉貝爾”號協定》。依《“幽冥”號與“恐怖”號諒解備忘錄》第1 條,英國作為沉船的所有人,65“幽冥”號與“恐怖”號為位于加拿大境內的英國皇家海軍軍艦,參見前注50。當沉船及船貨位于水下時,英國不放棄所有權或主權豁免,一旦確定沉船的位置及身份,英國將授予加拿大所發現的全部文物的所有權,66同上注,Art.1.包括授權加拿大保管和控制沉船及其船貨的權利,以及對其進行調查、發現和發掘的自由裁量權。依《“拉貝爾”號協定》第2 條規定,法國政府無使沉船返還其領土的迫切要求,但從未放棄或轉移、并將繼續保有沉船的所有權。該沉船由德克薩斯州歷史委員會保管,期限為自協議生效之日起99年,除非有相反約定,在期限屆滿后自動延長。67同前注40,Art.2.此外,協議還規定由法國國家海軍博物館與德克薩斯州歷史委員會共同協商決定沉船的保管、研究、存檔和展覽等工作。68同上注,Art.3.
(三)所有權擔保責任的免除
由于水下文化遺產的雙邊或多邊協定只對簽署國有效,而對其他第三方則無效,69《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4條規定:“條約非經第三國同意,不為該國創設義務和權利。”換言之,締約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個人和實體均有可能在協議簽訂后提出與所有權相關的權利主張。鑒此,締約國在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條款的商定中,尤其是在所有權轉讓或共享的情況下,還會考慮納入免責條款,要求受讓方免除出讓方的所有權擔保責任,并由受讓方向出讓方為因權利瑕疵所遭受的損失提供救濟。如在英國和意大利政府于1952年簽訂的《關于“斯巴達”號沉船撈救換文》(以下簡稱“《“斯巴達”號換文》”)中,該案涉及一艘在意大利海灣沉沒的英國皇家海軍艦船。70Exchange of Not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Italy regarding the Salvage of H.M.S.“Spartan”,6 November 1952.協議第1 條規定,英國政府同意接受意大利政府提出的獲取沉船打撈收益50%的提議。該協議將沉船的打撈權授予沿海國即意大利,并由雙方共享打撈所得。此外,協議第2 條和第3 條還規定,意大利免除英國在沉船所有權方面的任何責任。若第三人基于與沉船有關的任何理由提出索賠,意大利應補償英國由此遭受的損失。71同上注,Art.2,3.
除締約國外,潛在的主張財產權利的第三人主要包括:(1)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主張來源國優先權利的其他與該文物具有文化、歷史上實際聯系的國家;(2)水下文化遺產的原始物主;(3)協議簽訂前已開展打撈活動的私人商事主體;(4)協議簽訂后依然開展打撈活動的來自第三國的打撈者。具體而言,若來源國與沿海國在協議中將水下文化遺產視為無主物并對其權屬進行了分配,將涉及對原物主及其繼承人的補償問題,重點在于補償的標準為何,以及是否只有在第三人提出請求時才能予以救濟。72同前注27,William V.Dunlap,p.440.上述義務將由依協定實際取得所有權的一方來承擔,旨在平衡締約國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若涉及商業打撈活動,協議簽訂前符合沿海國法律的打撈行為,應該得到認可并依打撈所得給予打撈者相應報酬。協議簽訂后,相對國通常同時在協議中禁止私人未經許可的發掘和打撈活動,該禁止在締約國境內有效,因而也應成為規范在締約國境內從事打撈活動的第三國私人或其他商事主體的法律規范。73如根據英國與南非1989 年《關于“伯肯黑德”號沉船救助規范的換文》,英國政府不得就該沉船訂立任何救助合同,也不得反對南非政府根據適用的南非法律,維持其對沉船現有的救助安排,參見前注49。商業打撈者在協議生效后的打撈行為將受到限制。
四、對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的雙邊或多邊協定的評價
通過對現行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的雙邊或多邊協議的考察,爭議相對國在解決該問題時通常注重締約方的利益平衡,遵循共同開發的理念,促進了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糾紛的妥善解決。此外,所有權條款只是締約國協議的基本內容之一,此類協議還解決了爭議水下文化遺產的打撈、管理、保護以及打撈物的公開展示等具體問題。然而,此類協議通常僅體現當事國的合意和妥協,對第三方沒有約束力,實際執行效果因而受到限制。
(一)國家間訂立雙邊或多邊協定的優越性
從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議的角度來看,當事方為此訂立雙邊或多邊協定的優越性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國際協定是協調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法律沖突的直接調整方法。所謂直接調整方法,是指用直接規定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實體規范”來調整國際民商事關系當事人之間權利與義務關系的一種方法。74霍政欣:《國際私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0 年第2 版,第11-12 頁。作為直接調整方法的規范表現形式之一,統一實體規范有利于避免間接調整方法即沖突法方法產生的缺陷,如可預見性較低、難以兼顧實體正義等問題。雖然跨國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爭端的主體是主權國家,但其爭議的標的為私法上的所有權,可以通過國際私法的調整方法來解決。
從當前適用于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各國立法和實踐來看,要通過一般性的連結點和沖突規范來指引合適的準據法還存在較大障礙,如存在各國法律消極沖突明顯、連結點的重要程度受海域法律地位的影響較大等問題。75如領海范圍內更加注重對沿海國主權的尊重,更主張沿海國法的適用,而在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以及公海等海域,來源國的優先權更受重視。因此,通過國家間雙邊或多邊協定的方式來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法律沖突,能夠直接確立締約國的權利義務關系,根據締約國的立場和主張選擇最符合締約國利益的所有權制度模式,更能為締約國所接受,妥善解決國家主權豁免等特殊問題。當前水下文化遺產國際協定的所有權條款設計,兼顧了來源國優先權和沿海國管轄權,不失為協調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法律沖突的折衷選擇。
通過雙邊或多邊協議解決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爭議,可以避免因法律缺位或證據不足等問題而使訴訟難以進行或判決無法得到被請求國承認和執行的困境。76Irini Stamatoudi,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Insights on Cases of Greek Cultural Property: The J.P.Getty Case,the Leon Levy and Shelby White Case,and the Parthenon Marbles Cas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Vol.23:4,p.433-457 (2016).隨著國際協商和合作的原則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納,其理想的結果就是達成雙方均能接受的安排,妥善解決糾紛,避免對簿公堂。特別是對一國軍艦而言,無論其沉沒于何地,現有條約實踐已證明,國家間合作是最好的解決辦法。77Mariano J.Aznar,The Legal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Concerns and Proposals,in Carlos Espósito,et al.eds.,Ocean Law and Policy: 20 Years under UNCLOS,Brill Nijhoff,2016,p.146.
第二,國家間雙邊或多邊協議有利于促進國際規則的發展特別是國際習慣法的形成。目前國際上尚未有調整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統一國際法規則,締約國在現行國際公約的基礎上,通過締結雙邊或多邊協議,加強對水下文化遺產的保護,特別是對不屬于公約調整范圍的事項,如所有權問題的解決,將有利于促進公約一般目的的實現,78同前注2,Sarah Dromgoole,p.343.還可以彌補公約不足,為公約的修改和完善奠定基礎。
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國家實踐,是形成國際習慣之通例的重要途徑之一。國際習慣作為國際法的重要淵源,是“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79周鯁生:《國際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10 頁。首先,水下文化遺產國際條約實踐可以發展成國家間的一般實踐。當前,各國通過外交途徑處理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法律爭端的積極性較強,并試圖緩解船旗國主權豁免與沿海國管轄權之間的矛盾,以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80同前注25,Craig Forrest,p.47.但是,現有雙邊或多邊協議所采取的條款設計雖大同小異,但要形成一般實踐,還需要更多的國家實踐予以佐證。其次,協議中對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歸屬的認定,有待形成一般國家的法律確信。國際習慣的形成要求各國一般將這種實踐所表現的行為規則認定為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81同前注79。當前國際協定僅在締約國之間具有拘束力,但各國對所有權的約定方式,則有可能在實踐中被接納為國際通行規則,如兼顧沿海國和來源國利益,特別是所有權和管轄權的平衡等,從而形成抽象化的所有權規范結構。
(二)國家間訂立雙邊或多邊協定的局限性
當然,由于國際條約只體現締約國的意思自治,并不具有普遍約束力,其局限性顯而易見:
第一,相關協定對第三國沒有法律約束力。如前所述,依《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條約非經第三國同意,不為該國創設義務和權利。82《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4 條。因此,如果第三國國民或船舶打撈水下文化遺產而產生的所有權爭議是不能適用這些協議的。83同前注36,郭玉軍,第334 頁。除非爭議發生在締約國沿海主權管轄的范圍內,且沿海國已將條約轉化為國內立法并加以適用,那么該條約也應與本國相關國內法共同調整本國管轄海域內的打撈活動,其適用空間極為有限。此外,既有條約只針對特定的沉船和沉物,對于廣闊的海域內尚未發現的沉船及其他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依然處于未決狀態。從另一角度來看,盡管以條約的方式規定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難以對抗第三人,但實踐中參與協商訂立條約的主體一般是與水下文化遺產具有直接利益關系的沿海國或來源國,具有各自主張所有權的法律基礎,涉及毫無聯系的第三國可能性較小。協議的主要目的不是對抗第三人,而是文化遺產的開發、保護和管理,不應因所有權爭議而擱置對文化遺產的保護。
第二,對于以商業開發和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國際協定,將水下文化遺產分配給私人打撈者不利于制止商業打撈行為,進而阻礙文化遺產的妥善保護。如英國主張王室取得無人主張沉船的所有權,其最初的目的在于為國庫提供收入來源。84同前注2,Sarah Dromgoole,p.102.前文述及的《“伯肯黑德”號換文》和《“幽冥”號與“恐怖”號諒解備忘錄》,均涉及對打撈利益的安排,特別是對黃金等有價物的分配。此類協定將水下文化遺產作為財政收入和經濟利益的來源,而不是作為文化遺產加以善待,將會影響水下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和效果。
五、國家間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雙邊或多邊協定對中國的啟示
我國是海洋大國,同時也是水下文物大國。上世紀以來,我國水下文物遭到大規模的盜撈和破壞,文物流失嚴重,特別是南海地區的水下文物。85如1999 年英國商人邁克爾·哈徹在“泰興號”(Tek Sing)沉船上打撈上百萬件中國瓷器,并在德國拍賣行上拍賣。參見Discovery of the Tek Sing Cargo,kohantique (5 Dec 2021),http://www.koh-antique.com/discovery/teksing1.html.此后,水下文物保護的重要性逐漸受到立法機關的重視,但由于有些古代船舶沉沒的海域并非中國管轄海域,中國無法延伸本國的立法和執法管轄權。86如1989 年在越南附近海域發現的“頭頓號”(Vung Tau)亞洲商船,船上運載的近三百萬件珍貴瓷器在佳士得拍賣會上拍賣,其中有75%的拍賣所得最終被越南政府取得,參見Christie’s Amsterdam B.V.,The Vung Tau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Christie’s,1992.僅靠本國立法來解決水下文物的保護問題往往捉襟見肘,目前我國尚未有解決水下文物所有權爭端的國際法律實踐。
由于我國尚未批準《水下公約》,且該公約對水下文化遺產的所有權未作規定,加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水下文化遺產規定之模糊,使我國主張本國海域內的水下文物所有權或他國海域內來源于我國的文物缺少充分的國際法律依據。鑒此,為加強所有權保護,防止文物不當流失,我國可基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3 條的國際合作精神,與他國就水下文化遺產爭端加強協商與合作,并借助雙邊或多邊機制解決爭端。
第一,我國締結或參加的雙邊或多邊協定,應體現我國水下文物主權立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我國對內水和領海內發現的一切文物主張所有權和管轄權,無論其起源國為何。87《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第2 條第1 款、第3 條。這一規定并沒有將外國軍艦設置為例外,我國對領海內沉沒之他國軍艦的主權豁免尚未有明確主張,有待實踐檢驗。88LIU Lina &LIU Shuguang,From Difference to Convergen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and the 2001 Convention,Comparative Maritime Law,Vol.52:167,p.149-165 (2013).從互惠角度來看,目前主要的海洋大國大多承認他國沉沒軍艦或政府船舶在無明示放棄的前提下享有主權豁免。中國可以在堅持領海管轄權的基礎上,對除船體以外的來源于我國的船貨主張所有權,并與他國就遺址的共同開發和管理展開合作。除此之外,對于我國立法中主張所有權的其他水下文物,在進行國際談判時,可以聲明我國立場。在堅持我國對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基礎上,將勘探權和發掘權與締約國共享,甚至可以將除歸屬外的其他所有權權利,如占有、保管、公開展示等通過協商方式公平分配。
第二,我國可靈活利用雙邊或多邊協定,反補國內立法不足。對于領海以外的屬于我國管轄范圍的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只對來源于我國以及來源國不明的文物主張所有權和管轄權。89《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第2 條第2 款。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3 條第2 款的規定來看,至少在毗連區范圍內,沿海國有權制止和打擊文物販運活動,該條并沒有對文物的來源和性質作出限制。90《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3 條第2 款規定:“為了控制這種文物的販運,沿海國可在適用第三十三條時推定,未經沿海國許可將這些文物移出該條所指海域的海床,將造成在其領土或領海內對該條所指法律和規章的違反。”因此,對于毗連區內起源于外國的水下文物,我國對非法將其移出海床的行為享有管轄權,無單方作出自我限制之必要。91趙亞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水下文化遺產公約〉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 頁。我國在與他國就領海以外管轄海域的水下文化遺產締結協定時,可直接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主張管轄權,作為該海域水下文化遺產雙邊合作的基礎。此外,出于對他國主權和管轄權的尊重,對外國領海以外的其他管轄海域和公海,我國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僅享有辨認物主的權利,對于他國領海內來源于我國的水下文物則沒有規定。92《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第2 條第3 款、第3 條。通過簽訂雙邊或多邊協定,可以有效克服立法權的地域限制,保護我國管轄海域外來源于我國的水下文物,特別是對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水下文物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總而言之,國家間解決水下文化遺產所有權的雙邊或多邊協議在國際實踐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一方面有助于協調國內立法沖突,另一方面彌補了國際立法的缺陷,在規范結構上對所有權與管轄權的協調模式進行了有益探索,對我國開展水下文物保護的國際法律實踐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