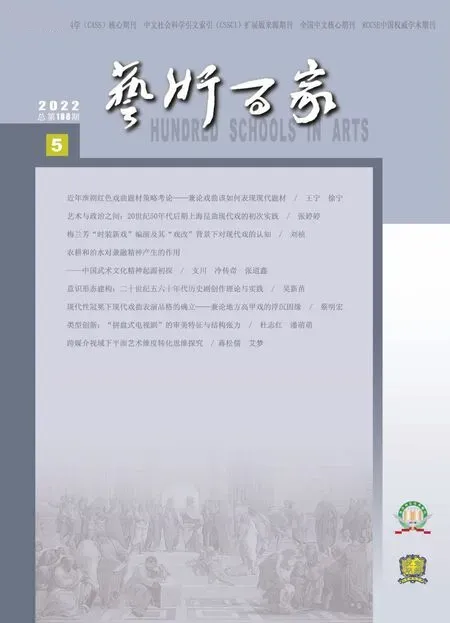農村題材精品豫劇的成功經驗?
王璐瑤,李偉
(上海戲劇學院,上海 200040)
2020 年9 月16—20 日,由中國戲曲現代戲研究會和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廳共同主辦的“紀念楊蘭春誕辰100 周年暨中國戲曲現代戲研究會第32 屆年會”在河南鄭州舉辦。 楊蘭春作為戲曲現代戲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豫劇《朝陽溝》創作于1958年,60 余年中演出超過了6000 場。 這個現象是不尋常的,它創造了中國戲曲現代戲的一個奇跡。 對于這部戲的學術探討,也是賡續不斷。 以中國知網收錄的文獻為例,從在河南鄭州的首場演出時間1958 年3月20 日到2021 年6 月,共有185 篇文章(包含學位論文30 篇);2016—2018 年達到了一個研究探討的高峰,共發表43 篇論文。 這三年的高產必然得益于《朝陽溝》60 周年演出的紀念熱潮。 185 篇論文包括以下四個方面:介紹《朝陽溝》劇本的生成及修改;介紹《朝陽溝》編劇導演、唱腔、舞美設計等各個環節的工作(其中介紹編劇、導演、唱腔設計占較大分量);辨析《朝陽溝》傳承至今的原因;總結河南豫劇院三團編演現代戲的成功經驗。 通過文獻梳理我們可得出一個普遍共識:豫劇《朝陽溝》久演不衰,它代表了豫劇藝術的精品高度,60 年過去了,這部戲并沒有退出舞臺,未曾讓觀眾忘記,它反而創造了較強的藝術鑒賞影響力,讓戲劇學界對其長久保持研究的熱情。
進入21 世紀,河南豫劇院三團成功編創演出的三部豫劇紅色農村題材精品《村官李天成》《焦裕祿》《重渡溝》,生動塑造了“村官”“縣官”“鄉官”一系列基層黨員干部形象,被稱為“公仆三部曲”。 這三部戲搬上舞臺,既是對豫劇現代戲優秀創作演出傳統的繼承,特別是對《朝陽溝》精品藝術精神的傳承,更是對豫劇現代戲紅色農村題材表現內容以及呈現形式的拓寬延展。 三部戲編劇環節的大量工作皆出自一名作家——姚金成①之手,這看似神奇的巧合,實則實至名歸。 “《村官李天成》熱演超過了16 年以上,《村官李天成》演出超過了800 場,《焦裕祿》演出超過了300 場。”[1]《村官李天成》自2001 年問世以來,先是唱遍河南,后又五上北京,兩進上海,在廣東、海南、山東、山西等省演出,該劇在新世紀的戲劇舞臺上掀起了一陣“村官旋風”[2]。 《村官李天成》榮獲中宣部第十屆“五個一工程獎”、文化部第十三屆“文華獎”的新劇目獎。 《焦裕祿》榮獲文化部第十五屆“文華大獎”、中宣部第十三屆“五個一工程獎”。 《重渡溝》榮獲文化部第十六屆“文華大獎”、中宣部第十五屆“五個一工程獎”。 以中國知網收錄的文獻為例,與《村官李天成》相關的論文從2004 年6 月至2018年12 月共有40 篇,其中2012 年的發表論文量達到高峰,19 篇論文反映了戲劇學界對該劇創演十周年、演出達800 場成績的肯定和藝術解讀。 與《焦裕祿》相關的論文從2011 年12 月至2021 年8 月共有43篇,其中2017 年發表的14 篇論文在數量上達到一個高點,因為該劇在該年8 月進京參加“第四屆中國豫劇節”,再一次引起戲劇學界的關注。 與《重渡溝》相關的論文從2018 年11 月至2021 年8 月共有20 篇,并在2019 年的中國第十二屆藝術節期間形成探討的熱點。
《朝陽溝》《村官李天成》《焦裕祿》《重渡溝》這四部戲獲得了國家領導、專家學者等多方肯定以及觀眾群體長久的認可贊揚,可以說是豫劇紅色農村題材的精品之作,代表了河南省現代戲創作的高度和深度。 精品創作演出是如何上升到這樣的水準,或者說一部現代戲是怎樣成為藝術領域精品的呢?
一、突破固有創作模式
《朝陽溝》《村官李天成》《焦裕祿》《重渡溝》等見證了豫劇現代戲60 年的發展歷程,孕育培養它們的河南省豫劇院三團(后簡稱為“三團”,“一團”“二團”同)更是舉起全國現代戲創演的大旗。 多位學者研究探討“三團”的風格和傳統,如安葵的《傳承藝術經典 弘揚優良傳統——〈朝陽溝〉為什么能夠流傳和它帶來的啟示》《賈文龍繼承弘揚了三團的傳統》,安志強的《豫劇三團現代戲藝術創作的傳承與發展》,朱鋒的《〈重渡溝〉對豫劇現代戲優良傳統的傳承與創新》等多篇文章,歸納總結了創作各個環節上生活化、鄉土化的特征突出,把握時代和社會熱點,人物形象塑造生動感人等三個特征。 我對這三個特征是認同的,但它們更應該定義為“三團”優秀傳統的表層呈現,而豫劇三團之所以能夠扛起全國現代戲排演的大旗,走過輝煌60 年,是因為它源于河南省豫劇院三團的精神——突破固有創作模式,這是“三團”藝術創作的內核驅動力。 如果未能理性認識這種創作上的突破,對“三團”現代戲精品的評鑒論述就會跌入概念泛化的窠臼,甚至評論者在評論各劇種的多數現代戲時都會運用這些“放之精品而皆準”的套話。
(一)《朝陽溝》的突破
《朝陽溝》產生之前,豫劇現代戲是什么樣的?
《豫劇傳統劇目匯釋》收錄的豫劇劇目共有914出,從情節內容上明顯可知,這些劇目已經初顯現代戲的雛形,比如《煙鬼顯魂》《改良新家庭》這類劇目是受辛亥革命以來的文化變革影響而編寫的。 1927年王鎮南在開封“游藝訓練班”時,先后編演過《長春慘案》《五卅慘案》《顧正紅》《袁世凱皇帝夢》等豫劇時裝戲。 抗日戰爭爆發后,豫劇現代戲的創作趨于穩定,這時上演了王鎮南編劇、常香玉主演的《打土地》。 大眾劇社1938 年編演現代戲《罵寇》,1941 年編演《沙區掃蕩》等。 這些劇目的內容是現實題材的,但表現形式上依舊運用傳統戲曲的“四功五法”和化妝道具。 比如《打土地》的故事情節是發生在抗戰緊急情態下的現實生活,但主演常香玉依舊以古裝打扮亮相,人物動作也是根據傳統戲曲的程式來進行選取運用。 1947 年冀魯豫邊區進行豫劇改革后,選定119 出戲,能演的舊戲78 出,修改后能演的舊戲20 出,新編的歷史劇14 出,新編的豫劇現實劇(現代戲)7 出。[3]151
新中國成立初期,河南省對全省的文工團進行整編,成立河南省歌劇團,1956 年歌劇團并入河南省豫劇院,更名為河南豫劇院三團,主要任務是創作演出現代戲。 當時香玉劇社被從陜西調回,并被命名為“一團”,其任務為古裝戲的排演。 “娃娃劇團”改為“二團”,演出新編歷史劇。 河南豫劇院對三個團的工作目標是進行明確區分的。 1949—1958 年“三團”現代戲創編的劇目主要為移植改編的劇目,比如為配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貫徹《婚姻法》等運動,推出了《小女婿》《劉巧兒》《血淚仇》《王貴與李香香》《羅漢錢》《小二黑結婚》等一批現代戲。 從上述兩段時間分期來看,新中國成立之前,豫劇現代戲已然創作上演,但并未找到適合其自身內容情節的外部表現方式;新中國成立后至《朝陽溝》搬上舞臺之前的1958年,豫劇現代戲從其他劇種的優秀現實題材作品中汲取藝術養分,創設營建本土劇種的舞臺呈現體制和方法。
《朝陽溝》自編自導自演,標志著豫劇現代戲在運用傳統戲曲形式、表現現代生活上進入了一個成熟階段。 “三團”的表演理念不同于“一團”“二團”古裝戲的傳統程式,它以楊蘭春為主導,多位演員共同實踐“從生活出發到舞臺上的真實生活”,“三團演員的表演深受俄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的影響,跟話劇靠得比較近……三團一切都是新的,雖然也學古裝戲,但最主要的是繼承話劇……《朝陽溝》中的銀環、栓保,跟京劇中的楊子榮、李玉和是不同的,雖然都是現代戲,《朝陽溝》更具生活氣息”[4]。 《朝陽溝》對固有創作模式的突破,不僅體現在編劇、導演、表演三個環節的生活真實方面,還體現在戲曲音樂環節上設計的中西合璧,“作為西洋歌劇的核心組成部分,交響作曲的完美性和表現力令人嘆為觀止。 而河南豫劇院三團在前輩音樂人王基笑、梁思輝、朱超倫等音樂家及歷屆領導班子的共同努力和堅持下,完整保留了目前全國唯一的一支中西混合管弦戲曲樂隊”[5]。
(二)“公仆三部曲”的突破
編劇姚金成在創作《村官李天成》之前,已經是一位作品豐富并且藝術技巧高超的劇作家了,《西門風月》《香魂女》等豫劇證明他是一位古裝戲、現代戲兼擅的創作者。 《村官李天成》是姚金成第一次觸摸“英模戲”的寫作,紅色農村題材的基層干部形象塑造確實不易,但它背后隱含的政府物質支持和榮譽贊揚以及強大的話語權地位,卻是創作者們無法忽視的現實。 姚金成談創作時說:“現代戲難寫,現代戲中的現實題材更難寫,現實題材中的‘英模戲’可謂難上加難。 ‘英模戲’也有一個最吸引人的優勢: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重視和支持,容易獲得排演資金。”[6]但是創作者與這一巨大“誘惑”之間,有一條難以跨越的鴻溝:英模人物的高大全、戲劇人物的扁平無味、故事設計俗套等因素導致戲曲敘事不真實。
《村官李天成》對固有“英模戲”創作模式的突破主要著眼于編劇和表演兩個方面:其一,編劇構思戲曲矛盾時的層層漸進而帶來人物內心的柔性升華,這種升華不是以往英模人物所被詬病的高峰突起的呈現。
該劇矛盾設計落在三點:其一是以李天成為代表的市場經濟思維模式與以老支書李德旺為代表的傳統陳舊觀念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浪潮下農村生活的貧富差距擴大,共產黨員在責任與利益上的失衡。 李天成回村帶領村民建大棚種蔬菜,很快就被鄰村學習,導致蔬菜價格降低。 他改變生產模式,拉長產業鏈,以科學技術為基點建立蔬菜加工公司,但這種市場經濟的思維模式并未得到全村村民的認可,第一點矛盾由此展開。 在李天成的勸說鼓勵下,13 位村委會的黨員簽字購股。 蔬菜加工公司良性運營模式帶來巨大經濟效益,貧富差距拉大,部分群眾諷刺13 位黨員是大款黨員,黨員撈大錢,群眾瞪眼看。 這是第二點矛盾。 這時的李天成并未因為揶揄嘲諷而想到擴股經營。 警醒他的是村里貧困戶老根爺為孫女巧巧掙學費拉千斤磚車而累昏倒的突發事件。 李天成拿著浸滿血的纖繩,想到一代代西李莊的村民都曾拉纖繩賺取血汗錢,市場經濟不能只讓少數人富足,他要帶領全村人共同脫貧致富。 而帶領全村人共同致富的直接途徑是擴大公司營業規模,讓全村人一起入股。 這個辦法引發了全劇的第三點矛盾。 13 位先富起來的黨員干部憑借改革開放的春風而脫貧致富,他們敢闖實干、真誠付出的背后卻是血淚甚至身體上的殘疾。 當初建廠時沒人愿意參與,一看見錢財就眼紅,馬上湊來攫取經濟利益,這個行為在他們看來是無法接受的。 李天成先以老根爺的苦情勸說,后以13 位黨員多年的兄弟情誼作為砝碼,讓大家考慮共產黨員的責任與利益間的取舍和平衡。
從三點矛盾的設計可以看出,編劇并未把村官李天成設計成一個高大全的英雄模范人物。 在真實的生活中,人不可能全知全能,編創者深諳此理,觀眾們也懷有不同于“革命樣板戲”時期的審美趣味。 李天成對于村官責任的認知是一步步漸進升華的,并引發對人物內心情感的深層挖掘,正如《村官李天成》的藝術指導黃在敏所說,“文藝作品不是為政策作注解的,更不是為解決具體問題開藥方的”[7]。
其二,古典戲曲是注重表現的藝術,通過唱念做打營造形式上的極致美感,而深入揭示人物的內心活動是其薄弱環節。 在現代戲中,“三團”的解決辦法是從表演切入的,從生活到舞臺,都表現出表演風格的真實性。 《村官李天成》的突破具體表現在“拉車舞”的身段動作設計上,它改變了以《朝陽溝》為范式的生活化表演,其核心唱段運用了大量傳統戲曲的程式。 這種突破,不僅是“三團”在編演現代戲上的有益探索,更代表了新世紀戲曲工作者對傳統戲曲表演的新思考。 賈文龍化用傳統戲曲“腿腳功”“毯子功”功法,合理搭配蹉步、跪步、劈叉、吊毛等一系列高難度動作,讓觀眾領略到現代戲不是“話劇加唱”,戲曲演員身上的傳統功底從未卸下,他們能夠找到傳統與現代在表演方法上的良性組合。 這種良性的創作模式也得到了羅懷臻的肯定:“《村官李天成》在11 年的創作演出的修改磨練中,實現了三個跨越。 一是從生活原型向藝術典型的跨越,二是從宣傳作品向藝術精品的跨越,三是從原創劇目向保留劇目的跨越,三個跨越或曰三個轉換正是當代戲劇人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河南省各級領導所關心的則是戲劇院團的良性創作與良性發展……我想這也是一條值得深入總結的河南經驗。”[8]正是編劇、表演兩方面對固有創作模式的突破,使得《村官李天成》生動展現了改革開放背景下農村農民生活的動態群像。
《焦裕祿》對固有“英模戲”創作模式的突破主要體現在編創上對特定歷史時期的反思。 1966 年2 月7 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由新華社記者穆青、馮健、周原三人采寫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焦裕祿作為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的符號刻在人們心中。 在20 世紀60 到90 年代的河南戲劇舞臺上,幾十個版本的焦裕祿形象得以塑造。 “今年九月間舉辦的河南省第三屆戲劇大賽……參賽劇目現代戲比例較大,而側重于表現現代英雄模范人物的劇目更受觀眾歡迎。 如開封市豫劇團創演的《焦裕祿》和河南省話劇團演出的《公仆》,都是刻畫一生為振興蘭考而獻身的人民公仆焦裕祿的模范業跡與崇高的精神。”[9]一些作品也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關注和肯定,“4 月9 日晚,江澤民、宋平、李瑞環、李鐵映等同志與首都觀眾一起觀看了現代豫劇《焦裕祿》。 江澤民同志說,你們演得好……這個戲細膩、真實、感人,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10]。 多個版本把重心放在對焦裕祿的贊揚和謳歌上,多是好干部干好事的淺層描述,“三團”創作團隊并沒有重復這一老路,而是帶著觸及社會深層矛盾的問題意識,把這段半個世紀前發生的蘭考往事編創得富有歷史深度。
全劇對以往戲曲敘事的情節突破有四處:剛上任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在火車站送蘭考百姓外出要飯;為林業技術員宋鐵成平反,宋鐵成摘下右派的帽子并受到尊重;帶領全縣購買議價糧;痛斥浮夸風,提出這不是天災而是人禍的控訴。 這四處皆是對以往藝術作品素材的再一次運用,但人性挖掘卻更深更廣。 這種帶著人性溫暖光環的挖掘,讓觀眾在社會發生巨變而關系復雜的今天,看到文藝作品對歷史錯誤的反思態度。 “從1958 年春開始,‘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運動在中原大地如狂飆突起,……各級干部人人自危,違心地說假話、說大話,然后又強行按虛報的產量向農民征糧,造成征購透底,饑荒大面積出現。”[11]劇中宋鐵成用專業技術消滅蘭考“三害”,為了守護這片家園,他一次次講真話,但巨大的社會壓力將他變成噤若寒蟬的啞巴。 這處對歷史的反思不僅僅是通過焦裕祿——黨的好干部——的言語動作來表達的,而且更多地是借助一位普通共產黨員的真誠行動來訴說的。 它的真實也巧妙地體現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走過100 年的風雨歷程,其中有像焦裕祿這樣的英模人物的閃閃亮光,但整片星海是由一位位像宋鐵成這樣敢于講真話的普通共產黨員匯成的。
《焦裕祿·蘭考往事》的最后一場是“病床上痛斥浮夸風”。 焦裕祿帶領群眾購買議價糧卻與當時的一些國家政策相左,人民的好干部從心底里感慨“讓群眾吃上飯錯不到哪里去”,可當他生病倒下,看到報紙上“蘭考大豐收”的浮夸虛假新聞時,這位縣委書記深知購買救濟糧只能緩解一時饑餓之困局,造成三年災害的關鍵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作為這場政治運動的親歷者,他更明白人禍會導致更為深重的危害,在這里焦裕祿叮囑老戰友顧海順說“我們不能再虧了老百姓啊”。 在舞臺呈現方面,該劇在“抗洪舞”唱段處加重演員群舞的傳統戲曲身段動作。 賈文龍化用跪劈叉、跪步、吊毛等多組程式凸顯焦裕祿在身體病痛的艱難處境下內心的掙扎與堅忍。
“公仆三部曲”前兩部的成功對《重渡溝》的創排造成巨大壓力,特別是《焦裕祿》剛剛獲得文化部第十五屆“文華大獎”和中宣部第十三屆“五個一工程獎”的榮譽,試圖超越這個精品的難度太大。 藝術水平高超的“三團”也在這次現代戲創作中被“逼”上陣。 有學者認為:“現實題材的‘英模戲’本身就非常難寫,而‘鄉官’和‘村官’‘縣官’題材又相類,同樣的團隊,同樣的演員,如何能做到別開洞天、另成新局,成為與《焦裕祿》《村官李天成》相映生輝的力作?這始終是我們團隊為之激烈爭論、苦苦追尋的課題。”[6]
《重渡溝》的突破主要表現在人物的塑造方面。首先,《重渡溝》的創作一改《焦裕祿》悲劇色彩厚重的正面人物的常態思維設定,劇中鄉官馬海明的語言動作帶有強烈的喜劇底色,勸說重渡溝鄉民也是隨口就來一段朗朗上口的快板,主角的喜劇化處理藝術性地把該劇的兩個主題——扶貧攻堅和生態保護有機結合起來。 其次,劇中一直“在線”但并未真正出場的張縣長暗含深意。 這是豫劇紅色農村題材作品中從未展現過的一個復雜符號,但又是一個非常真實的表征。 他既是馬海明信賴的老領導,又是表現馬海明人生困局的關鍵人物。 這個人物的設立是從黨員干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中凝練而成的,領導為什么會支持那個帶有明顯的利用資本市場攫取巨大利益之心思的呂二濤? 編創團隊并未給出一個具體明晰的答案,或者說《重渡溝》對藝術創作模式的突破恰好體現為面向復雜多變的社會生活的一種解釋,“生活是復雜的,也永遠是進行時的,就某一個節點來看,甚至常常是混沌的,這恐怕才是一種生活的真實狀態”[6]。
除了人物塑造上的突破,該劇在舞臺呈現上也堅持創新原則。 馬海明剛上場時展示的空中飛人,“雪地舞”里賈文龍化用硬把抖磕、跳轉跪、蹉跪、烏龍絞柱等一系列高難度程式,這些都是戲曲表演在傳統程式運用和人物內心情感的貼合上借助高科技手段的一次頗為成功的嘗試。
二 、編創人員的獨立思考
如果說突破固有的創作模式代表了河南豫劇院三團藝術創作的內核驅動力,那么這一驅動力的關捩點則是編創人員的獨立思考。
首先,“大躍進”時期的豫劇《朝陽溝》并不是對國家政策的簡單圖解與迎合,而是編創團隊思索社會尖銳問題后的答案,與黨中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相吻合。 《朝陽溝》里的銀環代表了城市的知識青年,在她剛開始下鄉勞動時心中便充滿對國家政策的擁護和肯定,可當她在農村不能適應勞動生活時,她卻真實地發問:知識青年去農村勞動不能發揮自己知識的長處,難道不是屈才? 后來經過栓保、老支書等人的勸說,其想法發生突變,認為只要思想正確,干什么都可以馬上適應。 這個故事梗概和人物行動進一步證實了《朝陽溝》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確實承擔了一定的政治政策宣傳教育任務,并且參與到構建國家意識形態和主流話語的工作中。 它從產生到“文革”之前,獲得了戲劇界的熱評和觀眾的掌聲,甚至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贊美表揚。60 年后的今天,一些學者反思這部精品的成功,認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就是一個反對知識的思想,丑化以小市民形象為代表的銀環媽,體現了對城市農村二元對立格局的認知局限。 這種評論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客觀,甚至是因為對一些歷史事件的漠視而導致的對《朝陽溝》的誤讀。
楊蘭春為什么要創作《朝陽溝》? 當年負責河南省戲劇工作的是省文化局副局長馮紀漢,他深諳豫劇藝術,也是楊蘭春尊敬的懂行領導。 他要求楊蘭春一周內拿出一部現代戲,并且要搬上舞臺,在全省文化局長會議上演出。 現在看來,這種工作的分配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但那是在“大躍進”的1958 年,一個劇團別說一周拿出一個現代戲,他們可能會在一個晚上“躍進”創作好幾個劇本。 社會上的“浮夸風”并沒有讓戲劇領域成為例外,遼寧藝術人民公社要求劇作者制訂“兩天寫一出大戲、三天與觀眾見面”的創作規劃,導致創作演出質量嚴重下降[12]13。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提出口號“力爭在國慶節前創作鼓詞、快板、壁畫、舞蹈、歌詞20 萬件”[13]67-68,1958 年10 月文化部召開的全國文化行政會議甚至提出,“要‘大放文藝衛星’以迎接國慶十周年,在全國創作5000 個高水平的藝術衛星向國慶獻禮”[14]10。 這種創作的集體狂熱和口號,隱含了那一代親歷者在特殊時代氛圍里理性的喪失以及深藏于戲劇工作者內心深處的恐懼。 七天半完成豫劇《朝陽溝》的創排在今天看是荒唐的,但在“大躍進”時期應該是正常的。
楊蘭春當時所選擇的“青年下鄉與思想改造”主題,并不是一個主觀迎合國家意識形態的題材,如果想博得更多的關注和支持,他可以寫大煉鋼鐵等更為符合“大躍進”運動的優秀主題,而在接下這個任務時,他只對馮紀漢表明由自己選取寫什么。 因為1957 年楊蘭春去農村勞動,已經促使他構思銀環的故事,那里的農民提出一個讓劇作者思考的問題:“老楊,你說這新社會,誰家的孩子不念兩天書,誰家的姑娘不上幾天學? 讀兩天書上兩天學都不想種地了,這地叫誰種呢? 哪能把脖子扎起來?”[15]61而《朝陽溝》暗含楊蘭春對這個問題思考后的回答,劇中農民的自豪感以及銀環行為的突變,皆來自作者對鄉村生活的憧憬和偏愛,雖然這種回答帶有明顯的阿Q精神,但這個回答顯然不是上級下達給楊蘭春的寫作意圖,也不是他配合自上而下發布的政治文藝要求的反映。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朝陽溝》的修改更能體現編創團隊的獨立思考,“在豫劇三團為亞非作家會議的代表演出《朝陽溝》之前,有人建議這次演出應該加上一段毛主席語錄,解決王銀環的思想改造問題。 楊蘭春認為不妥,被拒絕參加演出”,“1969 年8 月23 日,江青下令修改《朝陽溝》。她說《朝陽溝》是個寫中間人物的戲,實際上寫落后,但還不很反動下流,這個戲是可以改好的”,并給出修改辦法:女主角變為次角,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改造;男角改為主角、正面英雄人物,還得加強貧農父母的戲。[14]從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特殊的歷史語境里,《朝陽溝》是一出表達劇作家對農村農業農民看法的現代戲作品,而他的觀點并不是機械單一地迎合政府文藝政策的導向,更多的反映了個人創作觀點與教育政策的吻合。
其次,“公仆三部曲”表達了編創人員在社會變革環境下對英雄模范這一身份符號的新認知,將其從歷史創作經驗上的“高大全”形象衍化為人性視角下的普通人,演繹英雄模范人物的“由小見大”,即編劇姚金成所說的“低開高走”,避免作品陷入形式主義、簡單化的窠臼。 村官李天成、縣長焦裕祿、鄉長馬海明及其事跡都是真人真事,在這種局限下,很容易出現英雄事跡的堆砌,從而導致政治教化的無限放大。“三團”的編創人員從藝術構思上否定了戲劇人物的“高大全”:李天成在帶領第一批村民創收的時候,沒有想到擴充股權、全村人共同致富。 這一點較為符合從商轉政的人物形象,智慧勤勞的李天成在市場經濟大潮下找準商機,希望帶領全村一起辦廠,但是大多數村民無法接受現代商業的運作模式而選擇放棄。辦廠成功后的村官也沒有因為村民們的嫉妒而馬上擴股,因為擴股意味著放棄自身的經濟利益,而商品市場自帶冒險因素,創業時的觀望、不信任怎么可以換取利益的分紅? 鄉長馬海明甫一登臺,就在謀劃自己的晉升機會,當他后續遇到工作挫折時,也會因為心愛的照相機而內心發生動搖,這種情況在舞臺上是不多見的。 我們經常看到戲曲里的黨員干部不圖官職,一心只為人民群眾服務,可這樣的現代戲很難長久立于舞臺,原因便在于觀眾早已洞悉現實生活與舞臺表現上的巨大鴻溝,人物形象的極不真實生硬地造成英模戲只有謳歌,沒有故事。 《焦裕祿·蘭考往事》最為深刻地表現了編創團隊的獨立思考,直指“浮夸風”的錯誤,并將此歸結為“人禍”。 躺在病床上的好干部得知瓦窯公社虛報產量時,大聲疾呼“這不是天災,是人禍”,語言鏗鏘有力,猶如蒙塵的史書被清正之風吹去塵霾。 觀眾在劇場能夠瞬息間回溯至“大躍進”時期,感受“五風”泛濫而導致的人心恐懼和人性扭曲。 編創者的獨立思考是保證文藝作品反思歷史、回歸真實的有力支撐,這條成功經驗可謂是豫劇現代戲的一大傳統。 當姚金成筆下的焦裕祿呼喊“人禍”災難時,我們不禁想到杜赩、李殿臣所作的《謊禍》,一部現代戲從“反右傾”運動寫到浮夸風,撥開那段塵封歷史的迷霧,使迷霧籠罩著的大規模餓死人的現實事件呈現出本來的真實面目。 戲曲現代戲提出人民最關心的重大生活問題,它有激動人心的力量。
編創人員的獨立思考是紅色農村題材精品豫劇的成功經驗之一,那么思考的獨立是如何保證的? 我認為對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探索把握是重要因素,正如“豫劇現代戲之父”楊蘭春的創作體會,“生活是戲的生命,脫離群眾生活,藝術生命就會枯竭。 生活有多深,水平有多高,這是衡量作品質量的尺度”[16]。焦裕祿題材是河南現代戲創作的高頻主題,時至今日,多數劇目因其思想內涵的單薄而沒有走得更遠。
三、 良好的戲劇生態環境
如果說突破固有創作模式是紅色農村題材精品豫劇的內核驅動力,而其關捩點是編創人員的獨立思考,那么良好的戲劇生態環境,也是產生精品之作不容忽視的一個成功經驗。 豫劇現代戲所依托的良好生態環境至少有以下三點:政府部門的鼓勵支持,河南豫劇院三團的精準定位,專家學者的批評引導。
(一)政府部門的鼓勵支持
《朝陽溝》和“公仆三部曲”雖然創作時間不一,產生的社會背景和文化思潮也各有不同,但是有一個基點是不能抹去和忘記的——紅色。 它除了代表著藝術編創方面的高標準、高要求外,高揚主旋律也是該劇成為精品的重要因素。 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現代戲的編創演出,無論是出于宣傳的需要,還是期冀傳統藝術跟上現代社會的審美需求,在紅色農村題材精品豫劇的孕育過程中,政府部門的鼓勵與支持很多。 除卻特定歷史語境下政府部門對現代戲的肯定和鼓勵,《朝陽溝》甫一登場,就受到國家領導的關注,它首演于1958 年3 月20 日,一個月后在河南省軍區禮堂為周恩來等黨中央領導演出,同年夏天應邀到北京參加全國戲曲現代題材的展演,《人民日報》等多家大型媒體發表評論文章。 1963 年《朝陽溝》拍成戲曲藝術片,電影上映致使傳播力度更大更廣。 同年12 月31 日晚,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在中南海觀看了《朝陽溝》的演出,并予以表揚。 “公仆三部曲”之一的《村官李天成》更是得到國家領導人的鼓勵,甚至可以說,這部戲是在鞭策中“被動”創作出來的,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曾慶紅對當時河南省委常委、秘書長王全書說:“豫劇在群眾中很有基礎,要是以西辛莊和李連成的事跡為素材、為原型,搞成一臺豫劇現代戲,一定會受群眾歡迎! 兩年時間可以搞出來吧? 你們搞吧,搞出來我一定看!”[17]不僅《村官李天成》受到重視,而且《焦裕祿》《重渡溝》也得到國家藝術基金和全國“五個一”精品工程、“文華大獎”這類政府文化獎項的鼓勵和支持。
(二)河南豫劇院三團的精準定位
河南省文化部門對河南豫劇團在藝術創作上作了明確分工:“一團”整理改編傳統戲,“二團”專攻新編歷史劇,“三團”一心編創戲曲現代戲。 這樣明確的分工,在全國各省的文藝院團組織安排方面,也是較為罕見的。 60 年時光荏苒,“三團”在現代戲的耕耘培育上,留下許多有意義的實踐探索。 很多學者都一致認為,《朝陽溝》之所以流傳至今,最可取的優點便是音樂創造上的天然和諧。 筆者認為對豫劇現代戲音樂設計環節的重視,源于“三團”的精準定位。首先,“三團”是由歌舞劇團整編而成的,相較于傳統戲曲藝人和班社,他們對戲曲音樂有著自身更為獨特、現代的理解。 其次,楊蘭春在中央戲劇學院學習三年,擁有西方戲劇理論基礎和話劇創作體驗和經驗,從他畢業前夕創作的歌劇版《小二黑結婚》便可領略他在藝術創作方面的突破。 最后,主創人員重視音樂唱腔改革,但毫不過度。 楊蘭春要求王基笑、姜宏軒、梁思暉等作曲者要有音樂個性化的追求,“一個戲有一個戲的風格,雷同化是沒有生命力的藝術”[16]。 在具體創作上,例如主題音調,他們選用的是豫東調“二八板”的旋律并吸收豫西調“二八板”為一體,創造出一首新的曲調。 這種藝術上的創新,是“三團”基于精準定位的實踐探索。 不可否認的是,“三團”譜寫出新的樂章,讓現代戲人物唱出新的唱腔,他們從未拋棄傳統,而是在廣泛學習豫劇傳統音樂的基礎上,吸收豫東調、豫西調、沙河調、高調等地方聲腔的精華,融會豫劇各大流派的表演程式,使現代戲立于舞臺。 “公仆三部曲”繼承了“三團”重視音樂唱腔設計的優秀傳統,《村官李天成》之“吃虧歌”,《焦裕祿》之“百姓歌”,《重渡溝》之“干事歌”,皆為音樂設計方面的上乘之作。
(三)專家學者的批評引導
《朝陽溝》和“公仆三部曲”不僅受到國家政府層面的鼓勵和幫助,在其發展成熟的過程中,更是接受專家學者的批評引導,這使“三團”將感性的藝術創作認識上升為理性的規律認知。 前文已經列舉了多位學者對紅色農村題材精品豫劇的肯定和贊許,這里不再贅述。 豫劇現代戲發展至今,取得了較高藝術水平,若要繼續向上攀登,就更加需要專家學者的批評引導,并且這些評論要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 例如傅謹對前后兩版《重渡溝》的批評:“2017 年首演,它曾經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是當我在劇場看到《重渡溝》這個版本時,很是驚異。 我記得我喜歡的《重渡溝》不是這樣的。”[18]老版的作品里馬海明貴在“起點低”,也正因為起點低,所以他的戲劇行動才讓傅謹等專家、學者和觀眾深深信服。 老版《重渡溝》中的馬海明是富有生氣的鄉村干部,他質樸詼諧,可愛有趣,賈文龍也能有更多自由發揮、表演創造的空間。但修改后的《重渡溝》把這部分戲“修剪”掉了,造成馬海明像是翻版的焦裕祿,一臉嚴肅正派。 戲劇沖突也機械地把自然資源同資本市場對立起來,為了解決這種對立,甚至構思簡單而不可信的解決方案,讓馬海明用自己家的房子作為資產抵押來支持景區的開發。 這個故事創作的目標是弘揚主旋律,表現共產黨員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精神,但諸如此類的謳歌卻是干澀無味的。 另外,李偉、黃靜楓等學者也對新版《重渡溝》提出質疑:“矛盾的解決還是有點簡單化、概念化,都是外力干預的結果、道德感化的結果,而不是矛盾發展的結果、人性斗爭的結果。”[19]紅色農村題材豫劇只有這樣一次又一次經歷帶有問題意識的理性批評,才能夠走得更遠。
① 《村官李天成》編劇為姚金成、張芳、韓爾德,《焦裕祿》編劇為姚金成、何中興,《重渡溝》編劇為何中興、姚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