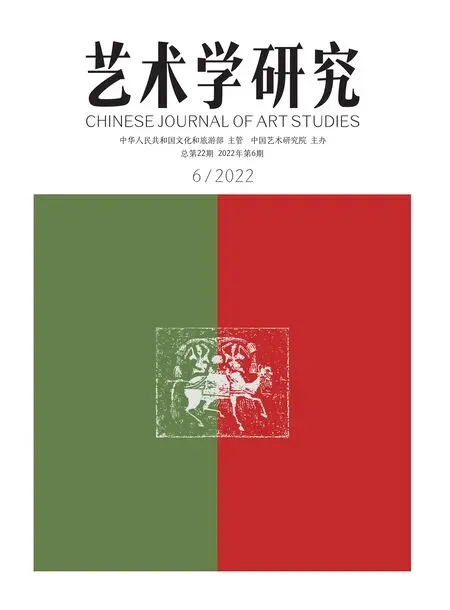宣傳、教育與審美:抗戰時期農村戲劇的功能
馬晶
重慶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
全面抗戰爆發后,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戲劇作為挽救民族危亡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而被推上了時代的潮頭。為了使廣大民眾積極參與到抗戰中來,戲劇下鄉、戲劇大眾化的需求越來越迫切,因為“在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中,誰都明白,千百萬的農民大眾是抗戰的主體”[1]徐鶴京:《改進農村話劇宣傳的商榷》,《河南省第十區行政周刊》第11期,1938年5月29日。。全國各地的救亡演劇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他們以戲劇為手段,將抗日救亡的種子撒播到農村各地,中國戰時的農村戲劇運動由此蓬勃開展。對這一時期農村戲劇的研究,學界更傾向于其政治性和宣傳性的表達,而忽略了其藝術性的呈現。本文認為戰時農村戲劇具有明顯的時代性、大眾性和民族性,其宣傳、教育和審美三大功能在特定時代需求下雖各有偏重,但仍融合為一。
一、救亡宣傳:戰時農村戲劇的時代使命
救亡圖存作為時代主題貫穿于戰時農村戲劇運動的始終,這一時期的戲劇也因此擔負著宣傳和動員的使命。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如何喚醒民眾,發揮全民族的潛在力量成為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抗戰的戰場不再局限于戰火紛飛的前線,也延伸到了相對平靜的后方。戰時的中國仍舊是農業國家,經濟基礎依賴于廣大農村,“農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要集中民族的力量,就不能不把廣大的農民動員起來,尤其是抗戰轉入第二階段,最后決勝之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內地鄉村,動員農民,愈覺重要而迫切”。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廣大農村地區成為開展戲劇運動的重要區域,而戰時農村戲劇運動的重要目的則是“通過戲劇的形式,喚起農民的愛國熱情,并且使這熱烈情緒,從具體的行動中動員起來”[1]鐘有材:《本校抗戰戲劇實踐社春假鄉村服務工作特輯:弁言》,《民大校刊》第26卷第9、10期合刊,1938年4月25日。。可見,宣傳動員是戰時農村戲劇運動最直接而鮮明的指向,也因此成為此時期戲劇的重要功能。
盡管已經進入全面抗戰階段,但農村對戰事知之甚少,更無法理解抗日救亡的真正意義。如鄰近廣州某村的農民抱怨駐村的軍事學生擾亂了村莊的太平寧靜,認為當前的戰爭只是中日兩國軍人之間的敵對行為,與鄉村沒有任何關聯。劇作家宋之的在去往成都的路上看到四處流傳的四川方言唱本,上面赫然寫著:“涅死有我‘求’‘先’干(意為兵士在前線打仗,打死了關我屁事!)。”[2]宋之的:《四川的文化動態》,《抗戰文藝》第1卷第8期,1938年6月11日。甚至是生活在戰地及戰線附近的民眾,也會因為無法分辨敵我而做出助敵的愚昧行為,“這種種使人寒心的現象,足昭示宣傳與組織的工作,均有加速度進行而不可偏廢的必要”[3]如琳:《農村演劇雜論》,《新戰線》第1期,1937年12月18日。。在這個民族意識還未普遍覺醒的時代,戲劇在戰事宣傳方面的功效就顯得極為重要——通過鄉村演劇讓農民了解抗日戰爭的情況,理解災難深重的國家和民族,從而真正喚醒他們,使他們堅持抗戰到底。
因此,在宣傳內容上,戰時農村劇本主要反映抗戰救國內容,如《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計》《血灑盧溝橋》等,都是當時非常經典的抗戰劇目,也都是戲劇下鄉的主要劇目。英勇抗敵的故事有著強烈的鼓舞性,雖然能在情緒上感染人,但戲劇工作者很快發現,在江南某些農村,表現東北義勇軍英勇抗敵的事跡、描寫全面抗戰下中國軍隊奮勇殺敵功績的故事、暴露漢奸無恥行徑的故事,本來足以深深感染當地農民,卻因他們對臺詞中的“義勇軍”“漢奸”“日偽軍”“東北”“關外”等名詞不甚了解,致使宣傳的效果不甚理想。因此,“農村演劇,主要的是:要給農民觀眾‘看’得懂,‘聽’得懂。否則將無法令他們接受所表演的戲劇內容”[4]嚴恭:《來自江南農村:農村流動演劇的報告》,《文藝月刊·戰時特刊》第2期,1937年11月1日。。要達到宣傳的效果,關鍵在于要貼近農民的生活,使他們產生親近感和熟悉感,實踐證明,“劇本如果對于農民生活距離太遠,他們沒有‘親知’可以接受,那么結果非失敗不可”。因此,戰時農村戲劇的劇本創作開始聚焦于農民的現實生活。不少演劇隊將農村工作實踐中的所見所聞編入劇本,隨寫隨演,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當然,“中國民族要求解放的時代,我們一方面要顧到農民生活之反映;將農民生活搬上舞臺,另一方面我們要將抗敵救亡的意義和農民生活配合起來”[5]潘一塵:《我們怎樣干戲劇運動》,《鄉村運動周刊》第3期,1937年4月19日。。可見,時代需求和大眾生活是戰時農村戲劇創作的兩個要素,既要突出時代性又要立足大眾化,兩者不可偏廢。也只有這樣,戲劇才能在農村的宣傳工作中取得良好的宣傳效果。實際上,在農村戲劇的實踐過程中,也只有貫徹這一原則的演劇隊才在戲劇宣傳中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如上海國民救亡歌詠遠征隊赴金華農村從事宣傳工作時,演劇劇目除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流傳較廣的經典抗戰劇目外,還有他們自己新編的《向前線去》《難民與傷兵》等劇[1]《上海救亡歌詠隊深入農村演劇》,《抗戰戲劇》第3期,1937年12月16日。。西北戲劇編審會為適應農村演劇之需要,特編就《自衛》《鋤地》《痛改前非》《模范團長》《此路不通》等獨幕劇[2]野奴:《西北戲劇編審會近為適應農村演劇之需要起見》,《文藝舞臺》第2卷第2期,1936年2月5日。。這些與農民生活緊密結合的創作,在演出過程中都收到了很好的反響,體現時代意義的同時達到了有力的宣傳效果。
在宣傳方式上,為了強化戲劇的宣傳功效,農村演劇以街頭劇為最主要的表演方式。街頭劇表演靈活、方便,對舞臺和道具的要求都較低;在表演過程中,因為演員和觀眾距離近,觀眾極易因演員的動作和表演融入劇情,把故事中的情節當作身邊發生的故事,進而產生強烈的共鳴。街頭劇的宣傳效果直接明確,但街頭演劇的觀眾數量有限,為了擴大宣傳效果,農村演劇隊也會選擇村里的廟宇或高臺處進行演出,這些地方更適宜大型演出,容納更多的觀眾,從而達到更廣泛的傳播效果。另外,“為求觀眾踴躍,在演劇前有普遍的街頭宣傳和家庭訪問”[3]馮越人:《演劇在鄉村(未完)》,《青年文藝》創刊號,1941年4月15日。。這些方式都是農村演劇隊獨創的,目的是更好地擴大宣傳,增強戲劇演出的效果。在向來安靜的村莊鳴鑼擊鼓、巡行街道、廣播消息,本來就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情,這樣的熱鬧傳到沿途商店住宅,大家都聞聲而出,等到真正開演時廣場前就會人頭攢動,水泄不通[4]李瀚源:《本校抗戰戲劇實踐社春假鄉村服務工作特輯:本社鄉村服務團工作記(二)》,《民大校刊》第26卷第9、10期合刊,1938年4月25日。。這種激發農民興趣的戲劇廣告方式在演劇隊的實踐中反響很好,確實達到了擴大宣傳的良好效果。家庭訪問則主要是為了解農民生活情況,以便在演劇過程中能更有針對性地貼近當地農民生活,從而以農民熟悉的方式來增強表達效果,引起其強烈的共鳴。
在宣傳主體上,戰時農村戲劇運動是全民參與的抗日救亡運動。除了專業演劇人員以外,更多的業余工作者擔負起了戲劇救亡的重任;全國各地,各種組織的鄉村救亡演劇隊紛紛成立,積極投身到戲劇下鄉的行列中;學校的師生也成為當時農村戲劇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組織校園劇團利用假期去周邊的鄉村進行救亡演劇宣傳。
時代呼喚戲劇,戰時農村戲劇運動在宣傳抗戰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曾有人懷疑戲劇的這些功效,認為戲劇工作者無法像士兵那樣走上前線,也就無法承擔起救亡的責任。然而,戰時農村戲劇運動的實踐證明,文化宣傳非常重要,在民族意識還未普遍覺醒的中國,抗戰戲劇作為最通俗、最易于普及的藝術形式之一,承擔起了宣傳和動員廣大農民的重任。農村戲劇的宣傳功能也在這種需求下被突出和放大,這是時代的必然要求。
二、民眾教育:戰時農村戲劇的必然責任
與宣傳功能密切聯系的,是戰時農村戲劇的教育啟蒙功能。農村戲劇在宣傳抗戰的同時也擔負著啟迪民眾的重任。在戰時的中國農村,農民的知識和文化水平較低,要在農村傳播知識,戲劇無疑是最有效的途徑之一。這一觀點,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熊佛西等戲劇家在河北定縣進行農村戲劇實驗時就有體現,而到了全面抗戰時期,戲劇在啟發和教育農民方面的功能更加凸顯,開展農村戲劇運動的緊迫性也更為強烈。戰時需要的是迅速及時、覆蓋面廣而起點低的教育,要在短時間內給予廣大民眾特別是農村民眾以民族國家的教育,并使其對戰爭有所了解與行動,單靠文字的傳播力量有限,當時“農民們的知識程度是很低落的,尤其農婦們,要是精密地統計起來恐怕有十分之九是‘目不識丁’的文盲”[1]嚴恭:《來自江南農村:農村流動演劇的報告》,《文藝月刊·戰時特刊》第2期,1937年11月1日。,而戲劇作為綜合藝術的優勢在此時就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文字所描寫的都可以從動作中表演出來,更能寫實,具體的講:戲劇能取得文字所描寫的優長而能減削文盲者不了解的弊病,所謂雅俗共賞,兼而有之。”[2]寒青:《農村戲劇技術講話》,《自衛月刊》第3期,1938年9月1日。這就是藝術教育的力量,所以當時參與農村戲劇運動的工作者急切地指出:“我們決不可忽視了藝術教育,尤其是綜合體的戲劇教育力量,較之其他普通教育的力量更偉大些,更容易收效些。”[3]史漢俊:《農村戲劇的要素與使命》,《湖北民教》第1卷第7、8期合刊,1937年4月20日。這種優勢,使得抗戰戲劇在農村大受歡迎,在傳播抗戰救國理念的同時,成為訓練民眾、教育民眾最好的手段,由此取得的成效也極為顯著。
戰時的農村戲劇對于廣大農民來說,首先是一種政治教育,是承載著民族國家觀念的教育。中國農村地域廣大,但大都較為閉塞,信息不易傳遞。對于國勢時事、民族危機,農民都不了解,“生活于文化落后的縣份底民眾,對國家民族的認識當更薄弱”[4]如琳:《農村演劇雜論》,《新戰線》第1期,1937年12月18日。。可以說,在當時農民的頭腦中,國家和民族的觀念并不明晰。不少戲劇工作者在深入農村的工作中,深感農民“因為教育的不夠,對國家民族沒有認識,便常常受到漢奸的誘惑與威脅,而走向錯誤的危險的路線,傷害了自己的財產與生命”[5]王介:《農村演劇通訊》,《戰斗》第2卷第1期,1938年1月18日。。這些令人痛心的事實更加凸顯了教育和組織農民的緊迫性。如前所述,戰時農村戲劇運動把戲劇送到鄉村,通過廣泛的宣傳傳播,以及上演各類抗戰救國的劇目,以栩栩如生的藝術表演,把農民帶入劇目情境中,使他們得以了解當時發生的戰事,對同胞的苦難感同身受,也更明了外敵入侵的危機。通過戲劇表演喚醒農民的民族國家意識,這種教育的力量是巨大的,效果是強烈的。河南話劇巡回第三隊5個月的實踐經驗顯示,戲劇的“力量是那樣的偉大,憤怒復仇的意念烙印在千百萬大眾的心底,各縣各村鎮不斷的來信要我們去公演,以及在各地公演后許多民眾的懇切挽留,尤其是表明出民眾的自發覺醒與決心”,“在經過我們話劇宣傳后的各地方,政府對征調壯丁,編驗槍支的行政措置較過去多少得到一些便利”[6]劉澗:《如何使話劇深入到農村去?》,《抗戰戲劇》第2卷第2、3期合刊,1938年7月10日。。廣東國民大學的抗戰戲劇實踐社利用春假深入鄉村演出后,也感受到農民對抗戰知識的渴望和對戰爭的關心,早已今非昔比[7]李瀚源:《本校抗戰戲劇實踐社春假鄉村服務工作特輯:本社鄉村服務團工作記(二)》,《民大校刊》第26卷第9、10期合刊,1938年4月25日。。可見通過抗戰鄉村演劇,民族國家的觀念在廣大農民的思想意識中逐漸深化。
其次,還是一種文化啟蒙教育。農村的經濟文化發展落后,農民文化水平低下,不能識字,自然也無法受到最基本的教育。戲劇下鄉掃除了農民無法閱讀文字的障礙,使他們只需看和聽便可以掌握許多知識,因此成為傳播基本知識最合適的方式之一。當時的鄉村戲劇改革觀點認為,“即使受了一二年的教育,亦沒有多大利益,倒不如看了幾夜戲的印象比較深些”,“就可對人生較為了解,就可知道忠奸善惡的結局報應,所以依民眾們的程度來判斷,戲劇的感化力量要比其他教育更快”[1]背影:《關于鄉村戲劇改革的幾句話》,《正義》第6期,1938年6月21日。。雖然在全面抗戰時期,文化教育已不是抗戰戲劇最重要的功能,但戲劇啟發民眾的作用仍不可忽略。比如,鄉村演劇對農村封建思想產生強烈沖擊。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許多閉塞落后的農村,封建思想較為濃厚。看到鄉村演劇隊的青年男女唱唱跳跳一起演戲,看到劇本中的女性角色不再由男人來扮演,而直接由女演員來擔任,許多民眾大為震驚,充滿疑惑。“因為在他們在意想中,女人決不會這樣亂狂,同時過去的班子人一向是沒有女子的。”[2]馮越人:《演劇在鄉村(未完)》,《青年文藝》創刊號,1941年4月15日。河南話劇巡回第三隊在戲劇工作反思中也強調,戰時農村戲劇工作的目標就包括對農村濃厚封建思想的破除,只有通過提高戲劇表演的純熟度才能達到此目的[3]劉澗:《如何使話劇深入到農村去?》,《抗戰戲劇》第2卷第2、3期合刊,1938年7月10日。。可見,戰時鄉村演劇在農村文化教育和民風開化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最后,農民在戰時農村戲劇運動中也得以初步接觸到專業的戲劇教育。中國的農民原來對戲曲更為熟悉,鄉村中逢年過節偶爾會有一些戲曲表演,但對于現代戲劇這個舶來品,他們幾乎沒有接觸過。戰時農村戲劇運動讓更多農民接觸到了現代戲劇,受到了專業話劇表演的熏陶。另外,為了擴大農村抗戰戲劇宣傳,面對農村戲劇人才短缺的現狀,各地積極培養戲劇人才,有的地方則利用短期青年培訓班來動員鄉村青年參加鄉村演劇[4]楊鑒青:《我怎樣動員鄉村青年演劇》,《力行半月刊》第12期,1939年8月1日。。國立中山大學在鄉村服務實驗區各分區積極推行戲劇訓練,不少鄉村能自主演出話劇[5]《鄉村服務實驗區舉行戲劇研究委員會訊》,《國立中山大學日報》1937年2月17日第12版。。可以說,戰時農村戲劇教育為農村培養了不少戲劇人才,這也為中國現代戲劇深入農村,以及戲劇的進一步大眾化奠定了基礎。
總之,全面抗戰以來,農村戲劇運動的實踐表明,戲劇對農民大眾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文化藝術水平的提升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戲劇作為一種藝術教育的方式,在農村的民眾教育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正如1939年的《今日中國》在介紹戰時戲劇時所說,“戲劇這一藝術,在今日的中國,已成為嚴肅的教育工具,而不單是娛樂品了”[6]《戰時中國戲劇》,《今日中國》第1卷第3期,1939年9月。。
三、藝術審美:戰時農村戲劇并未缺位的存在
抗戰時期的農村戲劇以其突出的宣傳和教育功能成為動員民眾的重要武器,而在鄉村戲劇運動的蓬勃發展中,作為戲劇藝術特質的審美性并未完全缺位。
首先,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體現出戰時農村劇本創作中的藝術性原則。鄉村演劇隊在實踐中切實感受到,劇本創作需要貼近農民生活,反映農民情感,只有從現實生活中取材,才能引起民眾的廣泛興趣。比如在某劇中,學生因演劇經驗限制未將漢奸貪財而破壞救國工作的行徑充分表現出來,一般觀眾對劇中資本家和買辦的故事背景不了解,該劇最終以失敗告終[1]化冥:《救亡戲劇在鄉村》,《風雨》第7期,1937年10月24日。。有了這些經驗教訓,救亡演劇隊將農村工作實踐中的積累作為素材編入劇本,通過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和生動的表演,以及真實的情感來打動民眾,由此獲得了很好的反響,給民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在某次農村巡回演劇中,揭發逃避兵役和保甲長舞弊的《壯丁》和《火焰》、啟示當漢奸下場的《菱姑》、描寫東北人民英勇抗敵的《東北的一角》、淪陷區內愛國老人大義滅親用計對付敵軍特務機關的《死里求生》,以及痛切指出做順民只有死路一條的《順民》,都在演出過程中引起了農民的強烈反響,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劇中人物的生活,性格和遭遇都和他們的切身問題發生密切關聯,而每一個劇中人物都代表著鄉村里某一種人物的典型,于是引起了觀眾們特別的關心,臺上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都在他們心上起了反應,糾正了一般認識不清者的觀念,把幾個活生生的故事,深刻的箝在腦中”[2]若白:《農村巡回演劇一月》,《抗敵戲劇》第2卷第3、4期合刊,1939年6月20日。。可見,真正體現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農村劇本是具有藝術性的,生動的人物形象塑造和真情實感的流露是這些鄉村演出獲得成功的關鍵。
這也同時表明,劇本的通俗化和大眾化并不一定會抹殺戲劇的藝術性[3]鄭英之:《通訊:從實踐中得來下鄉演劇的經驗》,《戰地通訊》第2卷第1期,1939年1月5日。,這兩者并非對立關系。相反,深入描寫農村生活,劇本才能更真實感人,在臺詞中使用當地方言,才能使觀眾感覺更加親切。正如農村戲劇工作者所言,“大眾的文藝和藝術的文藝,決不是互相對立的兩種不同的東西,而且,必須通過大眾化運動,才能有真正的藝術的文藝”[4]穆木天:《地方文藝運動的展開》,《新學識》第2卷第4期,1937年11月25日。。
其次,在演劇方面,藝術性仍然沒有被忽視。無論是演員表演、舞臺裝置,還是照明效果,農村演劇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都盡量顧及。不少演劇隊在實踐中深知,如果不以認真的態度來鉆研表演技巧,如果認為農村演劇不必如城市公演那么精細,對話、表情和動作都隨隨便便、馬馬虎虎,那么這種粗糙的表演將完全不能吸引鄉民,“‘戲劇’畢竟是戲劇,絕不能視同‘化妝演講’一樣搬運出一堆生硬的名詞出來”,“總是要透過藝術的手法,才會使農民們更深刻的受感動,更深刻的理解”[5]劉斐章:《如何解決劇本恐慌與克服演出上的困難:寫在話劇到農村去的聲浪中》,《光明》第3卷第3期,1937年7月10日。。鄉建師范話劇組的學生也在接受訓練時被教導要重視演劇,不然會破壞全劇藝術空氣[6]潘一塵:《我們怎樣干戲劇運動》,《鄉村運動周刊》第3期,1937年4月19日。。這些對表演藝術性的強調來自對農村觀眾戲曲鑒賞力的肯定,“殊不知農村觀眾的文化程度雖低,但欣賞藝術的能力并不見得比城市的觀眾(智識分子)差,明言之看劇的常識他們也都知道的”[7]若白:《農村巡回演劇一月》,《抗敵戲劇》第2卷第3、4期合刊,1939年6月20日。。所以,哪怕是“舊瓶裝新酒”,即用戲曲的形式來配合宣傳抗日救亡的時代內容,戲劇工作者也仍然強調:“透過藝術手法來感動他們,在形式上我們采用舊戲及各種鄉土戲的手法穿插許多小調,但是在內容上我們敢保證,是嚴肅的,是將內心的情感與表演的技巧調和一致的!”[8]劉斐章:《如何解決劇本恐慌與克服演出上的困難:寫在話劇到農村去的聲浪中》,《光明》第3卷第3期,1937年7月10日。可見,藝術性仍是農村演劇中重要的組成要素,從未被忽略。長沙白雪抗戰劇團的鄉村公演非常成功,觀眾有時與表演者同時聲淚俱下,有時與表演者同聲喊殺[1]《白雪抗戰劇團之鄉村公演》,《長沙青年》第30卷第1期,1937年11月1日。。如果沒有真情實感和生動的表演,是無法取得這樣的效果的。
同時,演劇還開拓了表演的民族化寫意審美方式。為了解決農村舞臺簡陋和音效傳播有限等問題,許多對鄉村演劇有經驗的演劇隊提出,可借鑒傳統戲曲表演方式,用動作來彌補舞臺布景的缺失;盡量夸大動作表演的幅度,以使遠處觀眾能清晰看到演員的表演,從而明白劇中內容。這些都是鄉村戲劇努力探索民族化道路的方式。
雖然在農村演劇只能因地制宜,選擇街頭、巷角、廟宇、祠堂、廣場等作為舞臺,但戲劇工作者仍會盡量根據當地情況選擇最適合表演的場地,以使戲劇的藝術性被呈現出來。比如在江南農村,由于每個村鎮都有戲臺建筑,所以鄉村戲劇一般選擇在這種三面的舞臺上演出,以便施展戲劇藝術固有的技能[2]鐘敬之:《戰時農村演劇運動雜見》,《新學識》第2卷第4期,1937年11月25日。。同時,劇場照明也是戲劇藝術價值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戰時農村演劇因舞臺條件限制,無法使用電燈,戲劇工作者就改用汽燈、火炬,如在原野上或山崗上(尤其是街頭劇)演劇用火炬照明同樣也能造就許多雄偉的場面[3]石叔明:《戰時農村演劇的照明》,《劇場藝術》第2卷第5期,1940年5月10日。。由此可見,戰時農村演劇條件雖然簡陋,但無論表演還是舞臺或舞美,從未忽視其藝術性。
結語
戰時農村戲劇是全面抗戰爆發后在中國農村地區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藝術形式,只不過在時代的影響下,其最具特色的審美鋒芒為救亡宣傳與民眾教育的功能所掩蓋。“藝術的審美和思想的教育,是戲劇與生俱來的兩個作用,人類對這兩者的追求并不總是平衡的。”[4]陳白塵、董健主編:《中國現代戲劇史稿:1899—1949》,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頁。可以說,抗戰時期的農村戲劇最首要的功能是對民眾思想情感上的宣傳鼓動和教育動員,但這并不等于其藝術審美功能被完全忽視和拋棄,相反地,在戰時農村戲劇的創作和演出中,戲劇工作者仍在小心翼翼地呵護其作為藝術的特質。在粗糙的生活環境中,在簡陋的演出條件下,在樸實的觀眾群體中,抗戰時期的農村戲劇努力探尋著一條接近時代和民族的發展之路。
綜上而言,宣傳、教育與審美三大功能仍然統一于戰時農村戲劇,三者的結合雖不完美,但也未被割裂開來。宣傳是藝術的宣傳,教育是藝術的教育,三者統一于時代的需求之下。正如四川省戰時鄉村服務團巡回隊的演出原則所說,“以服務,宣傳,藝術,三者打成一片的精神,將宣傳表演,組訓民眾的這任務,沉重的放在我們每一個同志的肩頭上”[5]剛斌:《四川省戰時鄉村服務團巡回隊戲劇的演出》,《青年人》1939年12月1日。。也正是在這樣的指導原則下,抗戰時期的農村戲劇運動才得以蓬勃地開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