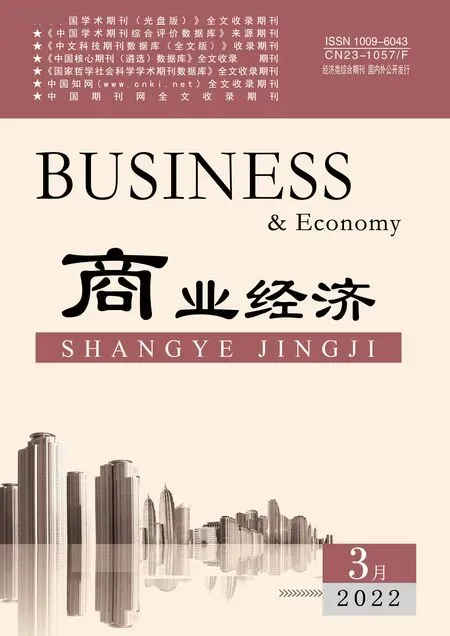平臺經濟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
魏永奇
(黑龍江大學,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
隨著平臺經濟的迅猛發展,新就業形態的概念逐漸被人們所熟知。新就業形態也是信息產業革命進行中的必然結果,但新就業形態的基本定義目前并未被完全界定。社會中對于“新”的定義也不盡相同,“新”既體現在生產資料的新形態。例如,互聯網+、互聯網平臺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又體現在從業者勞動者與互聯網平臺的非典型勞動關系。在平臺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對平臺經濟發展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勞動者權益理應得到更多關注。尤其是面對勞動者的數量不斷增加,就業形態不斷更新的新就業形態的情況更應增強危機意識。
一、平臺經濟中新就業形態用工關系現狀
(一)平臺經濟打破了傳統的勞動關系
平臺經濟發展過程中新就業形態逐漸發展為重要的就業形態。平臺經濟利用互聯網技術的資源整合、以及短平快的發展優勢,重塑了傳統的勞動關系二分法理論。但是與傳統觀念中以有無勞動關系,作為界定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的策略,并不能很好的解決新就業形態中的勞動者與平臺經濟企業的法律關系問題。例如,外賣騎手與“美團外賣”、“餓了么”外賣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網約車司機與“滴滴出行”打車軟件之間的關系,家政工人與家政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又如,美團騎手送餐途中發生意外,外賣平臺以不具有勞動關系拒絕承擔責任的現象不斷發生。那么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又該如何實現。
(二)新就業形態保護的空白
1.現行立法空白
2019 年8 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保障新就業形態的從業人員權益,避免產生路徑依賴,使用傳統的老辦法管理新就業形態。2020 年10 月中共中央發布“十四五”規劃綱要,綱要中把完善多渠道靈活就業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作為強化就業優先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行《勞動法》的立法者在立法之初所秉持的觀點是,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在簽訂勞動合同后,雙方必然會將懸而未決的法律關系確定為“勞動關系”。因此在立法時對“勞動關系”的內涵與勞動關系的界定都沒有進行相關的規定。隨著勞動關系的不斷更新與發展,相關立法中仍然是模糊的解釋與說明,沒有對其進行明確的認定標準,導致立法出現了滯后性,《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對認定勞動關系的存在與否進行了部分規定,在近幾年司法實踐中法官在裁判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平臺企業之間的勞動糾紛時大多以該條規定作為裁判依據。在《通知》第一條的規定中,對勞動關系的界定結合了三方面認定因素,分別是主體資格方面、管理性方面以及組織性方面。由于該規定是在2005 年制定,基于當時的社會背景該條規定實質上是對傳統的典型勞動關系的認定標準,適用該標準對當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這種大規模出現的新型靈活的勞動模式進行認定明顯過于僵硬。雖然我國近幾年的相關政策中也出現了許多調整政策,但是這些政策運用到實踐中仍然解決不了現存的亟須解決的實質性問題,如新型勞動關系的認定需要依據什么實質性標準等等。
2.司法現狀
由于平臺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之間的新型用工模式與傳統的用工方式不同,對于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應當認定為何種法律關系仍有較大爭議,相應的法律規制也較為不足。在司法實務的判決中,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平臺之間的勞動關系認定問題經常出現“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有些法官認為雙方存在勞動關系,有些法官認為雙方法律關系是合作協議關系、居間合同關系,有些法官則選擇回避認定雙方法律關系的問題。我國現行《勞動法》及相關法律文件,對于勞動者的保障多數基于存在勞動關系的有無,對于法律關系未厘清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并沒有具體的法律保障。因此,建立新型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法律保護機制,加強對從業人員的保障是促進平臺經濟有序發展的重要一環。
二、平臺經濟中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勞動關系分析
(一)傳統用工關系分析
1.傳統勞動關系的本質
第一,人格從屬性,通說認為勞動關系是基于勞務提供方與受領方之間的具有從屬性的特殊雇傭法律關系,這種從屬體現不僅在雇員在雇主的指揮下依據時間要素給付勞務,還體現在雇主可以隨時終止與雇員的法律關系。例如雇員需要遵守雇主規定的工作時間,每天按時打卡上下班,雇主會規定雇員階段性的工作內容,雇員不得自行安排自主性勞動,這些都體現了雇員對雇主的人格從屬性。第二,基于經濟從屬性,雇員的收入來源于雇主,喪失了其他獲取收入的渠道,一旦突然失去工作則無法正常生活。由于雇員相對于雇主的地位不平衡,所以現行《勞動法》傾向救濟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
傳統觀點認為勞動關系是適用勞動法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前提。基于人格從屬性和經濟從屬性對勞動關系雙方的關系進行界定是學界普遍認同的方法。所以基于從屬性的概念出發,勞動者與企業之間就存在著天然的不對等關系,也理應得到傾斜照顧。基于人格從屬性和經濟從屬性理論可以分為以下三類法律關系。

不同類型勞動者示意表
在我國第一類傳統勞動者由勞動法與非全日制用工的勞動法調整,第三類由民法調整,唯獨第二類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沒有專門的法律調整,眾多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就屬于這一群體。由此可見,相當多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都位于承攬關系與勞動關系的“中間地帶”,但他們應當受到的法律保護不亞于具有勞動關系的勞動者。
2.認定標準滯后
從屬性要素界定不清。其一,針對人格從屬性僅基于工作時間作為認定標準,不適用于所有類型勞動者。其二,針對經濟從屬性的雇員收入來源也較難認定。其三,收入水平不同的勞動者的經濟從屬性也不同,法律也能規定固定比例,只能由勞動仲裁或者法官自由裁量。
(二)新就業形態用工關系分析
1.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新特點
平臺經濟調整了以往的勞動關系,從而產生了與傳統勞動關系不同的新特點:
第一,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兼職勞動的就業范圍擴大,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可以以“線下+線上”非全日制兼職的模式參與平臺經濟,也可以以全日制的模式參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較傳統勞動者具有更強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可根據自己的時間自由安排工作市場以及工作地點等等。就業人員的構成豐富,例如大學學生、家庭主婦等。同樣對于新就業形態工作準入門檻相對傳統行業較低,例如外賣員,快遞員等等。
第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不僅需要對平臺負責,而且需要面對客戶的多樣化需求。傳統的勞動者僅基于勞動合同直接對雇主直接負責。例如網約車司機對于用戶更改出行地、外賣用戶更改送達地址等等,對比傳統勞動者的工作內容,這無疑增加了勞動者的工作壓力。
第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用工關系的連續性、穩定性與傳統用工關系相比較低,對于自身權益的保護也有同樣特點。例如,勞動保險、社會保險、工傷保險等都需要連續繳納,就會造成權益受損時無法維權的問題。
第四,新就業形態工作的準入門檻較低,法律風險高。許多從業人員并未接受較為完善的教育,甚至只完成了九年義務教育。例如許多城鄉結合地區的勞務派遣公司甚至不與勞動者簽署任何協議,更不會為勞動者或者第三人“買單”。
2.厘清新就業形態用工關系的法律意義
基于傳統勞動用工關系的勞動者由我國《勞動法》保護,那么基于新就業形態用工關系的勞動者如何進行保護?
其一,“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規模日漸擴大,其勞動關系的認定不僅關系到勞動者的權益保護,也關系到平臺經濟的利益分配問題,更關系到平臺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其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互聯網平臺經濟發展的今天,更加靈活多變,使得傳統的從屬性理論對勞動者與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更加難以判斷和理清。其三,基于立法的滯后性,是否應當傾斜保護勞動者仍然值得商議。綜上,認定與厘清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平臺之間法律關系的意義,于平臺經濟健康有序發展以及新經濟形態勞動者基本權益保護而言十分必要。
3.去“勞動關系化”新思考
平臺經濟模式下的新就業形態用工特點,勞動者時間自由、工期短、用工形式多種多樣。如將所有模式下的用工關系都以《勞動法》中的勞動關系加以規制,未免會出現勞動關系認定的泛濫,同樣也會增加平臺企業的用工成本。2015 年的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中提出,勞動爭議案件的審判中,應當明確勞動關系的界限,切忌脫離法律規定和客觀實際將勞動關系泛化。
但去勞動關系化不應是對法律關系的全面否定,否則依附于平臺的勞動者的利益會被平臺企業追求的利益進一步壓榨。但去勞動關系化的弊端之一是勞動者利益的犧牲,換取平臺短期的利益。隨著人口數量紅利的消失和實體經濟的回暖,平臺經濟也難免會遇到“線下”勞動力的用工荒。全面去勞動關系化,平臺短期“變現”退出市場,這與平臺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目標背道而馳,也不符合法律的公平正義。
我們應當追求平臺企業的長期發展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相對公平,既不能為了平臺的利益剝奪勞動者的權利,也不能憑空增加平臺企業責任。去勞動關系化問題仍需思考。
三、進一步完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保護機制
由于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工作時間、工作地點以及人格從屬性與經濟從屬性等方面與傳統勞動者的從屬性存在較大差別,因此相關制度也必然存在差別,現行《勞動法》無法直接適用于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護,應當引入和完善保障機制
(一)完善立法制度層面
我國現行《勞動法》制定于1994 年,對隨著互聯網發展新生的平臺經濟存在的問題不能很好的解決。現行的勞動管理模式也不能很好地應對新就業形態下,數據傳輸快、人員流動性強等復雜模式。為適應平臺經濟、互聯網經濟發展以及就業者的權益保障,應當完善相關勞動法規,建立多元的勞動保障法律制度。多層次,多角度平衡經濟發展與權益保護的關系。
完善平臺企業相關法律制度,可以從完善對平臺經濟與勞動者法律關系的認定方面入手。一方面,可以將傳統勞動關系的認定適當從寬,建立界定新就業形態法律關系標準,便于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進行保護。增加認定法律關系的彈性意識,順應改革勞動保護制度的目標意識。另一方面,基于個案的需要,利用現存的勞動法及相關條款,有選擇的裁量雙方法律關系。落實相關政策的完善確定,法官運用司法能動性可以解決困局。
同時,基于新就業形態的靈活性、多樣性等特點,也應當順應平臺經濟發展趨勢,適時完善法律規范。維護平臺經濟發展、平臺企業發展以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
(二)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保障機制是法律保障機制的一種補充。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從事網約車駕駛,外賣配送等工作時所面臨的職業危險,事故危險絲毫不亞于傳統勞動者。不僅是對從業人員造成的危險,還有對第三人的侵權。傳統勞動關系關于用工責任的界定較為清晰,但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造成危險可能會承擔巨額的賠償責任。目前大多平臺企業會采用強制要求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購買意外事故險,并在工資中予以扣除保費。
基于平臺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傳統勞動法律的不健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面臨勞動風險時既不能適用傳統法律加以保護,又不能得到其他救助時“孤立無援”。提供社會保障制度對勞動者進行保護可以增強勞動者的就業信心,以及對平臺和對社會的責任感。筆者認為,無論是否認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平臺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都可借鑒侵權責任法中的用工責任問題,平臺先行賠付,如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平臺可以向勞動者追償的制度。實現社會效果與法律效果的協調統一。
(三)平臺企業強化社會責任
平臺企業在享受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帶來的收益時也應當承擔社會責任,享受權利也要履行義務。平臺企業作為強勢地位理應為處于弱勢地位的外賣員、網約車司機進行保護和管理。外賣小哥送餐逆行闖紅燈違章,發生交通事故的現象層出不窮,理應加強此類問題的治理。無論是否具有勞動關系,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都是第一線人員,都應得到保護,這已為政策所認同。
平臺企業作為資源整合、組織生產要素的商業化平臺,貫通了線上平臺與線下市場的路徑,通過不斷交易所產生的大量數據及應用算法,既面對消費者又面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及平臺中的企業的雙邊市場。因此平臺企業除了應承擔傳統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外,更應在追求利益時肩負更多的社會責任。
平臺應當提供入職前安全教育,建立安全教育培訓機制,平臺企業建立健全勞動工會等部門,將勞動者的權益保護納入平臺服務標準。切實落實具體的平臺企業治理規則,十分有利于提升平臺企業的責任意識。
(四)運用新型保險制度保護勞動者
2021 年關于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保障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應促使平臺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進一步保障,同每次產業升級革命一樣,“大數據”“互聯網”“平臺經濟”等雖然代表新的信息產業革命,但仍需依靠勞動者這一要素條件實現發展“落地”。面對新經濟產業的發展趨勢,平臺經濟依靠低成本勞動力壓榨利潤的模式未必可以獲得持續發展,應當通過多險種適用的方法為新就業勞動者保駕護航,也可為平臺經濟穩定發展提供支持。
其一,對于工傷保險,鼓勵交通出行、外賣配送等平臺通過購買人身意外、雇主責任等商業保險提升平臺靈活就業保障水平,使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權益得到保障。因為這兩類的勞動者外部性較強,危險性較強,工作場所與工作時間自由支配,不宜僅適用工傷保險,應當建立健全新型工傷傷害保障管理服務規范和運行機制。其二,對于社會保險,農民工參保社會保險已有法律保障。因此對于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可參照《社會保險法》中針對農民工社會保護的方法,應當從“職工社會保險”轉向“勞動者社會保險”,這也可省去認定勞動關系的問題。
(五)完善政府監管
政府監管作為“有形的手”對于規制新就業形態所產生的問題有著重要意義。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區別于傳統勞動者的用工模式,互聯網發展速度較快,法律規制必然存在滯后性,所以政府部門的適時監管也是重要一環。第一,政府部門應當在新經濟、新業態的大環境中增強“問題意識”,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問題解決在事前。第二,加強對于平臺企業的監管,對于違規行為及時監管,定期監督。第三。強化政府作為社會治理者的責任,有關部門應當為勞動爭議頻發的某些勞動爭議開通“綠色通道”簡化辦事流程,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幫助,從而提升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的效率。
四、結語
平臺經濟的迅猛發展以及新產業的不斷迭代,不僅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便利,也帶來了新的就業形態和就業機會。新就業形態用工關系的規制與保護也愈發重要,但是仍存在法律關系認定不清與相關法律規范不足等問題亟需解決。隨著人口數量紅利的消失和實體經濟的回暖,平臺經濟也難免會遇到新就業形態勞動力的用工荒。在保障新就業形態優勢的同時,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護,不僅有利于維持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相對穩定的勞動狀態和職業技能提高,而且有利于平臺企業對發展質量的控制,推動平臺經濟健康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