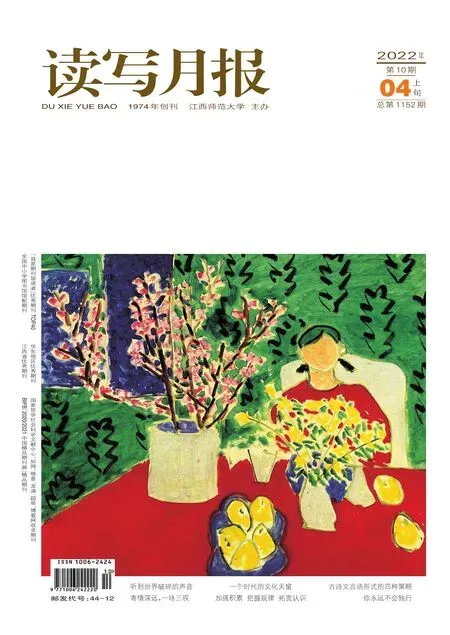《垓下歌》:虞姬的催命符
宋桂奇
司馬遷在《史記·項羽本紀》中寫道: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此中四句絕命詩(《垓下歌》),是一首英雄末路的悲歌,更是“千古不磨的杰歌”(梁啟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因而一直為人津津樂道。但學者對詩中“騅不逝”的理解,不僅存在分歧,而且均不妥帖。
如陸永品先生解說道:“從第二句的‘時不利’和‘騅不逝’來看,這里寫項羽著意突出的是‘恨’字。他怨恨天時對他‘不利’,又怨恨駿馬‘不逝’,使他不能逃脫漢軍重圍。”“第三句是說,天時不利則罷,可恨的是跟隨我多年的戰馬,也不向前跑了啊!這又有什么辦法呢?”(詳見《先秦漢魏六朝詩鑒賞辭典》)據上引原文可知,項羽悲歌時,突圍還沒有開始,這“怨恨駿馬‘不逝’,使他不能逃脫漢軍重圍”之說,又從何談起?而在后文“垓下潰圍”“陰陵失道”“東城快戰”“烏江自刎”等情節中,烏騅馬始終恪盡職守,奔馳不息,這“駿馬‘不逝’”之“怨恨”,又道理何在?
也有學者另辟蹊徑。如師為公先生就認為:此中“逝”并非“往(向前跑)”,而是“去(離開)”,進而解原詩為:“力能拔山扛鼎啊,豪氣蓋世,天時不利啊!烏騅馬并未離我而去。烏騅馬不離開我啊!我仍然無奈天何,虞姬啊虞姬!我如何安排您的生活?”(詳見《說〈垓下歌〉中的“逝”字》,《文史知識》1992 年第5 期)這個“新解”問題更多:“時不利”“騅不逝”均言當時困境,顯屬并列關系,可在“新解”中卻變成轉折;“可奈何”本是針對“馬”,“新解”竟想當然地改換為“天”,致使一句話成了兩句。若整體觀之,則全詩的內在邏輯更是混亂不堪:“(雖然)力能拔山扛鼎啊,豪氣蓋世,(雖然)天時不利啊!(但是)烏騅馬并未離我而去。(雖然)烏騅馬不離開我啊,(但是)我仍然無奈天何。虞姬啊虞姬!我如何安排您的生活?”如此“一波三折”,便使得“千古不磨的杰歌”成了“古今無雙的瘋語”!
筆者以為,項羽說“騅不逝”乃別有用心——借此來催促虞姬速死!
雖太史公“不紀美人死”(清吳永和《虞姬》),但就虞姬垓下后即從司馬遷筆下消失這一事實來看,她死于垓下當可以肯定。據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自漢初陸賈《楚漢春秋》記載,虞姬還有《和項王歌》,云:“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陸賈生活的年代比司馬遷早,此說似值得采信。明確了虞姬死于垓下,我們也就有理由認為——《垓下歌》是虞姬的催命符。
不妨再看文本:“漢軍四面楚歌”后,項羽先是“大驚曰”,繼而“夜起,飲帳中”,之后才是“悲歌慷慨,自為詩曰”。揆之以常理人情,“飲帳中”時,項羽定會考慮下一步出路,考慮的結果當是決定“直夜潰圍”;一旦做出這個決定,“難題”便隨之而來——怎樣處置心愛的美人虞姬?因傳中不涉虞姬平日隨軍轉戰時如何行進,我們只能據常情常理予以推斷:虞姬不能獨自騎馬當能肯定;若能獨騎,自會隨軍突圍,見于下文之中。剩下的還有兩種可能:一是乘車行進。但較之快馬,車行之慢自不待言;是夜,若乘車突破漢軍數重之圍,怕是難于上青天。一是項羽攜行。此說看似“現代”,有點無厘頭,卻有文本依據。“有美人名姬,常幸從;駿馬烏騅,常騎之”一語中,“常幸從”義即“(項羽)常幸(虞姬)使(虞姬)從”,“常騎之”則是“常使之(虞姬)騎(烏騅)”,用以說明“常幸從”;否則,這“(項羽)常騎之(烏騅)”豈不是十足的廢話?如改句中分號為逗號,太史公的本意便得以彰顯:戰事不緊時,項羽與虞姬時常共騎于烏騅之上,一路恩愛而行。這樣的動人畫面,能不扎根于項羽腦海?只是,烏騅平日可載二人優游而行,可今夜突圍卻關乎生死,若烏騅再負載二人,勢必會減緩速度,既不利前行,更不便殺敵。如此,不僅虞姬不得生還,怕還要連累項羽及全軍!明確了虞姬不可能隨軍突圍,如何處置虞姬也就成了項羽的當務之急:讓自己心愛的女人落入漢軍之手,受其凌辱,項羽當然不愿意。這就意味著,虞姬必須死!接下來便是死法:連烏騅馬也“不忍殺之”的項羽,自然不忍手刃心愛之人。于是,虞姬自殺就成了項羽最樂于見到的結果!可怎樣才能讓虞姬主動了斷呢?直言相告無疑過于殘忍!于是婉言——借悲歌來催促,也就成了最為可行的方式!
就這樣,項羽有了平生唯一的詩作。請看詩歌大意:雖然我力能拔山啊,氣可蓋世,但天時不利啊,烏騅不再奔馳;烏騅都不再奔馳啊,我該怎么辦?虞姬啊虞姬,我該如何處置你!雖首句尚存“風云之氣”(錢鐘書語),但后三句顯為一種“英雄失路之悲”(清吳見思語)。此中,之所以復言“騅不逝(烏騅不再奔馳)”,即在向虞姬傳達“烏騅不能載你我二人(若載二人則無法突圍)”之意,以此來渲染目前“我”之困境,而最后一句不僅強化了這種困境,更是在暗示對方——“我”之困境即由你造成!或許,從不吟詩的項羽突然詩興大發,令倍感意外的虞姬分散了注意力,以致她開始時未能領會其意,這才引發項羽反復歌唱(歌數闋)。但筆者更傾向于冰雪聰明的虞姬在項羽第一次歌罷即已心領神會,隨之則是強烈的震驚、失望、痛苦……曾叱咤風云的西楚霸王現在怎么竟沒有了一點當年的英雄氣概?這個自己本以為能終身依靠的男人怎么突然變得如此寡義薄情?而就在她內心翻江倒海之時,項羽的歌聲又一次響起。“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于是,在考慮到現實之不可改變后,她便決定英雄般了斷此生,成全這個她深愛的男人!若如此來理解項羽“歌數闋”后虞姬才“和之”進而自殺,是不是既切合文中語境,亦不違常情常理?
除此之外,將《垓下歌》視為虞姬的催命符,與項羽的性格也頗為相符。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第一冊)中有這樣一段精彩分析:
“言語嘔嘔”與“喑噁叱咤”,“恭敬慈愛”與“剽悍滑賊”,“愛人禮士”與“妒賢嫉能”,“婦人之仁”與“屠阬殘滅”,“分食推飲”與“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違;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兩手分書、一喉異曲,則又莫不同條共貫,科以心學性理,犁然有當。《史記》寫人物性格,無復綜如此者。談士每以“虞兮”之歌,謂羽風云之氣兼兒女之情,尚粗淺乎言之也。
錢先生雖未明言“‘虞兮’之歌”中存有項羽負面性格,但若將末句與前言“相反相違”等語并看,我們自能認定,在錢先生看來,《垓下歌》中,除表面的“風云之氣兼兒女之情”外,還有背后的丑陋在——若謂之“自私冷酷”,想必大體不差!
如果說這樣理解有“抹黑”項羽之嫌,會矮化其英雄形象,我們當然也可以做善意的想象:項羽悲歌僅僅是“吾口歌吾心”,傾吐自己當下困境;而深愛著項羽的虞姬為免其后顧之憂,便主動獻出生命。但顯而易見的是,無論作何種理解,《垓下歌》在客觀上都起到了催虞姬速死的作用。一孔之見,不知讀者諸君以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