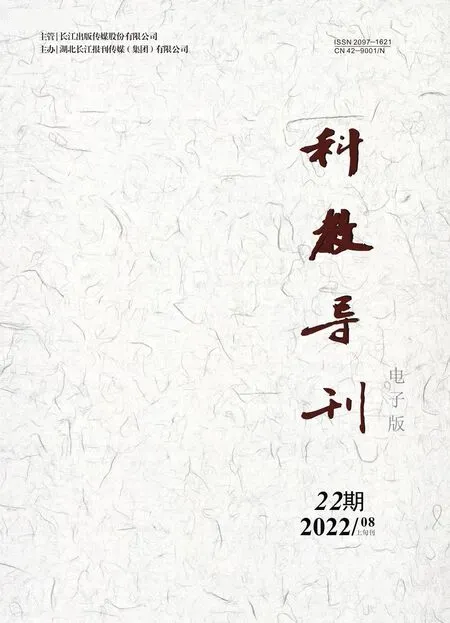去權力化的女性形象
郭昕敏,盧 敏,樊碩清,劉亞文
(重慶大學外國語學院,重慶 400044)
福柯認為“權力是彼此聯(lián)系、對立的力量關系總和,包括這些不同力量抗爭轉化的過程”(黃華,2005:54)權力擁有者和被支配者之間存在對抗,主要體現(xiàn)在前者對后者實施權力的剝奪,即對后者去權力化;而后者進行反抗。在19、20世紀英語短篇小說中,存在一些典型的男性形象與女性形象,構成上述權力關系。男性在話語、身體和人格三個層面對女性形象去權力化,最終建構女性成為依附男權的主體。
1 女性話語權被削弱
安東尼奧·葛蘭西(1929)在《獄中札記》中提出了文化霸權理論(Hegemony),他認為意識形態(tài)作為統(tǒng)治階級統(tǒng)治被統(tǒng)治階級的工具,其作用的發(fā)揮是雙方妥協(xié)(negotiation)的結果。路易斯·阿爾都塞(1970)也在《意識形態(tài)和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中指出,“詢喚”(interpellation)是意識形態(tài)發(fā)揮作用的重要手段。小說中女性話語權被削弱的過程與此異曲同工。男性通過“詢喚”建構女性,在女性的反抗過程中,雙方互有部分妥協(xié),從而強化了男性的“霸權”地位。
“詢喚”的實現(xiàn)需要雙方的互動。福克納的小說《干旱的九月》中,麥克倫登和妻子之間的對話就是男性角色對女性角色的詢喚。當麥克倫登回到家中,發(fā)現(xiàn)妻子未服從其要求早早睡覺,便呵斥妻子不許這么坐著等他,瞪著妻子,直到她低下頭,使其意識到不服從丈夫會有嚴重后果;在女性試圖解釋時,麥克倫登繼續(xù)大聲質問,甚至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推搡到椅子上,以強化他所想要妻子服從的事情:順從丈夫的要求。在整個過程中,麥克倫登的妻子始終無力反抗,解釋的話語全部被忽略,最終她不得不讓步,放棄自己的話語權,選擇服從。
“福柯認為,權力是通過話語來實現(xiàn)的”(黃華,2005:38)海明威的小說《白象似的群山》中,男友在情侶二人的對話中擁有更強的權力。當女主角問喝什么時,男友卻顧左右而言他,回答天氣好熱,隨后自行決定點兩大杯啤酒,始終未詢問女友意見;當女友對墮胎表示反對時,男友則反復強調(diào),那只是個再簡單不過的手術,并多次反駁女性的觀點,最終女性只能放棄對話。但男友依然沒有終止這一詢喚,他繼續(xù)勸說,不顧女友的一再反對。在遭到反抗后,男性角色作出讓步,如多次強調(diào)對女友的愛,實則以退為進,采取更間接的方式勸導女性放棄自主意愿,選擇墮胎。在這一過程中,女性的訴求得不到尊重和回應,男性自顧自地將自己的觀點加在女性身上,女性角色雖有表達,但其話語權在男性強勢話語權下被削弱。
2 身體權被分離
《白象似的群山》中的男友反復強調(diào)墮胎實在是一種十分簡便的手術,希望女友能夠聽他的話去墮胎,并通過削弱女性話語權達到對女性身體的掌控,抹殺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意愿。萊辛的《屋頂麗人》中,三名男性角色對屋頂上女人的行為評頭論足,“她覺得沒人能看見”“她就那么明顯地赤裸著”(王守仁,2014:246)等等,斯坦利談到自己的妻子,認為她絕不敢這么做。在厄普代克的《A&P》中,三名女孩穿著泳衣走進超市,被店中男性的圍觀和議論,超市經(jīng)理直接要求她們不能穿泳衣入內(nèi),盡管三個姑娘表示了反對,但并沒有取得成功,只能盡快離開。從男性的觀念和男性對女性的建構可以看出,女性對身體的著裝自由并沒有決定權,對自己的身體也沒有完整的支配權。
“若是女人達到了反抗的終點,那么只有一條出路還在向她開發(fā)——這就是自殺。”(波伏娃,1998:687)似乎女性對身體擁有完整支配權的唯有選擇死亡。勞倫斯的《馬販的女兒》中,長期生活在兄弟們建構下的瑪貝爾沒有話語權,被建構為柔弱無能的她自我認同感很低,最終選擇自殺以解脫自身,表達反抗。但是這樣的反抗無疑是失敗的。在男性的凝視下,女性被物化,其身體權被分離。女性不再具有完整的身體權。
3 人格權被剝奪
通過對女性話語權的削弱和身體權的分離,社會建構起了女性的多重身份,如母親、妻子等。這些身份優(yōu)先于女性自我主體意志,事實上是對她們?nèi)烁癃毩⑿缘膭儕Z。
親子關系將女性建構為“母親”,這一建構的影響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母親以孩子為生活重心;另一方面,她們認為孩子是與男性產(chǎn)生聯(lián)系的重要因素。這些女性形象普遍呈現(xiàn)出自主主體意識較弱的特點,逐漸形成以丈夫和孩子為核心的價值觀,不再追求自我的發(fā)展,或者將自我發(fā)展與婚姻和家庭和諧、丈夫和孩子的發(fā)展等同起來。歐茨的《四夏》中,茜茜的母親雖偶爾會表現(xiàn)出對婚姻狀況的不滿,如對剛出生的小女兒說她的出生只是個意外,他們并不想要她;在日常生活中也會時常與丈夫爭吵。但她只是把爭吵作為一種發(fā)泄的方式,并未想改變現(xiàn)狀。“但是女人和孩子一樣沉溺于象征的爆發(fā):她可能撲到男人身上拳打腳踢、又抓又撓,但這只不過是一種姿態(tài),來表現(xiàn)她實際上無法實現(xiàn)的反抗。”(波伏娃,1998:687)因此,她的反抗事實上是失敗的。在反抗和反抗失敗的過程中,她的自我主體意識也在逐漸被削弱。
與男性的關系裹挾了女性,使其價值判斷的依據(jù)由個人發(fā)展轉向了他人認可。華頓的《羅馬熱》中,艾斯利夫人的女兒芭芭拉實際上是與斯萊德先生所生。這個優(yōu)秀的女兒也是她自視在斯萊德先生爭奪戰(zhàn)中獲勝的體現(xiàn)。如小說結尾所寫,艾斯利夫人上前一步對斯萊德夫人說,她有芭芭拉,以此宣布斯萊德夫人的失敗。而斯萊德夫人在全文中情緒的爆發(fā)集中于當她得知丈夫當年的確赴了艾斯利夫人的約,丈夫是否出軌成了全文唯一影響到她情緒的因素。可以看出,兩名女性將衡量自身價值是否實現(xiàn)的標準集中在男性和孩子,其自我主體意識較弱。《干旱的九月》中,明尼·庫珀散布謠言自毀名譽,以求在年老色衰的情況下重新得到男性的關注。她已經(jīng)接受了被物化的現(xiàn)實,對自己的價值判斷也集中在外貌和受男性的關注度上。該女性形象不關注自身的發(fā)展,把男性的關注作為個體價值的判斷依據(jù),事實上是把自身的人格權交到了他人手中,成為被建構的,去人格權的女性形象。
4 結語
綜上所述,19、20世紀英語短篇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受到言語、觀念和社會關系等多方面的建構,女性在被詢喚中反抗,在反抗中走向妥協(xié),逐漸失去話語權、身體權,最終失去人格的獨立和自身的發(fā)展,屈從于男性的“文化霸權”。“當今社會,女性形象和性別意義逐漸隨著女性地位的提高而成為社會焦點話題。雖然女性的生存狀況在朝著好的方向發(fā)展,但真正的平等還沒有獲得,在追求男女平權的過程中,女性對于自我認知和自我定位上也存在著矛盾和困難。”(楊珍,2004)實現(xiàn)男女平權是女性主義研究的永恒追求。女性,唯有先覺醒其自主意識,獲得人格獨立和思想解放,才能沖破樊籬,走向平權,獲得個體和群體的全面發(fā)展。這一目標的實現(xiàn),在當代社會依然任重道遠。
注釋
① Doris Lessing,“The Woman on a Roof”,此處為作者自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