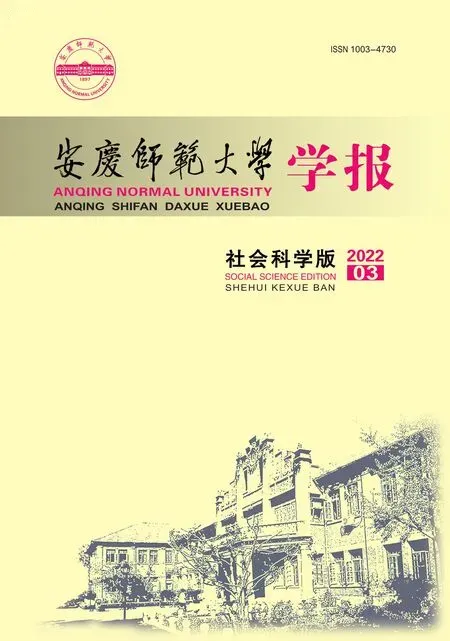南北戰(zhàn)爭后美國南部地區(qū)三農問題的形成
張 準
(四川師范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1)
美國是資本主義大農業(yè)的典型,家庭農場是當前美國農業(yè)的主要生產方式。根據美國農業(yè)部2016年的數據,99%的農場是家庭農場,其產量占農業(yè)總產量的89%,家庭農場中又有90%是年銷售收入低于35 萬美元的小型農場,經營著美國近一半的農田。在美國,農村人口總體上不屬于低收入群體;較之于全國平均水平,農場家庭比較富足,只有3%的農場家庭的財富少于美國家庭財富的平均數,且農場家庭債務很少[1]。因此,國內學界通常認為美國不存在所謂三農問題,至少不存在農民和農村問題。然而,從歷史來看,在南北戰(zhàn)爭后接近一個世紀內,美國南部地區(qū)長期面臨農業(yè)生產方式落后、農民貧困、農村社會發(fā)展滯后的“三農問題”,其影響甚至延續(xù)至今。這種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某一特定地區(qū)長期存在的三農問題,在世界范圍內都是極為罕見的,值得研究。
一、南北戰(zhàn)爭后美國南部地區(qū)長期面臨的三農問題
本文中的美國南部,專指南北戰(zhàn)爭中脫離聯邦、參加南部邦聯的11 個州,即南卡羅來納州、密西西比州、佛羅里達州、亞拉巴馬州、佐治亞州、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薩斯州、弗吉尼亞州、阿肯色州、田納西州和北卡羅來納州①關于美國南部的定義較多且不統(tǒng)一,本文的定義是較為常見的一種,反映美國輿情的蓋洛普民意測驗結果將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馬州也歸于南部,而美國人口調查局則將西弗吉尼亞州、馬里蘭州、特拉華州、肯塔基州和俄克拉荷馬州也歸于南部。參閱李楊:《美國“南方文藝復興”——一個文學運動的階級視角》,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33頁。。
南北戰(zhàn)爭后,不同于美國其他地區(qū),南部地區(qū)走上了列寧所謂的農業(yè)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普魯士道路”而非“美國式道路”。所謂“普魯士道路”是指“農奴制地主經濟緩慢地轉化為資產階級的容克經濟,同時分化出為數很少的‘大農’,使農民遭受幾十年最痛苦的剝奪和盤剝”[2]205。“美國式道路”則是指“地主經濟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沒收和粉碎封建領地的革命所搗毀了。農民在這種情況下占優(yōu)勢,成為農業(yè)中獨一無二的代表,逐漸演變?yōu)橘Y本主義的農場主”[2]205。根據列寧的上述定義,南北戰(zhàn)爭后,在美國全國大部分地區(qū)(以北部、中西部和西部為主)走上“美國式道路”的同時,南部卻走上“普魯士道路”,不僅“使農民遭受幾十年最痛苦的剝奪和盤剝”,也導致南部農業(yè)乃至整個南部社會經濟發(fā)展緩慢,使南部淪為美國最貧困的地區(qū),從而產生了具有美國特色的三農問題。
(一)生產方式落后
內戰(zhàn)期間,一方面大量青壯年從軍,農業(yè)勞動力短缺,另一方面糧食需求激增,農時不能耽擱,北部的農業(yè)機械化開始加速。到1892 年,美國除南部以外的地區(qū)已基本實現以畜力為動力的半機械化農業(yè),此后不到10 年又迅速過渡到機械化農業(yè)。19世紀80到90年代成為美國的“農業(yè)革命時期”,標志著美國農業(yè)整體進入社會化大生產階段[3]。1880 年的第10 次人口調查結果顯示,當時阿肯色州的分成農平均每15~20 英畝僅有“2 把鐮刀、一只籃、一匹馬或一頭驢”,不僅農民不知耕犁和棉花播種機為何物,“實際上種植園主本身也極少擁有這些生產工具”[4]。阿肯色州之外的南部其他七個主要產棉州根本就沒有關于農民擁有農具數量的統(tǒng)計,遑論農業(yè)機械,其農業(yè)生產工具可能比阿肯色州更為匱乏(阿肯色州鄰近北部,無論是內戰(zhàn)前還是內戰(zhàn)后都屬于南部相對發(fā)達的地區(qū))。此時距內戰(zhàn)結束已有15年之久,南部農業(yè)生產方式之落后可見一斑。通常認為南部的農業(yè)機械化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起步。換言之,從內戰(zhàn)后到1920 年,南部的農具和機械并不比內戰(zhàn)結束時有明顯的增長[5]。甚至有美國學者認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南方大部分地區(qū)的農業(yè)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差異不大……在全國其他地區(qū)實現了農業(yè)機械化和推廣了各種節(jié)約勞力的設備以后很久,南方農業(yè)仍然還在使用著大量的人力勞動。”[6]這種說法并非空穴來風,1934 年有美國學者在亞拉巴馬州一個典型的植棉縣份調查了612 個黑人農戶,發(fā)現其中竟有299 戶沒有任何農具——“連鋤和犁都沒有,他們采用的耕種方法還是和奴隸制度的時候一樣。”[7]
(二)農民貧困
內戰(zhàn)前的1860 年,南部白人人均財產高達3 978 美元,幾近北部人均財產(2 040 美元)的兩倍;南部的公民人數占美國的30%,而在全國最富有的人中卻占了60%;南部的人均收入(103美元)雖然顯著低于北部(141美元)[8]38,但如果把占人口近1/3的黑人奴隸排除在外,則南部白人的人均收入未必低于北部①內戰(zhàn)前南部黑人奴隸的人均收入沒有統(tǒng)計數據,福格爾和恩格爾曼的估計為34.13美元(1859年),蘭塞姆和薩奇的估計為28.95美元(1859年),參閱杰里米·阿塔克、彼得·帕賽爾:《新美國經濟史》(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96頁。黑人奴隸占南部人口的1/3,假設取高值34.13美元,則可推算出南部自由人的人均收入約137.4美元,與北部人均收入相當。。簡言之,內戰(zhàn)前的南部是美國的農業(yè)地區(qū)而非貧困地區(qū)。而內戰(zhàn)后的南部迅速淪為美國最貧困的地區(qū),南部農民迅速淪為美國最貧困的群體。1860—1880 年,南部人均收入水平持續(xù)絕對下降;1880年后雖然止跌回升,但直到1930 年也僅僅達到全國平均水平的55%[9]。南部農民尤其是內戰(zhàn)后除了“自由”外一無所有的黑人農民的貧困更觸目驚心。從產出來看,1859 年南部棉花種植園中黑人奴隸的人均產出為147.93美元,1879年黑人分成制佃農的人均產出僅74.03美元,降幅高達50%[10]382。從生活看,據估計,19世紀初南部奴隸的年均生活費用約20美元;20世紀初南部分成農家庭成員年均生活費僅10~12 美元,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其生活水平更是遠遠低于百年前的奴隸[11]173。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記錄也顯示19 世紀后期南部有些農民家庭“連面包也沒有”,生活在“赤貧狀態(tài)之中”,“比當農奴時的生活還慘”[6]。白人小農的處境同樣艱難,據統(tǒng)計,1857—1879 年,南部7 個以棉花種植為主的州的白人人均農業(yè)收入從124.79美元降到80.57美元,降幅達35%[8]339。南部農民的貧困狀態(tài)一直要到20 世紀40 年代后才得以逐步改善。但時至今日,南部尤其是“棉花地帶”②內戰(zhàn)前奴隸制種植園經濟占主導地位、內戰(zhàn)后仍然以棉花為主要作物的地區(qū),大致東起大西洋沿岸的南卡羅來納州,西到得克薩斯州東部,而以墨西哥灣平原的亞拉巴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三州為中心。參閱何順果:《美國“棉花王國”史:南部社會經濟結構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仍是美國最貧困的地區(qū),南部農民尤其是黑人農民仍是美國最貧困的群體之一。2017 年美國的貧困率為13.7%,最貧困的兩個州是南部的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貧困率分別為20.8%、20.6%[12]。
(三)社會發(fā)展滯后
內戰(zhàn)后,在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部以種植棉花為主的單一經濟模式變本加厲。南部11州總面積近200 萬平方千米,人口超過900 萬(內戰(zhàn)初期)。在如此巨大的經濟區(qū)內長期維持這種極度單一、落后、脆弱的經濟模式,顯然是極不合理、效率低下的,是內戰(zhàn)后南部尤其是農村社會發(fā)展長期滯后、人民尤其是農民生活困苦的根本原因。1866—1910 年,南部的棉花種植規(guī)模與棉花產量分別增長了3.1 倍和6.5 倍[13],為此付出的代價首先是農業(yè)生產多樣化和糧食自給。這不僅加劇了南部尤其是農民的貧困,甚至還影響到公共健康與人均壽命。南部黑人的情況尤其悲慘,“雖然二者的狀況都不如北方人”,但“南方黑人與白人相比,死亡率更高,健康狀況更差”。“據可靠估計,(南部)黑人的死亡率在1880 年要遠遠高于1860年的水平,而且直到20世紀初才重新回到1860年的水平。”[14]266
其次,由于棉花種植高勞動密集而低技術含量的特征,長期維持單一的棉花經濟與南部不重視教育的傳統(tǒng)互為因果,對南部教育尤其是公共教育的發(fā)展和科技進步造成不良影響。1880 年,南部20%的白人和超過70%的黑人是文盲[8]387。直到1960 年,南部25 歲以上的人口中,仍有39%的黑人和11%的白人未能接收最基本的5 年教育[15]。
最后,單一的棉花經濟下,工業(yè)化的姍姍來遲又導致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后。直到1900 年,南部城市人口比例為15.2%,不僅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甚至不及1860 年的全國平均水平[16]。換言之,較之全國,南部城市化進程滯后40年以上,是全國“最富有農村氣息和農業(yè)特點的地區(qū)”[17]。
20 世紀30 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tǒng)稱南部為美國的“首要經濟問題”[18]823。二戰(zhàn)前,美國學者寫道:“(南部)這是一個不正常的地區(qū),是一個被包圍在世界上最發(fā)達國家疆域內的落后地區(qū)。”[19]直到20 世紀50 到60 年代,當美國國勢鼎盛、自稱進入所謂“豐裕社會”時,《豐裕社會》的作者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還在用南部農村地區(qū)來闡釋他提出的“隔離式貧困”概念,稱之為美國的恥辱[5]。
二、戰(zhàn)爭破壞和戰(zhàn)后重建對南部地區(qū)社會經濟的重創(chuàng)
歷時4年的美國內戰(zhàn)基本是在南部進行的,尤其是在戰(zhàn)爭的最后階段,北方軍隊深入南部腹地,所到之處造成嚴重破壞,使得“1865年的南部呈現出一派殘垣斷壁、荒無人煙的凄慘景象”[8]225。據統(tǒng)計,內戰(zhàn)摧毀了南部資產總值的2/3、牲畜的2/5和一半以上的農業(yè)機械,被破壞的鐵路和工業(yè)無從計算,南部20 歲到40 歲之間的白人男性有1/4喪生[8]205-206。直到1870 年,南部的財產,即使除去奴隸所代表的部分外,還比戰(zhàn)前少30%[18]706。
以奴隸制棉花種植園為主體的南部農業(yè)在戰(zhàn)爭中受創(chuàng)尤深。除了農場建筑、農業(yè)機械和農作物、產品的大量損毀外,學者估計,戰(zhàn)前一個典型的擁有60 名奴隸的棉花種植園,投資于奴隸的費用至少占到全部投資的50%,有人甚至認為更高[20]。隨著奴隸解放,這筆巨額“資本”頓時化為烏有。據估計,1860 年全部奴隸的總市場價值達27 億美元,接近當時美國GDP 的2/3[10]360,而南部在內戰(zhàn)中的實物資本損失約14.87億美元[10]362。不僅如此,很多南部農場主還因為積極購買在戰(zhàn)后淪為廢紙的南部邦聯債券(1868 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14 修正案明文禁止償還這種債券)而耗盡了積蓄。文學名著《飄》中的女主角斯嘉麗一家本是佐治亞州的大種植園主,內戰(zhàn)前生活奢侈揮霍無度,內戰(zhàn)后一貧如洗瀕臨破產,雖是文學描寫,類似情形在當時的南部卻是司空見慣。而幾百萬被解放的黑人奴隸更是兩手空空,沒有最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更有甚者,由于內戰(zhàn)前的南部法律明文規(guī)定教奴隸識字是犯罪行為,他們幾乎全是文盲。總而言之,內戰(zhàn)后的南部,大多數種植園主除了土地,被解放的黑人除了自由,基本一無所有。
內戰(zhàn)后到1877年被稱為南部重建時期。在恢復被戰(zhàn)爭破壞的基礎設施方面,重建是成功的,到1870 年南部運輸體系已達到戰(zhàn)前最大運量[10]378。而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重建則是不成功的:在政治上,雖然廢除了奴隸制,但代表種植園主利益的民主黨重新控制南部各州政權后,黑人的政治權利被逐步剝奪,到1900 年已經到了基本完全禁止黑人從政的地步[8]390;同時又在社會生活中逐步建立起“從搖籃到公墓”的種族隔離制度,將黑人降為二等公民。在經濟上,內戰(zhàn)和重建沒有改變南部的經濟基礎,舊種植園主大多轉型為地主,而大部分被解放的黑人則成為佃農,繼續(xù)以種植棉花為生,整個南部經濟同樣建立在棉花種植的基礎上,愈加依賴、受制于北部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總體上發(fā)展緩慢、貧困落后。在文化方面,內戰(zhàn)和重建非但沒有改造,甚至進一步強化了南方文化中的一些負面因素,如種族歧視、暴力文化、宗教狂熱等。所以,不僅“1900年的南方人看待世界跟他們的父輩在1830 年看待世界沒有什么兩樣”,甚至有人認為內戰(zhàn)和重建“減緩甚至終止了南方向來自外部的新思想(北方的文化和北方的心態(tài),亦即現代思潮和現代心態(tài))發(fā)展的這一過程”[21]。總之,由于內戰(zhàn)后南部經濟、文化基礎未被根本改造,重建的失敗不可避免,南部就此走上錯誤的發(fā)展道路,工業(yè)化、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緩慢艱難,整個南部社會都為此付出慘重代價,而身為弱勢產業(yè)的農業(yè)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則受害尤重,這是內戰(zhàn)后美國南部地區(qū)三農問題的背景。
三、“三位一體”是美國南部地區(qū)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
馬克思指出,內戰(zhàn)前南部農業(yè)的主要生產方式是“一開始就是為了做買賣,為了世界市場而生產……接種在奴隸制上面的”種植園制,南部奴隸主是“把自己的經濟建立在黑人奴隸勞動上的資本家”[22]。美國學者也認為:“種植園本身具有許多現代工業(yè)企業(yè)的特征,被稱為‘牧場中的工廠’,這一點似乎是能夠達成一致意見的。”[14]251這一制度結合了資本主義和奴隸制最壞的東西——過度勞動和強迫勞動而極度殘酷野蠻,但經濟上的確有利可圖,在內戰(zhàn)前的美國乃至世界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美國學者估計奴隸主對奴隸的剝削率在50%~65%[10]336,而從19 世紀30 年代到內戰(zhàn)前,蓄奴的收益率在9.5%~18.5%[10]331,無怪乎“在1850年和1860 年的美國富翁排行榜上,南方的種植園主比比皆是”[14]253。簡言之,內戰(zhàn)前的美國南部,農業(yè)生產方式罪惡但高效,農業(yè)絕非弱勢產業(yè),種植園主更不是弱勢群體。而在內戰(zhàn)后的南部,小農經濟的租佃制、債務束縛、單一的棉花經濟構成了彼此依存、相互強化的“三位一體”,形成了一種頑固低效、受制于棉花市場波動、缺乏技術創(chuàng)新的需求和動力的農業(yè)生產方式,不僅使南部農業(yè)淪為弱勢產業(yè),更使廣大南部農民淪為弱勢群體,最終導致嚴重依賴農業(yè)的南部淪為美國的落后地區(qū),就此形成了具有美國特色的三農問題。
內戰(zhàn)后,建立在奴隸勞動基礎上的南部種植園制無以為繼,而幾百萬除了(名義上的)人身自由一無所有、世代以來除了種棉花一無所長的黑人無以為生。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和磨合,種植園主紛紛把土地分成小塊,出租給黑人或貧窮白人,小農經濟的租佃制成為南部農業(yè)經濟的主要生產方式。與典型的資本主義農業(yè)租佃制不同的是,南部的租佃農大多沒有基本的生產乃至生活資料,需向種植園主①此時已轉型為地主,但內戰(zhàn)后的南部種植園主往往自己也保留部分肥沃土地從事農業(yè)生產,所以本文統(tǒng)一仍以種植園主稱之。賒購,待收獲后再用收成交租還債,此之謂谷物分成制。內戰(zhàn)后初期,南部390萬黑人中有85.6%是谷物分成農。[11]170谷物分成農與普通租佃農的區(qū)別在于,作為向種植園主賒購生產、生活資料的代價,他們沒有經營自主權特別是自主選擇作物的權利,被迫長期從事單一的棉花種植,甚至連為自己種些口糧都不被允許,而他們生產的棉花在交租還債后即使還有剩余,也只能交售給種植園主。此外,種植園主賒銷生產、生活資料時的價格遠遠高于市場價格,美國學者伍德沃德(C.V.Woodward)指出:“雙價之差從來不低于30%,且頻頻沖向70%”[23];而在收購農民的棉花時往往強制壓價。某些特別惡劣的種植園主甚至做假賬,而南部黑人多是文盲②內戰(zhàn)前除極少數自由黑人外,南部黑人幾乎全是文盲;重建時期的一大成績就是黑人獲得了受教育的機會,1870年南部黑人文盲率降至79.9%,1880年為70%。參閱劉祚昌:《美國內戰(zhàn)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68頁。,很難搞清楚自己的賬目。他們也“很難去選擇最便宜的價格,因為在汽車時代以前,鄉(xiāng)村中平均每70平方英里才有一家商店”[8]344。地租、高利貸、雙軌價格、強制性壓價收購的多重剝削使得南部租佃農往往全家辛苦勞作一年到頭卻發(fā)現自己還欠著種植園主的債務。1880 年《美國棉花生產報告》指出,在南部,“小租佃農場主,主要是黑人,遇到竭盡全力都無法償還的債務情況是普遍的經歷。”[24]重建后,維護種植園主利益的民主黨在南部長期執(zhí)政,南部各州政府相繼頒布法律,把佃戶中斷合同的行為定為犯罪,從而使負債的佃農失去遷徙自由權,事實上被束縛在種植園主的土地上,只能以勞役的形式償債,人身自由徒具虛名。
白人小農的處境也相差無幾。早在內戰(zhàn)前,由于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顯然無法與奴隸制種植園相競爭,他們大多居住在農業(yè)生產條件較差的丘陵、山區(qū),靠雙手“主要是為自己的家庭準備糧食,偶爾種些少量的棉花”[18]711。他們中大多數生計艱難,被稱為“(貧)窮白人”,在南部白人社會中處于最底層。而內戰(zhàn)“永久地改變了南部白人自耕農的獨立生活方式”,一是戰(zhàn)爭造成的財產損失,二是“戰(zhàn)后一連串的農業(yè)歉收使他們的情況變得更糟糕”[18]711,結果就是他們與黑人租佃農一樣要靠借貸度日,被迫種植更多的棉花并以未來的收成為抵押。1860 年,白人小農生產的棉花占南部棉花產量的10%,到19世紀70年代中期已升至40%,足見其日益受制于借貸資本。相應的,“許多原來擁有土地的人此刻也淪落到分成租佃農民依賴他人的困境,只能租種他人的土地。”[18]71119世紀80 年代后,南部最終形成了種植園主和鄉(xiāng)村商人各自控制“棉花地帶”、內地與山區(qū)借貸業(yè)務的地域格局[25]。在債主的重重盤剝下,1889 年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分別有75%和70%的白人小農無力償還債務[26]。
總而言之,內戰(zhàn)后的南部,無論黑人還是白人農民都以小農經濟的家庭生產方式為主。由于缺乏必要的資金和生產、生活資料,他們被迫向種植園主或鄉(xiāng)村商人以賒購的方式借貸,條件則是種植棉花并以未來的收成為抵押。而債主之所以強迫農民種植棉花,美國學者蘭塞姆(Ransom Roger)等認為,一方面是為了強化對農民的債務束縛,“也許這樣才能使債務人難以擺脫其債務,即種植棉花減少了農場的食物自主性,從而確保農場主下一年仍需返回賒購糧食”;另一方面,“棉花存在一個發(fā)展成熟的國內和國際市場,這減少了棉花的交易成本,而諸如玉米等并不存在這一市場。”研究發(fā)現,越是貧窮的南部農民,越會因為債務束縛而“把更高比例的土地用于種植棉花”[10]391。1866—1929年,南部棉花種植面積增長了4.35倍,產量增長了7.31 倍,為此犧牲了糧食自給和農業(yè)生產多樣化[25]。過度植棉不僅耗盡了地力,更必然導致棉花價格下跌;棉花價格越低,農民為償還債務就必須種更多的棉花,導致其價格進一步下跌。1865—1900 年,美國市場上每百磅棉花的價格從39.34 美元下降到7 美元;1866—1900 年南部棉花種植面積卻從730.9 萬英畝增至2 407.1 萬英畝,同時南部人均糧食產量和牲畜飼養(yǎng)數量都有較大程度的下降[27]。低價出售棉花、高價賒購玉米和熏豬肉(當時南部農民的主要食物)是南部農民生活貧困、難以擺脫債務的重要原因。不僅如此,由于真正實用高效的摘棉機要到20世紀40年代才出現,在此之前的棉花生產基本是一種粗放型農業(yè),完全靠農民體力種植和收摘,對生產技術要求不高。在南部存在幾百萬缺乏文化技術、除務農特別是種棉花外無路可走的黑人勞動力的背景下,農業(yè)缺乏技術創(chuàng)新的需求和動力。換言之,這種極度單一的農業(yè)生產模式,又是內戰(zhàn)后南部農業(yè)生產落后、農村社會停滯的直接原因。
四、美國政府與南部地區(qū)三農問題之關系
如前所述,內戰(zhàn)后的南部,小農經濟的租佃制、債務束縛、單一的棉花經濟的“三位一體”使得農民尤其是租佃農遭受地租、高利貸、雙軌價格、強制性壓價收購等多重剝削,加之長時間內的棉花價格下跌,他們中絕大多數無力在還貸后自籌下一年度的生產、生活費用,更沒有積累資金、擴大再生產的可能,只能在“借貸—植棉—還貸—再借貸”的循環(huán)往復中無望掙扎、越陷越深。要打破這一循環(huán),除非有強大的外力介入,寄希望于政府是順理成章的思路。然而,從內戰(zhàn)結束到羅斯福新政前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總的來看,南部民主黨州政府的作為客觀上加劇了當地的三農問題,而聯邦政府雖然采取過一些積極措施,但未觸及根本,收效不大。
(一)民主黨州政府對南部的三農問題推波助瀾
內戰(zhàn)前的南部長期被民主黨把持,內戰(zhàn)后共和黨一度控制又逐步失去了南部諸州政權。1877年,最后一個南部共和黨州政府倒臺,此后民主黨獨霸南部各州政權的局面一直持續(xù)到20 世紀60年代。共和黨在南部短暫執(zhí)政期間曾有過局部、零散的解決黑人土地問題的嘗試,但成果寥寥。而在民主黨重新把持南部州政權后,諸多倒行逆施對當地的三農問題至少有推波助瀾的作用。除了前文中通過法律限制佃農的遷徙自由外,19 世紀70年代后南部各州議會相繼通過保護種植園主利益的“作物留置權法”(Crop Lien Law),使鄉(xiāng)村商人和種植園主得以控制租佃農的作物選擇,如一位農場主在接受國會調查時指出:“如果你想經營一個農場……拿你的棉花作物作為抵押,就不會有什么困難,但是我很少知道以谷物作為擔保獲得借貸的例子。”[28]這是內戰(zhàn)后南部長期單一棉花經濟的原因之一。又如民主黨上臺后,大肆削減公共教育支出,弗吉尼亞州州長公然在議會宣稱:“公共義務教育沒有必要。幾百年來,這個世界沒有它照樣在富裕、文化和精致中發(fā)展。”[29]“路易斯安那州在教育上的投入極少,以致它成為聯邦內唯一的、白人文盲比例在1800—1900 年不降反升的州。”[18]822內戰(zhàn)后建立起來的黑人學校更慘,到1900年,全美國學齡兒童人均教育經費為21.14美元,而在前奴隸制各州,白人兒童人均教育經費僅4.92 美元,黑人兒童更只有2.21 美元。20 世紀初有人考察了南部一所典型的農村黑人學校,發(fā)現該校“沒有課桌……黑板實在太小了以致老師盡量不使用黑板……約7 個孩子合用一本教材”[30]。公共教育的極端落后使得南部尤其是農村中文盲比例居高不下,而缺乏文化無疑是南部租佃農難以開展多種經營或謀求其他職業(yè)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一位種植園主所言:“我這里需要的是能夠種棉花的黑人”,“他們不需要接受教育就能種棉花。”[18]822
(二)聯邦政府對南部的三農問題少有作為
羅斯福新政前,聯邦政府很少干預地方經濟問題。重建的特殊時期,聯邦政府還曾介入、關心過南部的重建和發(fā)展問題,如1866年國會通過《南部宅地法》,試圖解決南部無地農民尤其是被解放黑人的土地問題。倘或這一法律得以充分落實,南部能多出幾百萬獨立小農,則南部農業(yè)也可能像美國其他地區(qū)尤其是西部那樣走上“美國式道路”,三農問題或許就不會出現,至少其普遍性和嚴重性會大大降低。但由于當時南部無地農民(無論種族)大多一貧如洗,無力承擔申請和開墾公地的費用,政府又沒有為之提供借貸支持,最終到1881 年該法律徹底失效之時,僅有21 598 人由此獲得了自己的土地,有學者感慨其為“失去的機會”[28]。此外,聯邦政府在1865—1872年間設立的主要負責安置被解放黑人奴隸的自由民局不僅在建立南部黑人教育、醫(yī)療體系方面有較大的貢獻,也曾有過幫助黑人獲得土地的努力,但成果寥寥。
從1877 年南部重建結束到羅斯福新政前,聯邦政府對南部三農問題乃至經濟社會發(fā)展問題少有關心過問,值得一提的只有1890 年的《莫里爾法》(Morrill Act),法案規(guī)定聯邦每年從出售公有土地的收入中撥款資助各州建立的農業(yè)和技術學院。法案還特別要求即使是存在種族隔離的州,補助金也要“在合理和平等的基礎上分配”,從而促使南部各州為了得到這種資助而紛紛建立起主要教授農業(yè)和機械技術科目的黑人學院。盡管直到1911年的一次調查還顯示上述黑人學院的水平“很多甚至低到公立學校四至五年級的水平”[31],但假以時日,它們逐漸成為南部農業(yè)高等教育的中流砥柱,對南部農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有助于解決三農問題。然而,如前所述,南部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小農經濟的租佃制、債務束縛和單一的棉花經濟,對這些關鍵問題,直到羅斯福新政前,聯邦政府基本不聞不問。
作為對比,羅斯福新政后南部三農問題的破局,一方面在于國會兩次通過《農業(yè)調整法》,以政府補貼的方式引導、鼓勵農民削減棉花種植面積;后來又通過專門的《棉花管制法》限制棉花收購量,進而限制棉花種植面積。另一方面,聯邦政府設立商品信貸公司,直接向農民提供低息貸款,聯邦緊急救濟局也向貧困農民提供信貸作為生產、生活費用,從而在事實上取代了南部種植園主和鄉(xiāng)村商人向農民提供借貸業(yè)務的職能,使之得以擺脫債務束縛。三位一體中的兩個得到解決,南部的三農問題乃至整個社會面貌隨之大為改觀,足見此前聯邦政府在南部三農問題上長期無所作為,是不為者,非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