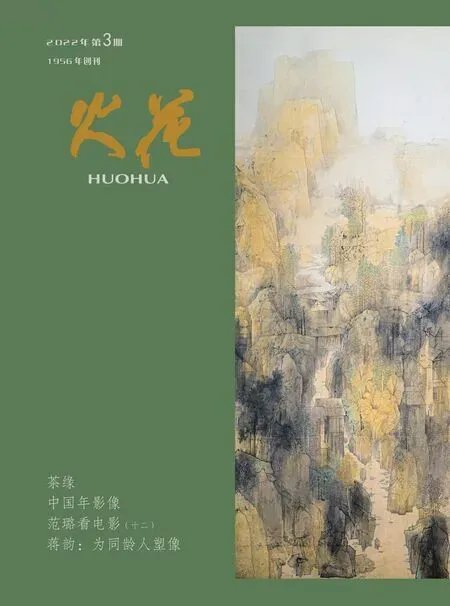小團圓
王舉芳

太陽真好。橙黃色的光輝給世界蓋上一層暖色。楊老漢一手拄著拐杖,一手摸摸衣服上的陽光,抬起手,抹掉眼角的淚,向養(yǎng)老院門外走。今天他請了假,不住養(yǎng)老院,他要回家去。
“老楊頭,你干啥去啊?”李嬸走出房門,正好看到楊老漢。
“我,不干啥,我想出去轉轉。”
“轉啥啊?外面的世界有什么好看的,吵吵鬧鬧的,你不嫌煩啊?咱們老了,老實呆在這里享清靜多好啊。”
“我想回家看看。”
“回家?你家里不是沒有親人了嗎?冷冷清清的有啥好看的?”
李嬸你才來養(yǎng)老院幾天啊,等你新鮮勁兒過去了你就不這樣說了。哪里都沒有自己的家好,家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讓你覺得安穩(wěn)踏實的地方,不管它是別墅豪宅,還是低矮的茅草房,那里有你的親人,那里處處都彌漫著溫暖的氣息。楊老漢心里這樣嘀咕著,嘴上敷衍李嬸一句:“就看一眼,我明天就回來。”
“你看你都這么大年紀了,還一個人乘車顛簸,也沒個人陪著,多讓人不放心啊。”
楊老漢盯著李嬸的臉,不吱聲。不一個人回去能叫誰陪著呢?
李嬸見楊老漢的臉色有些陰沉,覺得自己話太多了,但還是補充了一句:“那你一個人小心點哈,路上注意安全!”
楊老漢收回目光,“哎”一聲,走出了院門。
寬敞的大街人來人往,沒有人認識楊老漢,楊老漢也不認識他們。走在如流的人群里,楊老漢覺得自己好孤獨,對,很孤獨。楊老漢輕輕嘆一口氣,踽踽前行。
前天夜里,楊老漢做了一個神奇的夢,夢里他的老伴清晰地喊他:“老頭子,你回來啊,回來跟我們團圓啊。”說著把手伸向他。他高興地伸出手握住老伴的手,老伴的手竟是溫熱的,他喜出望外,說:“老伴啊,你等著,我這就回家。”老伴笑了,笑著笑著就不見了。楊老漢一著急,醒了。老伴已去世十多年了,這是他第一次這么真切地夢到老伴。
“嗯,是該回家看看老伴了。”
想起老伴,楊老漢的心開始隱隱地疼。那可是個難得的好女人哩。
那時楊老漢二十出頭,長得不說是英俊瀟灑,但五官端正,個頭高挑挺拔,也算儀表堂堂。也有幾個姑娘對他示好,可他想想自己重病在床的娘,還有那個愛抽煙喝酒賭博、整天沒正事兒的爹,無奈地搖頭拒絕。誰家爹娘會同意讓自己的女兒跟這樣家庭的孩子結婚呢?過日子是持久戰(zhàn),不是一時頭腦發(fā)熱,更不是圖惜一個人的外貌啥的,娶了人家姑娘,如果不能給人家好日子過,就不算好男人。做不了好男人,也不要去連累人家姑娘了,這樣思忖了好久,他便不再想結婚的事兒了。
他去村子附近的磚廠打工,他要掙錢,他不想讓娘眼巴巴在炕上等死。可事情并不是他想象中那樣容易。他沒來之前以為磚廠就是力氣活兒,只要自己肯下力氣就行,沒想到不光需要力氣,還需要技術和技巧。
他被安排在磚機旁,和一名女工友一起把磚機切好的磚坯子抬到推磚坯的小車上。才短短半個小時,他就受不了了,女工友說:“要不然咱倆交換一下位置吧,我看你左胳膊使不上勁兒。”
就這樣來回倒替著,終于挨到了午飯時間。大家伙兒去洗手吃飯,他拖著沉重的身子跟在后面。他從沒感覺到自己的身體竟是如此之重,也沒想到看似簡單的力氣活兒真干起來原來如此艱辛。好不容易挨到水盆邊,其他工友都已經(jīng)洗完手,拿著飯盒開始吃飯了。
他擰開水龍頭,水沖洗著他手上的泥,手慢慢露出本來的模樣,順著手淌下的水漸漸清澈,竟有了血的顏色。
“你的手怎么了?”是隊長。
“哦,沒事兒。”他關上水龍頭,兩手用力不停甩著,他想甩干凈手上的血水,卻怎么也甩不干凈。他知道自己的手之所以如此脆弱,是因為沒經(jīng)過勞動的磨練,沒有繭子。要是像母親的手那樣布滿了厚厚的堅硬的繭子,就不會被磨破了。母親沒病倒之前,從來不舍得讓他下地干活兒,說他的任務是上學,把學上好了就是對娘最大的孝順。
“接下來會很疼的,你下午不要再干了。”隊長對他說。
“不疼,隊長,我能行!”他望向隊長的目光溢滿了懇求。
“不行,你的手這樣,不能再干了,你看看這血泡都破了,你怎么干?會感染的!下午不要再來了,來了我也不讓你干!”隊長拿眼睛瞪著他。
他很懊喪,覺得自己與廢物無異。他向家走,察覺好像有人跟著他,猛回頭,是和他抬板子的女工友。女工友說:“我找你有事兒。”他疑惑地望著她。
“我同學在不遠的縣城里開了個店鋪,讓我給找個老實勤懇的人打下手。我覺得你是個實在人。你認字嗎?”
“嗯,我高中畢業(yè)的。復讀了兩年,還是沒考上大學。”
“哦,那太好了。這樣,我告訴你店鋪名和地址,你直接去,就說是我介紹的。”
“謝謝您,我回去和爹娘商量商量。”
回到家,躺在硬硬的木板床上,他望著滿手的血泡,血泡已不流血了,滲著點點露水似的清液,開始燎燎的疼。也許自己真的不適合在磚廠干,也許去店里打雜會更好。反復思索后,他按照女工友說的地址找到那家店鋪。老板一聽他說出女工友的名字,立馬讓他留下來。
第一次開了工錢,他想應該謝謝女工友,可怎么謝呢?請她吃飯嗎?她肯定不會去。給她買點什么禮物呢?思來想去,他給女工友買了一瓶花香洗發(fā)水。那一天他們兩個人抬板子,她身上陣陣花香彌漫,好聞極了。
后來一有時間,他就去磚廠看女工友。漸漸地,他對女工友暗生情愫,卻不敢說出口。直到一年后,女工友向他表白,說我知道你對我是真心的好,你對我真心好,我們就能把苦日子過得甜甜的。就這樣,女工友成了他的妻子。
妻子勤勞、賢惠,把母親照顧得好好的,不讓他有一絲后顧之憂。兒子出生后,父親戒了惡習,母親的病竟也奇跡般地轉好,一家人其樂融融。那么溫暖的時光,多讓人留戀啊。
想起這些,楊老漢的眼睛有些潮濕。
當初楊老漢來養(yǎng)老院是特殊照顧。他身無分文,養(yǎng)老院里的老人,只有他是“吃白食”,只因為院長張鵬和他兒子是朋友。楊老漢執(zhí)意回家還有一個原因,那天他看電視上說有老人突然病死在養(yǎng)老院,死者親屬大鬧養(yǎng)老院。人家院長好吃好喝好住地照顧了他近十年,臨了,不能再給人添麻煩。
十多年前,老伴患病受盡折磨離世,楊老漢十分悲痛,然而,上天還嫌他的心傷得不夠,又給他加了一把鹽。半年后,兒子駕車和張鵬外出,路遇大霧,遭遇連環(huán)車禍。張鵬受了重傷,沒有危及生命,兒子當場死亡。經(jīng)過兩次人生至極悲痛的打擊,楊老漢覺得自己的身子一下子空了,像極了一片搖搖欲墜的葉子。
兒媳受不了睹物思人的折磨,帶著孫子楊樂回了省城娘家。楊老漢不怨兒媳,兒媳還年輕,替他照顧孫子已很好。想起孫子楊樂,十多年未見,該是大小伙子了吧?楊老漢突然改變了主意,向汽車站走去。
坐在汽車上,往事隨著車身搖晃在楊老漢面前跳躍。
兒子大學畢業(yè)那年,領女朋友回家見爹娘。楊老漢望著這個涂脂抹粉、穿著時髦的女孩,在心里直搖頭。
他把兒子拉到一邊悄悄說:“這樣的女孩,你娶回家還不得供著啊。”
“爹,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多好,耐看。以后讓我媽也打扮打扮,誘惑誘惑你。”楊老漢抬手給了兒子一巴掌:“你這混小子,沒大沒小的。”
兒子說結婚不另外買房,就在家里和爸爸媽媽一起住,有車,上下班也用不了多少時間。楊老漢說:“咱這鄉(xiāng)下蒼蠅蚊子的,你媳婦能受得了?人家可是大城市里的人。”
“大城市里的人更向往田園生活。‘山溝里空氣好,實在新鮮……’”兒子學著戲里的腔調唱。
出乎意料的,兒媳不是他們想象中嬌里嬌氣的小姐性格,周末休息,她換上婆婆的樸素衣裝,跟著婆婆一塊兒下田,不同的是,她走在鄉(xiāng)間小路上,看見一朵野花會叫:“呀!好美的花啊!”會指著那些蔥蘢的莊稼問:“這是什么?那是什么?”像個天真又無知的孩子。
婆婆一一告訴她每一種莊稼的名稱和成熟后可以做什么食材,兒媳聽得很認真,然后撫摸著那些莊稼,表情嚴肅而神圣:“好偉大啊,是它們供養(yǎng)了我們?nèi)祟悺!逼牌趴粗残︻侀_,禁不住說:“看你,多像銀環(huán)啊。”
孫子楊樂的出生,讓幸福的日子增添了活潑與靈動的氣息,也把一家人的心凝聚得更緊。
其實楊老漢夫妻與兒媳相處也有爭吵的時候,不過都是些小問題,吵完了,大家把話說開了,心里都不存下什么,日子依舊平安無事。
與兒媳吵得最厲害的一次是因為孫子楊樂。那天,兒媳下班回來,剛剛學認字的楊樂撲進媽媽懷里說:“媽媽媽媽,今天爺爺教我認新字了。”楊樂用稚嫩的小手翻開那本看圖識字書,指著念:“蛤蟆,爺爺說蛤蟆會叫,這樣叫,呱,呱,呱。”看著楊樂可愛的樣兒,兒媳禁不住摟住他響亮地親了一口:“樂樂真棒!”娘倆嬉鬧了一番,兒媳忽然看到兒子的識字書上寫的不是“蛤蟆”兩個字,而是“青蛙”。兒媳收住笑臉問楊樂:“是誰教你這念‘蛤蟆’的?”
“是爺爺。爺爺說還要帶我去河邊看活蹦亂跳的蛤蟆呢。”
兒媳問楊老漢:“您怎么可以亂教孩子,孩子他不懂事,您也不懂事嗎?您這樣亂教他,會害了他的。”
楊老漢嘀咕一句:“青蛙和蛤蟆有啥區(qū)別啊?”
“青蛙是青蛙,蛤蟆是蛤蟆,您這樣亂教楊樂,會害了他的。”
楊老漢沒再說什么,悶悶地走出了院子。他怎么會害自己的孫子呢?那可是他們楊家的命根子啊。兒媳連著兩次說他害自己的孫子,他心里難受極了。一連多天,他都悶著臉不說話,誰勸都不行。
那天老伴正在田里干活,忽然昏迷暈倒,楊老漢嚇壞了,忙給兒子打電話,兒子說在外出差,讓他不要著急,快打120電話,說馬上讓媳婦回去。兒媳趕到醫(yī)院,跑前忙后跟著做各種檢查,一番忙亂之后,老伴被推進病房,一直昏迷著,楊老漢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來回打圈兒。
兒媳安撫他坐下:“爹,您別著急,有我呢。”兒媳頓了頓又說:“爹,我跟您說聲‘對不起’,前些天是我不好,惹您生氣了。”
“一家人,說啥對得起對不起的,我知道你是為樂樂好。你娘的病,醫(yī)生怎么說?”
“不太樂觀。醫(yī)生說是腦干出血,而且出血點不少,但希望還是有的,一會兒安排開顱手術。”
看著兒媳盡心盡力,楊老漢的心安定了不少。
老伴還是一直昏迷著,身上布滿了各種檢測儀器的線和管子,吃飯只能從插入食道的管子里用注射器推入一些米湯,稍不合適,還會被嗆到。幾個小時后,老伴又經(jīng)歷一次開顱手術,喉管也被切開了。看著老伴如此模樣,楊老漢默默地落淚。
兒子的電話隔幾個小時就打一次,每次兒媳都說:“你放心吧,有我和咱爹呢,你好好開車。”
老伴在醫(yī)院住了一天一夜,還是走了,沒有等到兒子回來。楊老漢從沒覺得一天一夜原來如此漫長,如從生到死那樣漫長。
然而,僅僅半年之隔,兒子也因車禍離開了人世。楊老漢的頭發(fā)一下子幾乎全白了,背也佝僂了。上完兒子的百日墳,兒媳跟楊老漢說:“我想帶樂樂回娘家住。”
“嗯,走吧,照顧好樂樂,他可是我們楊家的獨苗啊。”兒媳和孫子是哭著離開的。楊老漢看著他們的身影越來越遠,漸漸消失不見,禁不住老淚縱橫。
“妻不在兒也去,家破人亡,家破人亡啊。”楊老漢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雙手抹著滿臉的淚水。同座位的乘客看著他,眼神里有詢問與關切。楊老漢擠出一絲笑容說:“沒事,沒事,都過去了,都過去了。”
到省城已是黃昏,人車如流,楊老漢沿著馬路邊小心翼翼地走著。一個轉彎處,楊老漢望著紅紅綠綠的交通指示燈,猶豫了一會兒,正要走,一輛汽車嘎然停在了他的一側,楊老漢嚇得一下子蹲在了地上,司機是個小伙子,搖下車窗說:“大爺,咋?碰瓷啊?您這演技也太差了吧。”
楊老漢自己努力站起來,說:“小伙子,不是每個老人都喜歡賴人。我只是被你的剎車聲嚇到了才摔倒的,我不會賴你。你放心,我就是倒也不會故意倒在人家車上的。”
聽楊老漢這樣說,小伙子打開車門下車說:“老人家,您活動活動,看看哪里摔疼了沒?”楊老漢慢慢伸伸胳膊,慢慢伸伸腿:“都不疼。”
“要不,我還是帶您去醫(yī)院看看吧。”
“不用,真沒事兒,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知道,小伙子,謝謝你,你快去忙吧。”
楊老漢邊走邊自言自語:“再怎么著也得做個好人啊。做個好人,自己心里舒服啊。”
楊老漢記得親家的商鋪就在車站附近,過了馬路,走幾百米就到,只是十多年前的省城還沒有這么多的高樓、汽車和人。
“楊樂商鋪”,楊老漢看到這幾個字,停住腳步,躲到人行道旁樹后偷偷向商鋪里張望。
商鋪里,一個小伙子正熱情地招呼顧客,眉宇間透著英氣。“這小伙子肯定是楊樂,真像他爸爸啊,越來越像了。”楊老漢的眼里忽然蓄滿了淚水。
楊老漢向前走了幾步,又倒了回來。思忖再三,楊老漢決定不去打擾兒媳和孫子,知道他們生活得很好就心滿意足了。楊老漢找了一家旅館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坐車回了老家。
老家的房子年久失修,已破敗不堪,東廂房因為鄰居在里面放雜物,尚完好。見楊老漢回來,鄰居幫他收拾了雜物,搬來一個折疊床給他睡,楊老漢沒說謝謝,只一個勁兒地說:“遠親不如近鄰,這話一點也不假啊。”
第二天楊老漢沒回養(yǎng)老院,張鵬來接他,他說:“我想在家多呆幾天,我想家啊。”張鵬依了他,拜托鄰居好好照顧他。
楊老漢坐在陽光里,瞇著眼睛想往事。中年喪妻,又失去兒子,他偷偷哭醒過很多個夜晚,那些日子,他覺得自己的心和身都麻木了。兒媳帶楊樂回省城后,楊老漢看著孫子的照片,混沌的心智清醒了許多。他告訴自己不能再待在家里,便出去找活兒干,誰知從高架子上跌下來,傷了脊椎,醫(yī)生說怕是從此再也不能干重活。出院后,張鵬把楊老漢接到了養(yǎng)老院,親爹一樣侍奉。以前楊老漢總慨嘆自己命苦,今天一番回味之后,他覺得自己也是幸福的。
是啊,多好的日子,有人照顧,衣食無憂,有那么多美好的記憶暖著心窩,還有一個那么青春陽光的大孫子,多好啊。
夜里,楊老漢又夢見老伴喊他團圓。天色微微亮,他起床穿戴整齊,向村外的墓地走去。老伴的墳上荒草叢生。旁邊兒子的墳上也荒草叢生。一陣眩暈,楊老漢在老伴和兒子的墳中間緩緩地倒了下去。
不知睡了多久,楊老漢聽到有人喊他:“爺爺,爺爺,我是楊樂……”楊老漢緩緩睜開眼睛,笑了。
楊老漢指著張鵬對楊樂說:“這些年,都是你張鵬叔在照顧我,你要記得。人要懂得感恩。”
楊樂點頭應答著:“嗯,我記得的。我媽也常說這些年多虧了張鵬叔呢。”
張鵬說:“楊叔,其實這些年,是楊樂媽媽拜托我照顧您的,她每月都到養(yǎng)老院悄悄看您,交費用,還有您的衣服鞋帽也都是她買的。她后來又嫁了人,做到這樣,很不容易啊,比有些親女兒都強……”楊老漢嘴巴抖動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眼里擠滿了淚花。
“爺爺,我媽說這幾天就找人修房子,等房子修好了,我們立馬搬回來和你一起住。要不是我外公癱瘓了七八年,我們早就回來了。”
“哎,哎,好。”楊老漢一直盼的就是這一天呢。他轉念一想,又變卦了:“這可使不得,你媽不是成家了嗎?我不能拖累你們,給你們添麻煩。我還是回養(yǎng)老院的好。”
“爺爺,這件事我媽和繼父早就商量過了,他十分支持。爺爺,你看,這是我繼父家的妹妹,她也愿意和我們一起來陪您……”楊樂說著拿出手機打開相冊翻給楊老漢看。
楊老漢含著淚笑了。他知道,他的晚年再也不會一個人孤獨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