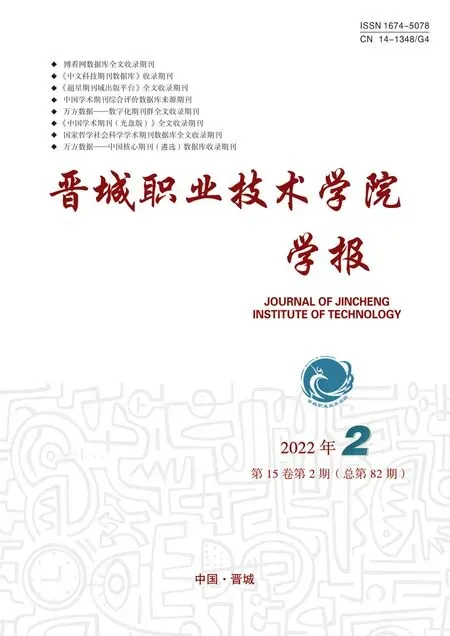《紅樓夢》與《牡丹亭》“學堂”風波比較論析
牛宇佳
(寧夏師范學院 文學院,寧夏 固原 756000)
《紅樓夢》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1]227,將《牡丹亭》第十出【皂羅袍】中的唱詞“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2]43-44三句引入小說,從這個背景看,《牡丹亭》與《紅樓夢》有天然的姻緣關系。
學者常將《牡丹亭》與《紅樓夢》比較對讀,比如《紅樓夢》對《牡丹亭》“至情論”思想的承繼與升華等。因此,從宏觀上比較研究這兩部著作是學界慣例。二者在微觀上也有許多可比較的內容,有學者從女性意識、女性命運、愛情觀、教學觀、藝術典型性和美學等角度來對比探討。本文選取“學堂”這一視角,通過論析《紅樓夢》和《牡丹亭》中的“學堂”風波,分析二者敘事手法之異同,管窺作者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對《牡丹亭》第七出“閨塾”和《紅樓夢》第九回中“鬧學堂”事件進行文本分析,可知學堂作為一種場所,不僅在故事情節中承擔敘事的功能,而且承擔著文化功能,而學堂功能又會隨著人們思想的流變而發生蛻變。
一、學堂功能的變化
學堂是舊時學校的稱謂,如唐代韓愈《秋懷》“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愿”[3]3771。《紅樓夢》中賈府的“‘義學’是清代康熙中開始設立的……乾隆以后,內地也廣泛設立‘義學’……一直到清末都是清代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義學分為私立和公立兩種”[4]227。因此,賈府的義學屬于私立的家塾。《牡丹亭》中“閨塾”的概念和《紅樓夢》中“家塾”的概念都屬于私塾的范疇。春秋戰國的文獻《禮記·學記》即有“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5]957。私塾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伴隨著土地私有制而出現的,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面,唐宋時已基本普及,明清時形成一種制度,在民間廣泛設立。
劉小楓在《沉重的肉身》中,講述了自己起初未能公平地給“美貓”與“丑貓”喂食,后來在鄰家女孩勸導下幡然猛省的故事。[6]9-10說明對美丑的“定見”影響了人的行為。在《牡丹亭》和《紅樓夢》中“學堂”的定見卻未能影響人們的行為。晚明時期,“王學”成為了一種新的時尚,給中國的思想帶來了自由之風。[7]323人們開始關注“個人”和“心靈”。“1625年6月,皇帝下詔,正式決定拆毀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7]320-325這種自由主義思想受到了來自統治階級的抑制,人們紛紛轉向了實用之學和重建朝綱的秩序之學。但隨著明朝的滅亡,滿族人入主中原,漢人的地位相對較低,曾經一度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也不能控制所有區域的思想,到清中葉,思想啟蒙思潮又一次涌起,《紅樓夢》《儒林外史》的出現,正是這種思想在文學上的折射。在兩部作品鬧學堂事件中,也可見中國儒家理學思想面臨的困境。如在《牡丹亭》第七出“閨塾”中,陳最良本要傳授后妃賢達,卻在春香的一次次提問中,變成了激發杜麗娘反抗意識的導火索。從春香的語言“溺尿去來”[2]27和“村老牛,癡老狗,一些趣也不知”[2]28。可見與傳統的學堂功能背道而馳。在《紅樓夢》第九回的“鬧學堂”事件中,一群紈绔子弟大打出手,說出一些類似于“親嘴摸屁股……”[1]97的言語,可知“學堂”功能發生了轉變,人們開始逐漸擺脫禮的制約,任性而為,忽略了學堂的真正功能。在《紅樓夢》第九回和《牡丹亭》第七出中借助閨閣女子的反抗和男子們性情釋放的故事情節透露出“學堂”已不再是傳授知識、交流文化的場所,而被學生娛樂化、自由化,甚至淪落為人性的禁錮之地與禮崩樂壞的集中體現之處。《紅樓夢》原文中的“一龍生九種,種種各別”[1]96和“斗雞走狗、賞花玩柳”[1]98更是體現了貴族子弟的荒唐與頹廢。此外,在《牡丹亭》第七出和《紅樓夢》第九回中對于人物之間的情感描寫展現了人們對自由的追求,隨著人物思想的轉變,學堂功能也發生了蛻變。
“學堂”本是教育場所,作者利用這一司空見慣的場所,以波瀾不驚的筆墨,從一個小小的側面,反映出封建倫理思想的缺陷、乃至于瀕臨崩塌的尷尬處境。如果說《牡丹亭》中“鬧學”一折,通過杜麗娘與春香的質疑,對封建迂腐的教育內容提出了挑戰,“學堂”之弊尚有改良的余地,那么到了《紅樓夢》第九回,“學堂”不僅喪失了教育的功能,反而成為貴族子弟不思進取、藏污納垢、交流不堪想法的污濁之地,“先生”不僅迂腐,而且缺位。湯顯祖戲曲的主情思想,受到泰州學派羅汝芳的影響。在《牡丹亭》“閨塾”這一出中,為后文的驚夢、尋夢的故事情節作了鋪墊。學堂本是用禮來約束人的地方,但卻成了杜麗娘感知情、釋放情的開始。在《紅樓夢》第九回中的家塾本是舉“年高有德”之人,專為族中弟子授課,但各家族子弟的天性和情感未完全受到傳統禮教的約束,而是遵從于心,發乎于情。《紅樓夢》中的“鬧學堂”事件與《牡丹亭》中“閨塾”的授課形式基本上是一樣的,均由先生傳授;不同的地方在于人數和規模的大小,《紅樓夢》第九回中上課人數要略多一些,規模稍大一些。《紅樓夢》中對氏族紈绔子弟風流情的描寫,從側面體現出了“學堂”功能的衰退,甚至是在主人公心中的喪失。
二、學堂的敘事功能
(一)“小我”的喪失
在兩部著作中均體現了“小我”的喪失,賈寶玉處于雙重“禮”的壓迫之下,一邊是來自家族禮儀制度的約束,一邊是學堂所帶來的入仕的制約,雙重的壓迫導致了雙重的人格,使人們在被動接受的道路上,一直在試圖做出反抗。在人物雙重性方面,《紅樓夢》“學堂”風波中賈寶玉的形象與《牡丹亭》“學堂”風波中杜麗娘的形象有異曲同工之妙,杜麗娘身上背負的是家族的束縛和所處時代的制約。不同之處在于兩部著作中作者的敘事手法和敘事角度不同。《牡丹亭》第七出的學堂風波在女性化的敘事空間中呈現,而《紅樓夢》學堂風波在男性化的敘事空間中展開。杜麗娘為情而生,為情而死,是靈魂“在世界上飄蕩,尋找外界的物種,以便借助它來起作用”[8]49,從而“增加了敘事的魅力,符合聽故事者的心理期待”[8]50。通過先生講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9]1的情節,激發了杜麗娘的自我意識,為《牡丹亭》后文的“天神”觀念和“人鬼”觀念的描述作了鋪墊。杜麗娘在夢中與柳夢梅相會,可見,在每一個“小我”的身上,都渴望實現真正的“大我”與環境融為一體[8]46。《牡丹亭》中杜麗娘在后花園中展現出對愛情的向往體現出制度是無法阻止人與自然共存的。《紅樓夢》第九回中作者對一群紈绔子弟動作和語言的描寫,透露出他們的風流本性和自我墮落的思想,同時也為下文《紅樓夢》大家族的命運埋下了伏筆。學堂不僅傳承文化,還承載著希望,而“鬧學堂”事件,不僅展現出紈绔子弟們未能融入學堂的文化氛圍中,且新一代的紈绔子弟不曾懂得生活的真諦而只顧風流,最終只能自食其果。杜麗娘通過“看”釋放自己內心的真情實感,而《紅樓夢》中的各位紈绔子弟則是“被看”的一覽無余,他們的丑陋被深入地揭露和呈現出來。作者分別從“觀察”和“敘述者”兩個角度寫出了鬧學堂事件中人們對禮的突破,閨閣女子和貴族少爺都開始追求情,甚至到《紅樓夢》時,為情者,不分男女,由于“小我”的喪失,未能更好地融入到“大我”之中,最終走向滅亡。
(二)需求的轉變
從敘事學的角度來看,兩部著作中均涉及主人公需求轉變的相關內容,但《紅樓夢》“學堂”風波中需求的轉變比《牡丹亭》更進一步。《牡丹亭》“學堂”風波中的敘事手法是先抑后揚,《牡丹亭》第七出中通過先寫恪守傳統倫理規范的杜麗娘以及希望杜麗娘能夠跟隨陳最良老師學習到更多傳統賢德文化的父母,后寫杜麗娘和春香去往后花園,使原本壓抑的天性被釋放了出來。但就《牡丹亭》第七出這一回而言,透過陳最良先生對《詩經》的解讀,可見杜麗娘的天性還是處于被壓制中,不過在春香的指引下亟待噴薄。《紅樓夢》“學堂”風波中的敘事手法是先揚后抑。在《紅樓夢》第九回中每一個人物絲毫沒有顧及禮的制約,“隨心所欲,發了癖性”[10]133,加之一些粗淺的語言。可見他們并沒有壓抑自己的性情而是胡亂地打鬧,在事情無法收場的時候,考慮到自身的身份和地位,金榮迫不得已壓抑自己的情感,作揖磕頭結束了這一場鬧劇。“人的欲望是其自身處境的折射”[8]57,伴隨著“學堂”功能的退化,人的欲望可能不再是考取功名,而選擇了“小我”情感的釋放。當人們對一種東西有“需求”的時候,就會想方設法地去“擁有”,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主張節制欲望以獲得內心安寧”[8]62。而在《牡丹亭》第七出和《紅樓夢》第九回中,則表露出人們開始去關注自己的需求,并為需求的實現付諸行動。《牡丹亭》第七出中杜麗娘內心情感的需求還停留在思想層面,到《紅樓夢》第九回中,頑童們的需求已轉化為實際行動。
(三)傳統的錯位
《紅樓夢》第九回和《牡丹亭》第七出中學習內容都涉及到了《詩經》,不同的是《紅樓夢》“學堂”風波中學習的內容包含《四書》,《牡丹亭》“學堂”風波中提及《昔氏賢文》《六經》等學習內容。《詩經》的內容是豐富多彩的,在歷史上,對于想要步入仕途的人而言,學習《詩經》是必備的。《四書》凝聚了儒家思想,曾是科舉考試的指定教材,對于一心想要讓寶玉考取功名的賈政而言,自然要求寶玉先把《四書》背熟,而《昔氏賢文》和《六經》中涉及儒家思想和道德規范的內容。可見明清之際,對于貴族子弟而言,深受儒家傳統禮教的束縛,而出現在課堂之上的滑稽鬧劇,表明了人們對于自由思想的向往。其次,作者賦予了人物鮮明的個性,無論是紈绔子弟還是閨閣女子都渴望擁有常人的情感和欲望,而不僅僅是家族光環下的賢達子孫。傅修延在《中國敘事學》著作中提到“我們要重溫‘原生態敘事’有助于鉤沉許多業已失落的生態記憶”[8]64。在《牡丹亭》和《紅樓夢》中均主張對于《詩經》的學習,以及《四書》《六經》。在《紅樓夢》“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中出現了三處賈政訓斥寶玉之語:“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哪里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10]225“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10]229和“胡說,偏不‘沁芳’二字。”[10]229可見賈政對于寶玉有一種更高的期待,希望他能博覽群書,考取功名。賈政一句“不讀書之過”[10]225指出的不僅是特定時期下紈绔子弟身上的通病,直至今日,這句話仍值得反思。《牡丹亭》中杜麗娘的讀書并非求取功名,正如《牡丹亭》第五出“……習《詩》罷。其余書史盡有,則可惜他是個女兒”[2]17。因此,《牡丹亭》中的學堂風波為后文杜麗娘情起奠定了基礎,開啟她思想中“情”的因子,結合《牡丹亭》的結局,可知思想的錯位,造成杜麗娘愛情的錯位。《紅樓夢》第九回父輩對傳統的繼承和新一輩人對傳統的遺失形成鮮明對比。寶玉本應承擔起大家族的重任,實則游離于功名之外,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的錯位,最終也造成了主人公人生的錯位。
(四)先生的缺位
《牡丹亭》第七出中通過對話的形式勾勒出了先生的形象,同時通過先生教育的缺位為杜麗娘情的萌發提供了條件。在《紅樓夢》第九回中,則是通過先生的缺位為紈绔子弟們的種種風流埋下伏筆。賈府作為“詩禮簪纓”之族,本應培養后繼人才,透過“鬧學堂”這一事件,可見新一代接班人教育的失敗也暗示著大家族的沒落。正如傅修延所提及的“空”與“滿”的理論,“‘空’是欲望的符號,‘滿’是實現的符號”[8]92。正如學堂的每一位學子大多是空空如也,而學堂就是實現對知識“滿”的手段。《牡丹亭》第七出通過陳最良滿堂灌的教學模式,更加凸顯了杜麗娘和春香的“空”進而激發出她們的情感,同時,湯顯祖借助“學堂”風波事件把杜麗娘的情停留在亟待噴發的階段。《紅樓夢》第九回中通過先生的缺位為頑童們情感的釋放提供了條件,從而引發了大鬧學堂這出鬧劇。
(五)細節描寫中的“情”與“禮”
兩部著作鬧學堂事件中均涉及細節描寫,不同之處在于《牡丹亭》從“情”的層面,引出對后花園的描寫,而《紅樓夢》是從“禮”的層面來敘事。在《牡丹亭》“閨塾”中的結尾處涉及到了后花園的描寫,環境代表了一種隱喻。正如“‘環境友好’意味著情感的投入……敘述者對自然美的欣賞態度才有毫不隱晦的流露”[8]53。杜麗娘對后花園景色的陶醉,正好映襯了她心中對于美好情感的向往,“驚夢”一出敘寫了杜麗娘夢里發情。湯顯祖通過建立“另一個經典世界”[11]444的方式,來體現杜麗娘的叛逆和反抗,同時以夢的形式構建了一個與儒家經典不同的精神世界,為后文杜麗娘為情生為情死的情節提供了依托。后花園作為連接兩個世界的交點,是杜麗娘精神世界和現實世界的載體,同時,后花園作為構建兩個世界的橋梁和紐帶,在結構和故事情節的起承轉合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可見作者敘事手法之高妙。
《紅樓夢》第九回中去家塾之前的請安和作辭的行為,也引人深思。孔子開創了私學,提倡克己復禮,周禮在孔子心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儒家學說,經過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韓愈等人的發展,到朱熹、王陽明發展到儒學新階段。明清之際,經過了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批判性地繼承發展。《紅樓夢》中賈寶玉去家塾之前,向長輩請安和平輩作辭的行為,說明了禮的觀念深入人心。通過這種由點到面的寫作手法,為后文敘述鬧學堂事件的細節埋下了伏筆,實現了由點到面的自然銜接,可見作者行文安排之縝密。
三、鬧學堂事件隱含的文化反思
在《紅樓夢》第九回和《牡丹亭》第七出中均表現出作者對學堂功能的蛻變和中國正統儒家思想的反思意味。湯顯祖和曹雪芹在鬧學堂事件中,都表現出了男女主人公對“情”的追求與釋放。在《紅樓夢》第九回和《牡丹亭》第七出中無論是人物塑造,還是情節的刻畫,都關注人物的內心。人不僅僅是個體的人,也是社會的人,在學堂這樣的環境下,學子們本應受到禮的束縛,而不是隨個人的性情而轉移。學子們通過發乎性情的方式在反抗傳統禮教的同時,也深深地沖擊著學堂之地應有的師道。《牡丹亭》第七出中杜麗娘對后花園的向往和《紅樓夢》第九回中紈绔子弟們生發的癖性,均可見作者對于人的自我意識的反思。通過語言描寫,刻畫了他(她)們內心空靈的渴望,透露出仁義禮教對學子們的扼制。同時,面對禮崩樂壞的學堂氛圍,也可管窺作者對學堂功能蛻變的反思之義。
正如傅修延在《中國敘事學》中所提到的“大小契約的矛盾沖突”[8]151,《紅樓夢》中的賈寶玉長期處于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小契約讓他獲得某種心理平衡,但最終無法突破大契約的限制。《紅樓夢》鬧學堂事件中頑童們一開始更關注自身精神追求的釋放,當事情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人們紛紛開始抑制自己的感情,最終屈服于大契約之下。可見人們向往精神自由,但又無法擺脫契約對人們行為的制約。在大契約與小契約的背后蘊含著“正統與非正統、自由與不自由”[8]166-167的深層敘事。在《牡丹亭》中作者賦予了杜麗娘為情而生,為情而死的能力,看似獲得了自由,但卻只能在夢中。杜麗娘夢醒過后,要按照正統思想征求父母的建議,最終柳夢梅踏上了考取功名的道路,可見,正統思想在人們心中的位置。在《紅樓夢》中賈寶玉更是想要走向正統的對立面,卻又不得不背負起家族的使命,可見“正統的不可戰勝,自由難以舍棄,人生注定是一場艱難痛苦的折磨”[8]166-167。兩部作品中的“鬧學堂”事件深入細致地描寫了人物的內心,在“學堂”的大環境下,可見作者對中國正統儒家思想的反思意味。
兩部作品的不同之處在于《牡丹亭》“學堂”風波中體現了湯顯祖對于情的形式虛假與內心真實的反思,而在《紅樓夢》中體現了作者對中國傳統處世哲學的反思。在《牡丹亭》第七出中湯顯祖通過春香和先生陳最良的對話,面對春香對“情”的發問,“為甚好好的來求他”,先生無法作答,只得說出“多嘴哩”。[2]26可見在湯顯祖的觀念里“情是不可論理”的,正如達觀認為“理之攻情,何情不破;情之攻理,誰當其攻。”[12]785體現了他對儒家傳統禮教的反思,情不應該是在一定的標準之下,而是內心真實的感受。在后文中,通過以夢傳情的方式,表現了杜麗娘的至情,也透露出湯顯祖對于情的形式虛假與內心真實的反思,杜麗娘借助虛假的形式才實現了內心情感的釋放。
《荀子·法行》云“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13]492。可見“寶玉”二字,作者便注入了情感,象征著君子之德,做人有修養、有追求,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紅樓夢》第九回的原文中提到“有兩多情的小學生,滿學中送了他兩個外號,一號‘香憐’,一號‘玉愛’”[1]96。憐的情感是由“瓷的易碎性”生發出來的,它觸動的是我們國人心靈深處的“悲憫情懷”[8]132-133,而愛是“憐愛加上珍惜,不是罔顧對方感受一味占有”[8]132。可見作者在描寫這兩個人物時不僅傾入了“情”和“愛”,還有一種保護欲,文中說道“亦未考其名姓”[1]96,可見作者對其隱私的一種愛護。傳統的觀念中主張“發乎情,止乎禮”[14]329,而在鬧學堂事件中恰恰相反,情是發乎于心,止于混亂,在混亂的場面描寫中,透露出作者對中國傳統處世哲學的反思。《文心雕龍·定勢》中說道“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15]530。在每個人的心底都有一個方正的“自我”存在,為了迎合某種需求,人們會將心底的穩重和安定轉化為外在的“圓”。金榮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表面上金榮在鬧學堂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實則在收場的時候,同樣扮演著善始善終的角色。正如原文中所言“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16]10。《紅樓夢》第九回“學堂”風波中不僅體現了作者“方圓”的敘事手法,還“將眼花繚亂的人物事件通過一個暗中的向心力統一起來”[8]104。雖然這些貴族子弟的個性各有差別,但因學業聚在一起,在打鬧過程中盡管丑態百出,但最終以金榮的磕頭認錯終結,看似混亂的場面,卻始終有一個“向心力”被作者用傳統的“方圓”處事原則所聚攏。人身為特定社會背景下的人,固然會受到一定社會規則的限制。“身份的概念是理解中國古代敘事的一把鑰匙”[8]111,身份的不同直接關系著人們的行為,看似是金榮的無理取鬧,但從茗煙的話語中“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子,給我們璉二奶奶跪著借當頭。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奶!”[10]139可見寶玉身份的尊貴和金榮地位的卑下,由于這種地位的懸殊,卑下者的身上就投射出畏畏縮縮的形態,就好比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1]97,連批語里都說“學中亦自有此輩,可為痛哭”[17]344。一方面,在封建等級制度的庇護下,學子們畏手畏腳地成長;另一方面,大家族光環也給學子們帶來了利益。正如傅修延所提到的“畏與悅”[8]104的相通性,人們一邊適應著社會的種種制度,一邊又渴望達到內心的歡愉。
四、結語
對比探討《牡丹亭》第七出“閨塾”和《紅樓夢》第九回“鬧學堂”事件,可見伴隨著人們思想的流變,學堂的功能趨向退化、喪失,衍生出了這一番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學堂”事件。從學堂的敘事功能入手,通過對人物塑造、情感變化、學習內容、情節推進、細節描寫等方面的深入分析,可見作者敘事手法之精微。同為鬧學堂事件,作者對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現了在禮的制約下,主人公的叛逆精神和學堂精神的遺失。兩部著作中“學堂”風波事件均體現了作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閱讀這些經典文本,也在警醒人們如何繼承和發展好當代的學堂精神。正如“經師易求,人師難得”[18]575的仁師精神;古之求學者有“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19]361的學者精神。學堂是傳播知識和塑造人格的地方,不是任性而為、抒發情感之地,一方面,在課堂上提倡平等、民主的新型師生關系,鼓勵思想的碰撞;另一方面,學子們也應該繼承學堂精神,認真、博學、篤行、善思[20]32,學堂中的景象應是傳道授業,而不是大鬧學堂。通過陳最良和賈代儒兩位先生形象的塑造,也在告知身為師者,不應腐朽缺位,而應用開放包容的態度傳道解惑,不扼制學生的提問和質疑。
通過對兩部作品中鬧學堂事件的深入分析,可見作者在敘事手法方面有異曲同工之妙。就鬧學堂事件隱含的文化反思而言,《紅樓夢》第九回在《牡丹亭》第七出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正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9]450之語,學習探究兩部作品“學堂”風波事件時不能忘記和背離學堂的功能,也要注重在具體的文本閱讀中反思傳統文化,學會傾聽文本的聲音,為當代價值體系的建構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