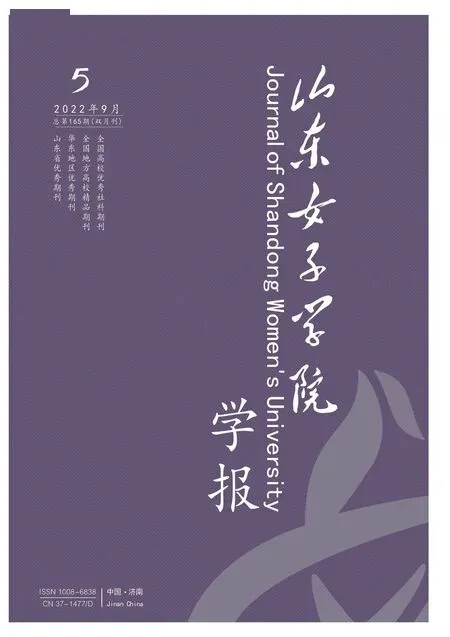悲情敘事、情感勞動與母職韌性:脊髓損傷兒童的“媽媽主播”個案研究
裴諭新,涂潤
(中山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0)
一、研究背景
2016年被稱為“網絡直播元年”,隨著“寬帶中國”戰略的深化和移動上網設備的推廣,性別、年齡、收入和城鄉差距所造成的數字鴻溝逐漸變淺,網絡直播在資本力量的推動下得到快速發展。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6年7月發布的第38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截至2016年6月,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到3.25億,占網民總數的45.8%[1]。根據第49次《報告》,截至2021年12月,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到7.03億,占網民總數的68.2%[2]。
中國直播行業的快速發展激發了中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從解釋網絡直播對于信息分享、人際互動、自我表達的意義,到對直播中的“PK”“打賞”“圈粉”行為的分析,以及對于直播平臺技術設置和商業邏輯的批判,既有研究呈現出網絡直播這一新技術對于現實生活的重構和對于學術研究的啟迪。然而,大多數研究的田野集中在網絡空間,較多篇幅用于討論“平臺”“算法”“工會”“文化生產”等,往往削弱了對于復雜生活圖景的考察與對于個體生命的社會關懷。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四位自2018年起開啟網絡直播的媽媽主播,其有一個共同的身份——脊髓損傷兒童的媽媽,她們直播的內容是陪伴孩子康復的日常。區別于其他的草根主播,“脊髓損傷兒童”和“媽媽主播”是她們最醒目的標簽,通常直接出現在她們發布的短視頻標題中。展示孩子身體的“殘缺”和她們的“困窘”,是其直播從不回避甚至有意凸顯的主題。她們直播最初的動機是消解漫長疲憊的康復日常,同時也冀望可以改變命運的可觀經濟回報。本研究追蹤了她們過去四年的直播和生活歷程,發現她們所得到的關注度和粉絲量歷經上升和頂峰期后,很快進入無可挽回的頹勢。直播的新鮮感褪去,直播本身嵌入了重復的日常,經濟回報遠遠達不到預期,她們甚至面臨網絡語言暴力、網友越界進入她們的線下私人空間、具有“戀童癖”“戀殘癖”傾向的獵奇目光,以及孩子們潛移默化渴求關注度和金錢的文化習得等不良影響。即便如此,直播所帶來的工具性和情感性資源,包括無劇本、碎片化、即時的聊天所滋生的“在場感”,溢出原有圈層的異質性社會關系,網絡濾鏡給孩子們自我表達的欣悅感以及自我效能感……這些都成為媽媽主播們在頹勢中仍能堅持網絡直播的緣由,反映了底層女性對于她們稀缺的文化及社會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彰顯了她們多樣的、復雜的、強大的母職韌性。
本文聚焦于媽媽主播們的生活歷程、直播策略和母職實踐,具體而微地呈現和解釋底層女性在時代洪流中的困境與應對策略,并從社會關懷的視角進行探討。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框架
(一)網絡直播的包容性和排斥性
網絡直播的包容性首先得益于其“去精英化”和“平民化”的特點[3],這種包容性令不同經濟地位、社會階層和地理空間的用戶跨越數字鴻溝,通過互動和表達建構新的自我和身份。網絡直播的即時互動性,打破了用戶之間地理與心理的交往壁壘。人們參與到直播當中,構建新型社交方式和基于興趣的“微型共同體”[4],在網絡直播中找到認同感。
網絡直播的包容性還表現在對于身體或精神健康問題人士的接納和呈現。Mark Johnson探討了慢性疾病患者在Twitch(國外流行的實時直播平臺)上直播的體驗。他們公開談論自己的身體和疾病,努力創建積極的支持性空間,追求更豐富的社交生活,獲得了很大的心理滿足與解放感,同時也得到了謀生的經濟收益[5]。鄭靜、裴諭新、高雅對于中國大都市殘疾女性網絡就業和創業的個案研究指出,網絡空間的彈性工作方式和匿名性令殘疾女性具有了通過網絡實現工作的可能。其中,網絡直播令她們不再通過隱匿自己“殘疾人”的身份以回避可能遭遇的身體歧視,而是強調“殘疾”,將其變成“自強激勵”的符號,以折中實現“互聯網公平”[6]。
網絡直播的排斥性首先表現為低俗文化對社會公序良俗的擾亂,包括暴力色情內容的輸出、同質性高及惡性競爭等特點[3]。網絡直播基于商業利益的驅使大量生產功利性內容[4],網絡主播本質是“文化工業批量生產的工業商品”[7],“炫富”等行為顯現的金錢主義亦會對大眾價值取向造成不良影響[8]。網絡直播的排斥性還表現為以健康人為標準設計的數字技術。相較于普通人,一些直播規范(norm)對身體或精神健康障礙人士是極具挑戰性的,他們必須更努力地工作才能獲得與普通用戶同等的地位或成功,這讓他們的數字體驗充滿挫敗的消極性,體現出“技術、社會和人類”之間的復雜關系。網絡直播雖然為身體或精神健康障礙人士提供了大量的數字化機會(digital opportunities),但其中的分化、等級和排斥依然明顯[5]。
(二)性別操演與情感勞動
直播產業是高度性別化的,網絡直播為女性提供表達、展示和創造價值的機會,體現出主體的多樣性和性別操演的不同模式[9];同時,“網絡直播放大了身體景觀的視覺效應”,凸顯的是以男性快感和欲望為中心的價值文化[4],直播空間是對女性身體產生規訓的場所,女性被男性觀看和凝視,成為父權文化的“表演道具”[10]。女主播通過私人的行為和情感以及塑造美麗年輕的身體形象換取經濟資本,直播間中充滿著以身體為對象的互動,對身體的審美可以看作是性欲望的表達,女性則是性欲表達的主要對象[11]。另一方面,在直播當中,男主播同女主播一樣需要注重身體和外貌形象,通過帶有性意涵的身體獲取資本,進行情感表達并持續輸出情感勞動[12]。
許多研究將焦點放在網絡直播中的“打賞”行為上。潘迪認為“聊天類直播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情感商品”,“打賞”行為實質上是資本制造的“情感消費”,由“打賞”獲得的情感體驗是一種“購買”,通過對主播呈現的“語言、姿態”等符號的消費以實踐自我認同[13]。另有研究將“打賞”稱之為“送禮”,當個體難以改變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時,則可通過“送禮”改變其在網絡虛擬空間中的位置,對現實生活形成反作用力。主播在直播時展現出“容貌、才能、情緒價值”等象征性的文化資本,觀眾通過購買虛擬禮物給主播“送禮”來進行象征性資本的消費,打賞金額被直播平臺和主播分成,最終又回歸經濟資本。由此,網絡直播當中的“禮物”互動,是結構、文化和資本的合謀。現實社會中個體社交圈較為閉合,其難以突破現實網絡結構,而直播間成為不同圈子中個體相互連通的“橋”[14]。虛擬禮物與打賞是主播完成“身體商品化”的過程,觀眾對虛擬禮物的消費則滿足了自身對主播身體的欲望和想象[15]。
情感勞動常被用來定義女主播的工作性質[16-18]。“情感勞動”一詞由美國社會學家Hochschild最先提出,她將這一概念用于解釋空姐值勤時必須服從的工作規范,如管理自己的情感,并將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等情感表達調整到符合公共層面的規范性期待以獲取工作報酬。在“物質”與“身體”之后,人的情感狀態變為可供出售的商品[19]。直播行業的情感勞動呈現出雙向互動的特征,網絡直播所體現出的現場感、即時性與粉絲黏性,在主播與觀眾之間建構了一種日常嵌入的親密感,這“在很大程度上擴展了人們在互聯網世界中的情感表達空間。因而,大量的觀眾進入直播間與網絡主播進行互動,尋求情感滿足與情感支持。相應地,網絡主播在直播互動過程之中,或多或少地付出自己的情感能量”[20-21]。同時,女主播作為勞動者,在資本或行業文化的引導下,通過身體的符號化和情感的商品化調動顧客,經營與粉絲的情感,以此引導粉絲“刷禮物”并轉換為經濟回報。這一“情感制造”的過程看起來是雙向的、互動的,掩蓋了資方價值觀的灌輸、身體規訓和制度設計。
王怡霖在探討女性主播與重要粉絲——“大哥”通過平臺形成的親密關系和關系勞動時,提出絕望勞動(desperational labour)的概念,意即在平臺設置的直播游戲中,處在底層的女性直播者不得不依靠大量的負面情感,如通過在游戲中自我羞辱和賣慘激發男性支持者的憐憫與同情,以獲得更多的虛擬禮物和在線陪伴。絕望勞動一定程度上展現了中國直播行業和平臺的殘酷,尤其是對于底層女性主播的壓迫[22]。
(三)母職
“母職”(motherhood)近年來是婦女研究的重要場域之一,意為女性對于母親角色的認同及照顧、養育等責任的履行。母職被學者細分為“母職經驗”(experience of mothering)與“母職體制”(institution of motherhood),前者指擔任母親一職所帶來的經驗和體驗,也就是母職實踐,后者是母親一職的社會角色期待帶來的經驗,是父權體制給母親一職所建構的角色期望[23]。女性主義對于母職的界定經由制度性母職向經驗性母職轉變,二者的最大差別在于界定主體的變化,也即母職究竟是父權制意識所建構的,還是女性自身在日常生活中所體驗或者自我認同形塑的[24]。早期的母職研究也經歷了從對母職迷思的批判到對母職賦權的肯定,俞彥娟指出,自1970年代女性主義者開始找尋母親角色的正面意義,她們肯定母職對社會和文化的貢獻,強調母親經驗對女性認同的重要性,甚至認為母性特質賦予女性權利[25]。
二孩生育政策實施以后,社會和學術界對母職的討論和分析掀起新一輪熱潮。國內關于“母職”的表達方式更加貼合本土的文化和社會情境,當前關于母職研究的熱點包括超級媽媽、喪偶式育兒、辣媽等。母職焦慮在不同群體中廣泛存在,其焦慮的具體表現方式不同。已婚已育女性的母職實踐受到市場、媒體等多種力量的影響,使女性面臨母職實踐和理想母職之間的沖突。阮琳雅在關于臺灣育有身心障礙子女的新移民女性母職經驗的研究中認為,新移民女性以母職韌力應對多重弱勢,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弱勢地位反而激發了她們的母職韌力來應對挑戰[26]。
韌性(resilience)也被稱為彈力、復原力、抗逆力,是一種從不幸或改變中快速調整的能力,是個體在遭受逆境、創傷或是巨大壓力時,處于不利環境中尤能與環境互動而發展出的保護機制,從而重獲自我控制能力以形成良好的生活適應[27]。韌性發揮作用的過程就是個體保護性因素與高危情景(如戰爭、災難、疾病、生活挫折等)相互作用的結果,韌性更強調個體遭受挫折后的新生與成長[28]。母職韌性通過母職實踐逐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制度和應對突發性社會問題的過程建構起來。在面對不斷變化的風險情境時,母職韌性不僅要求其具備風險的耐受性與抗壓性,而且需要經過不斷學習與提升,積極調動個人資源,獲得更多社會支持,提升個體的風險自治能力[29]。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個案研究方法深入考察四位媽媽主播的日常生活與直播策略。2018年,筆者在A醫院實習期間認識了四位媽媽:31歲的琪媽和小薇媽,32的小可媽以及33歲的杰媽。她們的孩子年齡相仿,受傷時都是7歲,進入A醫院進行康復治療時的年齡在7~8歲。我們見證了孩子康復、媽媽們開始直播這一重要歷程,并在以后3年多的時間里,保持著和媽媽們線上線下的聯系。
四位媽媽的個人經歷既有共性又存在較大的差異。她們分別來自廣東、湖南和甘肅不同的城市和鄉村,有的打過工,有的做過小生意,有的是公司職員,也有人很早結婚一直做全職媽媽。除了杰媽只生了杰杰一個孩子,其他的媽媽都有兩三個孩子。在孩子受傷后,媽媽們都放棄了工作,專心照顧孩子。
孩子們受傷的情況不同,共同點是脊髓損傷,損傷節段以下身體失去感覺,出現肌肉萎縮、步行障礙和大小便失禁等其他相伴生的癥狀。在3年多的康復治療期間,四個孩子已基本掌握了輪椅使用技巧,可自主完成穿衣、洗漱、床椅轉移等日常活動,但大小便、洗澡、上下樓梯等較高難度的行動仍需協助。本研究開始時,媽媽們已經接受“孩子離不開輪椅”這一事實,康復治療也從急性期進入穩定期和恢復期。也是在這一時期,媽媽們開始了直播。幾個月后,四個孩子相繼出院,進入長期的甚至是持續終生的功能恢復期。媽媽們的直播,也從那時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們收集資料的方法包括:
(一)文獻法
在征得媽媽們和醫院社會康復科負責人的知情同意之后,閱讀孩子們的病例和社會康復科個案面談記錄,以更好地了解孩子們的傷情、家庭背景資料等,全面理解媽媽與孩子們的處境。
(二)參與式觀察法
在孩子們出院之前的幾個月里,我們陪伴媽媽們帶孩子作醫療檢查、逛商場、外出就餐、散心等,當時的經歷記載于田野日記中。
(三)訪談法
訪談對象包括媽媽們和康復科社工,根據她們對于錄音的顧慮程度選擇錄音或者不錄音。錄音資料聽寫成文字,沒有錄音的作現場筆錄或者事后根據回憶整理成文字。
(四)網絡民族志
研究早期我們連續數小時觀看媽媽主播們的快手和抖音直播,觀察她們的直播行為、話語表達、與網友的互動方式等,并對直播的細節作相應記錄。此外,我們與普通網友一樣和她們互動、打賞。媽媽主播發布在快手和抖音上的短視頻我們也逐一瀏覽。短視頻是直播賬號運營的重要部分,通過短視頻可以看到研究對象的運營模式,管窺她們的心情和想法。研究中期和后期,我們每隔1~2個月會進入她們的直播間,同時用大量的時間瀏覽直播平臺上其他主播的直播和短視頻,以期對平臺的直播生態有整體的感知。
根據研究內容和理論工具,我們從海量的質性材料里歸納整理提煉出以下的研究發現和討論焦點,分別描述與探討母親陪護孩子治療康復和回歸日常生活的歷程,以及網絡直播實踐的影響。
四、研究發現
媽媽們開始直播最初的動因,有模仿效應,有暫時抽離康復日常的新奇感,也冀望從直播中獲取可觀的經濟回報。在以趣味、顏值、美食、萌寵、萌娃等為主導的直播娛樂生態中,“脊髓損傷兒童”和“媽媽”的標簽是對孩子及自我的直接而獨特的定義,也定下了悲情敘事的基調。她們的直播嘗試將“殘缺”的身體特征符號化為“稀缺”以獲取關注。短視頻的配樂采用旋律悠長而傷感的抒情歌曲或純音樂,如《明天會更好》《感恩的心》《我是一個媽媽》《親愛的小孩》等,再加上夸張的標題如“我才10歲就被醫生判了死刑”“截癱一年多,媽媽這樣對我!”直播的時候有的媽媽也會突然流淚,用悲傷的語調抽泣著訴說起家庭的變故,這被媽媽們稱之為“苦情戲”,可見“訴苦”的確是媽媽主播運營賬號的主要“戰術”。
然而,觀眾的同情心不會持續太久,缺少平臺的流量支持和無法獲得她們預期的經濟回報,日漸折損她們做短視頻和直播的原生動力和最初的激情。她們自己也成為被觀看的“景觀”,身體和性別身份有時會被一些觀眾以直接或者間接的語言策略把玩、侵犯,而有些“忠粉”很有可能帶有“戀童癖”“戀殘癖”傾向……媽媽主播日復一日的堅持,是否如王怡霖所描述的“絕望勞動”?她們如何應對自己的負面情緒或直播所帶來的情感剝削?直播對孩子們的影響是什么?這些又如何影響媽媽們的直播行為?這是以下我們重點探討的內容。
(一)網絡直播與悲情敘事
“受傷的前一天,我在這里玩。受傷的第七天,手術臺上漫長的8個小時,我挺過來了。干細胞移植手術的第二天出現排斥反應,當天住進了ICU重癥監護室。傷口感染,做了第二次縫合。一個媽媽、一個我、一副擔架,就這樣上北京……最開始只能綁著傾斜45度站床(1)站床是康復訓練中比較重要的一種訓練輔助手段。站立床是一種可由平臥位調到站立位的床,對于長期臥床的患者,站立床可以智能模擬正常人體的站立模式。,高了會頭暈,每星期加5度!直到筆直‘站立’。開始我連‘坐著’都辦不到,因為手沒有力氣,所以每天都要綁著4斤重的沙袋鍛煉臂力。受傷的第三個月,我學會了坐,雖然還會搖晃坐得不穩!受傷的第五個月,我開始學習四點撐……”(2018年7月21日小薇媽快手短視頻內容)
以上文字摘錄于小薇媽在快手發布的一個相集,文字說明以小薇的口吻寫就。這一記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他母親也陪伴脊髓損傷孩子歷經類似的手術和康復過程,他們的求醫之路無不充滿波折。兒童脊髓損傷的罕見性、醫療水平的局限和醫療資源的不均衡,導致幾個孩子都無法在居住地得到及時救治,他們從農村到城市,跨市跨省,每個孩子平均轉診5家醫院。
治療康復的費用令家庭陷入經濟危機。小薇兩年的治療康復花費了兩百多萬元人民幣,全由家庭自行承擔:“她就像個無底洞一樣,你就只能一直往里面打錢。一個月尿管加尿不濕就是2200~2300(元),她不吃不喝光拉屎拉尿就這樣子”。琪琪在重癥監護室“三天就花了五萬塊錢,醫生說這是非常燒錢的病。”小可一家因孩子的手術和治療欠下外債,“他爸一年的工資不夠她一個月的康復費用”。這種情況下,他們因經濟困窘中止治療或選擇轉回醫療條件較差但費用較低的醫院,也就不需要過多解釋了。
孩子從受傷急救到后期治療康復需要家長的全程陪護,杰媽、小薇媽和琪媽因此辭去工作。從醫院回歸家庭,孩子需要坐輪椅上學接受教育,學習之余的大部分時間用于居家鍛煉康復。母親們除了上下學接送,還需要在固定時間給孩子導尿,如小薇媽需在9∶30和12∶30這兩個時間點到學校給孩子導尿,15∶00小薇放學后也需導尿和洗澡;小可媽每隔兩節課帶小可去一次衛生間,約凌晨3點需再次協助孩子排尿……四位媽媽的很多時間用于往返學校,白天的時間被分割成碎片。此外,她們要承擔更多的照顧工作,包括協助孩子鍛煉、洗澡、灌腸等,不可能找到一份可兼職的有收入的工作,于是媽媽們開始了網絡直播。
開通網絡直播看似是四位母親的偶然之舉,卻和孩子的受傷有著必然的聯系,照顧任務和經濟壓力的擠壓之下,網絡直播具備的時間靈活性和經濟屬性使其成為脊髓損傷兒童的母親“掙錢”的最優選擇,也是她們持續直播的最重要因素。
網絡時代是注意力經濟的時代,注意力是一種稀缺資源,在內容極其豐富和多樣的快手和抖音中,能抓住觀眾的注意力就意味著成功了一半。“上熱門”言下之意即獲得觀眾的注意力,成為大眾的關注點。短視頻“上熱門”意味著賬號曝光率和點擊率的增長,連帶吸引更多的新粉絲進入直播間,增加獲得打賞的機會,更多的粉絲反過來又可以增加短視頻的播放量。源源不斷地吸引新粉絲的關注、觀看和打賞是維持直播可持續性的關鍵。
“上熱門”這一推薦機制的背后是平臺算法的運作,媽媽主播們對復雜的算法也不甚明了。伴隨直播時間的增加以及對直播平臺的深入了解,媽媽主播們對“上熱門”形成了自己的主觀經驗:直播平臺暗含著 “不推薦殘疾人上熱門”的游戲規則,媽媽們自行探求并發現了得到網友關注的途徑,那就是“封面和標題很重要”。媽媽主播們創作的標題常使用疑問句和夸張句達到強烈反差或渲染悲情的效果,以獲得網友自發的點贊或推薦。
短視頻的內容呈現了脊髓損傷孩子的生活狀態,從中可以看到:脊髓損傷兒童的治療過程;如何實現上廁所、從床到輪椅的轉移、出行等對健全者來說毫不費力的事情;與普通孩子一樣的校園時光等等內容。經由這些不到1分鐘的視頻碎片可以拼湊出脊髓損傷孩子及其母親們的生活日常,滿足網友對截癱患者如何行動的好奇,進而喚起同情之心。
每位媽媽在快手平臺上都發布了近200個作品,但悲情與艱難不是唯一的基調,作品當中不乏跟隨平臺潮流的模仿秀,也有孩子的才藝展示,小薇媽更是錄制了如小劇場般幽默的短視頻,看了令人忍俊不禁。短視頻中常能看到孩子們的笑容,在現實生活的接觸中,四個孩子同樣是活潑開朗的。我們跟隨媽媽們外出的時候發現,她們有相當一部分時間在撥弄手機,捕捉時機錄制短視頻,如孩子吃飯、上下階梯的時刻,碎片化的時間成為價值生產的空間。
媽媽主播直播間的觀眾高峰期曾超越200人,每場直播的打賞金額雖不固定,但維持在2000~5000快幣之間(即200~500元人民幣),節假日能獲得更多收益,如2019年的元旦杰媽直播間的打賞金額達到30000快幣(即3000元人民幣,通過平臺分成,媽媽能拿到1500元)。如同拋物線一般,高峰之后是跌落。最近一年,她們的快手直播觀看人數勉強維持著20~30人的規模,有時一場直播她們只能拿到幾塊錢。她們又陸續在抖音、火山、西瓜等平臺上發短視頻、直播,還開始做微商直播帶貨。其中只有琪媽將微商生意做得最為長久,因為她有獨特的貨源——家鄉潮汕的當地特產(如墨魚丸、魚膠、海鮮干貨)。她采用 “網絡直播+微信朋友圈”的方式展示和推銷產品,不用囤貨。其他三位媽媽的微商生意都失敗了,小薇媽在工廠找了一份工,白天上班,晚上直播。
(二)身體呈現與情感勞動
直播當中,很多網友直接表達“想看孩子的腿”,在網絡看客獵奇的眼光之下,孩子的“腿”與“完整的人”分離,“殘缺”成為符號化的工具,以滿足網友的“好奇”“憐憫”甚至是“慕殘”“戀童”心態。杰媽在使用快手過程中,發覺直播間有很多人有“戀童傾向”,因為這些人關注、點贊的對象多為小男孩。“如果只關注或點贊一兩個小男孩的視頻是正常的,但全部都是的話就很可疑”,杰媽說。同時她還講了一個經常打賞、送禮物的小哥的故事:
“他只要一閑就找杰杰聊天,杰杰又不跟他聊的,就這樣開著視頻,反正杰杰也不跟他聊啥……他們都不知道是怎樣一個心理,但總不能喊人家不要來呀。杰杰的輪椅是他買的,剛認識杰杰不久,他就送給杰杰了。”
小薇媽也說搞不清這些喜歡小男孩的男人的心理:
“就我自己會發現的嘛,他們就好像是一個團伙這樣。之前他不是帶了幾個人來我直播間嘛,就說這是他的弟弟,然后他也會去其他人的直播間嘛,反正就是這樣串客。他前一段時間不是帶了一個安吉(人名)來嘛,那個安吉也有一個弟弟的……太恐怖了這些人。”
琪媽也有相同境遇,一位50多歲的未婚男性常在琪媽的直播間“送禮物”,一次還專門從黑龍江飛到廣東揭陽琪琪的家里來看她,他的性格有種琪媽說不出的“怪怪的”:
“我不喜歡他跟琪琪接觸太多,還是得防著點,畢竟他也沒娶老婆……你說他來吧,肯定是我們大人接待他對吧,那他就會說,琪琪為什么不理我啊,哎呀你們大人對我好沒用啊,我主要是來看琪琪的,他會覺得我家琪琪不理他,他就會很難過,你說這是不是一種病。”
琪媽以“家鄉話不一樣,我家琪琪聽不懂你講話”回應該網友,雖認為該網友是“真心想幫助我們”,但她帶著戒備心不讓孩子和他過多接觸。我們查看此網友的快手賬號,發現他關注了眾多殘疾小女孩,琪琪、小薇、小可都在其中,他經常點贊轉發這三個孩子的短視頻作品。
對于這些可疑的網友,媽媽們沒使用“戀童”或者“慕殘”這樣的性心理學術語,她們的警惕是憑借對孩子的愛以及日常生活經驗。同時,她們又覺得,這些人不會對孩子們造成直接的威脅,而且又會在直播間打賞,所以自己會保護好孩子的安全,同時也要給網友留足面子。
媽媽們的身體和性別也成為被凝視的“景觀”。網友常見的寒暄就是對她們的外貌作出評價,以恭維的形式說出來,比如“年輕、漂亮”。媽媽們也用“相親”來形容直播的“看臉”邏輯:
“像我們這樣的群體,人家送禮物的還是比較少的,人家都是喜歡看那些美女呀、跳舞的呀、撒嬌的。還是個看臉的社會。”(小薇媽)
“真的是看臉的,人家看你漂亮就有再看下去的欲望。一看你好丑,人家走得比兔子還快。就像人家說找個人給你相親,第一眼看你好丑,你就不想去了解這個人好不好了。第一眼看好吧,最少不是很難看,就會說下一次了解一下,一樣的。”(小可媽)
“看臉”并不單單指對外在美的欣賞,更是對身體的幻想和欲望:
“任何一個主播,人家喜歡你,肯定是對你有目的……為什么人家會喜歡那些單身的小姐姐呀,就算是坐輪椅的,因為人家會覺得有可能可以怎么樣嘛。”(小薇媽)
雖然媽媽們內化了平臺的“看臉”邏輯,她們也都使用了平臺提供的美顏技術,屏幕當中的她們臉型瘦削、皮膚光滑白皙,但同時,她們非常強調自己的母親身份,避免被“欲望化”:
“你跟人家不一樣,因為我們是一個媽媽,我們不能說在孩子面前發嗲呀、撒嬌呀,那不是神經病嗎,對不對?而且你也不能說帶著小孩子去怎么樣,然后把不好的東西教給小孩。”(小薇媽)
“像我們這樣的肯定要說關于家庭(的情況),不可能在直播間嘻嘻哈哈。可能我們會覺得沒什么,但是人家會覺得你小孩都這樣了,你還這么開心。”(琪媽)
除了網友對于她們外貌和身體的凝視,媽媽們也會遭遇具有性騷擾意涵的語言,諸如“主播這么漂亮,你老公太沒福氣”“空虛寂寞冷”。還有人發私信說“我喜歡你呀,想撩一下你”,甚至有人發男性下體裸照等信息。對于后面這種明顯的冒犯,她們的應對方式是“拉黑”,并且不讓自己的孩子在沒有照看的情況下使用手機。對于不太明顯的言語騷擾,比如夸她們“好漂亮,你咋能這么漂亮”“看到你我就相信真愛了”“我可以養你嗎”,她們會嘗試用輕松、調侃的語氣來化解尷尬,盡量不搞僵局面。
有些網友會問一些具體的問題,比如“你老公呢”“他爸會給生活費嗎”“你有幾個孩子”“三個孩子都跟著你嗎”,媽媽們并不刻意隱瞞事實或撒謊,她們幾乎如實回答所有的提問。琪媽認為“問了就答唄,有些人問到最后可能會幫你”,杰媽對離婚的態度是 “離就離了唄,離了我還開心”。
媽媽們也曾遇到網絡“噴子”。在杰媽的某場直播當中,一位網友進入直播間就不停發送文字“傻子”,杰媽不予理會,但該網友并沒停止,于是杰媽把他禁言了。小薇媽被人指責說“小薇這樣子都是你害的”,起初她會委屈哭泣,后來她選擇無視,或者“揪著那個人不放,我就開始罵他了”。琪媽的直播曾被網友稱“好假”,質疑她假借孩子受傷來騙錢。一開始琪媽會生氣,“現在我就笑笑對他說,對,你說得對,如果你這句話是真的該多好”。
作為情感勞動的網絡直播,媽媽們在其中輸出的情緒價值不同于一般的主播。在這里,觀眾索求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情感滿足與情感支持,而更類似于一種“情感優越感”甚至是“情緒剝削”。為此,媽媽們幾乎不把直播看作一種工作,而將其視為“乞討”。正如琪媽所說:“其實我跟你說啊,能去工作的話,我是不愿意直播的。沒用的,像乞丐的感覺。”在媽媽主播們的概念里,網友的打賞如同行人對乞丐的施舍,網絡直播“悲情呈現—禮物打賞”的行動邏輯與乞討相似,雖能給媽媽們帶來經濟收入,卻沒有帶來認同感,這應該是媽媽們對于“情緒剝削”最直覺的體悟。
(三)關系勞動與母職韌性
媽媽主播們在關注度和經濟回報下降的頹勢中,仍能堅持網絡直播的緣由,除了較難就業之外,也和直播所帶來的工具性和情感性資源獲得有關。和前面所描述的“情感剝削”圖景完全不同的一個畫面是,媽媽們和網友大多數的聊天是一種情感療愈、陪伴和支持。杰媽因為直播當中“說多了”,所以她已經不再回避談杰杰受傷一事。小可媽離婚獨自一人帶著小可,曾經想過“我要帶著小可直接離開”。但她們在與網友不斷的講述、互動的過程中發展出了新的生命故事,逐漸脫敏、疏解并自我激勵。
她們也走出了原有的以血緣、地緣、業緣為基礎的圈層,建立起新的社會支持網絡。脊髓損傷是個長期乃至終生需要康復護理的疾病,原有關系網絡的支持額度用盡之后,網絡直播提供了一個跨越地理限制和社會階層的新的支持網絡。除了參與網絡直播,許多網友從全國各地趕來,到醫院、到他們的家鄉去看望孩子。杰杰10歲生日時,部分網友自發組織起來為他舉辦了一場生日會。琪琪的一部分醫療資金來自 “輕松籌”,捐款者也多是琪媽直播間的網友。
通過直播平臺,四位媽媽還看到了其他處于相同境遇的孩子和家長,他們彼此交流經驗,一步步探索適合自家孩子的康復鍛煉方式。身在甘肅的小可媽,學著直播平臺上其他孩子的康復方式訓練小可,小可的康復進展連康復師都感到驚奇。孩子們觀看彼此的直播或者短視頻,這種境遇相似所帶來的心理安撫感和集體認同感,是文字和圖片不能比擬的。
孩子們也因為直播而產生了積極的心理變化:
“確確實實就是說小孩子的性格會好很多,她會覺得說你看我有那么多粉絲,就是說還是有那么多人還是很喜歡我的。并不是說,我這樣子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她的心態會不一樣的……就像她去學校參加表演呀,她不會害怕呀。她說‘我直播的時候那么多人,現在這才多少人,沒事,我來!’心態會不一樣的,因為她會覺得沒有什么,因為她經常就好像我就站在別人面前啊。而且就像我給她發那些段子,大家都知道我要穿尿不濕,穿尿不濕我怎么啦,我坐輪椅我怎么啦,我就是這樣子呀。”(小薇媽)
“小可鍛煉辛苦的時候她就給我發脾氣,最厲害的一次直接發泄在我身上,直接打我。然后她看我的那個眼神,唉,就是那個眼睛不會動的,眼睛睜得很大,一句話都不說,怎么問她她都不說。她的手捏得特別得緊,就是去掰她也弄不了的那個狀態。真的好長一段時間她都是那個樣子。她生病好長一段時間都在指責我們嘛,覺得我們有問題,沒有照顧好她吧……她就是在那個(快手)上面有人逗她開心。如果是這個人待在她面前,她看著你會害羞。”(小可媽)
“像我們農村吧,其實直播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幫助吧,別說有沒有賺錢……很多農村人的話,你家里發生了這樣的事,很多人會看不起你的,會看著你怎么的那種。但是我家琪琪吧有直播,也有很多人知道直播,那他們對琪琪也就不一樣了,他們班的同學有看琪琪直播。”(琪媽)
四個孩子都因為網絡直播向積極的方向有所發展,發展程度因人而異。網絡直播滿足了孩子需要認可與肯定的心理,來自外部的關懷讓孩子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效能感。相對于現實生活,直播間從物理上隔絕了歧視和好奇的眼光,更為包容和關懷。不可忽視的是,孩子們積極的心理狀態與媽媽們的付出是分不開的。媽媽們作為“過濾層”,將網絡環境當中的負面信息和經歷屏蔽,不讓孩子看到。她們也不用殘缺的視角看待孩子,而是“把孩子當正常人看待”,培養孩子的獨立意識,鼓勵孩子學習知識、習得社會規范、與同輩游戲。
五、討論與總結
作為一項追蹤研究,本文發現媽媽主播們的直播策略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重點。直播初期主要靠關注度獲得觀眾打賞,主播的直播勞動更接近于情緒勞動,通過多重行動策略的合力來滿足網友的獵奇心理并獲取同情,將“賽博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具體策略包括:悲情敘述或夸張渲染吸引注意力,利用 “被觀看的權力”,呈現兒童殘缺的身體、“辛苦照料的年輕媽媽”的自我形象和“艱辛的”照料日常,并輔以“訴苦”或“勵志”話語激發網友的同情心或滿足窺探欲等,以得到流量、情緒關注、虛擬禮物和打賞。在直播后期,也即直播關注度拋物線下降的“去直播紅利期”,她們的直播更接近于董晨宇、葉蓁所提出的關系勞動,即與觀眾建立更為持久、多元的關系[20],用以編織社會網絡和“直播帶貨”,這也在認知、情感、界限、自我保護等諸多方面帶來更高的復雜性和持續性。
風險貫穿于媽媽主播們的直播生涯,包括:網絡語言暴力和具有性侵犯意涵的明示與暗示、網友侵入線下私人空間以及兒童被暴露于不安全的網絡空間和線下空間的可能。對于“乞丐”這一污名化詞語的反復提及,更展現出媽媽們所承擔的情感道德壓力與所付出的沉重的情緒代價。同時,媽媽們對網絡直播文化存在矛盾心理:一方面,她們內化了所謂的“看臉邏輯”,不自覺地對其迎合,也因此自我矮化;另一方面,她們自我定位為“媽媽”而努力去除“性感、制造曖昧”等潛在的網絡性別氣質規范,這可能是出于更具約束力的母職規訓,更有可能是實用性的自我形象定位,用王怡霖的“絕望勞動”來概括她們收益與風險并行的直播行為,是形象又恰切的。
盡管經濟回報不如預期,平臺也沒有因為她們的悲情敘事而給予相應的幫助,數字鴻溝難以跨越,風險只能通過個人與小集體智慧自行承擔,但媽媽主播們仍然苦苦堅持著,緣由在于其資源的匱乏。因緣際會,她們看似搭上了一趟時代快車,通過加倍付出和自我剝削品嘗到了一點時代紅利的滋味。雖然這難以幫助她們擺脫結構式的困境,但多多少少還是帶來一些工具性和情感性資源,包括無劇本、碎片化、即時的聊天所滋生的“在場感”,溢出鄉土圈層的異質性社會關系,網絡濾鏡帶給孩子們的自我表達的欣悅感以及自我效能感……這令她們日復一日的照料和直播生活多少具有了希望和慰藉。她們鍥而不舍、孜孜以求,不斷尋找新的網絡機會和陣地,持續性地進行稀缺的文化及社會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這彰顯了她們多樣的、復雜的、強大的母職韌性,展現出了她們的生活智慧和主體性。
從社會關懷的視角出發,呈現媽媽主播們的困境、掙扎和母職韌性是很有必要的。她們需要社會救助和持續性幫扶,更為包容的互聯網技術、文化以及社會環境,這也是社會介入需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