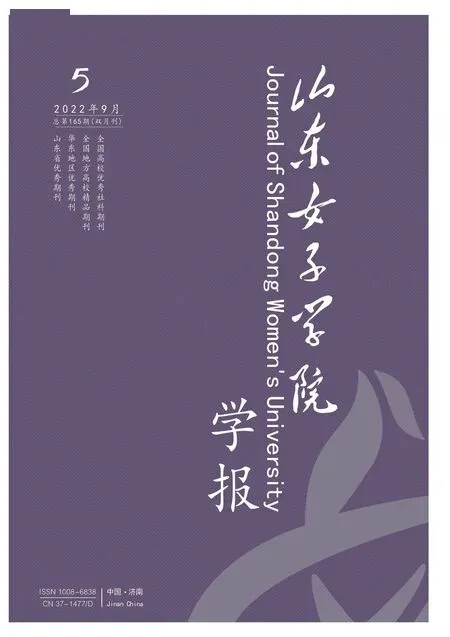“以女性之名”:女性高階領導職位晉升的進階追問與知識脈絡
王莉,王博雅,鄧硯方
(蘭州交通大學,甘肅 蘭州 730070)
一、女性晉升之“疑”:對女性晉升高階領導職位的思索與追問
“她力量”的不斷崛起,讓我們在越來越多的職業賽道上看到了女性的身影。然而,Bradley指出在企業各管理層級任職的人員中,女性管理者的能見度仍是銳減的,女性領導更多是在非業務領域從事各種服務性的協調工作,能夠晉升到“C字頭”(1)“C字頭”高管職務指的是首席信息官(CIO)、首席營銷官(CMO)、首席財務官(CFO)、首席法律顧問(CLC)、首席供應鏈管理官(CSO)、首席人力資源執行官(CHRO)、首席執行官(CEO)等。高管職務的鳳毛麟角。《2020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中國企業高層管理者的男女性別比例為100∶20.1,29%的內地上市公司董事會沒有女性參與,而在那些有女性董事的企業,其平均占比也僅為12.64%。即便是在女性人員構成占據半壁江山的金融機構,女性高管仍不占主流,我國36家A股上市銀行中,僅有4名女性擔任董事長或行長職務,女性高管比例僅占17%。事實上,不僅中國如此,舉世皆然。2019年瑞信研究院發布的CSGender3000報告顯示,全球女性首席執行官比例不到5%,女性首席財務官比例不足15%;全球大約只有36%的管理職位由女性出任,女性通常被排斥在經營核心決策層之外。為何女性晉升高管之路如此艱難?為什么企業普遍不愿聘用或晉升女性進入高階管理職位?相反,為什么又有少數企業選擇了“穆桂英掛帥”?這類有女性參與的高管團隊的企業究竟運行得如何?再進一步,是什么樣的女性晉升到了高階職位?她們是憑什么躍過龍門的?圍繞這一系列的問題,本文試圖以文獻回顧的方式,敘說職場中“以女性之名”存在的晉升桎梏、矛盾、裂縫與突破,并闡述女性晉升議題的主要知識脈絡。
二、女性晉升之“殤”:是什么在阻礙女性晉升?
審視今天職場女性的晉升之路,明朗中有疑慮,肯定中有偏見,女性晉升空間被壓縮到了有限區段,職場高層“倩影難覓”。為什么企業高階管理崗位不請“穆桂英”?整理學術界對此問題的應答,無論是理論脈絡抑或是實踐經驗都是視域寬泛、成果龐雜。系統梳理和分析后,本文重點陳述如下理論視角與研究路向。
(一)工作家庭沖突與工作努力差異
工作家庭沖突是解釋女性較少從事高階管理工作的主流觀點。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貝克爾1985年提出了“工作努力的性別差異”理論,該理論認為在工作強度方面是存在性別差異的,有家庭責任的女性與具有同樣技能與勞動力市場經驗的男性相比,她們在家庭之外工作上分配的努力和投入會更少,其結果是,“已婚女性在就業市場上尋求的是需要較小努力強度的工作,或者是與她們的家庭責任更一致的職業和工作”,而男性獲得了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就業機會。Barber和Bradley認為,高階管理工作由于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女性對家庭的自然回歸,以及其以家庭為先的立場決定了她們不可能在工作上付出太多時間,特別是生育和照顧新生兒帶來的職業中斷,使其錯失了晉升機會。此外,由于曾經做過全職工作的女性傾向于選擇兼職工作(Lovejoy & Stone,2012),而兼職工作本身,也就意味著更少的工作技能、更低的薪水以及更少的晉升機會(Durbin,2015)。工作努力性別差異理論明確提出了“女性因家庭需要降低生產力”的觀點,但經驗研究并未完全支持這一論調,甚至有研究犀利地指出,女性之所以在職場晉升中受阻,真正的罪魁禍首是“過度疲勞”的企業文化。在面對長時間工作的問題時,女性往往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諸多因素不斷提醒女性,她們并不真正屬于職場,女性更多地被鼓勵進行自我調整以適應兩難困境,因此,公司“完美地”轉移和遮掩了因過度工作文化導致的女性職場停滯不前的責任,將性別不平等鎖定在了適當的職位,也進一步阻礙了女性的職業發展[1]。
(二)玻璃天花板與性別歧視
女性晉升問題是性別歧視研究的重點領域,“玻璃天花板”(the glass ceiling)這一術語,即是該研究領域提出的用于指代女性在試圖晉升到企業或組織高層時所遭遇的看不見、摸不著的障礙。對于就業歧視的根源,存在著三種解釋路向:有意識的區別對待理論;統計性歧視理論;無意識認知過程導致的歧視結果。
有意識的區別對待理論認為,“人們根據他們對某一地位群體成員的消極情感或看法而對其實施區別對待”(阿爾卡特,1954;貝克爾,1957)。經濟學家拓展了歧視的概念范疇,認為雇主也可能是出于理性計算,有意識地歧視那些屬于生產力較低或雇用成本較高的種族、性別群體中的個人,并稱之為統計性歧視。以上兩種歧視理論均將歧視解釋為“有意識的故意行為”,其不僅長期占據主流觀點地位,且這種敵意性歧視的理論觀點成為了政府制定反歧視法律條款的重要理論基礎。第三種解釋路向拓展了前兩種歧視理論,強調無意識的認知過程在歧視中的作用,也意味著我們不能再繼續“把歧視鎖定在公平就業機會體系中的一些存在偏見的個人反常行為”(布萊克,1989)。相反,這種觀點強調社會結構中存在的微觀歧視行為是普遍的。人類無意識的“性別類型化”和“性別定型化”,歪曲了我們對女性群體成員的個人印象,從而引起了歧視。所謂“性別類型化”,是我們無意識地把他人類型化為“內群體”和“外群體”,類型化為“我們”和“他們”,并對內群體產生偏愛[2]307。 “男人是主體,是絕對,而女人是他者”[3]。Edwards指出由于男性長期主導高層角色,通過將機會賦予群體內的男性成員可以維持男性的認同和優勢,由此可見,內群體傾向有利于男性。“性別定型化”是一種推論邏輯,當我們缺少關于他人的完整信息時,我們就會求助于定型化,一個持有女性定型化觀念的雇主,在對女性晉升候選人的信息掌握有限時,有極大可能對其實行區別對待,在決策中下意識地將女性歪曲為負面印象,并影響其決策的公正性。內群體的成員資格、性別定型化不僅影響我們對男性和女性的認知判斷,還連帶影響了我們關于他人的績效預期[2]311。例如,我們習慣預期社會優勢群體(如男性)的成員會成功,而預期被人們貶低的群體成員(如女性)會失敗,并將男性的成功歸因于男性的才能,把一個女性的成功歸因于環境因素。高華聲基于中國數據的研究結果,佐證了性別歧視對高管職位的性別“指揮棒”效應,高性別歧視的省區市,女性高管平均占比明顯低于低性別歧視省區市平均水平。
(三)刻板印象和心理固著偏見
在傳統的性別認知中,女性被定義和分配了“溫柔順從”“軟弱依賴”等特征,伴生的社會分工論調是“男性主外做大事,女性主內經營家庭”,女性在職場表現出的積極進取、作風強硬通常被認為是背離社會“可接受行為”的,領導職務更是被天然賦予了男性,成為男性專屬,無論男人如何爾虞我詐、血腥殺伐都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而女性一旦“染指”其間,便會有不絕于耳的譴責之聲,甚至流行文化將成功女性刻畫成了疲于工作且沒有個人生活的形象[4]。 社會文化中對女性的這種心理固著(psychological fixation)偏見和刻板印象,不僅使得社會傾向于抑制具有雄心和領導力的女性,阻礙她們進入高級管理職位(Durbin,2015),而且進一步消減和阻滯了社會對女性領導力的培養。
矛盾性別偏見理論(ambivalent sexism theory)指出,性別偏見不僅包含對反傳統角色規范的厭惡和貶損,也包含對符合傳統的女性的肯定和褒揚,這種矛盾態度的一體兩面將性別偏見區分為敵意性別偏見和善意性別偏見兩大類別[5],敵意性別偏見正如上文所述,它表達直接且具有攻擊性和排斥性;而善意性別偏見則是一類主觀情感上愛護女性,但是卻將她們限制在傳統性別角色定位上的偏見類型,它隱蔽、間接,但具有蠱惑性,猶如“天鵝絨手套里的鐵拳”“蜜糖里包裹的砒霜”,使得女性會無意識地接受或依賴男性的特殊關照和保護,同時讓渡出了自身的權利,甚至還會無意識地進行著自我規訓,這讓女性在職場上的進取心表現得更為收斂,進而失去了職業成長和發展的機會。Debra Myhill指出,事業發展所依賴的通常是敢于冒險和自我表現,然而社會并不鼓勵和倡導女性表現出這種特質[6],女性之所以缺乏進取心和領導能力,完全是社會文化催生和強化的結果。
(四)勝任力與職業性別隔離
勝任力(competency)是麥克利蘭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概念。Spencer將勝任力定義為個體所具備的某種或某些潛在特質,這些特質與特定工作相關,并能區分出優秀績效執行者和一般績效執行者。高階梯隊理論認為,公司取得的優異績效是由高管組成的核心管理團隊勝任特征作用的結果[7]。Müller 和 Turner 認為,高管所具有的勝任特征直接決定了其管理與決策是否科學有效[8]。一直以來,高管職位的勝任特征符碼都與男性氣質捆綁在一起,Mann提出優秀領導者男性特征表現突出。對比男性和女性的氣質差異,Bradley、Browne等人認為,男性比女性更適合從事高級管理職位。此外,有關女性特質的研究也進一步推論了女性不適宜或難以勝任高階管理職務。女性在進行高收益等相關風險決策時所表現出的抗壓能力、風險偏好、決策風格、個人能力等都是不甚理想的。相對于男性而言,女性規避競爭(Niederle & Vestelund,2007),具有風險厭惡的特質(Eckel et al.,2015),因此決策表現更為保守(Barber & Vesterlund,2007;Flory et al.,2015),更多關注投資活動的不確定性和潛在損失,這對企業創新行為(李后建,2016;謝霏,2017)和價值創造(Wegge,2008)都是極為不利的,因此,從高階管理職位的勝任特征要求來看,對女性工作者技能和氣質的定型觀念,阻礙了女性的職業發展(Durbin,2006)。事實上,從全球范圍和歷史實踐來看,高階管理職位一直都是由男性主導的,女性參與其中也僅僅是以 “職業性別少數”的尷尬身份,屬于典型的職業性別隔離職業。所謂 “職業性別隔離”是指職業性別結構的不均衡狀態——勞動者因其性別的分類而集中于不同的職業或同種職業中具有不同等級制的崗位[9]。不同于就業歧視,職業性別隔離是基于職位或角色勝任特征的,對于高級管理職位來說,他們需要“堅強、控制力、競爭力、積極進取”等“男性氣質”,而在傳統的性別二元結構中,男性身份先賦性地獨享著“男性氣質的霸權”,因此,女性也就因為缺少這種氣質特征而被“合法地”、自然而然地阻隔在了高階職位門外,如果女性想要走進高級管理層,則需要像男性一樣行動。
(五)權威合法性與反彈效應
“權威合法性”理論另辟蹊徑,為解釋高階職位性別割據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Tannen認為,“對女性來說,通往權威的道路是艱難的,一旦她們到達那里,就會陷入荊棘叢生的境地”。身居要職的女性,仍然會受到權威合法性的質疑——女性權力擁有者被認為不如男性權力擁有者合法。所謂“合法”,是指領導者凌駕于他人之上的權力被視為是正當的或理所當然的(Caddick,1982;Tyler,2006),一個合法的領導者不需要通過強調權力來讓下屬服從或合作,當一個領導被認為是合法的,下屬會欣然接受并服從他或她的決定。因此,權威的合法性不是強制的,而是出于下屬的選擇(Levi et al.,2009;Tyler,2002)。女性權威相比男性更不被接受(Brescoll,2011;Eagly et al.,1992;Heilman & Okimoto,2007;Parks-Stamm et al.,2008)。美國的一項全國民意調查顯示,員工更喜歡男上司而不是女上司(Rifkin,2014;Rubner,1991)。Vial等提出,對女性領導的抵觸完全歸因于下屬對其權威的低合法性認知,除非女性領導能使自己的角色合法化,否則將引發一系列的負面結果和反彈效應。“反彈”(backlash)是Rudman提出的一個抽象概念,專門用于表征那些因從事與性別刻板印象不一致的行為或角色的男性和女性所遭受的社會經濟懲罰,反彈效應具有連鎖反應特征。在由女性領導的團隊中,低合法性認知會增加下屬的消極行為(例如,主動挑戰和破壞領導權威),同時減少合作等積極行動;與此同時,下屬的拒絕和缺乏合作容易導致女性領導者陷入不穩定的心理狀態,并引發她們對下屬的負面反應。研究表明,女性對自己不被接受非常敏感,她們會因此降低對自身影響力的期望[10]。于是,一種自我強化的非理性循環就這樣產生了——一方面下級認為女性領導不能達到期望,另一方面,女性領導認為她們不被尊重,這兩種情況都會產生消極的領導/下屬互動,對女性領導的負面認知被進一步證實和強化,權威也被進一步削弱和抵觸。在這種“玻璃懸崖”下,一些女性會選擇退出高級角色(Dubin,2015)。
三、女性晉升之“光”:高階領導職位為什么雇傭女性?
在傳統偏見、刻板印象、性別歧視以及現實壓力的夾逼下,女性的職場空間被阻隔在玻璃天花板之下,在這個以男性為標準的社會,女性努力證明著自己。不過,局面正在悄然轉變,女性在企業中的受關注度正慢慢提高,女性頭頂“C字”皇冠已不再是新鮮事。為什么女性能沖破玻璃天花板?企業高階管理職位雇傭女性源于何故?
(一)裝點門面與責任使然
象征主義理論提出者Kanter的經典研究認為,工作組織內某個亞群體的從業者數量不超過15%時,意味著該群體就是一種象征(Tokens),屬于典型的象征性雇傭。支持該理論的學者認為,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現代社會,企業雇傭少數派女性不是因為信賴女性對企業的經濟和社會價值貢獻,而是為了象征性地“裝點門面”[11]。在這樣的工作場域,女性遭遇“玻璃天花板”效應是顯而易見的,高管女性不僅占比少,且職位權力非核心化特征明顯(祁凡驊,2018),高管女性更多是在非業務領域從事服務性、綜合性的協作工作,核心業務領域中的高管女性形單影只(陳春花,2021)。Bradley指出,在管理行業中,女性經常從事人力資源管理工作,而諸如項目經理等高薪工作通常是男性;GSGender3000報告顯示,女性統領著1/3共享服務職能部門。此外,有證據顯示,位及公司最高層的女性,經常遭遇差別性工資待遇,她們沒有獲得與同等職位男性一樣的薪酬給付。
“象征性雇傭”觀點曝光和放大了企業在女性高管雇傭態度上的消極面,但卻不足以涵蓋和解釋全貌。誠然,消極動機不可漠視,但我們還應該看到企業雇用動機中的積極一面。正如Lydenberg等在確定企業社會責任標準時,強調女性高管職位參與,英特爾等企業也將提高高管女性人數作為企業踐行和推進社會責任的重要目標選擇。詹姆斯·格魯尼格也認為,支持女性并促進其職業發展是卓越組織的特征表現。由此來看,無論是要裝點門面還是責任使然,企業提高女性高管團隊參與率的努力是不爭的事實。
(二)女性主義與強制性別配額
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世界范圍內掀起了女性主義的第二次浪潮。一般認為,第二次婦女解放運動的基調是強調兩性間分工的自然性,致力于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現象,要求摒棄把兩性差別看成是女性附屬于男性的基礎觀點[12]。強制董事會女性高管配額是頗具女權主義色彩、實現男女平權的重大成就。挪威是世界上第一個實行公司董事會強制性別配額的國家。2004年,該國通過立法要求上市公司必須保持40%以上的董事會席位為女性。之后,西班牙、法國、冰島以及美國加州都先后制定了法案強制規定上市公司董事會中的女性配額。2020年,德國政府批準了首個“性別平等國家戰略”,最新進展是其日前通過法律草案,對企業管理層中的女性比例提出強制要求:從2022年起,一定規模的德國上市企業,如董事會成員超過3人,必須有至少1名女性董事;在聯邦政府參股的企業中,董事會成員如超過2名,就必須有一名女性董事。要求擁有三名以上高管的上市公司必須任命至少一名女性進入公司高層。Ahern和Dittmar通過觀察挪威強制性別比例法案頒布當天的股市波動發現,受不得不提高女性董事會比例影響的公司股價普遍大跌,其后,一些公司選擇退市規避立法,而繼續保持上市的公司則大多經歷了績效的下降。作者進一步分析認為,這種下降是公司替換相對年輕、缺少經驗的女性董事造成的。盡管基于挪威的數據結果對強制法案的推行略顯不利,但立法者堅信,這是改革的必然成本,只有推進該法案的實施,公司才有可能在未來重視和加大投入培養富有經驗的女性管理者。事實上,諸多市場經驗數據都顯示,增加女性高管比例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其實是積極的,光輝國際研究院2016年的一組數據顯示:女性董事比例10%以上的公司3年期平均資產回報率為6.4%,平均股本回報率為14.3%,相比之下,女性董事比例低于10%的公司同一時期內的平均資產回報率只有5.2%,平均股本回報率為11.8%。董事會性別多樣化的企業,財務表現更具優勢。
(三)女性特有的優勢與對組織的獨特影響
對于女性領導力的優劣勢存在著持續性的爭論。以Eagly為代表的學者普遍反對質疑女性勝任高階職位領導能力和領導特質的陳腐之見。“誰說女子不如男”,光輝合益2016年對全球90個國家5.5萬名管理者情商素質的研究發現,女性在12項關鍵情商素質中有11項都勝于男性;亞洲數據中,女性有8項能力超過男性,分別是團隊協作、組織意識、自我認知、同理心、培養他人、沖突管理、適應性和成就導向。類似地,大量經驗研究證實,女性高管所具有的敏感謹慎、經營穩健、重視員工、接納變化、心理韌性強和不過度自信等特征[13],是企業應對VUCA時代商業環境的關鍵技能(Wiersema & Bantel,1993;Moskal,1997),女性高管獨特的認知和領導風格不僅有助于促進高管團隊變革接受能力的根本轉變(Colin,2014)以及抑制企業過度投資行為(李世剛,2013;Adhikari,2018),而且有助于企業提高并購績效(李衛民,黃旭,2014),促進社會責任履行(朱文莉,鄧蕾,2017),甚至成為決定危機企業反轉的重要因素[13]。不斷積累的微觀實踐和實證結論,佐證了多元化商業管理情境中女性領導力的優勢,這也使得企業不得不重新審視女性在董事會的貢獻和價值,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過后,許多企業開啟了“搜索女董事”運動,女性董事隨之成為了全球企業的一個重要議題,越來越多的人在大聲疾呼女性“向前一步”(Sandberg,2015),倡導女性發揮性別優勢,由“隱匿”走向“偉大”。
高管團隊中“她力量”的介入確實帶給了企業積極的成果,但對于推動這些良性變化的機制,目前的研究尚不明了。一種觀點認為,任務的性別標簽以及工作群體的性別構成有可能解釋上述現象,對于那些被定型化為男性工作的群體任務,若工作團隊有女性介入,那么男性成員出于“供給者”角色的認知,會增強他們社會性彌補的努力傾向。即男性在混合性別工作群體中,會比在單一男性群體中付出更大的努力,以彌補女性能力的不足(Ridgeway et al.,1997;Kerr et al.,1985)。另一可能的解釋范式是自我圖示—角色定型觀點,地托卡發現,即使女性和男性在相同的競爭性環境下行事時,女性也傾向于把自己的競爭行為合法化為一種利他動機驅使的行為,并以和諧的群體關系為取向。女性這種視自我為合作和群體化的“自我圖示”傾向,也讓男性定型化地相信女性成員是合作的,并相應調整了自己的職場策略和行為選擇。
四、女性晉升之“謎”:哪些女性會晉升高位?
言說至此,一個更有意思的話題似乎被我們忽略了,那些高階女性主管是如何登上高管寶座的,她們是利用高學歷武裝了自己?是借力跳槽獲得職位經歷或行業閱歷?還是靠長期供職的彼得效應?什么樣的女性獲得了高階職位晉升?她們是如何躍過龍門的,或者說女性沖破天花板的策略是什么?事實上,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想要成為企業的高階主管,并沒有太多捷徑,但是女性在此過程中的獲選標準顯然要比男性更為嚴苛。可能正是因為女性在組織中晉升實踐和經驗數據的不足,有關女性晉升機制或晉升路徑的研究討論都是零散、斷裂且貧乏的,性別要素并未被納入研究主題的分析框架,因此,我們僅能穿插敘說一些零散的、以女性為對象的研究結論。
(一)錦標賽理論與“業績觀”
錦標賽理論(tournament theory)由Lazear和Rosen于1981年提出。該理論指出,由于存在高昂的信息和監督成本,公司對高層經理人實行了一種拉開薪酬差距、通過考察業績排名而非實績的辦法來選擇晉升人員[14]。周黎安等應用錦標賽體制較早研究了中國政治體制和經濟結構下地方政府行政領導政治晉升與經濟績效之間的互動機制,提出了作為強激勵和治理手段的中國地方官員“晉升錦標賽”模式[15]。 晉升錦標賽不僅在官員晉升領域具有解釋效力,國企高管晉升中同樣存在晉升錦標賽現象,滕越洋等稱其為“準政治錦標賽”。由于國企高管具有“準官員性質”,因此,國企高管追求企業績效同地方政府官員追求經濟績效無實質差異[16],企業業績會顯著改善國企高管的晉升前景[15]。作為硬性指標,民營企業更是遵循以業績為指導的高管晉升機制。可以說,業績論是解釋高階職位晉升的主流視角,經濟績效或企業業績可以直接體現地方政府領導或高管的能力,2011年麥肯錫的一項報告指出,男性的晉升基于其自身的潛力,而女性的晉升則是基于其已獲得的業績與工作成就[17]。
(二)人力資本稟賦與“能力論”
內部勞動力市場的升遷機會是勞動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陣地,經濟學家視升遷為隱性合約的重要面向,表示生產力與職位標準的合適相配。威廉姆森等相信,“生產力的不同是可以在長時段中被辨認出來的,在內部勞動力市場的職等分配上,使其更加名實相符”。傳統人力資本模型認為,人的能力與生產力緊密相關,能力是人體之中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能和體力,能力的概念被默認為是一種與生產能力緊密相關的認知能力[18],并采用教育作為代理變量進行測量。然而,隨著人力資本研究的推進,經濟學家發現教育不一定帶來更高的生產力,一些與生產技能無關的自律、責任心、風險偏好等非認知特征對職業發展、工資收入等勞動力市場行為具有預測效力[19]。于是,新人力資本研究框架擴展了人力資本的內涵,將非認知能力納入個人成就的經濟分析中,強調能力的復雜結構,肯定了非認知能力對于個體發展的重要影響。人力資本稟賦視角從教育背景(學歷)、學校級別、任職經歷、在職培訓(EMBA、MBA)等維度向我們解釋了職位晉升的能力邏輯,研究成果豐碩。佟新、劉愛玉關注了中國女性政治精英晉升的影響因素,其中,作為人力資本的第一學歷和最高學歷是否是重點大學對女性行政干部向更高行政級別的晉升具有顯著助推優勢(佟新,劉愛玉,2014)。Sandra等的研究結果表明了非認知能力個性特質的晉升意義,他們認為,無論工作性別定型觀念或評價者性別如何,具有男性特征的女雇員被認為最有晉升機會。
(三)社會網絡理論與“關系論”
社會網絡理論是當代社會學主流分析范式之一。社會網絡理論分析范式關于職位流動的經典研究主要有三個理論視角:(1)格蘭諾維特的強關系—弱關系理論。格蘭諾維特強調,勞動力市場行為并非“社會性孤立”的經濟行為,而是鑲嵌在社會互動網絡中,并受人口學因素限制的。一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取決于認識他/她的人的數目,因此,愈是資深員工,將會有愈長的時間去發展其政治影響及在“合縱連橫”里的中樞地位[20]。(2)林南的社會資源理論。這一理論關于職位獲取的基本觀點是:社會資本是從社會網絡中動員的社會資源,一個人職業獲得的關鍵變量是其擁有的社會資本的數量和質量[21]。(3)博特的結構洞理論。博特關心人們在社會網絡中的地位,強調結構洞具有的競爭優勢,當一個人在網絡結構中越自主,就越具有和別人討價還價的優勢,并能獲得更多的信息,從而在晉升中處于優勢地位。Podolny和Baron在對結構洞理論繼承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論框架。他們區分了四種不同的網絡類型:工作建議型、圈內關系型、策略信息型、社會支持型。其中,策略信息型是博特強調的網絡類型,按照博特的觀點,策略信息型網絡的規模與晉升呈正相關,即網絡越多,信息越多,越有利于晉升;網絡的密度與晉升呈負相關,當你周圍的人際關系網絡非常緊密時,很難進行討價還價,對晉升不利。圈內關系型是指那些對一個人升遷最有幫助、影響最大、對將來發展最有影響的關系。在這種網絡里,人們之間的網絡越密,對一個人的晉升越有幫助[22]。綜上,社會網絡分析強調關系網絡對組織內職位晉升的影響作用,大量實證研究證據均證實了該理論在勞動力市場的解釋效力,在女性職業流動領域影響依然顯著。新加坡國立大學Sumit和錢文瀾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在高端人力市場上,社會資本和人際網絡有利于職業成果形成,商界的女性高管參與男性主導的社交活動,諸如打高爾夫球,不僅可以擴大社交圈,積累社會資本,更有助于女性一定程度上沖破企業董事會性別天花板[23]。佟新、劉愛玉的研究發現,中國女性政治精英晉升依賴于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隨著晉升層級的提高,家庭的作用更為明顯,女性晉升具有精英再生產的意義(佟新,劉愛玉,2014)。
(四)內部勞動力市場理論與“忠誠觀”
內部勞動力市場(internal labor markets)是指企業內部建立的將員工納入晉升、技能教育、職業發展和福利保障的階梯制度設置[24]。 該理論認為,專用性人力資本和在職培訓強化了員工與企業之間的工具性依賴,促使企業與員工建立起長期穩定的雇傭關系,并最終演化成企業內部一套隱性或顯性的職位管理規則[25]。企業一般會在內部建立起一套正式化的職位晉升階梯,員工的晉升機遇存在路徑依賴,當階梯上某一級別出現職位空缺時,便由次一級員工晉升填補,越是位于階梯高端的職位,越少對外部市場開放,即使外部候選人明顯優于內部候選人仍是如此。依據內部勞動力市場的晉升規則,很多人相信,在科層組織中,只要一直堅持下去,媳婦就能熬成婆,水滴就能石穿,“忠誠”會成為一個人在公司晉升的特別通行證。彼得原理從側面說明了組織忠誠對員工獲得內部晉升機會的效力。作為“二十世紀西方文化三大發現之一”,彼得原理指出,層級組織中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和職位空缺,員工總是趨向于被晉升到其不稱職的職位,因此,彼得原理也被稱為“向上爬”理論,隱喻員工不斷被晉升的結果和趨勢。Sarah Dillard和Vanessa Lipschitz通過考察世界500強公司中的24位女性領導者的職業道路發現,超過20%的女性CEO畢業后工作的公司就是她們現在掌管的公司,長期不間斷供職于同一家公司是女性獲取晉升的普遍道路(Sarah Oillard,Vanessa Lipschitz,2014)。
五、結論與討論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各學科中的女性研究以不同速度、方式和力量,改變了本學科的知識圖譜,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心理學家像賴特·米爾斯所建議的那樣,承擔起了學科想象力重任,在各自領域把處于不顯眼地位的女性當作研究主體和知識創造者。回溯和梳理女性晉升的研究脈絡和理論淵源,可以歸納出如下思維范式和視野焦點的變遷:
第一,從過去聚焦“玻璃天花板效應”轉向關注高管團隊中的“她力量”。傳統女性晉升研究熱衷于探討“女性晉升困境”的話題,高度關注“性別歧視”“性別偏見”“職業性別分隔”等主要范疇,隨著微觀場景中女性參與高階管理職位事實和數據的不斷增多,組織與管理學科關于高管團隊異質性的討論成為一股熱流,女性領導的角色、影響力一度成為學者研究的重要議題。盡管今天學術界關于女性晉升高管職位機制和路徑的黑箱尚未完全開啟,但女性沖破玻璃天花板已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不斷豐富的經驗數據將為這一研究主題創造更多的話語空間。
第二,從過去強調兩性差異的識別轉向重視兩性差異的彌合。傳統職業晉升研究側重于尋找和探求男女氣質和能力差異,認為男女與生俱來的特征奠定了兩性職業分工和社會適應,這種將男性和女性預設為對立位置的觀點,主要是受到心理學范例的強烈影響。現今,對兩性差異的思維范式已由“差異識別”轉向了“差異彌合”。一方面,微觀企業實踐中女性領導展現出的男性化氣質,顛覆了性別氣質兩極化的傳統觀念,從性別氣質的二元對立走向了性別氣質的多元化彌合。另一方面,董事會性別構成多樣化的實證研究,刷新了我們對女性權力合法性的舊認知,女性參與高層決策的優勢強有力地論證了兩性差異在工作場景中的互相賦能與社會性彌補。
第三,從過去主張“女性生產力低下”轉向正視“她型領導力”。傳統女性職業流動研究傾向性地認為男女在勞動力市場上存在生產力的性別差異,從工作家庭沖突的解釋路徑,推演出女性從事兼職工作和低級工作的必然性。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她力量”不斷崛起,女性領導力備受關注,特別是VUCA時代的到來,女性獨特的氣質和認知領導風格完美迎合了多元化商業情境對異質性領導力的需求,高管職位“去標簽化”“去性別化”成為學術界的熱詞,企業開始愈加關注女性領導力的釋放與培養。
“以女性之名”,“她力量”正努力“向前一步”,漸漸從渺小走向偉大,從隱匿走向出眾,從質疑走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