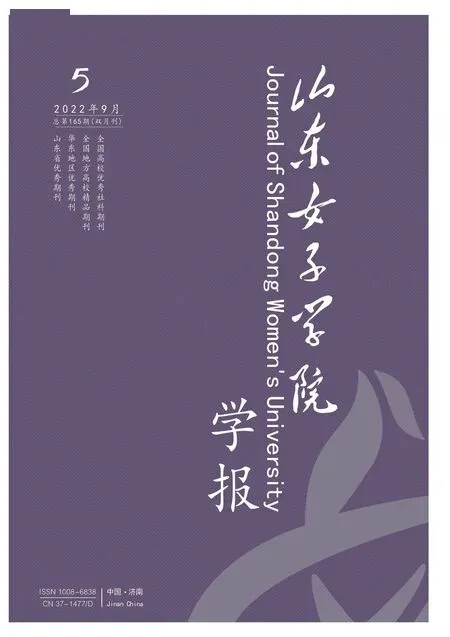在性別與階級之間:論何殷震的婦女解放思想
章舜粵
(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 100009)
婦女解放問題是近代中國的核心問題之一,婦女運動是近代中國諸多社會運動中的重要一環(huán)。一般認為,強調婦女解放與階級斗爭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特點。如有論者即指出:“十月革命后,隨著他們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化,他們的婦女解放思想也隨之變化、發(fā)展。他們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代替資產階級人權平等學說作為分析中國婦女問題的理論武器,幫助中國的知識婦女認識到只有投身社會革命,和勞動婦女相結合,才會獲得婦女運動的發(fā)展。”[1]67但事實上,將階級斗爭理論和婦女解放理論融合起來的最初嘗試,可以追溯到晚清時期的無政府主義女權主義者何殷震。她在強調婦女解放運動中的階級斗爭屬性時又強調階級斗爭中的婦女身份,亦即同時由“性別中的階級”和“階級中的性別”出發(fā),試圖走出一條以階級革命瓦解資本主義父權制的女界革命之路,從而在當時流行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等女權主義論述中顯得獨樹一幟。近年來,她獨特的理論貢獻已逐漸為學界所重視(1)例如劉禾、瑞貝卡·卡爾、高彥頤等人指出,何殷震以“男女有別”分析“資本主義國家形態(tài)、私有制、雇傭勞動和改頭換面的性別奴役”,對于當今跨國女權主義的理論建設工作具有方法論意義。宋少鵬指出,何殷震的理論具有無政府主義和女權主義的雙重特性,“使其‘女界革命’的思想具有了原創(chuàng)性,在晚清主流女權論述中獨具一格”,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今天仍有理論價值。而劉人鵬認為,何殷震的思想與中國臺灣20世紀90年代后性/別運動隱然有所呼應。見劉禾、瑞貝卡·卡爾、高彥頤:《一個現(xiàn)代思想的先聲:論何殷震對跨國女權主義理論的貢獻》,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5期;宋少鵬:《“西洋鏡”里的中國與婦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劉人鵬:《〈天義〉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視野與何震的“女子解放”》,載《婦女研究論叢》2017年第2期。。本文擬梳理何殷震以階級理論尋求瓦解資本主義父權制根基之路的思想,并予以相應之分析與評價。
一、將“男女革命”納入階級斗爭理論的視野
何殷震,江蘇儀征人,又稱何震,因為反對“用父姓而遺母姓”的男女不平等傳統(tǒng),她同時采用父母姓氏,自稱何殷震,在其主編刊物上往往以較小字號,并列何、殷二字[2]819。1907年2月13日,何殷震及其夫劉師培,聽從馬君武建議,應章太炎之邀請赴日本東京參加同盟會《民報》的工作。他們在日本與亞洲各國的革命者來往甚多,后深受幸德秋水、堺利彥等人影響,成為無政府主義者。1907年6月,何殷震組織發(fā)起成立“女子復權會”。6月10日,何殷震作為編輯兼發(fā)行人,開始出版《天義》作為“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報。后經無政府主義者張繼介紹,劉師培、章太炎和幸德秋水等人共同發(fā)起成立了宣傳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社會主義講習所”,《天義》慢慢也變成了“社會主義講習所”的刊物[3]81-82[4]。
男女之不平等,是近代以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普遍認識到的社會現(xiàn)實,但如何解釋男女不平等的起源、現(xiàn)狀以及應采取怎樣的破解之道,則各有看法。何殷震可能是最早將中國婦女解放納入階級斗爭范疇之中的女權主義理論家之一。1907年7月,她開宗明義地在《天義報啟》中指出,從古至今的所有社會,均屬不平等的階級社會:“地球之上邦國環(huán)立,然自有人類以來,無一事合于真公。異族之欺陵,君民之懸隔,貧富之差殊,此咸事之屬于不公者也。自民族主義明,然后受制于異族者,人人均以為辱;自民約之論昌,然后受制于暴君者,人人均引為恥;自社會主義明,然后受制于富民者,人人均以為羞。由是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遂為人民天賦之權。然環(huán)顧世界各邦,其實行種族革命者倚占多數(shù),若政治一端,雖實行共和政治者,猶不能盡人而平等,經濟一端更無論矣。試推其原因,則以世界固有之社會,均屬于階級制度,合無量不公不平之習慣相積而成,故無論其遷變之若何,均含有不平之性質。”[2]818換言之,她將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造就的民族與國家不平等、封建制度造就的政治權利不平等、資本主義制度造就的經濟不平等歸因于“階級制度”。尤須注意的是,何殷震雖然認可階級理論對各類不平等現(xiàn)象的解釋力,但仍毫不留情地批評這些“同道中人”缺乏性別視角,沒有意識到男女不平等亦是一種不平等之“階級制度”:“顧今之論者,所言之革命,僅以經濟革命為止。不知世界固有之階級,以男女階級為嚴。無論東洋有尊男輕女之風也,即西洋各國號為男女平等者,然服官議政之權,均為女子所無,則是女子所有之權,并賤民而不若。更反觀之于中國,則夫可多妻,妻不可多夫,男可再娶,女不可再嫁,服喪則一斬一期, 賓祭則此先彼后。即有號有均平者,既嫁之后,內夫家而外母家,所生子女,用父姓而遺母姓,又安得謂之公平乎?夫男女之間,其制度失平且若此,于此而欲破社會固有之階級,不亦難乎!”[2]818-819
何殷震鮮明地將階級視角引入性別問題之中,盡管她所批評的“今之論者,所言之革命,僅以經濟革命為止”可能并不確切。事實上,梁啟超早在1899年便曾在《論強權》中提到男子對婦人有“強權”,正類似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階級關系:“今日資本家之對于勞力者,男子之對于婦人,其階級尚未去,故資本家與男子之強權,視勞力者與婦人尚甚遠焉。故他日尚必有不可避之二事,曰資生革命(日本所謂經濟革命),曰女權革命。經此二革命,然后人人皆有強權,斯為強權發(fā)達之極,是之謂太平。”[5]354可見,近十年前,梁啟超便曾以女權革命和經濟革命作為未來平等世界的必經之道。但在梁啟超看來,彌平資本家與勞動者之不平等的經濟革命與彌平男女不平等的女權革命是并舉的兩種革命,二者之間沒有密切關系。
何殷震的獨特之處在于,她不僅提出“非破壞固有之社會,決不能掃除階級,使之盡合于公”[2]819,而且更進一步將階級斗爭與婦女解放結合在一起,指出“故欲破社會固有之階級,必自破男女階級始”[2]819。因為男女階級制度最為頑固、壓迫最為深重,所以她主張由打破男女階級入手,破壞階級制度:“夫以男女階級之嚴,行之數(shù)千載,今也一旦而破之,則凡破壞社會之方法,均可順次而施行,天下豈有不破之階級哉!”[2]819換言之,她將男女革命內嵌于整個社會大變革中,“把破‘男女階級’視為開啟一切革命的起點,貫穿諸革命過程,也是革命的終點”[6]153,指出“夫居今日之世界,非盡破固有之階級,不得使之反于公;居今日之中國,非男女革命與種族政治經濟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2]819。因此,可以說何殷震雖不是中國最早用階級話語解讀性別問題者,但卻可能是最早將男女革命納入階級斗爭范疇,并將其置于全體人類的解放中不可缺少的一環(huán)的思想家。
二、同時注重“性別中的階級”和“階級中的性別”
何殷震何以突破梁啟超等人割裂地看待經濟革命與女權革命的觀點,而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這與她對婦女受壓迫起源的認識密切相關。
何殷震指出婦女受壓迫起源于階級制度。她認為,原始社會實行原始共產主義,男女較為平等:“試觀太古之初,人民于共產制度外,兼行共夫共妻之制,未嘗以財產為私有,亦未嘗以女子為私有也。”[7]197她將婦女之受壓迫起源于財產私有制及由其衍生出的階級壓迫:“及人民欲望漸萌,欲去他人之財產為私有,并欲取他部婦女以為一己私有物……是女子私有制度之起源,與奴隸制度之起源,同一時代,均共產制度破壞之時代也。”[7]197-198何殷震特別強調婚姻關系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發(fā)生變更,“貧富之級既嚴,由是,男子由奴隸之制度進為農奴之制度,由農奴之制進為今日雇工之制;女子由掠奪結婚之制進為買賣婚姻之制,由買賣結婚之制進為今日一夫一妻之制”[7]197-198。這就把私有制的產生、生產關系的變更與“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了”聯(lián)系起來[8]68。
何殷震指出,自資本主義工場生產以來,婦女在家庭手工業(yè)中生產的產品無法與機器大生產相競爭,且不再占有生產資料,“生產機關遂為富民所獨握,致貧女所勞之職業(yè)鮮克支持,不得不為富民司工作。”所以原有的家庭婦女不得不脫離家庭,成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產者:“為女子者,不得不仰資本家之鼻息,以投身工場,而昔日家庭之女王,遂為賃銀制度所束縛,以為賃銀勞動之人。”[7]112
此前的中國女權主義者主要從“性別”的角度著眼探討男女不平等問題,往往強調婦女共同的“女子”身份,將婦女作為一個被壓迫的整體,從而要求爭得與男性一樣平等的權利。而何殷震在指出作為性別的婦女在整體均是受壓迫者的前提下,點出前人所忽視的“性別中的階級”問題。
她指出,婦女中也有社會上層和下層的階級分別,而女工等勞動婦女是婦女中受壓迫最為深重的群體:“中人以上之家,女子舍育子、治家而外,鮮事工作。……惟中人以下之家,鮮克支持,為女子者多自食其力,或從事農作,或出為雇婢,其下者則為娼妓”[7]134,而賣身于“富民”的貧女,“所罹之苦,罄竹難書”“生殺之權”卻全然操于同為婦女的“主婦”之手[7]111。即便在限于困厄的貧苦婦女中,也可分為四等,“最下者為娼妓,稍進則為妾御,又稍進則為婢仆(此指鬻身者言),進而愈上,則為雇婢及女工。”[7]115她指出,正如男界中分貧富階級之外,“女界之中,以貧民占多數(shù),或為工女,或為雇婢,其衣食亦仰給富民”[7]140。有的富豪之妻妾,置裝、化妝的花費抵得上貧戶數(shù)年之用,她們養(yǎng)名犬、乘豪車、飾艷服等等,“而制紗各廠之女工,則垢衣惡食,日受鞭撻”。何殷震問道,“則貧女之陷于此境,孰非爾等貴女所掠奪?”貧苦婦人沒有飯吃,“各衙門、各公館里面,做太太、做小姐的,何等闊氣!”[7]168“孰非由于財產之不均乎?孰非由于資本家之罪乎?”[7]112
何殷震不僅重視“性別中的階級”,同時也敏銳意識到“階級中的性別”,指出女性無產者之痛苦,還受傳統(tǒng)男女性別秩序之深刻影響。她哀嘆:“今世界可悲、可慘之境,無過于勞動者,而勞動者中,舍少年勞動而外,即以女子勞動為最苦。”[7]290由于資本主義工場(工廠)所生產的物品并非民生日用所必須,導致民生日用品價格攀升,使男性工人的工資“不足以贍其身家”,為了維持家庭的勞動力再生產,因此逼迫家庭婦女參與到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來,“出而謀食,以供朝夕之需”[7]112。且赤貧之女既無可能占有機器等生產資料,“復無入學之資”,所以“女子失業(yè)者必日眾”[7]115,從而使女子在勞動力市場上更處于弱勢地位,成為廉價勞動力,以至于在全球范圍內,女工的數(shù)目甚至接近男工的兩倍[7]113。
在資本主義父權制社會,女工除了在工廠做工,“于家庭為妻、為母”,還要承擔養(yǎng)育子女和家務勞動的重任,“彼之勞動,終夕不休”[7]113。更令何殷震憤怒的是,“資本家之于女工,妨其日力,害其健康,弭其幸福”“役他人之力,以生一己之財;既迫人于貧,又利用其貧以增一己之富”[7]119,不僅“以女子為生財之具”[7]113,更借此把女子當成“玩物”乃至“用物”“復以丑惡之行而敗其節(jié)操”[7]119。正因為女工工資之低,于是往往“于工作之外,兼業(yè)賣淫,以補其不足”,或成為婢女、小妾,但還要因此承受污名[7]117-119。何殷震不由得感慨,“今日之制度,則勞力、辱身之苦,畢集于貧女之一身”[7]120。
總之,何殷震一方面強調“性別中的階級”,即從階級的觀點看待性別問題,指出婦女受壓迫的來源是私有制和階級制度,特別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婦女深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且同為婦女亦有階級之別。另一方面,也強調“階級中的性別”,從性別的觀點看階級問題,指出在資本主義父權制下,婦女因性別弱勢更受剝削,且還要受家庭、生育、婚姻制度的多重壓迫。
三、以女界革命求得解放
明晰婦女受壓迫的原因之后,自然要對癥下藥提出解決方案。近代中國早期女權主義論述從“文明論”出發(fā),認為婦女作為“國民之母”和“文明之母”,對于現(xiàn)代國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自晚清開始掀起了“倡女權”“興女學”等一系列風潮,為構建民族國家而服務。繼而又有自由主義的女權主義訴求,要求男女平等,提出婦女與男子既要同擔責任,亦要共享權利,確立獨立地位。在這樣的思潮影響下,近代中國發(fā)起了婦女參政等一系列婦女運動[6]。而何殷震既然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視為當下婦女受壓迫的根本原因,自然對上述方案有所批判,認為這無法從根本上達到婦女解放的目的。
從性別的角度看,何殷震認為男子主張“興女學”有為“一己之自利計耳”之嫌疑。她指出,有的男子要求婦女進女校以學習手工、烹飪等技術,以至于學習師范、醫(yī)學、理科等,“蓋欲使女子學成之后”,可以到社會上謀得職業(yè),賺取錢財,“以紓一己之困耳”。又因為當時的女子教育,“首崇家政一門”,女子即便不到社會上工作,也是為家庭服務,而在男權社會中,“實則家為男子之家,治家即系為男子服勞”[7]137。而女校中的倫理一科,更是從道德層面對婦女進行規(guī)訓,第一認同家庭倫理,第二推崇相夫教子,第三夾雜以軍國主義,“以激發(fā)女子革命之心”,事實上是為男性占主導地位的家庭、國家服務,“非迫女子為家庭奴隸,即迫女子為國家奴隸”[7]194。
從階級的角度看,婦女進女校學習紡織、裁縫、烹飪、造花或醫(yī)學等各專科學問、技術,除了替男子賺錢之外,更維系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何殷震指出,婦女表面上得到了“賃銀”(即工資),獲得了(經濟)獨立,但實際上并不是真正的獨立:“然倚賴男子為生活,與依賴資本家為生活,其陷于奴隸,正復相同”。故而學習了技術而參加勞動生產,從而獲得表面上一定經濟獨立地位的婦女,實際上是淪為了無產階級,“非獨立也,乃依賴資本家為生活者也”。從這個角度而言,參與工廠勞動的婦女和進行家庭勞動的婦女一樣,均為勞動婦女,只不過一個是“為夫服勞”,一個是“為資本階級服勞”而已,并無本質不同[7]194-195。因此,何殷震雖然不否定婦女學習文化知識的意義,卻在其維護固有階級和剝削制度這一更深遠的意義上,認為這無法達成婦女的真正解放。
針對婦女爭奪選舉權等參政運動,何殷震認為婦女解放的“根本之改革,不在爭獲選舉權”[7]139。何殷震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認為那不過是資產階級實行階級統(tǒng)治的工具而已,所以“此國會政策所由為萬惡之原也”。即便是號稱追求社會主義,搞議會斗爭的西方社會黨人,盡管有不少已經當選議員、參與政權,但勞動人民受階級剝削、壓迫的情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變,“勞動之民,仍屈身于賃銀制度,以作富民之奴隸,虐待之苦,與昔不殊”[7]140。她點明婦女參政運動在性別口號下被遮蔽了的階級問題,指出無論是在限制財產的少數(shù)選舉還是在普選的基礎下,只要存在階級差異,“則以貧富階級不除,貧民衣食系與富民之手,不得不媚富民也”,所選出來的無非是上層階級的婦女而已,“其議員亦仍屬貴女”[7]140。因此,即便婦女爭得普選權,其結果相比過去的婦女受壓迫于政府和男子之外,無非是“另受制于上級之婦人”“別增一重之壓抑也”[7]141。換言之,必須看到婦女群體這一性別同一性內部的階級差異性,在階級制度下所爭得的男女平等參政權,“不獨男女不平等,即女界之中亦生不平等之階級”[7]142。
對于婦女解放問題,何殷震給出的根本解決途徑在于進行“女界革命”,而所謂的“女界革命”事實上內嵌于政治、經濟、社會革命之中。何殷震所創(chuàng)辦的《天義》,其宗旨為“破壞固有之社會,實行人類之平等”“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種族、政治、經濟諸革命”[7]580,而“欲實行種族、政治、經濟、男女諸革命,均自破壞社會始”[7]45-46。破除私有制及其所帶來的階級制度,在其“女界革命”理論中具有核心地位。她認為,“欲實行女界革命,必自經濟革命始”,而所謂的經濟革命,“即顛覆財產私有制度,代以共產,而并廢一切之錢幣是也”[7]204。換言之,即廢除私有制,“惟土地、財產均為公有,使男女無貧富之差,則男子不至飽暖而思淫,女子不至辱身而求食,此亦均平天下之道也”[7]50。在《論女子當知共產主義》一文中,何殷震更直接呼吁“實行共產”。她引述蒲魯東的話:“財產者,掠奪也”,以白話告訴婦女們“就是因為有錢的人,把財產掠奪了去,所以弄得多數(shù)的人,窮的沒有飯吃”,因此必須實行“共產制度”,才能解決問題[7]168-169。何殷震甚至以極為激烈的語氣,高呼“勢必實行公產”“勢必排斥富強學說,勢必殺盡資本家”,以解決“財產分配不平均”,才能真正解放婦女,并且解放全人類[7]115,118。
總之,何殷震等人認為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婦女受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將“階級中的性別”和“性別中的階級”結合起來,以受壓迫的婦女尤其是其中的勞動婦女為革命的主體,與政治、經濟、社會革命同步推進,反對現(xiàn)有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以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不平等而達到人類的真正平等、共同解放為革命目標。這一系列論述不得不說是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與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相融合的先聲。
四、馬克思主義傳播史視域下的階級斗爭理論與婦女解放思想之結合
何殷震的理論著述主要發(fā)表在《天義》,而它自1907年6月出版第一號起,至1908年3月共出版了十九期,文章二百余篇,僅存在了短短9個月的時間[7]5。大約十年之后,即五四運動前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一步傳播,一些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剖析中國婦女問題。考察他們的觀點,不難發(fā)現(xiàn)與何殷震的思想有不少相似之處。如陳獨秀指出,“照現(xiàn)在的經濟制度,婦人底地位,一面脫離了家庭的奴隸,一面便得去做定東家的奴隸”[9]47,這與何殷震所指出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婦女“倚賴男子為生活,與依賴資本家為生活,其陷于奴隸,正復相同”之說,如出一轍[7]195。又如李大釗評論爭取參政權的自由主義女權運動所追求的“都是與中產階級的婦人最有直接緊要關系的問題,與那些靡有財產、沒受教育的勞動階級的婦人全不相干。那中產階級的婦人們是想在紳士閥的社會內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權力。”[10]414這一觀點也與何殷震批判參政運動“亦不足以濟多數(shù)之工女,不過使少數(shù)女子獲參政之空名而已”[7]141相類似。何以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與何殷震觀點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其實,何殷震等無政府主義者正是有意識地將馬克思主義文獻傳入中國的最早一批知識分子。盡管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李大釗等人直接受過何殷震的影響,但或許可以說他們共同從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汲取了理論資源。
1908年3月,《天義》第十六至十九卷合刊(春季增刊)中發(fā)表的《女子問題研究:第一篇 因格爾斯學說》[7]497-499,實際上即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第二章里資產階級婚姻家庭部分的摘譯,這可能是中文世界里第一份關于《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中文譯文。此外,《天義》還于1907年12月30日刊登了《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一節(jié);1908年1月15日刊登了《〈共產黨宣言〉序言》;1908年3月刊登了《〈共產黨宣言〉序》和《宣言》的第一章全文[7]204,264-270,419-430。盡管在1906年,中文世界中就有大段摘引《宣言》的文獻,但如《天義》這樣單獨將《宣言》某一較為完整的部分提出來作為理論背景的介紹,是晚清所罕見的。
在這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階級理論和婦女解放理論是最核心的主題,這顯然體現(xiàn)了摘編者的理論旨趣。1908年1月15日所登恩格斯的《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之后,附有一段編者按語,盛贊“《宣言》發(fā)明階級斗爭說,最有裨于歷史。”[7]2703月所刊登的《宣言》第一章全文之前,劉師培又作序介紹《宣言》的歷史,指出其要旨為“萬國勞民團結,以行階級斗爭,固不易之說也。”雖然無政府主義者并不完全贊成馬克思主義的所有觀點,但對于《宣言》中介紹的階級斗爭理論卻十分贊賞,認為《宣言》“復以古今社會變更,皆有階級之相競,則對于史學,發(fā)明之功甚巨。討論史編,亦不得不奉為圭臬”[7]421。并在最后解釋“紳士閥”(bourgeoisie)和“紳士”(bourgeois)等階級斗爭理論所常使用的術語時,指出“紳士閥”即為“含有資本階級、富豪階級、上流及權力階級諸意義。”又解釋“紳士”“系指中級市民之進為資本家者言,與貴族不同,猶中國俗語所謂‘老爺’,不盡指官吏言也。”[7]431而全文刊登的《宣言》第一章,正是《宣言》里最為集中闡述階級斗爭理論的篇章之一。又如《天義》還曾翻譯哈因禿曼(今譯亨利·邁耶斯·海因德曼)的《社會主義經濟論》,而譯者指出“惟階級斗爭,則古今一軌”,認為自從有了階級斗爭理論,社會主義理論才算有了根據(jù)[7]431。
如果說劉師培更重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則何殷震似乎對其婦女解放理論更感興趣。1907年12月30日附在何殷震《經濟革命與女子革命》一文后的《宣言》中關于資本主義婚姻和家庭制度一節(jié),正是為了佐證在財產私有制度下婚姻的實質為金錢關系這一觀點。因此編者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學說雖然與無政府共產主義不同,但對《宣言》中所指出的“以為資本私有制度消滅,則一切公娼、私娼之制自不復存;而此制之廢,必俟經濟革命以后”這一觀點深表贊同,表示這直擊問題本質,“可謂探源之論”[7]205。而1908年3月刊登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之節(jié)選,編者再度重申婚姻關系背后的金錢關系,“實則均由經濟之關系而生耳,無異雇主之于工人也”,因此要想破除這種金錢婚姻,爭得婦女解放,“必自經濟革命始,彰彰明矣”[7]491-495。何殷震的多篇文章顯然受此影響極深,如她指出“處貧富不均之世,娼妓、妾御之制,絕無消滅之一日”[7]119,即表明娼妓制度與私有制的根本聯(lián)系。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天義》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最早出現(xiàn)的文本被命名為《女子問題研究》,其主旨是關于家庭的起源和私有制的關系,亦即關于婦女解放的。因此,與其說何殷震是引介了階級斗爭理論而運用于婦女解放問題,不如說她是為了說明婦女解放問題,而引介了階級斗爭理論。換言之,至少在何殷震那里,婦女解放問題是第一位的,階級斗爭理論是第二位的,階級斗爭理論是為婦女解放服務的。這是她與劉師培等人的巨大不同。
總而言之,何殷震是一位杰出的早期中國女權主義理論家,其關于婦女解放問題的諸多論述在當時相當獨特。她對“性別中的階級”和“階級中的性別”的關注,對當時的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女權主義論述都是一種超越,而與若干年后的馬克思主義者遙相呼應。當然,她的理論還不夠成熟,也不成系統(tǒng),更沒有太多的具體實施方案,但不可否認的是她對此作出的努力大大推進了中國婦女解放思想的深度和廣度。盡管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后來人未必都了解她的理論貢獻,但其理論嘗試仍在其后中國大地上風起云涌的婦女解放運動中有所回響。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不少她所試圖解決的問題仍然擺在我們面前。從這個角度講,何殷震的婦女解放思想不僅有其學術史意義,也有一定的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