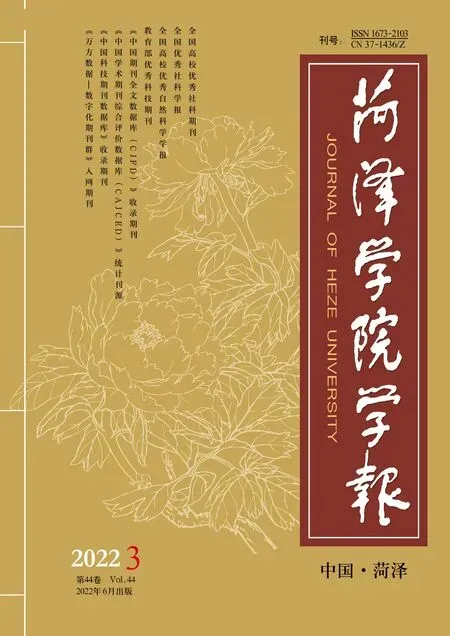中國古典“藝術心象”本體論的詩學闡釋*
陶永生,陶怡順
(1.淮陰師范學院文學院,江蘇 淮陰 223300;2.哈爾濱工程大學外國語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
中國古典藝術理論的諸多重要論斷,只言片語多散見于歷代的詩論、文論、書論、畫論等眾多典籍之中,這些歷史文化的碎片近乎囊括、貫通了古代經學、史學、子學、文學等諸多領域。伴隨著諸如書法、繪畫、音樂、戲曲等各藝術門類漸趨于成熟、定型,也就為藝術本體論、藝術創作論、藝術審美論等諸領域勾勒出其認識論意義上的邏輯脈絡和知識論層面上的體系架構提夠了充分的理論資源與學理依據。其中,位列“宋四家”之首,以詩文、書法、繪畫成就彪炳千古的大文豪蘇軾首倡的“成竹于胸”說,后幾經淘洗、凝練,提煉為“藝術心象”論,無疑發揮著藝術詩學理想和藝術哲學觀念上的“本體論”引領和“方法論”規約作用。
在當下情勢下,對于中國古典藝術評論的深度挖掘和系統整理,如何將哲學的、美學的、文論的、詩論的等其他領域浩如煙海、汗牛充棟般的典籍文獻吸納進來,迫切呼喚清晰的藝術哲學與藝術批評學的學科意識與學科自覺。建構當代性視野下的中國古典藝術哲學,尤需構筑一種多元共生、平等對話的展示平臺和流通環境,特別是與文化詩學、審美詩學、形象詩學等當代主流詩學理論達成雙贏共享的對話條件,進而實現當代詩學視域下中國古典藝術哲學話語范式之現代性轉換的重大飛躍。
一、意象塑型——“藝術心象”本體的“文化詩學”尺度
中國古典藝術批評理論的文本呈現形態固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大塊頭高頭講章,但確鑿無疑的是事實上確切存在的,有著充沛豐盈的典籍文獻可以佐證、撐持。相較之下針對各門類藝術領域的批評理論與創作經驗的探究和提煉可能會更勞神費力,本文將梳理重點鎖定在古代文人對藝術創作、藝術批評和藝術審美等范疇理論和經驗的概括與總結上。例如,蘇軾首倡的“藝術心象”思想,是對魏晉時期“意在筆先”(王羲之語)、“窺意象而運斤”(劉勰語)等觀點的補充與豐富,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批評理論和審美理想,成為古代藝術創作與批評所追求的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審美取向。
植根于藝術創作實踐中的“藝術心象”本體論,完整地闡釋了從“觀萬物之變”到突然產生,繼而“胸有成竹”起承轉合,再到“隨物賦形”形之于手的藝術創造過程,雖然可能像靈感一樣“倏然而來、倏然而逝”只是一剎那的功夫,但其中還需經歷一個構思的過程,蘇軾在其夫子自道中曾提及的“成竹于胸”說便是文藝構思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后世者同道亦頗多,譬如名列“揚州八怪”之首,以三絕“詩、書、畫”聞名于世的有清一代才子鄭板橋則直接承祧了這一思想,進而具象化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三竹”藝術創造論,極其形象地將文藝構思過程的仿真推演發揮到了極致。
蘇軾所著《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篇可以稱得上關于“文藝創作論”的夫子自道,包括繪畫在內的文藝創作的起點設定為藝術觀察,正所謂“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1]這是一種可觀可察、“看得見摸得著”的自然現象,作為自然物的“竹”的生長過程呈現于藝術觀察者的眼前。借助于觀察者各感官功能的釋放,自然界的物化之“竹”映入眼簾,自此管道“由外入內、長驅直入”進入觀察者的頭腦中,或言之,又可稱之為內心世界。一旦登堂入室進入人的腦海中,來自不同渠道的訊息殊途同歸,共同指向、聚焦到一點,不斷淘洗、積淀,最終形成了自然之“竹”的鏡像,一種人化的物象,具體呈現為“節葉具焉”的生動鮮活狀貌。
這些形形色色的“關于‘竹’的方方面面的先見或稱成見”激蕩融合,“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暫時達成一種妥協、平衡,形成了一種深深烙印上觀照主體“這一個”特質的“個性獨異、意蘊豐贍”的意象綜合體。驀然回首,怦然遭遇了那個“熟悉的陌生人”,“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2]。于是乎,從“映射了大千世界多樣物象的眼中之竹”到“雜糅了觀察主體主觀情志的胸中之竹”,最終完成了由物化的自然向“人化的自然”轉化的質的飛躍。
“成竹于胸”,或曰“胸有成竹”,這一“心中之竹”其實就是心中視象,意中“人與事”,即“心象或意象”。何為“心象”?簡單而言,即創作主體心中之象、意中之人。南朝梁代著名文論家劉勰最早提出了“心象”問題,《文心雕龍·神思》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3]意即創作主體在進行創作時會根據聲律而遣詞造句,通過觀照、體悟心中的形象而謀篇布局。當下藝評界多有學人把此處原典意義上的“意象”內蘊理解、闡釋為文藝作品中業已固化、定型的典型形象,甚至直接將之視為已身處再創造階段的接受主體所檢視的閱讀對象。這種理解顯然疏離了劉勰格外重視創作主體意志張揚的初衷、原意,近乎背道而馳。
條分縷析一下“窺意象而運斤”的認識論路徑,顯而易見的是所窺之“心中之意象”理應前排就坐,揮毫潑墨的“運斤”緊隨其后,實際操作階段的“運斤”則忠實地秉承、踐行著意象的“掛圖作戰”來排兵布陣、攻城略地的。由是觀之,《文心雕龍》字典里的“意象”一語題中應有之義就是經過“神思”這一復雜精神活動后,厚植于創作主體心中的“藝術心象”。
當下中國藝評界積聚凝練的一大共識就是,文學藝術理應是詩情畫意的,我們倡導一種文化詩學的文本闡釋方法,一種格外關注藝術主體“自我塑造”流程的藝術本體論[4]。有鑒于此,在文藝創作活動的構思階段,“藝術心象(意象)”的塑型歷程是一個關乎全局、語定乾坤的關鍵環節。蘇軾在這里提出的“成竹在胸”,是對藝術心象“情本體”(李澤厚語)問題的進一步拓展、深挖[5]。心中的雜多意象持續發酵中,胸中之塊壘愈積愈多,環伺周遭,“心有郁結不得不發”,或借助于文字的線條,或憑依繪畫的色彩,由內到外“噴薄、流瀉”,盡興釋放、物化出來。由“積聚了創作主體太多愛恨情愁的心中之竹”再到“挫萬物于筆端的手中之竹”又是一次躍遷,“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6]從而完成了首期的閉路循環。
蘇軾并未就此止步,這也是他的高明之處,他超越了就事論事的狹隘,突破了單純文藝創作規律的窠臼和規約,將“反映文藝創作規律的藝術心象”升華為“映照心路歷程的人生心象”,進而又躍遷到了一個新的詩學高度,每一首詩、每一幅畫均凝練著一曲曲大氣磅礴、壯志凌云的詩化人生。卒章顯其志,蘇軾大膽發出了驚天拷問,“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7]個中款款心曲,難道僅僅惟有畫竹如是嗎?情不自禁,和盤道出了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認知規律:個別事象寓于一般規律之中,猶如朵朵浪花消融于浩渺煙波之中。
忠實地承繼了蘇軾“成竹于胸”說衣缽的鄭板橋更向前推進了一步,他格外重視弘揚創作主體的主動性、能動性和發掘認識客體的豐富性、多樣性,提出了“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藝術創造論。鄭板橋在《竹》中的如是說:“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8]這段話生動形象地說明了藝術繪畫創作的三個重要階段,是眼中之竹(“晨起看竹”)、胸中之竹(“胸中勃勃遂有畫意”)、手中之竹(“落筆倏作變相”),也就是由外入內的藝術感知“內化”環節、內外兼修的藝術構思環節、由內及外的藝術物化“外化”環節,但凡優秀的藝術創作都必須經過這樣一個蘊含著“從物象經意象、再由心象到屬文的兩次重要飛躍”的認知過程,創作出生動鮮活的、極富感染力的文藝作品。
以蘇軾“藝術心象”本體論為主要表征形式的古代詩學與文論、畫論、書論等交互融通闡釋,進而構成中國古典藝術創作論以及藝術批評觀的基本框架,成為古代藝術審美的主導塑型范式和主流評價指標。古代藝術創作論詩學居功甚偉,彰顯了中國古典藝術批評理論具有超越時代、貫通歷史的無限生命力。
二、詩性闡釋——“藝術心象”本體的“審美詩學”造型
從人類精神科學的變遷史來看,人類大致存在兩種精神文化的智慧:“一種是敘事學的智慧,一種是詩學的智慧。”[9]詩性之美君臨一切,詩學與哲學殊途同歸,在本源性層面上握手言歡。耕耘在“人的生活世界和社會存在”土壤上的“心象本體”之株綻放出詩性之美、生命之光。藝術心象具有了“情本體”屬性,審美觀念的傳統規定也大為改觀,藝術家和哲學家開始交換各自的審美領地和學科位置。此種情形正像分析哲學的主要批判者、新實用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理查·羅蒂所言,現代哲學“就其主要文化功能而言,已被文學批評所取代。”[10]
擅長“詩性闡釋文本及其聯合體(作品)”的文化詩學批評家是在用“文學的”概念來注釋式分析和歷史化闡釋歷史文本或稱歷史材料,理解“過去的傳統”和歷史記憶,賦予傳統和記憶以新的意義構成。這種“詩性寫作”可以全面而多視角的揭示文學文本的多義性內蘊,緣此,我們在解讀闡釋文學作品時,也才得以體驗真實的文化世界和感悟詩性的生命存在,我們的閱讀行為也隨之從“詩性閱讀”上升到了“價值閱讀”。
正如美國美學家蘇珊·朗格所說,“真正能夠使我們直接感受到人類生命的方式便是藝術方式。”[11]審美詩學正是在與文藝批評、文藝理論的互動、變異中,匯進了西方藝論的總體演進之中,并在這一交匯中強調了審美意識和詩性記憶。作為藝術創作過程核心環節的藝術構思階段最終構塑形成的“藝術心象”水乳交融般融入了藝術家傾注其中的詩性情感與審美理想,盡性揮灑著濃郁的詩意和綿緲的情愫。
如蘇軾名詩《飲湖上初晴后雨》,作者將心中“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詩情畫意完美地投注到了“山色空濛雨亦奇”的西湖美景之上,用這種審美之心、詩性之情去看取、觀照自然之景物,碰撞、交融、升騰為詩人所專屬的人化西湖“情本體”,由此所形成的“西湖心象”必然不是客觀外物的光影全息拍照、簡單復制,而是深深烙印上了詩家本人的愛恨情愁與情有獨鐘,往往渲染了一種迥異于世故常態,令人耳目一新、恍然頓悟、靈光徹悟的詩意氛圍和通感特效。
這樣的文例俯拾即是,又如蘇軾在他的《郭熙畫秋山平遠》一詩中云:“離離短幅開平遠,漠漠疏林寄秋晚。”[12]默然凝眸尺牘畫作,鳴鳩乳燕、白波青嶂皆是人間實實在在的自然美景、此岸仙境,只因為此景美不勝收,此景只應天上有,強烈地傳達出美到極致的“非人間”內心感受,這已是首次藝術創作基礎之上的再創作、再創造。
這幅畫作雖然所占篇幅不大,僅可稱得上“離離短幅”,但它用最經濟的筆墨,烘托出了最大化的“開平遠”思想容量和“寄秋晚”情感流量。雖是吟詠畫中之形,屬于“隔靴搔癢”的二次創作,卻極速入戲、睹物思情、感同身受,熔鑄了詩人本人的人生閱歷、主觀情志、審美情趣甚至于情感判斷、價值取向,“入乎畫中”又“出乎畫外”,將自身魂化為作畫者,同呼吸共命運,將作畫者創作時的審美“心象”烘托了出來。詩人宛若全知全能的智者一樣,取得了胸有成竹、洞燭隱微、君臨一切的主人翁姿態。
作為蘇軾“靈魂上的摯友”的畫家郭熙,對“藝術心象”的“情本體”性與詩意性也多有闡發,可稍作引述,作為參考。郭熙認為,創作者胸中的心象應籠罩在一種“神與物游”的審美視角與“物與情興”的詩意視點的透視之下,要襟懷“林泉之心”、戒除“驕侈之目”,唯有如此才能超越俗世、超拔高潔、遺世獨立,抵達“看山水亦有體”這一體現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價高”境界。他曾言:“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13]藝術家不能以功利之心、驕侈之目去感受著大千世界、蕓蕓眾生,如若時時處處蠅營狗茍、利欲熏心,就會受到“斬刻之形”的規約限制,而應秉持一種無利害、無功利的審美態度,以直指本心、返璞歸真、純凈簡約的“林泉之心”去觀山覽水,這樣的“山水意象”也就有了生意機趣、詩情畫意、盡態極妍。
不同季節的山仿佛一一映射著待字閨中的花季少女“艷冶如笑、蒼翠如滴、明靜如妝、慘淡如睡”的四類表情包[14],情狀各異,各擅其長,雖“意態”不同,但都飽蘸著楚楚動人的綿緲情愫和萋萋詩意。這早已不再拘囿于藝術感知階段的純粹的對山水“物象”的觀察打量,反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長驅直入跨越了“物”的邊界,直接進入到了“意”的領地,也即“心象”的勢力范圍,因此之故才能躍遷到了“兼并、雜糅了個性(一山之意態)與共性(數十百山之意態)對立統一的”二象性勃興的醞釀發酵黃金期[15],所謂“意態”正是心中印象的又一別名。
中國古代的藝術家在醞釀心象時,極力張揚自身的主體性,充分調集自家的聰明才智、審美情趣,“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極大地突破了所觀照對象物的外部特征和物理概貌,深入到了物象地貌的內在構造最深處,同時并行不悖的是又能反觀諸己,將自身的類本質力量和自我塑型力量雙向耦合后對象化為心中之象,試圖將其作為自己審美情趣的反照、投射。心象花園里最美的那片風景,其實歸根結蒂就是詩人自然流露的一種心里情愫和詩性圖畫。“成竹于胸”,具體而形象地體現了藝術構思的關鍵詞,此“竹”非彼“竹”,映入眼簾的絕不僅僅是自然物態的“竹”,更醞釀著觀竹、賞竹時的內心感受和人生體悟。
由是觀之,“意象”之境,是古代藝術家表情達意,直抒胸臆所孜孜以求的“天地人三位一體”的最高藝術哲學境界,它責無旁貸地寄寓了“心象”與“物象”,“無形”與“有形”的矛盾統一觀念。毋庸置疑地可以說詩性闡釋從本源意義上就是一種審美塑型,審美意象既是一種內斂與外釋有機統一的、蘊含豐沛而又高度凝聚的心象存在,又是一種極富象征意味的藝術審美效應。而“意境”之象,則是表現主觀情思與客觀境象渾然無跡、羚羊掛角般地融會貫通、珠聯璧合,具體而微之地映照出宇宙勃勃生機和人生真諦的深刻寓意。
那么,究竟何謂審美呢?或者,再具象化一點,文藝領域中的“情本體”審美范疇具體包含了幾多內容呢?這是一個很復雜的學理問題。簡言之,審美從本質內涵上來講是人類諸多復雜精神活動范疇中的一種對象性活動,在這一精神性勞動中,人們憑依閱讀、欣賞、品鑒與理解等詩性闡釋行為實現了認知的傳導、情感的評價、價值的判斷。對象物本是“有情物”或“情理結構”[16],認識主體傾注了太多心血、情感覆蓋、滲透其中,它幸得“萬千寵愛于一身”,由物象華麗轉身為意象,位極巔峰。藝術家們以激情四射的情感去觀照它、評價它,回旋往復地開展著所謂的“情以物興”與“物以情觀”(劉勰語)之間“平等對話、能量流通”的雙向交流活動。
“情”與“物或景”作為中國古典美學的一對重要范疇,本就同宗同源、異質同構,南宋詞人張炎在他的《詞源·離情》中就有感而發,“全在情景交煉,得言外意。”這也應是蜚聲文壇的“情景交融”說的最早出處,后直接啟發明末清初詩評家王夫之提出了“情景相生、情景交融、情景合一”三命題的“情景”論[17]。中國古典美學的情景觀,一方面突出了“物或景”的客體性和觸媒性,“情以物興”是由外及內、由物及心,是“物”觸動了藝術家銳敏充沛的情感神經元,剎那間倒逼著促使創作者的情感敏感起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繼而振奮起來,甚至慷慨激昂、亢奮激越起來;另一方面凸顯了“情”的主體性和攝控力,“物以情觀”是由內及外、由心及物,藝術家用他那雙“發現美的眼睛”,飽蘸著“愛得深沉、愛之深恨之切”的情感去觀照、去親吻“這一個”物,使“獨一無二”的物籠罩上了專屬于他、情有獨鐘的情感色彩,一切隨他應節而舞、應時而動。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也好、鳥也罷,早已不是獨立個體,雖然大自然里的它們也同樣是獨立的生命個體,但來到了藝術家的綠野仙蹤里,只好忍痛割愛,毅然決然放棄了個人的喜怒哀樂,踩著創作者的節拍霓裳羽衣、舞姿婆娑。在藝術家的眼眸里,目之所及整個世界都是“有意味的形式”,“落紅不是無情物”[18]。即便渺如落紅、一粟,它們也是有愛意情誼、有志向抱負的,詩人用移情于物的手法,借“物態”的落花春泥翻出“情態”的發抒“護花”情懷的新意,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極為瑰麗、高格的“價高”境界。
中國古典美學語境中的情景觀,不僅是文學藝術、哲學、美學論域,而且還是個文化學、政治學、社會學命題。依憑德國美學家伽達默爾的界說,“‘文化世界’是構成我們生活體系的一切概念細節之總和”[19]。這里尤其格外突出了“我們”作為認知主體的承上啟下、中流砥柱的樞紐作用,包括文化在內的一切創造物皆從人類出發,又歸宿在了人類這里。人與歷史(時間狀態中的文化文本)如影相隨,主體的歷史性與歷史的主體性并行不悖、交互相長,形成想象的歷史這一想象的地圖,在價值取向上體現為詩性評判。這種對話的邏輯構成創作者與文化文本之間有趣的交流。就在這所抒之“情”與所狀之“物”的雙向交流和互釋評價活動中,藝術家內心波動的跌宕起伏將呼應著所直面的對象物的變換,進而呈現出美感、崇高感、歷史感、家國情懷等百感交集的情狀。
在藝術審美范疇里,藝術家同樣發揮著調節“情與物、情與景”主客統一、融會貫通的主體性作用。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邕州馬退山茅亭記》中說: “夫美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于空山矣。”[20]這里他提出了一個極具現代意義的美學命題,“美從何處來,何為美?”自然界的事物為什么會美、給人以美感呢?他給出了終極解答:“夫美自美,因人而彰。”都是因為“人”的緣故呀!
他進一步舉例說,久負盛名的蘭亭為什么一直被人津津樂道呢,其實并非是因為它“清湍修竹”風景好,那都是拜王羲之之賜呀,倘若世上不曾有過膾炙人口的千古佳作《蘭亭集序》,估計可以想見世上再無蘭亭矣,“蕪沒于空山矣”。由此可見,還是“人”這一“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發揮了巨大的主觀能動性,由于強調人對于物的世界在觀照中的攝控、彰顯作用,本文以為此言最能說明審美的實質。
文學藝術之美閃爍著人性之美,從質的規定性上應當歸屬于社會美范疇,因而它的“情本體”審美主航道中勢必會百川歸海般匯聚進政治的、文化的、倫理的、民俗的、地域的等支流因素。但在具象化的審美評價活動的剎那,人的個性心理活動則處于無障礙、無利害、無功利的“三無”自由狀態和詩意棲居。誠如童慶炳在《蘇軾文論解讀》中所指出的:“在優秀的文藝作品中,詩情畫意與文化含蘊是融為一體的。”[21]
三、成竹于胸——“藝術心象”本體的“形象詩學”蘊涵
當代形象詩學批評學派的領軍人物趙炎秋將藝術形象推高到了可與語言藝術比肩的高位階,“形象、語言一直是文學理論的核心問題。”[22]他將形象問題作為一種藝術本體觀予以闡發,文學藝術的“心中視象”研究隨即升騰為一種“形象詩學”。創作主體借助于語言文字符碼或線條色彩作為媒介、橋梁,將構思階段鍛造成的“藝術心象”等“情本體”外化出來,同時對“心象”群落的生存狀態、品格高下也是一次全面檢閱、精準檢視。
在文藝創作活動的構思階段,“藝術心象”的形成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蘇軾在總結自身文藝創作與批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成竹于胸”說,是對藝術心象“情本體”問題的進一步拓展與深化。尤其是落實在形象完整性和生命活力兩個層面上,蘇軾引經據典,交互印證,做了詳盡、深邃而又深入淺出地詮釋與闡發。經此種種努力,從個體性性情層面的“情”演繹出群體性觀念層面的“理”,事實上也就賦予了“情本體”結構一種社會性的價值取向。
首當其沖的一點,“神思”活動中“自我塑造”而成的“心中視象”,雖然這一視象仍還蟄伏在心靈深處,但它卻是能夠完整地傳情達意,或厚度描述事件來龍去脈、或濃墨重彩渲染人生遭際悲歡離合的心象綜合體(意象)。藝術創作伊始,就像建造蜂巢一樣,最笨拙的工匠也比最勤奮的蜜蜂要高明,他的勝出就在于開工之前心中就有了一幅造巢的藍圖,哪怕是零星的、破碎的、模糊的草圖,在畫師那里亦同歸此理。畫師意欲“畫竹”動筆之先,“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在自己心中已經初步勾勒了一株完整的“意象之竹”,因此“心象”不再是“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的碎片化的物象,而是枝繁葉茂,葉葉交通、枝枝連理,更又一枝一葉總關情的“有情物”或曰“情理結構”。
北宋著名文學家、號稱“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師從了蘇軾的“成竹在胸”文藝觀,他又進一步形象地闡發道:“與可畫竹時,胸中有成竹。經營似春雨,滋長地中綠。”[23]所謂“成竹”即完整的心中形象,已非斷壁殘垣的片斷之物。后來者南宋著名文學批評家、筆記體文論巨著《鶴林玉露》的作者羅大經頗多精辟、獨到的文藝評論見解,曾在《畫馬》一文中批判地繼往開來,開創性地提出了“全馬在胸”說,“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24]一如“成竹”所指,此處所說的“全馬”同樣強調了“心中形象”的“必先有”之重要性與完整性。同時還指明了“如何去做”的切實可行、極具可操作性的技術路線,“積精儲神,賞其神駿”,久久為功,日積月累,“胸中有全馬”則立馬可就、指日可待矣。
無論是心中的“成竹”抑或是“全馬”,它們都是藝術家勞神費力、殫精竭慮,積精儲神,賞其神駿,才隨物賦形,百煉成鋼塑造而成的所謂伊人“情本體”。這些心中形象生機盎然,“大略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一個又一個珠聯璧合的“心中視象”生動活潑、機趣盎然,宛若一群蹦蹦跳跳、鮮活可愛的生命個體在向我們揮手致意,遠遠地向我們走來,愈來愈近,我們似乎已經嗅聞到了它們散發出的沁人心脾的芬芳氣息,于是乎我們陶然其中,沉浸在“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的無我、忘我“魂化莊周”癡迷混沌狀態,所以“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25]。
一旦形象塑造的“靈感來襲”,藝術家們“急起從之”“追其所見”,生怕稍縱即逝,他們將“心中的視象”視為摯愛珍寶,能跟自己進行“心與心相流”的靈魂對話的對等個體,一個有血有肉、活力四射、有生命的情感對象,他們休戚與共,共同聯姻成了同一個生命共同體。正因為珍愛有加,藝術家們從一開始就擔憂這個心儀已久的對象會如“兔起”和“鶻落”一樣稍縱即逝、瞬間逃逸,因此愛屋及烏,也就極為珍惜這個怦然心動的短暫時刻。
那么,這些藝術心象“情本體”的蓬勃生命活力源自何方呢?蘇軾似乎早就預感到了讀者會提出這樣的疑惑,他不厭其煩地一再論證道,“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神。”[26]心中這些視象呈現出的“見竹不見人”、“嗒然遺其身”的情狀,實際上是指創作者的感同身受、物我兩忘的精神狀態,一種“忘我”的、無利害的、超于功利的“逍遙游”愉悅精神。
創作者迷醉其中,“心游無何有之鄉,神馳于六極之外”,以致深陷于“忘我、無我”之境,導致作者“不知是莊周化蝶,還是蝶化莊周”,最后連自身的存在線索也尋覓不到了。在這種凝神忘我、物我兩忘以至于移情于物、物我同化的“物我歸一”精神狀態中,其實是人的生命源動力投射到了作為對象物的“心象”上,使“心象”似乎獲得了栩栩如生的生命活力。這一生命活力源自于創作者自我的生命力量,是作者的生命力量運用“自我塑造與自我被塑造兩過程持續地雙向構塑、并行不悖”手段展開的對象化行為。
藝術創作中的這種“藝術的直覺”外射到自我世界、深入自己“心中視象”的移情說,這一論斷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德國美學家費肖爾、里普斯那里,他們將這種“人把他自己外射到或感入到自然界事物里去,以造成‘對象的人化’”的心理現象稱為“移情作用”[27]。藝術家們移情于物,將內心蓄念已久的熾熱情感投射到對象物上,也就完成了創作者內心情感的對象化,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藝術心象“情本體”獲得生命活力與社會能量的深層原因。
無論是“成竹于胸”說、“全馬在胸”說,還是“三竹”論、“情景”論,都是對魏晉時期“意在筆先”“窺意象而運斤”等經典文藝觀的有益補充與豐富,是一種比較成熟的古典“藝術心象”本體論。隱匿在藝術家內心深處的“心象”是觀念意義上的“成竹”“全馬”“三竹”“情景”,又非簡單物象層面上的“成竹”“全馬”“三竹”“情景”;是既成事實的已然,又是尚未成事實的未然;是完整的已能表情達意的形象,又是未定型的仍處于現在進行時之中的形象。藝術心象“情本體”的飄忽未定性和能量因子活躍性,使它成為文學藝術創作最具有創造性的核心要素和中心環節。作為以上諸理論的集大成者,“藝術心象”本體論不僅是對這一最具有創造性時刻的理論概括,也為中國古典藝術批評的形象詩學形態的成熟、定型化提供了充分必要的理論資源和實踐依據。
當今文化世界已躬逢一個多元共生的全球命運共同體時代,中國當代藝術批評理論要想與其他文化共同體平等對話、互通款曲,若離開古典藝術創作論這條根基,只落得舉步維艱、寸步難行。因為中國古典藝術創作論最能折射出本民族感性思維方式的本色與特質,它是從中國傳統藝術與傳統文化肌體上生長出來的,承載、基因著自己獨具特色的批評范式及獨特的表達方式,這也是建構當代中國“本土”藝術創作論的永不衰竭的文化源頭與文本資源。具體到具象化的“中國藝術的”本體論詩學,力圖凸顯“中國藝術心象”審美闡釋和文化造型的雙重特質,倡揚在一種跨文化、跨學科、跨文本的間性智慧的燭照下,秉持以審美想象為中心的“社會想象”與以審美文化為中心的“文本再現”的雙重視野來把握中國“藝術心象”這一文本聯合體和想象共同體的構塑流程的[28]。
由此可見,培育高揚中國“藝術心象”主體意識的藝術創作論不僅是中國藝術批評學與藝術哲學自身發展的規律使然,而且已是勢之所趨,同時它還勾聯起當下的社會現實關系,構塑著“自我力量和自我形象內構而成的”主體本身[29]。中國“藝術心象”主體應該是一種活的脈絡,既包涵著生生不息地生成著的文化現實,又把活動個體與生活世界囊括在其中,把“歷史語境”追溯與“文化塑型”展望蘊涵在其中,把個體的生存與社會的生存涵蓋在其中。這不但要求我們重新返回到“生活世界”的“共鳴性”現實體驗,而且要在全球多元境域與“本土”多重資源互動共生的格局中勾聯起今古人文的諸種雜多關系。
一言以蔽之,以詩學視域下中國古典“藝術心象”本體論的現代轉換問題研究為核心論域的古典藝術創作新論是最為直接反映我國古代藝術審美理想與藝術哲學觀念的新銳藝術批評學。作為一種生成中的理論形態,中國藝術本體論詩學必須主動出擊、敞開心扉,去擁抱疊彩紛呈的文化世界和歷久彌新的生活世界。它既要反思藝術批評研究的歷史經驗與藝術傳統,更要積極面對此時此刻的文化社會現實。這一重要文化事件已在世界藝術批評理論史冊上濃墨重彩地書寫了輝煌燦爛的一頁。這已是不爭事實、不刊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