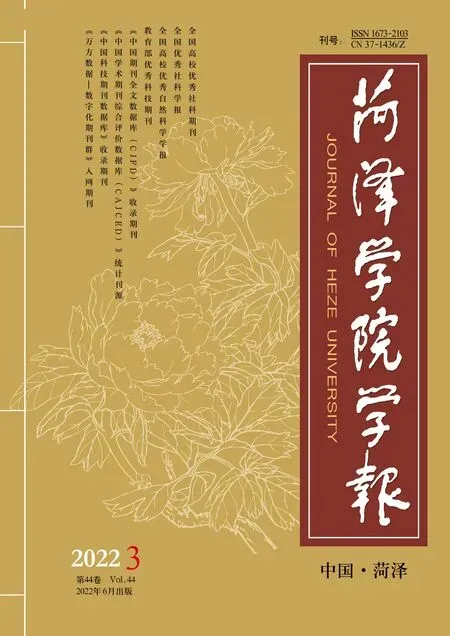后殖民主義視域下《追風箏的人》中的身份認同分析*
陳 紅
(合肥經濟學院外國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001)
阿富汗裔美國作家、后殖民知識分子胡賽尼(Hosseini)創作的小說《追風箏的人》從問世以來便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小說以主人公阿米爾為敘述視角,描述了20世紀后半葉阿富汗戰爭中,一段以種族、階級、性別為要素的關于成長與救贖的故事。國內對于《追風箏的人》的研究集中在主人公阿米爾身上,如學者黃露娜與曲濤通過故事發展的三個階段追溯了阿米爾自我認同的過程[1];學者聶慶娟、劉志冉等人則從倫理角度探討血緣關系引發阿米爾的身份焦慮及血緣回歸[2]。也有探討故事中不同民族、不同階級的人的身份缺失情況的研究,如學者陳玉香[3]、譚娟[4]等人的研究。本文認為,從后殖民主義視角下出發的身份認同并不是傳統阿富汗人身份的回歸,也不是在美國文化影響下的混合型回歸,而是由與仆人哈桑的血緣關系所隱喻的對整個阿富汗民族的認同。胡賽尼通過阿米爾視角傳達了阿富汗并不僅是普什圖人的、上層階級男性的阿富汗,而應該是每個成長于阿富汗的不同種族、不同階級、不同性別的人的阿富汗。
一、身份認同危機的產生背景
(一)戰爭下的社會分裂
阿富汗是亞洲中部的內陸國家,地處伊朗高原的東北部。日本考古學家樋口隆康在其著作《絲路文明》中曾將阿富汗稱為古代東西方的“文明十字路口”[5]。一方面,阿富汗作為東西方貿易、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受到外國侵略;另一方面,由于多部落、多民族、多宗教的社會結構,導致阿富汗各派別擁兵自重、內戰不斷的局面。近代以來,不斷的戰亂更使其成為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近代首先對阿富汗發起侵略的是英國。英國在取得對印度和尼泊爾的控制權后,出于與沙俄爭奪中亞控制權的目的,在1839—1919年間三次侵略阿富汗。由于阿富汗人民不斷艱苦反抗,英國于1921年正式承認阿富汗獨立。20世紀70年代,蘇聯霸權主義開始膨脹,在蘇聯代理人推行的俄化政策遭到阿富汗武裝反對的情況下,蘇聯于1979年出兵襲擊阿富汗。蘇聯駐地與交通線不斷受到阿富汗游擊隊的騷擾,雙方對峙持續到1988年蘇聯簽署《日內瓦和平協議》[6]。
《追風箏的人》展示了20世紀60年代至21世紀,蘇聯入侵與塔利班獨裁統治下混亂動蕩的阿富汗社會。戰爭中的阿富汗隨處響徹著炮彈和機槍的聲音。被遺棄的破舊房屋、布滿彈坑的街道、從廢墟中爬出的無助的人,無不昭示著戰爭的無情,“焚毀的舊俄軍坦克殘骸、銹蝕的傾覆的軍車”,而這樣殘破的景象只在“電視上看過”[7]。無數的生命在戰爭中殞命,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殘破不堪,“廢墟和乞丐,觸目皆是這種景象”,“街頭巷尾都能看到他們,身披破麻布,伸出臟兮兮的手,乞討一個銅板。而如今乞食的多數是兒童,瘦小,臉色冷漠,有些不超過五六歲。”[8]餐館附近被吊起的年輕人渾身是血,廣場上一個男人售賣自己的義腿,伽茲體育館中一對通奸的男女被石頭砸死。
阿富汗戰爭導致阿富汗社會結構的改變,生存環境的變化引發固有社會階層身份認同困難。生活在阿富汗社會性劣位的哈桑將社會對哈扎拉人的認同接受為自我認同,作為忠實的仆人為主人“千千萬萬遍”;而處在社會性優位的阿米爾由于戰爭前往美國,失去了熟悉的主人地位,面臨強調倫理、血緣和親情的伊斯蘭文化與強調理性、自我和個人西方基督文化的沖突。
(二)民族宗教間的沖突
戰爭帶來的文化交融使得阿富汗形成多民族、多教派的復雜社會結構。雖然大部分阿富汗人信仰伊斯蘭教,但是歷史原因導致阿富汗分化出眾多派別,其中以遜尼派和什葉派的矛盾最為突出[9]。阿富汗民族中人口數量最多的是普什圖族,哈扎拉族人口則位居第三。哈扎拉族被認為是成吉思汗及其后人在阿富汗留下的后裔。13世紀上半葉,蒙古占領中亞和西亞部分地區后,留下部分鎮守官員與駐屯軍隊。后來,成吉思汗的孫子孫蒙哥以千戶為單位駐守阿富汗,所以,“哈扎拉”表示的便是“千戶”的后裔[10]。哈扎拉人與東方人相似的黃皮膚、黑眼睛、扁平的鼻梁的長相與高鼻梁、白皮膚的普什圖族、塔吉克族相區別。哈扎拉人在阿富汗屬于下等階層,基本從事苦力和擺攤商販工作。《追風中的人》中對哈扎拉人的侮辱性稱呼,如“塌鼻子”“吃老鼠的”“載貨蠢驢”等,就是哈扎拉人邊緣性身份的體現。阿富汗對哈扎拉人的歧視不僅源于歷史原因,而且受到宗派斗爭的影響。哈扎拉族基本為什葉穆斯林,而普什圖族則屬于遜尼派穆斯林,雖然他們都信奉共同的神(安拉)與先知(穆罕穆德),但教派間沖突十分激烈[11]。
《追風箏的人》中展現了哈扎拉人在塔利班統治和民族歧視下的悲慘境遇。阿塞夫是從小崇拜希特勒的極端種族主義者,在他看來,哈扎拉人不是人,而是阿富汗的垃圾。他曾對哈桑說,“阿富汗是普什圖人的地盤,過去一直是,將來也永遠是”,而像哈桑這樣的“塌鼻子”則污染了阿富汗的土地與血脈[12]。除阿塞夫外,哈桑的鄰居、士兵、阿米爾的老師、風箏比賽中的路人,都對哈扎拉人表現出優越感與歧視。小說結局,身為哈扎拉人的哈桑為了反抗塔利班霸占阿米爾老宅的行徑而慘遭殺害,他甚至沒有機會像阿米爾一樣感受異質文化的沖突。阿米爾父親的朋友辛拉汗與鄰居仆人的女兒戀愛后將自己的感情告訴家人,卻遭到無情的反對,種族與教派成了愛情無法逾越的鴻溝。
二、后殖民主義作家胡賽尼
(一)后殖民主義及其研究者身份
后殖民主義研究的三位代表人物及其代表理論,分別是薩義德(Said)的東方學、斯皮瓦克(Spivak)的身份文化與女性話語以及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民族文化差異。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標志著后殖民主義的誕生。他將東方視為與西方對立的“他者”,與西方的理性、人道、發達形成對照的是東方的混沌、愚昧、落后,西方對于東方的現象與構建體現了一種書寫上的權利關系[13]。薩義德是巴勒斯坦人,曾在英國占領巴基斯坦和埃及開羅時接受過英式教育,后來移居黎巴嫩并在歐洲流浪。斯皮瓦克是美籍印度裔女學者。霍米·巴巴是成長于印度的波斯人后裔,但他后來分別在美國和英國執教。三位研究者都有著共同的混雜性東方身份。英國學者吉爾伯特(Gilbert)在《后殖民批評中》的導論中認為,后殖民主義與后現代主義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后殖民主義和其肇始者的身份有著極為重要的文化性、政治性和地理意義[14]。后現代主義與后殖民主義都是西方文化語境下的思潮,但前者是西方內部發展出的思潮,而后者是肇始主體以西方的結構策略從邊緣向中心進行挑戰的武器。三位研究者的特殊身份決定了他們主動以“他者”身份進入西方學術界,并代表東方或者第三世界向西方中心主義發出挑戰。
相較殖民主義文化批評致力于對非洲本土文化尊嚴的維護,以薩義德為首的東方主義在西方后現代文化思潮下多表現為激進主義,他們高舉東方主義大旗客觀上是為了維護巴勒斯坦和印度本土文化的尊嚴,主觀上則是為了讓自身進入西方文化主流。少數族裔的身份成為第三世界學者進入西方學術領域的敲門磚。西方學者對薩義德的東方主義進行過評論,首先是堅持西方知識和以意志與權利控制世界其他地區的關系;其次是堅持殖民主義話語;最后則是堅持東方主義對中東政治的持續性影響。這對當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關系構成產生實質性影響[15]。因此,無論是從小說作者身份,還是從文化、政治與地理方面來看,用英語寫作的《追風箏的人》可以看作東方主義的文學讀本。
(二)胡賽尼經歷與作品關系
阿富汗裔美國人胡賽尼是典型的流散后殖民作家。1965年,胡賽尼出生于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市,其父為外交官,其母是喀布爾女子學校的教師。小說中阿米爾的母親也被設定為大學老師,名為“索菲亞·阿卡拉米”[16]。1970年,胡賽尼的父親受到委派帶領全家前往伊朗的德黑蘭,三年之后又回到喀布爾。同年7月,由于政權交替和阿明政府上臺,阿富汗的穩定局面被打破,胡賽尼的美好童年至此終結。1976年,胡賽尼的父親前往法國巴黎就職,由于國內政權的混亂,一家人之后不曾回國。1979年,蘇聯侵入阿富汗。一年之后,胡賽尼的父親在向美國申請政治庇護后舉家移民到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圣荷西。小說中的阿米爾也是于1980年與父親一起前往美國加利福利亞的福里蒙特。1984年,高中畢業的胡賽尼就讀于圣塔克拉拉大學的生物學系,畢業之后在加州大學圣地牙哥分校醫學系就讀,并于1993年取得行醫執照[17]。阿米爾的大學專業則是英語,他希望成為作家。
小說中人物的行動是胡賽尼經歷與愿望的投射,小說主人公與作者本人有著不可剝離的聯系。阿米爾想忘卻過去,因而在美國努力奮斗,順利完成學業并成為一名作家。從主人公職業的選擇也可以看到胡賽尼的影子,阿米爾正是胡賽尼想象中的自我。但是即使成為作家,外族身份依舊導致他難以被美國主流社會接納。不僅如此,阿米爾內心對于哈桑的負罪感并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抹去,他想遺忘掉自己的阿富汗身份,但是在辛拉汗告訴他哈桑是他同父異母的兄弟后,他再次踏上阿富汗的土地。阿米爾經歷了從僅認為哈桑為自己的仆人到認同哈桑是朋友的過程,但是真正讓懦弱的阿米爾重新踏上返回阿富汗之路的是他與哈桑的血緣關系。戰爭打碎了阿富汗既有的牢不可破的種族、階級關系,同時讓阿米爾有機會直面何為“手足”的問題。血緣不僅是小說中的倫理關系,也是連接破碎阿富汗的精神性象征。
(三)胡賽尼身份的混雜性
胡賽尼人生中三次離開阿富汗,其中兩次過的是流亡生活,時間跨度讓他不得不與童年的自己告別,而空間移動則讓他遠離曾經的文化語境,成為美國主流文化中的邊緣人。薩義德認為,流亡的知識分子是被放逐者與邊緣人。“流亡是最悲慘的命運之一”,因為流亡者與環境一直處于沖突之中,他們“對于過去難以釋懷,對于現在和未來滿懷悲苦。”[18]流亡并不意味著完全的切斷與孤立,因為對于當代人而言,家鄉其實并非遙不可及。因此,流亡者實際上處于一種“中間狀態”,一方面懷鄉傷感,另一方面又是模仿者或流浪者。霍米·巴巴在其著作《民族與敘事》中提出后殖民意味濃厚的詞語“含混復義”或“模棱含混”,表達了他反本質主義與反文化本真的具有混雜性的批評方式[19]。他在《文化的定位》中還提出“第三度空間”,認為“意義的產生要求兩個不同地方的事物移動到一個‘第三度空間’”,而后殖民主義作家身份“自我”與“他者”的沖突中,二者并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具有混雜性的文化身份。
回歸故土意味著通過距離的縮短,面對過去的、傳統的自我。無論是作者胡賽尼還是其在作品中塑造的眾多人物,都面臨相同的問題,即對于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確認。缺失的民族身份促使流散者不斷反思屬于自己的特定的身份認同。胡賽尼與其他后殖民主義作家一樣,跨文化的混合性思維是他們認知自我與世界的方式。正如霍米·巴巴所主張的一樣,“最真的眼睛也許屬于移民的雙重視角”[20]。當一個人屬于不同的文化并且可以運用多種語言時,那么他就不會被單一的語言和文化所囚禁,而是與單一文化保持距離,進而審視文化與文化中的自我。可以看到,后殖民主義為了給自己的“他者”身份以西方學術中的平等性,以“混雜”“中間狀態”“第三度空間”等強調非傳統、非西方第三種“狀態”。這種混雜性的狀態描述同樣適用于胡賽尼,如果說東方主義滿足了西方理論界對中東的理性認識,那么《追風箏的人》則是西方人在9·11事件后對阿富汗的感性認知。
三、主奴身份認同的混雜
(一)哈扎拉人奴隸身份的認同
阿富汗各民族擁有各異的價值體系與觀念信仰,內部長期存在歧視與斗爭。普什圖族作為阿富汗的主體民族,長期奴役、統治哈扎拉族。在塔利班統治時期,當權者更是實行殘酷的種族歧視政策,由此導致大量無辜的哈扎拉人被殺害。阿米爾的仆人哈桑便是哈扎拉人的典型代表,哈桑沒有受教育權,甚至連基本的生存權也無法得到保障,而他最終也死于殘忍的種族屠殺。小說中對于哈扎拉人沒有正面的描述,但哈桑“斜如竹葉”的雙眼、大而平的鼻子和兔唇,哈桑的父親哈里則是個丑陋的瘸子等,仿佛哈扎拉人就是殘缺、丑陋的人。而與“塌鼻子”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普什圖人索拉雅高挺的鼻子,這也是阿米爾對心愛女人的最重要的記憶點。
哈桑純潔善良且寬厚,擁有許多優秀的品格,但由于種族原因,他沒有機會讀書認字,只能作為社會底層,遭受阿米爾的嘲笑與其他普什圖族人的羞辱。即使在他成家后,當妻子受到塔利班成員的毆打時,他也無法維護妻子,最終慘死在恐怖分子手中。雖然哈桑的真實身份是阿米爾同父異母的兄弟,但是由于哈桑母親是哈扎拉人,種族間的矛盾導致勇猛果敢的阿米爾的父親也不敢承認哈桑的身份,直到哈桑去世。哈扎拉人從來沒有懷疑過歷史和宗教賦予其的“奴隸”地位,為了主人,哈桑可以付出“千千萬萬遍”。
阿米爾是哈桑的主人,同時哈桑也把阿米爾當作自己的兄弟與朋友。他在任何情況下都愿為阿米爾挺身而出,在為阿米爾追逐最后一只風箏的時候,哈桑寧愿被阿塞夫強暴也要守護風箏,幫助阿米爾贏回父親的喜愛。黑格爾(Hegel)在主奴辯證中提出,自我意識只有在另一種意識中才能得到滿足,即只有通過與其他意識的對峙,人才能發展自我意識。黑格爾認為奴隸具有創造性,他們可以通過制作與發明產品,在勞動中獲得自我意識與人格獨立。作為“邊緣人”的哈桑在主奴意識的對抗中并沒有選擇抗爭,而是接受自己的“奴隸”地位,選擇討好主人。從后殖民主義角度來看,哈桑行為固然有其忠誠的一面,但也包含哈扎拉人長久以來對普什圖人所施加的奴役的接受,他將主人看成朋友的行為并不能排除心理上渴望階級躍升的可能性。當然,阿米爾面對哈桑被阿塞夫凌辱時的逃避也不能僅僅歸結為小說作者所描述的懦弱,“我從來沒有認為我與哈桑是朋友”,“我是普什圖人,他是哈扎拉人,我是遜尼派,他是什葉派,這些沒有什么能改變”[21],“他只是哈扎拉人”[22]。暴戾的阿塞夫本身就是謹守階級和種族傳統的舊阿富汗社會象征,他曾經說過阿富汗是普什圖人的阿富汗。因此,阿米爾的逃避也可以解釋為作者對哈扎拉人阿富汗人身份的逃避。不過這種傳統的阿富汗人的身份隨著蘇聯侵略、阿富汗內戰以及父親秘密的暴露而漸漸瓦解。
(二)普什圖人主人身份的轉變
《追風箏的人》中移民美國的阿富汗人都是富有的普什圖人,而作為社會底層的哈扎拉人只能留守在阿富汗,哈桑就被拉辛汗從哈扎拉人聚集區召回看管阿米爾的宅院。戰爭逃難令曾經身為主人的普什圖人不得不面對身份與地位的轉換。阿米爾的父輩作為第一代移民的身份認同首先來自根深蒂固的阿富汗伊斯蘭文化與美國基督教文化的沖突;其次來自從文化中心到文化邊緣的社會地位的移動,即由主人被迫轉向奴隸的沖突。他們希望通過否定美國文化來尋求逝去的自我,小說中以阿米爾的父親和塔赫里將軍為典型代表。
小說中阿米爾的父親出生于經濟優渥的家庭,是喀布爾首屈一指的商賈,娶的妻子也是貴族的女兒。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前,阿米爾的父親是擁有極高社會地位的風云人物。蘇聯入侵后,他帶著阿米爾歷經艱險,前往夢中的美國。在父親看來,除了英國和以色列之外,只有美國才算的上“真正的男人”。但是當他真正來到美國后,真實而異質的美國生活讓他無所適從。自然環境不夠自然與純凈,無法順暢交流,且固執地拒絕學習英語,只能從事卑微的底層工作,恪守制度的美國文化與遵從信義的阿富汗文化產生沖突。在喀布爾,他們“折斷樹枝,拿它當信用卡”,支付支票也不需要檢查身份證[23],因而,美國對于阿米爾的父親“是個哀悼過去的地方”[24]。與父親的悲戚形成對照的是塔赫里將軍,他期待阿富汗解放而被征召服役來否認美國文化。塔赫里將軍在到了美國后也不愿意從事與自己身份不匹配的工作,而是選擇穿著灰色套裝領著救濟金過活。他唯一的興趣是在圣何塞巴利雅的二手市場與阿富汗朋友聊天,這里不僅是進行商品交易的空間,而且是阿富汗人尋找共同文化記憶的空間。阿米爾父親的失落與塔赫里將軍的期待都是對過去主奴地位中優勢位的懷念,缺少哈扎拉人對他們主人身份的認可,他們只能淪落為劣位的奴隸。
作為第二代移民的阿米爾而言,“美國是個埋葬往事的地方”[25]。美國可以讓他遺忘對哈桑的背叛,可以擁有父親全部的愛。他積極地為適應美國生活而努力,高中順利畢業后進入大學研修英文并以寫小說為職業。雖然阿米爾的美國生活如魚得水,但是阿富汗文化規范并影響著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阿米爾身份認同的焦慮產生于前往阿富汗對哈桑兒子索拉博的營救。在美國人眼里,他是阿富汗流浪作家;在阿富汗人眼里,他是回鄉變賣家產的美國人;在塔利班眼里,他是在祖國危難時的叛逃者。但無論如何,血緣關系讓他不得不面誰是阿富汗人的問題。血緣不僅是倫理關系,而且隱喻著戰爭后阿富汗各民族間的連帶關系。正如拉辛汗告訴阿米爾的一樣,身為典型的阿富汗男人的爸爸“是被拉車成兩半的男人”,一半是被社會承認的合法的部分,但卻令人疚恨;另一半則是沒有名分和特權的一半,但卻高貴純潔[26]。阿米爾父親的兩面性正說明了阿富汗民族的復雜性,缺少了誰都不再是完整的阿富汗。由此,阿米爾的身份認同從普什圖人上升為真正意義上的阿富汗人。
戰爭不僅打破了阿富汗人平靜的生活,而且打破了維持多年的社會結構。胡賽尼的小說《追風箏的人》通過主人公阿米爾表現了流亡海外的阿富汗知識分子在經歷文化沖突、優勢位到劣勢位的轉換和如何重建國家時,不得不面對自身混雜的離散性身份與誰為真正的阿富汗人的問題。不論種族、階級與性別,也不論保守與激進,成長于阿富汗并受到阿富汗文化熏陶的人都是阿富汗人,被拯救出阿富汗的少年索拉博將成為未來阿富汗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