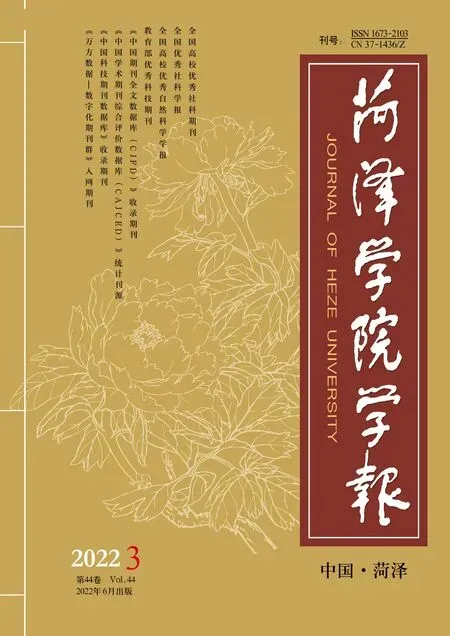《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中的關目評點思想*
周姝岐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李卓吾視《水滸傳》為“古今至文”[1],肯定小說文體的地位,并積極投身小說批評實踐。他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左右完成《水滸傳》評點,開《水滸傳》評點之先河,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的文人評點由此發端。隨后,容與堂書坊聘請文人在李卓吾《水滸傳》評點本的基礎上模仿、增改、擴充、定型,使其成為完整的《水滸傳》評點本,并于萬歷三十八年(1610)刊刻了《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這一評本雖是偽作,但其中之精神血脈仍然是李卓吾的[2]。
該本評者在批點過程中使用了許多諸如“關目”“關節”等評點術語,單“關目”一詞便出現21次之多,指向關目的批語則更多,創造了豐富的關目史料。“關目”是萬歷年間戲曲批評家們熱衷于使用的有關戲曲情節結構批評的術語,它“一般指戲曲情節的安排和結構處理”,“有時也指戲曲的情節故事或情節的關鍵部分”[3]。評點家將這一戲曲術語移用至小說評點,其對小說情節之“真”“趣”的審美追求以及對伏應、刪減等結構安排的巧思極具評點價值,因而得到了學界的關注。但美中不足的是,學者們對其批評的研究雖有涉及,但至今尚未有系統的專門論述。本文擬結合此評本中的關目批語,深入探析其中所蘊含的關目評點思想。
一、審美基礎:“真”與“趣”
重視情節的審美因素,是中國小說美學的重要特征[4]。該書批評者之審美思想可分為兩方面,即尚“真”與崇“趣”。
(一)尚“真”
李卓吾本人的思想是此評本的重要來源。他所提出的“童心說”[5]在本質上是真實論,即提倡發自真心、真實自然的文學作品。在《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中,評點家基本承繼了李卓吾的尚“真”思想,關注情節的真實性。
評點者在評點時融入了“畫工”與“化工”這兩個概念,它們屬于真實論的范疇。李卓吾曾評“《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他認為“畫工”是指由人之筆力所描繪出的逼真境界,即人工,而“化工”則是“能奪天地之化工”,指自然真實、不露雕飾痕跡、出神入化之境界。“畫工雖巧”[6],卻無法與“化工”這等自然之工比肩。評點家借用這兩個概念來衡量小說情節真實性。第十三回,作者著力描繪楊志與周謹、索超的打斗場面,以刻畫其不同面貌。接下來,作者使用“出神入化手段”,即“化工文字”[7],引出劉唐這一人物,情節過渡得自然巧妙。之后,他又評第七十六回“是一架絕精細底(的)羊皮畫燈”,屬“畫工之文,非化工之文,低品,低品!”[8]此一回包含大量對于旗幟、陣勢、將領等的鋪敘,描繪精細但無神采,得到了評者的否定評價。“畫工”與“化工”在評者心中的地位高下立見,此二者不僅貫穿于其評點之中,且和李卓吾本人的評判一脈相承。
評點者所推崇的真實是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辯證統一。他稱贊作家將假事寫得逼真的藝術手法,認為《水滸傳》妙處在于“事節都是假的,說來卻似逼真”[9],以及“《水滸傳》文字原是假的,只為他描寫得真情出,所以便可與天地相終始。”[10]依其所見,文學作品只須呈現“逼真”效果,符合人情即可,此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其“假事真情”理論。
該評者從情理角度嚴格審視小說情節、情境,針對事件的呈現效果進行評價。他認為“其(《水滸傳》)妙處,都在人情物理上”[11],贊賞符合生活邏輯與人情物理的情節。如宋江潯陽樓上題反詩一回,宋江因吃魚而腹瀉不已,因此在潯陽樓上點肉食時“魚便不要”,合理生成點菜關目,評者稱贊道:“是何等照顧,直恁聰明。”[12]接下來,在酒精催動下,宋江的反叛情緒不斷生發,達到頂峰之時,他趁著酒興,在墻壁之上題下反詩。作者精心描繪,使其行為合理發生,將此關目敘寫得“光景欲真”[13],得到了評點者的肯定。
評點者亦基于情理角度進行思考,為部分情節賦予合理性。如宋江救了劉高之妻,沒換回其感恩之心,反被她誣陷為之前強擄她的賊寇。站在常人的角度來看,宋江好心救人反為自己招來禍端,實不劃算。評點者卻轉變思路,指出救人情節對宋江形象的重要性,為其不計后果的義舉賦予存在的合理性:“今人只看后來事體,便道宋公明不該救劉高妻子,殊不知宋公明若無這些,直是王矮虎一輩人了,如何干得許多大事?彼一百單七人者,亦何以兄事之哉!”[14]又如第九十一回批語:“人說宋江人馬到征方臘時,漸漸損折,不知此正是一百單八人幸處。不但死于王事為得死所,倘令既征方臘之后,一百單八人尚在,朝廷當何以處之?即一百單八人,亦何以自處?”[15]評者從現實的角度分析宋江等人于戰中傷亡情節存在的必要性:一方面,在戰爭之中,刀劍無眼,諸位將士即便武藝高強也難保能夠全身而退。另一方面,梁山兄弟人數較多,如若人員沒有減少,便會在朝廷中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且其之前的“強盜”身份勢必會為他們招來災禍,因此,宋江人馬逐漸折損才符合常理。
對于小說中虛假失真、違情違理之處,評點者在批點過程中亦將其一一指出。如第六十五回“文字極不濟”,一者,張順隨安道全至李巧奴家,恰巧在她家見到之前搶走其金子并將其推進江里的張旺,欲殺張旺,卻殺李巧奴家四人,評點者對此提出質疑:“那(哪)里張旺便到李巧奴家?就到巧奴家,緣何就殺死他四命?不是,不是。”二者,“王定六父子過江,亦不合便撞著張順。張順卻緣何不渡江南來接王定六父子?”在他看來,雙方偶遇得太過巧合,不如安排張順前去接王定六父子,使雙方自然相遇。作者刻意追求奇巧效果而忽略了情節真實性,故“都少關目”[16]。第九十回中亦存在與現實不符的情節。宋江等人面圣,皇帝命光祿寺大設御宴,但現實中,此類事情實難出現。一國之君設宴款待一群強盜,屬實不合情理。評點者對此提出懷疑:“強盜安得如此遭際”,并連言“不可信,不可信”,建議“刪之為是”[17]。
自古以來,我國便有著崇實的文藝思想傳統。司馬遷以秉筆直書為著史之標準,追求“不虛美、不隱惡”[18]的“實錄”精神,這一觀念對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影響深遠。至明代,《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的評點者對小說藝術本質產生深刻認知,直面小說虛構事實,明確指出小說情節出自虛構的性質,這一觀點突破了傳統“實錄”觀念的桎梏,具有進步意義。此后,小說虛構的本質成為學界共識,學者們在“真實”與“情理”方面不斷生發觀點,后世馮夢龍的“事贗而理亦真”[19]之論,金圣嘆評點《水滸傳》時所提出的“因文生事”[20]說,以及張竹坡所論“做文章,不過是‘情理’二字”[21],皆可視為該評點者思想的發展,其真實論觀點在中國小說理論史上具有奠基性作用。
(二)崇“趣”
“趣味是藝術作品和情調的表現。藝術作品若沒有趣味,便會讓人興致索然。”[22]“趣”是古代文學家們品評作品的重要審美標準之一,亦是該書評點者審美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
該書評點者崇“趣”之舉或源自于李卓吾哲學思想之啟發。李卓吾曾在《寄京友書》中明確指出“自娛”的創作目的:“大凡我書皆為求以快樂自己,非為人也。”[23]他以獲得自我滿足感為旨歸,崇尚關目的趣味性。評點家繼承了李卓吾的評點旨趣,在評點《水滸傳》時多次以“趣”批之。其標舉之“趣”,可理解為由作品情趣所產生的藝術感染力[24],其內涵主要包含以下兩方面:
一是情節之詼諧幽默,趣味盎然。第二十七回,孫二娘命伙計將武松拖走,店小二們拖行未果,孫二娘怒斥其無用。然而待她親自動手時,卻被武松的實力完全壓制,發出殺豬似的嘶喊聲,這種強烈的反差生出無限趣味,頗具喜劇色彩,評點者評此“趣絕”[25]。再如第七十四回,李逵到壽張縣縣衙,先將知縣嚇跑,后冒充縣官判案。這位“風流知縣”[26]辦案時不按常理,放了打人的人,卻枷了挨打的人。這一關目趣味迭起,評者先后共批七個“趣”[27],稱此為“千古絕唱”[28],可謂對此推崇備至。
二是讀者在閱讀中所獲得的心理快感。作者為突出忠義主題所設置的快意恩仇、除暴安良情節亦具有“趣”的審美效果。評點者以能否獲得審美愉悅為評判尺度,致力于挖掘小說中能夠滿足讀者情感需求的情節。如第九回,在魯智深護送林沖去滄州的途中,兩位公差淪為侍從,而林沖卻在趕路途中過得有滋有味,評點者連批“妙”[29]“更妙”[30]。魯智深到來之前,林沖受盡欺辱,甚至差點被殺,但自他來后,局面反轉,公差們為保命而做小伏低,甘當苦役,評點者為之感到暢快,不由贊嘆道:“妙絕,快絕。”[31]又如小說第十回,林沖發現陸謙等人的陰謀后,先了結了差撥和富安,但殺陸謙時卻不似這般干脆,作者對林沖手刃陸謙的過程詳加描繪。評點者不禁評道:“殺得快活,殺得快活!若如那兩個也一槍戳死,便沒趣了。”[32]其拍手稱快之形象躍然紙上。他并非因喜愛殺戮方覺有趣,而是為林沖手刃仇人的行為感到痛快。在死板僵硬的假道學盛行于文壇的背景下,該書評點者以閱讀趣味為先,這一理念突破了“文以載道”傳統律條的束縛,為當時的學術界注入了新鮮血液。
該評點者對富含真實性與趣味性的關目贊嘆不迭,同時,他對二者的關系有著深刻認識:雖然情節需符合生活邏輯與情理,但卻不能以刻板的標準去衡量它,當“真”與“趣”產生矛盾、不可兼備之時,“真”應當服從于“趣”。關于李逵獨劈羅真人反被懲罰一事,有一村學究曾言:“李逵太兇狠,不該殺羅真人;羅真人亦無道氣,不該磨難李逵。”評點者并不認同這一觀點,對此批評道:“此言真如放屁,不知《水滸傳》文字,當以此回為第一。試看種種摩寫處,那(哪)一事不趣?那(哪)一言不趣?”他認為“天下文章當以趣為第一”,因此不必“一一推究”[33]情節,而應以能否給讀者帶來審美愉悅來判斷情節內容的價值高低。評者所推崇的“真”與“趣”是其關目評點思想的審美基礎,二者并非敵對關系,而是相得益彰,共同展示其關目美學思想。
二、結構安排:“嚴密”與“緊湊”
小說屬于敘事文學,情節是其基本要素[34]。如何安排情節以及如何將各情節聯結得自然嚴密是該書評點者極為重視的問題。他基于結構視角,提出“密”之標準,即敘事之嚴密和行文之緊湊。
(一)伏應之美
伏與應是古代文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指后邊出現的人物和事件前邊要有伏線,前邊出現的人物和事件后邊要有交代,有呼應[35]。毛宗崗“隔年下種,先時伏著”[36]之論,金圣嘆所提出的草蛇灰線法[37],皆屬伏應。在此之前,該本批語中便已透露出伏應思想,《水滸傳一百回文字優劣》中言《水滸傳》“照應謹密”[38],這一觀念亦體現在具體情節的評點文字中。
一方面,評點家對各情節間的伏應關系十分贊許。如第十回,大雪壓倒了林沖的草屋,林沖“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評點者以“密”[39]字批之。大雪足以撲滅火盆這一細節暗伏后文,表明后來草料場著火是有人蓄意為之,而非意外,所以批評者為此情節之嚴密而稱道。又如第九十回,燕青欲進城賞燈,李逵意欲同去,燕青卻恐李逵再生事端,照應前文“李逵元夜鬧東京”之事。李逵向其保證不再生事,評點者念及前事,連連提醒道:“也信他不得。”[40]“忘卻已(以)前李師師家故事了么?”[41]這一評點觀念有利于展示故事的前因后果,啟示讀者體會小說結構之嚴謹細密以及首尾貫通的美感。
另一方面,該評者從反面論證伏與應的重要性,指出前后矛盾之處。第二十三回,在宋江與武松見面的情形時,柴進“誤稱”宋江為“宋押司”,宋江因此在武松面前暴露了身份。事實卻并非如此,上一回末尾,柴進便有意引導武松猜出宋江的身份。評點家以整體性視角審察前文,批道:“與前不應”[42]。被批評之處還有第五十回,祝朝奉稱石秀便是燒他店屋之人,但實際上,他并不知曉此事是石秀所為。評點者道:“擾攘之中那(哪)里就知是石秀?況且燒了店屋,亦未必便曉得是石秀。”他批評作者“只為太密不漏,所以關目便不像了。”[43]作者為照應前文石秀燒屋關目,刻意安排店家指認石秀這一情節,卻忽視了祝朝奉這一人物視角的限制,致使此處情節與前文矛盾。可見,邏輯嚴密需建立在情節之嚴絲合縫的基礎上,不容疏漏。
(二)去繁從簡
繁與簡是我國古代文論的常見命題,該評點者繼承古文論“簡要”之標準并將其應用于小說評點。在他的《水滸傳》評點中,這一理念體現如下:
他主張刪除冗雜的情節。“宋江智取無為軍”一節中,宋江率領眾兄弟投奔梁山泊,其間穿插著兩段關于坐船人員安排的關目,此二段列舉致使關目呈現繁復之貌,因此“可刪”[44]。又如第九十回中,宋江與盧俊義就機遇與能力何者更為重要而爭辯,評點者認為“此段雖閑適有趣”,但“畢竟無謂”,因此“刪之為是”[45]。諸如此類于情節發展無益、甚至影響情節敘述的關目為其所厭,故往往被他拈出并建議刪去。
對于部分具有重復性的內容,他亦予以指出或建議刪除。第二十四回,西門慶欲與潘金蓮茍合,王婆言他須得滿足“潘”“驢”“鄧”“小”“閑”五項要求。西門慶稱他符合這五項標準,并將這五項標準重復一遍,評點者認為“說出便無味,亦沒關目。”[46]因而可“刪”[47]。又如第三十一回,武松回想起自身坎坷的命運:“止(只)有一個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負(甫)能來到這里,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評家認為這一安排“多”[48]。武松是小說的主要人物之一,自“武松打虎”至“大鬧飛云浦”,前文已花費八回篇目講述其身世,讀者對其遭遇已十分了解,此關目并無存在價值,實屬多余之舉。
刪除重復的、無關緊要的情節有利于避免篇幅冗長、散漫拖沓的弊病。評點者崇尚文字簡凈、關目緊湊之美,從小說結構藝術角度對情節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訂。從評點形態來看,他并未真正修訂其中情節,而是在不滿意之處施以擬刪符號,刻上“可刪”字樣,通過符號與批語表達刪改意愿。其刪改理念推動了評點體制的變異,為后世小說評改形態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敘述節奏:“張”與“馳”
敘述節奏在敘事效果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其改變可以造成或加劇敘述中波瀾起伏、情勢變化的審美效果[49]。該批評者指出《水滸傳》在敘述節奏方面達到了以下兩種效果:
(一)曲折有致
情節之轉折伸縮能夠引起敘事節奏的改變,使情節產生跌巖起伏的藝術效果,進而造成讀者審美感受的變化,故而引起了評點者的關注。
其一,重視情節之轉折。第三十五回敘寫宋江率眾人投奔梁山泊之事,作者卻在途中安排石勇送家書情節。宋江得知父親亡故后,急忙趕回家奔喪,評點者評道:“此回文字不可及處,只在石勇寄書一節。若無此段,一同到梁山泊來,只是做強盜耳,有何波瀾,有何變幻。真是不可思議文字。”[50]此一關目使得情節發生突變,打破了讀者們的心理預期,令原本平順的情節忽起波瀾。金圣嘆承襲此論,評道:“一路寫宋江部署眾人投入山泊,讀者莫不拭目洗耳,觀忠義堂上晁、宋二人如何相見也。忽然此處如龍化去,令人眼光忽遭一閃,奇文奇格,妙絕,妙絕。”[51]又如第四十四回,石秀以為楊雄一家閉店是因懷疑自己貪污,故向潘公辭行,潘公卻問:“叔叔何故出此言?并不曾有個甚事。”評點家為此情節點贊,認為“此處亦都有關目。”[52]潘公知曉其意后,便述說事情原委:為給潘巧云前夫做功果,故而暫時不做生意。作者先敘誤會,后作解釋,轉折極妙,使情節跌宕起伏。
其二,認為敘事不宜平鋪直敘,而應曲折伸縮。如第七十八回回評:“《水滸傳》文字不可及處,全在伸縮次第。但看這回,若一味形容梁山泊得勝,便不成文字了,絕妙處正在董平一箭,方有伸縮,方有次第,觀者亦知之乎?”[53]項元鎮假裝敗陣,以暗箭偷襲董平,射中其右臂。在此之前,梁山起義接連大勝,但《水滸傳》之妙處卻在于董平中箭之變,正如此本之批語所言:“一味形容梁山泊得勝”有平淡乏味之嫌,勝中有敗的“伸縮”之法方能造成敘事的波瀾,營造曲折之美。又如第七十九回,張清以一石子將梅展打得鮮血迸流,緊接著,張開一箭將張清戰馬射倒在地,逼得張清執槍步戰,評點者認為“一勝一敗,都有伸縮,妙,妙。”[54]不僅如此,“這回文字沒身分(份),敘事處亦欠變化”[55]“敘處卻沒伸縮變化,大不好看”[56]等評價皆是其提倡情節伸縮變化之論。
(二)點綴之妙
“閑文”是該評點者基于文法觀念所提出的概念,是“閑筆”理論的初級形態。葉朗認為“閑筆”這一概念最早由金圣嘆所提出,金圣嘆將《水滸傳》“血濺鴛鴦樓”一回奉為使用閑筆的典范[57]。而早在此評本中,“閑筆”的理念便已經初步形成,只是尚未形成系統的理論。
該本評者十分關注閑文內容,推崇閑筆手法。以“楊志比武”關目為例,評點者注意到此回目中兩次閑筆手法的運用。第一次是楊志與索超比箭關目中,作者由展現二人比武過程轉入對梁中書挪位置的描寫,使得讀者于緊張氣氛中稍獲喘息之機,屬實是“閑處都不放過,神手,神手!”[58]在此之后,又以“紅旗”“金鼓”“炮”等意象轉入二人對戰的激烈場景,雙方對戰五十余回合都未能分出勝負,作者便將筆觸轉移到觀眾們那里,從看臺上旁觀者的角度表現二人的武藝高強,就連經驗豐富的軍官與將士們都喝彩不迭,評點者贊以“好點綴”[59],肯定此處閑文之作用。通常來說,敘事節奏應當有張馳與變換,長時間出現緊張的比試場景會使讀者長期處于緊張的情緒狀態中,進而產生審美疲勞。由于閑文內容的參與,情景突然轉換,緊張的形勢稍稍緩和,情節發展出現冷熱交替的特點,從而變得精彩紛呈,滿足了讀者的審美心理。同樣的例子還有“三打祝家莊”中對于扈成前途的介紹:“后來中興內也做了個軍官武將。”李逵血洗扈家莊,其所見之人皆被砍殺,作者“忙里偷閑”[60],在如此血腥的氛圍中插敘扈成這樣一個小人物的好結局,有“節外生枝”之美,悄然緩和殺戮給讀者帶來的血腥感。
“閑文”這一概念與法國敘事學家巴爾特所提出的“衛星”事件有異曲同工之妙。巴爾特按照情節的重要程度,把意義小一些的事件稱為“衛星”事件[61],“閑文”亦如是,它與“正文”相對,雖意指非中心情節,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既閑也不閑,負責補充、豐富、完成正文內容,使之豐滿和具體。
“文似看山不喜平”,敘述節奏在調節讀者審美心理方面起著獨特作用,是敘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該書批評者此方面的論言具有啟蒙意義,不僅為“閑筆”這一文法技巧提供理論支撐,更對后世小說敘事理論的發展起著引領作用。金圣嘆提出的“舒氣殺勢”[62]筆法、張竹坡對“穿插”[63]技巧的總結等皆是就敘述節奏方面生發出的理念。
總之,此書批評中雖未形成系統的關目理論,但該書批評者實際上已經提綱挈領地向我們展示了《水滸傳》的關目藝術,許多關目理念已然萌芽,《水滸傳》的關目研究由此發端。其作為早期評點者能夠有如此精辟的見解,這本身便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對后世更是影響深遠。其一,此評本為后世批評家提供了一些《水滸傳》的關目論題,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批評家們對《水滸傳》關目的思考,其啟示之功不可磨滅。其二,此評本之關目批語對后世評點本有著借鑒意義。作為第一部《水滸傳》評點本,其關目批評思想較為前衛,其評語難以避免地被其它評點本沿襲或改用,對推動“關目”術語的流行有著積極意義。其三,該批點者擬刪符號的使用以及刪改意愿的表達對評改形式的形成亦有著推動作用。該評本的關目之評意蘊豐厚,其“假事真情”“趣為第一”等關目批評思想是中國古代小說批評史上璀璨奪目的一環,值得我們給予更多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