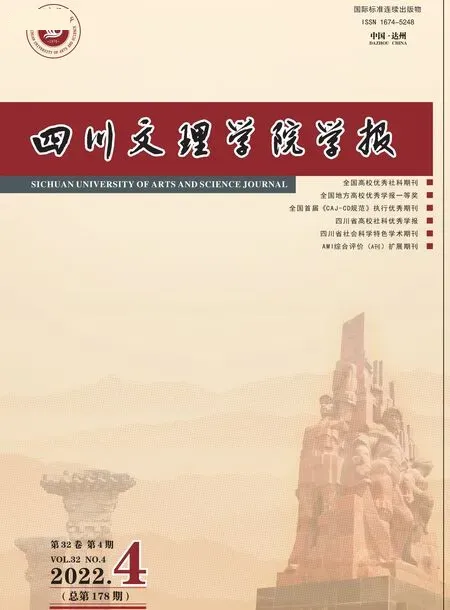《回聲制造者》中的后現代身份建構
趙燕嬌
(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北京 海淀100871)
當代美國著名作家理查德·鮑爾斯(Richard Powers, 1957—)是繼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和唐·德里羅(Don DeLillo)之后新興的“X一代”的后現代小說家的領軍人物,被譽為“后品欽時代的代言人”和美國“最有前途的小說家”。在其十余部文學作品中,榮膺美國全國圖書獎的《回聲制造者》(TheEchoMaker, 2006)是一部典型的融合了環境保護、生態學、倫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等多專業領域知識的信息小說,也是一部“集推理小說、神經科學案例研究與生態小說于一體的鴻篇巨作”。[1]在鮑爾斯筆下,沙丘鶴是人類先祖與過往文明在當下社會的現實回音,是歷史事實在現實記憶的傳聲筒,它們表現出超凡的記憶力,隱喻我們人類對過去理應保有的認知態度;而“雙重錯覺綜合癥”這一罕見病癥則影射后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個體認知分裂和記憶錯位現象,作者巧妙地將人類古老文明化身的沙丘鶴這一意象與“雙重錯覺綜合癥”這一后現代社會的醫學頑疾串聯起來,通過對兩者之間錯綜復雜關系的有效編織,鮑爾斯得以不斷追問并反思,“我們是誰?我們認識誰?我們又不認識誰?我們如何構建一個看似可靠的,連續的,整體的自我,即使它有時并非如此?”等一系列生存哲思。[2]實際上,罹患“雙重錯覺綜合癥”的患者并非沒有記憶,只是患者的大腦中只保留了特定的記憶片段,遺忘的恰是與親人建立情感關聯的那一部分,換言之,患者對情感認可的缺失遏制了記憶的理性組合,“理智與情感”在后現代虛幻現實的“荒原”中失去了平衡,為此,“何時需要記憶,何時不如遺忘”,圍繞記憶與遺忘這一宏大主題,鮑爾斯引入對個體認知分裂、記憶錯位、精神異化、情感無能等后現代社會人類普遍存在的生存現象的憂思。
在《回聲制造者》中,鮑爾斯獨具匠心,借用隱喻、互文性和對位敘事策略等文學創作手法,借助想象,以面臨家園破壞和種族滅絕的沙丘鶴沿內布拉斯加州普拉特河的年度遷徙與圍繞主人公馬克的車禍懸疑案為兩條敘述主線,借罹患“雙重錯覺綜合癥”的“精神病人”馬克的不可靠敘述、卡琳作為“正常人”的可靠回憶與“認知神經學專家”韋博對科學研究與醫者仁心的辨證認識這三個敘事視角,互相交織,貫穿全文,生動再現了后現代視閾下人類的生存焦慮狀況,傳達出鮑爾斯強烈的生態憂患意識與對后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人與家園以及人與過往文明之間疏離現象的反思,飽含作家對由此帶來的個體認知分裂與身份認同危機的文學關切。鮑爾斯筆下的主人公徘徊在記憶與遺忘、情感與淡漠、以及背離故土與回歸家園的夾縫中,最終,他們在感性與理性之間尋找平衡,返璞歸真,重新定義自我,選擇回歸家園擁抱承載人類先祖文明的故土,實現了個體身份在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歸屬,同時,三位主人公的身份建構之旅也照見了后現代社會人們應保有的生存法則和生活智慧,表達了作者對生活在虛幻現實中的人們如何在“孤立的個體之間尋求聯結”、進而重塑自我、認識他人和建構自我身份的思考。[3]
一、身份危機:記憶的碎片與重組
虛幻現實或真實感的喪失是后現代文學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后現代文學研究者杰姆遜認為,生活在后工業社會的人們,因為類象的大規模生產和復制,類象與真實之間的界限變得異常模糊,人們逐漸失去了對現實真實的認知,眼前所見都是對現實重復刻制的虛假的影像,正如作品中的三位主人公,均生活在虛幻現實帶來的錯覺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淪落為后現代社會網絡、通訊等高科技技術操控下“聊以自欺”和“愚弄他者”的符碼,整日為滿足“虛假的需要”而機械地奔波忙碌。法蘭克福學派左翼代表人物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對這一后工業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畸形供需關系的分析極具見地,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為了特定的社會利益而從外部強行施加于個體身上的,使艱辛、侵略、痛苦和非正義恒久化的需要,是‘虛假的需要’。”[4]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的選擇不再出于內心真實的需求,而是為了滿足虛幻社會的期待,并于潛意識中理所當然地認可其存在的合法性,致力于追求物質、名譽、利益和機會主義等帶來的快感,最終,“依附于現有的制度和秩序,悲哀地實現了人的本能需要與社會需要之間的‘虛假的統一’。”[5]
鮑爾斯筆下的“雙重錯覺綜合癥”,既是對生活在虛幻現實中的人們普遍存在的心理頑疾的隱喻,又是對后現代社會和資本主義制度催生的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等生活常態的影射。在《回聲制造者》中,鮑爾斯對當代美國社會的物質至上主義和極端享樂主義等集體病態深具洞察,對后現代社會給人帶來的身份危機、精神異化等現象的分析鞭辟入里。小說中的三位主人公(馬克、卡琳和韋博)生活在物欲膨脹的后現代社會,他們深受人類中心主義和物質至上主義的侵蝕,專注于各類通俗廣告和大眾媒體的教唆,被各種低俗的快餐文化和琳瑯滿目的商品沖昏頭腦,追求庸俗的物質主義,背井離鄉,沽名釣譽,最終,其鮮明的個性和迥異的性格也在后現代社會大熔爐的打磨下逐漸失去了棱角,成為鮑爾斯對病態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精神異化現象展開抨擊的代表。
主人公馬克是后現代虛幻社會中被物質至上主義侵蝕而致精神異化的典型受害者。車禍發生前,他專注于研究各種各樣的賽車比賽等刺激性質游戲,淪落為現代宣傳媒介和娛樂方式的忠實粉絲,對各式印有美女畫像的海報和流行音樂情有獨鐘,甚至陷入電子產品和通訊網絡帶來的虛幻快感中無法自拔,在毒品、搏斗、血腥和廝殺的電子游戲中虛度光陰、消耗著生命,“一種新游戲馬克能夠連續玩24個小時,甚至都不起身上廁所”,[6]136正如生活在內布拉斯加州小鎮上的居民所說的,即便不是因為車禍,馬克“也會遭遇類似的禍事”,[6]169這是對馬克紙醉金迷、渾渾噩噩生活方式的詬病,也是對以馬克為代表的一類人的生存狀態的批駁,更是對他所處時代的虛幻性的最有力控訴。
車禍發生后,罹患“雙重錯覺綜合癥”的馬克失去了識別親人身份的能力,誤認為自己在世上的唯一親人是被機器人特工所取代,隨著病情的惡化,他逐漸對自己身邊的其它事物也產生了懷疑,認為他的家鄉、住宅和愛犬也是被匿名頂替者所代替。馬克由對親人身份的懷疑逐漸發展為對周遭一切的否定,某種意義上,對他人身份的不認同也就意味著他對自我與他人關系的否定,因而也是對自我身份的否定。雖然,姐姐卡琳等人想盡辦法試圖幫助馬克找回對過去的記憶,但是,記憶錯位的馬克“始終無法將自己的過去與現在融為一體”,[7]同樣,Jenell Johnson分析道,“馬克的病癥在于他無法將現在的自己與過去的自己等同看待,而那個過去的自己正是通過與周圍的人建立社交關系而得以建構的。”[8]換句話說,“雙重錯覺綜合癥”徹底割裂了馬克與過去的聯系,改變了馬克對自己與他人關系的認知,使他陷入對他人身份和自己身份定位的雙重認識危機中。鮑爾斯引用這一病癥反映出后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自我認知斷裂,再現了虛幻現實中人們的病態生存狀態,對鮑德里亞 “類象”和“真實”概念之間的模糊狀態作出了最好的文學注解。
馬克對姐姐“真實”身份的質疑成為一面反光鏡,映射出卡琳的自我矛盾心理,使她開始回望過去,審視自身,重新思考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尋求身體和精神兩個層面的統一與富足。由于卡琳和馬克姐弟倆從小生活在一個缺乏溫情與呵護的家庭中,父親酗酒成性,母親淡漠冷酷,卡琳一直都想逃離這個隨時會帶來“暴風雨”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童年的家庭遭遇導致后來的卡琳與家園逐漸疏離,并輾轉于背離故土和回歸家園的兩難選擇中。長大后的卡琳來到了蘇德蘭市,按照別人對成功的標準過活,用他人的評價丈量自己的得失,她滿足于一份帶來不菲收入的工作,一套象征成功與名望的公寓,甚至一段帶來盲目和虛幻的快感的戀情。表面生活的光鮮也遮擋不了她內心莫名的孤獨和虛無感,甚至她自己也慢慢地開始拒斥這種戴著面具的生活,卡琳的自我認知在后現代病態社會這塊濾鏡下處于分裂狀態,誤以為有婦之夫卡什是最“懂她心思的人”,是一個能夠“讓她找回真實自我”的人。[6]44實際上,卡琳和卡什之間的愛情是一種交易,是一種卡琳逃離內心孤獨與寂寞的大膽嘗試,是個人縱欲在污穢的都市生活中得以宣泄的手段,更是一種排遣內心虛無感的方式,結果不言而喻,卡琳在自己追逐的這份功利性的愛情中迷失自我,異化自我,喪失了辨別人的情感真假的能力,宛如馬克難辨真偽的“雙重錯覺綜合癥”,卡琳成為人的情感層面的“錯覺綜合癥”患者。直到她意外獲悉馬克企圖自殺的消息,才領悟到弟弟在自己與特工和機器人之間難辨真偽并非沒有原因:
她終于明白了弟弟不認她的原因。她已經沒有什么可以識別的特征了。她已經被扭曲的面目全非了。一個小小的欺騙行為重疊在另一個欺騙行為之上,直到連她自己也無法道出自己的狀態,說出她在為誰工作。她推諉、否認、撒謊,甚至對自己隱瞞事實。對所有人隱瞞所有事情。…
她一無是處,卑微無名。比卑微無名更糟的是,她內心一片空白。
她必須改變自己的生活,從她那污穢的巢穴中挽救出點什么。[6]407
卡琳開始意識到導致自己情感無能的病因,并積極為拯救自我開具良方。她逐漸從一個沒有情感和思想的“寄生蟲”蛻變為一個有著道德思辨和理性判斷能力的“正常人”。她認清了自己所生活的社會對人身體和靈魂的腐蝕性,拒絕繼續充當被謊言編織的社會網絡里的“空心人”,個體雖然渺小,依然努力尋求精神“荒原”中的“星星之火”,于是,她摒棄了世俗眼中的物質和虛榮,看清了以奸商卡什為首的精致利己主義者的虛偽、貪婪和瘋狂,同時,也感受到了以丹尼爾為代表的環保主義者的真實、無私與偉大,終于追隨自己內心真實情感的呼喚,在婚姻與家園歸屬選擇中重新定義自我,重新建構自我身份。
如果說馬克的身體頑疾——“雙重錯覺綜合癥”,割裂了他對人際關系在“過去”的真實認知與在“現在”的虛幻認定之間的聯系;卡琳幼年時代的家庭創傷與成年后的情感無能使她聯結過往記憶與當下現實,進而找到重構自我身份的基點;那么,認知神經學專家杰拉德·韋博的身份建構之旅則融合了他在科學試驗(對馬克病癥的療愈)與精神需求(對卡琳情感糾葛的見證與對妻女態度的轉變)的雙向成長與蛻變。韋博最初決定對患有罕見病癥的馬克展開科學研究,其目的無非為自己博取名利,借“雙重錯覺綜合癥”,韋博把馬克的故事寫進自己撰寫的暢銷書中,活生生的病例成為他在科研專著中大肆叫囂的文字符碼,成為自己沽名釣譽的镢頭,尤其,在對馬克病情的描述中,韋博夸大其詞,掩蓋了馬克病情的真實情況。他窺探病人的隱私,卻不能對病人的遭遇感同身受,介入患者的病癥,卻對患者的痛苦熟視無睹。韋博在初見卡琳時許諾的針對馬克病癥的認知療法“戲弄了大家的期待,甚至玩弄了馬克的友誼”,[6]183“雙重錯覺綜合癥”、馬克和卡琳都淪落為韋博為博取名利而進行的科學研究的試驗品,成為物化的存在。
韋博的思想轉變得益于姐弟二人在配合自己接受診療的過程中,姐弟二人表現出的患者對醫生的超乎尋常的配合、信任與托付,這使已有妻女的韋博深受觸動,他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認知開始悄然發生改變。當新書《驚訝之國》的出版飽受惡評、負面評價將他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卡琳也開始對他的研究表現出質疑時,韋博才真正的開始反思自己的科研動機,審度救死扶傷的職業操守,追問醫者仁心的道德品性,終于,他深刻檢討自己以往過分關注馬克的“病癥”,卻對馬克作為“病人”秉持淡漠的“不介入”的態度,意識到他不應該把病人當作科研的素材,試驗的標本,更不應該利用馬克的罕見病癥作為吸引大眾眼球、誘導眾人輿論與提升個人關注度的幌子,相反,醫者需要將“病人”視作“變化著的生命形式”,尊重他們與“非病人”一樣的生命體的尊嚴,關注他們的人性,對病人加以平等看待,并注入人文關懷。[6]308
“雙重錯覺綜合癥”將三位主人公拴在一起,透過這一病癥,我們見證了人類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弱點,也感受到了自我完整的認知對人類精神異化的救贖力量。在小說中,鮑爾斯對人的“記憶”話題的引入,“打破了時間的線性(敘事)特點,模糊了自我與他者的界限,進而在人類與自然之間建立一個共同體。”[9]馬克、卡琳和韋博的身份危機就是在馬克認知分裂的前提下,通過不斷地記憶與回望,在過去與現在之間搭建橋梁,尋找自我在過去與現在之間、自我與他者之間以及自我與自然之間的“共同體”而得以化解。
二、自我定位:家園情節與情感召喚
美國后現代主義思想家、生態女權主義理論家查倫·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指出,在后現代社會,生命成為一架靈肉分離的機器,被動而機械地脫離了曾經熟悉的、給予他們心靈滋養的“自然”和“地方”,到鋼筋水泥構筑的城市里,過著“非真實”的生活。因此,現代性興起并盛行的表現之一便是割裂個體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同時“逃離地方”。[10]作為一位具有強烈的生態憂患意識和家園情節的后現代小說家,鮑爾斯在《回聲制造者》中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后現代社會“身體”“自然”和“地方”三者之間的矛盾存在關系,并積極為化解個體身份危機尋找濟世良方。一方面,在鮑爾斯筆下,馬克的“雙重錯覺綜合癥”成為他對后現代病態社會帶來的認知障礙與靈魂異化現象的隱喻,這一病癥造成了馬克的自我認知斷裂,割斷了他與至親的情感紐帶,成為斯普瑞特奈克筆下靈肉分離的機械性存在;另一方面,這一病癥也成為以卡琳和韋博為代表的“普通人”和“醫生”實現個體身份重構、尋求自我精神救贖的契機,通過不斷地回望過去、反思當下,卡琳和韋博思忖著自我身份建構的方方面面,從與親人和家園的紐帶中尋求情感的依附和精神的寄托,尤其,鮑爾斯對卡琳和韋博的歸家之旅中情感的蛻變與強烈的家園情懷著墨甚多,足以照見作家對見證人們成長、承載歷史創傷與記憶的土地或“地方”在重塑自我、維系自我與他人親密關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卡琳長大后遠離家鄉,生活在大都市,但是每次當她“剛剛開始新的生活,試圖以常人的姿態出現時”,她的家鄉卡尼小鎮就會把她“拉回來”,對卡琳而言,卡尼小鎮就如同一片磁場的磁源,幼年時候的她千方百計想要逃離,但是,無論她怎樣掙扎,強大的磁力總會把做離心運動的她拉回來,實際上,卡琳“根本不曾離開”,[6]75使卡琳產生向心力的是故鄉和家庭在思想和精神上根深蒂固的影響,來自家園親和力和家庭溫情的召喚使她始終無法抹除那段記憶留下的烙印,即便在卡琳長大后遠離家鄉,依然不能從內心深處真正擺脫曾經生養她的那片土地。當卡琳因為馬克的車禍返回卡尼小鎮時,家鄉熟悉又陌生的景象使她從心底“生發出一種怪誕的,不正常的”家的感覺。[6]6這種怪誕感和不正常感源于卡琳幼年時期的創傷記憶,體現了卡琳從小到大因親情缺失而對故土文化所秉持的逃避心理,同時,也反映出卡琳對來自家鄉和親人關愛與呵護的渴望。所以,面對世上的唯一親人,她選擇了遵守曾經對父親立下的誓言,“無論發生任何事情,絕不拋棄對方”,[6]425事實上,卡琳從內心深處非常珍惜這次照顧弟弟的機會,這是她得以重溫記憶,感受曾經與弟弟親密無間的親情的最佳時機,也是彌補幼年親情缺失的最好辦法,于是,卡琳順從內心深處時常被“拉回來”的家園情結的召喚,她辭掉了大都市體面的工作,重返質樸單純的卡尼小鎮,憑借自己的回憶逐漸喚起認知斷裂、難辨真偽的弟弟的記憶,與馬克一起守護這片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土地。
認知神經學家韋博雖然沒能如卡琳一樣最終選擇返回家鄉,但是,作為專門研究馬克的“雙重錯覺綜合癥”的“專家”,在對馬克的認知障礙病癥的研究過程中,韋博意識到了人的完整的記憶的重要性,也逐漸體會到,為了在認知神經心理學領域有所建樹,他曾經急功近利,罔顧作為一名醫生的職業操守,最終聲名狼藉,與妻女關系疏遠。一定程度上,馬克病癥的療愈得益于他逐漸接受自己與過去的聯系,尤其表現為馬克和姐姐卡琳之間關系的改善,相較而言,經歷了感情和事業的雙重打擊,韋博開始從記憶中重拾完整自我的組合碎片,終于明白,“他失去的并非作為一名著名作家和心理學家的光環,而是通過回憶過去能夠與他人建立的精神紐帶。”[9]于是,他從內心深處更加珍視自己與親人之間的情感維系,決定修復自己與故鄉的弟弟之間的關系。尤其,當他揭開芭芭拉的真實身份,曉得導致馬克車禍的罪魁禍首就是整日陪在馬克身邊,照顧他日常起居的芭芭拉時,馬克對芭芭拉的寬恕啟迪韋博,使他結束了對芭芭拉的癡迷,鼓起勇氣踏上“歸家”之旅,努力征求妻女的原諒,更為珍視自己與妻子希爾維兩人之間美好的回憶,他們曾經“一起擁有寶貴的東西,擁有無法言說的過去”。[6]451這份珍貴的過去和無法言傳的記憶“正是韋博想要和妻子一起重建的‘地方’,那里有他‘真實’的家園”。[11]
在鮑爾斯看來,故土家園這一意象在確保自我認知,維系自我與他人、自我與家園之間的關系中至關重要。它不僅見證了家鄉物理環境的興衰變遷,也是承載個人創傷記憶、情感認知與精神救贖的地方。棄井離鄉、背離故土會割裂自我完整的身份認知,進而陷入精神異化的危機中。個人自我身份的建構離不開與之有千絲萬縷聯系的“曾經熟悉”卻又“不斷陌生”的地方,“從大世界著眼,由小地方做起,做有愛心的‘地方人’,是緩解生態危機、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的重要途徑。”[12]
三、身份之根:呦呦“鶴”鳴與遠古記憶
貫穿《回聲制造者》全文的除了馬克車禍懸疑案以及與之相關的系列情感糾葛這條線索外,還有面臨家園破壞和種族滅絕的沙丘鶴與人類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它們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正如享有“現代環保之父”美譽的美國環保主義先驅李奧帕德在《沙郡年記》中描述的那樣,“當我們聽到鶴的鳴叫時,其實我們聽到的不僅僅是鳥鳴聲,它是我們無法駕馭的過去的見證,也是那不可思議的漫漫歲月的象征,這些漫長的歲月又是生物和人類生存環境變遷的見證。”[13]在文中,鮑爾斯追本溯源,挖掘沙丘鶴在各國古文明中或褒或貶的指涉,從古希臘神話中阿波羅的鶴身原型假說,到印第安科里族的沙丘鶴攜兔奔月的傳說,再到鶴鳴給人類啟迪而創造的拉丁語、波斯語和阿拉伯語等語言,甚至鶴文化在中國和日本等東方國家不同的文化指涉,從西方到東方,由古至今,鶴文化源遠流長,無所不包,為此,鶴成為一種承載文化記憶的符號,它喚起我們對遙遠的古文明的回憶,誠如Siegleman所言,“對鮑爾斯來說,沙丘鶴首先指代對遠古的記憶,是一種承接過去與現在的符號,它們傳遞出源自大自然的最本真的祝福,而我們人類對待自然卻總是肆意地踐踏,無情地掠奪。”[1]又如Stock所說,該小說“強調的主題之一就是現實與傳統之間怪誕而顯著的沖突。”[14]沙丘鶴不得不面對人類的無情射殺,它們賴以生存的家園被破壞,處于瀕臨滅絕的邊緣,其生存現狀影射了后現代社會人類與過往文明之間的疏離與割裂,而人們對鶴群生存狀態的熟視無睹恰如馬克對姐姐的認知錯位一樣,最終導致個人自我身份的不完整,與此同時,作品中的沙丘鶴這一意象也引發我們反思鮑爾斯的生態憂患意識與生態倫理主張。
從小說開篇起,沙丘鶴的悲壯出場場面就集中體現了人類與自然、人類與文化的分裂狀態。圍繞沙丘鶴年度遷徙的是以卡什為首的旅游業開發商與以丹尼爾為代表的生態保護主義倡導者兩股勢力之間的較量。卡什是后現代社會典型的身心均被異化的形象,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他信奉“人類中心主義”機制,在看待人類與過往文明關系的問題上,他深受“物質至上主義”思想的侵蝕,孤注一擲,對環境保護和生態平衡等生態倫理嗤之以鼻,他大肆開發鶴群的棲息地,罔顧這些生靈的生命安危,打著發展旅游業以振興地方經濟的幌子博取公眾眼球。卡什高喊口號,“保護自然的目的正是為了讓人們欣賞”,這冠冕堂皇的辯詞恰恰印證了開發商生態保護主義謊言掩蓋下的人類中心主義機制,卡琳就此坦言,“整個人類都罹患了雙重錯覺綜合癥。”[6]347在此,鮑爾斯借卡琳的口吻將馬克的“雙重錯覺綜合癥”影射到整個人類身上,流露出對人類集體認知錯亂狀態的批判,諷刺了活在虛幻現實中的人們,因迷失在物質主義至上的欲望中而喪失人的本性,貪婪地向自然界過度索取,搶占其它物種的生存空間,并蔑視其生命尊嚴,這是鮑爾斯對人類生態短視的抨擊與鞭撻。
事實上,作為人類自遠古時代幸存下來的活化石,沙丘鶴與人類之間源遠流長的超越物種和血緣的親緣關系不可否定。“那些翩翩起舞的鳥兒就像人類的近親,它們的模樣就像人類的近親;他們呼叫,表達意愿,生兒育女,在飛行中確定方位,這一切都像人類的血肉至親。”[6]347-48同樣,評論家Harris也認為,“鶴類如果不是我們的血親,也無疑是遠親,它們和我們有著一樣的基因鏈,追溯到30億年前我們有著共同的祖先。”[15]時間逐漸改變了人類和沙丘鶴之間的物種分界,但是,時間抹不掉兩者之間古老的親緣關系,改變不了人類與沙丘鶴之間曾經血脈相連的事實,即便現在,沙丘鶴依然飽含情感,充滿靈性:這群曾經跟我們擁有共同祖先的精靈以它們獨特的方式表達著對親人的懷念,比如,有一家三口在飛行時遭遇人類的槍擊,當鶴寶寶看到“父親”被射傷躺在地上時,它和鶴媽媽在空中不停地打轉,不停地繞圈,不停地呼喚,以這種“宗教儀式”祈求死者的復活,祈禱鶴爸爸重新回到它們的身邊,但是“它沒有出現,只有昨日,只有去年,只有六千萬年之前的時光,只有遷徙的路線,只有盲目的自生自滅的回歸”。[6]278鶴爸爸被與它們擁有共同祖先的人類射死了,留給鶴媽媽和鶴寶寶的只有記憶,只有亙古未變的飛行路線和遷徙軌跡,它們憑借曼妙的舞姿和凄婉的啼鳴表達出對同類的懷念、記憶和追悼,與人類相比,沙丘鶴具有更牢靠的記憶,它們的記憶就是一幅幅地圖,每年的飛行路線就印在它們的腦海中,使它們能夠在一年一度的遷徙中準確導航,不至迷失,而這理應是對人類情感表達的真實寫照,理應是我們對待逝去的文明應該持有的姿態。
作為承載著人類古老文明在當下社會的記憶符號,沙丘鶴喚醒我們對人類先祖與過往文明的記憶,沙丘鶴與人類基因的相似性,以及它們在記憶能力上表現出的超越性,成為鮑爾斯對罹患“雙重錯覺綜合癥”的整個人類族群生存狀態的辛辣諷刺和無情批判。因而,在環境保護倡導人丹尼爾的感染下,卡琳和馬克姐弟倆決定追隨他的生態保護理念,在小說結尾處,恢復了正常記憶的馬克開始潛心鉆研李奧帕德的《沙郡年紀》這部倡導生態保護的專著,逐漸成為一名熱心公益、致力于生態保護的環保主義倡導者,而姐姐卡琳毅然決定留在卡尼小鎮接管沙丘鶴的保護工作,通過在自己與家園、自己與自然的親密接觸中建立聯系而重新建構自我身份,可以說,小說主人公卡琳最終的選擇折射了生活在后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尋求人類先祖之根、尋找斷裂的文明以獲得靈魂救贖的理智之舉。
結 語
在《回聲制造者》中,鮑爾斯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豐滿真實,他沒有規避人性的脆弱:記憶錯位,自我迷失,精神異化,情感無能,家園缺失等都是對后現代社會人們普遍的生存狀態的真實再現;而“個體與軀體之間的關系,以及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與家庭的關系、與文化的關系等,都是個人身份的構成性元素。”[16]對此,鮑爾斯在小說中敏銳地捕捉到了致使后現代社會個體身份異化的種種因素,借助文學想象,以“虛構”的故事展現“真實”的現實,批判了后現代社會發展帶來的身份危機。在后工業時代,由于物質至上主義和精致利己主義等思想的侵蝕,人的精神逐漸被異化,慢慢偏離了文明發展的正常軌道,整個人類都成為“雙重錯覺綜合癥”患者,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以及人與過往文明之間均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割裂和疏離。
即便如此,鮑爾斯依然對醫治這一后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認知分裂、身份異化頑疾保有信心,在這個“理智與情感”被科技逐漸操控甚至取代的精神“荒原”中,人類雖然渺小,但是,依舊可以“自由地扮演自我,自由地冒名頂替,自由地即興表演,自由地想象任何事情,自由地通過我們所愛的事物塑造我們的心靈”。[6]426“亙古律動,現實回聲”,鮑爾斯倡導的自由精神不失為給迷失在商品符碼的機械社會中的人們開出的一劑良藥,使他們逐漸擺脫人類中心主義機制的圈囿,摒棄物質至上主義和精致利己主義思想的侵蝕,正視記憶,追隨內心情感的真實需求,重塑自我與他人、自我與家園、自我與先祖文明的關聯,回歸自我身份的真實性,最終,實現精神的救贖與靈魂的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