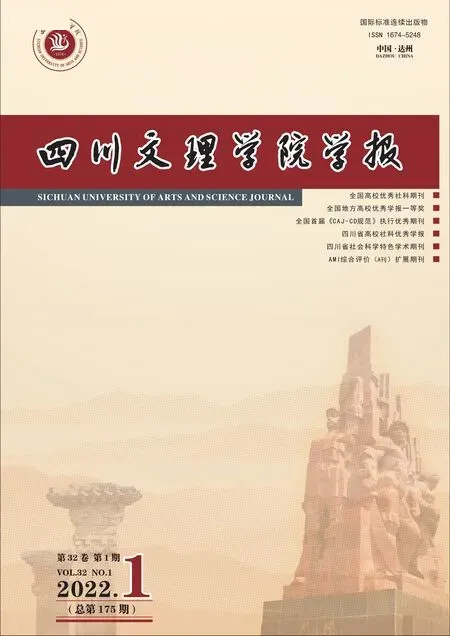《有所思》與《上邪》兩首詩的互文性解讀
杜自波
(四川文理學院 文學與傳播學院,四川 達州 635000)
關于《有所思》與《上邪》二詩關聯性的研究,一以清人莊述祖《漢鐃歌句解》為代表,他解兩詩“當為一篇”,前后姻聯,是“敘男女相謂之辭”;一以聞一多《樂符詩箋》為代表,他解為二詩“不見問答之意。反之,以為皆女子之辭,彌覺曲折反復,聲情頑艷。”然從這兩首詩的本事、結構、情感進行觀照,不難發現前后文本的互文性邏輯,即是說后文本是對前文本的吸收和轉化,它們是同一文本中不可割裂的前后兩個部分。
一、《有所思》與《上邪》的本事關聯性
本事者,本于事者或根于事者,即所謂“感于哀樂,緣事而發”[1]之“緣事”,是“詩性的歷史實存”。[2]其詞最早見于東漢桓譚《新論·正經》:“《左氏傳》遭戰國寢廢,后百余年,魯人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3]樂府本事,固然就是指一首樂府曲辭創作之初所依據的事情之本來,所依據的“詩性的歷史存在”。向回《樂府詩本事研究》:“樂府詩本事,就是指那些與樂府曲調、曲名或是歌辭的創作、傳播、變化等有關的歷史事實或是民間傳聞,它是對與具體作品直接相關的作者(或故事主人公)行事(包括逸聞逸事)及其創作、傳播過程的真實記錄,或是對它們的藝術化處理。”[4]樂府詩本事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結構,因為它涉及作品創作、傳播、變化。就《有所思》與《上邪》而言,我們可以根據“本事——本意——本義”的進行態對二詩進行一個“人類文化的集體回憶和詩性還原”。[2]即是說先考究文本創作的歷史背景,然后去推論作者的主觀創作意圖,最后形成讀者對文本的原義集合。當然本事在這里只是較為指向性的被定為創作背景。故此,在莊述祖和聞一多關于二詩本事批評的指引下完成進一步的本事探究和考證,從而證明二詩“實為一篇”之可能。并不是所有如此背景本事相關甚至一致的不同詩文都可以當做一篇而論,《有所思》與《上邪》同屬《漢鐃歌十八曲》中的情愛詩,原列第十二和十五,我們就有一定理由去猜測二詩可能為一篇之文。《漢鐃歌十八曲》據《宋書·樂志》所載之漢明帝四品樂和蔡邕敘漢樂中,可見“短簫鐃歌”之名,并獨得一類,由此可證《漢鐃歌十八曲》確屬西漢之作。《古今樂錄》載漢短簫鐃歌古辭存二十二曲:
《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翁離》《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君馬黃》《上陵》《有所思》《雉子斑》《圣人出》《芳樹》《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云》《黃爵》《釣竿》,[5]后四篇古辭俱已亡佚,故其實存十八曲。其中可約略推定創作年代的是《上之回》《上陵》《遠如期》。《上之回》后世多從吳兢之言:“漢武帝原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后數出游幸焉。其歌.......皆美當時事也”。[6]也就是說大都認為《上之回》作于漢武帝時期(-156年~-87年)。《上陵》因詩中所記“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甘露是漢宣帝第六個年號,從公元前53年至公元前50年共4年時間。而《遠如期》則寫于甘露三年述匈奴單于來朝之事。雖然其余諸篇創作時間難以考證,但我們可以根據郭茂倩《樂府詩集》之編類法即時間推移法進行推測,《上陵》至《遠如期》之八篇是在漢宣帝甘露年間(-53年~-50年)即西漢中后期所創,包括《有所思》以及《上邪》。在這一時期,婦女地位是處在一個不斷下降的境地。楊樹達先生在《漢代婚喪禮俗考》收錄了《史記》《漢書》里關于漢代主動改嫁和被迫離異的史料,其中主動改嫁的有外黃富人女、張負孫女、朱買臣妻、王皇后、蘇武妻、淳于長的小妻共七條,除淳于長之小妻出自漢宣帝外,其余皆出于漢武帝及以前。被迫離婚或被丈夫驅逐回家的有五條,包括陳平嫂、王吉妻、霍光女、王政君的母親以及枚乘小妻,而王吉妻、霍光女、王政君的母親多生活在漢宣帝時期。她們被棄原因不盡相同。陳平嫂之被棄因口舌之嫌“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也就說了句陳平不務生產的閑話卻被離棄。王吉妻之被逐因“盜竊”之事,史載:
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日:“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7]
王吉休妻是因為他妻子摘了鄰家幾顆垂到自家院的棗給他吃,這也是為彰顯自己學官之志氣。而王政君的親母是因妒忌之故遭丈夫休離。
據此,我們可以對比得知,第一,在漢宣帝以前,婦女在家庭、婚戀中的地位較高,而漢宣帝及以后的婦女地位漸趨弱勢,其命運多受制于丈夫。第二,婦女被驅逐或休棄的原因并不是不忠不仁不孝,而是男子主觀認為婦女不守禮節,行為出格。這種婦女地位的變化是有深刻歷史原因的,一是儒學的影響日漸擴大,二是以“三綱五常”為中心的禮教逐漸形成。儒學和禮教對婦女的束縛在漢宣帝時期已漸趨強化了。
綜而論之:《有所思》與《上邪》的背景本事是漢宣帝時期,婦女地位漸趨下降,婦女在曲辭中激情熱烈的怨詛決絕是向世人昭示自己是保留著一片貞潔之操守的,指日可鑒,同時諷刺男子仗著政治優勢二三其德。我們來細究文本,先看《有所思》之所言: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瑇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飔,東方須臾高知之。[8]
這是言男子二三其德,女子怨而怒,怒而不可得便生思情,而后欲告知上天一些東西,這大可認為是一篇文章的前半部分以及一個完整本事的上半部分。我們再看《上邪》之所言:
上邪! 我欲與君相知, 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 江水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與君絕![8]231
這是言女子向上天表明自己的貞潔誓言,這大可認為是一篇文章的后半部分以及一個完整本事的下半部分。
因此,筆者認為二詩若合而為一,便成就一個完整的背景本事,也就是說漢宣帝時期,婦女地位漸趨弱勢,婦女在曲辭中表現的是在男子政治優避下深沉而無奈的盟誓,《有所思》是為盟誓之深沉,《上邪》是為盟誓之無奈。所謂深沉,是女子祈望“與君絕”之權利,而所謂無奈,是女子面臨著“為君絕”的現實。此本事之斷論較莊述祖之“男女相謂之辭”更確切的表明是女子一人之心聲,而絕無男子之言;較聞一多“獨立各篇”更趨向于“合為一篇,成其完整”。故此論綜合二人之言說,并詳加補充其本事,以構建二詩“層累型發展”的完整結構。這是從本事出發對文本本義進行闡述,其“實為一篇”之論證雖為可行,但還需要從二詩文本的結構與情感進行具體的解讀論證。不過值得肯定的是在本事探究或是本事批評的指導下,我們可對文本進行多元開放的解讀甚至對其進行二度生成。
二、《有所思》與《上邪》的結構銜接性
已被廣泛接受的文本自有其結構的完整性,內容的統一性,意義的相對穩定性。[9]《有所思》與《上邪》在結構上的首尾銜接、前后照應以及時空對接關系能更進一步說明本事探究或是本事批評的可行性。
《有所思》之詩末言“東方須臾皓知之”,其中“東方”一詞出自《詩經·邶風·日月》:“日居月諸,東方自出。”[10]漢·司馬相如《長門賦》亦有言曰:“觀眾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11]此東方之意即太陽升起的那個方向,可代指“上天”。“知之”一詞是說等天亮了,上天自會明白我的心意,可是我的心意是什么呢?覺得“知之”其后還有話說。故《上邪》開篇一句“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順勢承接前文之“東方須臾高知之”,“上邪”即承接“東方”,“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承接“知之”。女子向上天所要表露的是自己的鐘情以及貞操:上天啊,我不僅與他相知,而且要到天荒地老的永遠。正如余冠英在《樂府詩選》里所注:“上”指天,“邪”音“耶”,“上邪”猶言“天啊”,指天為誓。“相知”相親也。“命”令也,使也。從“長命無絕衰”以下是說不但要“與君相知”,還要使這種相知成為永遠,除非天地間起了亙古未有的大變化,一切不可能的變為可能,如高山變為平地等等,咱們的交情才會斷絕。這也是情詩,似和上篇有關聯,有人認為合為一篇。兩篇同是一女子的話,上篇考慮和情人斷絕,欲決未決,這篇是打定主意后的誓辭。[12]
此二詩便是在“指天為誓”之下完成了巧妙的結合。曲辭中女子本是因對遠隔天涯的心上人“有所思”,故打算用玉纏繞的“雙珠瑇瑁簪”來表達自己一片鐘情癡愛。然男子二三其德,心有他者,這不得不使女主人公由愛而恨,因恨而怨怒,故將這信物“拉”“雜”“摧”“燒”“揚其灰”,以發泄內心積郁的情感,可謂是不如此深刻描寫,難以窺見女子一時之憨恨。本是要忘掉負心人,并斷絕關系,但是“情不知所起,以往而情深”啊,便在欲決絕之際懷想起過往約會驚動巷犬與兄嫂的事,這決欲不決的矛盾心理昭然若世,但女主人公內心真實的想法只有上天知道。此詩怨且怒,怒之急切,是為望之深切。行文至此,女主人公的“望之深”并未戛然而止,而是繼續潮漲,其望之深切便在這天地四時萬物之間:山丘沒有了棱角,江水枯竭了,冬天打雷,夏天飄雪,天地合而為一,我們的交情才能斷絕。故二詩合為一體成其文者如是: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瑇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飔,東方須臾高知之:上邪! 我欲與君相知, 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 江水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與君絕!
這是據二詩結構之一進行論證的,整篇文章以“上天”前后銜接巧妙過渡,使得結構完整渾融,絕無隔斷,自然形成一篇文章的前后兩部分。筆者認為二詩如此整合為一,便是本事探究以及本事批評對文本分析的作用——文本再生成,它能夠讓“互文性”更加作用于此文本與他文本,并讓“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忠實存在”。[13]
前面已從結構之一首尾銜接進行論證,這里將從結構之二前后照應進行論證,力求證據的充足性。《有所思》有“相思與君絕!”之句,而《上邪》有“乃敢與君絕”之句,二詩因此形成前后照應的關系。“相思與君絕”是因為鐘情之女子得知心上人“有他心”,自己的一片癡情化為憨恨,于是想要與他斷絕關系,但想起昔日約會驚動巷犬和兄嫂,這是多么愜意浪漫的回憶,怎么能說斷就斷的呢,這說明的是“與君絕”很難。若是“與君絕”,又應該如何?《上邪》作為整篇文章的下半部分給出了答案:山丘沒有棱角,江水枯竭,冬雷轟隆,夏日飛雪,天地合一。唯有這樣,女子才能“與君絕”。這些超自然的現象說明了“與君絕”不可能,可能的只有“為君絕”。整篇文章,由《有所思》之“與君絕很難”輾轉為《上邪》之“與君絕不可能”,其實質是“為君絕”的可能性結果甚至必然性結果。
最后,我們再從時空維度來進行探究。《有所思》之女子,立足現在,有所思念是因為“乃在大海南”,有所怨怒是因為“聞君有他心”;回溯過去,有所牽掛還有所纏綿是因為“秋風肅肅晨風飔”;祈望未來,有所期待還有所無奈,是因為“東方須臾高知之”。這是根據“過去——現在——將來”的時間維度演繹的。而《上邪》言“山、江水、冬雷、夏雪、天地”之物象,則是根據“天——地——自然”的空間維度演繹的。也就說,兩者形成時空維度的對接互補,形成了文本與文本在橫向上以及在縱向上的“文本性”或是“文本間性”關系。
三、《有所思》與《上邪》的情感接續性
正因為《有所思》與《上邪》在結構上的銜接關系,才有了二詩在情感上的接續關系。《有所思》是為情感之蓄勢,表現成激情深沉,《上邪》是為情感之接勢,表現成熱烈決絕。我們細析文本便可知二詩如何蓄勢與接勢的:《有所思》起篇便著一“思”字,為全文墊下纏綿悱惻的情感基調。繼而因其所思者遠在大海之南,引發女子造信物以能睹物思人也。然現實不成所祈望,男子二三其德,有了他心,女子之信托之情陡然枯索,頓生怨怒,使一連串動作“拉”“雜”“摧”“燒”“揚”似與之斷絕,此女子憨恨之態也。轉念思之,過往之繾綣令女子難能決斷,一負心人如何挽回?只能述己愿于天,方可鑒也。此部分由思轉怨,怨而怒,怒而復思之,欲決未決,但可是未決耶?非矣,《上邪》之辭以詳其心意。《有所思》之情感蓄積于此,欲破未破,似有下文,故《上邪》順其自然接其情勢而述之。“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就是此女子的決絕,她以天為證,發出誓言要同心愛的人相識相知,相親相守,并且到永遠。“上邪”之聲再并之“欲”字,將此女子激情深沉之情推向另一個浪峰即熱烈決絕之情,其表現為五個異常的奇特想象,合其為三,即山水、氣候、天地,合其為一,即自然。其意表明自然的一切,連絕非出現的物象都無法阻止我的情誓貞節,況一切正常之物象?
二詩合成的總的情感實為熾熱背后的無奈,熾熱是就二詩言辭而論,無奈則是就其背景本事而論。熾熱之情,在《有所思》中主要是五個動詞“拉”“雜”“摧”“燒”“揚”的表達效果,這一連串的動作行為將憨恨之女子的“思—怨—怒—望”的情感變化生動地表現出來。在《上邪》中則主要是五個超凡想象“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的表達效果。當然,二詩言辭除卻熾烈,其背后也潛藏著無奈的。再論其無奈,主要是二詩所構成的背景本事造成的,在封建等級制度社會,在漢宣帝那個儒學與禮教盛行的朝代,女子只能是“為君絕”,而非“與君絕”,因此就算是男子變心,女子也難能主動取得生命支配權。
結 語
通過《有所思》與《上邪》兩首詩的互文闡釋,[14]可以發現彼此有著嚴密的互文性邏輯。它們在本事上互為補充,并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本事結構:在漢宣帝那個儒學與禮教盛行的朝代,女子只能是“為君絕”,而非“與君絕”,因此就算是男子變心,女子也難能主動取得生命支配權,若得貞節,需指天為誓,故感其“哀樂”,成二詩之文。它們在結構上首尾銜接,形成密合無間的文本故事:《有所思》之尾句“東方須臾高知之”與《上邪》之首句“上邪”的巧妙銜接;《有所思》之“相思與君絕”句與《上邪》之“乃敢與君絕”句的前后照應;《有所思》之時間維度與《上邪》之空間維度的妙合無間。它們在情感上前后呼應,以形成連綿接續的情感場域:《有所思》實為情感之蓄勢,表現成激情深沉,《上邪》實為情感之接勢,表現成熱烈決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