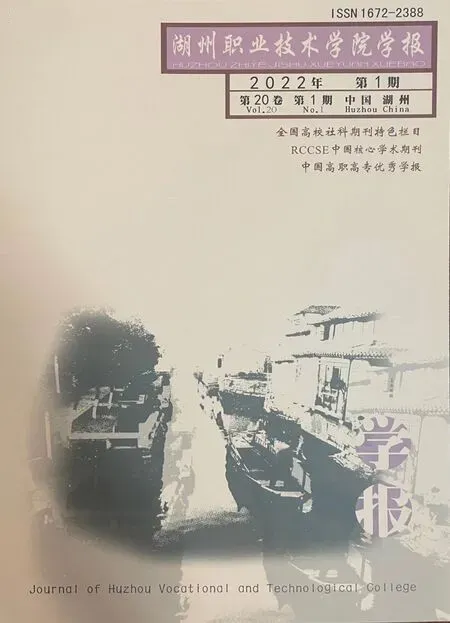論《源氏物語》的“物哀”美學*
劉曉昱
(鄭州商學院 外國語學院, 河南 鞏義 451200)
《源氏物語》成書于日本的平安時期,全書近百萬字,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小說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時期為背景,細膩詳盡地描繪了主人公源氏一生的感情經歷。作者紫式部憑借其自身的女性視角和散韻結合的寫作方式,為全書營造了一種婉約哀傷的獨特美感,并由此開啟了日本文學的“物哀”時代。其所傳達出的以“真實”為基礎的“物哀”精神影響了包括川端康成、夏目漱石等在內的一大批日本作家。“物哀”這一文學理念最早由日本江戶時代的國學大師本居宣長提出。其通過對《源氏物語》的研究,認為“物哀”即是心感于外物而有所嗟嘆,如看到美麗的櫻花盛開,內心生出愉悅之情;望見黃葉飄零,心中生出哀傷愁緒,這都可以看作是“物哀”之情[1]124。《源氏物語》中的“物哀”之情表現在源氏生活的方方面面,感情生活的失意、宮廷生活的枯燥、自然風光的轉換等都可以成為其抒發“物哀”之情的契機。紫式部的高明之處在于:通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將主人公的真情精準地傳達出來。《源氏物語》的“物哀”美學是日本文化中最重要的美學范疇之一,是讀者了解日本文化的必經之路。
一、《源氏物語》的成書背景
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出現都深受其所處時代的影響。同樣,一種新文學觀念的生發也必然被其產生的時代所塑造。《源氏物語》的平安時代是一個深受漢文化影響的朝代。但是,到了平安中后期,隨著莊園制經濟體制的建立,日本開始對漢文化進行本土化,并產生了自己的文字----假名。在此背景下,日本文學也開始了一些新的嘗試:詩歌方面出現了篇幅較短的和歌,散文創作上出現了當時日本獨有的日記體文學,而在小說方面則出現了以《源氏物語》為代表的描寫貴族宮廷生活的長篇小說,同時也孕育出日本文化中獨特的“物哀”美學[2]189。
(一)和風文化的形成
據統計,從公元7世紀到9世紀的兩百多年間,日本共向中國派出遣唐使18次。正是通過這200多年的交流,日本全面學習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深入了解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同時還將中國的書法、建筑、繪畫、醫學等引入國內,有力地促進了日本社會的全方位發展。到平安初期,漢文化對日本的影響達到頂峰,甚至出現了漢文化一家獨大的情況。這使得日本國內的文化精英感到迷失和不安,他們渴望發展本民族文化的意識開始強烈起來。《源氏物語》中也曾提到:“凡人總須以學問為本,再具備和魂而見用于世,便是強者。”[3]361學習中國文化必須以本民族的精神信仰為前提,日本古代漢學家菅原道真所提出的“和魂漢才”即是此意。
在此背景下,日本于平安時代中后期創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字----假名文字,將漢字逐漸日本化。此舉極大地增強了日本文字的表現力,使其文字能夠與日常口語統一起來,從而更好地展現日本民族的情感世界和審美情趣。《源氏物語》中就出現了大約2/3的假名文字。同時,當時的日本文人學者也開始尋找日本民族獨有的審美趣味。《源氏物語》以“真實”為基礎的“物哀”美學的出現,即標志著日本古代文學開始擺脫漢文化的影響,創造出自己獨有的“物哀”文學[4]83-84。這一階段的日本,完成了從漢風文化向和風文化的過渡,這對日本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
(二)紫式部生平
紫式部本姓藤原,其名已不可考,曾在宮中作侍讀女郎。因其兄長在朝中任式部丞一職,而當時宮中女官多以父兄的官銜為名,以顯身份,故稱為藤式部。后又因其所著《源氏物語》中紫姬一角被廣為傳頌,遂改稱為紫式部。紫式部生長的藤原家是平安朝數一數二的大貴族,其父兄皆是當時有名的“歌人”,家中文藝氛圍濃重。紫式部從小便跟隨父親研習中國古典文學,聰穎過人,同時又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這一點在其之后的文學創作中有明顯的體現。
22歲那年,紫式部奉父命嫁給一個比自己大20歲的地方官藤原宣孝,不久即誕下一女,取名賢兒。已有三任妻子的藤原宣孝非常欣賞紫式部的才華,將其引為知己,百般呵護。不料,婚后不久,藤原宣孝便身染重疾去世,留下紫式部獨自撫養女兒。孤寂的孀居生活一方面讓紫式部變得多愁善感,另一方面也為其創作提供了充裕的時間。其間,紫式部的一些文章開始受到好評,在宮中引起關注。隨后,太政大臣藤原道長見其才華出眾,便召她入宮為自己的女兒講讀典籍。紫式部雖才學過人,但苦為一介女流,地位卑下。身為女官,紫式部一方面可以參加宮中的許多文人集會,另一方面又深感自身的卑微弱小,不過是男性貴族的附屬。這種矛盾復雜的生活體驗和心理狀態,使得紫式部開始用一種清醒而又略帶哀傷的目光去審視宮廷生活。基于其個人真實的生活經歷和情感體驗,紫式部最終完成了百萬字的《源氏物語》,成為一代文學巨匠。
二、《源氏物語》中的“物哀”美學特征
“物哀”這一概念最早由日本江戶時期的大學者本居宣長提出。從字面意思來看,“物”是指認識感知的對象,而“哀”則是認識主體的情感流露,那么“物哀”便是指人在接觸外物時自然生出的或喜悅或哀愁的情感。《源氏物語》中“物哀”美學的出現與日本所處的自然環境有密切關系。日本是一個島國,物產資源有限,且自然災害多發,這使得日本民族本身就有一種無常之感。在此情況下,他們只能抓住眼前的事物,尋求瞬間的永恒,故而對自然和人世的變化十分敏感。紫式部從小便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再加之青年喪夫,人生幾多變故,更生無常之感。因此,“無常”這一主題在《源氏物語》的“物哀”美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此外,《源氏物語》雖是寫王宮貴族的宮廷生活,卻沒有過多地著墨于政治斗爭,只是一心追求純粹的美與善,抒發主人公心中的無限愁情。
(一)遠離政治,追求純粹的美
在《源氏物語》中,紫式部寫的大都是男女私情,極少涉及政治內幕,哪怕源氏貴為王子,也未見作者對其政治活動進行過多描繪,這是《源氏物語》“物哀”美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源氏公子對世俗的倫理道德一概不顧,整日只是風花雪月、歌舞游宴,一切以內心的愉悅為出發點。在小說中,源氏也明確說道:“我回京以后,復官晉爵,身為帝室屏藩,但我對富貴并不深感興趣,唯有風月情懷,始終難于抑制”。[5]53在日本文化中,源氏這種身處權力中心卻一心只求風月的人格和行為被看作是“風雅”。這是一種摒棄了功利之心的審美境界,是日本人最典型的審美心理之一[6]53。這種審美心理的根源在日本以佛教為主導的文化結構中,而佛教思想本就是形而上、超脫于現實之上的。中國著名的日本文學研究專家葉渭渠認為:“‘物哀’的思想結構是重層的,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人的感動,以男女戀情的哀感最為突出;第二個層次是對世相的感動,貫穿在對人情世態包括‘天下大事’的詠嘆上;第三個層次是對自然物的感動,尤其是季節帶來的無常感,即對自然美的動心。”[7]20-36
《源氏物語》有著濃重的唯美情結:(1)在小說結構上,《源氏物語》的各卷看似獨立,實則相互勾連,彼此應和,宛若多個樂章共同奏響一曲美妙的音樂,充滿了和諧之美。(2)在行文風格上,作者采用了散韻結合的方式,散文的敘事配以韻文的抒情,使得原本單調的物語文學變得飽滿而富有表現力[8]71-72。(3)在小說意境營造上,《源氏物語》全書都浸潤在一種詩的意境之中,柔美動人,如在《須磨卷》中,源氏謫居須磨,意興闌珊,在面海的回廊中望見清幽的暮色、浮沉的小舟、低鳴的寒雁以及初升的明月。這些意象組合在一起營造了一個唯美哀愁的動人意境,感人至深。
(二)具有濃重的死亡情愫
日本近代“物哀”美學的代表作家川端康成認為:“死是最高的藝術,是美的一種表現,藝術的極致就是死滅。”[9]431而另一位大作家三島由紀夫更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表達這一觀點,為了追求瞬間的美麗,他獻上了自己的生命。可見,死亡在日本的“物哀”美學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在《源氏物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與死亡有關的意象,如黃昏,黃昏本就代表著白日的結束。在小說中,作者更是將黃昏這一意象描繪得蒼涼蕭索,其每一次的出現都暗示著一些生命的凋零和逝去。同時,《源氏物語》中也有對人物死亡的直接描寫,如桐壺更衣、葵姬、夕顏、六條妃子、紫姬、源氏等。她們或抑郁而終,或重病不治而亡,或因極度傷心而死。甚至可以說,小說情節的發展就是在這些人的死亡中一步步向前推進的。
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李澤厚曾用“惜生崇死”來概括日本人的生死觀。但《源氏物語》中的男男女女卻是留戀生命的,只是心中明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作者的厲害之處就在于從不直接描寫人物的死亡場景,而是選擇為人物的死亡營造一種凄美哀傷的氛圍,通過生者的悲傷情緒來感染讀者。這種寫法將死亡提升到了審美的層次,同時,這種唯美的死亡畫面也成了《源氏物語》“物哀”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深受佛教“無常”思想的影響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是佛教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觀念。佛教認為,萬事萬物都處在時刻變化流動之中,沒有一個恒長的自性(即自體之本性)。平安時代中后期,貴族統治開始衰落,社會變得動蕩不安,故而,佛教的無常思想在這一時期發展得尤為迅速。上層的貴族感到往日榮華不再,從而生出一種落寞感,而下層的人民則更加感到社會的變動和人生的不可控。這種無常思想和日本人生就敏感的性格結合在一起,使得追求精神上的解脫成了當時日本人的主流選擇。這也是整部《源氏物語》彌漫著人生無常之感的原因之一。
主人公源氏的一生本就是無常的一生:身為皇子的他一生下來便遭受喪母之痛;本想遠離政治,閑散度日,卻被貶為臣子,流放須磨;好不容易重回皇宮、榮耀加身,等待他的卻是至愛紫姬的離世。命運仿佛總是在和他開玩笑,往往在他最快樂、最得意的時候給他當頭一棒。在書中,源氏也親口說到:“我生在現世,榮華富貴,可說沒有缺憾了。然而又不斷地遭逢比別人更痛苦的厄運。想是佛菩薩要我感悟人生無常、世途多苦之理,所以賦給我這命運的吧。”[10]724《源氏物語》對于“無常”的展現是細微而精妙的,總是將人的生死浮沉與自然景物的枯榮變化結合在一起,如源氏經常對月抒懷,面對著萬古如一的月光感慨生之憂患、死之哀傷[11]93-96。紫式部在“無常”基礎上所創造出的這種“物哀”美學是日本神道思想與佛教融合的產物,是一種超越生死的審美境界。
三、《源氏物語》中獨特的“物哀”視角
在《源氏物語》中,“物哀”美學的表現是多維度、多視角的,從四時風物的變化、世態人情的浮沉以及女性人物的命運中,都可以感受到“物哀”之情的縈繞。當然,這些視角在小說中并不是單獨出現的,往往是多個視角交織在一起,共同營造出一種詩的意境,使人物的情感氤氳其間,更富有真實感。在這三個視角之中,女性視角通常是隱藏在文本之后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作者的女性身份,即使其表現得很客觀,也難免將女性視角不自覺地代入其中。而自然和世情兩個視角之間的相互作用則更為明顯:現實生活的變化會使得人的心境也隨之變化,而作為人的認識對象的自然景物也必然會蒙上一層感情的光暈,所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即是此意。
(一)自然“物哀”
日本文學自古以來就有描寫自然景物和季節變換的美學傳統。著名學者葉渭渠認為:日本固有的神道信仰先祖神,首先就是太陽神和樹神。“在日本民俗信仰中,將太陽神視作最有靈感的,將古樹和山視作神圣的東西,并非偶然。他們將樹木視為神樹,最早祭祀的是樹木神。”[12]50他們愛自然,認為自然是本來的美與真實。《源氏物語》很好地繼承并發揚了這一美學傳統,從對自然景物的審美中發展出了“物哀”美學[13]26-39。《源氏物語》全書共有54卷,其中25卷的卷名都是從植物的名稱中得來,如“松風”“楊桐”“夕顏”“藤花”“梅枝”等,既有高大挺拔的喬木,也有芳香馥郁的花卉。
同時,這些植物的名稱還具有高度的象征意義,暗示著人物的命運走向。如“夕顏”本是生于荒野小屋旁的小白花,這種花總是在最不堪的環境中獨自綻放,而以“夕顏”為名的女子也正是這樣的命運。她居無定所、天真膽小,長于貧民窟中,但卻自有一種“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麗之美,就如同“夕顏”花一樣。在《源氏物語》中,這些花草樹木不只對文本起到了點綴的作用,更是小說人物抒情的載體,同時也承擔著轉換時間、推進情節發展的任務。紫式部以自然的物象為媒介來表現人物之間的情感糾葛,使得那些哀傷、幽怨的負面情感也多了一份美感。
(二)世情“物哀”
《源氏物語》雖然主要寫宮廷貴族的生活及男女情愛,但也從側面反映了整個日本平安時代的歷史面貌。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紫式部身為女性,很難直接參與到王朝的政治事宜之中,只能以個人的見聞體驗為基點展開描繪。也正是這種具體而細致的個人經驗,賦予了《源氏物語》獨特的“物哀”之美。同時,青年喪夫、家道中落、枯坐宮中等生活經歷也使紫式部對世情人生有了更強的感受力和洞察力。這些難忘的生命經驗也是其創作《源氏物語》的重要動力。
展現世態炎涼、人情淡薄的段落在《源氏物語》中多處出現。其中,最精彩的一幕莫過于桐壺皇帝去世前后的情形。桐壺皇帝雖退位多年,但實權在握,每逢年節其門前必是“車馬盈門,幾無隙地”。但在其去世后不久,便是“門前車馬稀”了。桐壺皇后被迫搬離皇宮,就連深得桐壺帝寵幸的源氏也被貶“須磨”。桐壺皇帝貴為一國之君尚且如此,可想而知,當時的普通貴族會是怎樣的遭際。在《源氏物語》中,紫式部通過對人物細膩的心理描寫,將這些世情變化展現出來,讓主人公像對待一片落葉、一次黃昏那樣來對待人生的變故,哀傷之中蘊含著唯美。
(三)女性“物哀”
《源氏物語》用了大量的篇幅來描寫源氏與十幾個女性之間的情愛故事,刻畫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女性形象,如端莊高貴的桐壺皇后、清麗動人的紫姬、紅顏薄命的夕顏、心懷嫉妒的六條妃子等等。這些女性形象和書中的自然景物一樣,都是構成《源氏物語》“物哀”之美的重要元素。然而,作者越是將這些女性描繪得美麗動人,她們的死就越給人以深沉真切的情感體驗[14]40。在書中,這些女性人物要么早早離世,要么落發為尼,要么獨守空閨,無一不是以悲劇收場。以紫姬為例,她是整本書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既有閉月羞花的容貌,也有溫良賢淑的德行,還善于琴棋書畫。但就是因為她的女性身份,使其有情難言,有志難抒,年紀輕輕便抑郁而終。在作者眼中,這些女性的逝去就是一場美的悲劇,越是美麗,越令人傷感;越是美麗,越讓人回味。
綜上所述,《源氏物語》是日本“物哀”美學的源頭,也是日本文學走向自覺的標志性作品。《源氏物語》所表現出的“物哀”之美是全方位、多層次的,從自然風光到人情世故再到女性命運,無一不籠罩在一種唯美哀婉的詩一般的意境之中。《源氏物語》中的“物哀”之美以佛教的無常思想為底色,追求純粹的美與善,甚至不惜以死亡為代價來完成對美的祭獻。《源氏物語》成書的年代雖然距今已有千年之久,但其創造出的“物哀”美學傳統,在當下的日本乃至全世界,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和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