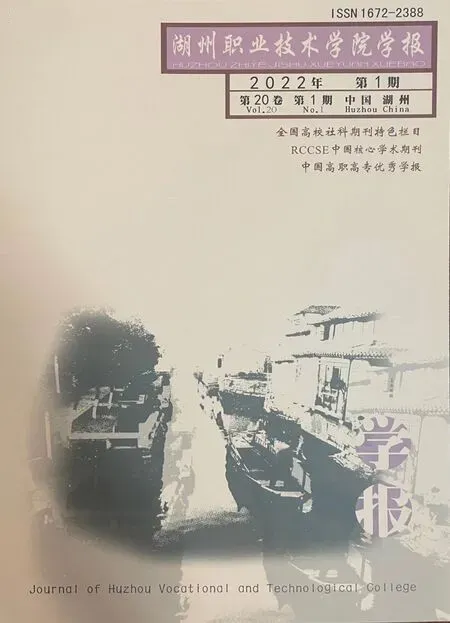賽珍珠《群芳亭》中的中國女性形象*
拾景樂
(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 徐州經貿分院, 江蘇 徐州 221000)
賽珍珠(Pearl S . Buck,1892-1973年)是美國歷史上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性作家。賽珍珠創作《群芳亭》時已定居美國,憑著自己對中國社會和文化,以及中國各階層人民生活的了解,用客觀的筆觸,在《群芳亭》中塑造了許多生動的中國女性形象,向世界展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風貌。
一、《群芳亭》的成書背景
(一)賽珍珠的特殊成長經歷
賽珍珠出生后一直跟隨身為傳教士的父母生活在中國,與普通百姓比鄰而居。從鎮江到皖北再到南京,賽珍珠以“外族人”的身份長期生活在中國。賽珍珠在中國的生活經歷并不都是愉快的。“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讓年僅8歲的賽珍珠成為中國民眾口中的“洋鬼子”。她第一次感受到中國民眾對異邦人的排斥。1927年,有士兵襲擊外國人的教堂和學校,賽珍珠被迫跟隨家人倉皇離開。這兩次經歷使賽珍珠認識到,民族之間缺乏了解與溝通是造成矛盾沖突的原因。賽珍珠“清晰地了解中西兩種文化的異質和沖突”[1]2,這讓她“堅定了為增進東西方,特別是中美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而奮斗終生的決心”[2]5。因此,她將文字作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工具,開始自己的創作生涯。
1934年,賽珍珠回美國定居。此后,由于世界局勢動蕩不安,她再也沒有回過自己的第二故鄉——中國,但她仍致力于向美國人民講述真實的中國,推薦中國的文學作品。賽珍珠年幼時不僅接受母親的西式教育,而且跟隨中國教師學習中國的經典文學和傳統文化。賽珍珠曾在演講中談到,雖然自己生來是美國人,但恰恰是中國小說決定了她在寫作上的成就。中國的經典文學作品對賽珍珠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她的作品大多采用中國傳統小說的章回體。她喜歡用白描的手法,她的創作對象涵蓋了包括女性在內的大部分人群。
賽珍珠作品的特殊之處在于:她用自己“質地精良的文學著作,使西方世界對于人類的一個偉大而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重視”[2]1。賽珍珠雖然自1934年后再也沒有回過中國,但她憑著自己對中國社會的熟悉,對中國局勢發展、變化的了解,在大洋彼岸寫出了許多中國社會題材的作品。《群芳亭》就是其中之一。回到美國后,賽珍珠的“思想和事業仍舊與中國及中國人民緊密相連,繼續致力于促進中國人民與西方人民之間的跨文化交流”[2]24。
(二)“五四”以后興起的女性解放運動
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早在戊戌維新時期就拉開了序幕。隨著西方民主思想進入中國,部分中國青年不滿封建社會制度,他們渴望平等,期望實現精神和思想上的真正解放,其中也包括一些進步青年女性。
1898年,維新派以撤銷女性纏足和禁止女性入學兩項舊習為契機,開展女性解放運動。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西方女權思想傳入中國。為實現女性解放,辛亥革命頒布了一系列諸如禁止纏足、允許自由戀愛等法令,還建立了女子學校。一些女性還提出了“要求參政”的口號。但這兩次女性解放運動均未取得實質性成果,要求自由平等的只有少部分女性。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中國的女性解放運動達到了新的高潮。無產階級自此登上了歷史舞臺,為女性解放創造了許多有利條件。五四運動時期,女性知識分子走上街頭,在表達愛國情懷之余,發出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呼聲。深受封建思想荼毒的下層女性,在這些年輕女性的帶領下,也加入了追求平等的行列。人們對于女性解放問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女性解放運動的主體從女性知識分子擴展到數量更多的勞動婦女,女性解放運動走向更加光明的未來。
隨著民主運動的興起,賽珍珠看到了中國女性思想的變化。她贊揚為爭取平等權利而不斷斗爭的中國女性,但她也發現封建思想對大部分中國女性的影響仍是不可磨滅的。因此,在《群芳亭》中,賽珍珠不僅塑造了追求自由平等的吳愛蓮、露蘭和琳旖,還塑造了深受封建思想束縛的康太太、萌萌、秋明和茉莉等人物形象,通過描述個性鮮明的中國女性形象來展現當時中國的社會風貌。
二、《群芳亭》中的中國女性形象分析
(一)吳愛蓮:徘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反叛者
《群芳亭》中的吳愛蓮,是賽珍珠重點詮釋的人物。她是一個有著自我意識和反叛精神的女性,但仍然擺脫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縛。小說以吳愛蓮的思想變化為主線,從自我意識的萌芽到最終自我意識的覺醒,吳愛蓮終于過上了理想的生活。
吳愛蓮有一個思想開明的父親,但她仍舊沒能擺脫敝習陋規對女性的約束,奉父母之命嫁給了吳老爺。她希望與自己的丈夫有精神上的契合,但她漸漸發現吳老爺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丈夫。于是,她在40歲生日這天做了一個重大的、令人驚訝的決定——與丈夫分居,并為他納妾。在周圍人看來,雖然吳老爺并沒有非得納妾的理由,但吳愛蓮為了開啟新生活,毅然搬到了公公的書齋,獨自沉浸在甜蜜、幽靜的生活中。此時,吳愛蓮還沒有找到使自己真正獲得自由和幸福的方式,封建思想仍對她的行為處事有著深刻影響。她站在金字塔的頂端,用自己所謂的責任心,強勢地讓所有人過上她以為的幸福生活。吳愛蓮以傳統的標準為丈夫選妾,包辦三兒子峰鏌的婚姻。但秋明和琳旖的到來,并沒有使吳家過上安定的生活,反而引發了一場場風波。
直到安德雷修士的到來,吳愛蓮在與安德雷的交流中,逐漸發現自己難以獲得真正自由和幸福的原因。安德雷的話像純露一般沁入她的心田,讓她內心那朵向往自由的美麗花朵悄悄綻放。吳愛蓮意識到她的強勢造成了吳家兩代人的悲劇,因此,她開始盡力彌補。后來,善良的安德雷被青幫毆打致死。吳愛蓮這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愛上了這個讓她唯一崇拜的人。安德雷的博愛和善良讓她從一個出于責任心生活的人,變成了一個通過愛去生活的人。吳愛蓮繼續照顧安德雷收養的女孩們,甚至同意吳老爺娶妓院女子茉莉。她勸兒媳婦要實現自我,不要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孩子身上。“她不信神仙菩薩,也沒有宗教信仰,但她永遠有愛心。”[2]332她將安德雷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走出被困40年的庭院,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賽珍珠筆下的吳愛蓮詮釋了中國傳統女性賢良淑德、仁愛孝悌的美德。她是丈夫眼中溫柔的妻子,是孩子眼中敬畏的母親,是仆人眼中嚴厲的家族管理者。在安德雷的引導下,她的自我意識終于覺醒,開始打破世俗觀念、破除陳規舊俗。吳愛蓮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勇于追求個人幸福、具有現代意識的女性,但其思想深處仍殘存著封建的陳腐觀念。吳愛蓮在傳統思想與現代意識中徘徊著前進,走向自由幸福的生活。
(二)康太太:封建女性倫理的犧牲者和維護者
賽珍珠在《群芳亭》中也塑造了一些最能夠反映中國封建社會陳腐觀念的女性形象。她們深受封建思想觀念的束縛,是生活在倫理規范下的傳統女性。她們生平最大的快樂就是綿延后代,處處為丈夫和孩子考慮而逐漸失去自我,在囚籠一般的庭院過完余生。
康太太就是中國傳統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深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和束縛,沒有追尋自我的意識,在深宅大院里度過了自己的一生。康太太認為,自己的使命就是生育。她的生活始終充斥著小孩、婢女和仆人的吵鬧與喧嘩。她沒有考慮過除生育以外的其他事情,因為她認為自己一旦停止生育,就沒有了存在的價值。當得知自己再次懷孕時,她這個中年女人既快樂又悲傷。她高興的是自己還沒有喪失作為女人存在的價值,悲傷的是在這個年紀懷孕并不是值得慶幸的事。
當康太太發現好友吳太太的思想逐漸發生轉變時,她并不能接受吳太太的一些出格行為。因此,兩人漸行漸遠。直到康太太難產,兩人的關系再一次發生了變化。在傳統家庭中,男人不被允許進入產房。但是,吳愛蓮堅持讓康老爺在產房,看女人生產的不易。康老爺因此下定決心,不再讓妻子生育。然而,康太太卻因好友過于介入自己的私生活而心生不滿。由于吳太太對康老爺的勸解,康太太失去了生育的權利,再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雖然仍舊過著稚子繞膝的嘈雜生活,但康太太的心境發生了變化。她躺在藤椅中的身體與椅子變得吻合無間,成為一具失去自我價值的軀殼。
(三)秋明:勇敢走出庭院的新一代“娜拉”
賽珍珠在《群芳亭》中塑造的秋明具有十分復雜的性格特點。其復雜性在于進入宅院生活后思想、性格產生的變化。秋明原來是一個小心翼翼求生存的底層勞動女性,后來開始考慮自己的未來。在有著積極進取精神的新派女性露蘭的影響下,秋明選擇跟她離開,回到圍墻外的世界,過上自由的生活。
秋明是完全按照吳愛蓮對妾的想法找到的農村女性。她處事小心、自卑、沒有自我意識,長著姣好的面容,有著適合生育的身體,是一個深受封建思想影響的女性。秋明是被拋棄的孤女,在進入吳家前甚至沒有自己的名字。在過去的二十幾年中,秋明是養母兒子未來的媳婦。來到吳家對她來說雖然不是最好的選擇,但總好過被媒婆賣到花窯。因此,她小心翼翼地服侍吳老爺,對吳愛蓮尊敬且畏懼。當秋明告訴吳太太自己懷孕時,吳太太不悅的表情讓她產生自殺的想法;當英英告訴秋明她懷的可能是女孩時,秋明擔心自己不能生兒子會被厭棄而選擇自殺。秋明具有下層勞動女性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典型性格,她懂得為了生存必須掩飾內心的真實想法。她守著對峰鏌的愛情,默默生活在宅院內,只為完成生育責任而活。
秋明最后選擇離開吳家,一方面是她內心有對完整家庭的渴望;另一方面是她對命運有一種本能的反抗。秋明雖然生活不幸,但她并未喪失自我,她的心并不在吳家。從賽珍珠對秋明的一系列細節描寫中,可以看到秋明內心對命運的抗拒:第一次去見吳老爺時,秋明不自覺地退縮,她不愿走進這個家;秋明拒絕了吳太太一邊吃蓮子一邊談話的提議;在生產時不顧吳太太的懷疑,執意要與安德雷見面;秋明甚至直接告訴吳太太,這個嬰孩是違背自己意愿生下的。秋明與露蘭這個宅院中孤獨的女人相互傾訴心酸與痛苦。在露蘭的影響下,秋明開始向往遠離吳家的生活。于是,她和露蘭征得吳太太的同意,來到鄉下為村里的孩子辦學堂,在遇見生母之后選擇離開這個傷心地。這個愛與恨都被宅院限制的女人,終于離開了囚禁自己的“鳥籠”,過上了自由的生活。
三、《群芳亭》折射出賽珍珠的女性觀及其局限性
(一)追求傳統與現代兼具的完美女性形象
從賽珍珠的作品及演講中可以看出,賽珍珠的女權主義思想發生了三次轉變,即從贊美女性獻身家庭到支持女性走出家庭,再到希望女性回歸家庭的同時不放棄追求自我。這三次轉變與她的生活環境、所接受的思想有著密切關系。
1931年,賽珍珠的《大地》出版。憑借這本小說,她獲得了普利策文學獎和諾貝爾文學獎。賽珍珠在《大地》中塑造了一個完美展現中國傳統道德品質的女性阿蘭。阿蘭踏實勤勞,為家庭犧牲了一切。創作《大地》時賽珍珠仍生活在中國,沉迷工作的丈夫和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導致賽珍珠無法投身于婚姻和家庭。賽珍珠看到了普通中國勞動婦女身上的寶貴品質和她們獻身家庭的精神。她將自己折射于小說中的阿蘭,贊美了熱愛家庭和甘于獻身的偉大女性。
19世紀末20世紀初,女性自由主義思想開始在美國萌芽,許多美國女性走上街頭,為爭取個人權益而斗爭。1934年,賽珍珠回到美國,她看到了美國女性為獲得平等所做的斗爭。1941年,賽珍珠在《男與女》中指出:婦女的獨立自主對美國民主的存在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她呼吁女性走出家庭,實現自我價值。這一主張與此前她提倡的女性獻身家庭的觀點背道而馳。所以說,致力于東西方文化融合的賽珍珠,在西方自由和中國傳統兩種思想的沖擊下,試圖從“自由主義的女性關懷重新解讀中國傳統美德”[3]17。
賽珍珠在《群芳亭》中塑造了既具有傳統美德也有自我意識的現代女性吳愛蓮,她的思想上的矛盾在吳愛蓮的身上得到調和。40歲之前的吳愛蓮是傳統的賢妻良母,她壓抑自我,成為吳家的“主心骨”。吳愛蓮身上體現出的傳統性,是賽珍珠對中國女性傳統美德的認同。賽珍珠認為,封建社會的女性只有在家庭中才能得到身份認同。但是,賽珍珠著力展現的還是吳愛蓮的自我意識覺醒的過程。40歲之后,吳愛蓮發表了自己的“獨立宣言”,開始追求個人的幸福與自由,挑戰傳統道德的權威。她與丈夫分居,住到公公的書齋,翻看公公說的那些只有男人才能看的書;她跟隨安德雷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與思想,她感到自己空虛的靈魂日漸充盈起來。
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中曾提到,賽珍珠在作品中提出了一個最嚴肅也最憂郁的問題——中國婦女的地位問題[4]83。賽珍珠女權主義思想的變化,對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她對深受封建制度壓迫的中國女性深表同情,同時也肯定了她們身上傳統女性的美好品質。《群芳亭》中的吳愛蓮是一位勇于喚醒自我意識的新女性,但她沒有放棄自己在家庭中作為妻子、母親的責任。這是賽珍珠在自由女權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對中國傳統女性形象的重新解讀,對中國傳統文化、封建社會制度的重新認識和深度思考。
(二)以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來審視中國女性
學界對賽珍珠的評價褒貶不一。這位異國作家雖然從客觀角度寫出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風貌,塑造了一批生動的中國人物形象,但大多數人仍然認為,賽珍珠作為“一個比較開明的基督教徒”,受到了西方思想限制,她并不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的真實面貌[2]15。
魯迅在看過《大地》后,也認為賽珍珠從“一位生長在中國的女教士的立場”,看到了浮于表面的中國社會。張子清也認為,賽珍珠以中國視角,在“中國語境里展開故事情節、刻畫人物性格”,是讓他們在與外國人的交流中得到展現的[3]44。正如封建思想會對吳愛蓮產生深遠的影響,西方思想也會對賽珍珠產生影響。因此,賽珍珠回到美國后創作的中國題材小說,多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敘寫故事,這也是《群芳亭》略遜于賽珍珠其他中國題材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中國封建社會的皇帝還沉浸在唯我獨尊的優越感中時,西方國家已經開始了邁向新階段的工業革命。在當時的外國人看來,中國是一個落后迂腐的國家,中國人生性狡猾、不可理喻。在大國沙文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下,大多數西方人對中國人表現出強烈的排異心理。直到20世紀,這種思想仍然存在于大多數西方人的心中。“西方的風俗習慣,哪怕荒誕不經,也被看做是同行全球的行為準則。”[2]8因此,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是為了讓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普通民眾獲得幸福和永生。在《群芳亭》中,安德雷對吳愛蓮的思想轉變和形象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完美詮釋善良、博愛、博聞、廣識的安德雷,第一次與吳愛蓮見面就看出她生活的不幸福,短短幾次交流后就斷定吳愛蓮生活不幸的原因是她的責任心,并指點吳愛蓮要用愛去生活。在面臨死亡時,安德雷心里還是只惦記著收養的女孩們。他雖然沒有給吳愛蓮留下其他話,但他的言行卻給吳愛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為支撐吳愛蓮日后生活的精神支柱。
賽珍珠借助安德雷這一形象,使吳愛蓮完成自我意識從萌芽到覺醒的過程。安德雷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對吳愛蓮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消解和影響,使吳愛蓮變成像安德雷那樣博愛、善良的人。客觀來講,賽珍珠試圖在《群芳亭》中塑造吳愛蓮這個從“中國傳統女性向現代女性轉變”的理想典范[5]102,但安德雷這個外國修士對吳愛蓮造成的影響,卻減弱了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意義。賽珍珠試圖在寫作時完全從中國人的角度出發,但她潛意識仍被西方思想和理論所影響,這使《群芳亭》中的安德雷實際上成為引導吳愛蓮找尋自我的角色,而非只教授語言和知識的家庭教師。她作品中隱含的西方中心論,成為中國文學界對她的主要詬病。
四、結 語
賽珍珠的《群芳亭》之所以能贏得讀者的喜愛,是因為:(1)這部小說真實地再現了中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社會現狀,塑造了許多生動的中國女性形象。(2)這部小說創作的基礎是男女平等。在《群芳亭》中,賽珍珠塑造了勇敢自覺的進步女性形象,也展現了封建社會中逆來順受、以當賢妻良母為人生樂趣的傳統女性形象,以真實的視角和同情的筆觸,對中國封建社會女性群像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