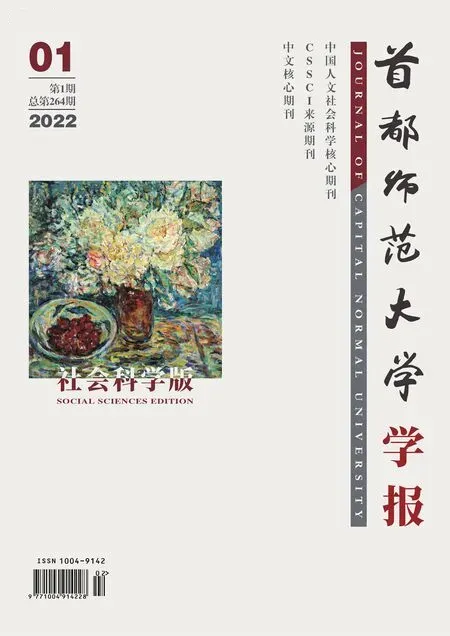虞通之《妒婦記》新考
李曉華
《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著錄《妒記》二卷,虞通之撰。《妒記》原稱《妒婦記》,見于《宋書》卷四十一《后妃傳》:
宋世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敩當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為敩作表讓婚……
據此知宋明帝劉彧敕虞通之撰《妒婦記》,使人為江敩作讓婚表。徐堅等編撰《初學記》卷十載“宋虞通之《為江敩讓尚公主表》”,認為虞通之撰讓婚表,當有所據;故嚴可均《全宋文》卷五十五稱虞通之撰《為江敩讓尚公主表》,錢鍾書先生稱“蓋《記》《表》為一事而發,且出一人之手也”①錢鍾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324頁。。《妒婦記》《為江敩讓尚公主表》既為一事而發,出于一人之手,二者撰述時間當一致。那么,作為帝王,宋明帝為何敕虞通之撰《妒婦記》?又使之作《為江敩讓尚公主表》?這是頗值得關注和深思的。關于虞通之撰《妒婦記》的時間、背景、意圖等問題,目下學界研究并不充分,且認識不一,如吳志達先生著《中國文言小說史》未交待時間、背景,乃稱“皇帝命近臣撰《妒婦記》,旨在警誡婦女,為自己的腐化生活張目”①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齊魯書社1994年版,第218頁。。侯忠義先生著《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上冊)稱《妒婦記》“乃受明帝敕命所撰,成書約在宋末”,“《妒記》的主要內容,是勸諫、諷喻上層婦女妒忌的行為,提倡、贊揚婦女不忌之德,肯定一夫多妻制,維護封建夫權,基本傾向是不可取的”。②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頁。林正三先生著《虞通之〈妒記〉研究》稱“成書的年代:宋明帝泰始初年”,“編撰《妒記》的目的:勸誡妒婦止妒,以維護夫綱”。③林正三:《虞通之〈妒記〉研究》,參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第十四集,臺北學生書局1997年版,第312-313頁。苗壯先生著《筆記小說史》稱“成書當在南朝宋末”,“在一定意義上妒悍體現了婦女自我意識的覺醒,是對夫權的反抗”。④苗壯:《筆記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頁。向楷先生著《世情小說史》稱“書成于劉宋末”,“從現存的一些佚文看,寫的雖都是妒嫉的婦女,客觀上卻明顯地反映了不合理婚姻制度下的夫婦不和諧關系及不協和的家庭生活”。⑤向楷:《世情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然考諸史冊,可以發現,上述諸家之說,值得商榷:其一,關于虞通之撰《妒婦記》時間,諸家或無考證,或推斷不準確,乃至錯誤;其二,關于《妒婦記》撰述背景,諸家未作具體考證,尤其未將《妒婦記》與《為江敩讓尚公主表》聯系起來考察;其三,關于明帝敕虞通之撰《妒婦記》《為江敩讓尚公主表》意圖、目的,筆者認為意在警誡“諸主”,安撫諸尚公主士族,以維系劉宋政權。換言之,明帝敕虞通之撰《妒婦記》《為江敩讓尚公主表》,乃與當時的政治態勢密切相關,是為維護、鞏固統治而采取的重要政治舉措。以下試作具體考察。
一、《妒婦記》《為江敩讓尚公主表》撰述時間與時局態勢
宋明帝劉彧在位僅八年,即泰始先后七年、泰豫一年,虞通之撰《妒婦記》,自然在此八年間。體味《為江敩讓尚公主表》所述、尋繹史家所載,可以斷定虞通之撰《妒婦記》時間,當在泰始五年(469)至七年(471)間。證據有二:其一,《為江敩讓尚公主表》稱“如臣素流,室貧業寡,年近將冠”⑥沈約:《宋書》卷四十一《后妃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90頁。,江敩自道此時“年近將冠”,是直接的證據,是可信的;據《南齊書》卷四十三《江敩傳》,江敩卒于齊明帝建武二年(495),年四十四,可推其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452);古代男子二十而冠,那么,江敩“年近將冠”,當在泰始七年(471)稍前;這就是說,《為江敩讓尚公主表》撰述時間下限為泰始七年。其二,《為江敩讓尚公主表》撰述時間,與江敩尚孝武帝女時間當大致同時,因為江敩在明帝授意下故作“讓”之姿態,實并不影響其尚公主進程;據《南史》卷三十六《江敩傳》,江敩“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敩嘆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可知江敩尚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時,袁粲為丹陽尹;據《宋書》卷八十九《袁粲傳》,袁粲泰始五年(469)加中書令,領丹陽尹;七年遷尚書令,丹陽尹如故;泰豫元年(472)四月,明帝殂;據此而推,江敩尚臨汝公主當在泰始五年至泰豫元年四月間,其時間上限為泰始五年,這自然也是《為江敩讓尚公主表》撰述時間上限。綜合上述所論,則推斷《為江敩讓尚公主表》作于泰始五年至七年,是可確定的。既然“《記》《表》為一事而發”,那么,虞通之撰《妒婦記》,也當在泰始五年至七年。
泰始五年至泰豫元年,是劉宋王朝走向衰亡的關鍵時期。《宋書》卷八《明帝紀》稱“親近讒慝,剪落皇枝,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道出劉宋王朝走向衰亡的直接原因,是明帝親近邪惡奸佞之人,“剪落皇枝”。“皇枝”,指皇帝的庶子或宗族;明帝所剪落“皇枝”,一是孝武帝諸子,一是文帝諸子。大明八年(464),孝武帝劉駿崩,太子子業即皇帝位,即前廢帝。廢帝幼而狷暴,即位不久便誅害宰輔,殺戮大臣;又疑畏諸叔父,恐其在外為患,遂聚之建康,拘于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景和(465)末,廢帝將加害湘東王劉彧,彧乃與腹心阮佃夫、李道兒等密共合謀,殺廢帝于后堂,建安王休仁等擁戴彧纂承皇極,彧賜孝武帝第二子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死。泰始元年(465)十二月,劉彧即皇帝位,即明帝;然孝武帝第三子晉安王子勛、第四子安陸王子綏、第六子尋陽王子房、第七子臨海王子頊不受明帝命,并舉兵反;子勛于泰始二年(466)正月在尋陽即皇帝位,改元義嘉。劉彧與孝武帝子之間的皇位之爭,導致“九域沸騰,難結天下”①沈約:《宋書》卷八十《孝武十四王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071頁。。那么,這場叔侄間的皇位之爭,孰是孰非?沈約稱“泰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劋悖亂,事惟拯溺,國道屯诐,宜立長君”②沈約:《宋書》卷八十四《鄧琬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63頁。,認為從當時的情勢看,國家應當立長君。劉彧與諸侄相爭的結果,是劉彧獲勝:八月,子勛、子綏、子頊、子元并賜死;十月,孝武帝子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并賜死,“世祖二十八子于此盡矣”③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一《宋紀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1頁。。而至泰始五年,明帝與兄、弟之間疑隙已萌:其一,此年二月,因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太尉廬江王祎,祎與欣慰等通謀,為人告發,明帝詔降祎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宣城,并遣心腹楊運長領兵防衛。其二,司徒建安王休仁任總百揆,朝野輻輳,明帝不悅,休仁表解揚州;十二月,以桂陽王休范為揚州刺史。上述二事表明,明帝與其兄、弟之間猜忌,矛盾已公開化。泰始六年(470)六月,免祎官爵,逼令自殺。泰始七年二月,明帝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刺王休祐“性剛很”,明帝“慮將來難制”,遂趁射獵之際使人“共毆拉殺之”。④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三《宋紀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頁。五月,遣人赍藥賜休仁死。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賜死于第。“時上諸弟俱盡,唯休范以人才凡劣,不為上所忌,故得全”⑤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三《宋紀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2頁。。此時,武帝七子已亡,文帝諸子唯劉休范以“人才凡劣”幸存,而孝武諸子盡殞。“東晉一朝,皇帝垂拱,士族當權”⑥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頁。;鑒于東晉“士族當權”終至晉室滅亡的教訓,武帝劉裕建宋后乃分封宗室,以圖藉此強化皇權。裴子野稱:“高祖思固本枝,崇樹襁褓,后世遵守,迭據方岳。”⑦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四《宋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8頁。說明武帝之后,分封宗室成為定制。劉裕分封宗室,意在“思固本枝”,而“本枝”至此為明帝剪落殆盡!《宋書》卷七十二《文九王傳》史臣慨嘆“太宗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正道出個中實情。
泰始五年明帝詔降其兄祎、弟休仁解揚州,實已釋放出一個明確信息,即明帝擔心其兄、弟覬覦皇位,遂考慮為身后幼子繼位掃清障礙;因而,剪落兄弟,便成為必然選項。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明帝敕虞通之撰《妒婦記》,又使之作《為江敩讓尚公主表》,可謂用心良苦;因為這涉及一個重要而迫切的現實政治問題,即“剪落皇枝”之后,劉宋政權依靠誰來維護?
關于南朝皇權政治特點,田余慶先生指出:“南朝皇帝恢復了絕對權威,可以駕馭士族;而士族縱然有很大的社會、政治優勢,卻絕無憑陵皇室之可能。只是士族有人物風流的優勢,皇帝擢才取士,贊禮充使,都離不開士族,甚至還要向士族攀結姻婭。”⑧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頁。道出南朝皇帝專權,士族為公卿輔佐,互相利用之事實。那么,皇枝剪落,無疑削弱了劉宋王室的力量,因而明帝不得不倚重士族以維系政權;而“向士族攀結姻婭”,利用政治婚姻將王室與士族利益捆綁在一起,以圖維護、鞏固劉宋政權,遂成為明帝考慮的重要政治問題。
二、政治聯姻背景下的尚公主士族生存狀態
事實上,自武帝以來,與士族聯姻,成為劉宋統治者維系政權的重要手段。《宋書》卷五十二《褚叔度傳》載:“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世胄,猶世家,貴族的子孫,可見武帝為公主擇偶均為世家子弟,高門士族;門閥是第一位的,是否“有才能”并不重要。而文帝、孝武帝、明帝為公主擇偶,亦莫不如此。那么,尚公主士族主要有哪些?政治聯姻背景下的尚公主士族生存狀態究竟如何呢?
考《宋書》《南齊書》《南史》,可知劉宋一朝尚公主士族主要有:瑯邪王氏。王曇首,“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①沈約:《宋書》卷四十二《王弘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311頁。;曇首子僧綽,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②沈約:《宋書》卷七十一《王僧綽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850頁。王偃,“晉丞相導玄孫,尚書嘏之子”,尚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偃長子藻,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③沈約:《宋書》卷四十一《后妃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89-1290頁。又,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當以適王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④沈約:《宋書》卷八十五《王景文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78頁。景文妹乃明帝皇后,景文亦王導玄孫。陳郡謝氏。謝述,“祖據,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城內史”,述子緯尚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⑤沈約:《宋書》卷五十二《謝景仁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93-1497頁。《為江敩讓尚公主表》稱“謝莊殆自同于蒙叟”;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稱“案《謝莊傳》,無尚主事,疑以目疾辭,遂停尚主”。⑥沈約:《宋書》卷四十一《后妃傳》校勘記引,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301頁。大約皇帝欲使謝莊尚主,而事不諧。謝莊父謝弘微,曾祖乃謝萬。廬江何氏。何尚之,“曾祖準(準,穆章皇后父),高尚不應征辟。祖惔,南康太守”,父叔度,紫金光祿大夫,吳郡太守。⑦沈約:《宋書》卷六十六《何尚之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32頁。尚之子劭,尚文帝第十六女南郡公主。⑧沈約:《宋書》卷六十六《何尚之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37頁。此事《冊府元龜》卷八百六十六亦載。尚之子偃,偃子戢,尚孝武帝女山陰公主。⑨沈約:《宋書》卷五十九《何偃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609頁。尚之弟悠之,悠之子颙之,尚文帝第四女臨海惠公主。⑩沈約:《宋書》卷六十六《何尚之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38頁。何瑀,“晉尚書左仆射澄曾孫也(澄,準第三子)。祖融,大司農”,瑀尚武帝少女豫章康長公主。瑀女令婉,乃前廢帝皇后。瑀子邁,尚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11]沈約:《宋書》卷四十一《后妃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93頁。東海徐氏。徐羨之,“祖寧,尚書吏部郎,江州刺史”,羨之子喬之,尚武帝第六女當陽公主。[12]沈約:《宋書》卷四十三《徐羨之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329-1334頁。羨之兄子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公主;逵之子湛之,湛之子恒之,尚文帝第十五女南陽公主。[13]沈約:《宋書》卷七十一《徐湛之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843-1848頁。濟陽江氏。江湛,曾祖虨,晉護軍將軍,父夷,湘州刺史;湛長子恁,尚文帝第九女淮陽長公主[14]沈約:《宋書》卷七十一《江湛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850頁。:恁子敩,尚孝武帝女臨汝公主。河南陽翟褚氏。褚叔度,曾祖裒,晉太傅;祖歆,秘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孫曖,尚文帝第六女瑯邪貞長公主。叔度長兄秀之,秀之弟湛之(案,《南史》卷二十八稱湛之為秀之子,《南齊書》卷二十三亦稱湛之為秀之子),尚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哀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15]沈約:《宋書》卷五十二《褚叔度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505頁。湛之子淵,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16]蕭子顯:《南齊書》卷二十三《褚淵傳》,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425頁。淵弟澄,尚文帝女廬江公主。[17]蕭子顯:《南齊書》卷二十三《褚淵傳》,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432頁。此外,又有汝南周氏,周嶠,“父淳,宋初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18]沈約:《宋書》卷八十二《周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089頁。下邽趙氏,趙倫之,孝穆皇后之弟,“外戚貴盛”,“久居方伯”;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19]沈約:《宋書》卷四十六《趙倫之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389-1390頁。濟陽蔡氏。蔡廓,曾祖謨,晉司徒;廓子興宗,興宗子約,尚孝武女安吉公主。[20]李延壽:《南史》卷二十九《蔡廓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774頁。從《宋書》載述看,太原王氏、穎川庾氏,也是劉宋王室聯姻對象,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適太原王景深,離絕。[21]沈約:《宋書》卷八十五《王景文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78頁。泰始初,以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適豫章太守庾沖遠,未及成禮而沖遠卒;沖遠乃庾登之子,登之曾祖冰,晉司空。太原王氏、穎川庾氏,在東晉顯赫一時。因而,沈約所謂“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是合于史實的。毋庸置疑,尚公主之諸士族,與劉宋王室關系密切,在朝廷中乃居機樞之地。以文帝一朝為例,文帝寵信的重臣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王)僧綽,凡十二人。”[22]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六《宋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7頁。其中,瑯邪王氏三人、陳郡謝氏一人、廬江何氏一人、東海徐氏一人、穎川庾氏一人、濟陽江氏一人。這表明,在文帝寵信的重臣中,尚公主士族占比為三分之二;那么,尚公主士族在劉宋政權中之重要性,于此可見一斑,而孝武帝朝、明帝朝亦大致如此。
文獻表明,尚公主士族,其生活難言愜意,生存狀態可謂堪憂。《為江敩讓尚公主表》詳細敘述尚公主士族諸多不如意處:日常生活忍氣吞聲,“勢屈于崇貴,事隔于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飽受控制,“制勒甚于仆隸,防閑過于婢妾”;難以交游,“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亦乃兄弟疏闊”;姆媼刁難,“姆奶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尼媼自倡多知,務檢口舌”;不得自由,“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生涯無趣,“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公主疑忌,“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妨礙子嗣,“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甚至有性命之憂,“王藻雖復強佷,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冤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絕”。①沈約:《宋書》卷四十一《后妃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91-1292頁。王藻“為冤魂”事,《后妃傳》如是載:“公主性妒,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前廢帝景和中,主讒之于廢帝,藻坐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關于褚曖,《宋書》卷五十二《褚叔度傳》載褚曖“尚太祖第六女瑯邪貞長公主,太宰參軍,亦早卒”。據《為江敩讓尚公主表》知褚曖早卒,乃由尚主“憂憤”所致。史載:“于時貴門子弟,咸以尚主為憂。”②許嵩:《建康實錄》,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89頁。這就無怪乎江敩疾呼“伏愿天慈照察,特賜蠲停”③沈約:《宋書》卷四十一《后妃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92頁。了。
須指出的是,由于前廢帝悖逆無道,從而引發尚公主士族的不滿。譬如,廬江何氏,在文帝、孝武帝朝均位居要津。何邁尚文帝女新蔡公主劉英媚,英媚乃廢帝姑,而廢帝“納公主于后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④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宋紀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8頁。;永光元年(465)十月,“以宮人謝貴嬪為夫人,加虎賁靸戟,鸞輅龍旂,出警入蹕,實新蔡公主也”⑤沈約:《宋書》卷七《前廢帝紀》,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45頁。;何邁不能容忍廢帝悖亂人倫之行,“謀因帝出游,廢之”;事泄,廢帝自將兵誅邁⑥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宋紀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8頁。;十一月,何邁下獄死。何邁被誅,對于何氏家族的打擊,是不言而喻的。再如,何戢尚孝武帝長女山陰公主劉楚玉,《宋書》卷七《前廢帝紀》載:“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主以吏部郎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備見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褚淵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乃山陰公主姑父,則山陰公主之悖亂于此可見。那么,對于何戢而言,作為男子、作為丈夫,在官場與家庭,有何尊嚴可言?其境地之窘迫、內心之憂憤,可以推知。而即使以瑯邪王氏、陳郡謝氏之門高族盛,王藻猶不免因讒而“遂為冤魂”,謝莊因為殷貴妃作《誄》稱“贊軌堯門”——以貴妃比于鉤弋夫人,廢帝遂欲殺之,等等。廢帝諸如此類的悖逆無道之舉,必然招致尚公主士族的不滿,并因此導致尚公主士族對劉宋王室產生疏離。
三、《妒婦記》《為江敩讓尚公主表》撰述意圖、目的
須強調的是,明帝敕虞通之撰《為江敩讓尚公主表》,托江敩之名,實為諸尚公主士族發聲。《為江敩讓尚公主表》明確稱:
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己,規全身愿;實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⑦沈約:《宋書》卷四十一《后妃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92頁。
所謂“諸門憂患之切”,正是指諸尚公主之門因“尚主”而帶來的“憂”與“患”。據此,我們就不難推見明帝之用心了:借江敩尚孝武帝女臨汝公主之機,敕虞通之撰《為江敩讓尚公主表》,盡吐尚主生涯之“憂”與“患”,一方面警誡諸公主,另一方面則是做給諸尚公主士族看,意在安撫這些“世胄”,取得這些高門世族的支持,以便于維系劉宋政權。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見出明帝敕虞通之撰《妒婦記》《為江敩讓尚公主表》的意圖和目的:至泰始五年,明帝已剪落諸侄,并已決意剪落諸兄弟,為幼子繼位掃清障礙;那么,明帝在當時面臨的迫切問題是,他必須獲得士族——尤其是諸尚公主士族的支持,因為這些“世胄”,是維系劉宋政權的中堅力量。而現實問題是,尚公主士族婚姻生活并不如意,甚至可以說是畸形的。在明帝看來,這顯然不利于維系統治;尤其在前廢帝悖逆無道,導致尚公主士族對劉宋王室產生疏離的情況下。現在看來,尚公主婚姻生活之所以是畸形的,根本原因乃在皇權專制與政治聯姻;然而明帝看不到這一問題的本質,卻認為原因在于公主性妒,因而敕虞通之撰《妒婦記》,又授意江敩讓婚,并使虞通之為作讓婚表;明帝如此大張旗鼓的一系列舉措,顯然有其政治用心——那就是警誡諸主,安撫諸尚公主士族,以便獲得諸尚公主士族的支持,從而為其幼子繼位作準備。
那么,《妒婦記》《為江敩讓尚公主表》在當時的作用如何呢?《后妃傳》載“太宗以此表遍示諸主”,于是臨川長公主上表請求“乞還身王族,守養弱嗣”,明帝許之。這說明,明帝之意,諸公主是心領神會的,尤其在山陰公主被賜死的情況下;而湖熟令袁慆之妻因妒忌被賜死,實為明帝震懾諸公主的一個犧牲品而已。據此而言,明帝警誡諸公主的目的表面上達到了。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明帝采取的這一系列舉措,最終未能改變劉宋王朝傾覆的命運。其中原因,據史家所述,主要有三點:其一,明帝剪落皇枝,導致宗室寡弱,劉氏政權終為蕭氏取代。《宋書》卷七十二《文九王傳》載,明帝卒后,“時主幼時艱,宗室寡弱”。《宋書》卷七十九《文五王傳》稱:“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素族當權,近習秉政。”所謂“素族”,乃指不屬于皇族的宗族。明帝崩于泰豫元年(472)四月,顧命大臣有袁粲、褚淵、劉勔、蔡興宗、沈攸之,五人之中竟無宗室成員,尚公主之門有二:褚淵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蔡興宗子約尚孝武女安吉公主。蔡興宗于泰豫元年八月卒①司馬光:《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三十三《宋紀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5頁。,劉勔于元徽二年(474)討桂陽王休范叛亂戰敗死。蕭道成使人弒后廢帝劉昱,沈攸之于昇明元年(477)起兵反蕭道成,兵敗自縊;袁粲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依然據石頭反蕭道成,事敗被殺。明帝幼子,終為蕭道成所殺,史臣對此慨嘆:“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根!”②沈約:《宋書》卷九十《明四王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239頁。其二,明帝不修德,奢靡,親小人,失民心。明帝不修德,史家載述較多,如《后妃傳》載:“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適,實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此一細事,見出明帝行止之一斑。明帝奢靡,《宋書》卷九十二《良吏傳》載:“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余菽粟,土木衣綈繡……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祚,彌篤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橫流。”明帝親近小人,終失民心。《宋書》卷九十四《恩幸傳》載孝建、泰始時期,“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明帝幸臣有阮佃夫、壽寂之、姜產之、李道兒、楊運長等,對于這些幸臣的危害,史書如是載:“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懾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剿。民忘宋德,雖非一途,寶祚夙傾,實由于此。”③沈約:《宋書》卷九十四《恩幸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302頁。其三,明帝剪落皇枝,又誅殺有功將帥,賜王景文死。據《建康實錄》載:“時太子及諸皇子并小,上稍為身后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并殺之。”④許嵩:《建康實錄》,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42頁。尤其是臨終前賜王景文死:“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為純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乃遣使送藥賜景文死。”⑤沈約:《宋書》卷八十五《王景文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84頁。對于王景文之死,史臣慨嘆:“若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群公方驂并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⑥沈約:《宋書》卷八十五《王景文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85頁。明帝剪落皇枝,欲倚重諸尚公主士族,最終又因疑忌過重而自毀長城,終致“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⑦沈約:《宋書》卷八《明帝紀》,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1頁。。
要言之,作為帝王,明帝敕虞通之撰《妒婦記》《為江敩讓尚公主表》,實乃為維系劉宋政權而采取的重要政治舉措,這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是罕見的。
四、《妒婦記》佚文及其小說史地位
《隋書·經籍志》載《妒記》二卷,《新唐書·藝文志》亦載《妒記》二卷;而宋以后書目不載,學界一般認為,當亡于宋。魯迅《古小說鉤沉》輯錄七則佚文,以下即對其佚文作分析。
就現存佚文看,七則故事旨意明確,即勸誡妒婦止妒。需強調的是,《妒婦記》所載,乃是當時或者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事實,而非虞通之個人杜撰、虛構,這也是《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將其置于史部的根本原因。但是,虞通之對于相關歷史人物、事件的處理,還是別有用意的。試舉一例,以作說明。《為江敩讓尚公主表》稱:“自晉世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才名,至入王敦攝氣,桓溫斂威,真長佯狂以求免,子敬灸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露于北階,何瑀缺龍工之姿,而投軀于深井,謝莊殆自同于蒙叟,殷沖幾不免于強鋤……”①沈約:《宋書》卷四十一《后妃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90-1291頁。虞通之于表中羅列晉、宋尚主之名流:王敦、桓溫、劉惔、王獻之、王偃、何瑀、謝莊、殷沖共八人。那么,這八人是否也寫入《妒婦記》中?筆者認為可能性是較大的。而現存《妒婦記》佚文之一,就涉及桓溫與南康長公主事;此事《世說新語》亦載之,而旨趣顯然不同。先看劉義慶之載述,《世說新語·賢媛》曰: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后。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發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還。
《太平御覽》卷一五四引《世說》作“李勢女”。劉孝標作注引《妒記》曰:
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把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發,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于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②《世說新語·賢媛》“桓宣武平蜀”條注引。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92-693頁。
《藝文類聚》卷第十八“美婦人”引《妒記》,與上文不盡相同,“斂手向主”后有“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③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八“美婦人”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頁。。據《晉書》卷九十八《桓溫傳》載:桓溫“選尚南康長公主”,穆帝永和二年(346),桓溫率眾西征成漢;三年(347),漢主李勢降,勢及宗室十余人送建康。在此背景下,李勢女成為桓溫妾。從《世說新語》記載看,南康公主本欲率婢“拔白刃襲”李勢女,然在李勢女不卑不亢的沉痛言辭后竟敗下陣,結果是“主慚而還”。這一結局,意味著桓溫妻妾之間的矛盾并未得到解決。劉義慶卒于元嘉二十一年(444),以理推之,作為明帝近臣,虞通之當見過《世說新語》。然虞通之對于南康公主的敘寫,卻不同于《世說新語》,《妒婦記》以公主“善之”——即桓溫妻妾和睦相處作為結局。兩相比較,不難見出,《妒婦記》所敘妻妾和睦相處這一結局,才契合明帝旨意,這也是為現實中所謂“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開出的良方。④林正三《虞通之〈妒記〉研究》稱:“我推測南康公主之事有兩種傳說,《世說》與《妒記》各取一說……《妒記》的結局如此理想化,也可能是虞通之改寫、潤飾的結果。”參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第十四集,臺北學生書局1997年版,第316頁。
當然,現存《妒記》佚文集中表現出來的,還是婦女妒忌所帶來的危害。事實上,魏晉以來,婦女不尊禮法現象屢見不鮮,干寶《晉紀總論》探究西晉滅亡的原因,其中就涉及當時社會風氣大壞的問題,而婦女不尊禮法恰是他批評的一個重要方面:“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哉!”①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四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88頁。干寶有感于世俗風氣大壞,遂將婦女背棄儒家禮法,視為西晉滅亡之一原因,雖未必恰當,卻也見出當日世風之一端。而現存《妒婦記》佚文,則生動、形象地展示了當日妒婦們的諸多面相。概而言之,婦女妒忌導致三方面危害:其一,給丈夫身心造成傷害。貴門子弟“咸以尚主為憂”的一個原因,就是不堪受虐待,《為江敩讓尚公主表》稱:“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露于北階”,史家載述稍異,“(王)藻父偃,初亦尚世祖少女永嘉公主。公主常裸偃縛之庭樹,時天寒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排闔詬主,得免”。②許嵩:《建康實錄》,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89頁。無論是“裸露于北階”,還是裸“縛之庭樹”,對于那些貴門子弟而言,都是可怕的夢魘。而《妒婦記》亦載述此類故事:“諸葛元直妻劉氏”條敘劉氏“大妒忌”,“恒與元直杖”,“與杖之法,大罪十,小罪五”;“京邑有士人婦”條敘京邑士人婦“大妒忌”,“于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乃至“常以長繩系夫腳,且喚,便牽繩”;劉氏、京邑士人婦如此對待丈夫,則諸葛元直、京邑士人日常生活之戰戰兢兢可以想見;而“武歷陽女嫁阮宣子”條敘阮宣子妻“無道妒忌”,“禁婢:甌覆盤蓋,不得相合”(大約擔心甌覆盤蓋之舉,引發丈夫交合之性聯想),家有一株桃樹“花葉灼耀”,宣子“嘆美之”,妻“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花”;較之劉氏、京邑士人妻之所為,武歷陽女對阮宣子之折磨、摧殘,非在肉體,乃在心理、精神層面。其二,婦女妒忌危害家庭。《為江敩讓尚公主表》稱“專妒之行,有妨繁衍”,而《妒婦記》載有具體案例:“有人姓荀,婦庾氏”條,敘荀妻“大妒忌”,“荀嘗宿行,遂殺二兒”,其行為令人發指!“凡無須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荀手,無不痛打;客若共床坐,亦賓主俱敗”,則荀氏之家,可謂家無寧日。《禮記》宣揚,婚姻乃在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而庾氏之所為,無異敗家毀族!其三,婦女妒忌引發家庭之外的其他矛盾。婦女妒忌,其危害有時不限于個人家庭,往往波及他人、社會,從而產生不良社會影響。王導是東晉開國名臣,號為“仲父”,《世說新語·輕詆》載:“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游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輕詆,有輕微詆毀之意;那么,王導為何對蔡謨有詆毀之意?《妒記》如是載述: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眾妾羅列,兒女成行。后元會日,夫人于青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不能自忍,乃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余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爾。”王大愧。后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憤蔡前戲言耳。③據《古小說鉤沉》本。參見魯迅:《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445頁。
據《晉書》卷七十七《蔡謨傳》載,蔡謨博學,在當時“于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④房玄齡等:《晉書》卷七十七《蔡謨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041頁。,因而他說“朝廷欲加公九錫”,王導便信以為真;豈料蔡謨是嘲譏之語,這對權傾一時的王導來說,不啻是莫大的羞辱,因而記恨在心,公開貶抑蔡謨。顯然,王氏與蔡氏之間產生嫌隙⑤《晉書》卷七十七《蔡謨傳》載:“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床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第2041頁)這一記載,既反映出王導與蔡謨個人私生活方式不同,也見出蔡謨對王氏心存芥蒂之意。,乃由曹夫人“性甚忌”并導致家庭矛盾一事而引發;這樣,王導與曹夫人之間的家庭內部沖突,就波及朝中官員,而朝廷官員之間心存詆毀之意,于己、于人、于朝廷,均無益處。由此言之,婦女妒忌,不但摧殘丈夫身心,危害家庭,還可引發其他社會矛盾;那么,嚴禁婦女有妒忌之行,也就顯得格外迫切而必要了。
不過,有意味的是,虞通之在宣揚嚴禁婦女妒忌時,不經意中暴露出男權中心論這一社會問題。“謝太傅劉夫人”條載: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寵。公既深好聲樂,不能令節,后遂頗欲立姬妾。兄子及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為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語也。”①據《古小說鉤沉》本。參見魯迅:《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45頁。
劉夫人,乃名士劉惔之妹。謝安看來是懼內的,既“深好聲樂”“頗欲立姬妾”,而又有所忌憚;謝氏子弟自然理解謝安的“苦衷”,遂試探劉夫人;既為詩書之家,謝氏子弟便抬出《關雎》《螽斯》:依據《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②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一,《十三經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頁。,“《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③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一,《十三經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頁。;劉夫人當然明曉個中之意,遂問撰者為誰,謝氏子弟乃抬出周公,豈料劉夫人對曰“若周姥撰詩,當無此語也”。劉夫人此一對答,實道出男權主宰社會與家庭的歷史真相,這也反映出劉夫人之識見,確與眾不同。對于這一載述,余嘉錫先生稱:
自古未聞有以《關雎》《螽斯》為周公撰者。謝氏子弟不應發此無稽之言。且夫人為真長之妹,孫綽就謝公宿,言至雜,夫人謂“亡兄門未有此客”(見《輕詆篇》)。何至出辭鄙倍如此?疑是時人造作此言,以為戲笑耳。然亦可見其以妒得名,乃有此等傳說矣。④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95頁。
余先生因《關雎》《螽斯》的撰者問題進而質疑此一載述的真實性,似乎有些膠柱鼓瑟了。因為謝氏子弟意欲抬出周公以壓服劉夫人,所以不免杜撰,而劉夫人則搬出周姥以對。如此,則謝安大概也就無計可施了。應該說,這一載述,是可信從的;謝氏門高族盛,且當時與虞通之同朝為官之謝家人不少,因而虞通之不當以不實之辭唐突謝氏。
宋明帝敕虞通之撰《妒婦記》《為江敩讓尚公主表》,在當時影響頗大,故沈約載入《宋書》。而《妒婦記》所載妒婦系列自此進入中國文學殿堂,歐陽詢《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五特立“妒部”,《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王方慶《續妒記》五卷,《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七十二“婦人三”列“妒婦”一類,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三著錄《補妒記》一卷,《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著錄王績編《補妒記》八卷,明代楊若曾有《妒記》十卷,等等。⑤袁行霈、侯忠義編:《中國文言小說書目》,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頁。因而,盡管《妒婦記》僅存七則佚文,研究者們還是給予充分肯定,向楷《世情小說史》即稱《妒婦記》“大約是我國古代第一部以夫婦關系為題材的小說集,很值得重視”⑥向楷:《世情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正見其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之地位。